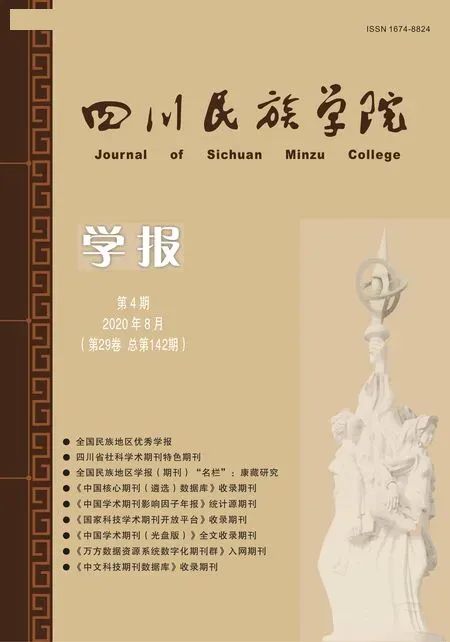论传教士的康巴学
——康巴学的谱系之一
喻 中
(中国政法大学,北京 100088)
在传世文献中,关于康巴地区的记载,虽然不如关于中原地区的记载那样丰富,但毕竟还是有迹可循。譬如,在《史记》这样的典籍中,就可以找到有关康巴地区的早期信息。根据《史记·西南夷列传》:“自巂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徙、筰都最大;自筰以东北,君长以什数,冉、駹最大。其俗或士箸(1)“士箸”,从文意看应为“土箸”。定居某地,长期不移动。“箸”,通“著”。详见,杨钟贤,郝志达.全校全注全译全评史记第五卷[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7:300.,或移徙,在蜀之西。自冉駹以东北,君长以什数,白马最大,皆氐类也。此皆巴蜀西南外蛮夷也。”到了秦代,“常頞略通五尺道,诸此国颇置吏焉。十余岁,秦灭。及汉兴,皆弃此国而开蜀故徼。巴蜀民或窃出商贾,取其筰马、僰僮、髦牛,以此巴蜀殷富。”[1]670《史记》中描述的这一片处于“蜀之西”的广大区域,与今天的康巴地区多有重合。而且,对于汉初巴蜀的“殷富”,在“蜀之西”的康巴地区还提供了物资上的重要支撑。
在《史记》共计六十九篇“列传”中,紧接着《西南夷列传》的,就是《司马相如列传》。如此安排,看似巧合,更大的可能则是司马迁刻意为之。按照《司马相如列传》所载,蜀郡人司马相如的岳父卓王孙乃临邛之巨富,拥有“家僮八百人”[1]672,堪称《西南夷列传》中所说的“巴蜀殷富”者群体的代表人物。《司马相如列传》还记载,汉武帝曾就“西南夷”地区的治理问题,专门征求过司马相如的意见,司马相如的回答是:“邛、筰、冉、駹者近蜀,道亦易通,秦时尝通为郡县,至汉兴而罢。今诚复通,为置郡县,愈于南夷。”对于这样的政见,“天子以为然,乃拜相如为中郎将,建节往使。”[1]678据此,司马相如曾受汉武帝的派遣,作为汉王朝的代表前往康巴地区。这段史实表明,经略康巴,譬如,在康巴地区设置郡县,乃汉武帝与司马相如两人的共识。《史记》中的这两篇“列传”表明,康巴地区很早就见于中国的传世文献。自《史记》以降的各种官方正史中,对康巴地区的记载亦不少,这里不再逐一征引。
如果要写一部“康巴史”,我们可以追溯到汉初,甚至还可以追溯到先秦。但是,如果要写一部“康巴学史”,恐怕只能追溯到近代。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康巴学作为藏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毕竟是相对晚近的产物,总体上说,是西方近现代学术体系示范之下的产物。在当下,如果我们以现代学术的眼光看待康巴学,着眼于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康巴学,并由此去探寻康巴学研究的开创者,则可以追溯至19世纪中后期开始出现在康巴地区的外国传教士。从康巴学的演进历程来看,如果要写一部“康巴学史”,那么,最初的康巴学实为传教士的康巴学。康巴是中国的,康巴学作为一门学问,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在19世纪中期至20世纪中期,在近百年的时间段里,在特定的国际关系与世界格局中,外国来华的传教士作为一个特殊群体,开启了近现代意义上的康巴学。因此,要全面把握康巴学的萌芽与兴起,要全面描绘康巴学蜿蜒而来的身影,应当从外国传教士开始说起。
一、走进康巴的外国传教士
较早进入康巴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是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古伯察(Régis-Evarist Huc,1813-1860)和秦噶哔(Joseph Gabet,1808-1853)(2)有学者认为:“第一个进入康藏的巴黎外方会传教士罗启桢(Charles R. A. Renou)1863年病逝于江卡,是在康藏去世的第一个传教士。”详见,赵艾东:《19 世纪下半叶康藏天主教士的天花接种与藏文编纂》,《四川民族学院学报》2016年第1期。这种观点也是可以成立的。因为,罗启桢(也称罗勒拿)是自主决定进入康巴地区的;而古伯察进入康巴地区,是被动的、被迫的、身不由己的,是在押解出境的过程中途经康巴地区的。此外,关于罗启桢(罗勒拿)其人的专题研究,可以参见,郭净:《十九世纪中叶法国传教士罗勒拿滇藏传教史略》,《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16年第1期。。 在古伯察撰写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中,详细记述了他在中国的经历,其中就包括他在康巴地区的短期经历。见于此书与康巴地区的有关记载,可以视为外来传教士考察康巴地区的早期文献。
根据《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译者的梳理,古伯察最初抵达中国的时间是1839年8月。其间,由法国天主教修会之一的遣使会主教孟振生(Joseph Martial Mouly,1807-1868)委派,古伯察与秦噶哔一起,“于1841年2月20日离开澳门,并于同年6月17日到达当时法国在华传教区的所在地——北直隶的西湾子(今河北省崇礼县境内),由此出发,经过热河、蒙古诸旗、鄂尔多斯、宁夏、甘肃、青海、西康地区,”“最终于1846年1月29日到达西藏首府拉萨。”[2]1按此说法,古伯察与秦噶哔在前往拉萨的路途中,已经到过“西康地区”。
古伯察与秦噶哔在拉萨停留了两个月之后,遭到了琦善的驱逐,被迫离开拉萨,且被迫按照琦善规定的路线返回内地。《鞑靼西藏旅行记》第十章的内容,就是叙述他们在康巴地区的经历。这段“康巴见闻录”以察木多(今天的昌都)作为起点:“中国政府在察木多设立了供应给养的兵站,其管理工作交给了一名粮台。兵站共由300名左右的士兵、四名军官组成,包括一名游击、一名千总和一名把总,维持这一兵站和属于该兵站的军队的花销,每年都要高达一笔万两白银的钱。察木多是康省的首府,建于被高山环抱的一个山谷中。从前,该城由一道土城墙环绕,城墙现在到处都已坍塌,每天都有人于那里取土以修房子的平屋顶。”(3)关于这段话中的“游击”一词,原书有一个脚注:“游击是一种军官的名称。”[2]553进一步察看,“虽然察木多是一个没有多少豪华和高雅生活的地区,但大家可以在那里欣赏一座庞大而又豪华的喇嘛庙,位于西部一个俯瞰全城的高台上。该寺庙共有2000名喇嘛,他们不像在其他佛寺所通行的那样,即每个人都有他们的小僧房,而是共同居住在宽敞的和环绕大雄宝殿的大房间中,点缀这一寺庙的豪华装饰使它被视为西藏最漂亮和最富有的喇嘛寺之一。察木多喇嘛寺的住持是一名呼图克图喇嘛,他同时也是整个康地的一名世俗官吏。”[2]554-555
按照这样的叙述风格,古伯察记录了他们在察木多、察雅、巴塘、理塘等地的经历及所见所闻。在经历了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们最终平安无恙地到达到了汉地边境,我们于那里告别了异常寒冷的西藏气候。在翻越到达打箭炉城之前的那座山时,我们几乎被埋在雪下,那里的雪每次下得既厚而次数又频。大雪一直伴送我们到达建筑这座汉地城市的山谷,一场瓢泼大雨又在那里迎接我们。时值1846年6月初。我们离开拉萨已近三个月的时间了。据那部汉文图识记载,我们共走了3050里。‘打箭炉’意为‘打造箭矢的熔炉’。该城享有此名是由于武侯(诸葛亮)军师于公元234年率军平定南番时,曾派遣他的一位将军去建造打箭炉。该地区曾先后属藏族人和汉族人,它在100年以来一直被视为中国中原王朝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们在打箭炉休息了三天。在此期间,我们每天要与当地的主要官吏争执数次,因为他不想让我们坐轿继续赶路。但必须如此行事,因为我们不能再忍受继续骑马旅行的想法了。我们的双腿已骑过各种岁口、各种身材、各种颜色和各种特征的许多马匹,再也不能忍受了。双腿急需在轿子中平静地伸开。由于我们一直坚持自己的要求,他们终于同意这样做了……次日黎明,我们便钻进自己的轿子,以官库开支的经费被一直抬到四川省府。我们在那里又根据皇帝的旨意而在天朝要员面前正式受审。”(4)这段话中的“各种岁口”,是指马匹的各种“年龄”。通常,从牲口牙齿的多少可以看出牲口的年龄。[2]583-584古伯察到达了四川省府成都,整部《鞑靼西藏旅行记》也至此结束。
古伯察作为一个法国传教士,在他的《鞑靼西藏旅行记》一书中,写下了他在康巴地区的若干见闻,其中的“康巴旅行记”是否属于严格意义上的“学术研究”,还可以再讨论,但毕竟已经形诸文字,体现了一个外来传教士对康巴地区的认知与理解。而且,通过古伯察在康巴地区与当地人的交往,既有助于我们理解外国传教士的一些精神与风格,也有助于我们理解那个时代的康巴人,尤其是他们对待外来者的立场与态度。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关于康巴地区的记载,可以视为传教士康巴学最初的萌芽,因此有必要给予一定的关注。
在古伯察之后,法国传教士——主要是巴黎外方传教会的传教士,对康巴地区的热情有增无减,在19世纪40至60年代,甚至可以说是“法国传教士‘独占’康区的年代”[3]。根据杨健吾的研究,1848年,就在古伯察途经康巴地区两年以后,“道光三十年(1850年)(5)“道光三十年(1850年)”原文误写为“道光三十年(1852年)”,笔者直接校改。,巴黎外方传教士丁盛荣受罗马教廷之命赴西藏传教,路途受阻,折返打箭炉(今康定),于炉城北郊设堂传教,康定遂成为康区天主教传播的大本营。咸丰二年(1852年),华郎廷、圣保罗在巴安(今巴塘)城区建教堂,天主教传入康南地区。随后的10多年里,法、意、加、奥、德等籍传教士数十人先后在康区修建教堂15座。”[4]109
1864年,“传教士吴依容(Houillon)被派驻打箭炉,巴布埃(Bourry)被派往巴安(今巴塘)。后古特尔(Goutelle)在打箭炉建立了教会,原云南助理主教丁盛云(Joseth)被任命为西藏代牧主教。他取道川南,经叙府、嘉定、雅州于1865年12月21日到达康定。此时,进藏的全体传教士都在当年被赶出西藏,巴黎外方传教会感到进入西藏困难很大,遂决定在康定安置主教,购买土地,修建教堂。主教府乃由化林坪迁至康定。1877年丁盛荣死后,毕天荣(Biet)继任主教。此后,倪德隆(Giraudau)、李雅德(Leard)、任乃棣(Genesier)等相继前来,或被留在康定,或被派往巴安、盐井、泸定和云南维西等地,修建教堂,开展教务。特别在巴安购置土地、修建房屋及教堂3座,作为进入西藏的前哨阵地。”[4]110
由这个过程来看,在古伯察之后,在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里,法国天主教传教士一直都在康巴地区努力拓展他们的传教事业。在传教的过程中,一些传教士开始从事具有学术意义的康巴学研究。其中,1855年入华的法国传教士戴高丹(Desgodins Auguste,1826-1913)做出的贡献较为明显,他的《从康藏巴塘到川南打箭炉的游记》等作品,在法国传教士所写的有关康巴的著述中,享有一定的地位。不过,对于传教士的康巴学来说,一个比较重要的转折点是在20世纪初期发生的。“1901年,倪德隆继任代牧主教,在康定、泸定等地大量购置土地、修建教堂,创办拉丁学校和修道院,极力开展教务;还深入研究康藏历史、文化,开办学校,编撰《藏文文法》《藏文读法》《拉丁法文藏文字典》等工具书。”[4]110根据这样的史实,可以认为,主要是在倪德隆的主导下[5],法国传教士对“康藏历史、文化”进行了“深入研究”,具有学术意义的康巴学,由此迈上了一个实质性的台阶,或可视为传教士康巴学正式形成的标志。在此基础上,又出现了法国传教士古纯仁(Francis Goré,1883-1954)及其《川滇之藏边》(Notes Sur les Marches Tibétaines du Sseu-T'chouan et du Yun-nan)这样的代表性著作(详后)。
从古伯察、戴高丹到倪德隆、古纯仁,法国传教士在康巴地区的传教事业,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与之相伴随,法国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也以康定为中心逐渐形成。回顾这个历程,可以发现,如果说古伯察的《鞑靼西藏旅行记》、戴高丹的游记代表了法国传教士康巴学的萌芽,那么,倪德隆时期编写的《藏文文法》《藏文读法》《拉丁法文藏文字典》等文献,特别是古纯仁的《川滇之藏边》等论著,则代表了法国传教士康巴学的典型形态。如果说,现代意义上最早的康巴学是传教士的康巴学,那么,在各国传教士中,法国传教士的康巴学,较之于其他各国传教士的康巴学,在时间上相对领先了一步。
在法国传教士进入康巴地区的过程中,英国传教士也来到康巴地区。“1876年,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康慕伦(James Cameron)从湖北出发,抵达四川,沿途考察了打箭炉、理塘、巴塘和金沙江西岸的西藏边境。以康慕伦的考察工作为基础,1897年内地会成员西瑟端纳(Cecilpolhll-Turner)等5位传教士在打箭炉建立了康藏地区第一个传教基地。”[6]192在此基础上,1905年4月,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James Huston Edgar,1872-1936)来到康巴地区,他在康定“建立了福音堂。每逢星期一用藏、汉语传教,同时向听众散发宗教图片和藏、汉文的《马可福音》。其后, 英国人顾福安、加拿大人纳尔逊、英国人裴元弟、美国人郭纳福先后到达康定传教。”[4]112
英国内地会传教士叶长青、顾福安等人到达康定的时间,虽然略晚于法国天主教传教士倪德隆,更晚于古伯察,但是,在传教士康巴学这样一个领域,叶长青、顾福安等人取得的成就却不容忽视。叶长青、顾福安等人长期生活在康巴地区,他们既传播基督教,同时也从事康巴研究,堪称“英国传教士康巴学”的代表性人物。下面,依据进入康巴地区的先后时间,分别略述法国传教士的康巴学与英国传教士的康巴学。
二、法国传教士的康巴学
上文已经提到,在古伯察之后,法国传教士针对康巴地区的历史与现实写下了比较丰富的作品,对此,学界已有比较细致的梳理[7]。在这些各具特色的论著中,古纯仁的《川滇之藏边》一书,颇具代表性,可以作为法国传教士在康巴学研究领域取得的标志性成果与代表性文献。
1907年,古纯仁受巴黎外方传教会的派遣,与华朗廷、佘廉霭、窦元楷、伍胡纳等数名传教士一起,来到康定。古纯仁“先在四川泸定沙坝堂区学习语言;1914-1920年,任川西打箭炉本堂神父;1920-1930年,任西藏盐井本堂神父,在此学习藏语,并对西藏历史文化进行深入研究。1931-1951年,任云南茨中本堂神父,他对语言学研究较有天赋,编写了一部藏语语法书,参与了倪德隆主教编著的藏法词典。……被教会赞誉为近代西藏研究的‘双子星’。”[7]129
虽然有教会机构把古纯仁称为“西藏研究专家”,其实,更加精准的说法是,古纯仁实为“康巴研究专家”。从1907年到达康巴地区之始,古纯仁的足迹遍及康巴各地。在康巴地区生活了15年之后,古纯仁于1923年出版了他研究康巴的著作《川滇之藏边》。此书的主要内容,由李哲生(又名李思纯)译成中文,在康藏研究社组织出版的《康藏研究月刊》上,以专题文章的形式连续刊发。从1947年12月至1949年8月,一共连载了十多次。从见于《康藏研究月刊》上的文章的题目《川边之打箭炉地区》《川边霍尔地区与瞻对》《里塘与巴塘》《维西》《旅行怒江盆地》《旅行金沙江盆地》《察哇龙之巡见》《康藏民族杂写》等,大致可以了解《川滇之藏边》一书的主要内容。
古纯仁刊于《康藏研究月刊》上的第一篇文章,题为《川滇之藏边·第一篇 川边(四川之藏边)》,此文具有导论或概论的性质。此文以“概说”开篇,首先解释文章的题旨:“自格林威克(Greenwich)以东,东经九十九度至一○三度,凡北纬二十九度至三十三度间之广大地域,中国人称之曰‘川边’。而欧罗巴人较早之名称,则曰‘藏边’。为求称谓之较为精确,吾人称之曰‘四川之藏边’,所以别于云南及甘肃之藏边也。”(6)此处的出版时间,在本期杂志上,误印为“中华民国卅七年十二月卅一日”,亦即1948年12月31日,现笔者直接校改为“1947年12月31日”,下同。[8]5接下来,文章主要概述了“川边”的简史:从1720年清军平定西藏,一直讲到1918年的现状,时间跨度近两百年。在历史回顾之后,文章分述“川边”的“现刻界域”“地形概要”“河流”“道路”“居民”“农业”“语言”“矿产”“商业”以及“政治与经济状况”诸方面的情况,但都比较简略。譬如,在“地形概要”这个小标题下,古纯仁写道:“此地域全为山国,而为奔流其间之四大河流所割断。凡河流与山脉皆自北而南,呈平行之状。河流咸迅急。山则有时高达海拔六千米。通常地形变化,其高度在海拔四千米与五千米之间,在四千米之地,常可得牧场与高原,在三千五至四千米之间,则有森林。在二千与三千五百米之间,则有可耕作之河谷高地。当北纬三十度下之雅砻江及金沙江与澜沧江河谷,约为一千五百米,是即此边地中之较低下者,如吾人考察大渡河之谷,则为一千六百米。”[8]7这就是古纯仁关于川边地形的总体描述。
在概论性质的“第一篇”之后,再看《川边之打箭炉地区》一文,此文开篇也是“历史概略”,文章称:“毛牛国,亦称木雅(Mounia),或曰鱼通(Goutong),即现今打箭炉地区。二百年前成为中华帝国之一部。汉武帝曾征服西南夷,于岷江岸边置犍为郡,西南夷与中国关系臻于密切,所谓西夷,即邛国与筰国。即毛牛国是也。使者司马相如曾至此地宣示朝廷威德,后于此区设二武官镇辖,官名都尉。武帝建元六年(纪元前一三五年)于筰国地置沉黎郡,毛牛国为其附属。其后土人叛变,于纪元前一○○年(译者按即汉武帝天汉元年,距建元六年,凡三十四年),毛牛国脱离沉黎郡,汉乃废郡为毛牛县。”(7)需要说明的是,在今天通行的《史记》中,这段话中的“沉黎郡”写为“沈犁郡”。详见,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2006:671.[8]2以这样的历史追溯开始,文章对打箭炉地区的历史进行了比较细致的叙述,一直讲到1922年明正土司的判乱、系狱与投河自尽。在“历史概略”之后,文章再叙述打箭炉地区的“地理概略”,虽名为“概略”,但文章对打箭炉地区的地理状况,还是做了比较翔实的分析。在文章的最后,相对简略地叙述了打箭炉地区的“县治与人口”“商业贸易”及“矿产”。古纯仁关于打箭炉(亦即康定)地区的论述,大致如此。
再看《里塘与巴塘》一文。在《康藏研究月刊》中,这篇文章分两期刊出,分别叙述“里塘地区”与“巴塘地区”。
关于里塘(8)这里的“里塘”,亦即现在“理塘”,但见于《康藏研究月刊》中的这篇汉译文章,从标题到正文,都写作“里塘”,这里仍存其旧,不再更改。, 文章开篇即称:“里塘地区之界,北接尼雅龙,一曰瞻对,东以雅砻江与甲拉土酋领土为界,南接四川木里土酋地,与云南之中甸桂西接巴塘之界。征之往史,里塘自来臣服于西藏,并属蒙古人,及丽江之摩些人。摩些人之占领里塘,似在十六世纪至十七世纪之初年,由于吴三桂将军之经略云南(译者按吴三桂曾征服云南之木氏)。拉萨之西藏政府,乃得重使里塘,服属于藏。以此为基础,文章继续叙述里塘地区的历史,一直讲到古纯仁生活的时代:“一千九百二十一年之春,乡城盗寇侵略雅砻江东之木雅地方,大肆蹂躏,川边镇守府欲派兵击之,适刘禹九将军,方回师重据雅州,于是进讨之计划,亦未能确定。乡城群盗方肆侵略,及于中咱之地,更扰及河口,至巴塘之大道。”[9]30在“里塘历史”之后,文章简述了里塘地区的两条主要道路:一是从打箭炉至巴塘的道路;二是由喇嘛寺至乡城的道路。
《里塘与巴塘》一文的续篇见于《康藏研究月刊》第二十期,主要讲巴塘:“巴塘地区,在川边之西南。其疆域,北与德格为界。东与里塘为界,南与中甸及维西之县境为界。西与三岩(即武成县)江卡(即宁静县)为界。由北至南,长六百里。由东至西,长三百里。”关于巴塘之县治,“中国史册,于此地未能详征,或以为即古白狼国。其地有若干颓祀之建筑遗迹。为兵事及地震所损毁者。其一方面,该地土人,尚保持许多之传说,据传其地最初主人”,“自尼雅曲河而来,偕其牲畜帐幕,居于此谷中,颇乐其气候之温煦,逐安宅于其地。经若干年后,夜间每以羊鸣之声所扰,乃沿河而上溯,此河即在平原之西,更向北进,羊鸣之声,亦更明瞭,最后在一山旁,寻得一穴,实为羊巢,中有一牝绵羊,或又云为一牝山羊,于是称此山为庐玛拉,义曰‘牝羊之山’,巴塘之最初主人,即奠成于是,自称曰巴,义曰:‘羊鸣’也。”[9]20-21这些都是关于巴塘地区的概况。随后,文章历述巴塘的历史、主要道路及商业贸易。
通过以《川滇之藏边》一书的若干代表性章节,大致可以看到,古纯仁对康巴各地的历史与地理,有比较深入的论述。他关于康巴地区的论述,既立足于实地考察,同时也高度重视历史过程的梳理,体现在对一个特定地区(譬如打箭炉、巴塘,以及其他地区)的历史进行了贯通性的叙述。他甚至对《史记》中的相关记载,也有较好的对接与回应。
自《川滇之藏边》一书1923年初次问世以来,已近百年。时至今日,中国学界对此书仍有积极的评价。如有学者认为,“该书价值表现为:其内容涵盖了康区各大地区,如打箭炉地区、理塘、巴塘、霍尔、瞻对、金沙江,盆地、维西、察哇龙,涉及范围之广度和深度为同时期其他西人论著所无法比肩;其内容的丰富性和综合性也远远超过同时期其他论著,书中所记康区各大地区的历史、政经、地理、交通道路、民族、风俗等内容是珍贵的康藏民族志史料。”[10]20-21这样的评价,表达了当代中国学者对于古纯仁之康巴研究的肯定。此外,还有论者注意到此书的风格,“古纯仁笔下的藏区总是活灵活现的。他的视点立足于藏族的日常生活, 从而他关于藏族文化的概述便由一幅幅细碎的生活画面拼接而成,其间没有历史的考证,也没有理论性著述,读过之后藏族人民的生活形貌栩栩如在眼前。”[11]20-21古纯仁在论著中表现出来的这种风格,或许可以体现法国文化中的某种传统。
三、英国传教士的康巴学
如前所述,相对于法国传教士,英国传教士进入康巴地区的时间稍微晚一些,但是,活跃于康巴地区的英国传教士的人数也不少。在英国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中,很多人都做出了重要的贡献。相对说来,叶长青的影响更为显著。叶长青既是一个传教士,又是一个康巴研究者,他不仅积极从事康巴学的研究,而且还是一个重要的学术组织者。此外,他还担任了上海《字林西报》驻康定的记者。由于在多个方面都做出了贡献,他在“英国传教士的康巴学”这个特定领域,颇具代表性。因而,可以通过叶长青等人的康巴学研究,来透视英国传教士康巴学之旨趣。
概括地说,从1902年至1935年,在长达三十多年的时间里,叶长青反复前往理塘、巴塘、乡城等地考察。“1922年夏,他带领一队传教士从四川灌县(今都江堰市)前往打箭炉考察,在此过程中,他发起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主要成员包括戴谦和、莫尔斯(W.R.Morse)、布礼士(A.J.Brace)等,当时已是英国皇家学会会员的叶长青成为该学会荣誉会员。学会于1922 年发行了英文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到1946年结束,共16卷20册,刊载论文300 多篇,涉及西南人类学、民族学、宗教学、历史学、生物学等方面,有不少成果与康藏地区有关。而自该杂志创办初期至1936年为止,叶长青就发表了60余篇文章,可谓该刊的支柱之一。”[12]58根据冯宪华的梳理,叶长青对康巴学研究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是对川边嘉绒地区自然人文状况的研究。“叶长青是较早进行川边嘉绒研究的传教士,对嘉绒的关注已持续多年,有多篇发表的文章中提及这个地区部落。在其文中,提到他1915年大多在嘉绒巡回布道,认为嘉绒是一个不知道其来源的神秘游牧部落,从富林(fu-hin)移居黄河支流的大草原,几个世纪以来占据大渡河。嘉绒人说本地语言,但是许多人汉语说得好,僧侣和受过教育阶层的人藏语口语流利,但只认识藏文字母。嘉绒有数千僧侣花费数年时间在拉萨或者其他尊崇的教派圣地修学。叶长青在一篇书评中提到巴底的居民是嘉绒人,巴旺居民是由雅砻迁移来的摩梭人,1923年他提到在川藏边界地区,有一个巨大的嘉绒部落,他们操着不为人知的语言,其人数不低于25万。在川西以文明、影响和人数而论,最重要的部落无疑就是嘉绒,他们大部分居住在汶河和金川河流域。”[13]61由此可见,关于嘉绒藏区的研究,是叶长青的康巴研究的一个重心。
另一方面,是对川边藏传佛教及白石崇拜等宗教信仰习俗的研究。“叶长青多篇文章考察研究了川边白石崇拜信仰,他于1923年4月刊发的文章说拜石教(Litholatry)或者石头崇拜,是古代闪米特人(Semitic)的特色。它流传到很远地区,在随后的很长一段历史时期上它也曾经是摩尼教的特征,叶长青关心波斯的玛尼是否曾经抵达过川边地区。从打箭炉到松潘,在所有宗教中石头崇拜是很普通的,特别是在巴底巴旺(Badi-Bawang)交界的地区。在Badi-Bawang的人口是很重要的,那些热情的僧人,表达出对三个主要寺庙的信仰,它们是两个藏传佛教一个苯教寺庙,石头崇拜在当地各处习以为常,那些触目可及的圣石摆放在门口、墙上、屋角、土堆,或者其他显眼的位置或者重要的地方,其普及程度可与其他藏族地区的风马旗媲美。叶长青总结白石的功用有以下5种:关于拜石的解释常常因地区不同而已,有时候会被认为它们是有男性生殖崇拜的意义;再者,根据方位性的不同,白石起了护身符保护的作用;或者它们被当做生火的材料加以敬畏,抑或曾经是圣洁物资的起源。它们被描述为山王菩萨和天菩萨。这含有朝拜山神的思想,白色石头代表雪。”[13]63-64
这就是说,康巴地区的宗教信仰是叶长青的康巴研究的另一个重心。申晓虎、陈建明认为,“叶长青对康区宗教的研究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对语言的敏感性;二是善于不同宗教间的比较及对结论的大胆猜想。他从词语含义及其背景入手,采用比较宗教学的方法,对康区的苯教、藏传佛教及白石崇拜与其他宗教进行了比较研究,而且通过实地调查,对宗教仪式、神职人员和仪式进行了较为详细的记录。”[12]60-61申晓虎还认为,“叶长青对藏传佛教的研究,也同样具有语言学的特色。与苯教研究一样,他首先关注的是佛教的六字真言,通过逐一解析六字真言的含义,分析其来源。他以真言中‘嘛呢’(Mani)二字与摩尼教(Manicheism)名称中‘Mani’相似,通过对比两种宗教教义、组织结构与神灵体系的相似内容,大胆地猜测摩尼教与藏传佛教之间存在某种程度的联系。”[14]
除了嘉绒藏区研究与康区宗教研究,在叶长青的系列论著中,关于康巴语言的研究也很有特色,他的《华西语言变迁》《藏语语音系统》《藏语与闪米特语的对应词》等等,就是他在这个领域的代表性作品。
叶长青作为英国传教士康巴学的主要代表,“虽然没有接受过专业的人类学训练,但从叶长青在地理学、语言学及比较宗教学的研究取向和科学收集方法当中,却看到鲍亚斯( Boas)的影子。同一时期在华西从事民族学研究的葛维汉,正是鲍亚斯弟子萨丕尔(Sapir)的学生,他广泛收集了康藏地区各民族的文物标本,主持进行了西南地区考古学、民族学等方面的田野工作,同时认可并结合了中文文献,在羌、苗少数民族研究方面颇有建树。葛维汉的研究反映了鲍亚斯人类学理论的影响,大量的田野调查、丰富的未加解释的事实和信息,几千页的神话和经文翻译及收集艺术品的自然方法。由于缺乏坚实的理论框架及担心西方价值观的影响,葛维汉在得出研究结论时显得小心谨慎。相反,叶长青以敏锐而极具开创性的思维,大胆推论、小心求证,而且颇为有趣的是其中部分结论为后来的研究所证实。”[12]64
这就是说,相对于美国汉学家葛维汉(David Crockett Graham,1884-1961)在学术上的小心谨慎,叶长青更加相信自己的直觉,具有更强的判断能力、预见能力,这样的研究取向与研究风格,在一定程度上,带有预言家甚至是先知的某些色彩。这样的色彩,或许体现了传教士这种职业或身份对于他的康巴学研究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微妙的,但也是深刻的。这样的风格与彩色,为叶长青的康巴学研究增添了更多的个人化、个性化的魅力。
在叶长青之后,还应当提到他的助手顾福安(Robert Cunningham,1883-1942)。在汉语文献中,顾福安也称为顾福华。他生于苏格兰的爱丁堡,自1907年来到中国,就以打箭炉为基地传播基督教,直至辞世。他在康巴地区度过了35年的漫长岁月。
从年龄上看,顾福安比叶长青年轻11岁。他从英国来到康巴地区,主要是协助叶长青开展传教事业。“在博学多才的叶长青的引导和带动之下,顾福安对独具特色的康藏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刻苦发奋学会了汉语和藏语。他以打箭炉为中心,常年在周边的汉族和藏族区域传教,并坚持写作,记录他的传教经历和对康藏社会的考察,直至1942 年在打箭炉去世。”数十年间,顾福安在《华西教会新闻》和《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这两种英文刊物上发表了50多篇文章。其中,“他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上发表的9篇文章全部围绕宗教主题展开,内容覆盖了藏传佛教的起源、教义、轮回、宇宙观、六字箴言、活佛转世、文学传奇等,具有较强的学术性。相对而言,顾福安发表在《华西教会新闻》的46篇文章,展现的则是他作为学者和传教士的双重身份、两种角色。分析这46篇文章:7篇为学术性较强的研究型著述《西藏的信徒、僧侣和朝佛者》《藏区的牦牛》《论牧民》《喇嘛小议》《喇嘛教的方法论》《打箭炉简介》《边疆记事》,属于康藏研究的直接成果”,其他的一些文章大多属于游记或杂记,“在记录传教经历和心得体会的同时,也间杂、分散地记载了康藏地区的社会现状,风土人情、宗教信仰等,可视作康藏研究的间接成果。”[7]197-200
按照朱娅玲的比较,“顾福安和叶长青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两者同属于英国内地会,都长期在打箭炉传教,同是华西边疆研究学会的荣誉会员,都发表过大量康藏研究的论文,都是当时熟知康区文化的西方藏学家。但叶长青1905年就抵达打箭炉,首先建立了福音堂,是基督教新教在康区正式传播的创始者,1907年来华的顾福安是作为叶长青的助手抵康的。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成立之初的1922年,叶长青即是当时唯一的荣誉会员,先于顾福安成为荣誉会员的20世纪20年代晚期。虽然顾福安的论文数目和级别都远远高于当时一般的研究型人类学传教士,但较之论文数量最多的叶长青(仅在《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就发表论文67篇),还是处于下风。因此,当后世的研究者将关注的目光聚焦到卓越的开拓者叶长青身上之时,无意地忽略了后期跟进的顾福安,即使后者也在同一领域做出了巨大的贡献。”[7]205-206
按照这样的比较,在英国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中,如果叶长青是第一小提琴手,顾福安则是第二小提琴手。在两者之间,虽然叶长青的成就更为突出,具有更为耀眼的学术光芒,但顾福安的成就也不可小觑。因此,以叶长青、顾福安的康巴学研究,来代表英国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也许是一个恰当的选择。
四、传教士康巴学的特质
法、英两国传教士在康巴学研究领域的代表性论著,尚不足以展示外国传教士在康巴学研究领域的全貌。在古纯仁、叶长青等人的康巴学论著之外,其他传教士写下的康巴学论著,也是各有所长。但是,通过古纯仁、叶长青等人的康巴学研究,大致可以体会外国传教士康巴学的主要特质。
(一)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与他们的传教活动相互交织,是传教活动的衍生物与副产品
外来传教士的本职工作是传教,他们的康巴学研究主要是传教活动的衍生物。譬如,关于叶长青的传教活动,冯宪华就有一段很翔实的描述:“他传教的主要方法就是散发圣经(Let Loose The Word of God),他在旅途中把宗教作品散发给同行的赶牦牛者和骡夫手中。一次他曾收到从远方闻所未闻的寺庙寄来的一封索要更多基督教小册子的书信。为完成他认为的一年发送二三万的圣书和印刷品正常的工作量,他忍受常人难以忍受的酷暑严寒,常常食不果腹,大多数时候遭人白眼,在山区流浪。从1922年的8月开始,叶长青卖掉和发送掉的文字材料如下:中文书12747本,藏文书4600本,藏文小册子传单19000份,合计36347份。在Bawang与Badi,各派别僧人都很愿意大量接受传教士的文字材料。叶长青在另外一篇文章中提到,虽然打箭炉教堂发展处在低潮衰退时期,但是那种友好气氛仍然在藏族人中存在。当9年前他抵达打箭炉时,遇到的是僧人们的敌视怀疑,但在最近的3个月(1923年)他就卖出派发14000本中文福音书和最少5000本藏文小册子。20000份藏文传单给了当地的藏民和抵达这个城市的商队。人们所见到的围着寺院门前高声吵嚷的不是佛教神舞仪式,而是一些游牧民众在蜂拥讨要基督教书籍。”[13]65这是作为传教士的叶长青的本职工作剪影。
顾福安作为叶长青传教活动的助手,则尽可能采取多种灵活的方式,实现其传教的使命。朱娅玲写道:“除了采取主动出击的宣传策略,到街道闹市进行撒网式的布道,顾福安也会选择以逸待劳的传教方式。他把自己的住处兼传教的地点称作‘后门’,任由当地居民随意进出。‘后门’的屋内摆放的矮桌子和许多座位,是专门为藏族人的习惯而设的,桌子上零散放着藏文版的福音书和一些破旧但插图丰富的《国家地理杂志》(National Geographic)。常常有闲逛的藏族扎巴(小喇嘛)被‘后门’随意的氛围吸引进来,坐下来慢慢翻看藏文版福音书和《国家地理杂志》,此时顾福安并不打扰对方,而是安静在一旁守候。待到扎巴看完杂志准备离去之时,顾福安才上前询问,看扎巴读懂了多少福音书的内容,并试着用藏语向他们宣讲基督教义。”[7]194除了这种直接针对单个的当地受众做出的点点滴滴的努力,顾福安的传教方式还包括办班教学、送医送药等等。
外来传教士的职责与使命决定了他们的康巴研究,主要是传教活动的副产品,是传教士履行其传教使命的衍生物。为了在康巴地区更加有效地传播他们信仰的宗教,特别是,为了适应传教对象的具体特点与实际情况,传教士们必须认识康巴、理解康巴,康巴地区的历史、地理、语言、风俗、信仰以及经济与政治,都是传教士们必须理解的对象。否则,就不可能有效地传播他们信仰的宗教。特别是康巴地区的语言、习惯与信仰方式,如果传教士们没有很好地把握、适应,传教活动就无法正常进行。因此,适应当地人的语言、习惯与信仰,乃是有效传教的前提条件。对于这种“适应”的要求,1943年出生的美国汉学家孟德卫有专门的阐述,他说:“在耶稣会传教事业发展中,这条在中国开辟的路线能设身处地从中国人的立场出发,并显示了其灵活性,笔者因此称其为‘适应性的’(Accommodative)或‘耶稣会的适应政策’(Jesuit accommodation)。”[15]从这个角度来看,古纯仁、叶长青等人对康巴地区文化环境的研究,特别是对康巴地区语言习惯的研究,与他们作为传教士的“本职工作”是不可分割的,甚至是一个优秀的传教士应当具备的基本功。
但是,严格说来,传教士的使命与康巴学研究者的使命是有差异的,宗教传播与康巴学研究是有差异的,布道行为与学术活动是有差异的,在两者之间,从业者的身份不同,承担的角色不同,目标各有指向,甚至方法也不一样。正是由于这个缘故,虽然有一些传教士对康巴学研究做出了贡献,相比之下,传教才是他们的第一职责。像叶长青这样的传教士,可能已经是传教士群体中的一个异数了。正如申晓虎、陈建明所言:“传教士与文化人类学者之间身份的冲突是难以调和的。前者希望通过福音传播,改变受者的观念与行为,而后者更多是以‘观察者’的身份,游离于目标人群之外。叶长青除了分发基督教书籍之外,从宗教的角度而言几乎没有以其它方式介入康区社会,这与内地会的其他传教士以福音传播为中心的行为有较大差异,从这一点来看,他是一个‘不务正业’的传教士,但同时却是一位勇于探索的人类学者。”[12]62也许正是因为叶长青及其他一些传教士的“不务正业”,他们才可能把一部分精力用于康巴学方面的研究与著述,才能成就我们现在所看到的“传教士的康巴学”。
(二)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与汉学研究相互交织,构成了传教士汉学的一个组成部分
传教士的外国人身份,提示我们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来理解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本身就是汉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汉学的历史由来已久。针对汉学的演进历程,赵继明、伦贝有一个概括,他们认为,欧洲早期的汉学有三个阶段,分别是耶稣会士汉学阶段、欧洲汉学兴起的阶段以及学院派汉学阶段[16]。张西平则直接提出了“传教士汉学”这个概念,他说:“从西方汉学的历史来看,我主张采用‘游记汉学时期’,‘传教士汉学时期’和‘专业汉学时期’的分期到更为合适。”其中,“传教士汉学的学术特点是很明显的”,“首先,我们从西方学术与文化的角度来看它。传教士汉学实际上是西方汉学的奠基石。”其次,“传教士汉学的独特性还在于,作为一种对东方文化的介绍与研究,它与西方思想的变迁是紧密相连的。”[17]既然“传教士汉学”可以概括汉学发展的一个阶段,那么,传教士康巴学作为汉学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完全可以归属于传教士汉学。
前文提到对叶长青的一个并非贬义的中性评价,就是他的“不务正业”。这个评价主要着眼于叶长青作为传教士的角色。因为他是一个传教士,所以,他的第一“正业”或本职工作就是全心全意地传教,让他的受众接受他所传播的宗教。但是,他却花费了相当多的时间、精力来从事具有学术性质的康巴研究,由此对汉学研究做出了较大的贡献。紧随其后的顾福安,虽然较之于叶长青,显得“更务正业”一些,传教士的角色意识更为明显、更为强烈,但他在汉学研究方面取得的成绩,同样值得称道。由叶长青、顾福安以及古纯仁的康巴学研究,可以让我们看到,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与汉学研究是相互交融的,甚至是同一个事物的两个侧面:一方面,从汉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他们的康巴学研究作为“传教士汉学”的一个部分,前承“游记汉学”,后启“专业汉学”,已经融入了西方汉学的历史;另一方面,从康巴学研究的角度来看,传教士们在传教的同时,还从学术研究的层面上,开启了康巴研究的学术之路。
汉学虽然是中国之外的学者研究中国的一种学问,但在总体上,汉学又可以归属于东方学,这就是说,传教士的康巴学研究,也可以归属于东方学,也具有东方学的性质。东方学的性质是什么?萨义德认为:“东方学的一切都置身于东方之外:东方学的意义更多地依赖于西方而不是东方,这一意义直接来源于西方的许多表述技巧,正是这些技巧使东方可见、可感,使东方在关于东方的话语中‘存在’。而这些表述依赖的是公共机构、传统、习俗、为了达到某种理解效果而普遍认同的理解代码,而不是一个遥远的、面目不清的东方。”[18]按照这个说法,东方学之下的汉学,汉学之下的传教士汉学,传教士汉学之下的传教士康巴学,也具有这样的性质:外来传教士描述的康巴,同样是西方人借以认识自己的“他者”,描述这种“他者”的一个重要旨趣,就在于通过一种异己的文化,用以反衬西方文化的优越。事实上,“传教”这种行为本身,就已经蕴含着这种“东方学”的趣味——试想,如果不是坚信自己的文化(尤其是宗教)更加优越,有什么理由不惜历尽千辛万苦、千难万险去传播?
结 语
从19世纪中叶开始,一直延伸至20世纪40年代,来自法国、英国等西方国家的传教士来到康巴地区。在传教的过程中研究康巴,对于康巴学的萌生,做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如何全面评价那个时代进入康巴地区的外国传教士,是一个涉及面较宽的综合性问题,比较复杂,由于不是本文的主题,这里暂付阙如。但是,从康巴学萌生、发展的过程来看,外来传教士的培植之功却是不容忽视的。在相当程度上,现代意义上的康巴学,就是从传教士康巴学开始的。上文概述的传教士康巴学,在时间维度上,代表了“康巴学史”的第一个阶段。正是在传教士康巴学的基础上,康巴学才持续不断地发展起来,并形成了如今这种蔚为大观的、谱系化的康巴学理论景观。
从发生学的角度来说,传教士康巴学的兴起,是特定时代、特定语境下的产物。简而言之,是外来传教士在那个特定的时间段里持续不断地进入了康巴地区,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历了西方现代学术的熏陶,他们在传教的过程中,以西方近现代学术的眼光研究康巴、从事著述,促成了现代学术体系中的康巴学的发生。康巴学经历的这种发生方式,与其他学科的发生方式,有一个明显的区别。在现代意义上的汉语学术体系中,像哲学、经济学、法学、社会学、人类学等学科,基本上都是出国留学、学成归国的中国本土学者培植起来的。譬如,胡适、冯友兰等人对于现代中国的哲学学科,就有培育之功。以此类推,其他的学科也可以找到本学科的“第一代学者”(9)譬如,关于法学这个学科,有学者就把近代以来的中国法学家分成五代。其中,“第一代法学家成型于清末民初,其主要人物大略包括沈家本、梁启超、严复、伍廷芳和王宠惠等诸公。这辈人构成复杂,既有前清名宿,若沈家本、董康乃至于薛允升者;又有洋装新秀,如伍廷芳和王宠惠这样的留学生;更有像梁任公、严几道这样来自逊清,却成为新时代的启蒙大师的伟大人物。”详见,许章润.书生事业 无限江山——关于近世中国五代法学家及其志业的一个学术史研究[C]//许章润.清华法学:第四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4:42.。 与这些学科相比,康巴学的发生略有不同:它是外来传教士来到康巴地区,率先培植起来的。
20世纪中叶以后,外国传教士退出了康巴地区以及中国的其他地区,这标志着传教士康巴学由此走向终结,从此进入了康巴学的历史——从汉学的角度来看,则是进入了汉学的历史。不过,在传教士康巴学兴起之后,以及在传教士康巴学终结之后的数十年间,康巴学作为一种专门的学问,继续蓬勃生长,呈现出更加多元化的格局,其发展既见于中国本土,也见于中国之外的世界各地。
——林俊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