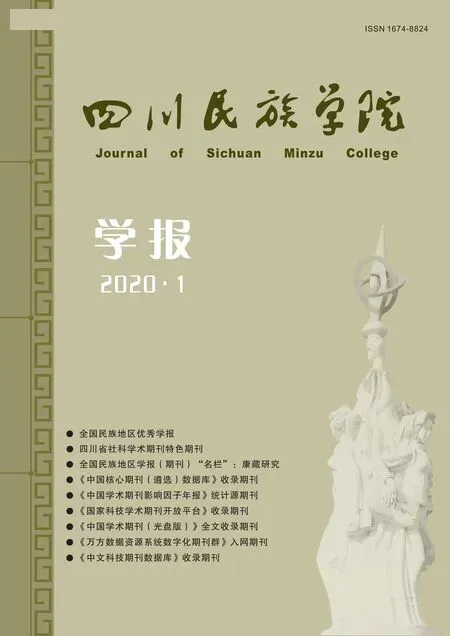浅析瞻对工布朗吉事件
扎西机
瞻对(今四川新龙县)位于康区中部,地处雅砻江中游高山峡谷地带。雅砻江自西北流入,纵贯全境。大江两岸山峦起伏,群山环绕,地势险要。该地区东连道孚、炉霍,南接理塘、雅江,西临白玉,北达甘孜、德格,南北长达五百余里,东西广约三百里。(1)《新龙县志》,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新龙县志编纂委员会编,四川人民出版社,1992年出版。
19世纪中叶,新龙地区的工布朗吉,依靠强大的军事实力占领了大片邻近土司的辖区,迅速崛起成为康区的一大霸主。1862年,他控制川藏大道,梗塞邮路并阻滞了驻藏官兵粮饷运送。工布朗吉的强势扩张,既搅乱了四川治理川边的政局,也对清廷和西藏地方政府的权威带来了严重的挑战。此时,风雨飘摇的清廷正穷于应对内地爆发的诸多内乱和鸦片战争等外患而无力西顾川边,只好由西藏地方政府于1863年初派兵进剿工布朗吉,最终以后者失败而告终。[1]
在康区历史上出现的这位赫赫有名的人物,他的事迹广为流传,影响深远,自然引起史学家和学者的广泛兴趣,纷纷著述发表文章。但受不同时期、不同学术思想环境的影响,大家对历史人物形象关注的视角和看法,也可谓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各有各的道理。因为我们知道史学理论通常强调的是,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是客观存在的,它不以人的意志而改变。但史书是由人书写,就避免不了融合人的主观意志,研究人员在文献资料的取舍上面,也无可厚非地受到当时思想潜移默化的影响。由此,对于人物分析的切入点也就出现了上面所说的现象。
一、 相关研究动态
目前查找到的有关研究工布朗吉人物形象方面的文章非常之多。官方的汉文文献《清实录》,记载:“中瞻对野番工布朗结,负固不法,出巢滋事,先后抢去上瞻对、下瞻对嘓陇、喇滚、各土司等印信号纸。占去有号纸纳、撒墩、土千户地方二处,并无号纸头目地方九处……前督臣,以外番狡逞,未经理论。乃野番竟其凶顽,夜郎自大,又欲侵占里塘。查里塘系通藏大道,该野番逞其强梁,一经占据,大路梗塞,所关匪细……”这个奏折赤裸裸地把工布朗吉刻画成“野番”“凶顽”“夜郎自大”,肆意抢占领地,蛮狠无理的一个形象。从而可以窥视出清朝官员对这些地方的控制微乎其微。郑勒的《试论工布朗吉其人》试图从三个方面阐述工布朗吉的一生。首先,探讨了他的出身问题,分别从藏、汉、调查报告三处的相关资料来论证这个问题,从而得出他不是出身于破产土司的家庭,就是普通平民之家,这个问题很好地为其之后起义埋下了伏笔;其次,简单介绍了起义的口号和纲领措施;再次,从宗教关系来评判工布朗吉是否存在宗教信仰,根据民间传说和上层喇嘛的著作分析了这个问题,从而得出工布朗吉是有宗教信仰的,只不过他对宗教存在取舍,并不会一味地盲目迷信,对自己有利的会非常尊重,反之就会极力打击;最后,研究趋向于极度地赞美工布朗吉的起义,并称赞他是农奴领袖。丁人的《布鲁曼其人》与郑勒的内容没有太大的出入,主要也在探讨上面的几个问题,只是补充了一个新内容,即对工布朗吉的家庭和经济状况做了一个简单叙述。从而分析他起义的时间选择在儿女成人之后,是考虑到自身社会地位低下,在等待社会地位和经济实力得到提高,再进行一次彻底的完全推翻农奴主的起义;这是对工布朗吉起义筹备阶段背后隐藏的细节方面的分析。邓明浩的《布鲁曼》,考察了工布朗吉的出生年代,由于史料的局限性,只能借助民间传说来论述他的这个问题,民间传言工布朗吉生于藏历火牛年(公元1817年),死于公元1863年,年仅46岁。这似乎跟丁人所言的,工布朗吉40岁发动农奴起义,最后起义失败战死,享年65岁的说法之间出现了一些时间上的分歧。这缘于在史书上确切记载工布朗吉生平的内容几乎为空白,研究这些内容只能依据民间传说,而民间传说因为与时代的距离较为久远,在一定程度上会存在不确定性和不真实性,由此做出的结论也就大不相同。徐铭的《工布朗吉是农奴起义领袖吗?》通过引用大量的批评工布朗吉军事行动的汉藏文官方文献分析得出,工布朗吉在康区兴起的起义不是一场农奴起义,也不是“康区人民反抗清朝统治者的开始”,或“部落之间的战争”,而是一次长时期大规模的叛乱。并将他描述为执行封建农奴主政权的扩张领土的野心家,迫害人民的刽子手。还进一步指出史学家对工布朗吉肯定的态度,是基于调查报告,而没有利用好汉藏文文献。陈一史的《清代瞻对事件在藏族地区的历史地位与影响(二)》一文,在注释中点明曾在《略论1889年川边藏地区撒拉雍珠领导的农奴起义》中认为,工布朗吉是农奴起义的领袖。但是,自从参阅清代档案资料之后,修正了这个看法。他并没有全盘吸收官方档案对工布朗吉谴责的观点,而是通过客观地分析指出,工布朗吉是一个土司和农奴主,并且在政治和宗教上具有自己独特见解的有胆识的藏族领袖。但是,作为一个农奴主,工布朗吉压迫和剥削广大农奴,扩张领土,给康区社会经济带来极大危害。最后,纵观工布朗吉一生的所作所为,作者认为他不配称为农奴起义的领袖。喜绕俄热的《新龙工布朗吉兴亡史》,对工布朗吉的评价相对比较客观和公正,并没有持非褒即贬一边倒的态度,而是对他行为积极方面给予了正面的评价,反之就是批评。文中最后对他下的结论是,“工布朗吉的一生确有传奇色彩,但他确实是一个不足效法的悲剧性的历史人物。”
通过对这些文章的解读,让我们深刻地了解到,史学家和学者是如何塑造工布朗吉形象的。也更加认识到对于这个历史人物,大家所持的矛盾观点。笔者借用玉珠措姆的观点来解释出现矛盾观念的原因,“历史叙述依靠当时流行的叙事方法在一个叙事结构中来塑造历史人物。”[2]从目前研究的成果来看,相关研究存在以下特点:首先,关于对工布朗吉的研究缺乏系统、翔实、深入专题研究的学术著作;其次,近年来对工布朗吉关注的学者日见增多,学术论文数量较多,但多数仅仅从一个侧面或某个角度来探讨,研究上明显存在片段性和分散性;最后,研究史料的运用分割。有的论文仅用汉文资料,缺少藏文史料,有的则侧重藏文史料的运用。多数论文都缺乏外文资料的应用,出现将多方文献资料综合并多重使用的现象。清朝末年,清朝为了达到对康区的控制,实行土司制度,缓解地方矛盾,在维持边疆安稳的时候,出现工布朗吉这样的历史人物,其事迹影响深远。将这一研究放在清朝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这个大背景下,深入探讨他的活动对清朝统一西藏,并对清朝和西藏之间产生的影响再做分析是非常必要的。
二、 历史背景的概述
要想深入探讨和了解工布朗吉事件,必须要从国内外格局来全面认识这一历史事件。当时帝国主义用鸦片和大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清政府对外妥协,先后签订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使我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同时,各族人民纷纷掀起反帝反清的斗争,席卷全国的太平天国运动兴起,顿时举国上下陷入动荡中。与此同时,在号称“天府之国”的四川,清政府表现出内强外弱的态势,多次镇压人民起义,导致起义战败,民不聊生。地方各级官吏,趁势盘剥和打压人民,钱粮不入国库,从而影响中央政府的利益。而远在康区的瞻对,也因忍受不住清朝官吏和地方土司的剥削,开始了一次自下而上的农奴大起义。明清时代中央政府为了对边疆少数民族特别是藏区进行有效管理,根据藏区的特殊性,推行了土司制度。“清康熙三十九年,四川提督康希顺在平定打箭炉营官杀死明正土司的叛乱后,陆续在康区设立了土司,直到雍正时已设了大小土司128名,瞻对就设立了3个土司。”[3]在康区施行的是一个不同于政教合一的政教联盟制度,在政教联盟制度之下,寺院喇嘛和土司之间往往会因为利益问题,时而联合时而分离。依附于土司土地上的人民不仅给土司提供充足的兵源,也为土司生产了剩余价值,土司拥有独立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实力。随着其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在领土扩张野心的驱动下,土司之间相互争斗,相互仇杀屡见不鲜。其实,土司势力越大,对中央政府的统治来说隐藏的威胁就越大,尤其是清朝政府前后八次大规模用兵于瞻对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藏区自古以来“夹坝”出没,抢掠商旅弱民是一种常见的社会现象,当然此现象在瞻对地方表现得尤为突出。瞻对分上中下三部,其中有“上瞻对茹长官司、峪纳土千户、蒙葛结长官司”。 雍正六年,下瞻对土司策冷工布,在川藏道路上出没无常,劫掠过往财物,地方官员几经干预,却遭到反抗。于是,川督派高奋志带领汉、土兵前往镇压。高奋志采取欺诈行为打死了土司策冷工布,这引起了下瞻对人民的无限愤慨,他们设法报复高奋志。但是,清廷没有追查高奋志罪行,而是继续派兵进剿下瞻对。此事使瞻对和清廷之间首次播下矛盾的种子。中瞻对的土司罗布七力,因为与邻近土司部落常常发生争夺牧场、土地及聚众抢掠等土司兼并战争,遭到清朝官兵的镇压。刚开始罗不七力并没有打算要和清军反目。但是,由于清廷仍坚持讨伐,必置其于死地方可甘心,逼迫罗布七力走向与清廷作战的绝路。当时罗布七力运用得天独厚的地理优势,几度把清军打到无所适从的境地。但据记载,“五月清兵攻克藏多山梁,抢占险要之地。六月,破其巢,罗布七力焚死”。清军官员虚报奏折给朝廷,说罗布七力被“焚毙”。暂时停止了进攻,这无形给罗布七力父子卷土重来,引发之后的工布朗吉事件提供了机会。
三、工布朗吉事件
首先,有必要了解清楚是什么原因导致工布朗吉事件的发生。据《布鲁曼起义》调查报告记载,1848年前后,瞻对地区连年发生天灾,无数农奴,十室九空。可是,如狼似虎的农奴主却不顾此情,依旧对农奴施行盘剥打压,农奴不忍,愤而举旗反抗。“举起一面黑旗帜冲向土司官寨,杀死了瞻对土司及其全家老小”。 由于天灾再加农奴主的剥削,加剧了起义的进程。但是,据《瞻对·工布朗吉》记载,工布朗吉世代为封建农奴主,从祖父开始就扩张领地,打压周围的土司,到了工布朗吉的时候,规模更大、波及范围更广。对于事件起因的不同记载,如何做到比较公正地看待呢?笔者认为应该做到汉藏文有机结合并且有鉴别性的取舍。
其次,简述一下事情的经过,对我们有效了解事件最后导致的后果和影响会有帮助。工布朗吉(1799-1865),于清嘉庆四年出生于新龙切依地方的瓦达塞子。工布朗吉因一次械斗中被打伤左眼,人们便根据其一只眼睛的特征而呼之为“布鲁曼”,意为盲人娃娃。他的祖先是瞻对地方最古老的日鲁家族,以劫掠而远近闻名,清代因多次叛乱受到镇压。其父罗布七力与清军之间的斗争在上述已做了简单叙述,在此不赘述。据传工布朗吉生而神力绝人,兼有胆智,至幼嬉戏,儿童多受其指挥。既长而驰马、试剑无虚日,每顾盼自雄曰:“天何生我在蛮夷之中。” 共青团新龙县委编撰的一个资料里记载到,“他从小喜爱骑马习剑,在赛中儿童游戏时多为指挥者,结交朋友甚多,常常把家中食品给穷孩子和他年龄一般的人,都拥护他,为‘娃儿王’”。从这段材料里,可以看出工布朗吉从小就具有的头人风范,他品行中兼具着霸气和善良。工布朗吉长大后是一个“身躯高大,蛮力过人,皮肤黝黑、智勇双全的男子汉”。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他开始为统一全瞻对,兼并邻地土司而努力。工布朗吉首先采用联姻策略扩张势力,他自己娶了上瞻对两位头人的女儿为妻,分别是拉滚的妹妹卓玛和细瓦班登的妹妹亚吉。让大儿子其美工布娶搭格土司的女儿为妻,还把自己的女儿先后嫁到理塘、道孚等处,从四面建立起世俗的联姻关系。还把两个儿子送去当和尚,间接与寺庙集团也建立了关系。道光二十九年成都将军裕诚,川督琦善奏称“工布朗吉先抢去上、下瞻对,嘓陇、喇滚各土司印信号纸,占去有号纸峪纳,撒墩千户地方二处,并无号纸头目地方九处。侵凌各土司,杀毙其民人,掳掠银钱牲畜,劫夺茶包什物,各处土司被其蚕食,莫可谁何。” 如若这份奏折如实陈述了当时工布朗吉的作为,那我们就可以判定,此时他的势力已经开始慢慢伸展到瞻对全境及其他部分区域。上书奏折的目的分明是要进兵去镇压工布朗吉的势力。琦善率领士兵四千余人前往瞻对。不过,他明白雍正、乾隆时期数以万计兵士进攻下瞻对都尚未全胜,此次人少更难以取胜,于是派心腹去瞻对与工布朗吉洽谈。此时,工布朗吉权衡形势,表示不愿再继续扩大战争,愿意受抚。琦善立即上书奏折“中瞻对野番出巢滋事,琦善饬汉、土官兵击之,歼其渠。五月移师进剿,野番哀慑,献所夺土地、人民。” 明显这份奏折严重夸大了自己的战绩,清廷闻此消息十分高兴,大赞琦善,并且对工布朗吉授予土封官。只不过这份头衔的授予并没有制止工布朗吉的扩张活动。1861年,他完全控制了整个瞻对地区。此时,太平天国起义正如火如荼,清军忙于奔命,早已无暇顾及工布朗吉的扩张,只求维持川藏大道安全。同治初年,工布朗吉的势力已经扩张到康区的大半区域,并且提出由察木多进攻拉萨,从东侵入明正地界,南攻理塘、巴塘,截断清廷与西藏联系要道的计划。同治元年,其进攻理塘,截拦川藏大道,阻塞茶路,文报被劫,严重影响川藏交通,还中断中央政府和地方之间的联系。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实不忍工布朗吉继续进行扩张和阻拦川藏道路,同治二年初,清廷决定川、藏会剿瞻对。
最后,工布朗吉在敌众我寡,内部出现叛乱的情况下,实力大为减弱。在川藏联军的步步紧逼下,工布朗吉家族及其核心力量最后被围困于中瞻对仑朱官寨,藏兵乘机进攻,救出二百余名人质,并将工布朗吉等人烧死。“迨我兵进攻之时,该酋父子三人子嗣,家丁三十余名,人财房屋,全行烧灭,只有驱美工布及伊女三人从窗内飞绳下地,亦已擒获。”[4]至此,工布朗吉在此事件中已告失败。
四、工布朗吉事件产生的影响与作用
工布朗吉事件不仅仅只是单方面反映康区内部和外部矛盾,它可以折射当时藏区的整个局势。
第一,把瞻对及这个事件放在整个藏区来看的话,它成为中央王朝与西藏地方政府之间的一个重要连接点。仅仅一个“弹丸之地”就足足让清朝中央政府连续用兵七、八年,清朝曾调和组织四川、青海各路汉、土兵对工布朗吉势力进行会剿,就足以证明这个小地方的重要性。瞻对作为藏区的一个小部落,它身上的很多细微的文化更多折射出整个藏区的博大精深的文化,就比如说,工布朗吉的婚姻制度,选择近亲结婚和近村结婚的习俗,这在现在的社会里也是体现得很明显,人们普遍相信这样的婚姻保质期会更持久。还有在征战时都习惯性地找喇嘛占卦,选择良辰吉日。特别值得一提的是,现今瞻对地区都会过一个有别于藏区其他地方的一个节日,被称之为“十三节”。此种节日在当地民众心里就足以抵过藏历春节,每家每户都会为此举行隆重的庆典。这种别样的地域文化,也与他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宗教信仰是无法相分开的。因此,可以说瞻对是一朵奇葩。特别是工布朗吉发动叛乱的时候,其势力遍及大半个康区,还危及西藏地方政府的威信,由此可以看出,这个事件的影响是极大的。清朝历朝历代派兵镇压瞻对土司的叛乱,其耗费的人力和财力无法估量,虽然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战绩不太理想。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起到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第二,清朝长期对瞻对地区的征讨,加强了对东部藏区的震慑与控制,使其从间接控制到直接控制起到了一定的过度作用。进入瞻对深入作战也使得清军的势力渗透到康区,对全面了解康区的民族特性和地理条件也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再者,通过军事上的商洽和对接,也更是对之后彻底围剿工布朗吉势力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每一次的交锋,每一次的交接,对清军和康区的士兵来说都是一次次适应对方,相互学习的过程。
第三,其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促进藏汉文化相互交流的作用。几次征兵围剿工布朗吉事件,清王朝动用的财力规模之大,人员繁杂。不光是召集了汉兵,还有藏区的土兵,在长期的交战中,士兵也会被一方的乡土文化潜移默化。交战过程中的文化交流在所难免。纵观工布朗吉事件,可以大概地了解到,工布朗吉本人在瞻对逐步扩张的势力,对当地民众内心是一种大的征服。如果一个领导者,不能给自己的民众生存上的保障,而让人民的生命财产受到威胁,在他的统治下人民则不能安居乐业,那么,民众一定会采取各种途径推翻他的统治。工布朗吉恰恰满足了人民的愿望,既得民心,又有杰出的领导才能,才干出的这番事迹,具有如此大的影响力。
结 论
总之,瞻对这个地方对汉藏之间的交往有着桥梁的作用,工布朗吉事件对清朝政府逐渐控制整个康区起到必要的推动作用,在一定程度上对社会的进程有一定推动作用。我们在分析一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时候也不能太过于绝对和片面,要以特定的历史事件作为背景,结合当时的社会环境,客观公正地给予评价。对于工布朗吉,人们对他的评价虽褒贬不一。但是,唯一值得肯定的是,他利用自己的实力,一一打败了各个地方的土司。在当时缺乏从事正当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的条件下,使其自然演化成了掠夺性的政治实体,实施盗窃和劫掠从而赖以求生。毫无疑问,劫掠活动使工布朗吉和属下变得富有,这种集体活动和个人行为的动机基于广泛的文化价值观,这种文化价值观进一步增强了工布朗吉和属下的团结一致性,精神和观念是导致他成功的至关重要的因素。
工布朗吉也会经常教导僧侣和民众明白看书、识字的重要性,其中有趣的是,他觉得僧侣识字才能诵读经书,不然就跟泥塑相没有区别,所以识字读书很重要,不然会跟哑巴没有区别,这是对僧侣的要求。其对男性讲,识字可以互相通信、讲故事,而对女性讲识字没用。从这些细节中可以看出,工布朗吉依旧受到传统男尊女卑观念的影响。
——基于对口述史料的文献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