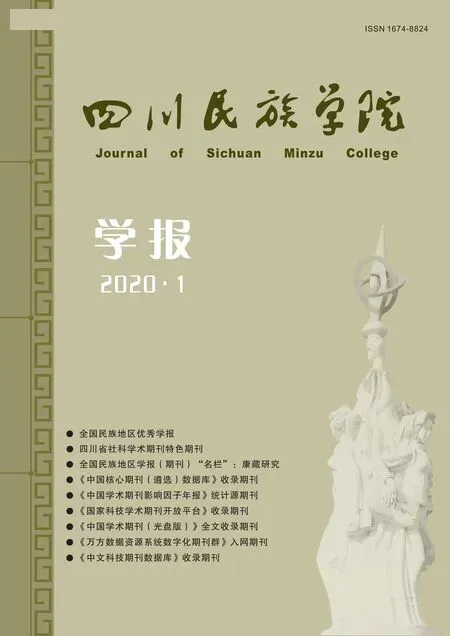基于良性互动的民族史观教育体系建构略论
黄晓通
中国是一个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少数民族在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中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民族历史和文化,贡献和丰富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和内涵。民族史教育担负着传承中华民族文化的重大作用,目的在于培育中华民族精神,增进中华民族认同,增强民族凝聚力,为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贡献力量。随着时代的发展,传统的民族史教学体系陷于陈旧,以民族间自然良性互动的新民族史视野为核心的体系建构更富于现实深蕴和时代意境,融入中华传统文化以完成从旧至新的话语体系转换,使民族史教学回归本真、更具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之风貌,并提升新时代民族社会治理的效用。
一、 传统民族史教育体系存在弱点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根据2010年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少数民族人口占内地总人口8.49%,比2000年增长了0.08%。对一个普通学生来说,历史教育贯穿其初等教育至高等教育全过程(尤其2009年《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纳入大学思想政治课课程以后),政治—历史教育对于当代大学生的国家观的形塑具有重大的意义。近代以来,中国国情发生深刻变化,随着“西方近代民族学说的引入与流传”[1],在先进知识分子的努力呼吁和中国社会形势需求下,中华民族史观开始形成并在不同阶段显现出各自的特点:在西方话语权与“现代性”强势扩张的情况下,古代的华夏认同受到巨大冲击,晚清-民国时代的人们,甚至许多知识分子都在不同程度上产生了自我认同的疑惑;在当今国家富强的时代语境与诉求下,加强民族团结、构筑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理念充满了宏大的国家统一视野和深切的现实关怀,是各族人民的最高利益。因此民族史教育在目标上追求各少数民族达成中华民族共同体之认同,进而自觉维护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传统的民族史教育体系对于中华民族形成过程的描述忽视了各民族融合的一般建构过程,存在不足。
(一)民族史一体化陈述的断裂
民族史本身并非单一和孤立的史学学科,而是融合了古代历史、社会学、政治学、民族学、社会伦理学等的综合交叉学科。民族间历史的发展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其间存在着战争、交流、共存等表征。在历史的进程中,有的民族吸纳了其他民族的东西存续和发展下来,有的民族则由于各种内部或外部的原因消逝了,民族与民族间充满着各种形式内涵丰富的互动和影响,构成整体而一体化的民族史脉络。将汉族与其他少数民族二元对立的潜在意识主导了民族史教育的性质导向,引致了民族史一体化内在连续性的断裂,以及民族间文化上的隔阂和误解。某种程度上说,这是中国古来“华夷”二元对立及“本部”与“藩部”之分思想的延续,是应当批判对待的。
同时,在传统民族史教育体系中,部分教材的叙述和一些教师的讲授亦缺乏整体史观的视野,难以站在从古至今的人类社会发展高度的视野下对历史进程进行宏大的叙述和思考,容易忽略重要的发展支脉和局部事件的重要作用,形成对于许多时间性历史结果在原因解释上的模糊和概念化,亦消解了许多特定阶段少数民族的重要作用,固化了教师知识蕴藏的话语向导,造成了一定程度上教育的僵化和停滞。因此,各级课堂的民族史教育陷入矛盾难解的话语困境,也使许多少数民族学生的文化心理产生隔膜。当今信息化时代飞速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进入一个新的时代,传统民族史的陈述方式和脉络已难以满足社会的需求,亟待改革。
(二)民族史教育话语的陈旧落伍
在我国几十年传统型历史教育的过程中,形成了一套固化的历史表达的语言模式,长期主导历史教育话语表达领域。常常为“自古以来”“有史以来”等。如何“有史以来”,往往简单带过,中华民族历史表达更多为了促进民族和谐而选择表面上“团结”“进步”的历史,而忽略了表面上不那么“积极”的历史。其实,从内在的历史发展逻辑来看,那样一些看似不那么“积极”的历史反而在一定程度更深入地促进和推动了中华民族的形成模式。
让我们以历史表述中经常出现的“民族融合”为例:民族融合一般意义上多从民族间关系上考虑,讲究各民族之间在长期的历史演进中,在政治、经济、文化、风俗等方面的交流影响,民族间差别缩小乃至消失,因此更强调各民族之间的相对平等性。然而,古代至近代的民族融合交汇仅依托屯垦、战争、行商、宦游、逃难、谪戍几个有限的路径,尤其是民族之间的征战,作为民族之间矛盾斗争最激烈的一种表现形式,给各民族人民带来的往往是灾难和痛苦的民族记忆,我们近年来的历史教育所存在的一种倾向就是尽可能对此避而不谈。我们认为,这是在教育工作中回避矛盾、掩盖问题、绕着困难走的一种表现。从深层次看,中华民族建构的历史变迁纵向上时间漫长,横向上囊括丰富,征战和民族压迫在民族关系当中是统治阶级的短期行为,和平友好的贸易往来是长期性的,相互依存、相互吸收,进而共同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是民族关系的主流。所以,只有不回避民族关系中的这些历史事实,才能真正动态地、多层次地、立体地呈现中华民族史与民族关系史,并丰富民族史话语内涵,使之更具现实性教育意义。
(三)民族史教育内容的匮乏单一
在浩瀚的几千年的中国历史进程中,各少数民族在实践中形成璀璨丰富的文化和风俗习惯。我们纵观各历史或者民族史的通用教材,在教材内容的呈现上偏重于主流汉民族的文化发展演变史。在汉民族主政的王朝历史教材式的表述中,更多地强调和凸显汉民族的文化人物、文化事件、文化作品,而对同时期少数民族文化却不太重视。著名历史学家陈寅恪先生曾在1936年2月“晋南北朝史”课上指出:“每闻人言:中国文化最高,或谓汉族文化最高。汉族文化自为一极高之文化,然遂谓其为世界上最高之文化,则殊不当。如读藏文之正续《藏》,则可知藏族学问甚高。又如在中古时,阿拉伯人有极高之文化。不能因为自己无知遂谓某民族文化甚低,或文化不足道。”可谓灼见。
据我们的观察,通用教材的文化史叙述中,许多少数民族的文化往往被流水账化,表达过于概括式,失之于简略,似乎只作为主流文化的陪衬,甚至呈现边缘化的趋势。各少数民族历史文化在民族史教育体系中不能得到其应有地位,对于少数民族受众来说会施加一种不平等的心理影响。例如朝鲜族的农乐舞、满族刺绣文化、锡伯族民间故事文化等等,虽然很多进入非遗名录,但是在许多教材的表述中,只用一些简单的词语一掠而过,甚至有些并不提及。类似这样对少数民族文化展示重视的不足,造成民族史教育内容的匮乏和单一,危害较大。
二、 基于自然良性互动的民族史教育体系的重构
“中华民族”概念产生于近代,并在近代历史发展过程中得到强化。而中华大一统则最早实现于秦汉,此后历经分裂又归于一统。中原华夏族与周边少数民族的融合是一个漫长的过程,而在这个过程中的种种历史样态并不应该被刻意隐藏,因为中华五十六个民族的历史生态进程无法被割裂看待,割裂反而容易被肆意扭曲。在传统历史教育的建构中,这条主线的陈述往往过于笼统和简单,新民族史教育内涵意在形成一统的民族史教育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完成各民族历史和文化的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建构中华民族统一性,同时切实保护各民族自身文化的传承。因此,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形势下,我们应构建展现良性互动的民族史教育体系,真正体现多元一体,才能真正达成基于各民族内心真实性基础上的中华民族共识。
(一)完成民族史教育范式的转换
从自然生态进程来看,中华民族大一统的概念培育立足于对各民族及其生态发展的基本尊重。人类生态发展和沿革呈现出自然性的发展面貌,蕴含内在的规律。马克思主义者强调“并没有什么唯一的民族特征,而只有各自特征的总和”,“各自”蕴含相应的平等状态。追溯中华民族理念的产生,我们可以发现,1905年梁启超先生在《历史上中国民族之观察》阐释了“中华民族实由多民族混合而成,后在时代浪潮的推动下五四运动之后,中华民族和中华民族精神被广泛应用,被社会主流所倡导”。但我们不难发现,当今主流教育体系仍缺乏对各民族发展原生态的重视。
例如关于藏族先民在青藏高原所建立的吐蕃王朝,共存在两个多世纪,而我们的历史教科书对吐蕃的介绍以及学生对这一政权的认识,仅仅停留在“唐蕃会盟”“甥舅之亲”几个基本概念以及松赞干布、禄东赞、文成公主、金城公主几个历史人物而已。对于吐蕃鼎盛时期与周边各政权的关系,吐蕃在唐代丝绸之路上所起的作用,古吐蕃人的宗教、文化、科学技术的发展则几乎没有涉及。其中央王朝对西南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改土归流”,其时间跨度之长、涉及民族之多(至少涉及今壮族、彝族﹑苗族﹑哈尼族、布依族﹑侗族﹑瑶族﹑水族等民族),使其成为历史教育中无法回避的大事件。通行历史教科书对这一事件时间断限的确定及其与“摊丁入亩”经济政策的关联都存有商榷之处。我们认为,在历史教育中,中华民族各成员发展史、兄弟民族历史不可以做浮光掠影的介绍,这种教育是旧史书(尤其是被称为“正史”的纪传体通史)中“诸蕃传”“四夷传”落后思想的残余。历史教育中对少数民族史部分的介绍必须以“对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经济文化的发展有无积极意义”为标尺,同时尽可能吸纳已被史学界承认的新成果,衡之以党的民族政策决定去取。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都为中华民族形成和发展作出了卓越贡献”。[2]因此,转换传统史教范式,即要淡化汉民族主导的民族融合史,尝试书写各民族共同作为、良性互动的历史长卷,展示参与的各民族同等的行为表达和话语力量。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塑造,应得益于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的各个民族的共同历史文化的表达和传承。
(二)提升民族史教育体系的时代辐射力
民族史,不仅仅包含历史变迁和发展,更应关注当下,聚焦现实,体现时代意境。中国自古形成的多民族历史文化形态被费孝通先生称之为“中华民族多元一体”,这一极具概括性的提法被广泛传播和应用。“多元一体”,“一”将“多”容纳其中,“多”是“一”囊括中的多种表现形式,“一”是“多”的发展趋势和目标指向。现代中国“多元一体”民族格局提出三十年来,已成为中国民族学论述和民族史教育的根基,这一根基,是长期的民族田野考察,以及20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问题讨论的切磋琢磨中产生的。而当今社会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的形塑,不仅需要完善的民族史理论,更需要在中华大地上生活过的各个民族的历史文化的共同表达和传承。而这种传承和表达,需要如今的民族史教育富含更多的社会意境和时代辐射力,才能肩负起更多的现实担当,真正成为凝聚中华民族共识的有效途径。
民族史教育体系时代辐射力的凝聚,需要更密切地关注当今少数民族的生活样态、文化境遇、心理诉求,让其成为推动民族间历史-现实蕴含增长的有效动力。比如辽宁省沈阳市,有西塔朝鲜族聚居区、西关回族聚居区、北郊石佛寺锡伯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区。在历史的变迁中,他们陆续迁往城市居住和生活,如今他们的生存状态、文化心理、情感趋同,以及当今民族政策对他们有什么影响等等应该得到充分关注,并且融入教材内容中来。即要深刻地根植于民族历史变迁、民族文化积淀、民族发展状况、民族现实状态,并且要贴近民族群体在时代和社会的动态变化,才能让少数民族感到自己真正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才能在空间-区域-城市-社会多层次记忆中构建共同的精神文化家园,这样的史教体系才能更接近少数民族的心理,发挥更好传播和教育的效果,才能由内到外增强各民族人民的国家认同感。
(三)加强民族史教育话语的逻辑生成
民族史教育作为以民族分类为特征的教育样态,成为民族文化传承的重要途径。卷帙浩繁的文献材料成为历史课程的内容设置的详尽来源,文献体现文化烙印和延续,因此编著的课程也必然承担了民族文化传承的功能。在学校教育领域中,一方面,课程载体之书本话语展现了民族史教育的意境选择;另一方面,教师的二度阐释话语亦反映了民族史教育的色彩偏向。除此两个主要方面外,课程的目标、课外活动的安排、学生的学习模式、现实媒体的宣传导向等方面亦影响民族文化的传播。其中最关键的因素之一,是民族史教育话语的内涵和趋向,其直接关系了民族文化传承的质量和效果。
话语的现实的影响乃至塑造能力是我们不能忽视的。古代统治阶级反复宣称“夷狄,禽兽也,畏威而不怀德”,这本身就是用一种政治权威话语对民族观进行构造。直至20世纪三四十年代,芮逸夫等学者受政府委托,考察西南各少数民族,订定“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将带有污辱性的族名(如“犬”“牛”“羊”偏旁之名目),改为“人”字之偏旁,“以期泯除界线,团结整个中华民族”。新中国成立后,更是对挫伤民族感情有碍民族团结的话语进行了整顿和清理。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壮族,它在历史上被称为“狸獠(俚僚)、蛮、土人、俍”等等,后来统一改用宋以来常用的“僮”,后来因为“僮”在汉语中有奴婢、低贱之意,六十年代在周恩来总理的建议下改为“壮族”,遂为今名。可见话语问题并不简单,关于民族的话语,除了要考虑历史传统,还要考虑民族所在区位、主要产业、独有文化等等,而不能以一元化的强势话语来进行强制命名与观念塑造。
由此可见,我们在民族历史的表达和转述中,尤其要加强话语的逻辑生成,包括文本话语和教学话语,对于因果发展、制约和影响、推动和阻碍等众多关系的剖析须符合正常思维的结构,避免为了某种结果而构建原因,或模糊产生之条件。尊重民族间自然良性互动的原生态,加强史教话语的逻辑脉络,可以为受教对象构建清晰可触的民族文化发展基本概貌,提升民族史教育的成效。
三、 融入中华传统文化蕴涵创新民族史教育体系
教育和文化相互促进,相互影响。教育让文化更有效地传播、延伸和扩展;文化促使教育的内涵和意境获得提升和丰富。中华传统文化博大精深,源远流长,汇聚了各民族共同的历史记忆和风俗传承,在聚合过去并力图解决现实问题中一步步走向未来,并在继承、传播和不断丰富中推陈出新。以中华传统文化蕴含融入新民族史教育体系,完成民族史教育纵向和横向的层次创新,推动新时代民族史教育体系整体性质的提升。
(一)融入“中华民族”的历史性整体视野
“中国以地域辽阔,人口数量庞大、资源丰富、少数民族众多,区域间发展不平衡,经济发展水平中等偏下为主要现实,其中不少与教育相关的问题均存在‘安全隐患’”,因此在全球化背景加剧下,要确立“教育安全”的意识,“帮助人们在国家前途和民族利益的高度上审视与各类教育发展相关的问题”。[3]知识界的个别人士把民族看作是给一定人群以情感联系与归属感的“想象的共同体”,是可以被建构甚至被“发明”的。而近年来世界上在“民族自决”口号下各类“独立”运动的猖獗(如苏格兰脱英公投事件、加泰罗尼亚公投事件),其后往往有“想象的共同体”的拥趸者为之背书。足见民族教育关系国家教育安全,未可看轻忽略。国家教育安全关系着国家大局稳定和中华民族的前途命运,应该引起我们的警醒和重视。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势下民族史教育体系的对象,包括汉族在内的中华各民族,不再重点针对汉族或者其他少数民族。民族史教育应融入“中华民族”历史性的整体宏大视野,中华民族的历史进程,是各个民族互相融合、共同奋斗、开拓进取的历史。近代以来,中华民族在遭受外侮的情况下历经磨难,团结一致,勇敢抗击侵略者,维护了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延续了民族和历史的血脉传承。共通互融、血脉相连、难以分割的民族间的历史和文化记忆构成了中华民族共同体理念坚实的思想基石。因此,要基于家庭-社会-国家三重维度的整体性考量,这意味着民族间的真正融合的推动需要汉族与少数民族以及少数民族之间真正的尊重和了解,包括从政治、经济、文化、语言等层次和方面去思考和作为。少数民族要了解汉族,汉族也需要了解少数民族,过去过于强调少数民族要去学习和融合汉族文化、而汉族似乎不用去过多了解少数民族文化、一般也不需要刻苦学习某种少数民族语言的教育趋势和压力会造成少数民族难于消除的不平等心理,民族间融合难以达成,反而加大隔阂,损害民族团结大局。因此,融入“中华民族”的整体性视野,才能尊重差异,包容多元,提升民族共识。
(二)以传统文化滋养民族史教育的动态发展
“文化是民族的重要特征,是一个民族长期的共同生产和生活的产物,是维系一个民族生存、延续的灵魂和血脉”[4]。民族文化,“是指各民族在历史实践中所创造的具有本民族历史特点的物质文化和精神文化的总和。”[5]中国的传统文化多元化,是在吸收各周边各民族地区的文化因素,逐步形成一个动态的体系并在时间的推移中又向周围传播的历程,周而复始的影响和被影响。
中国作为一个传统的多民族国家,各地区少数民族在各自的生存和发展中贡献了作为整体的中华民族历史文化的价值和内涵,充实了中华传统文化的宝库,是各民族联结的纽带和血脉。比如壮族的壮锦文化、满族的旗袍文化、傣族的泼水节文化等等,绚丽缤纷,多姿多彩,通过不断挖掘、书写、传播各民族传统文化,展示中华各民族在历史进程中缤纷多彩的生活方式、风俗习惯、精神理念、审美趋向,凸显时代变迁中各民族文化的交融和升华,滋养民族史教育的动态发展,才能让民族史教育更贴近人心,获得情感升华和理念认同。
(三)以“文化自信”引领民族史教育体系创新
文化自信,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对自身文化的高度肯定和认可,包含强烈的文化归属感和价值认定。影响民族意识形成的诸多因素中,历史/文化根源是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项。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重要讲话中明确提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并阐明“文化自信,是更基础、更广泛、更深厚的自信”[6]。民族史教育的内在模式创新,依托于强大的中华传统文化渊源;而完成对中华传统文化自身的高度肯定,弘扬文化自信,也赋予民族史教育最持久最深厚的创新动力。以中华文化自信为核心,构建民族史传承体系的创新基点,进而带动整体民族教育保持长久的生机和活力,前提必须强调各民族文化的平等。
以“文化自信”引领民族史教育创新的重大意义,包含以下三个维度:其一,通过书写和传达中华传统历史文化的深厚积淀增强中华民族成员的民族自豪感,培育坚定的爱国和爱乡情愫;其二,通过传承理性、和谐、客观、公正的民族历史观,形塑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和价值观自信,提升全体民族成员的民族团结理念;其三,通过推动中华传统文化由国内至世界的展示和传播,提升全体公民的中华文明全球意识,增强中华民族国家的话语力量。
结 语
“现代中华民族观念的形成和演变,思想论证和社会接受,凝聚着作为现代国民的中国人之整体认同的政治文化底蕴与时代精神走向。在新时代,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更需要深化和强化这一政治性和文化性蕴含”[7]。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深化民族团结教育,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加强各民族交往交流,促进各民族像石榴籽一样紧紧抱在一起,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8]。在中国这样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史书写和民族史教育是一个重要并且敏感的话题,涉及各少数民族的文化心理和接受视阈,更是关系到各民族和谐稳定的大局。要真正促进民族间互动和团结,“其主导力量来自自上而下的国家建构,也源自自下而上的民族社会垒砌”[9]。教育作为最为关键的社会意识培育和社会文化传播途径,承担着重大的历史和现实责任,“教育将面临如何促进一体化和多样化协调统一的问题”[10];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念赋予了民族史教育新的使命和职能,我们应该在遵循中华各民族多元一体基本格局上,挖掘民族史教育发展的内在良性互动规律,积极倡导各民族平等的历史抒写局面,让各民族文化同力发光;在相互尊重和理解的民族史教育中真正凝聚民族共识,才能集全民族之力,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完成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