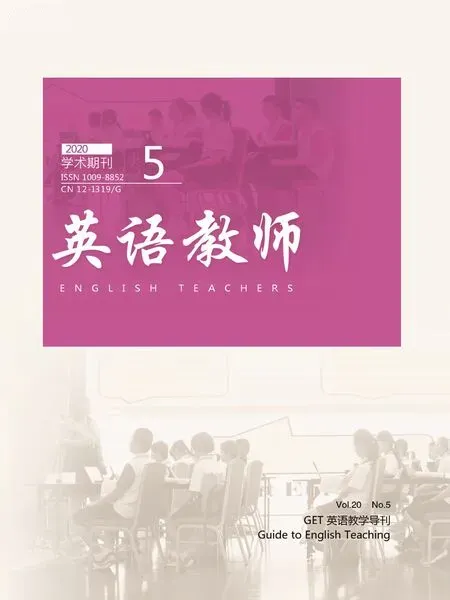语言与思维关系研究:回顾与展望
冯雪勤
引言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研究可以追溯到古希腊哲学家柏拉图提出思维即无声的语言:“我有一个想法:心灵在思想的时候,它无非是在内心里说话,在提出和回答问题……我认为思想就是活动,判断就是说出来的陈述,只不过是在无声地对自己说,而不是大声地对别人说而已。”从古至今,人们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的好奇与探究从未停止过,各个历史阶段语言学家尝试从不同的角度去探索。哈曼和赫德(Hamann&Herder)认为语言是思维的起源,不同语言国家的人有不同的国魂,反映在语言中各自独特的思维方式。洪堡特(Humboldt)通晓梵语和巴斯克语,他把语言看作一个独立的系统,语言编码了独特的世界观,即“每种语言都围绕着它所依附的人画一个圈”,人只有学习其他语言,才能跳出“语言圈子”。洪堡特的语言观影响了爱普斯坦(Izhac Epstein)、维果茨基(Vygotsky)、博厄斯(Boas)等人。博厄斯的学生萨丕尔(Sapir)也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进行了论述,沃尔夫(Whorf)继续发展了萨丕尔的思想,经后人整理,他们的理论观点被称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Sapir-Whorf Hypothesis)。然而,该假说的发展并不顺利,在20世纪80年代之前,它一直遭到很多学者的批评和抨击。20世纪90年代,随着语言多样性的迅速增长,双语研究领域得到巩固,人们才开始慢慢认可该假说的价值。
已有研究中对母语和思维的关系的研究和讨论较多,本文仅从双语或多语言角度探讨二语与思维的关系。究其原因,一是人类没有统一、确切的证据证明到底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二是双语理论不再把焦点放在语言与思维的孰先孰后上,而是研究双语者对于多语言的在线思维加工,语言在哪些方面影响思维,且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以及语言与思维的双向互动。
一、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单语视角
单语视角就是人们从一个单一语言内部或广泛抽象的视角考虑语言是如何影响思维的,如语言如何影响非语言的认知。在单语言的框架下进行研究的语言学家主要有洪堡特、维果茨基、皮亚杰、萨丕尔和沃尔夫。洪堡特曾说:“如果语言能够决定思维,那所处同一语言或语境下的人都该具有同样的思维方式了。”维果茨基(2010)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讨论了语言与思维的内在本质联系,以及思维和语言的发生学根源,即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皮亚杰根据儿童思维发展的变化,站在历时的角度考察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这些理论阐述都没有从跨语言的角度分析语言与思维,而是探讨其辩证关系,到底是语言决定思维,还是思维决定语言。
(一)早期研究
受洪堡特思想的启发,第一个对多语言和思维进行学术研究的是爱普斯坦。他指出,“每一个国家都有一种特殊的、有特点的方式,将事物及其性质、行动和关系进行分组,以命名它们”。他认为双语者的思维过程由于要激活不同语言而放慢,还总结出“多语者是社会残疾”。对双语者持消极态度的还有奥托·叶斯柏森(Otto Jespersen),他认为儿童学习两种语言不会像只集中学习一种语言那样学得好,或许在表面上说话像本族语者,但他不能掌握语言的要点。洪堡特和波捷布尼亚(Potebnya)的语言与思维观影响了苏联学者,受其影响最大的是发展心理学家维果茨基,他在回顾了爱普斯坦等人对双语的负面影响的观点基础上,总结道:“对待多语现象的积极方法是进行合适的教育,多语现象和思维的复杂关系问题需要进一步的实证研究。”此时的维果茨基可以说是第一个尝试突破“双语限制思维”的牢笼的人,至少他认为可以摆脱这种限制。
(二)萨丕尔—沃尔夫假说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提出已有近百年的历史,该理论的提出引起了语言学界和心理学界的争论。萨丕尔—沃尔夫假说主要有两方面,即语言决定论和语言相对论。最初的理论是语言决定论,即语言决定非语言的思维,思维无法脱离语言而存在。人们对该假说一直存在误读,资料记载,萨丕尔和沃尔夫并没有提出过理论假设,这只是他们的学生后来整理他们的工作而总结出来的。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是由语言人类学家哈利·霍衣哲(Harry Hoijer)于1945年首次提出。萨丕尔当时跟着博厄斯学习,在哥伦比亚发表了他的论文The status of linguistics as science,认为人类在客观世界与社会活动中并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被表达他们社会的媒介——语言所支配。这段表述很容易使后人把语言决定论归于萨丕尔。沃尔夫在耶鲁大学跟着萨丕尔学习,他也把学习外语当作一种超越自己原有范畴的方式,只有这样,人们才能摆脱长期以来的俗套,因为外语就像是立在人们面前的一面镜子。
当时,人们推崇的是单语文化,认为双语会阻碍人的思维发展,拖慢思维的运行速度。因此洪堡特、萨丕尔和沃尔夫受到很多抨击和打压,认为语言相对论思维不清晰,缺乏严谨性,甚至是不道德的。萨丕尔—沃尔夫假说认为人的思想是由语言提供的范畴所决定的,其较弱的版本——语言相对论,认为语言之间的差异导致了说话者思想之间的差异。20世纪80年代,人们形成了一种共识,这种共识是由支持“自由思想”的政治气候形成的,却对语言多样性持敌对态度。人们对于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批判甚至比褒扬的声音更多(Aneta Pavlenko 2014)。
(三)维果茨基和皮亚杰的争论
维果茨基和皮亚杰围绕内部言语(无声思维)和外部言语(有声思维)对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展开研究。维果茨基(2010)在《思维与语言》一书中提到,要深入研究语言和思维,就要探索超越语义方面的内部言语。他认为,如果不能清楚地理解内部言语的心理本质,那么就无法理解思维和言语关系的复杂性。关于内部言语,最初似乎被理解为言语记忆,如默诵一首牢记心中的诗。在这种情况下,内部言语和有声言语的区别仅仅像一个物体的观念或意向与实际物体的区别。缪勒(Muller)认为内部言语是“言语减去声音”,或者“次级有声言语”。贝特列夫(Bekhterev)把内部言语界定为其运动部分受到阻碍的言语反射。皮亚杰认为内部言语为从外部带进来的和社会化一起形成的新东西,而维果茨基称其为自我中心言语发展的结果。
皮亚杰认为学前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是思维的工具,7—8岁以后自我中心言语消失,变成社会化言语。思维发展的路线是从我向思考言语过渡到社会化言语,从主观的胡思乱想过渡到关系的逻辑性。维果茨基则认为言语的主要功能(不论是儿童的还是成人的)是交流,也即社会学接触。因此,儿童的最初言语基本上是社会的。起先,它是多功能的,后来开始分化。思维发展的路线应当是从社会思维到个人思维,这与皮亚杰的言论相反。维果茨基还提出了语言上的种系发生学和个体发生学。种系发生学是指把人类当作一个物种来看语言和思维发生的根源,如黑猩猩,它有声音,却和思维没有联系。也就是说,它的有声言语发展中有一个前思维阶段。按照种系发生学原理,人类也必定经历过一个有思维但没有语言的阶段。个体发生学是指单个人的发展过程的研究。
皮亚杰是第一个注意到儿童自我中心言语并看到它的理论意义的人。他认为儿童的自我中心言语是儿童思维的自我中心主义的直接表述,是介于儿童思维的初级我向思考和逐步社会化之间的一个中间阶段。但随着年龄的增长,自我中心言语被社会化逐步取代,走向消亡。维果茨基则持和皮亚杰相反的观点,他认为自我中心言语是逐渐增强的,发声减少,逐步转化为内部言语。内部言语为个体自身的言语,而外部言语则为他人的言语。外部言语是思维向言语的转换,是思维的具体化和客观表现。而对于内部言语,该过程被颠倒过来:言语转化成内在思维。所以,它们的结构必然不同。
这一时期的研究是站在历时的角度,研究语言与思维的发生、起源,从幼儿到成年时期思维和语言的变化。这些研究尝试从生物发展的视角来研究,究其本质,还是在探讨是先有语言还是先有思维,是语言影响了思维还是思维影响了语言。
二、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双语视角
(一)什么是双语视角
双语视角即把语言与认知的关系放在跨语言的视角去理解和研究。主要考虑双语者或多语言者的思维变化,即他们是如何加工不同的语言的;双语者的思维和单语者有何不同;考虑到不同语言对世界范畴的认知划分是有差异的,他们是如何在不同的范畴之间转换的。在语言与认知发生双语转向后,人们对洪堡特、萨丕尔和沃尔夫的思想观点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从抵触、批评到赞同、继承和发展。同时,对于二语和思维的关系的研究也逐渐丰富起来了。
(二)双语转向的萌芽期
洪堡特曾说,“一个人会把他原有的世界观、说话习惯映射到另一种外语上”,这是一种跨语言的观点。安尼特帕·弗兰克(Aneta Pavlenko,2014)认为这句话会成为下个世纪双语现象研究的基础之一。洪堡特的思想理论从一开始就是为双语或跨语言准备的,但是在20世纪初双语或跨语言研究并不受欢迎。维果茨基在学习了洪堡特的理论之后对双语并不排斥,认为多语言和思维的关系需要进一步探讨,然而他也没有大力支持双语思维的积极作用。
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出现只是语言与思维关系历史中的一个插曲,但这个小插曲是人们从单语视角看待语言与思维关系转向双语视角的桥梁,且其旋律延绵至今。正是因为对语言相对论的探讨,人们才意识到了双语或多语与思维的关系存在的研究空缺,把该假设应用到二语和思维的关系中,发掘该假说新的价值。
研究者埃尔温(Susan Ervin)和奥斯古德(Osgood)在这一时期提出了术语:并列双语者(coordinate bilinguals)、混合双语者(compound bilinguals)和从属双语者(subordinate bilinguals),并把它们和语言学习历史相联系。埃尔温和奥斯古德提出只有并列双语者能够提供真正意义上的、跨文化的翻译。埃尔温随后做了实证研究,受试者为日—英双语者和法—英双语者,利用同一套材料对受试者进行两次测试,每六周用各自的语言进行一次测试。结果表明,测试反映的内容随受试者语言的变化而发生转变。来自加拿大的兰伯特(Lambert)和其同事发现,并列双语者比混合及从属双语者的对等翻译存在更大的语义差别,翻译起来比另两种双语者更为困难。麦克纳马拉(Macnamara,1991)把语言相对论与双语能力相联系,认为如果沃尔夫的理论是正确的,那么双语者只有满足以下其中一个条件才能符合语言相对论:一是当用A语言或B语言说话的时候,用A语言去“思考”,结果B语言的人无法理解;二是用一种不适合两种语言的混合的方式去“思考”,冒险不去理解任何一种语言或者不被任何一种语言理解;三是根据不同语言的变化,思维也发生转变,因此他们无法很好地与自己交流,更不用说把一种语言翻译成另一种语言。
这一时期的研究已经开始慢慢转向双语和跨语言,只是人们还没有意识到多语言的发展已经迫使他们不得不跳出单语的束缚。直到1980年和1990年两篇奠基性文章的问世,双语研究领域的地位才开始得到巩固。人们逐渐意识到“单语言”理论在解释双语和多语者认知加工方面的局限性——双语和多语思维需要自己的理论。语言相对论聚焦于不同语言之间的结构差异,一些现代学者称不能把语言归结为结构。因此,他们不再局限于研究不同语言的语法结构差异,而是超越对萨丕尔—沃尔夫假说的传统理解的界限,并设想语言可以在很多层面上影响思维。
(三)新时期的二语和思维关系研究
新时期人们对于双语者和多语者思维的研究不断增多。思维的定义包括两个方面:一是思维的内容,即说话者对世界的概念;二是思维的加工过程,如注意力、记忆和推理。事实上,很有可能只有双语者才直接经历了语言相对论的影响。为了了解这些影响,更应该多关注双语者。近阶段对于跨语言和思维的研究更多的是以时空思维和隐喻性语言为切入点。
1.二语学习影响思维
首先,在范畴认知层面。学习者所接触到的二语或许比自己的母语在某些范畴层面划分得更加细致、全面或概括。那么,双语者在习得二语之后思维会发生怎样的变化呢?二语是否会对他的母语概念范畴造成影响呢?研究者阿萨纳苏拉斯(Athanassoulas)称新范畴的学习会使双语者对原有范畴进行重组。维维安·库克(Vivian Cook)称双语者表现出一种中间模式,在认知中同时保留两种范畴(Benedetta Bassetti&Vivian Cook 2011)。贝内德特·巴西特(Benedetta Bassetti)认为二语使用者存在单概念场景和双概念场景,如关于午餐(lunch)概念的认知。英语中的“午餐”一词最相关的食物是三明治和薯片,而意大利的“午餐”一词则倾向于指主食和肉类。研究发现,一部分英语—意大利双语者在讨论午餐时想到的是三明治和薯片,另一部分想到的是主食和肉类。英语为母语的意大利语初学者在讨论午餐时更倾向于三明治和薯片,而水平较高的意大利语学习者则会想到主食和肉类。意大利语的蓝色分为深蓝和浅蓝,英语的蓝色只用一个词来概括。在双概念场景中,二语使用者有两种分开的概念,说不同语言时会有不同的思维方式。二语者说英语时,午餐就对应三明治和薯片,而说意大利语时,对应的是主食和肉类。同样,用意大利语说蓝色时,思考的是深蓝;而说英语时,思考的是浅蓝。
其次,在时间思维层面。从20世纪末开始,一些研究者不再用传统的眼光看待语言与思维的关系,而是在承认二者相互关联的双向关系的前提下,研究语言与思维在同一时刻的联系,即从共时角度来研究语言与思维之间的关系。21世纪以来,西方语言学流派开始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考查语言与思维的关系,如波诺迪斯基(Lera Boroditsky 2001)、陈振宇和帕得里克(Jenn-Yeu Chen&Padrdaig,et al.2013)、富赫曼和麦考密克(Fuhrman&McCormick,et al.2011)等从时间思维方式入手研究语言对思维的影响,运用心理学的启动刺激(priming)原理研究受试者对不同排列方式的时间事件的反应时间。启动刺激是指由于之前接受某一刺激的影响而使得之后对同一刺激的知觉和加工变得容易的心理现象。通过不同母语者对时间的隐喻性表达,以及在实验中对于时间事件发生前后呈现的方式的反应时间,得出不同的时间思维倾向性的结论。在汉语普通话中,除了使用“前/后”之外,讨论星期、月份和学期等时习惯用“上/下”来表示。英语时间表达是单线型的,呈现水平不对称的轴线分布,而汉语时间表达则是复合型的,有水平和垂直两个方向。富赫曼和麦考密克等(2011)在实验中考查了不同水平的汉英双语者,在母语为英语、二语为汉语的一组结果中发现,汉语水平高的英汉双语者垂直时间思维倾向更像汉语母语者。由此可见,二语者的时间思维会受到第二语言的影响。
2.思维影响二语加工
国内研究发现,思维对语言也存在反作用,尤其是对二语的加工处理(杨文星2015)。母语作为第一语言,对思维习惯有着长久深远的影响,是第二语言不能替代的。杨文星、文秋芳(2017)称思维方式影响语言加工。这里的思维方式不只局限于母语思维,也包括二语思维。人类在使用语言时会受其思维方式的影响,为了适应这一语言而转变思维方式。母语加工会受思维方式的影响,二语加工同样也会受思维方式的影响。
3.隐喻性语言与时间思维的关系
陈光明(2017)的实验采用非正式访谈形式对受试者表达时间事件时所用的手势语进行采集,发现人们的认知加工和隐喻性语言并非完全一致。比如,汉语中垂直的时空隐喻方式,受试者在说“上个星期”的时候,他的手势也会指向左;而英语母语者的手势和英语中的时空隐喻方向一致,呈水平轴线分布。然而,英语受试者在回答汉语问题时则表现出典型的汉语认知模式。由此可以得出,母语构建了惯性思维模式,而第二语言的学习也会影响思维和认知。
三、总结
从古至今,人们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慢慢揭开了其神秘的面纱,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也不断加大。研究视角从单语到双语,研究方法从哲学辩论到实证研究,通过控制变量使研究更加科学严谨(杨朝春 2015)。人们越来越以审慎、客观的态度来看待二者的关系。思维是一个抽象概念,想要把它具体化来看其与语言的关系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但是各个研究领域在不断地寻找新的突破点。
语言与思维的关系从单语转向双语的研究视角,不仅促进了双语理论的发展,还使沃尔夫的语言相对论焕发了新的活力。新时期语言与思维关系的研究摆脱了单语的束缚,以实验法对比研究不同的语言及双语者的第二语言习得,呈现出更强的跨语言、跨学科趋势(陈佳 2011)。本研究通过分析语言与思维的发展历程及最新发展趋势,希望能够深化对语言与思维关系的认识,未来可以从更多创新的角度去研究语言、研究人的思维与认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