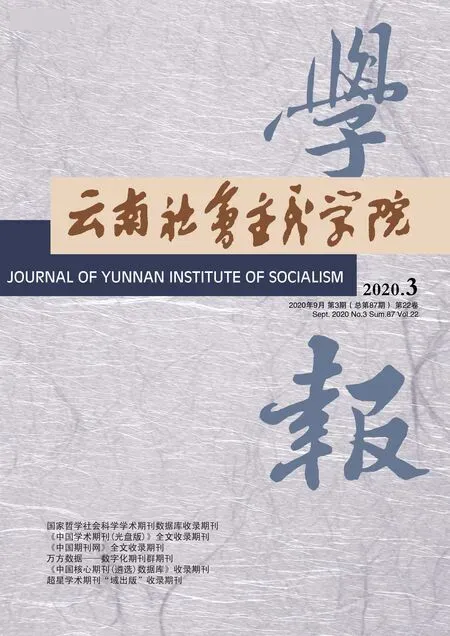为国而歌:人民音乐家聂耳的战斗青春
朱家麟
(云南省社会主义学院,云南 昆明 650031)
聂耳(1912—1935),原名聂守信,是中国近代著名的音乐家。聂耳祖籍云南玉溪,出生于昆明。18岁以前,除了曾到湖南郴州短暂参军,他一直生活在昆明。1930年,聂耳来到上海,开始短暂而辉煌的音乐创作生涯。聂耳短暂的一生中创作的37首乐曲,全部创作于其人生的最后四年,其中就包括被选定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
来到上海之后的短短五年时间里,聂耳从业余音乐爱好者成长为优秀的人民音乐家,从青涩的热血青年成长为成熟的中共党员。研究聂耳最后五年的活动轨迹,对于我们认识聂耳的革命思想和音乐成就,了解其作品诞生的时代背景和思想基础,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一、在艰苦岁月中走上音乐道路
1930年7月,18岁的聂耳从云南省立师范毕业。由于有人告密,国民党当局知道了聂耳在校期间加入共青团并组织革命活动的事,开始对他进行监视并准备逮捕。为了躲避风头,他的三哥聂叙伦决定让他代替自己到上海远东皮毛公司开设的“云丰申庄”工作。
7月10日,聂耳匆忙乘火车离开昆明,这一走就没能再回来。当时,从昆明到上海没有直达火车,乘客只能先从滇越铁路到越南海防,从那里乘船前往香港,再从香港换船前往上海。7月18日,聂耳到达上海,按原定计划开始在“云丰申庄”当店员。
此时的聂耳,为了糊口,每天做着繁重的工作。当时,聂耳没有接受过系统的专业音乐教育,也没有多少人相信他能在人才济济的大上海走上职业音乐创作的道路。然而,不管条件如何艰苦,聂耳从来没有忘记他的音乐梦想。
(一)自幼与音乐结缘
据三哥聂叙伦回忆,聂耳从小就对音乐感兴趣。他们家住在端仕街的时候,邻居中有一位姓邱的木匠师傅,平时很喜欢吹奏短笛,年幼的聂耳经常听得入神,并跟着曲调反复哼唱。邱师傅知道后,主动教聂耳吹笛子,并成为他人生中的第一个音乐老师。
就读昆明县立师范附小、私立求实小学、云南省第一联合中学和省立第一师范学院期间,聂耳在刻苦学习文化知识的同时,还利用校内外各种学习机会掌握了简谱和五线谱,先后学会了演奏二胡、三弦、月琴、铜号、扬琴、笙、古筝、小提琴、钢琴等中西乐器,甚至还接触到了《国际歌》《伏尔加河》《马赛曲》等革命歌曲。(1)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北京:人民出版社,2019年,第152—153页。
在音乐方面,聂耳除了勤于学习,还有很强的表演热情。根据当时留下的资料,从高小(当时的学制把小学分为“初小”和“高小”两个阶段)开始,聂耳就开始利用课余时间参加学生乐团,除了在校内演奏,还经常到翠湖、文庙、大观楼等昆明市内人员较为集中的场所公开表演。除此之外,聂耳和二哥聂子明、三哥聂叙伦还组织了家庭小乐团,除了在自家铺面表演,他们还经常带着乐器到西山、圆通山、金殿等风景名胜演奏,所到之处,行人纷纷驻足聆听。
就这样,在昆明的18年里,尽管聂耳没进过专业的音乐院校学习,却在不断的学习实践中充分发展了他的音乐才能,还通过音乐接受了革命思想的熏陶,为他日后成为一名优秀的人民音乐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二)在初到上海的艰难岁月中发掘音乐天赋
1930年7月,刚到上海的聂耳在“云丰申庄”当店员。按商号当时的规定,工作的第一个月没有工资,只提供食宿,每天的工作时间长达十小时以上。在这种艰难困苦的条件下,聂耳依然没有忘记他的革命理想和音乐理想。
到达上海仅3个月,聂耳就通过云南老乡的关系加入了中共地下党领导的“上海反帝大同盟”,再次投身到革命的洪流中。同时,通过接触革命文艺作品和阅读相关论文,他对于艺术的“大众化”也有了新的认识。(2)《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1年,第276页。
聂耳也把热爱读书学习的习惯带到了上海。在“云丰申庄”工作几个月之后,他每月终于有了15块钱的津贴。工资一到手,他马上就用来买书。为了更好地学习国外的先进文化,聂耳一直重视外语学习。就读云南省立师范期间,他除了主修英语,还选修了日语。到上海后,他又买了《日语读本》《英语周刊》等书籍,继续坚持自学。
当然,聂耳最热衷的还是学习音乐。1930年底,他有了一些额外的收入,马上买了丰子恺的《音乐入门》等书籍,还买了一把廉价小提琴,每天坚持自学,努力提高自己的音乐水平。
但这样的日子没能持续多久,1931年3月29日,“云丰申庄”倒闭,聂耳失业了。为了生存,他只能四处求职。4月1日,凭着对音乐才能的自信,聂耳参加了“联华影业公司音乐歌舞班”的考试,面试官是当时的著名音乐人、被后人称为“中国流行音乐之父”的黎锦晖。根据黎锦晖之子黎泽荣回忆,聂耳在初试时非常紧张,演奏小提琴频频出错,但黎锦晖还是给了这个年轻人复试的机会。(3)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10页。4月8日复试时,聂耳的表现有了明显提高,终于被歌舞班录取。1931年4月22日,聂耳进入联华歌舞班,取艺名“聂紫艺”,正式走上了职业音乐人的道路。
虽然聂耳从小自学乐理知识和乐器演奏技能,并积极参加音乐活动,但由于没有受过专业音乐训练,刚进入联华歌舞班时他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据黎泽荣回忆,为了帮助聂耳提高小提琴演奏水平,黎锦晖安排歌舞班的首席小提琴手王人艺来教他。王人艺虽然比聂耳小半岁,在指导聂耳练习时却毫不含糊,要求非常严格。由于聂耳乐理基础不牢,听不懂专业术语,经常招来同龄老师的严厉批评,但他并不因此气馁,反而加倍努力学习和训练,每天在工作之外还要练琴8小时以上,甚至在患病时也坚持不辍。(4)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11页。正是在这个时期,他开始在日记中使用“聂耳”这个名字。
聂耳的辛苦付出很快得到了回报。由于小提琴演奏技艺突飞猛进,进入歌舞班第二年,黎锦晖就将他升格为正式登台的小提琴手,在王人艺到北平养病和学习期间,更让他担任乐队首席小提琴手。根据现有资料,聂耳最初的音乐作品,如口琴曲《圆舞曲》和歌舞曲《天伦之爱》等,正是创作于1932年初。(5)《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上卷),第256页。
1932年3月,联华影业公司精简机构,歌舞班脱离公司组建明月歌剧社,聂耳担任负责音乐研究股的执行委员。至此,聂耳终于在竞争激烈的大上海站住了脚,也在音乐道路上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二、在革命斗争中成长起来的人民音乐家
凭着出色的天赋和超乎常人的努力,没有受过一天音乐专业训练的聂耳在来到上海短短一年半的时间里就成长为一名优秀的职业小提琴手。然而,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内忧外患、民族危机日益深重的紧要关头。中学时代就加入共青团、积极参与爱国学生运动的聂耳,在急剧变化的大环境下,不能更不愿“两耳不闻窗外事”,完全沉浸在自己的音乐世界中。正是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思考,影响了聂耳的音乐和人生道路,让他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音乐家。
(一)在学艺道路和革命实践中完成自身为人民创作音乐的思想转变
聂耳能在初试表现不理想的情况下入职联华歌舞班,得益于黎锦晖的慧眼识珠;能在短时间内成长为歌舞班的首席小提琴手,也离不开黎锦晖的青眼有加。对于音乐底子薄,在上海又人生地不熟的聂耳来说,黎锦晖无疑是他的恩师与伯乐。聂耳从小就很喜欢黎锦晖创作的儿童歌舞剧,与之合作共事后更是对其尊敬有加。亦师亦友的两人一度关系融洽,经常在一起畅谈对个人发展和中国音乐的思考。
随后,日军在上海制造了震惊世界的“一·二八”事变,深重的民族危机和人民高涨的爱国热情都让身在上海的聂耳受到了很大震动,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的人生观和艺术观。他在日记中写道:“所谓classic,不是有闲阶级的玩意儿吗?一天花几个钟头苦练基本练习,几年,几十年后成为一个violinist又怎样?你演奏一曲贝多芬的《Sonata》能够兴奋起、可以鼓舞起劳苦群众的情绪吗?”(6)《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392页。由此,他继续苦苦思索如何用音乐表达劳苦大众的呼声和中华民族解放的主题。
1932年4月21日,聂耳第一次与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负责人田汉会面。当时的两人也许不会想到,彼此的合作会成就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品。相近的革命理想与艺术理念很快让两人产生了惺惺相惜之感,成为了忘年之交。与此同时,明月歌剧社在南京、武汉等地的公演由于不能反映高涨的抗日爱国热情和表演不够纯熟等原因失败了。因此,聂耳更加积极地参加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各种活动,他的革命音乐理念与黎锦晖的平民音乐理念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
聂耳开始用“黑天使”等笔名在各大报纸杂志上发表一系列评论文章,主张艺术应该服务于人民大众的革命和救亡事业。7月22日,他发表在《电影艺术》第3期上的《中国歌舞短论》一文,将矛头直指黎锦晖,批评其在民族生死存亡紧要关头仍然坚持“为歌舞而歌舞”的理念,尤其是为了经济收益而迎合市民阶层的低级趣味。(7)《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4页。由于文中部分言辞比较激烈,这篇文章最终导致聂耳与黎锦晖师徒关系决裂,也让聂耳被明月歌剧社大多数成员孤立。8月5日,明月歌剧社召开全体会议;8月7日,聂耳乘船离开上海前往北平;8月10日,明月歌剧社在《上海时报》刊登启事,声明聂耳已经“因故退出本社”。(8)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15页。
(二)在共产党的影响下走上人民音乐创作的高峰
1932年8月11日,聂耳到达北平,住进云南会馆。通过省立师范同学张天虚,聂耳又结识了陆万美、许可、于伶等中共党员和左翼艺术家。在北平,聂耳同样积极投身左翼文化运动,观看了北平左翼戏剧家联盟组织演出的《血衣》《战友》《九一八》等进步剧目,积极参与北平左翼音乐家联盟的组建。10月28日,他还在清华大学毕业同学会组织的给东北抗日义勇军募捐的晚会上用小提琴演奏了《国际歌》。(9)《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10页。
9月,聂耳报考国立北平大学艺术学院,可惜未被录取。不久之后,他从朋友来信中得知联华影业公司有意请他回去工作,于是马上向党组织汇报了准备返回上海的事。此时,中共正准备与国民党当局争夺电影这块新兴的文化阵地,刚刚在瞿秋白领导下在上海成立了电影党小组,正设法派一些左翼剧联成员到各大电影公司。北平的党组织马上批准了聂耳的请求,并请他将三份材料转交上海党组织。
11月8日,聂耳结束了短暂的北平生活,返回上海。回到上海后,他马上找到党组织,向夏衍转交了三份材料。12月26日,聂耳到联华影业公司一厂工作,据他的日记记录,他最初从事的是剧务工作。这一时期,聂耳与夏衍、田汉等中共党员及任光、安娥等左翼音乐家积极联络,研究讨论发展大众化音乐和成立音乐研究会的事。
根据赵铭彝、夏衍等当事人回忆,1933年初,经赵铭彝、田汉介绍,聂耳正式加入中国共产党。入党宣誓仪式是在联华影业公司一厂的一个摄影棚举行的,当时的条件比较简陋,因为没有现成的党旗,只能临时在纸上画一面。(10)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25页。出于安全和保密方面的考虑,聂耳本人并未在日记中留下任何相关记录,使得后人无从了解他当时的心情,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憾事。入党以后,聂耳在党组织的直接领导下,以更加饱满的革命热情投入到音乐创作中,为我们留下了数十首经典的音乐作品,也为中国音乐开创了一个属于无产阶级与革命群众的新时代。
1933年,聂耳创作了《开矿歌》《饥寒交迫》和《卖报歌》,这是他最早公开发表的三部音乐作品。到1934年,他的创作开始井喷,短短一年内创作了19首歌曲,其中不乏《翠湖春晓》《金蛇狂舞》《码头工人》和《毕业歌》这样的传世名曲。
除了忘我地进行音乐创作,聂耳也没有减少参与革命活动的次数。1933年,在中共党组织的指导帮助下,上海的左翼文艺工作者先后成立了“中国电影文化协会”“中国新兴音乐研究会”和“苏联之友社”等组织,聂耳都在其中担任了重要职务。此外,聂耳还经常通过具有工会性质的联华影业公司同人会,带领同事与资方势力进行斗争,旗帜鲜明地反对其反动的制片方针。由于这些斗争活动,聂耳成了联华影业资方的眼中钉,终于在1934年1月找借口将他解雇。4月,在左翼戏剧家联盟的安排下,聂耳进入上海百代唱片公司,负责录音和作曲。(11)昆明文史研究馆编:《聂耳——从昆明走向世界》,第227页。
在短短两年的时间里,通过大量的艺术创作实践活动和革命斗争的洗礼,作为青年革命者和作曲家的聂耳快速成长起来,创作了大量为劳苦大众呐喊的音乐作品,成为了一名真正的人民音乐家,为他的最高杰作《义勇军进行曲》的诞生奠定了思想基础和音乐基础。
三、为国而歌、为民族呐喊
1934年,聂耳的音乐生涯迎来高潮,在作品数量井喷的同时,其革命性和艺术性也达到了新的高度。然而天妒英才,正当音乐创作渐入佳境,准备向更高的目标前进时,聂耳却在异国海滨意外亡故,年仅23岁的生命戛然而止。然而,正是在人生的最后一年,聂耳完成了个人生涯乃至中国近代音乐史上最重要的作品。
(一)聂耳短暂人生的音乐创作巅峰
1934年春,为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协助左翼文艺工作者成立了上海电通影片公司,田汉、夏衍、许幸之等地下党员在公司担任要职,聂耳也为公司创作歌曲。由聂耳作曲、田汉作词的《毕业歌》,是电通公司第一部影片《桃李劫》的主题歌,其很快就成为当时脍炙人口的歌曲。
同年秋,面对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侵略活动的加剧,田汉创作出了《风云儿女》的故事梗概。这是一个描写青年知识分子受到革命思想影响,从个人的艺术世界走向民族救亡战场的故事。这个故事由夏衍写成电影剧本,于1935年1月开机拍摄。写完故事梗概后,田汉马上着手创作电影片尾曲,而聂耳在听到消息后马上主动要求承担谱曲的工作。这首歌曲,就是今天每个中国人心中神圣的国歌《义勇军进行曲》。
《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的过程充满波折。田汉刚写出第一段歌词,就于1935年2月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聂耳和《电通》画报的主编孙毅师对歌词进行了一些修改,其中“冒着敌人的炮火,前进”就是这次改动的结果。由于工作繁忙,聂耳大约到3月才正式开始《义勇军进行曲》的谱曲工作,但他刚完成初稿,就在4月1日得知国民党当局要逮捕他的消息。(12)《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63页。
为了保护聂耳,同时满足他本人出国学习深造的愿望,党组织决定安排他尽快出国。4月15日,聂耳带着还没完成的《义勇军进行曲》,匆匆登上了日本邮船“长崎丸”号。
由于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录,相关当事人在多年后的回忆中也有相互矛盾之处,聂耳完成《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确切时间已难以考证。结合司徒慧敏、孙瑜等当事人的回忆和百代唱片公司的记录,《义勇军进行曲》曲谱的定稿应该是在4月底从日本寄回上海,于5月3日由电通公司合唱队在百代公司录音棚内演唱录音的。(13)向延生:《影片〈风云儿女〉及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第414—424页。也就是说,聂耳是在到达日本后不到半个月的时间里完成了曲谱定稿。
1935年5月24日,电影《风云儿女》上映,《义勇军进行曲》唱响上海滩。不到两个月后的7月17日,聂耳在日本神奈川县藤泽鹄沼海滨意外溺亡,《义勇军进行曲》成了他的人生绝唱。
聂耳逝世后,《义勇军进行曲》继续在中国乃至世界上传唱。在中国共产党发表“八一宣言”后,响应号召的中国文艺界把《义勇军进行曲》作为“国防音乐”的前奏。1936年6月7日,上海西门公共体育场出现了数千民众齐唱《义勇军进行曲》的盛况。
抗战全面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成为了中华民族抵御外来侵略的战歌,极大地鼓舞了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在各条战线的抗日斗争。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义勇军进行曲》更是走出国门,走向世界——美国黑人歌手保罗·罗伯逊演唱了这首歌曲,美英法印等国的广播电台经常播放该曲,以中国人民反法西斯战争为题材的好莱坞电影《龙种》也选择这首歌作为插曲。(14)向延生:《美国影片〈龙种〉与〈义勇军进行曲〉》,《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第310—311页。
抗战胜利后,《义勇军进行曲》又超越了抗日救亡的主题,成为中华民族团结一心、不屈不挠、英勇斗争、奋勇前进的爱国精神的象征,最终在632件国歌方案中脱颖而出,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
(二)聂耳的战斗青春在音乐和人民中不朽
聂耳于1935年4月15日登上日本邮船“长崎丸”号离开上海,16日经停长崎,17日下午到达神户后乘电车前往大阪,当晚10点又乘坐火车,最终于18日上午8点抵达东京。聂耳坚持记日记的习惯,让我们得以一窥这趟短暂的旅程的大致情况。(15)《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69页。
根据相关人士的回忆,按照上海地下党组织的安排,聂耳原本是计划经由日本前往意、法、德等国,最后到达苏联,一路上学习和创作。根据日记的记录,虽然日本只是此次行程的第一站,但聂耳在赴日之前还是制订了四个“三月计划”——第一个“三月计划”的重点是提高日语水平,第二个“三月计划”主要是提高阅读能力和音乐技能,第三个“三月计划”是开始翻译和创作,第四个“三月计划”主要是学习俄语准备赴欧。
聂耳到达日本后,马上就按照计划分秒必争地开始学习。他18日上午8点到东京后,顾不上舟车劳顿,马上到东亚日语补习学校听了两个小时的课。之后,他每天的日程表都安排得很满,除了听日语课、练小提琴等日常学习活动,还要广泛与日本文化界的进步人士联谊交友,大量观摩电影、音乐、话剧、舞蹈等文艺作品,学习吸收其中的优秀元素。由于太过繁忙,他甚至中断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只能不定期补记近期发生的重要事情。4月到7月,日记的篇目很少,但文中日语词汇的出现频率越来越高,说明这期间聂耳的日语水平稳步提升,掌握的词汇量越来越多。
到了7月份,日语学校开始放暑假,聂耳的第一个“三月计划”基本提前完成。在东京紧张的学习生活暂时告一段落,他准备前往离东京不远的藤泽来一次短期旅行。7月8日之后,他又恢复了每天记日记的习惯,而且日记内容也很翔实。
7月9日,聂耳与在日本认识的朝鲜籍好友李相南等人一同乘车前往藤泽,并借宿在李的同事滨田实弘的姐姐家。因着热情外向的性格,聂耳很快就和滨田一家熟络起来。之后几天,他在朋友们的陪伴下游览了江之岛等藤泽周边的风景名胜,还到片濑和鹄沼海滨浴场去游泳,为大家演奏小提琴,与收藏有很多唱片的滨田实弘聊音乐,同时用有限的时间阅读日文报纸杂志以强化日语学习。
即使是在这样轻松愉快的时刻,聂耳仍然不忘反思和自省。7月16日是原定的第一个“三月计划”结束的日子,他在日记中回顾了过去三个月的学习生活,在看到日语能力的进步之外,也检讨了小提琴练习不足、整整三个月没碰钢琴、没进行作曲等。他告诫自己要牢记来日本的原因,从第二天开始加倍努力读书和练琴。(16)《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中卷),第585页。
未曾想,这篇日记竟然成了聂耳的绝笔。第二天,年仅23岁的聂耳与李相南、滨田秀子、松崎厚等友人结伴在鹄沼海滨浴场游泳时,不幸溺水身亡,留下了未能完成的旅欧计划和不能继续用音乐报效祖国和人民的无限遗憾。
由于聂耳入境日本时未办理正式手续,中华民国领事馆拒绝了张天虚等中国留学生提出的由领事馆全权处理善后事宜的要求,在藤泽警方给出验尸报告后,当地火葬场火化了聂耳的遗体。因为这一稍显草率的善后处理方式,再加上当时已非常紧张的中日关系,聂耳被日本特务暗杀的阴谋论从那时候开始流传至今。然而,根据滨田实弘第一时间向聂耳朋友张天虚提交的报告和当时在现场的松崎厚的回忆,以及聂耳日记中关于几年内多次头部受伤导致昏迷的记录,再结合当时聂耳在日本还默默无闻的事实,向延生、崎松等研究聂耳的知名学者倾向于认为聂耳的死的确只是意外。(17)关于聂耳死因的研究,参见向延生:《聂耳死因的调查及郭沫若的墓碑文》,《聂耳全集》编辑委员会编:《聂耳全集》(下卷),第456—459页;崎松:《聂耳在藤泽遇难的死因探析》,《聂耳与日本》,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10年,第243—254页。
聂耳去世后,他的中日两国朋友首先悼念了这位热情友善的年轻人。随着《义勇军进行曲》在中国各地唱响,越来越多的人知道了这位英年早逝的人民音乐家。吕骥、夏衍、田汉、郭沫若等长期活跃在文艺战线的中共党员都高度评价了聂耳的革命精神和创作成就,肯定了他对中国人民的革命和解放事业做出的突出贡献。
聂耳去世次日,日本《朝日新闻》社会版刊登了一条短讯,通报了“民国学生聂守信”溺水身亡的消息,但其中的住址等信息有误,也未提及其作曲家的身份,可见当时日本社会对这位年轻的作曲家完全不了解。5个月后的12月21日,日本进步剧作家秋田雨雀在《朝日新闻》上发表文章,第一次向日本人介绍了聂耳的生平和音乐成就。(18)[日]齐藤孝治:《聂耳——闪光的生涯》,庄丽译,上海:上海音乐出版社,2003年,第232—234页。1954年,藤泽当地的友好人士在聂耳溺亡的鹄沼海滨自发建造了“聂耳纪念碑”,并将7月17日定为当地的纪念日,藤泽与昆明也因聂耳的因缘而在1981年缔结为友好城市。聂耳作为最著名的抗日歌曲的曲作者,得到了中日两国人民共同的尊敬和纪念。
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聂耳把满腔的爱国热情和忧国忧民的情怀化为了一曲曲慷慨激昂的乐章,这些鼓舞劳苦大众精神、激励中国人民斗志的不朽作品最终成为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图腾,激励着一代代中华儿女披荆斩棘、奋勇争先。聂耳本人在逆境中努力学习、艰苦奋斗的精神,还有他热情开朗、待人友善的宝贵品质也将留在人们的记忆中。
在新时代的今天,当我们再度回顾聂耳革命和创作的短暂一生时,应当从中汲取精神力量,继承和发扬他为国而歌的崇高爱国主义精神、不屈不挠的革命斗争精神、在逆境中不惧困难艰苦奋斗的精神和他为劳苦大众呐喊的人民音乐家情怀,学习他惜时如金、刻苦学习、努力工作的良好作风,尽己所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奋斗。
——李海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