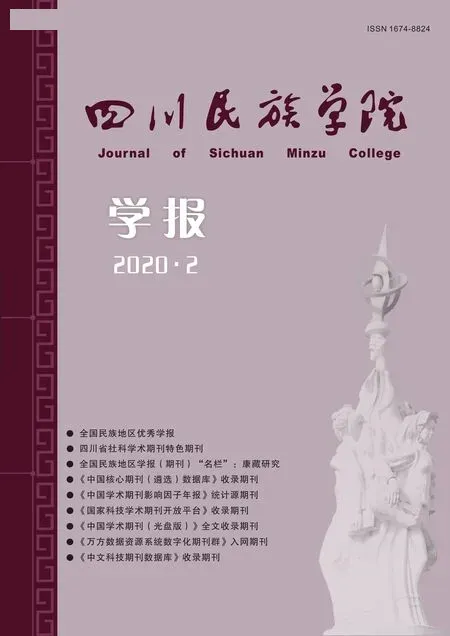从“甥舅之邦”到“兄弟一家”:“天下”视域下藏族参与华夏民族建构的理路逻辑
柳 欢 李红阳
(陕西服装工程学院 陕西西安 712046;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藏族是华夏共同体的重要组成部分,西藏自元朝开始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然而,长期以来,“元代非中国”的观点在国外学术界甚嚣尘上,对中国之于西藏地方的主权地位予以质疑。这是不顾中国历史以及文化的特殊性,单纯从西方叙事框架出发阐释中国的短视行为。华夏民族有着不同于西方民族以及西方近现代民族主义理论的深刻特殊性,对此,汪晖认为:“由于传统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帝国,历史文化传统极其多样,在这一基础上形成的‘现代中国’,并不能通过西方民族主义的知识谱系得到有效阐释。”[1]帝制中国时期关于国家建构思想的特殊性主要表现为在华夏民族中根深蒂固的“天下”观念。藏族在“天下”观念的知识图谱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总体来说,藏族参与华夏民族构建的过程经历了从政治上结盟缔造“甥舅之邦”到文化上认同结为“兄弟一家”的发展过程。
一、 “蛮夷戎狄”:“天下”观念下的中心与边缘
(一)帝制中国的“天下”观
“天下”是中国古人对于自身国家的最早阐释,对此,《诗经·小雅》提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2]315,《尚书》中也曾提到“皇天眷命,奄有四海,为天下君”[3],早期国人把“天下”作为自身故土家园的共同认知。“天下”观念认为,不仅早期夏、商、周建立国家的“中国”之地在“天下”范围之内,“四海”之内也是“天下”之“王土”;不仅以夏、商、周部族为核心的“华夏”(1)“华夏”,《尚书》释义:“冕服彩张曰华,大国曰夏”。是“王臣”,以“蛮夷戎狄”为主体的周边少数民族也是“天下”子民。《诗经·商颂》的“昔有成汤,自此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2]508,意为商代之时氐羌等“四夷”拥护商王统治,为“天下”子民。
许多学者认为,早期“天下”之中,华夏民族与“蛮夷戎狄”等周边少数民族之间的差异只有文化的差距,没有血缘、语言的不同。文化差异使得“四夷”能习中国“礼法”便可“以夏变夷”,加入“华夏”集团,反之,亦可“以夷变夏”,从“华夏”变为“四夷”。
“华夏”是长期以来各兄弟民族共同缔造的结果,各民族祖先共同谱写了多民族统一国家的宏伟篇章。在此过程中,以“蛮夷戎狄”为代称的周边少数民族对“华夏”的空间延伸多有贡献,华夏民族的发展包含着周边民族不断融入的鲜明内涵,一个又一个的少数民族合并到逐渐扩大的华夏民族之中。在此过程中,作为藏族祖先的古代羌人同样扩展了“华夏”概念的理论内涵。
(二)“羌”在“天下”中的位移
“羌”,许慎在《说文解字》中解释为“西戎牧羊人也”。“羌”属于“四夷”之西戎集团,是西戎的一支,商代指居于现在陕西、山西、河南三省交界处的“羌方”,后随着华夏地域的逐步扩大,内地羌人融入华夏集团,“羌”所指的范围不断西移,之后发展到青藏高原及其周边地带。古代羌人很早就加入了华夏民族的建构过程,《史记》记载:“禹兴于西羌。”[4]138根据司马迁的观点,作为“华夏”主脉的“夏”部族即为古代羌人的祖先,而禹为黄帝之孙颛顼之后。因而,根据这种观点,黄帝部落也存在发自西羌的必然性。对此,王明珂经调查指出,不少现存羌人认为“夏代是中国第一个朝代,而建立夏朝的大禹又是羌族,因此,羌族必定是中华民族中的核心民族,或说是最古老的华夏”[5],这种祖先记忆至今仍深刻地烙印在羌族直系后裔的记忆之中。此外,更有古代学者根据《公羊传》等史料将羌称为“姜戎”,认为羌为以“姜”为姓的炎帝部落祖先。尽管《史记》以及《公羊传》等相关记载存在后人附会古史之嫌,但“羌”属“天下”应为华夏民族祖先的共同历史记忆。
春秋战国时代特别是随着秦汉大一统帝国的形成,在“华夏”民族开发经略西部地区过程中,随着和平交流和武力征服,大量羌人支系跨过长城边疆(2)拉铁摩尔认为在中国农耕与游牧文明之间有一个中间区域,称为长城边疆,大体与200毫米等降水量线相一致。进入内地,深入参与到华夏民族的建构之中。据史料记载,公元386年羌人首领姚苌仿华夏制度,于长安自立为帝,国号大秦,史称“后秦”,姚苌为后秦武昭帝。皇帝制度为华夏政权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始创于秦朝,“皇帝”二字取自三皇五帝,自视为“天子”。“天子”为上天之子,代表“天”统治天下,“天子”思想自商代即已萌芽,“帝立子生商”[2]506即为华夏统治者确立自身正统性的关键表述。羌人政权领袖自立为“皇帝”“天子”,足见其加入华夏集团的意愿以及对华夏文明的认同。后秦文桓帝姚兴时期,大兴儒学,仿汉制设官,更加速了这支羌人集团与华夏民族整合的步伐。
远古炎、黄等“华夏”人文初祖源自西羌的史料表述以及之后羯、羌、氐等边疆民族参与华夏建构的历史事实,都是“天下”观念下,各族祖先认同华夏文化的客观依据。对这一观念的认同以及历史的惯性作用使得部分羌族与青藏高原本土古藏人融合后所形成的藏族追求“天下”认同的努力有例可循。
二、 “甥舅之邦”:藏族融入华夏政治体系的努力
(一)藏族的族源叙说
藏族族源中含有古代羌人成分,对此大量历史学及人类学资料给予了充分论证。《新唐书·吐蕃传》记载:“吐蕃本西羌属,……,祖曰鹘提勃悉野,健武多智,稍并诸羌。”[6]6071“鹘提勃悉野”即吐蕃创始者悉勃野家族,《新唐书》的记载论述了悉勃野家族兼并党项、羊同等羌人部落,逐步发展壮大的事实。虽然其观点忽略了西藏本土的古藏人因素,认为藏族为羌人直系,但在一定程度上论证了羌与藏的血缘关系。对于藏族族源,众多学者进行过相关研究,罗贤佑认为:“藏族应源于远古就生活在青藏高原的人类,以后又融合了临近各族,特别是西羌诸部,而发展演变而成的。藏族真正形成一个民族共同体,应以吐蕃政权建立为标志。”[7]
随着吐蕃悉勃野家族的兼并战争,整个青藏高原纳入其统治范围,青藏高原东部及东北边缘的“羌人地带”(3)王明珂认为在历史发展过程中于青藏高原东北、东部边缘形成了一条羌人地带,长期以来,古代羌人在此地带生活流动。部分消失,吐蕃与唐王朝直接接壤。基于对华夏先进文明的认同以及学习的需要,吐蕃赞普松赞干布主动采取与唐和亲政策,吐蕃与唐王朝之间的“甥舅之邦”自此缔结,此为藏族通过与中原王朝政治联盟融入华夏体系的开端。
(二)“甥舅”关系的缘起
“甥舅”,《尔雅》释义“谓我舅者,吾谓之甥”。“甥舅”关系源自古代氏族社会。氏族社会族外婚的婚姻形式为“甥舅”关系的产生奠定了现实基础。《释名》认为:“甥”为“出配它男而生”[9],指氏族女子与它氏族男子结为配偶,所生男孩为女子兄弟之“甥”,称女子兄弟为“舅”。国家形态出现之后,“甥舅”关系成为统治者(即天子)巩固统治同盟,维系自身统治地位的重要形式。《礼记》记载,天子“异姓谓之叔舅”,即天子与异姓诸侯结为“甥舅”关系;“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者,虽大曰子”,“子”即“公侯伯子男”最末两等之一“子”爵,可见“蛮夷戎狄”不在天子“甥舅”关系构建之列。由此可知,西周“异姓谓之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者,虽大曰子”[10]的论述是天子为维持包含“华夏”以及“蛮夷戎狄”的“天下”统治而制定的阶级礼法秩序。
春秋战国时期,“甥舅”关系出现了重大转变,即随着周王朝“礼崩乐坏”,“甥舅”不再仅局限于在“天子”的同姓诸侯与异姓诸侯之间构建。诸侯国为在统一“天下”的兼并战争中占据优势,壮大自身实力,在同异姓诸侯国缔结同盟的同时,也开始了同“蛮夷戎狄”的联姻。《左传》记载,晋献公“娶二女于戎,大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11]288-289。晋为周成王弟唐叔虞所创,本为姬姓之国,到春秋时期业已打破“华夏”与“蛮夷戎狄”的限制,同西戎缔结婚约。这种从内部开始的“礼制”破坏,为“甥舅”关系的进一步变革提供了先例。此外,《史记·匈奴列传》记载:“周襄王欲伐郑,故娶戎狄女为后,与戎狄兵共伐郑”[4]758。然而后世史家却给出了与司马迁截然不同的看法,《资治通鉴》中认为:“盖上世帝王之御夷狄也,服则怀之以德,叛则振之以威,未闻与之为婚姻也。”[12]同时,周襄王联姻北狄引来狄人入侵的后果,其后周王室也未因襄王曾以狄女为后,对“蛮夷戎狄”之成见有所稍减。如,针对秦晋两国迁西戎于洛阳,周景王强烈反对,称:“戎有中国,谁之过也。”[11]1270可见,周襄王之做法不为后世认可,也未成定制,不足以认为是先秦“甥舅关系”之变革。
秦汉之交,作为“戎狄”后裔的匈奴统一北方草原,以“华夏”为主体的中原王朝第一次面临统一的北方强邻,这对“天下”秩序的稳定形成新的考验。汉初经过白登之役,匈奴的强大实力对中原王朝形成巨大心理压力。在此情况下,汉臣刘敬向刘邦建议:“陛下诚能以適长公主妻之,厚奉遗之,彼知汉適女送厚,蛮夷必慕以为阏氏,生子必为太子,代单于。何者?贪汉重币。陛下以岁时汉所余彼所鲜数问遗,因使辩士风谕以礼节。冒顿在,固为子婿;死,则外孙为单于。岂尝闻外孙与大父抗礼者哉?”[4]694据此,通过与匈奴和亲,汉匈之间事实上的“甥舅”关系得以确立并为后世承继。以“华夏”为核心的中原王朝与“蛮夷戎狄”后裔所建政权和亲,建立政治联盟,开创了“甥舅”关系的新的发展阶段。至此,西周之后“甥舅”关系的两次转变为华夏大一统局面的形成以及藏族通过联姻融入“天下”体制,参与华夏民族建构创造了条件。
(三)唐蕃缔结“甥舅”关系的历史考察
藏汉亲属称谓作为一种文化符号,反映了两个民族亲属关系及家庭婚姻理念和制度[13]。唐朝时期,唐蕃统治者间“甥舅”关系的建立成为藏族逐渐进入“天下”之中的重要体现。
公元638年,吐蕃入侵唐境,唐败吐蕃军。吐蕃赞普遣使议和,请求和亲。唐太宗以宗室女文成公主予松赞干布为妻,令江夏王李道宗护送入藏。松赞干布亲往黄河源头青海扎陵湖迎亲,对李道宗“执婿礼甚恭”[6]6074,同时对李道宗说:“我父祖未有通婚上国者,今我得尚大唐公主,为幸实多”[14]。唐蕃“甥舅”关系由此开始缔结。公元710年,唐中宗李显又以养女金城公主嫁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初唐时期,大唐两次赐婚吐蕃,为唐蕃“甥舅之邦”的构建奠定了现实基础。
自文成公主入藏至吐蕃分裂二百年间,双方互相遣使多次,史料可见之往来信函数以十计,“甥舅”二字时常见诸笔端,成为双方习惯性称谓。例,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唐征伐高句丽,松赞干布上《贺平辽东表》中称“奴忝预子婿,喜百常夷”[15]15577。此外,唐王朝致书吐蕃也往往以“舅”自称,称对方为“甥”。如唐朝官员封敖代皇帝所撰《与吐蕃赞普书》中夸赞赞普“外甥雄武挺生,英威特立”[15]8430。双方通过习惯性的“甥舅”称谓对双方关系予以确认和维系巩固。
唐蕃“甥舅”关系实为政治联盟性质,对此,唐与吐蕃都有着清醒的认识,从双方表述中可见其端倪。在唐官员陆鸷代皇帝撰写的《赐吐蕃将书敕尚览铄》中称“国家与大蕃,亲则甥舅,义则邻援”[15]5453,意为双方在面对同一敌对势力时,统一立场,互相援助。对此,吐蕃赞普赤德祖赞在《请修好表》中也曾提到,对于“骨吐禄(部落),阿舅亦莫与,外甥亦不与交”[15]15578。此外,公元729年,赤德祖赞致书唐玄宗:“外甥是先皇帝舅宿亲,又蒙降金城公主,遂和同为一家,天下百姓,普皆安乐。”[6]6084733年,金城公主又上《请置府表》说:“今得甥舅和好,永无改张,天下黔庶,并加安乐。”[15]1164由此可见,双方结亲除想达到互相军事援助的目的外,还有致力于实现“天下百姓”的“普皆安乐”。吐蕃虽地处偏远,然而“天下”“百姓”(即华夏子民)已在其视野之内。
《国语·鲁语(上)》中称“重之以婚姻,申之以盟誓”[16],联姻是先秦姬姓以外异姓诸侯加入华夏集团的重要方式,由此,双方成为政治共同体。吐蕃建立后,松赞干布向唐朝主动请婚,缔结唐蕃“甥舅”关系也成为藏族融入华夏政治体系的关键环节。
藏族通过政治上的“甥舅”关系逐渐进入了“天下”之中,然而不可否认的是,此时藏族在“天下”中的地位仍还处于边缘地位。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政治上仅仅是一种暂时性的军事联盟关系,帝制中国时代的官僚体系还无法对西藏形成直接的统辖;二是文化上还比较疏远,虽然禅宗对藏传佛教的形塑有一定的作用,但此时的藏族文化还未能在青藏高原之外形成较大的势力和影响。
三、“兄弟一家”:藏族基于蒙藏认同的祖先亲族重塑与华夏民族认同
(一)“蛮夷戎狄”重塑自身祖源的历史考释
王明珂在其《华夏边缘》一书中提道:“族群是由集体祖源记忆来凝聚,并以改变、创造新的集体祖源记忆来达成认同变迁。……,‘寻找失落祖先的后裔’及‘寻得或假借一个祖源’这样的双向或单向认同活动,是华夏改变自身族群边界,及边缘族群华夏化的一种基本模式。”[17]在同中原华夏民族交流过程中,重塑自身祖源是“蛮夷戎狄”等周边民族融入“华夏”的重要方式。大量的史料记载以及民间叙事为周边民族的华夏祖源提供了间接证据,如司马迁在《史记》中记载“匈奴,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4]758,夏后氏即禹,司马迁认为匈奴为华夏民族的重要族源夏部落创始人禹的后裔。此外,“禹兴于西羌”同样是“蛮夷戎狄”华夏祖源的理论依据。在司马迁对于匈奴(北狄)、羌(西戎)两方面的论述中,华夏成了戎狄的共同祖先。
(二)藏族族源的再建构
作为一种真实存在的民族历史与被“天下”观念建构的历史之间存在着巨大的鸿沟,而“天下”观念所建构的“华夷一家”的秩序显然更符合古代中国“天下一统”的要求。于是,真实的历史慢慢淡出地平线,一个被建构和创造的历史逐渐进入历史文本。匈奴通过祖先重塑融入华夏的历程也同样出现在远晚于匈奴时代的后兴藏族追求华夏民族认同的过程之中,这一过程的关键环节在于藏族“基于蒙藏认同的祖先重塑”。
西藏史书中有大量关于藏族族源的祖先亲族记忆,有印度外来说、猕猴与罗刹女造人说以及卵生说。其中猕猴与罗刹女造人说称其子孙包括“六氏族”“四种人”等相关说法。其中“四种人”的说法最具普遍性,其内涵也几经转变。据阿底峡《柱间史》记载,吐蕃先民为“穆”“色(塞)”“董”“东”四大部落。“穆”指的是象雄,“色(塞)”指的是吐谷浑,“董”指的是党项,“东”指的是苏毗[18]。此外,对于“四种人”一说,又有藏族史籍称包括“内外四族”。据《汉藏史集》记载,“外部四族系是草山沟里的鼠、有皮膜的青蛙、猿、猴等四种;内部四族系是格向汉人、金尚蒙古人、卡勒巴蒙古人、悉补野吐蕃人等四种。其中汉人又分为两系,即穆氏和格拉氏;蒙古人也分为两系,即森察和拉察;门巴人生出三支,一支是门巴本身的族系。另有汉藏交界处的木雅人和工布人。”此外,《汉藏史集》又将“六氏族”与“四种人”之说结合了起来,称“吐蕃人叫赤托钦波,他生有六子,即查、祝、董三者,加上噶为四兄弟,及韦、达二弟,共六人”[19]。
根据史料成书年代可见,随着历史变迁,藏族起源神话之一的“四种人”内涵不断扩充,从最早的包括党项、吐谷浑在内的青藏高原各族到形成包括蒙古人、汉人的论述体系,形成了对于藏族祖先亲族的不断重塑。说明随着同外界接触的增多以及认识的不断加深,藏族有着强烈的同外部连为一体的愿望,在政治上体现为对吐谷浑、党项的兼并战争以及唐蕃“甥舅之邦”的塑造,在文化上体现为通过对祖先亲族“四种人”故事的重塑同汉族、蒙古族形成思维上的血缘关系,成为“兄弟一家”,这是藏族认同华夏民族的外部表征。
(三)藏族进入“天下”的中心
吐蕃崛起过程中为实现统一青藏高原的需要,包含吐谷浑、党项、象雄等“四种人”的神话应运而生。1247年,藏传佛教萨迦派首领萨迦班智达贡嘎坚赞同蒙古王子阔端于西北凉州进行了著名的“凉州会盟”,蒙藏关系由此缔结。元朝建立后,为管理西藏事务,元中央设宣政院“掌释教僧徒及吐蕃之境而隶治之”[20],于西藏地方置朵思麻、朵思甘、乌斯藏纳里速古鲁孙三个都元帅府,同时在西藏进行籍户和置驿,西藏地区正式纳入中央行政管辖。此外,蒙古统治者极度重视藏传佛教的意识形态作用。元世祖忽必烈以萨迦派宗教领袖为“国师”“帝师”,“统领天下释教”,藏传佛教在蒙古族中得到广泛传播。基于共同宗教信仰,蒙藏民族认同得以形成。作为华夏“王统”的继承者,元代经营西藏的努力使得藏族同“华夏”的关系在蒙藏认同的基础上已由唐朝时期的“甥舅”政治联盟发展成为事实上的“天下合同为一家”。据此,包含汉族、蒙古族、藏族的祖先亲族神话开始重塑。
此时的藏族已经进入了“天下”的中心,并成为华夏民族重要的组成部分之一。这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西藏进入了帝制中国的管辖之内,此时的西藏实行的行政体制是中原郡县制的延伸;二是藏传佛教不仅是当时官方倡导的宗教形式,而且对华夏民族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三是西藏在经济上与蒙古高原、云贵高原和中原地区的联系不断加强,“茶马古道”成为各区域经济交流的生命线。更为重要的是,藏族在“天下”的这种中心地位在之后中国历史的演进中不仅没有减弱,而且得到了持续的增强,特别是清代在承德修建的“喇嘛教之都”成为藏族“中心”地位的鲜明例证[21]。
总之,迟至12世纪前后,西藏不仅纳入了帝制中国的统辖范围之内,而且以藏传佛教为代表的西藏文化已经对蒙古高原、中原地区产生了重要的影响,藏族在“天下”中的地位已然从边缘进入中心,并以此为基础建构着其祖先的历史神话。
结 语
“华夏”是一个包含多种元素的论述体系,它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天子同姓谓之叔父,异姓谓之叔舅,其在东夷北狄西戎南蛮者,虽大曰子”是天下格局中为区分“华夏”与“蛮夷戎狄”所制定的“礼法”制度。然而随着东周以来的“礼崩乐坏”,大量“华夏”周边“蛮夷戎狄”开始了华夏化历程。在藏族融入“华夏”的历史进程中,从唐朝时期政治结盟,缔结唐蕃“甥舅之邦”,到元朝以降形成文化认同,构建“兄弟一家”,完成了从“蛮夷戎狄”到“华夏”的重要跨越。
综上可知,从6世纪到13世纪,藏族在“天下”的知识图谱中逐渐从边缘进入中心,而且这种中心地位在后续的历史演进中不断加强。藏族参与华夏民族建构的历史逻辑是数千年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形成过程中的典型案例。华夏边缘匈奴、鲜卑、羌、满、蒙、回、藏等“蛮夷戎狄”通过政治参与、文化认同,打破了“天下”体制下僵硬的“礼法”体系,从“天子”异姓变为“华夏”同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