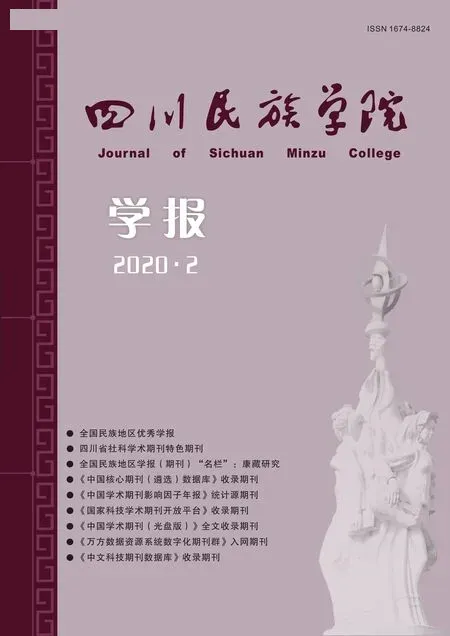羌绣与苗绣的图案比较研究
王齐霜 杨震华
(成都纺织高等专科学校,四川成都 611731)
在中国众多的少数民族中,生活在西南山地的羌族和苗族都是历经磨难却又创造了灿烂文化的古老民族。羌族聚居地以川西高原山地的茂县、汶川、理县、松潘、北川等为主,苗族广泛分布在以贵州、湖南和云南为主的西南地区。两个民族的女性都心灵手巧,擅长刺绣,羌族用以装饰服饰的刺绣被称为羌绣,苗族用以装饰服饰的刺绣被称为苗绣,都是优秀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是其美学智慧和民族文化的载体。羌绣与苗绣的图案以造型、色彩、材料和肌理等为表现手段,经过无数代人的总结提炼,最后以程式化纹样的形态固定下来,并自成一套体系。羌绣和苗绣看似联系不多,各自发展,苗绣由于突出的艺术性和文化内涵很早就受到国内外的关注从而开发较早,羌绣在5·12大地震之后从默默无闻到广受关注,由于开发之初就受到专业文化机构全程助推从而起点较高,目前两者的开发都遇到瓶颈,需要静下心来深入挖掘。俗话说,有比较才更有鉴别,通过两者相似性和差异性的比较研究,能够更好地梳理各自的艺术特征和文化脉络,为强化各自的民族辨识度、弘扬民族文化提供理论支持。
一、羌绣与苗绣图案的相似性
(一)羌绣和苗绣图案都大量来源于其生存环境
羌绣和苗绣的图案题材中有很大一部分来源于其生活的地域环境,主要反映在各种动植物纹样和自然物象纹样之中。人们将身边常见的植物、动物和自然物象等整理归纳出来,以具象或抽象的方式创造出极富民族特色的图案纹样。
羌族长期生活在高原,被称为“云朵上的民族”,羌绣中最常见的羊角花纹样其实就是川西高寒山地常见的高山杜鹃的形象,其枝干粗壮,花朵硕大,羊角花既是羌人对大自然的崇敬,又是对顽强生命力的向往;还有备受赞誉的羌族“云云鞋”上的云云纹,把虚无缥缈的云朵和鞋子联系在一起生发出脚踩祥云的创意,也是对“云朵上的民族”生活在高原山地的创意性再现。苗族长期游走在自然环境更优越的南方地区,苗绣中植物纹样、花卉纹样、蝴蝶纹、鸟纹、鱼纹等动物纹样都非常常见,种类繁多而技法多样,被绣在衣袖、裙子、围腰、背扇等位置极富装饰效果。有一些极具表现力的动植物纹饰甚至成了苗绣的杰出代表,例如黔东南州榕江摆贝的百鸟衣,由于鸟纹刺绣图案的高度装饰性和风格化,让百鸟衣成了广受关注的明星服饰。相较于羌绣图案而言,苗绣图案中的动植物纹饰更加丰富多样,这也可解释为南方地区相较于川西高原而言,自然环境明显更加优越丰富。
(二)羌绣和苗绣图案都体现了其民族的图腾崇拜
在远古时代由于生产力低下,人们对大自然产生敬畏和崇拜,于是诞生了图腾崇拜,常常表现为对某种动物、植物或事物的崇拜[1]31-32,羌绣和苗绣的图案题材不少都来源于图腾崇拜文化。古羌人的谋生对象、食物来源和御寒保暖都离不开羊,据汉学家考证,“羌”字其实就是“羊”字的变形[2]11-12,足见羌族与羊的深厚关系,羊在其心目中有特殊的地位以至于以羊为图腾。刺绣图案中常见各种羊的纹样,经典的“四羊护宝”纹样就来自对羊的崇拜(见图1),另外把高山杜鹃称为羊角花也是对羊的图腾崇拜的另一种方式。苗绣中的图腾崇拜更是随处可见,并且数量繁多,不同的领域有不同的崇拜对象,姜央、蚩尤和枫树纹等表现的是对祖先的崇拜,蝴蝶纹、鱼纹、蛙纹和石榴纹表现的是对生殖繁衍的崇拜,而苗龙、牛、狮子等图腾崇拜表现的是对神灵和神力的崇拜与召唤。

图1
(三)羌绣和苗绣图案保存了民族迁徙的记忆
羌族和苗族都曾历经磨难、颠沛流离,历史上由于战争、灾害和统治压迫等一再迁徙,这些迁徙基本都是被动的、逃亡式的,为了缅怀故土、记录迁徙路线或铭记史实,在没有发明文字的情况下刺绣图案就成了书写民族迁徙记忆的载体。
羌绣中对羊的图腾崇拜其实也来自对故乡的怀念。东汉许慎《说文·羊部》释:“羌,西戎牧羊人也,从人,从羊;羊亦声。”[2]2羌人的祖先最早生活在今甘肃、青海一带的黄河上游地区,是古代西戎的牧羊人[3],可见羊与羌族先民的密切关系,历经迁徙来到川西高原后,为了留住历史的记忆,羌绣中常常出现羊的纹样,也将高山杜鹃赋予羊角花的称谓,都是通过对羊的崇拜强化对故土和祖先的缅怀。苗绣图案中对民族迁徙的记录更加外化。相传古代有个叫兰娟的苗人首领,在带领族人南迁的过程中,为了记录迁徙路线就用刺绣纹样来描绘,每次渡河和翻山都在衣服上绣上特定的纹样,外人眼中的装饰纹样其实是苗人的迁徙密码,后来这种绣有迁徙图案的服饰被称为“兰娟衣”。不仅是兰娟衣,在其他苗绣图案中也常常能找到有关民族迁徙的佐证,例如常见题材苗族女英雄务茂媳。公元1735年黔东南地区爆发了苗人反抗清朝压迫的“雍乾起义”,包括这次在内的一系列起义失败后,苗族人被迫进行了最后一次大规模迁徙,大量苗人从贵州向云南迁徙,甚而迁往东南亚诸国[4]。务茂媳就是雍乾起义中牺牲的一位真实人物,在苗绣中她被描绘为武艺高强的女英雄,总是以举魔伞(有时是武器)、穿厚裙、露大脚、骑大马、有时还带小孩(她是单亲妈妈)的形象出现在清水江流域的施秉、台江、剑河、镇远的苗绣图案上(见图2)。务茂媳的经典纹样没有直接记录迁徙的路线,却通过对一个女英雄的怀念揭示了迁徙的缘由。
图2
二、羌绣与苗绣图案的差异性
(一)羌绣和苗绣图案种类的差异
苗绣图案种类众多,据不完全统计,苗绣纹样中的动物纹饰有蝴蝶、苗龙、凤凰、饕餮、鹡宇鸟、狮子、麒麟、鱼、牛、马、蛙、鼠等60种以上,植物纹饰有枫树、桃树、石榴、牡丹、八角花、菊花、各种花卉蕨类等40种以上,人物图案除了一般的男女老幼外还有始祖姜央、伏羲、蚩尤、女娲、务茂媳、葫芦兄妹、巫师神怪等众多人物[5]。图案题材包括祖先崇拜、神巫信仰、繁衍崇拜、图腾崇拜、迁徙路线、节庆活动、植物动物以及各种纯装饰纹样等。羌绣图案中的动物纹饰包括羊、龙、猴、狗、狮、蝶、各种鸟类等,植物纹饰包括杉树、柏树、羊角花、牡丹、八瓣菊、石榴等,还有自然物象纹饰、抽象纹饰等,题材包括图腾崇拜、主题纹样、吉祥纹样、装饰纹样等。总的说来苗绣图案在纹饰种类和题材数量上更加丰富庞杂,之所以有这样的差异主要与地理环境和民族支系亚文化有关。
(二)羌绣和苗绣主题纹饰的造型多样化的差异
苗绣同一主题纹饰在不同支系的表达中具体造型各不相同,再加上针法变换和材质肌理的运用,外观视觉感受差异化极大。例如蝴蝶妈妈的主题,仅在黔东南州台江地区的不同支系中的造型差异都会较大,有的造型带有解构趣味充满想象力,有的还和鹡宇鸟等其他纹饰交错融合形成新的共生图形,同时再配合剖线绣、布贴绣、绞籽绣、挑花等不同技艺来表现,其造型特征和肌理材质等各具特色,纹饰造型和视觉感受多样化程度很高。而羌族服饰类型相比而言较为集中,同一主题纹饰在各支系中的差异化较小。以羊角花为例,不同支系不同针法绣制的羊角花在纹饰造型上都偏重质朴粗放的风格,组织构成关系也较为接近,纹饰造型和组织形态差异程度较小,在视觉感受上非常整体和统一。
(三)羌绣和苗绣纹饰色彩的差异
图案学中除了造型因素之外,色彩因素同样极大的左右着图案的外观视觉感受。苗绣的色彩搭配丰富多样,除了热烈华丽的高纯度对比色搭配之外,也有和谐秀丽、色差适中的类似色搭配,还有典雅柔和的低色差暗色调搭配。例如贵州贞丰一带的挑花纹饰甚至需要走近细看才能辨别。羌绣的图案色彩大致分为彩绣和素绣两类,彩绣是热烈艳丽的高纯度对比色搭配,在羌族服饰中广泛运用,素绣是深色(一般为黑色、深蓝和蓝)与白色的低纯度二元对比,一般以锁绣或挑花的技法绣制在围腰等服饰单品上。相较而言苗绣图案的色彩搭配效果多样,羌绣图案的色彩运用更加单纯,情感表达更加强烈和直接。
(四)羌绣和苗绣图案精致程度的不同
羌绣和苗绣由于生活环境和审美追求的不同,其图案在视觉形态上的繁复程度也不同,主要体现在纹饰造型和工艺制作上。苗绣图案非常重视细节的表现,在造型和工艺上精益求精,不惜时间和精力成本,追求精致度和装饰效果的最大化,以贵州台江施洞镇的剖线绣为代表,其纹饰和工艺的精致程度令人惊叹。而羌绣则难以做到苗绣那样的精致,究其原因并非羌族女性不够心灵手巧,实为生存环境所制约,在恶劣生存环境的重压之下,羌绣不得不放弃了对精致度的追求,转而更加重视效率,利用有限的时间制作适度的装饰效果是羌绣的制作原则,羌绣图案不会过多追求纹饰造型的复杂度和制作工艺的精细度,这既是羌绣无奈的选择也是羌族女性智慧的体现。
三、形成羌绣与苗绣图案差异的文化背景
前文分析了很多羌绣与苗绣图案的差异,概括来说苗绣图案在技巧性和表现力等方面比羌绣更加丰富多样,这只是民族文化和美学追求的差异,并不妨碍羌绣的艺术和文化价值。之所以会形成这种差异,与地域环境、民族支系族群的亚文化和刺绣的文化需求等息息相关,是外部环境和内部需求共同作用的结果。
(一)地域环境对羌绣和苗绣图案精致度和多样化的影响
用地理环境的观点来分析,审美观念的形成和自然环境的影响密不可分。图案艺术在本质上是一种物化了的人的意志与精神,羌绣与苗绣的图案正是自然环境在功能需求和审美需求上形成的物化结果。
古羌人自唐代中期之后基本游走在青藏高原东北部,长期生活在苦寒贫瘠的高原山地,女性在巨大的生存压力之下没有更多的时间精力从事刺绣这种精细化工作,甚至绣线等材料的供应有时都不能满足,导致羌绣图案在功能性上讲求实用和高效,技法与装饰性上适度即可,追求投入成本和装饰效果的性价比,不过分追求造型的多样和制作的精致。苗族长期游走在湿润丰饶的南方地区,肥沃的土地解放了苗族女性,让她们有更多的时间精力来研究琢磨刺绣,不计时间成本和脑力成本,丰富的物产也让刺绣材料的选择多样而充裕,因而苗绣图案在造型、色彩和技法上非常多样化并极其注重细节的精致化表现。仅以刺绣图案的精致度和多样化来说苗绣技高一筹,但如果仅仅以此来评判其技术和艺术的高下是简单粗暴和有失公允的,应该看到地域环境对人行为和意志的巨大影响,精致与质朴主要归因于外部的条件和制约,次要归因于内部功能需求和精神需求的选择。
(二)地域环境对羌绣和苗绣图案美学风格的影响
苗族人对南方湿热瘴气的深山密林既充满敬畏又渴望拥有神力战胜它,于是就产生了诸多神话传说、图腾崇拜和对生命繁衍的渴望,丰富了苗绣的图案内容,加之苗族女性非凡的想象力和创造力,逐渐形成了苗绣图案庞杂丰富、精致华丽、神秘生动,尤其是精致繁缛而不失灵气的美学风格。而羌人长期生活在高寒、贫瘠又苍茫的川西高原山地,恶劣的环境更加激发单纯炽热的情感,以致羌绣在审美风格上对粗放质朴的造型和艳丽鲜活的色彩更加认同,造型上无暇追求更为精致的细节表达,色彩上无暇顾及过于丰富细腻的层次,逐渐形成了羌绣图案刚健饱满、博大壮美、质朴鲜活的美学风格,与川西高原的壮美苍茫相得益彰。
(三)苗绣图案追求精神世界,羌绣图案直面现实世界
审美的本质是一种价值的认同,羌绣和苗绣图案正是这种群体价值认同的外化形式。刺绣在装饰服饰的同时也阐释了本民族的美学价值观,包括自然观、生命观、现实需求和精神需求。总的来说,在美学价值的追求上,苗绣图案更着重于表现精神世界,羌绣图案更着重于表达现实世界。苗绣图案中有大量动植物纹饰,其中很多动植物纹饰都被赋予了精神和文化的寄托,例如蝴蝶纹、鱼纹和蛙纹表现的是生殖崇拜,枫树纹表达的是对祖先的崇拜和对自身的价值认同,很少描绘人们日常的生产劳动等现实生活场景,这些都反映了苗族人的生命观和精神世界。苗族在历经苦难和迁徙之后,在自身价值认同上回避苦难的现实,转而追求精神世界的表达。羌绣图案中也有大量的动物纹饰、植物纹饰和自然物象纹饰,尤其看重象征美好幸运的羊角花,这些纹饰总是被描绘成饱满积极有旺盛生命力的样子,当它们组合起来又往往构成有美好寓意的吉祥纹饰,可见乐观的羌人早已面对恶劣贫瘠的现实环境,羌绣图案始终着力表现现实世界,而对精神世界的探索则更多的交给了羌族社会的特殊群体“释比”去完成。我们在羌绣图案中并没有看到羌人被现实压垮,反而直面现实,处处都是对生存环境的接纳和赞美,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和憧憬。
结 语
羌族与苗族同为没有文字的少数民族,刺绣成为民族文化的承载者与传播者,在国家大力倡导发展文化产业的当下,对羌绣和苗绣的开发都成为当地文化产业的重头戏。而在以往类似的开发中,容易出现同质化倾向和民族辨识度模糊的问题,究其原因发现,不同文化本源的刺绣图案在相互借鉴的过程中,忽略了各自的美学特征和背后的文化内涵。本文通过研究和比较羌绣与苗绣图案的异同,梳理了各自的题材内容、纹样特征、美学风格和文化内涵,以期能够更好地理清各自民族文化的脉络和轨迹,为羌绣和苗绣的文化产业开发提供一定的理论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