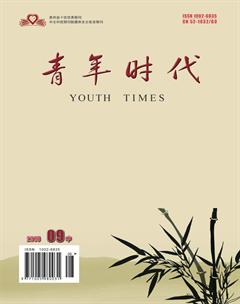浅析敦煌壁画的民族精神及文明传承
张颢恬
摘 要:古往今来,我们华夏民族不缺那些甘愿为江山社稷奔走呼号,为之抛头颅、洒热血的无数民族英雄。正是他们甘以热血作为养料,我们华夏才能像那生命力旺盛的野草一样,始终绵延不息。在我看来,敦煌之盛之美,不是来自于那高高在上的庙堂,而是源自民间的疾苦与欢喜。敦煌莫高窟正是为芸芸众生立传的,它的洞穴、壁画、塑像、佛经里凝聚的皆是普通人的爱恨情仇,无一处不是生动的、形象的。
关键词:华夏民族;敦煌;壁画
一、民族不死之魂
沙洲虽远离中原,乃祖宗开拓,当为汗土。我辈子民,虽久居此地,却还是华夏子孙。斯土斯民,岂容夷狄久占,我料定西夏也会与吐蕃一样,最终必然归去。届时我辈的子孙,正如原野上的荒草,仍旧是“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
宋朝年间,宿敌契丹虎视眈眈,西部边境不宁,新兴的西夏日益壮大、屡犯边境,诸多少数民族趁此作乱,妄图分一杯羹,而文官当道的宋朝实行“绥靖”政策,用一再忍让来换取国都繁荣。
曹氏家族作为节度使世袭镇守沙、瓜二州,面对西夏太子元昊的入侵,瓜州太守曹延惠不战投降,他没有足够的兵马与西夏相抗衡,他是消极而悲观的,他不妄图以蝼蚁之力而撼泰山,他希冀以求和换得战火不要烧及瓜州、换得百姓安宁,作为一名佛教的忠实信徒,他不舍瓜州的寺庙以及所藏典籍、佛经。然而终究只能换来数月的安息,唇亡齿寒,还未降的沙洲作为繁荣富庶之地,贪婪的敌人又岂会放弃趁胜追击的机会?再加上朱王礼支部的叛乱,使瓜州成为众矢之的。瓜州子民四散而去,整个瓜州毁于熊熊大火,无数房屋、寺庙、佛经化为灰烬。我记得瓜州太守曹延惠在沙州时一直坐在一把大椅子上,身体紧紧地缩成一团,跟瓜州撤退的前夜一模一样,仿佛一尊亘古不变的绝望的塑像。也许他怯懦,但他也不失勇敢,当西夏入侵沙州之时,耻于逃避,遂独自留守城中,于大火中自焚身亡。其兄沙州太守又兼曹氏家主曹贤顺比他弟弟英勇无畏得多,一腔热血、铮铮铁骨,拒当亡国奴,他身先士卒,最终战死疆场,以身殉国。曹氏兄弟无愧于他们固守的疆土,他们在灿烂中死去,而华夏子孙仍会在这片土地上从灰烬里重生。
二战时期盟军中阵亡军衔最高的将领张自忠上将在前线与日军浴血奋战整整16天,最终换得马革裹尸还,他的遗书中写道“为国家民族死之决心,海不清,石不烂,决不半点改变”。八年抗战,近代史中百年耻辱,我们的五星红旗确是用无数烈士、仁人志士的鲜血染红的。而他们的信仰只是不死的民族魂,华夏民族不会亡、不能亡,即使在最危机的时刻,他们也始终相信华夏未来的复兴和荣光。吾辈子孙,应当谨遵先辈教诲,不负先辈所托,不辱民族之魂,为中华之崛起和伟大复兴而奋斗。
二、“家国”情怀之承
家国情怀是一种生命自觉和家教传承。“家”是“国”中最基础的一环,而千千万万个小家汇聚成统一的大国。那些与国家民族休戚与共的壮怀,那种以百姓之心为心、以天下为己任的使命感,就来自那个叫做“家”的人生开始的地方。人们为之生又为之死的,实是为了能让“家”安身立命,因为没有“国”,又何来完整的“家”?
项羽曾经说过“富贵而不归家如锦衣夜行”,狐死尚且首丘,更何况最重视家庭的华夏民族呢?如落叶归根一样,除非死于耻辱的人,莫不希望回到故土的。
朱王礼原为宋军,不幸被西夏军俘虏,只得为西夏冲锋陷阵。他置生死与度外,在战场上英勇无畏,但却一直坚持要赵行德承诺,若自己死了而赵行德能生还,一定要给他在战场上立碑,立碑的须是汉字,因为毕竟是名汉人。这样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武将,心心念念而又最为恐惧的一定是若自己死后,无人识得自己,无人识得自己是名汉人。人活着时有百般无奈、万种心酸,惟愿死后的墓碑能在历史的洪流里被冲刷得慢一些、再慢一些。
英雄最怕的不是身死,他们怕的是死后无人知晓他们的存在,怕的是无人祭奠。一个忘记历史的国家是不配有未来的,因为忘记代表着背叛。漠视历史的行为只会让英雄心寒,长此以往,一个民族将会失去他们的英雄。
其实五湖四海,古往今来,大家莫不希望后人能记住自己。在《寻梦环游记》电影中,墨西哥传说人有一个理想的极乐世界,人死后可以在这个世界里永生,在每年的固定一天甚至还可以回到现实世界里与亲人团聚,但唯一的要求便是现实世界里一定要有个活人还记得你,如若现实世界里无人记得,将会永远地消失。
假如死去的人能一直活在世人的心里,那么他必然是可以永生的。
三、文明传承之殇
我们至今仍不知道敦煌莫高窟藏经洞那四万余件文物的来历,这些珍贵的文物是被谁以怎样的原因,而又以怎样的心情藏入的呢?
也许正如作者所虚构的那样,是在沙州(今敦煌)城被烧毁之前,由三名僧人及進士赵行德骑着骆驼在一个晚上匆忙转移的?也许这正是赵行德的夙命,不然他何以从那繁花似锦的富贵地、温柔乡来到这茫茫大漠上呢?跨过这万水千山,蹉跎这数十年的时光,也许只是为了那一夜的使命。
而今现实是“敦煌之学不在敦煌”,藏经洞中四万余文物只余少量于国内,大量文物散落在国外博物馆。我们又以怎样的颜面去见我们的祖先?这些文物背后是无数个赵行德们的努力,我仿佛看到了学者们只身深入西域、呕心沥血地建立少数民族与汉字的联系,僧侣们专心致志翻译佛经,著书者甘为贫苦,奔波四处,搜集各地风俗、珍贵史料,我看到了战火纷飞中运送的文物史籍,我看到了那一个个坚毅的剪影,我看到了为给后世留下珍贵文物而在乱世中奔走的无惧背影。而我们,却做了什么?毁灭,是容易的;敦煌的壁画只需轻轻一刮,那些曼丽的飞天、佛教的菩萨、传说的人物就会褪尽所有色彩,只留一片斑驳。毁灭这些遗产只需一瞬,而成就这些却需千年。
四、芸芸众生之苦
赵行德作为故事的主人公,他原为进士,从四川老家奔赴都城赶考,但因睡过头而错过了考试,最终无缘殿试。缘分是件很奇妙的事,误了他考试的梦就是关于西夏的安边策的对答,也许这是来自远方的召唤,来自冥冥中的天意。
“我命由几不由天”恐怕是在太平盛世才能畅快抒发的豪情壮志,在风雨飘零的乱世中,每一个普通人都只是一叶浮萍,命运无常,命运的洪流将你冲到哪。赵行德原来不过是想去凉州学习西夏文字,谁知却被西夏俘虏充军,而后再无归家。乱世中的无数人都是如此,他们没有去处,没有目的地,没有可以安家扎根的地方,只是回不去的永远是家乡,忘不了的永远是故土。浮萍是没有根的,但汉民族以及汉语言所产生的归属感,就是他们的根。赵行德自离开故国后,世界只剩白茫茫一片,每一座城都是陌生而相同的,因为这些城都不是汉人的城。
赵行德的一生经历了两次顿悟,第一次是在街头,被西夏女人对生死的漠然所震撼,促使他踏上了前往西部边境的路。
第二次是因为“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的爱情。赵行德与回鹘王女在甘州烽火台上一见钟情,赵行德许下一年之约的誓言,然而命运的无常和这段爱情的虚无缥缈再加上他自己的懦弱与拖延,他在逐渐淡忘王女的容颜中食言了。一年半后再次回到甘州城的他,发现王女已被西夏太子元昊强占为妾。马背上最后的对视,王女终于等到了自己的归人,但却等不到自己追求的爱情。几天后,王女从城墙上一跃而下,魂归西天。她为了爱情的忠贞,为了一个迟来的负心汉,付出了自己年轻的性命。烟花易冷,人事易分,我仿佛听到临死前的王女在问赵行德,他是否还认真?
这段爱情还未开始就已结束,如梦似幻似幻影,始终围绕着化不开的迷雾,但却更添凄美。也许这一切的一切不过是赵行德“取经”路上的一难,终极目标只是为了最后的使命。经历此事,赵行德彻底悟佛。也许江山早为你我说定了永别,于是你把性命抛弃,换我把你刻在佛经前。他将这份遗憾而凄婉的爱情在佛经中换得了永恒,他将这个传世的爱情故事埋葬在了千佛洞的佛经中。他用那一夜的使命换得了后人对这段爱情的吊唁、叹息。当后人发现藏经洞的传世瑰宝时,这段爱情也将重现于世,世世代代传颂。
“于是发心,敬写《波若波罗密多心经》一卷,安置洞内已。伏愿天龙八部长为护助,城隍安泰,百姓康宁,次愿甘州郡主乘此善因,不溺幽冥,现世业障,并皆消灭,获福无量,永充供养。”
爱情如此,世间千万种感情可得一瞥。相爱的人们在乱世中流离失所,而莫高窟却在乱世中繁荣。人们的美好感情在亂世中变得不幸,但在苦海中挣扎、茫然的芸芸众生更不会放弃心中的美好希冀,于是他们只能拼命抓住超脱于现实生活的宗教信仰作为自己的唯一浮木。我什么也没有,只有一颗向佛的心,我愿日日夜夜手抄佛经,化为香火永世供养西方佛陀,只盼牵挂的百姓、亲人、爱人能在来世换得盛世安稳,只盼佛佑华夏大地。
站在壁画前,你仿佛能看到在岁月流逝中丧失了颜色的壁画重新鲜活了起来,这画卷是多彩而流动的,仿佛还能听到盛世中宴席上的丝竹乐器声、能看到舞伎飞天的灵动身姿、能嗅到西域美酒的芳香、能尝到美味佳肴的口感、能触到丝绸衣物的顺滑。你也能看到逐渐黯淡的色彩和画面,你能听到婴儿的啼哭、老妪的叹息,你能看到参军时青年头也不回的坚持,你能看到身后默默伫立、抹泪的母亲,阁楼上痴痴等待的绣花女子,你能听到战场上的厮杀声,你能看到归于寂静的战场上惨白的月色、凋零的花瓣以及散落一地的被血模糊的还未寄出的家书。
跨过千山万水,踏遍万里河山,在沙漠中跋涉。为了敦煌,不会后悔。
参考文献:
[1]刘朝霞.文化资源艺术转化的“敦煌模式”[J].学习与探索,2016(02):142-146.
[2]颜廷亮.季羡林先生对敦煌文化研究的一大理论贡献——从敦煌文化的历史定位问题谈起[J].甘肃社会科学,2008(06):177-181.
[3]王建疆.全球化背景下的敦煌文化、艺术和美学[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06):26-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