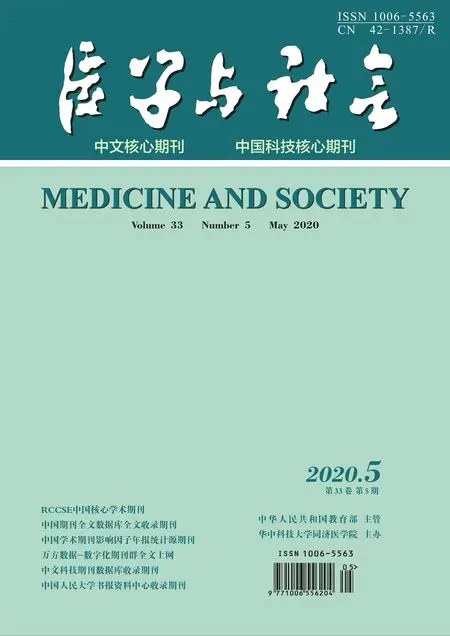双面信息策略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疫情谣言治理中的作用
程 辉 周 琼 刘小莉 袁柏春
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武汉,430022
近二十年来,我国先后出现了一系列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如非典型肺炎、H7N9禽流感、甲型H1N1流感、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以下简称“新冠肺炎”)等。伴随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而来的往往是各种谣言的兴起与快速传播。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各种谣言层出不穷,在新媒体中呈病毒式传播,引起了一定的社会恐慌,也扰乱了社会秩序的稳定,更加大了抗击疫情的压力。因此,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中,尤其是本次新冠肺炎疫情期间,谣言治理具有广泛的现实需求。当前,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治理研究主要集中在谣言产生的原因、传播机制以及阻断措施。但相比较而言,传播信息的特征更具有可控性[1]。因此,结合有关心理学和传播学理论,从官方及媒体传播信息的内容入手,实施双面信息策略,对于减少谣言产生空间、降低谣言传播的可能性、提升政府及官方媒体辟谣效果,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也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
1 双面信息策略概述
双面信息(Two-Sided Message)是指在沟通陈述过程中既包含正面信息又包含负面信息[2]。双面信息策略是指在传播信息中适当加入负面信息,从而提高信息的可信度,最初多运用于商业传播,特别是广告领域。相较于双面信息,单面说服因为陈述的片面性和绝对性,会引起接受者对特定观点的更大压力,接受者抵制该观点的可能性增大[3]。Pechmann等人也指出,双面信息策略能够在强化对信息的注意和处理动机、提高可信度、减少反驳等方面增强说服效果[4]。因此,面对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谣言传播时,为提高官方和媒体信息的客观性和可信度,改变传播信息结构,既传递正面的、积极的信息,也坦诚披露现实中的缺点、问题甚至危机等负面信息十分必要。
2 新冠肺炎疫情中谣言产生及传播的原因
2.1 事件的重要性和信息的未知性是谣言产生的根源
传播学理论中有一个谣言传播公式,即谣言=事件的重要性×事件的模糊性。事件本身的未知性越大,就越容易引起人们的猜测与关注,谣言正是起源于事件的重要性和状况的暧昧性[5]。新冠肺炎疫情爆发初期,国内多地第一时间启动“一级响应”。之后,世界卫生组织将本次新冠肺炎疫情上调至“大流行病”级别[6]。世界卫生组织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3月24日,全球已有194个国家和地区发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确诊病例突破37万[7]。本次疫情影响范围极广、危害程度极大、具有很强的不可控性,是一次重大的国际突发卫生公共事件。在本次新冠疫情肺炎爆发初期,学界对该病毒的认知尚在探索中,公众对该病毒的传染性、严重性、传播途径等信息知之甚少,且不具备相关的知识储备,再加上初期地方政府未能高度重视,官方信息披露不及时、不全面。正是疫情有关信息的未知性给谣言提供了滋生的土壤。据不完全统计,截至2020年1月29日,有关病毒本身、防治措施、城市管控等的谣言就多达90多起[8]。
2.2 公众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需求是谣言传播的助推器
本次疫情来势凶猛,严重威胁着公众健康、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担忧、恐惧、猜测成为主要社会情绪,社会意识结构失衡[9],为谣言的传播提供了特定的背景和环境。谣言是常见的释放焦虑与恐慌的安全渠道[10],特别是年龄较大和受教育程度不高的人群,由于接受信息渠道有限,对谣言的识别能力较低,容易成为谣言的传播者和受害者。而且,随着疫情的发展,不同时期公众对信息需求的重点不同,导致不同时期出现的谣言侧重点不同。疫情初期谣言主要集中在新冠肺炎防治、城市管控等方面,因此“新冠病毒可以通过蚊虫叮咬传播”,“中部战区空军今天会在武汉上空播撒消毒液,请大家不要出门”等谣言相继出现;随着复工的稳步开展,学校开学成为社会关注热点,江西省将于2020年4月5日开始逐批次开学等谣言随之而起;随着海外疫情加剧,境外输入相关谣言开始出现,如“全国的国际航班都要降落到上海等”。虽然这些谣言有很多缺陷,但它们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不同时期人们的信息需求和心理需求,即利用这些信息来消除内心恐惧、获得心理安全感。此外,《中国新媒体发展报告No.7(2016)》研究也发现,对于十分重要却真伪难辨的信息,70.3%的受访者表示“宁可信其有”[11],这种从众心理也进一步扩大了谣言传播的覆盖面。
2.3 政府及官方媒体公信力下降导致谣言反驳效果不佳
Bordia等人研究发现,只有诚实胜任的辟谣者否定谣言才能降低公众对谣言的信任[12]。所以,要提升对谣言的反驳效果,需要辟谣者具有较高的可信度。但是,主流媒体往往只强调正面积极的信息,忽略甚至掩盖缺点、问题等负面信息[2],这种传统的单面报道模式,使公众形成思维定式,即官方不会报道负面消息,从而降低对官方媒体的信任度。另外,近年来部分地方政府处理重大突发事件时被动的处置方式,也降低了政府的公信力。由于缺乏必要的信任,在政府和官方媒体进行辟谣时,公众接受度不高,辟谣效果不佳,导致谣言继续扩散。比如近年来有关红会的各种负面新闻极大降低了公众对红会的信任度,导致寿光蔬菜事件、红会收取手续费、拦扣上海医疗队专用医疗物资等谣言快速扩散。而疫情期间口罩分配风波、司机擅自从库房领取口罩等事件,引发了对红会新一轮的信任危机,虽然湖北省红十字会发布了有关情况说明,但仍难以平息公众的质疑。
3 双面信息策略在新冠肺炎疫情谣言治理中的作用
3.1 提升信息全面性与透明度,减少谣言产生的空间
Brehm的心理抗拒理论认为,当个体感知自己对行为的控制自由受到限制时,往往会采取对抗的方式,以保护自己的自由[13]。而单面信息由于信息的片面性和绝对性,公众抵制该信息的可能性会增大。因此在疫情初期,由于信息不充分不全面,公众会抗拒已有的片面信息,同时又急于需要一个合理解释,从而给谣言产生及传播提供了机会。而双面信息策略既公开正面信息,也公开负面信息,能够及时还原事实真相,让公众对疫情的了解更加全面客观,降低了公众抵制该信息的可能性,自然也就压缩了谣言产生的空间。疫情初期,关于新冠肺炎防治的谣言很多,国家卫生健康委发布并不断修订诊疗方案,做到公开透明。以传播途径为例,从最初的尚未明确传播途径,到《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五版)的通知》提出“气溶胶和消化道等传播途径尚待明确”,再到《关于印发新型冠状病毒肺炎诊疗方案(试行第七版)的通知》明确“呼吸道飞沫和密切接触传播,存在气溶胶传播可能,且人群普遍易感”,虽然一定程度加剧了公众的紧张情绪,但公开透明的信息使公众能更客观地了解新冠肺炎,也更易于接受官方的各种信息,有关谣言自然失去了传播的空间。据中央政法委长安剑公众号显示, 2020年3月8日-22日辟谣的22例谣言中,有关新冠肺炎防治的谣言仅3例。
3.2 满足公众信息需求和心理需求,降低谣言传播的可能性
Katz的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受众使用媒介,并非被动接受,而是基于一定需求[14]。双面信息策略包含两个方面的需求和满足:一是能够满足公众对未知信息的全面了解需求,从而缓解未知信息带来的猜疑和恐慌心理;二是满足公众的共情需求,使其获得心理归属感。以黄某英离汉返京事件为例,事件发生于全国疫情防控最严峻的时候,公众对于黄某英如何突破层层防控顺利进京以及有关政府部门防控能力存有诸多疑惑,从而引发有关黄某英身份、过往经历的联想和不实传言。中央对黄某英事件果断出手调查,及时通报有关情况,直面个别部门工作存在的问题,严肃问责有关官员。通过双面信息策略,一方面能够让公众全面了解黄某英事件背后的真实情况,从而打消各种猜疑,有关不实传言自然不攻自破;另一方面,体现了政府部门对社会关切的及时回应,加强了公众与政府的“共鸣”。
3.3 为提升政府及官方媒体辟谣效果提供新的切入点
Sherif的同化—对比理论认为,公众习惯于将新的刺激与原先形成的刺激进行对比,如果新的刺激与原先刺激距离不大,被接受的可能性增加,反之则会抗拒[15]。双面信息策略因为加入了负面信息,与具有对立观点的人缩小了距离,从而增加了真实信息被接受的可能性。此外,焦进寒认为,公众会综合各方面的信息形成自己关于政府信任的认知,这一归因过程对修复公众对政府信任的效果有很大影响[16]。以李文亮事件为例,在前期,当地政府对包括李文亮在内的“8名散布谣言者依法查处”并予以训诫。这与后续疫情发展存有较大出入,当地政府公信力大大降低,各种谣言也随之四起。国家及时派出调查组对该事件进行全面调查,并于2020年3月19日发布详细调查通报,要求公安机关撤销训诫书,对相关人员追责。通过双面信息策略,既提高了公众对政府辟谣内容的接受度,同时也给公众留下政府及官方媒体传递的是客观信息,没有为了自身利益而刻意报道正面信息、隐瞒负面信息的印象,从而提升公众对官方媒体及政府的信任度。基于此,公众也更容易接受政府和官方媒体对于各种谣言的反驳和辟谣。
4 结论
在当前公众对谣言传播存在从众心理、而官方媒体及政府公信力下降的情况下,双面信息策略为减少谣言产生空间、降低谣言传播可能性以及提升政府和官方媒体辟谣效果,提供了新的理论和实践视角。但本研究还有待进一步深化,需要通过实验设计、问卷调查等方式,进一步探索公众在不同情境和传播信息不同呈现方式下,对于谣言的信任、传播和抵制的态度,以及在不同年龄、教育水平的受众中,不同的传播媒介对双面信息策略辟谣效果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