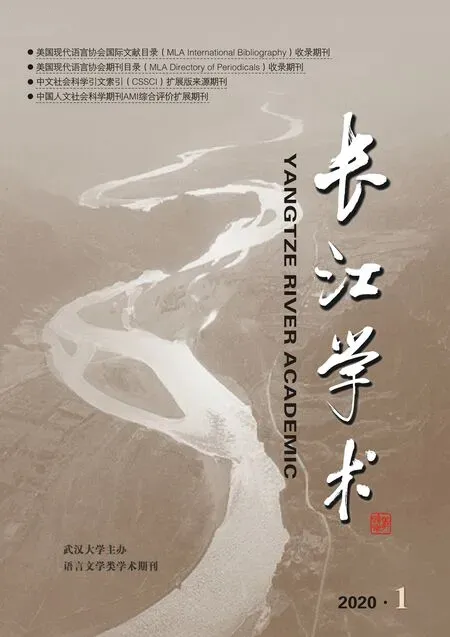谁主沉浮:敦煌莫高窟《维摩变》的图式与语境※
罗世平
(中央美术学院 人文学院,北京100102)
据《维摩诘所说经》(以下简称《维摩诘经》)绘制的《维摩变》,自1943 年在敦煌莫高窟的翟家窟(今编号第220 窟)剥离出唐贞观十六年(642)的大型经变画后,敦煌《维摩变》的系统调查和研究随之展开。著录于《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维摩变》壁画,唐宋的遗存有近60 铺,而以第220 窟的《维摩变》年代最早。以此为起点,敦煌的大型《维摩变》壁画皆以第220 窟为范本,在唐宋数百年间持续得以绘制,虽然壁画内容在不同的时段有增有减,但万变不离其宗,其祖本仍是贞观十六年的《维摩变》,故本文将其称为“贞观样”。①第220 窟《维摩变》是敦煌唐代纪年最早,也是敦煌石窟中不断被重复的主导图式。对于这一图本样式的来源,王逊先生曾撰文将壁画中的皇帝画像与传为唐朝画家阎立本的《历代帝王图》、《职贡图》(中国国家博物馆藏)进行比较,推论该窟的《维摩变》壁画图样可能来自长安。参见王逊《敦煌壁画中表现的中古绘画》,《文物参考资料》1951 年第2 卷第4 期。敦煌《维摩变》的“贞观样”,经过盛唐的摹绘复制,图样得以定型。中唐以降,敦煌经历了吐蕃时期和归义军时期的历史变迁,《维摩变》也发生了图像样式的改变,由此形成了“贞观样”以后的两种变体。这两种变体同样在吐蕃、归义军时期的洞窟中得到摹绘,成为明确表述各自历史语境的固定图式。本文将这两个时期的《维摩变》分别界定为“吐蕃样”和“归义军样”。敦煌《维摩变》的“贞观样”“吐蕃样”和“归义军样”,表面上是祖本和变体的差别,但图式都紧紧扣合着敦煌的历史变迁,表述着各自独特的历史语境。
一、“贞观样”的图式与语境
敦煌莫高窟第220 窟的《维摩变》壁画是莫高窟唐代大型维摩变中格制成熟、现存纪年最早者,位于洞窟主室的东门壁,画面中绘有《维摩诘经》十四品中的九品,即序品、佛国品、方便品、问疾品、不思议品、香积佛品、观众生品、入不二法门品、见阿閦佛品。②《维摩诘所说经》传有三种汉译本,分别为:三国时支谦译《维摩诘经》二卷,十四品;东晋鸠摩罗什译《维摩诘所说经》,三卷,十四品;唐玄奘译《说无垢称经》,六卷,十四品。三种译本中以鸠摩罗什译本流传最广。经变画中的两位主角文殊菩萨和维摩居士隔窟门相对而坐,构图创意参照了佛寺高僧讲论升高座的形式。人物分为两组,文殊菩萨位于门北,面南高坐于莲台,台座下方是唐朝的皇帝及其臣属;维摩居士位于门南,面北持麈尾坐于帐榻,帐榻下方是探疾赴会的西域南海诸国王及其眷属。其余诸品分情节插绘于画面的构图之中。

图1:维摩变 北魏永熙二年(533)
在“贞观样”出现之前,敦煌莫高窟保存有隋代绘制的《维摩变》壁画,莫高窟第420 窟属于隋窟的代表,壁画中的《维摩变》还只是文殊菩萨和维摩诘对谈论辩的简单构图,未出现围绕文殊问疾为主体,摄入多品内容的多情节画面。按现已调查获得的石窟和其它图像资料,敦煌的《维摩变》壁画在“贞观样”出现之前,未发现大型经变画的实例,尚停留在“前图样”阶段。
“前图样”的《维摩变》脱胎于佛说法图。甘肃炳灵寺石窟第169 窟保存有前秦建弘元年(420)的3 铺《维摩变》壁画,是现存《维摩变》最早的纪年作品,画面采用的即是佛说法图的形式。①炳灵寺石窟169 窟《维摩变》壁画图例收录于《中国石窟·炳灵寺》,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这时的图像以佛陀为中尊,左文殊,右维摩,书以榜题提示身份,属于《维摩变》图像的滥觞。《维摩变》形成特色可能始于盛行义理谈论的东晋南朝,画史文献中曾记载东晋顾恺之、戴逵等画家名手创画的维摩诘形象“有清羸示病之容,隐几忘言之状”②〔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五“顾恺之”条,于安澜《画史丛书》本,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年版。,南朝时还有根据经文画出的添品《维摩变》。③〔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第六“袁倩”条,于安澜《画史丛书》本,上海: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1962 年版。若求证于图像遗迹,则有镌刻在四川绵阳杨氏阙石上的梁大通三年(529)前后的《维摩变》石刻画像,共有3 铺,分龛并置。文殊手持如意,趺坐双狮莲台,身后线刻听法人众;维摩诘手持麈尾,前有几案,坐帷帐中,亦有僧众随从。1995 年成都市出土的南朝造像中也有文殊、维摩对谈论辩的图像。这样的构图随后也流行于北朝,纽约大都会博物馆藏北魏永熙二年(533)《维摩变》造像碑,图像分上下两层,上层为文殊、维摩对谈论辩,下层为排列整齐的供养人像行列(图1)。洛阳龙门石窟莲花洞北魏时期的造像龛存有多例,文殊与维摩对坐论辩的线刻,繁简都有,对称地刻在造像龛外。大型《维摩变》的图例有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的遗存。宾阳中洞是北魏皇家开凿完成的洞窟,《维摩变》雕刻在洞窟门壁的两侧,上栏维摩、文殊二人论辩,下栏赴会听法的人众分为两组,一边是皇帝及随从,一边是皇后和眷属。④龙门石窟宾阳中洞《维摩变》浮雕在20 世纪初被古董商盗毁,今仍能见其造像痕迹,图见《中国石窟·龙门石窟》,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 年版。南北朝后期出现的《维摩变》已经具备了大型经变的基本结构,与壁画相比,石刻造像由于材质的限制,相对概略一些,但对坐论辩的格式业已确定下来,离《维摩变》的经典“贞观样”仅一步之遥了。敦煌因僻地偏远,江南及中原地区已经流行的《维摩变》图样,一时还未出现在敦煌石窟中。
莫高窟第220 窟的《维摩变》“贞观样”,好似从天而降,突然来到了敦煌,成了敦煌石窟大型《维摩变》经变画家族的领头羊。自“贞观样”落地敦煌后,这一图样就不断被摹绘。人们会问,它到底有着怎样的奥妙,如此这般地受到敦煌人的青睐呢?笔者以为,其要义在于《维摩变》“贞观样”的特定图式和时代语境,它的“画眼”则是画面人物的身份及所在的方位。
观察敦煌莫高窟的崖面,洞窟的方位坐西面东,窟门皆东向。第220 窟的《维摩变》就画在主室内东壁的窟门两边,画面的人物分为两组:文殊菩萨与赴会的皇帝侍臣为一组,位于窟门壁的北侧,人物皆南向;维摩与外国王子为另一组,位于窟门壁的南侧,人物皆北向。由此构成了“贞观样”的主体画面。按古代的礼仪,人物的南北位向是君臣位。画面上唐朝皇帝北面南向,正是君位,外国诸王南面北向而立,是臣位。画面作如是安排,直观而明显地提示出了人物的主次和尊卑。壁画绘制的年代正值唐朝“贞观之治”时期,当其时,唐帝国的崛起引得周边诸国额庆仰戴,欣欣向荣的大唐帝国如日中天,引得万国来朝,故而有了图中依照国家礼制安排的人物座次。画面一边是皇帝的雍容华贵,一边则是拘谨谦卑的西域南海诸王,形象对比鲜明,所表达的即是“万国来朝”的语境。推敲得如此成熟的画稿图样,应该不是敦煌画工所能措意创绘的。(图2)
“贞观样”创绘的图式遵循中国古代的礼仪,可从唐以前的古礼习俗中寻索到多种佐证。按传统的礼制,人物所据东西南北的方位秩序各有讲究。如前所述,南北向为君臣位,故北面南向者为君,南面北向者为臣。东西向为主客位,待客之礼,东为客位,故东面西向坐者为客,西面东向者为主。历史上按位向之礼而得以避祸称王的典型事例之一是鸿门宴。司马迁《史记》“项羽本纪”写项羽设鸿门宴请刘邦一节,特别详细地记述了人物的方位座次:
项王即日因留沛公与饮。项王、项伯东向坐,亚父南向坐。亚父者,范增也。沛公北向坐,张良西向侍。范增数目项王,举所佩玉玦以示之者三,项王默然不应。
项羽设鸿门宴,原是要杀刘邦,故以主客之礼留东方位以待刘邦,不曾想刘邦用张良计,主动落坐于南面,以示面北称臣。刘邦的落座举动顿时让项羽释怀,因而生不杀之心。司马迁用如此写实的笔法描述鸿门宴的人物座次,刘邦因此逃过了鸿门宴一劫,即隐含了古人遵礼的这层意思。
古人讲究方位座次,历史上还有多例。又如《史记》“孝文本纪”,述汉文帝欲即帝位而让座的表演:
代王西向让者三,南向让者再。文帝为何要再三让座?司马迁笔下很含蓄。《资治通鉴》卷十三“高后八年”条“胡三省注”则言明了汉文帝让座背后的深意:

图2:维摩变 唐贞观十六年,莫高窟第220 窟
盖王入代邸而汉廷群臣继至,王以宾主礼接之,故西向;群臣劝进,王凡三让,群臣遂扶王正南面之位,王又让者三;则南向非王之得也,群臣扶之使南向耳。以为南向坐,可乎!文帝欲即帝位而又故作姿态,三让而不南向坐,这是汉文帝权谋之术的表演,在于笼络人心。是知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位置”的重要。古人遵礼,帝王欲礼贤下士,也在座次上特有讲究。如刘向《说苑》卷一“君道篇”谈君王求才之道,援引郭隗与燕昭王例:
今王将东面目指气使以求臣,则厮役之材至矣;南面听朝,不失揖让之礼以求臣,则人臣之材至矣;西面等礼相亢,下之以色,不乘势以求臣,则朋友之材至矣;北面拘指逡巡而退以求臣,则师傅之材至矣……于是燕王常置郭隗上坐,南面居三年。
燕昭王南边居三年,他在位时人才汇集,燕国得以大治。即使是在入主中原的拓跋鲜卑的北魏朝堂,君臣师徒之礼在尊卑座次上仍不能混乱。如《魏书》“崔光传”记宣武帝延昌二年(513 年)拜太子师事:
(延昌)二年,世宗幸东宫,召(崔)光与黄门甄琛、广阳王渊等,并赐坐。诏光曰:“卿是朕西台大臣,今当为太子师傅。”……令肃宗拜光,光又拜辞,不当受太子拜,复不蒙许,肃宗遂南面再拜。詹事王显启请从太子拜,于是宫臣毕拜,光北面立,不敢答拜,唯西面拜谢而出。崔光谨慎知礼,不得已受太子南面拜师却不敢在北面回礼,而是回到西边的客位上答拜。后来肃宗继位当了皇帝,崔光得以继续受到皇帝的重用。
佛教典籍中也不乏位向礼俗方面的记载。唐道宣《集神州三宝感通录》记述隋僧昙延为国祈雨的神迹:
至六年亢旱,朝野荒然,敕请三百僧于正殿祈雨……帝遂躬事祈雨,请(昙)延于大兴殿登御座南面授法,帝及朝宰五品以上咸席地,北面而受八戒,戒授才讫,日正中时,天有片云,须臾遍布,便降甘雨。
昙延和尚求雨,是在皇帝坐北面南的御座方位上,皇帝则屈尊南面,同五品以上的官员一样席地受八戒。从上述礼仪可知,在古代,方位座次并不是可以随意为之的,尤其在表现国家政治形象的绘画作品上,人物所在的位置直接关系到上下尊卑,更需经过认真推敲。按此再看贞观样《维摩变》的画面,尊卑主次分明,唐朝皇帝画在正中的南向位上,外域诸国王都是仰慕大唐来朝的藩属国或外交国,故画在北向位上。画面图式提示得很明确,给出的正是“万国来朝”的图像语义。
在莫高窟,初盛唐时期的《维摩变》共计有13窟,壁画几乎都遵循贞观样画在东壁窟门,代表作如初唐第335 窟、盛唐第103 窟。第335 窟的《维摩变》,画于窟门北侧仪仗前的帝王,原样照搬了“贞观样”,皇帝双臂张开,姿态雍容;而位于门南维摩一边的各国王及其臣属,都是谦恭礼敬的姿态。盛唐第103 窟,《维摩变》同样绘于门壁,壁画构图、人物位置皆如“贞观样”,仅在画法上有所变化。可见“贞观样”是在敦煌画师工匠中流传有年的经典图式,大唐盛世的气象在绘画上表现得格外醒目。所以有理由认为,“贞观样”《维摩变》这一祖本曾在初盛唐的敦煌画工中长时间流传使用。
另有一点需提及,第220 窟《维摩变》被覆盖之年是在宋代,在壁画覆盖之前,终唐一代的敦煌画工都有观摩临习“贞观样”的机缘。220 窟曾经在中唐、五代和北宋有过三次补绘,门道南壁的两处小龛和壁画是吐蕃时期的补开新绘,五代时门道北壁又添绘了一铺新样文殊像。至少在这两次补绘时,工匠进入洞窟都能直接观赏到《维摩变》这一原作,故在讨论敦煌随后发生的《维摩变》变体时,“贞观样”的确是不可不提及的经典图式。
二、“吐蕃样”的图式与语境

图3:维摩变(局部) 唐贞观十六年,莫高窟第220 窟
中唐时期的敦煌,进入吐蕃占领的特殊历史阶段,时间长达60 余年之久。①从唐建中二年(781)敦煌陷于吐蕃,至唐大中二年(848)张议潮率义军收复瓜、沙二州,敦煌复归唐朝,吐蕃据有敦煌前后67 年。按《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莫高窟在蕃据时期的营建可分为两个阶段,分期的时间节点是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的唐蕃会盟。在会盟之前,新开的洞窟中基本不见绘制《维摩变》的壁画,调查所见属于中唐蕃据时期的10 铺《维摩变》,都出现在唐蕃会盟之后的洞窟中,其中除第186 窟整幅画在洞窟主室的南壁,第231窟整幅绘在主室东门的北壁,第240 窟分画在主室西壁龛外的南北壁上,其余的7 铺,即第133、144、159、236、237、359、360 窟,均绘于主室东壁门的两壁。这些《维摩变》主体仍是“贞观样”的图式结构,改变的只是位于维摩居士帐榻下的人物部分。壁画中特别突出了吐蕃赞普及其侍从,他们画在各国诸王的队首,与文殊菩萨座下的唐朝皇帝隔门相对,形成文殊-皇帝组合位于门北,维摩-赞普组合位于门南的对称图式。①中唐吐蕃时期《维摩变》的这一变化多有研究者给予关注并做过尝试性解释,详见樊锦诗、赵青兰:《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的分期研究》,《敦煌研究》1994 年第4 期。为便于下面的讨论,本文将绘有唐朝皇帝、吐蕃赞普的《维摩变》称为“吐蕃样”。(图3)
《维摩变》的“吐蕃样”是“贞观样”的第一个变体,也可以说是《维摩变》的新图样。所谓变体,是指主体的图样不变,变动的部分是画中的图像或人物。在“贞观样”中,与文殊相对的维摩居士下方是一组没有首领的各国王及其酋帅,而在“吐蕃样”中,这组人物是以吐蕃赞普为首领的诸国王。以第360 窟《维摩变》为例,位于文殊下方的皇帝仪仗基本没变,而在维摩的下方,队列前的中心人物是一位戴缠头红帽(朝霞冠),着翻领白袍,脚下踏方座的吐蕃赞普。在他的身前有侍卫作先导,身后是打曲柄伞盖的侍从,拖后的才是各国诸王人众。从图式而知,这时的《维摩变》是从“贞观样”而得来的变化,所以是“变体”。它又是新图样。理由是因为维摩下方吐蕃赞普及其侍从的出现,画面形成隔门对峙的构图。一边是礼仪庄重的唐朝皇帝,一边则是跸从森严的吐蕃赞普,“贞观样”中“万国来朝”的盛大气象消退了,而换成了“天下二主”的格局。皇帝与赞普的同时出场,图式被更新,自然不再是“贞观样”的语境了。此时的敦煌,处在吐蕃人的统治之下,与唐朝音问不通,壁画中吐蕃赞普及侍从人物的新图样,则完全出自敦煌画工之手。所画的场景、人物服饰及赞普仪仗等等,也是得自对吐蕃礼俗的移写,这样的《维摩变》只见于敦煌的洞窟中,所以又是新图样。(图4)

图4:维摩变 中唐-吐蕃,莫高窟第159 窟
不过“吐蕃样”的《维摩变》无论是看成“贞观样”的变体或是新图样,图式和语境依然抹不去“贞观样”的底色。对于蕃据时期的敦煌汉人而言,奉唐朝为正统,认祖归宗,是“身份认同”最根本,也最深刻的记忆,这种记忆会时时从敦煌人陷蕃的伤痛中被唤醒。举两个实例。其一是敦煌陷蕃的经历。吐蕃占领河西的战争,敦煌城被围,军民同仇敌忾,进行了11 年的守城抗战,直到“粮械皆竭”,在吐蕃答应敦煌人“毋徙佗境”的条件下,敦煌才归附吐蕃,这是河西最后一座沦陷的城池。其二,是蕃据时期敦煌人的“归唐情结”。吐蕃据有敦煌前后60 余年,这期间敦煌人曾因抵制吐蕃人“辫发易服”等政策,发生过多次驿户起义,玉关起义是其中规模最大的一次。虽然起义未果,但敦煌人的归唐情结始终没变。如《新唐书·吐蕃传》记述敦煌汉人:“州人皆服臣虏,每岁时祀父祖,衣中国之服,号而藏之。”唐熹宗乾符年间(874—879)左散骑常侍李众甫去敦煌,见沙洲开元寺保存唐玄宗的像,“叹念敦煌虽百年阻汉,没落西戎,尚敬本朝,余留帝像……人物风华,一同内地。”①《张淮深变文》,《敦煌变文集》上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 年版,第124 页。这该是敦煌人民族身份认同的真实写照。当唐朝与吐蕃在唐穆宗长庆二年(822)结盟修好,民族关系发生转机之时,敦煌汉人身份认同的心情更为迫切,期盼唐蕃和好的愿望成了这个时期石窟营建最明确的主题。根据吐蕃占领时期莫高窟洞窟壁画分期调查,《维摩变》壁画主要集中绘制于唐蕃会盟后的第二期洞窟中。吐蕃样《维摩变》的出场主角和人物身份一目了然,图像中隐含了蕃据时期敦煌人的“归唐情结”与“身份认同”。②详见罗世平:《身份认同:敦煌吐蕃装人物进入洞窟的条件、策略与时间》,《美术研究》2010 年第4 期。壁画图像中的种种曲折和历史隐情,见证着敦煌功德主和画工高度的艺术智慧。
基于这样特殊历史下构画的《维摩变》,其图式语境就要比“贞观样”复杂很多,以下从三个层面对“吐蕃样”《维摩变》试作分析。
图式分析一:“吐蕃样”《维摩变》的人物方位直接取法于“贞观样”,在于表达敦煌功德主仍奉唐朝正统的心态。以第159 窟《维摩变》为例,文殊-皇帝组居北,人物皆南向。如前所述,按中国礼制,此位为君位,即是“君子北面为尊”的位向;维摩-赞普组居南,人物北向,即是“坐南面君”的方位。蕃据时期敦煌的《维摩变》按此图式画成的洞窟另有第133、144、236、237、359、360 窟。第231 窟的《维摩变》虽将隔门相对的构图合为一幅,置于东门壁的北侧,但并没有改变壁画的基本结构和人物位向,仍是《维摩变》吐蕃样的图式。蕃据时期的《维摩变》壁画共有10 幅,而吐蕃样就占了其中的8 幅,说明“吐蕃样”是敦煌人最为认同的图式。
“吐蕃样”在莫高窟也有变动改编的图像。如第186 窟,维摩变画在南壁,是一幅没有拆分开的完整构图,移画时画工并非原样照搬,平移上壁,而是重新改过了图像的方位座次,将文殊-皇帝组绘于南壁的西边,人物东向;维摩-赞普组置于东边,人物西向。如前所述,古代的礼仪,东西向时,东向者为主位,西向者为宾位。这样的位向在古代的昭穆制度上是父位与子位的关系。如《汉旧仪》:
宗庙三年大袷祭,子孙诸帝以昭穆坐于高庙,诸隳庙神皆合食,设左右坐。……子为昭,孙为穆。昭西面,曲屏风,穆东面,皆曲几。①《后汉书·祭祀志》(下)注引《汉旧仪》,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
昭穆制是以祖先为中心的排位方式,《决疑要注》对此说得很明白:“始祖特于北,其后以次夹始祖而南,昭在西,穆在东,相对。”②《后汉书·祭祀志》(下)注引《决疑要注》,北京:中华书局1987 年版。昭穆制不仅在宫廷施行,也在宗族家祠中使用,敦煌画工在就壁移画时一定对此作过考量,所以186 窟《维摩变》的人物位置才有了这样一番对调。座次经此调整,壁画中皇帝居于父位,赞普处在子位。如果按当年唐蕃联姻的辈份而论,唐朝是舅,吐蕃是甥。也正合了敦煌文书中屡见的“舅甥之国”的说法。③P.2255 文书:“……使烽飙不举,万里尘清,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生(甥)之好。”谁主谁次,其实敦煌的画工理得很清楚,而作这样的移画,目的也一定很明确。作画的过程,比起直接搬用现成的图式更要多费些事,自然不应该视为画工的即兴所为。将吐蕃样《维摩变》图像汇集在一起,足以说明蕃据时期敦煌功德主和画工所认同的王朝正朔仍是唐朝。图式给出了“谁是正统”的第一层语义。
图式分析二:敦煌“吐蕃样”《维摩变》绘唐朝皇帝北面南向,吐蕃赞普南面北向,属于定型的图式,它的流行还有地理方位的依据。唐与吐蕃,在地理方位上,唐朝在北,吐蕃在南。敦煌人在陷蕃后习惯称吐蕃为“南国”,而以“北疆”代称唐朝,有敦煌文书为证。如P.2807《行城文》:
……先用庄严皇太子殿下,伏愿长承南国之重奇(寄),永奉北疆之慈颜,福将山岳而齐高,寿比松筠而转茂。
这件文书写于唐蕃会盟之后。唐穆宗长庆二年,唐、蕃在清水关会盟,刻会盟碑记其事,吐蕃又立藏、汉文二体碑于拉萨大昭寺前。会盟后,唐蕃重结舅甥之好,故有愿吐蕃皇太子“永奉北疆之慈颜”的文字。唐蕃样《维摩变》安排汉人皇帝北面南向,吐蕃赞普南面北向,因有了地理方位上的客观依据,敦煌画工也就有了按此方位结构画面的正当理由。这点正是敦煌画工的高明处,既能避开吐蕃人的审查管制,又通过壁画表达了自己的心愿。这是图式给出的第二层语义。

图5:维摩变 中唐,莫高窟第159 窟
图式分析三:文殊-维摩对位与皇帝-赞普对位,表现文殊问疾的情节,要义在文殊与维摩由辩难到息诤,起到宣说《维摩诘经》不二法门的宗旨。下方皇帝与赞普同往问疾,并赴盛会,其寓意在于唐蕃由交兵到会盟,永结舅甥之好的时代主题。(图5)对蕃据时期的敦煌人而言,唐朝皇帝与吐蕃赞普是关系他们生存境遇的两位关键人物,画中的主角也即是蕃据时期敦煌的主角。敦煌画工巧妙地将图像与经义、心愿与历史结合起来,经文与图像间对应得既贴切又不露痕迹。潜藏于图像中的真实用意,线索在敦煌文书和会盟碑中皆能读到。例如P.2255 文书:
……使烽飙不举,万里尘清,四邻绝交诤之仇,两国结舅生(甥)之好。①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357、357、356 页。
又S.6315《愿文》:
……又将殊胜功德,最上福田,奉用庄严我当今神圣赞普,伏愿永垂禅化,四海一家……使两国还好,重圆舅生(甥),四方艾安,保无征战。②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357、357、356 页。
又《唐蕃会盟碑》誓词:
彼此不为寇敌,不举兵革,不相侵谋……如斯乐业之恩垂于万代,称美之声遍于日月所照矣”。③樊锦诗、荣新江、林世田主编:《敦煌文献·考古·艺术综合研究:纪念向达先生诞辰110 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2011 年版,第357、357、356 页。
祈愿唐蕃和睦相处,永离战争之苦,这是吐蕃样《维摩变》图式给出的第三层语义。
观察上述的图式语境,历史情境的骤变成为图式语境新变的内因,敦煌的功德主和画工通过经变人物的出场和站位,将“贞观样”杨柳翻新,推出蕃据敦煌时期的“吐蕃样”。从“贞观样”中演绎出新的语境,概因特定的时代背景和敦煌的民情物态使然。图式语境的改变,线索虽留在画面出场人物的形象特征和座次位向上,重点则是落在图像所生成的特殊语境上。蕃据时期的敦煌汉人借重于《维摩变》,艺术地传达了对家国的系念和身份认同,将现实困境所造成的内心纠结释放在经变图像中。
三、“归义军样”的图式与语境
敦煌“吐蕃样”对《维摩变》的成功改编为敦煌归义军,尤其是曹氏归义军时期的《维摩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范例。④吐蕃于唐大中二年(848)退出敦煌,敦煌开始了归义军时期的历史。前期由张议潮家族掌管敦煌事务,习称张氏归义军时期(848—907)。后期由曹议金家族掌管敦煌,习称曹氏归义军时期(914—1036)。敦煌现存归义军时期的维摩变计有30 余铺,是敦煌石窟描绘《维摩变》数量最多的时期,其中最具有时代标志的《维摩变》多见于曹议金家族或其姻亲眷属的功德窟中。如莫高窟第61、85、98、100、108、138、146、454 窟等,皆有经过改编的大幅《维摩变》。⑤上述洞窟的功德主名属问题,从20 世纪50 年代以来便有讨论,意见虽然不完全一致,但在属于曹氏归义军或其姻亲眷属的功德窟这点上认识基本一致。详见金维诺《敦煌窟龛名数考》,《文物》1959 年第5 期;万庚育《珍贵的历史资料——莫高窟供养人画像题记》、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这个时期的《维摩变》,画面结构发生了两处重大修正。变化之一,对调了文殊组与维摩组的方位。这时期的文殊组位于主室东门的南壁,人物北向,维摩组位于东门的北壁,人物南向。按前述“贞观样”所显示的中国古礼的方位,维摩组人物处在了主位,文殊组人物则在次位。这一方位的调整,完全改变了“贞观样”《维摩变》图式的语境。如何看待图像上的这一位置变动,似需再对敦煌归义军时期的敦煌形势作出判断。谁主谁次?这是归义军时期的《维摩变》将被追问的潜台词。
变化之二,方位对调后的《维摩变》,文殊菩萨座下的世俗人物换成了着汉式朝服的一组官员,中心人物虽然也穿戴帝王的衮冕,但已不是之前的皇帝气象,随行的仪卫是受北宋赐封的归义军节度使及其随从。维摩诘下的外族人物变成了于阗、回鹘等西域诸王及其部从。第85 窟是归义军时期《维摩变》的代表作之一,该窟属于曹氏归义军首领的家族窟,《维摩变》整铺画在主室门壁的北侧,新变的因素比常见的隔门相对样式更为直观。归义军时期《维摩变》图式的独特语境,成为敦煌《维摩变》继“吐蕃样”之后的又一新图样,即本文所称的“归义军样”。(图6-1、图6-2)

图6-1:莫高窟第61 窟《维摩变》(局部)
归义军样《维摩变》出现在唐末五代藩镇割据、中原板荡、天下无君的乱世,原来的“贞观样”和“吐蕃样”中的唐朝正朔已经不再,敦煌的归义军政权如何自处成了这个时期的主题。大约从曹议金继张氏执掌瓜、沙河西节度政权的914 年起到11 世纪上半叶,曹氏一族前后统治瓜、沙长达120 余年。①按贺世哲考订,曹议金代张承奉执掌归义军的时间为梁乾化四年(914)。参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其中曹元忠(945—974)执政31 年,曹延禄(979—1002)掌节度23 年,这期间是敦煌营建石窟的高峰期,留下了大量的遗迹,时代的烙印深深留在了石窟之中。以当时敦煌的地缘关系来看,东有甘州回鹘,西有于阗,北有契丹,归义军政权虽有心依靠中原朝廷,但敦煌孤悬边地,仅在名份上受中原皇帝的庇护。为求得自保,曹氏归义军政权一方面尽力维护与中原的政治联系,遣使修贡,曾先后于开宝三年(970 年)、太平兴国五年(980 年)接受北宋朝廷“西平王”“敦煌王”的封号。②莫高窟第427 窟墨书题记:“维大宋乾德八年岁次庚午正月癸未朔二十六日戊辰敕推诚奉国保塞功臣归义军节度使特进检校太师兼中书令西平王曹元忠之世创建此窟记。”此乾德八年即宋开宝三年(970),是知曹元忠曾受宋朝廷封“西平王”。曹元忠被封“敦煌王”在宋太平兴国五年(980)夏。据《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十一,同时封其子曹延禄为归义军节度使,延晟为瓜州刺史,延瑞为衙内都虞侯,母封秦国夫人,妻封陇西郡夫人。一方面斡旋在于阗、回鹘、契丹政权之间,利用联姻等外交手段维护其政权的稳定,保住一方安宁,在河西的政治格局中如履薄冰。曹议金娶回鹘公主,嫁女于阗王等等,都是出于地缘政治,保一方平安的实际考量。有敦煌曲子词《望江南》歌颂敦煌曹氏的功绩:“曹公德,为国托西关,六戎尽来作百姓,压坛河陇定羌浑,雄名远近闻。尽忠孝,向主立殊勋,靖难论兵扶社稷,恒将筹略定妖氛,愿万载作人君。”③任二北:《敦煌曲校录》,上海:上海文艺联合出版社1955 年版,第56 页。就归义军而言,他们既不愿失去一方诸侯的尊严,又不敢妄自尊大,这种复杂的心理在曹氏家族窟中得到明显的表现,《维摩变》“归义军样”正可看作归义军统治者心路历程的真实记录。

图6-2:莫高窟第61 窟《维摩变》(局部)
通过改编移画的《维摩变》“归义军样”,图式语境完全符合归义军治下的敦煌形势,生存在夹缝中的曹氏家族,深知中原王朝与西域强族之间力量的轻重。按“贞观样”《维摩变》推定的主次方位,“归义军样”放下了天朝正统的身段,将坐北朝南的上位让给以回鹘、于阗为首的西域强族,将归义军拥戴的中原王朝皇帝移至南面北向的下位。这一修正的图式语境表明了敦煌曹氏政权示好西域强族的立场,若权衡当时的力量对比,或者也可以理解为归义军的一种“自保”策略。
“归义军样”的图式语境另有与之相辅助的两类图像可供参校,其一是画在《维摩变》下方的供养人像。例如第98 窟,《维摩变》绘于主室东门的南北两壁,门南文殊下为于阗国王李圣天及男女供养人11 身,门北维摩诘下画回鹘公主等男女供养人7身。按贺世哲考订,第98 窟的功德主为曹议金,①关于第98 窟功德主名属问题的辨析,详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他在营建洞窟时特别将回鹘公主和于阗王的供养像与《维摩变》相配置,题材选择和位置安排皆有特殊讲究。
曹议金初在张承奉割据政权下供职,后接掌归义军政权,东面结好甘州回鹘,娶回鹘圣天可汗女陇西李氏为妻,又嫁女甘州回鹘可汗,莫高窟、榆林窟中留存的多处回鹘公主、甘州圣天可汗公主的供养像题名是这个时期的见证。曹议金同时对敦煌以西的于阗示好,嫁女于阗王李圣天,曹议金孙曹延禄后又娶于阗公主李氏(第61 窟供养人中题署曹延禄姬者即是)。通过联姻,于阗与敦煌保持了较长时间的友好往来,于阗太子、公主长期居住在敦煌,敦煌文书P.2704《曹议金疏》所谓“于阗使人,往来无滞”,是这时敦煌的实写。于阗王、皇后、太子、公主的供养像在莫高窟第61、444、窟,榆林第31 窟中都有实例保存。②参见敦煌研究院:《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版。关于曹氏归义军时期的历史及外交,详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第216—236 页。第98 窟门壁绘回鹘公主和于阗王供养像,进一步强化了“归义军样”《维摩变》所提示的曹氏自保的意图。
第100 窟《维摩变》门南文殊,其下配画的题材是《曹议金统军图》,门北维摩诘下,是《回鹘公主出行图》。第100 窟是曹元忠为纪念乃父曹议金所建的功德窟,③莫高窟第100 窟即《腊八燃灯分配窟龛名数》卷子所称的“大王天公主窟”。有关该窟窟主的考证,详见贺世哲:《从供养人题记看莫高窟部分洞窟的营建年代》,载敦煌研究院编《敦煌莫高窟供养人题记》,北京:文物出版社1986 年版。壁画题材作如此配置同样是有意为之的,进一步说明在曹元忠执掌敦煌时,回鹘在敦煌曹氏家族中的份量。
第454 窟《维摩变》门南文殊菩萨座下于阗国王等供养像6 身,门北维摩诘下,回鹘公主供养像6 身。该窟为曹元忠之子曹延恭及夫人慕容氏的功德窟,④第454 窟功德主据该窟甬道南壁第5 身男供养人题名:“窟主敕归义军节度瓜沙等州观察处置管内营田押蕃落等中书令谯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实封五百户延恭一心供养”;窟内南壁第4 身女供养人题名:“窟主敕授清河郡夫人慕容氏一心供养”。供养人画像的位置格局仍依照98 窟,似可认为到曹氏第三代,回鹘和于阗仍是当时归义军特别仰仗的政治力量。
第二类图像是归义军洞窟中集中绘制的于阗瑞像和于阗守护神像。据《敦煌莫高窟内容总录》的辨识统计,于阗瑞像有坎城瑞像、媲摩城释迦瑞像、海眼寺释迦圣容像、牛头山瑞像、舍利弗与毗沙门天王决海像等。于阗的守护神通常画在窟门甬道的盝顶上,根据榜题,知有迦迦那莎利、莎那末利、莎耶摩利、阿隅阇、毗沙门、阿婆罗质多、摩诃迦罗、悉他那八位,是直接根据于阗八大守护神图样绘制的。这些瑞像和守护神像有规律地绘饰在洞窟中,是曹氏家窟中常见的题材,也是归义军时期的洞窟中频繁出现的新图像。
上述例举的曹氏“归义军样”《维摩变》,图式语境并不单独存在于《维摩变》中,而是有着更多来自于阗和回鹘的题材和图像加入补充,相互印证。这些新引入的题材和图像或隐或显地向观者提示,“归义军样”《维摩变》的图式紧紧扣合着归义军时期敦煌的历史和地缘政治。经变人物细节上的种种改变并非偶然,而是敦煌画工和功德主在特定历史背景下富有深意的创造。敦煌壁画和文书中见存的画院工匠题名,进一步加重了敦煌创绘“归义军样”《维摩变》的意愿和目的。
敦煌《维摩变》由“贞观样”引导的图式变化,直接或间接地与敦煌河西的历史联系在一起,曲折而隐晦地传递着不同族群和政治势力在敦煌地区的消长。敦煌的功德主和画工借助佛教的功德行为,总能将时代的主题和现实生活投射其中,生动而独特。《维摩变》经由“贞观样”而“吐蕃样”而“归义军样”,其图式语境的阶段性转换,自身已构成了一段趣味隽永的历史,这是敦煌的《维摩变》与其它地区的《维摩变》在图式语境上的截然不同。
问敦煌,谁主沉浮?《维摩变》可为之注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