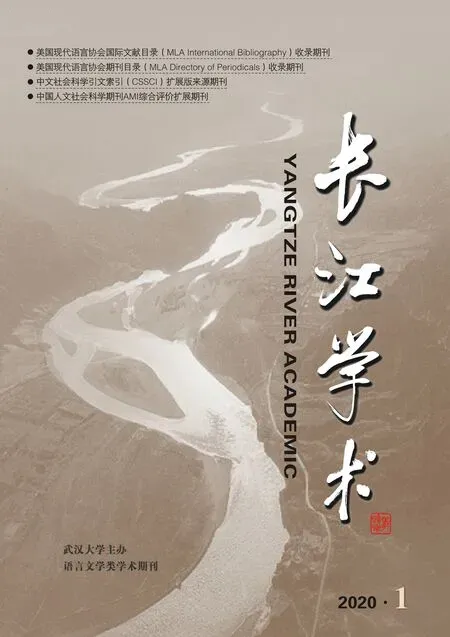“马赛克”与“万花筒”:巴别尔特写的叙事修辞
王树福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430079)
作为“一位臻于完美的故事大师”,“俄国散文的最新伟大成就”,①〔英〕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324 页。巴别尔的创作大致可以分为小说、剧作、特写以及书信四个部分。其中,小说部分是巴别尔全部创作的核心和艺术的精华,为他带来世界性的文学声誉,是进入其艺术世界的主要基础;剧作部分是巴别尔文学创作的重要构成,是其文学实验和艺术创新的重要方式;特写部分是巴别尔文学创作的重要补充,是其小说创作的重要补充和创作生涯的艺术注脚;书信部分则是巴别尔精神世界的直接显现,是进入巴别尔内心世界的便捷路径。一如著名学者刘文飞教授所言,“阅读巴别尔的书信,是步入他的内心世界、理解他的文学创作的一条捷径。”②刘文飞:《巴别尔的生活和创作》,《中国俄语教学》2016 年第1 期。在巴别尔创作中,特写部分主要指随笔、札记、素描、速写、报道、纪实等亚文学文体或文学衍生类型,主体是为报纸而撰写的“新闻、速写与随笔”,包括“彼得堡系列特写”“格鲁吉亚系列特写”和“法兰西系列特写”。在体裁类型上,这些特写可归入亚文学、次文学或类文学创作,介乎诗歌、小说和戏剧三种文学主要体裁之间或之外,兼具三者某些特点或与三者有部分关联,具有比较明显的跨界性和杂糅性。

就特写主题而言,在“彼得堡系列特写”和“格鲁吉亚系列特写”中,巴别尔以新闻速写的纪实方式和特写札记的剪影技巧,将其在革命风暴中心彼得堡的所见所闻,在第比利斯和巴统的经历感受,巧妙而大胆地抒发胸臆,严肃表达对时局、社会和民众的强烈反思。在“法国系列特写”中,巴别尔以新闻记者的敏感和严肃作家的多思,将其在法国各地的访问经历和个体感受付诸笔端,含蓄表达对苏联社会问题的思考。所有这一切,以明显的纪实性和强烈的片断性,体现出不同于时代主流的思想诉求,具有强烈的不合时宜性和个性主义色彩。
一、叙事的亲历与旁观:视角转换与个性表述
在巴别尔的特写故事中,几乎都存在第一人称叙事者“我”。“我”带有比较明显的知识分子特色与旁观者的局外眼光,表现出比较冷静审慎、反思质疑的总体态度。从特写故事描述来看,“我”既以旁观者的身份与眼光,比较客观地记录着革命后的彼得堡和格鲁吉亚或1930 年代法国发生的社会乱象和民众哀苦,也被革命与战争裹挟与胁迫着,被动或主动参与着革命洪流与革命事件,沉浮于波诡云谲的历史波涛之中。
(一)视角转换与叙议杂糅
就叙事艺术而言,“彼得堡系列”中多种叙事视角并存,叙事、议论与抒情杂糅,耐人寻味,值得关注。前者的转换嵌套带来叙事话语的层叠,悄然影响着后者的个性诉求;后者的聚合分离呼应着叙事视角的闪现,隐秘规约着个性话语的表述。
其一,多种叙事视角并存。受特写札记的制约与新闻报道的影响,“彼得堡系列”多采用第一人称视角、第三人称视角或全知全能视角并存的叙事策略。根据彼得堡系列特写,“我”是一个年轻人,对社会现实和革命战争抱有热情、激情和理想(《线与色》);“我”是“一位无家可归的诗人”(I:269),④半夜时分在彼得堡阿奇尼科夫宫皇后宫殿,在尼古拉耶夫车站睡觉(《在皇后住处的一个晚上》);“我”在宰马场游荡,报道战争期间马匹被杀的记者(《马》);“我”去彼得堡太平间,统计枪击死者数字(《死者》);“我”在彼得堡动物园,目睹动物因经济崩溃、缺少食物而或被饿死,或被毒死,或被征用,或被杀死(《沉默的动物》);“我”是“一个俄国人”(I:315),参与并见证1918 年俄芬边境的革命动乱(《芬兰人》);“我”“作为一个游荡的旁观者”(I:318),战争间隙在彼得堡市郊,与士兵们在荒地上修建菜园(《新生活》);“我”“从铸币街转道涅瓦大街”(I:320),见证断臂男孩的乞讨遭遇(《涅瓦大街偶遇》);“我”“在彼得堡组建了一支残疾人志愿队,到伏尔加流域来征集粮食”(I:328),参加萨拉托夫省卡捷琳娜施塔德酒店音乐会(《卡捷琳娜施塔德的音乐会》)。一言以蔽之,“我”是一个20岁左右的年轻俄国知识分子,对革命与战争充满理想主义色彩,革命期间滞留彼得堡,目睹了发生在彼得堡市内及市郊的种种社会乱象。
“彼得堡系列特写”关涉种种社会现象,凡宰杀马匹、枪杀民众、家庭破裂、婴儿奶水、囤积居奇、巧取豪夺、文化破坏、宗教信仰,几乎无所不包,无所不涉。如何应对革命后出现的流血事件,怎样救助游荡在城市街道的孩子,是考验新生政权的重要一关。对此,首刊于《新生活》1918 年3 月9 日“日记”专栏的《急救》,对此给予颇具嘲讽性的描述与回应。特写一开篇,作者以第一人称视角感慨,革命期间人们相互残杀,过去现在皆如此;“如果您想了解在彼得堡是如何救助的,彼得堡的救助有多么快,我可以讲给您听。”(I:272)对革命后乱杀马匹的现象,叙事者进行了实地跟踪与田野考察。“我在牲口棚里游荡,它死一般地空寂,空得惊人。”(I:274)几经波折,“我在找宰马场。而过了四分之一小时,我在空旷的院子里也没见到一个可以问路的人。最终还算幸运,画面一变,这里已不再空寂;相反,我看见了站在马栏里的几十匹、上百匹无精打采的马”(I:275,《马》)。由于战争频仍,经济崩溃,普通民众生活艰难,孕妇更是缺衣少食,营养不良,由此导致奶水不足,无法给婴儿提供充足的奶水。对此,《早产儿》中“我”只身来到妇产宫,进行考察报道。临走之前,这些可怜的孕妇们“向我讨要购物票,讨要补贴票,苦苦哀求着”,然而无奈之下,“我向外走”(I:278)。此外,“彼得堡系列特写”中的少量篇什,采用第三人称视角或全知全能视角。此类特写比例较少,诸如《公共图书馆》《伙计》《格鲁吉亚人、克伦卡和将军的女儿》。
其二,叙事、议论与抒情并置。该系列特写普遍存在内在叙事线索与外在抒情线索,前者侧重冷静客观的场景描绘和故事叙述,后者多为充满激情的沉思嘲讽和抒情议论,由此将故事叙述、时世议论与个人抒情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内外主辅结合、叙事议论抒情并置的叙事艺术。《急救》首刊于《新生活》1918 年3 月9 日“日记”专栏。对革命期间的暴力行为,故事开篇表明态度:“每一天,人们都互相刺伤,都把对方从桥上扔下黑黢黢的涅瓦河;每天都因为错误或不幸的出身而流血,过去如此,现在如此。”(I:272)按照常规配备,急救站应该有工作人员、急救大夫、急救汽车或应急马匹、必备药品、日常经费、办公用品、汽油物资等等。颇为可笑的是,“我们没有这种博物馆,我们什么都没有,快速抑或救助。有的只是——日常生活的根基遭受强烈震荡的三百万人口的城市;有的是大街上和房子里流淌出的大量鲜血”(I:274)。最具讽刺意味的是,“为调度该机构的行动,专门备有一本书——回绝指南,里面列举着不提供救助的情况。厚厚的一本书,最重要的唯一的一本书,其他的用不到”(I:273)。
《夜晚》首刊于《新生活报》1918 年5 月21 日,主要叙述两个彼此对照的图景:在彼得堡军官街,工人卫队随意拷打小伙计,警段警察任意杀死男孩;在咖啡馆中,日耳曼士兵衣着华美,色彩鲜艳,寻欢作乐。这样的“故事很平常”,“我不准备下结论,我做不来”(I:303)。目睹小伙计被拷打,“心阵阵地疼,绝望攫住了我”(I:304);从警段出来,“我感到忧伤,走进咖啡馆。里面的景象让人震惊”(I:305)。处于战争动乱中的首都彼得堡,“透明的夜色下,花岗岩露面的大街在奶白色的薄雾中伸展,空空荡荡”(I:305)。目睹此情此景,叙述者心中既绝望又无奈:“万籁俱寂。渐渐隐去的夜色中,刺眼的汽车灯光倏忽飘过,无踪无迹。无形的夜幕笼罩着金色的屋顶。寂谧的荒凉之中隐藏着最浅薄也最无情的思想。”(I:306)看似平静的叙述与点到即止的议论、大胆奇特的抒情,恰到好处地交融在一起,氤氲着无尽的感伤、痛苦与绝望。
(二)西方技巧与民间因素
西方技巧与民间因素的融合,构成“格鲁吉亚系列特写”的主要叙事特色。前者主要体现为蒙太奇手法与视角转换,后者主要体现为讲述体(即故事体)与喜剧夸张。
蒙太奇手法将两种或数种不同或相悖的情节或因素,先后并置,同时叙述,使特写故事充满跳跃的联想感与强烈的既视感;视角转换策略不仅暗示着主人公的身份立场、视野趣味、道德伦理,而且巧妙地呈现出文本之内与文本之外的跨界与关联。在《在疗养院》中,夜色中的阳台,闪烁的星星,雪青色的群山,簌簌响的水墙,潺潺的溪水,浅蓝色的烛火,由远及近,远近相交,彼此辉映,构成一幅颇具线条感与色彩感、充满主体感与印象感的美妙画面。“阳台外,满盈着迟缓的喧哗声和庄严的黑暗的夜。滴滴沥沥的雨逡巡在雪青色的山间,灰蒙蒙簌簌响的水墙的丝绸,以严峻而冰凉的昏暗笼罩着沟壑。在奔流着的小溪不知疲倦的絮语声中,我们的蜡烛浅蓝色的火焰,像远方的星星在沉甸甸、含有深意的錾子凿出的起皱的脸上隐约颤动。”(III:328)叙述者以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出场,雨夜阳台五人喝茶,烛光中谈疗养说未来,论新旧谈变化。“三个温文的裁缝、迷人的M,还有我”(III:328),不经意间透露出叙述者的视角与身份。特写随即笔锋一转,叙述转换为议论,视角随时改变:“如果你们看见我们在这儿怎么休息……如果你们看见被机器银灰色的下颌嚼烂的脸颊在发光……”(III:328)类似情形令人过目不忘,回味无穷,在其他特写故事中亦经常出现。
讲述体以浓郁的民间气息和面向广场的姿态,夹叙夹议,铺陈奇崛,使叙述者呈现出多重文风、不同口吻、数种面具;喜剧夸张让文本生动活泼,有声有色,让凡人凡事增添了神奇的靓丽之色,让非凡人非凡事具有了传奇的异域之风。二者的有机结合生成的文本张力,使特写的广度、力度和深度超出了文本篇幅的局囿。《没有祖国》的叙事艺术颇为有趣,在相当程度上可以与《骑兵军》系列故事相提并论。该特写故事以俄国古老的讲述体开篇,简洁生动,内涵丰富:“……结果是,我们抓到了小偷。”(III:335)这种富有力度的简洁与颇具深度的明晰,颇有普希金的《暴风雪》开篇之风:“我们驻扎在XX小镇”,①与列夫·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开篇颇为相似:“奥勃朗斯基家的一切都乱套了。”②接下来,特写的描写夸张而幽默,让人忍俊不禁:“小偷的后脖领子大极了。里面容得下两艘客货轮。侵略者傲慢的旗帜沮丧地低垂着,桅杆的顶端有另一面染上战争的血迹和紫红色的胜利的旗帜在飘扬。”(III:335-36)然而,没有护照的旧俄老司炉,被新政权强制驱逐出境,内心倍感绝望:“如果我们是哪一个国家的国民,这条秃顶的狗就不敢这样欺负我们。”(III:338)这句带有抱怨与牢骚的话语,虽然有人身侮辱之嫌,但却让人不禁深思,为之深深动容。
(三)“局外人”或“旁观者”
在叙事策略方面,《法兰西纪行》以“局外人”或“旁观者”的身份,多采用第一人称限制性视角“我”或“我们”,部分采用第二人称限制性视角“您”或“你们”,两者或通篇并置,或彼此转换,带有比较明显的新闻报道的痕迹与报告文学的倾向。彼时彼刻,苏联完成从白银时代多声道文学向苏维埃一元化文学的转型,苏联文坛的自由宽松之气逐渐消弭,肃杀冷峻之气逐渐生成。
《“灯塔之城”》开篇即点明叙述者的个人化视角:“从童年起我就听人谈到大城市”(III:377),让人对法国和巴黎平生一种浪漫自由之想象:“法国人称之为‘灯塔之城’,在西方它被认为是世界之都……”(III:377);紧接着以群体化视角叙述法国之行的进程:“就这样,我们的火车驶到巴黎北站。我们下到站台,似乎很扫兴”,“我们离开火车站”,“我们不曾见到我们所期待的”(III:377-378)。由于特写意在向苏联公民介绍法国之行的见闻感受,《法兰西纪行》在素描巴黎后,随即与理想读者或虚拟读者进行潜对话:“在巴黎住了一阵子,你们会遇到某些你们所不清楚却很重要的人”,“这样,你们渐渐摆脱了给别人让路的最初印象”(III:378-379)。在《法兰西学校》中,面对法国基础教育的繁重,特写开篇以“苏联人”的群体视角予以评论:“按我们苏联的观念,它的学校的设置很糟糕”(III:380);但对法国大学的自由风气,特写则以“我”的个体视角发表己见:“我不知道这个秩序怎样,——无论如何,它不是高高在上的。”(III:382)在《人民阵线》中,巴黎人民涌上街头,载歌载舞,欢庆攻陷巴士底狱的纪念日,对此“我永远不会忘记一九三五年六月十四日”(III:386);对于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反苏法西斯分子,特写则将视角悄然转换为“我们”:“我们在香榭丽舍大街看见的是另一个世界和另一种人。”(III:387)如此细微的视角转换,在《法兰西纪行》中颇为常见。《法兰西纪行》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我”,虽然时常以“我们”这类群体性视角抒发吻合苏联意识形态的胸臆,但其情感态度与价值立场却表现出比较明显的个人性,是一个游离于中心但又不脱离中心的“局外人”形象。
整体来看,受报刊文体的制约与新闻报道的影响,三大系列特写在叙事视角上多采用第一人称(个体或群体),以明显的个性叙事隐蔽地针砭社会历史。正是这种个人主义叙事和知识分子色彩,使巴别尔系列特写从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范式中悄然逸出,树立了不同于官方文学和主流文学的审美品性与反思力量。
二、修辞的并置与嵌套:象征隐喻与幽默讽刺
经由蒙太奇式的情节并置与碎片化的场景嵌套,巴别尔系列特写以极强的个性化色彩与悖论式修辞,营造出幽默嘲讽、象征隐喻和异国情调的别样氛围,恰如五彩斑斓的马赛克和斑驳陆离的万花筒,由此在时代主流话语之外小心翼翼地表达着不合时宜的思想。
(一)蒙太奇与碎片化
在“彼得堡系列特写”中,蒙太奇与碎片化手法得到比较充分的运用,构成一幅极具个人识别度和社会时代性的艺术画卷,体现出比较明显的悖论式艺术风格和矛盾式美学特征。
《公共图书馆》首刊于《选刊》1916 年第48 期,寥寥数字,短短几句,勾勒出在风雨激荡、波诡云谲的革命激流裹挟下,民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的日常生活图景,颇具绘画素描之神,兼有速记剪影之色。该日记速写以简洁明了的笔触、对比幽默的手法,描绘出革命动荡期间图书馆读者的众生相:远处的喀尔巴阡山区,暴力频仍,鲜血流淌;彼得堡的涅瓦大街上,人声鼎沸,混乱嘈杂;图书馆的窗户外,雪花飘扬,寒气凛然;图书馆内安静如初,神态各异:存衣处的服务人员双重心理,前倨后恭;胖子记者家庭不和,消磨时光;图书管理员衣着寒酸,身材消瘦;大学生身有残疾,奄奄一息;胖大女人高谈阔论,观点庸俗;瘦弱上校郁郁寡欢,埋头写作;各色官员埋头报纸,揣度事态;外省青年神情激昂,备受鼓舞。总之,在公共图书馆中,一切充满着动乱时期秩序的混乱感,混杂着特定时期精神的紧张感、社会人群阶层的无序感,由此构成一幅颇具工笔之简洁与报道之斑驳的时代画面:“一张张桌子旁坐着一动也不动的人影,这是疲倦感、求知欲和虚荣心的聚会……”(I:262)
《伙计》首刊于敖德萨《剪影》1922 年第1 期,副标题为“选自《彼得堡》一书”。该特写笔力冷峻奇崛,开篇描绘出一幅令人不寒而栗的战时场景:“铁面无私的夜。令人惊诧的风。一具尸体的指头在翻拣彼得堡冻僵的肠子。紫红的药房冻僵在角落里。药剂师把精心梳理的脑袋歪向一旁。严寒攥住了药房那紫红的心脏。药房的心脏于是衰竭了。”(I:269)接下来,整个城市陷入一片死寂之中:“涅瓦大街上空无一人。墨汁的泡沫在空中爆裂。深夜两点。铁面无私的夜。”(I:270)在战争混乱中,中国人与拉脱维亚人趁火打劫,买卖商品,流连妓院。①巴别尔在其小说《路》中,同样写到中国人曾用面包招妓的情节。在《伊·巴别尔》(1924)一文中,著名俄国形式主义批评家维克多·什克洛夫斯基曾提及此事:“巴别尔写得很少,但很用力。他有一个中篇写妓院里的两个中国人。”.:,..,“.”. :-- (1914—1933)..: , 1990,C. 366.“一位身着皮衣的中国人打一旁经过。他把一整块面包举在头顶上。他用发青的指甲在面包表皮上划出一道线。”在彼得堡纳杰日津街,中国人瓦修克与姑娘格拉菲拉谈妥交易:“‘你干净吗,啊?’‘我很干净,同志……’‘一磅’。”(I:270)交易结束后,瓦修克、格拉菲拉与阿里斯塔尔赫之间发生小争端。故事最后以“句号”I:271)戛然而止,人物形象之暧昧,图景转换之快速,故事发展之迅捷,让人感慨错愕——战争之后首都变得如此凄凉悲哀,民众生计变得如此艰难不堪,各色商人则变得如此投机取巧,女性个体变得如此卑微无奈。
(二)异国情调与幽默嘲讽
异国情调与幽默嘲讽的结合,写景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的并置,不仅赋予“格鲁吉亚系列”别样隽永的艺术特色,而且将诙谐幽默的格鲁吉亚写进忧伤阴郁的俄国文学。《骑兵军》《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故事》等小说系列,不仅将这种热烈幽默的艺术风格提炼得愈加纯粹奔放,而且形成独树一帜的“敖德萨学派”(即“南俄学派”)之风气。
较之前辈作家与同时代作家,巴别尔将笔触对准少有涉及的俄国边疆地区与少数族裔群体,描写出格鲁吉亚及其民众在革命战争特殊时期的风土人情与个人遭遇。在喧哗而明亮的夜晚,叙述者“我”与裁缝和五金工人在姆茨赫塔工人疗养院的阳台上聚会,喝着用古法沏的冷茶,“懂得了很多喘息的哲学,关于恢复被消耗的精力的学说”(III:329,《在疗养院》)。在格鲁吉亚巴统港湾中,各色各国船只鳞次栉比,五颜六色,生机勃勃:“卡莫号和邵武勉号的红色吃水线在浅蓝色的海面上发光,恍如日暮时分的火焰。土耳其小帆船优美的轮廓在它们附近轻轻摇晃,红艳艳的菲斯卡帽在小驳船上燃烧,有如海船上的提灯,轮船上的轻烟不紧不慢地向令人目眩的巴统天空腾升。”(III:333,《卡莫号和邵武勉号》)在切尔特莫尔特兰港中,各色人物杂处期间,高尚与卑微、整洁与脏乱、优雅与粗俗,彼此相应,令人目不暇接:“鲜红色玫瑰的苍白火焰……瘦削的腿上的灰色丝绸……叽叽喳喳响的外国话……成年男人的胶布雨衣,用银灰色小棒熨平的裤子……发动机刺耳而精力饱满的吼声。”(III:336,《没有祖国》)如此鲜艳热烈、诙谐幽默的笔触,以蒙太奇、素描、隐喻等多样手法,勾勒出一幅充满异域情调的南俄画面,迥然异于果戈理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笔下彼得堡的阴沉冷郁,不同于马雅可夫斯基、布尔加科夫和茨维塔耶娃笔下莫斯科的厚重传统,有别于屠格涅夫与布宁等人笔下俄国腹地的风土人情,更不同于普里什文笔下俄国北方的自然风情。
巴别尔善于以幽默诙谐、嘲讽戏谑的笔调,描写独立于人之外的各种物质客体或抽象客体,赋予其丰富的主体意识、情感、思想,使其具有高度的象征隐喻性和强烈的情绪调节功能,由此呈现出客体主体化与主体客体化交相辉映的并置特征。
首先,景物描写呈现主体化倾向。巴别尔最热衷的景色描写对象既有太阳、大海、树木、月亮等自然景物,也有白昼、夜晚、正午、黑夜等时间概念。在巴别尔的小说与特写中,此类景物如同被施魔法,充满生机,获得人一样的行动能力、感知能力和抒情能力。历经战争与革命风暴,在雨夜品茶的静谧惬意中,“难以言传的安宁像母亲的手时时抚摸我们神经质的、瓷实的肌肉”(III:328,《在疗养院》);在艰难外事交涉中,终于得到卡莫号和邵武勉号轮船,“今天我们却像撵走六月的苍蝇一样撵走了循序渐进”(III:334,《卡莫号和邵武勉号》)。其次,景物描写具有高度隐喻性。无论是写景状物的拟人手法,还是描写客体的主体化倾向,巴别尔笔下的景物描写均具有强烈的情绪调节功能,其本质仍在于大胆新奇的隐喻。值得注意的是,此类隐喻往往具有强烈的情绪渲染效果。历经革命洗礼重获生机后,“小城消瘦的两颊上开始泛起胆怯却充满期待的微笑”(III:345,《加格拉人》);伴着地中海温润潮湿的海风,恰克瓦茶园美景如画,“霞光像五彩缤纷的火焰铺洒在蓝色的水面上,又向着那海岸的弯曲处倾泻而去”(III:354-55,《在恰克瓦》)。最后,景物描写具有结构性功能。系列特写中的写景篇幅大多短小,三言两语,寥寥数句,短短几行。巴别尔常常把它们置于小说中的最重要位置,或在开头,或在结尾,或在情节突转点,或在有意省略处,让其发挥着重要的结构支撑作用。《在恰克瓦》叙述恰克瓦茶的种植之方、采摘之道、制作之序,结尾描写恰克瓦的景色之美:“矮棕树和龙血棕榈树的树冠岿然不动,为窄小的道路镶上了两道边。沾满灰尘的银色桉树树冠高耸入云,直入发红的天空高原——这一幅如同用最纤细的日本丝线绣出的华丽织锦,让人心旷神怡。”(III:355)这在叙述结构上呼应着恰克瓦的地形之特色与山茶之朴实。
(三)斑驳陆离的“万花筒”
在艺术修辞上,《法兰西纪行》多采用悖论手法,具体表现为两种或多种不同的场景前后对照,彼此相异的事件相互对比,前后反差的叙述错位嵌套。对此,该系列特写以诙谐幽默、略带嘲讽的笔调叙述,让人在领略异国情调时不禁会心一笑,在接近法国时不免自我反思,由此呈现出悖论矛盾、幽默戏谑的万花筒式的艺术风格。
在《“灯塔之城”》中,巴黎街头的乱象与普通民众的自由形成对比:前者的火车站“肮脏,嘈杂,乱七八糟”,“古老而模样难看的城市;一排排宽敞而豪华的人行道,夹杂着狭窄的小巷、死胡同,混乱而巨大的蠕动”(III:377-378);后者的样子“难看、快捷而自信”,“这么多各国的艺术家来巴黎住上一个星期或一个月,在这个作为艺术品的城市里住上一生”(III:378)。由此,巴黎表面的喧闹浮泛与内在的安逸自信,构成强烈的对照与明显的反差。巴黎城市及市民生机勃勃,有对爱情、自由和审美力的不同追求,本身就是“小型的艺术世界,它有别的地方所没有的特色”(III:378);其文化的包容性、综合性与自由度,充满强烈的文化自信心、文化认同感和文化厚重感:“巴黎有出版社,百年历史的小铺,书铺里经常坐着三百年前创业的人的直系玄孙,那时候,我们莫斯科的郊区,还有狼和熊在出没。财富的储蓄、知识、技术的力量比我们早一百年就开始了。法兰西的文化不是银样镴枪头:它需要人们付出能穿越它的深处的注意力和认真。”(III:380)
在法国,初等教育的糟糕、虚假、繁琐,让学生空耗生命和精力:“按我们苏联的观念,它的学校的设置很糟糕。法兰西在这方面,属于欧洲落后的国家之一,它的学习充满了古老的经院习气,基础教育只走读死书一途。”(III:380)然而,正是这种穷途末路的基础教育,却为自由、快乐、多样的大学提供了源源不断的优质生源,培养出无数的文化精英和世界名人。巴黎大学的自由之风气,学术之争鸣,课程之多样,令人印象深刻(《法国学校》)。城市的阴暗冷漠与乡村的自然快活,农场的封闭隔离与小镇的浪漫安静,马赛自然环境的优美与民众生活状态的糟糕,处处营造出充满对比与对话的图景(《城市与乡村》)。在作者笔下,法国的司法恰如闹哄哄的集市随意混乱,议会犹如娱乐式剧院无聊无序,懵懂无知的法官则像埃及的木乃伊。总之,“法国议会的秩序也好不到哪儿去”(III:385,《司法与议会》)。然而,恰恰是在“好不到哪儿去”的议会里,每个人拥有言论自由和人身权利,允许不同思想、主张、党派和意识自由合法存在。“议会最近一次选举,加强了共产党党团的作用和意义。”(III:385)作为“反法西斯主义人民阵线的缔造者”(III:385),法国共产党和社会党、激进党人依法选举,组成人民统一战线,发挥着监督政府、维护和平的作用(《人民阵线》)。
简言之,不论是“彼得堡系列”中的蒙太奇与碎片化,“格鲁吉亚系列”中的异国情调与幽默讽刺,还是“法兰西纪行”中变幻不定的万花筒,在新闻纪实性与文学审美性之间都显示出卓尔不凡的艺术张力,在艺术影像性与文本物质性之间都彰显出显而易见的跨界性。
三、主题的反思与质疑:不合时宜与个性呈现
一本书“每次阅读,都为它暂时提供一个既不可捉摸,却又独一无二的躯壳;它本身的一些片断,被人们抽出来强调、炫示,到处流传着,这些片断甚至会被认为可以几近概括其全体。……一本书在另一个时空中的再版,也是这些化身中的一员”①〔法〕米歇尔·福柯:《二版自序》,《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1—2 页。。在文本与化身之间,在错位与等同之外,在认同与反思之上,巴别尔系列特写以鲜明的个性主义姿态,游离于真像与假象之间或之上,横亘在主流与边缘之间或之外,穿梭于历史与现实之中或之外,呈现出知识分子的批判性与反思性。
(一)不合时宜的知识分子反思
从普通人的怀疑目光和反思视角出发,“彼得堡系列特写”通过碎片化、报道式、随笔式的纪实性笔法,关注历史事件裹挟挤压之下的日常生活,观察革命动荡期间的首都世态万象,审视战争时期的京城人生百态,进而呈现出明显的知识分子反思性和批判性。在巴别尔的笔下,十月革命爆发后数月间的彼得堡,革命风暴席卷后的京城民不聊生,哀鸿遍野,苦难遍地,秩序混乱。一如高尔基的系列文化反思文章《不合时宜的思想》,巴别尔的“彼得堡系列特写”也显得极其“不合时宜”,颇为耐人寻味。
在革命后的都城彼得堡,大家都在破坏彼此的生活,宰杀自己的马匹,拿家具当柴烧,把书籍扔进壁炉。其中,革命之后宰杀大量马匹是颇为常见的现象。彼时彼刻宰杀的多为奄奄一息或年老体衰的淘汰马匹,此时此刻宰杀的却是正值壮年或尚在役用的优质马匹,“据统计,自十月起(大规模的屠杀正是始于此时)被杀马匹的数量,足供正常时期十二至十五年屠宰。”(I:276)形成如此强烈反差,造成“无马化”的深层原因,当然耐人寻味,值得深思。《马》对此进行了专题报道,首刊于《新生活报》1918 年3 月16 日。在特写结尾,作者心情沉重地写道:“所有人都羸弱不堪,我们所有人都穷困不堪,过得好的只有鞑靼人,这些开采富足生活的快乐的掘墓者。随后这念头便被打消了,何止鞑靼人呢?大家全是掘墓人。”(I:277)战争期间,社会的经济状况严重失常,人们的精神状态十分糟糕,人际之间的关系非常恶劣:“我目睹了这一切——光脚的阴郁的孩子们,可笑的阴沉着胖脸的教员们,崩裂的下水管道。我们的贫穷和平庸真是无可比拟。”(I:293,《慈善机构》)人们杀人如麻,视生命为儿戏:“以前还询问一番——死者是谁,死亡时间,被什么人打死的。现在不问了,在小纸条上记下——‘姓名不详的男人’,然后就运到停尸间。”(I:280,《死者》)种种乱象不禁激起巴别尔对革命的思索和疑惑:“扛起枪并相互射杀——在某些时候,这大概并不愚蠢。但这还不是革命的全部。谁知道呢——这或许完全不是革命?”(I:284,《妇产宫》)在《至圣宗主教》一篇中,“我记录了他们的发言并转述如下”,平静而客观地转述教会人士的“满腹牢骚”:“人家告诉我们:这就是社会主义。我们的回答将是:这是抢劫,是俄国大地的灾难,是对神圣而永恒的教会的挑衅。”(I:322)
总之,“持续近三年的国内战争,对俄国生活的影响甚于世界大战。各个阵营,无论红军、白军还是绿军,均表现出难以名状的残忍。各种传染病肆虐,一切物质文明均遭毁灭。”①〔英〕德·斯·米尔斯基:《俄国文学史》下卷,刘文飞译,北京: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252—253 页。面对复杂而多样的社会态势,巴别尔的“彼得堡日记”不仅旁涉战争时期的公共生活与社会秩序,而且深入革命期间的私人空间与内在情感,整体色彩比较灰暗阴沉,总体基调比较压抑暴力,显示出明显而强烈的不合时宜性与个人主义色彩。
(二)反思战争、暴力与革命
“格鲁吉亚系列特写”以装饰性风格与纪实性笔法,巧妙反思战争、暴力与革命,其叙事“既不全为假象,亦非完全等同”,②〔法〕米歇尔·福柯:《二版自序》,《古典时代疯狂史》,林志明译,北京:三联书店2005 年版,第2 页。而是对彼时彼刻现实问题的历史构拟和迂回叙事。
就内容而言,《卡莫号和邵武勉号》讲述“卡莫号和邵武勉号”船只修理回国,前半部文本重在议论抒情,后半部文本重在叙述故事。“倘若欢乐不是这样强烈地压迫着心灵,关于这件事情本来可以谈得合情合理、认认真真……”(III:331,333)在开篇与中间复沓出现,不仅将整个文本一分为二,也呈现出战争给海运贸易带来的影响。《没有祖国》讲述革命后无辜船员被驱逐出境,不见容于新政权。对此,老司炉愤懑感慨:“我们是什么人,我们是俄国人,却不是公民。这儿的人不接受我们,他们要撵我们走。俄国人不认我,英国人从来都不认我。我要到哪儿去,从啥地方开始?”(III:337)《加格拉人》讲述加格拉小城在革命前后似曾相识的命运:革命动乱之前,小城中“宫殿是为精英们而建造,而茅舍是仆人们的栖身之处”(III:343);伴随革命战争的深入,红色浪潮时涨时消,随之而来的是五年的冷清寂寥:“许多时兴的疗养地没有了病人,护理员也没有了面包。……死人般的加格拉在破败的悬崖上沉寂下来,如同一个雄伟的怪物,为人所遗忘,也毫无用处。”(III:344)革命之后,小城焕发出活泼生机,疗养院仍然干净整洁,资源丰富,金碧辉煌,只是换了新主人,“就在今年,新主人上台后加格拉迎来了首个疗养季”(III:345)。《烟草》中,突如其来的战争给社会民生以毁灭性打击:“一九一四年之后,战争开始了其摧毁一切的进程”(III:347),阿布哈兹地区的烟草因战争遭到毁灭性打击;结果,“阿布哈兹人的物质生活条件在急剧恶化。他们衣衫褴褛,住在年久失修、破烂不堪的房子里”(III:349)。《修理与清洁》中,战争与革命让外省小城濒临崩溃:“去年苏呼米的经济濒临崩溃的边缘……苏维埃化后的最初几个月也没有带来显著的改善”(III:355);乌托邦理想很美好,社会现实却很残酷:“新经济政策有时(遗憾的是不是永远)是如何在某些地方(遗憾的是不是在所有地方)得以正确执行的”(III:355)。由此,苏呼米的过去之崩溃、现在之艰难、未来之美好,发人深省。
“格鲁吉亚系列特写”涉及对象林林总总,五花八门,凡社会、政治、经济、教育、文化多有涉猎:疗养院兴衰、中等学校教育、度假区命运沉浮、烟草业衰落、恰克瓦茶种植工序、新经济政策效果、铁壳船易旗换帜,可谓国计民生皆有涉及,社会现实多有反映,见闻所思见诸笔端。就体裁风格而言,该系列特写时常将数据统计、时政报刊、议论说理等内容嵌套进故事叙述中,夹叙夹议,叙中有议,叙议结合。就主题话语而言,该系列特写相对集中明晰,即经由战争与革命期间小地方、小城镇、小人物的沉浮际遇,表达知识分子的自由主义诉求——反思战争的代价与成本、暴力的伤害与后果、革命的方式与效果。
(三)倾心欧洲的“同路人”
就主题内容而言,《法兰西纪行》分别涉及巴黎表面印象与内在文化的对比、法国初等与高等教育的差异、法国城市与乡村的不同、法国司法与议会的混乱、人民阵线的特点与作用、金钱与权力的共谋、法国共产党的作用。其中,有首都与外省之别,有中心与市郊之差,有城市与乡村之别,有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差异,有共产党与其他党派之纷争,有工人与资本家之斗争。就话语层次而言,该系列特写多采用集体主义至上与自由主义反思两套不同话语,两者内外有别,彼此明暗不同,前者多处于叙述的中心与前台,后者多处于叙述的边缘与背景,由此小心翼翼地表达着作者不同于时代主流的个人主义诉求。
“从1930 年代初起,尤其是作家代表大会后,(苏联)文学中越来越明显地表现出千篇一律的倾向,使文学趋于单一的审美范式,而且还找出了一个学术名称——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方法。”①〔俄〕阿格诺索夫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2 页。1935年前后巴别尔随团出访欧洲,1937 年《法兰西纪行》发表于《少先队员》杂志;彼时彼刻,“(苏联)文学中日益推行的不仅是思想的划一,而且还有语言的单一。”②〔俄〕阿格诺索夫主编:《20 世纪俄罗斯文学》,凌建侯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 年版,第392 页。在风雨如晦、敏感多思的此时此刻,针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共产党与其他党派、无神论教育与宗教教育、工人与资本家等敏感问题,巴别尔采取了两种态度与两套话语的叙事策略。就叙述态度而言,对于与苏维埃意识形态相对或相异的现象,作者多采用贬抑、嘲讽或批判的态度;反之,则多采用褒扬、赞赏或肯定的倾向。对巴黎的美丽、自由与包容,特写不乏溢美之词:“需要时间去感受这座城市,它的市民,它带有精美、爱情和审美力的瑰丽的国家”(III:379-380);对于巴黎的政权与制度,特写则以惋惜嘲讽收尾:“不幸的是,资本家的政权、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令这个国家极美好的外貌变丑陋,损坏了它生命的核心”(III:380,《“灯塔之城”》)。对法国基础教育的繁琐与机械,作者从群体视角予以否定:“按我们苏联的观念,……它的学习充满了古老的经院习气,基础教育只走读死书一途”(III:380);对宗教教育的危害与后果,给予旗帜鲜明的批判:“宗教教育的毒药如此精妙和潜移默化地、如此柔性和完善地侵入孩子们的意识,其危险性实在不容小觑”(III:381);对高等教育的自由开放,则颇多欣赏认同之情:“尽管巴黎大学的教学大楼由灰蒙蒙、沉甸甸、冷冰冰的建筑物组成,但里面沸腾着快活的、南腔北调的热闹人群”(III:381,《法兰西的学校》)。对金钱与权力合谋危害社会民众,作者义愤填膺:“到处都是收买和出卖的谎言……腐败以形形色色的贪婪和财富侵蚀着国家,侵蚀着伟大的学者、诗人和画家的国度”(III:389,《金钱的权力》);对共产党人领导下市郊的学校,则充满自豪认同之感:“法国人习惯于黝暗的中世纪学院,共产主义学校成了世界的第八大奇迹。”(III:392,《“红色腰带”》)
对于法国之行的见闻,巴别尔并非全部认同或完全接受,而是认同中有反思,接受中有舍弃,在认同与疏离、接受与拒斥之间,如同钟摆一般左右摇摆又变动不居,若即若离又不即不离。其总体基调是认同巴黎,喜欢法国,倾心欧洲,其伦理身份是苏联文化的“局外人”,其价值立场则是官方文学的边缘人,与1920—1940 年代的“同路人”颇多相似之处。从认同叙事角度而言,在叙事特色、艺术风格和主题话语方面,《法兰西纪行》经由对法国纪事的见闻评议与欧陆之行的所思所想,隐蔽表达着巴别尔对苏联体制与苏联文化的态度,即认同苏联的社会主义理想与集体主义荣誉,疏离苏联的极权主义体制与一元单声文化。

从多种视角到多重结构,从叙议并置到修辞嵌套,从多重主题到多重话语,巴别尔系列特写在悄然之间,开启了《敖德萨故事》《我的鸽子窝的故事》《骑兵军》的叙事之法、修辞之风和思想之门。巴别尔或以平凡的笔法描写不平凡的人事,或以不平凡的修辞描写平凡的景物,或以不平凡的技巧反映不平凡的对象,创作出别具一格的自传传奇与艺术世界。他以“局外人”或“热带鸟”的独特身份,以“同路人”的第三条道路,巧妙将传奇的人生经历、重大的历史事件、独特的社会情状、变化的时代话语,打碎揉捏,取舍有度,融汇一炉,形成五彩斑斓的“马赛克”与斑驳陆离的“万花筒”,为从白银时代文学向苏维埃文学转型之际的社会历史、族群遭遇与个体际遇,镌刻出一个热烈而悲情、破碎而真实的时代影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