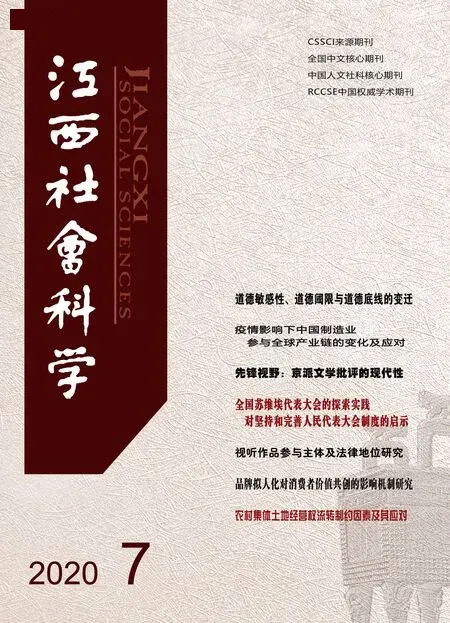中国隐逸文化的嬗变
——以魏晋南北朝佛教为中心
■周 锋 陈 坚
佛教和中国隐逸文化都有强烈的出世性,因此,佛教在传入中国后便与传统隐逸文化发生“剧烈的化学反应”,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发展产生重要影响,尤以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兴盛的佛教对传统隐逸文化带来的改变最为显著。在隐逸思想与佛教思想的双重影响下,出现了佛化隐逸组织,山林佛教就诞生于此。中国的隐逸文化也是在佛教义理的影响下才走向成熟。隐逸思想与功名划清界线,间接导致出家僧尼数量的增加,佛教的兴盛也与此有很大关联。
历来不乏学者对佛教思想与隐逸文化的研究,但几乎没有专门研究二者关系的论题。为此,本文特别选择魏晋南北朝这一历史时期作为考察背景,研究佛教传入给中国隐逸文化带来的影响,一方面是因为在魏晋南北朝佛教融入中国并上升成为主流文化的一部分,另一方面是因为中国隐逸文化也恰恰在这一时期才有正式记载,当时佛教与隐逸之间的文化交互可谓十分精彩且重要。
一、隐逸的含义
隐逸,现代词典通常把它解释为隐居、退隐,有时候也代指隐居的高士。这种解释从一般意义上理解没有多大问题,但要明确和界定隐逸具体是一种什么情境,仍然比较困难,如隐居可不可以在家里,在山间庙观的僧道团体中算不算隐逸,诸如此类的问题难以回答。我们不妨把隐逸拆分开来,分别从隐和逸的语义发生情境来看。
隐,《尔雅·释诂》释:“隐,微也。”《说文解字》注:“蔽也,蔽謪,小儿也,小则不可见,故隐之训曰蔽。”也就是说,隐就有如植物初生之叶芽,微小到几乎看不见。这里需要注意两点。第一,隐在发生情境中是一种视觉行为,表现为我们视觉官能的失效,比如说植物埋在土里生长,从最开始星点不见到后来逐渐长大,我们才看到有一棵树在生长。第二,隐的主体是一种实在,它不会因为隐就消失不见,失去其存在性。即使是一个念头,隐而不说,它仍然存在于拥有这个念头的载体中,并且隐会在一个生存过程中通过显的情境来彰表其意。因此,可以知道,隐是针对所隐对象的不可视,而这种不可视并不一定是不可知,而是或可以耳闻,或会有记载,总之能够通过一定的途径了解到隐的主体,否则,就不是真隐,而是消失或不可知。鲁迅就说,那种彻底声闻不彰、息影山林的人物,世间是不会知道的。对于这消失行为,便无从谈隐,有如历史朝代中的招隐行为,如果彻底消失,自然也无隐可招。
再来看逸字。《说文解字》注:“逸,失也,从辵兔,兔谩銛善逃也。”逸是一个会意字,意思是像兔子一样善于奔逃。我们都知道,兔子是食草动物,处在食物链的底层,为了躲避猛兽的追捕,有善跑躲避的本领。在分析语言发生情境中,我们也需要注意逸字至少包含一种逃避行为,就必然会有一个逃避对象。在原始语境中,是对敌人的躲避,当没有敌对关系时,也就没有逸的必要性,而是追求安稳,是一种生存判断行为。当逸的主体引申为人时,是出于一种安全、适宜的需要,主动逃避其他的人、事或社会关系。
综合以上可以看出,隐逸行为是隐逸主体为了保障自我而选择的对特定隐逸对象(可以是具体的人,也可以是复杂的社会关系)的逃避行为,然而隐逸不同于消失,它仍然会通过其他途径彰显出来,只不过对隐逸的对象而言仍然是看不到的。
二、隐逸与佛教的交涉
明晰隐逸的概念后,可以推断隐逸并非中国特有的“专利”,也并非道家特有的“专利”,佛教中那些过着出世生活的僧人,很多也是在隐逸。他们之所以出家,是为了逃避那些对其造成苦难的社会关系和人,即使一个寺庙容纳很多僧人,但对个体而言,他逃避了让他觉得不适的关系和对象,离开了特定对象的视野,这仍然可以视为隐逸现象。
现在,我们回到中国隐逸文化的发展进程中,当佛教这一庞大的宗教体系传入后,确实在某些方面引起了隐逸文化的跃变。隐逸作为一种文化现象在中国有着特殊的意义,梁漱溟就把隐逸文化①总结为中国文化的主要特征之一。要寻溯隐逸文化的发展演变历程,中国本土的儒、道文化固然于之影响深远,但是,作为“外来”的佛教对中国隐逸文化的影响必也不可忽视,姜亮夫把隐士分为僧道、准僧道的修士和逸士两种类型。[1](P19)自佛教东渐传入中国,便不断与本土文化交融会通,进而与隐逸文化发生“化学反应”。
(一)隐逸致的“佛迹”
就隐逸文化的起源而言,传说中伏羲以前便有隐士出现,故而又把隐士称作“羲古上人”,较早的史传隐士记载有:《高士传》中拒绝尧禅位的许由,《庄子》中凤歌笑孔丘的陆通,《史记·留侯世家》中不仕刘邦的商山四皓,他们属于汉代以前的隐士。至汉末,由于战乱频发,社会动荡,隐逸现象盛况愈增,《后汉书》开始专辟《逸民列传》以记载诸方名隐事迹,隐逸作为一种传承文化正式在中国文化中登台亮相。
隐逸与佛教的交涉在汉魏之际已露端倪,正始年间有著名的隐士集团“竹林七贤”,陈寅恪认为,“竹林”二字就是时人取法于释迦牟尼居住过的“竹林精舍”,以标类趋同。魏晋时期,玄学开始兴起,受其“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潮影响,当时的高士名流隐逸成风,佛教教义因与玄学意趣相似,受到各方隐士青睐,隐逸与佛教交涉更甚。如陶渊明与高僧慧远同居庐山留下“虎溪三笑”的美谈;戴逵终身不仕却酷爱佛教造像,并首创中式佛像艺术;谢敷深隐太平山,却笃信佛法爱好注经等。
南北朝时期,佛教弥盛,正史记载中的佛隐交涉现象也更为频繁,如《宋书·隐逸传》中记载了隐士宗炳、周续之、雷次宗等人长期师事庐山慧远法师;《魏书·逸士传》中记载了冯亮好佛,不但被召讲佛经,死后也按佛教方式燃灰起塔归葬;《齐书·高逸传》《梁书·处士传》中则几乎所有记录的隐士都与佛教有关,或好居寺庙,或好谈佛理,或好注佛经,两者交涉已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二)教门中的隐逸
随着佛教在中国的流行,隐逸与佛教的关系越来越密切,汉朝传入之初,佛教被认为与“中国黄老方技相通”[2](P67),至魏晋与玄学形成会通(义理),而后南北朝时期得到大力弘扬,佛教逐渐上升进入中国主流文化圈中,当时的隐士不但有崇佛、事佛的现象,甚至出现大量皈依佛教、削发为僧的隐者,如《南史·隐逸传》就记录僧人隐士:
时有沙门释宝志者,不知何许人,有于宋泰始中见之,出入钟山,往来都邑,年已五六十矣。齐、宋之交,稍显灵迹,被发徒跣,语嘿不伦。或被锦袍,饮啖同于凡俗。[3](P487)
一些学术研究向来也只论儒隐、道隐,对佛家隐逸绝口不谈,可以参照《南史》作者李延寿的观点:“(僧人宝志)虽处非显晦,而道合希夷,求其行事,盖亦俗外之徒也。”[3](P365)实际上,无论儒、释、道哪一家,只要是存在归隐思想,有隐逸的实质行为,都可以视为隐逸文化现象。又如东南亚的某些整体信仰佛教的国家,其中也不乏佛门隐逸人士,以此观之,魏晋南北朝的佛门隐者,实难以胜数。孙绰《道贤论》中就将支遁、竺法潜等人喻为佛门“竹林七贤”:支遁乐于游艺山水,好谈玄学佛理,虽受诏策而复辞归山林,其生平足具隐士风骨;竺法潜隐于剡县仰山,逍遥其中,当时支遁想向其购山以居,法潜道,“欲来则给,岂闻巢、由买山而隐”,“风鉴清贞,弃宰相之荣,袭染衣之素,山居人外,笃勤匪解”[4](P157),足以说明竺法潜隐逸之实。再如《梁书·处士传》中记载隐士刘慧斐:“尤明释典,工篆隶,在山手写佛经二千余卷,常所诵者百余卷。昼夜行道,孜孜不怠。”[5](P1259)像这样勤修佛法、常行不怠的隐士,已然无法界别他与佛教僧人的差异。随着佛教的隆兴,越来越多的佛教徒避世隐修,天下名山被占其半矣。
(三)佛化隐逸组织的出现
除了个体隐逸与佛教的交涉,伴随着佛教的传播与流行,隐逸与佛教进一步融合,最主要表现为一些避隐的高僧,即使身处山林,隐居幽野,仍会有许多信慕者追随,如上述支遁、竺法潜等人,即使在山野隐居,总会有人追随问学。这类情况与“竹林七贤”那种隐士团体不同,它是隐逸与宗教结合的产物,这里姑且称之为佛化隐逸组织。佛化隐逸组织的出现并不是偶然现象,而是历史逻辑的必然,本质上仍然是个体隐逸的延展。
首先,佛化隐逸组织②的出现是个人生存的需要。传统的山隐穴居是极为恶劣的生存环境,隐者们不但要忍饥挨饿,为获取食物发愁,还要遭受自然环境中的各类危险,用现代语言来说,这种独隐山林就是一种“极限运动”。而集聚在山林寺庙中,则可以有一个相对安逸稳定的隐居场所,既可以避开俗世的扰攘,又可以抵抗各种自然风险。
其次,古代隐士大多轻物质需求而重精神需要,佛教义理的思辨性和哲理性为好思好学的隐士们提供精神食粮。他们为了学习佛教理论,就需要集中起来,向精通佛法的高僧学习,进而推动了佛化隐逸组织的形成。
佛化隐逸组织是隐逸的集体形态,仍然有隐逸现象的基本属性,这体现为佛教以解脱道为立教根本,佛化隐逸组织与佛化隐逸一脉相承,其内涵已折射出一种隐逸心态,即使教门中有各式各样的清规戒律对个体行为进行限制,但并不与个体追求自由解脱相冲突,所以,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寺庙普遍宽容于僧人去留自由,并鼓励他们游方、行脚。
三、隐逸中的崇佛行为
当佛教与隐逸有了交涉,具体的隐逸行为中自然也会有与佛教相关的内容。这里从佛教的佛、法、僧三方面内容来研究佛教化的隐逸行为,并以东晋庐山慧远教团③为例进行说明,因为当时在庐山的慧远教团就是一个典型的佛教化隐逸组织。
(一)对佛的信奉
慧远教团是东晋隐修于庐山的佛教团体,团首慧远是佛教净土宗的创始人,同时也是中国山林佛教的开创先驱,他一生既不受招隐受爵,也不出庐山方界,终生隐于山中修行,《高僧传》记载:“卜居庐山三十余年,影不出山,迹不入俗。”[4](P221)慧远作为隐逸高僧吸引了许多隐者追随,像刘遗民、周续之、雷次宗都是历史中有名的隐士。
慧远教团把佛教信仰行为当作隐逸生活的主要内容,史载: 周续之,“入庐山事沙门释慧远……遂终身不娶妻,布衣蔬食”[6](P2260);雷次宗,“暨于弱冠,遂托业庐山,逮事释和尚,于时师友渊源,务训弘道”[6](P2293)。这反映了他们隐居庐山时虔诚的信徒生活,在东晋佛教大为兴盛的特殊历史背景下,隐士们空虚的生活被丰富的宗教教义内容介入,引发了佛教信仰在隐士群体中快速传播。从历史记载中可以看出慧远教团的举止行持都遵守着佛教教仪,庐山莲社的成立以追求极乐净土为目标,也是隐逸组织佛教信仰化的具体表现。
(二)对法的信持
慧远针对跟随在他身边的隐者们开展了一系列佛法教育活动,将佛教教义进一步在庐山隐士群体当中普及,使佛法在庐山大为流行。首先,慧远依照佛教戒律制定了一系列僧制,包括《法社节度序》《外寺僧节度序》《节度序》《比丘尼节度序》等用来规范团众学修佛法[7](P437);其次,他总结佛教教育,“经教所开,凡有三科,一者禅思入微,二者讽味遗典,三者兴建福业,三科诚异,皆以律行为本”[8](P85),有系统地推行佛法理论。第三,他还在佛教教义中选择比较简单容易的净土法门让大家学习,告诉教团成员,“宜简绝常务,专心空门”[8](P304),一心追求往生西土。通过这些举措,庐山隐士集团大部分都对佛法产生了信仰和依赖。
(三)对僧的信赖
由于慧远的个人魅力,庐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隐逸组织,隐士们集体皈依佛教,拜慧远为师,学习佛教。《高僧传》中记载:
彭城刘遗民,豫章雷次宗,雁门周续之,新蔡毕颖之,南阳宗炳、张菜民、张季硕……延命同志息心贞信之士百有二十三人,集于庐山之阴般若台精舍阿弥陀像前,率以香华敬廌而誓。[4](P214)
这就像是一个宗教皈依仪式,所以参加者几乎已半入僧籍。不过,随着慧远离逝,这一佛教组织也逐渐衰颓,雷次宗与侄书中说:“渊匠既倾,良朋凋索,续以衅逆违天,备尝荼蓼,畴昔诚愿,顿尽一朝,心虑荒散,情意衰损,故遂与汝曹归耕垄畔,山居谷饮,人理久绝。”[4](P178)这反映了宗教信仰只是隐士生活的部分内容,不能完全把宗教和隐逸等同起来,二者交叉影响,互有涉入。
四、隐逸思想的佛化
思想内涵反映了一种文化的精髓,同样,隐逸思想也是隐逸文化的文化灵魂,所有隐逸行为和隐逸现象归根结底都是隐逸思想的外在表达形式。中国隐逸思想内涵在佛教盛传以前是一种模式,在佛教盛传之后则产生巨大变化,需要说明的是,佛教虽然是两汉之际传入中国,但在《汉书》隐逸传中几乎没有与佛教相关的内容记载,佛教对当时的文化影响微乎其微,考虑到这一点,本文以魏晋南北朝为佛教盛传时期,分别考虑佛教盛传前和盛传后对中国隐逸思想的影响。
(一)佛教盛传前的隐逸思想文化
隐逸作为一种行为现象,背后存在一定的隐逸动机,而隐逸动机实际上就反映了隐士的隐逸思想和隐逸观念。南朝范晔在编撰《后汉书·逸民列传》时把早期的隐逸动机分为六种:
《易》称“遁之时义大矣哉”。又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是以尧称则天,不屈颍阳之高;武尽美矣,终全孤竹之洁。自兹以降,风流弥繁,长往之轨未殊,而感致之数匪一。或隐居以求其志,或回避以全其道,或静己以镇其躁,或去危以图其安,或垢俗以动其概,或疵物以激其清。[9](P2755)
其中第一类是为了保全忠节,朝代更替中的遗民以不仕全其志,如“商山四皓”之流;第二类是为了养生延命,道家隐逸基本上归属这一类;第三类是为了远离尘嚣,在“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环境获得清静;第四类是为了逃避战乱,如《桃花源记》所记载桃源人的先祖就是这类人;第五类是不愿屈从时弊,如孔子所说“邦乱则隐”就是针对时政凋敝的一种选择;第六类是厌离物欲羁绊,不愿为物欲名利沾染影响。
分析这六类隐逸动机,实际上可以划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相对彻底的隐逸,如陶氏的自然浪漫主义隐逸、心理的逃避主义的隐逸;而另一种则是不那么彻底的隐逸,如“邦乱则隐”、避乱而隐,他们不是发自内心的意愿,而是迫于时事的不得已为之,甚至有人想以隐逸的“终南捷径”④求名求利。清朝李光地就说:“古来高隐人,不尽是忘世,多是志愿极大,见不能然,遂决意不臣人。”[10](P388)这背后反映的是一些隐士在内心深处仍然有着强烈的政治抱负和人生追求。
(二)佛教盛传后的隐逸思想文化
由于佛教在魏晋南北朝时期渐趋兴盛,受佛教出世观念和宗教性质的冲击,传统隐逸思想接收了新的内容,并产生了深刻的变化。
首先,佛教有着完整的理论体系。佛教认为“有情皆苦”,唯有学佛修行方能离苦得乐,得到永恒自在,并以此形成具有实践价值的苦、集、灭、道的“四圣谛”学说,这对急于逃避失意人生的人极具吸引力,尤其在魏晋南北朝连年战乱的大环境中,佛教为隐者点亮了一盏明灯。
其次,佛教有旨在获得彻底解脱自由的修正体系。如净土宗、天台宗、禅宗等各宗派都有具体的修行方式。于是,在佛教理论体系和实践系统的双重作用下,佛化隐士的生活有了明确的目标性,他们为解脱成佛而过着一丝不苟的宗教生活,如庐山莲社众人为往生极乐世界而勤修念佛不怠,便是如此,这反映了佛教影响下隐逸思想内涵的扩张。通过正史隐逸传的记载即可以印证出,魏晋南北朝以降的绝大多数中国隐士都与佛教有着密切关系,佛教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全方位地影响到了隐士群体。
再则,佛教的出世观对中国隐逸思想带来转变尤为重要,前文提到李光地对中国隐士的看法,事实上,中国传统隐士中很多都有着极大的政治抱负,他们在隐世与入仕的抉择上摇摆不定,但在佛教理论与实践的影响下,“隐”与“仕”被隔离为两条人生路径。东晋权臣桓玄曾对佛教进行强势沙汰,并提出“君道兼师,而师不兼君”[8](P34),意在约束包括山野城市的各类僧人,而慧远则以理抗辩:“天地虽以生生为大,而未能令生者不化,王侯虽以存存为功,而未能令存者无患。”[8](P30)佛教的目标是让人彻底解脱,“斯沙门之所以抗礼万乘高尚其事,不爵王侯而沾其惠者也”[8](P32),他认为学佛是比出仕入相更为“高尚”的事情。应该说,这种宗教说辞极具煽动性,《易经》的“不事王侯,高尚其事”,在佛教中则得到升格。于是,在这种佛教观念的影响下,隐逸思想需要与功名人生观划清界线,这与“终南捷径”完全不同,得到部分有隐逸想法人的认同,间接导致出家僧尼数量的增加,其实后世佛教的兴盛与此就有很大的关系。慧远还明确区分佛教的在家众和出家众,他认为,在家众乃是顺化之民,应协助君王进行教化;而出家众,乃是方外之宾,迹绝于物,应遁世高尚其迹。正是通过这些宗教家们口中的佛教理论,对后人的隐逸动机、隐逸方式和隐逸行为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五、结语
从上文可以看出,佛教的传入与流行对中国隐逸文化产生了巨大影响,丰富了隐逸文化的内容,延扩了隐逸文化的内涵。隐逸文化在认同佛教出世观的前提下,受到佛教的洗礼和改变,如今,中国隐逸文化已经是包含儒、释、道三位一体的文化体系,与积极的处世之道形成的社会文化体系互为衬托,共同影响到社会中的每一个人。
注释:
①原文称作隐士文化,为便于讨论,本文对此不作区分。另外,一般论及隐士都是指具有一定知识文化的人,本文提到的佛教性质隐士则是精于佛学或是兼通于各家的隐士。
②佛教传入之前或许就存在这种现象,但真正形成组织化、规模化,应当是在佛教传入之后,如中国道教组织制度基本上就是在佛教影响下形成的。
③指东晋时期以慧远为中心的庐山佛教修行团体。
④指借助隐逸来获得名声,从而达到出仕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