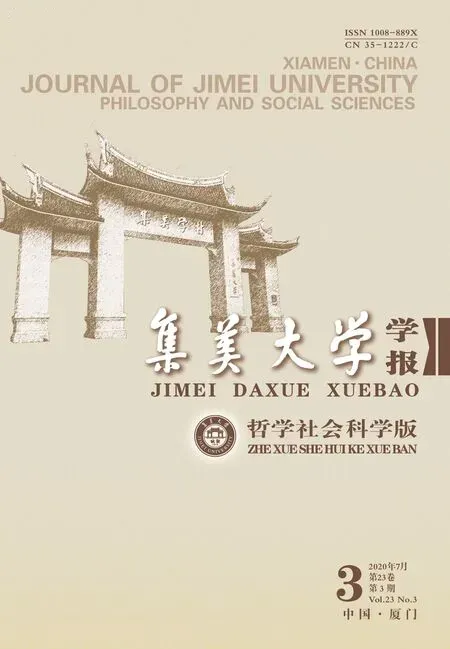论东亚对叶采《近思录集解》的推崇与质疑
程水龙
(苏州大学 文学院,江苏 苏州 215123)
南宋淳熙二年(1175),朱熹、吕祖谦在福建武夷山的寒泉精舍共同编撰了《近思录》十四卷,该书浓缩了北宋周敦颐、张载、程颢、程颐四子学术思想之精髓,彰显其穷理正心修己治人之要,成为人们研学“《四书》之阶梯”,差不多在南宋后期“被经典”。叶采《进近思录表》认为此书乃“求端用力之方,暨处己治人之道,破异端之扃鐍,辟大学之户庭,体用相涵,本末洞贯,会六艺之穾奥,立四子之阶梯”,赞赏此书“规模之大而进修有序,纲领之要而节目详明,体用兼该,本末殚举……是则我宋之一经”。[1]
《近思录》面世后,在宋元明清各朝不断得以刊刻传抄,同时注解、续编、仿编者络绎不绝,又形成大量“《近思录》后续著述”,可见集理学之大成的《近思录》,在经过多年的累积后,已被公认为最能代表中国古代主流学术思想的经典之一,长期被奉为“入德之门”“入道之阶”。《近思录》及其后续著述几百年来在中国本土流布的同时,又广泛流布于东亚朝鲜半岛(后文简称“朝鲜”)、日本列岛(后文简称“日本”),在东亚理学思想史上产生过深远影响。
叶采,字仲圭,号平岩,叶湜仲子,南宋建安人,主要生活在南宋理宗朝。曾先后从蔡渊、李方子、陈淳问学,为朱熹再传弟子,颇有远见。几十年用心集解《近思录》,自云:凡“其诸纲要,悉本朱子旧注,参以升堂记闻及诸儒辨论,择其精纯,刊除繁复,以次编入,有阙略者,乃出臆说”[2]。他又依据《近思录》各卷内容,拟定了与之相契合的各卷篇名,并简要阐明各卷内容提要。其注文常常引朱熹语注解四子语,犹作评析,以发扬光大该书主旨,至“意稍明备”方休。
叶采经“朝删暮辑,踰三十年”,于淳祐八年(1248)完成《近思录集解》十四卷(以下简称“《集解》”)。此书被叶采“授家庭训习”,后在理宗皇帝的垂询和叶采进书的背景下,便迅速推向全社会。《集解》各卷纲目、提要的创建,使得《近思录》原书体例显得更加明晰完备,使程朱理学思想内容的表现更趋明朗,在后世影响深远,其所拟纲目差不多成为后世《近思录》续编、仿编者所倚重的范式,为诸家所宗,儒林学界,久嘉赞誉,云“叶采本文公旧注、诸儒辩论辑为注解,而后四先生精蕴昭然日星”[3],《近思录》“原本之美备,实足以该四子之精微,而叶注之详明,又足以阐《近思》之实理”[4]。
一、中国本土的推崇
叶采《集解》在中国本土宗朱的社会背景下颇受推崇,得到元明清《近思录》绝大多数注者读者的褒扬。
(一)《集解》是注《近思录》者中现存最早的注本,七百年间几乎替代《近思录》原书而行传播程朱理学思想之实
叶采“采辑朱子之训,参以诸儒之说,补以自家之意”而撰《集解》,以汇集朱熹论说文字为主,故在南宋之后历代宗朱的学术背景下,此书一直为元明清学者所称道,不断被重刻再造,几乎替代《近思录》而行传播程朱理学之实。
依据现存文献资料,加之笔者多年的实地调研,目前中国本土现存南宋至民国年间的“《近思录》文献”版本有近200种,而其中叶采《集解》系列(1)叶采《近思录集解》系列版本,主要包括重刻本、周公恕类次本、吴勉学校订本等。参见程水龙:《东亚〈近思录〉版本考述》,凤凰古籍出版社待刊书稿。版本就达36种之多,这是《近思录》其他注释本难以企及的。诸如《集解》元刊本、元刻明修本,明初至明末刻本皆行于世。清代刻抄本尤多,如《集解》清康熙年间邵仁泓校刊本,雍正年间三多斋、尚义堂刻本,在兹堂、培远堂、安定书院、广仁堂刊本,《四库全书》本,以及《重镌近思录集解》、《近思录原本集解》本等。相较之下《近思录》原文本仅存17种。可见《集解》确实成为南宋后期、元明清时期士子进修理学的重要入门津梁,其传本之多、种类之繁,几乎替代《近思录》原书而行传播程朱理学思想之实,成为《近思录》文献中的中流砥柱。
通过对《近思录》历代注本的考察,我们发现在清乾隆朝之前,数叶采《集解》影响最为深远,其编撰体例、注解思路为后世诸家所宗,后世的《近思录》注者、续仿编者多倚重叶采所拟纲目。从现存《近思录》文本少而叶采《集解》传本众多的史实可以考察,在该注本诞生至今的近七百年间,因程朱理学在中国本土长期处于官方哲学的地位,极少有敢于公开批驳者,世人对朱子门人也多持尊奉的态度,故叶采《集解》传本久盛不衰,且因其价值之巨,历代学人青睐有加,以致其流布甚广。
对于《集解》,清初朱之弼说:“四先生之精蕴萃于《近思录》,《近思录》之精蕴详于叶注,遵原本则条例该括,存叶注则义理详明,后之学者其亦从事于此,而无旁求矣。”[3]乾隆初年陈弘谋重刊《近思录集解》时云:“叶氏用力于此书最专且久,所著集解原本朱子旧注,参之诸儒辩论而附以己说,明且备矣。”[5]很显然,崇尚朱子学者肯定了《集解》的纯正性,叶采注文将宋儒之精蕴详明地阐释,使得《集解》在后世学者眼里是一部非常值得信赖的理学入门读本,被绝大多数崇尚朱子学者奉为圭臬。
(二)尽管在中国本土偶见学者言及《集解》不足,但并未影响其在理学史上的地位
作为后出的《近思录》注本,清康熙年间茅星来《近思录集注》(以下称“集注”),既有继承前世注家的地方,也有后出转精之处。由于叶采《集解》有许多精当之解,茅氏集注时也多加引用,如在《集注》卷十第16条语录下有引用,“叶氏曰:二五相应。然时方睽违,上下乖戾,故二必外竭其力,内尽其诚,期使疑者信、睽者合耳。”“叶氏曰:内竭其诚以感动君心,外尽其力以扶持国政,此尽其在我者也。推明义理,使君之知无不至;杜塞蔽惑,使君之意无不诚,此正其在君者也。”[6]卷十,9
然而,作为清初考证学者的茅星来,在读过南宋叶采《集解》、杨伯嵒《泳斋近思录衍注》后,认为这两种注本“粗率肤浅,于是书(笔者按,即《近思录》)了无发明,又都解所不必解,其有稍费拟议处则又阙焉”[6]序,1,故对《集解》不是很满意。如对于《近思录》卷二第30条语录:“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二之则不是。”叶采集解说:“此条疑当在首卷。”而茅氏云:“此为论性、论气者言之,非论性与气也。叶氏谓‘当在首卷’者,非。”[6]卷二,19叶采在此认为这是谈论理学中的“性”“气”命题,以为这条语录应归属卷一“道体”。而茅氏以为此条语录则是告诉人们,在为学过程中如何对待“性”“气”,若分开来单论“性”或“气”则会出现差错,当二者皆备。将此条语录归属于卷二“为学大要”中是恰当的。又如卷六最末“婢仆始至”一条,是朱、吕选辑来阐述“齐家之道”的结语,其意深长,而叶采并未注释,仅云:“提掇,谓提起警策之也。”
虽说《集解》在中国本土偶有被人捎带批评,但不是对其主体作批判。又如对于《近思录》卷十“人教小童”条谈论教童子之益,叶采以为“此段疑当在十一卷之末”,茅星来则认为:“此条所论,皆教小童时所以自处之道,非论教小童之道也。叶氏谓‘当在十一卷’者,非。”[6]卷十,26因而茅氏《集注》仍归于第十卷。
其实,叶采的“疑”并没有错,或是受到朱熹的影响,因为朱子尝曰:“《近思录》大率所录杂,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事君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在一段。”[7]2629后世自然会对此有不同的理解和接受,叶氏之解当属正常现象。就《近思录》而言,往往因为其中某些文字存在多义性,在后世被阐发时则会获得不同时期不同阶层读者的认可。
但是,在中国本土的朱子学者眼里,叶采《集解》一直充满魅力,历代学者争相传阅。如即便在清代中后期盛行江永《近思录集注》,此注本虽说未依从叶采所拟卷目,明显地“以朱释朱”,却在注释朱熹论说未备之处,仍取用叶采注文来进行注解。
二、朝鲜、日本学者的质疑
从现存文献资料可见,历史上叶采《集解》曾广泛流布于朝鲜、日本,甚至欧美(2)1953年《近思录》被Olaf Graf神父译成德文,该德文译本以藏于日本的南宋叶采《近思录集解》为底本翻译而成。陈荣捷翻译的《近思录》英文译本,1967年由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皆传播于世。。朝鲜高丽朝与李氏王朝刊印抄写的中国学者“近思录文献”,韩国现存版本有近80种版本,其中以叶采《集解》为绝对主体,达40种之多,其中有木板本、活字本、写本等;日本现存“近思录系列文献”近140种,其本土再生的“叶采集解系列版本”有20多种,其中多为和刻本。
史上东亚学界对《集解》青睐程度之高由此可窥一斑,故“叶注之为世诵习久”。特别是尊朱的学者,认为“叶氏私淑于北溪陈氏,其说宜得朱子之意”[8],以致于“叶采之注,在日本甚为通行,日本注家几皆全依叶注”[9]3。世界著名朱子学专家陈荣捷此言不无道理,叶采创制的各卷篇目、解题,使得《近思录》原书体例显得更加明晰完备、其内容表达更趋明朗,又多为后世《近思录》续编、仿编者所宗,因袭沿用,故《集解》成为《近思录》众多注本中流布最广者。
初步考察朝鲜半岛、日本现存“《近思录》文献”便会发现,与清代中后期中国本土学者多推崇江永《集注》相比较,朝鲜、日本学界对这位考据学家的注本并不感兴趣,因为韩、日现存版本中他们刊抄的江永《集注》寥寥无几。
因而,朝鲜、日本学者读者主动或被动接受《集解》的行为,在其朱子学思想发展史上,特别在其本邦理学文本建构中表现明显,如朝鲜朝朱子学名家金长生、郑晔《近思录释疑》采用了叶采《集解》的卷目,日本海西朱子学派代表中村惕斋《近思录训蒙句解》依叶采《集解》而用浅显的文字进行注释,京都朱子学派传人宇都宫遯庵《鳌头近思录》兼采叶采注解甚多。
(一)朝鲜学界在积极传播《集解》之后,不久出现了辨疑之声
历史上叶采《集解》也是最受朝鲜欢迎的注本,或直接翻刻,或活字印制。韩国学者认为叶采“出于朱子……采为《集解》,而并收吕成公及张南轩、黄勉斋、蔡节斋、李果斋之说,而献于朝,广诸海内”[10]序,能助益朱子学的传播,因而叶氏《集解》在朝鲜朱子学派眼里地位甚高,在李朝初期理学思想的传播过程中发挥了积极作用。他们借助重刊叶采《集解》来建设本邦朱子学入门读本,韩国现存文献确实佐证了叶采《集解》传本数量远超《近思录》原文本,可以说《集解》成为他们了解宣扬理学的基础文献。
李朝前期的儒家对叶采《集解》持肯定意见的占绝对多数,诸如金长生、宋时烈之流,承继本邦李珥朱子学思想,忠信程朱理学,取叶采《集解》“以理旧学,则字有其训,句有其解,不翅若瞽者之有相矣”。他们在自己的注文中多处引用李珥、李滉、金长生之言,以体现本土学者的主张;又多引朱子之说补入各卷,互成部居,注释之中兼有续编。在注释校刊《近思录》时,即使对叶采注解的文字偶有訾议,然对其主体依旧肯定,仍以此《集解》为底本进行释疑。等到李朝中后期,朝鲜学者在接受《集解》时不再无原则的苟同,接受的同时对其注文的质疑、批驳之声渐多,一味赞同叶采注释者渐少,如姜奎焕《近思录集解札疑》、李宗洙《近思录叶注札疑》、南汉皜《近思录叶注记疑》、李汉膺《近思录叶注疑义》、柳鼎文《近思录集解或问》等,他们质疑《集解》,评其不足,纠其失误。
概而言之,朝鲜学界对《集解》既接受又扬弃,在肯定中又流露出疑问,如《近思录释疑》的编校者郑晔、金长生、宋时烈不只是对《近思录》部分条目进行了诠释、考证,更多地是对叶采《集解》的注文进行质疑评析,或解释《集解》中的注文,或指出叶采注文的未稳、未安、不衬切、语序不当、牵强处,然而《释疑》的注文在字里行间包蕴着商讨的口吻。如《释疑》卷一第21条对于叶采注文“人之有生”至“是之谓性”,《释疑》云:“‘生之谓性’,告子语也[11]卷一,32……此性字乃气质之性也。叶氏所谓‘理囙具焉,是之谓性者’,此以理言也。释生之谓性,似不衬切。”又如卷二卷首对于叶采所拟提要“‘总论为学大要’止‘尊德性矣必道问学’”,指出其未安处,注云:“沙溪曰:‘首卷论道体,非尊德性也。’叶氏以尊德性言之,恐未安。若是泛论以起道问学,则又似赘。”[11]卷二,1再如对于卷二第81条语录中叶采注文“杂揉之质”,《释疑》注云:“‘质’字未稳,‘揉’恐当从‘米’,杂也。”[11]卷二,45
《释疑》对叶采“集解”的评析质疑,不能说他全无根据,其所阐发的见解自有可取之处。《释疑》在李朝儒学史上影响较大,其注释的态度反映出李朝前期朱子学者对《集解》的尊重,多处用“恐”或“似”字表示商榷之意。正如李朝学者自己所说,“此书固与平岩本注多有异同,而不以为嫌者,本欲公天下之义理而无一毫彼我之私”[11]。可见他们对叶采集解文字不过于讳忌,对其不当之处进行释疑,又体现出学术乃天下公器的思想,故在李朝“读《近思》者不可以无此”书。再者这种敢于质疑叶采注文的举动,说明李朝学者在面对朱学嫡传者叶采的注解时,“墨守之心”有所动摇,他们“能操其戈以入平岩之室”[11]后序,多少也透露出辨疑的胆量与几份自信,显露出李朝中期儒学者具有的批判精神。此《释疑》本因便利于李朝读者阅读理解《集解》,故史上传本较多,以致韩国现存版本多达12种。
李朝后期,学界在肯定《近思录》及叶采集解价值与影响的同时,已经有意将本邦朱子学者的思想资料适时运用于注解《近思录》。如朴履坤认为《近思录》“叶氏之解尚有不能详明者”,于是“用力于是书,复搜宋儒之论,参订东贤之语,随得随札”[10],撰成《近思录释义》十四卷。该书对《近思录》622条语录中的“十之七八”作了注释,既引用中国的程子、朱子、黄勉斋、真西山、饶双峰、陈潜室等先贤语录,又参照本邦李滉、李珥、金长生等名贤的语录进行解说,对叶采集解提出异议,阐发己见。“所引所按,井井有据,足以资益于读者”。如《近思录》卷三第49条,叶采集解云:“‘沿流而求源’,谓因言以求其意也。”朴履坤却认为:“叶注谓因言求意,愚则以为因《传》而求《易》也。”卷十四第17条,朴履坤又云:“‘教人而人易从’,注(笔者按,即叶采集解)‘教人各因其资’。按,注说恐非。诚在言前,故人自化而易从也,且非但指学者。”[10]卷三,4
(二)日本学者则对叶采注解文字提出质疑或生发不满
日本现存刻印、抄写中国学者的“近思录文献”版本约51种,叶采《集解》占其中41%,其传本数量在日本远超《近思录》原文本,这充分说明叶采《集解》最为历史上日本学界青睐。其中部分重刻本内容与《集解》汉籍原本完全相同,甚至连版式也完全相同,如出一辙。如朱熹、吕祖谦编集,叶采集解,明代吴勉学校阅的《近思录》,日本宽文十三年(1673)石渠堂重刊本,国立公文书馆有藏。其版式为:每半叶九行十八字,注文小字双行十八字,白口,单鱼尾。其版式、卷首书名页等与中国本土明稽古斋刻吴勉学校阅本基本相同。
历史上日本注家注释《近思录》时,基本依据于当时的通行本叶采《集解》,又在自己的注本中直接批驳其不足,他们尊信朱子又不盲从朱子思想。例如,贝原笃信主张读《近思录》当先明此书各卷文字之意,然后方能通其义理,故其《近思录备考》强调训诂考据,以助本土读者理解文辞。《备考》卷十第2条针对叶采《集解》注文“得乎一丘之民,则可以得天下”,考述云:“王观涛《四书翼注》云:‘得乎丘民,非只是得一丘民之心,即天下之民归心也。只论个得民心可以有天下的道理。’愚谓,王说可据,叶氏注‘得乎一丘之民,则可以得天下’之说,恐未是。”[12]卷十,1笔者以为,结合叶采此处的其他注文,可见其强调治国当有“恻隐爱民之心”,贝原要表达的主旨与其一致。
与贝原笃信学风相近的仲钦,专奉宋儒之学,长期在本土宣扬程朱理学思想。他在编辑《四书钞说》之后编撰《近思录钞说》十四卷,认为《近思录》是从为学修身论及修齐治平,直至成贤成圣、明晓道体,而叶采《集解》却让“初学之士不能得致思之端而了其旨归”,故批驳叶注不足。[13]于是,他以《集解》为底本,抄录叶氏注解“难通之章,而各附录诸儒之说”,并增补自己的注解,冠以“钞说”之名,撰就《近思录钞说》。其《近思录讲说》对山崎闇斋训点本《近思录》注解甚详,也引朱熹、陈淳、三宅尚斋等学者之论说,兼而评析叶采注解。
客观地审视《集解》我们便会发现,相较于史上其他《近思录》注本,《集解》有许多可圈可点之处,然亦并非完美。如朱熹在《近思录》第十三卷“辨异端”中汇辑四子关于释老的论说,借四子之言对其有过甄别和简评,指出理学与这些学说的差异。后世注家在注解时,当有必要探寻本源,将理学思想和其他诸家思想学说的差异之处阐明,以释读者疑惑。叶采《集解》只是笼统地说两者似同实异,至于哪里同,读者恐不甚明了。对此,清代茅星来《集注》在注解关键词后,比较了佛、儒之同,引用朱熹相关论述来佐证自己见解。故而,茅星来指出叶采《集解》“稍费拟议处则阙焉”,并非妄言。
对《集解》此类不足,日本学者在批评时也有与中国注家略同,如与茅氏同时期的日本朱子学家山崎闇斋注释《近思录》时,认为“叶仲圭为《集解》,杨伯嵒为《衍注》,皆未能深有所发明”[14]。故弘化三年(1846)高津泰《近思录训蒙辑疏序》云:“叶氏私淑于北溪陈氏,其说宜得朱子之意,而其注往往不满于人意。故我先儒闇斋山崎氏尽除之,单以白文行于世。”[8]现存史料也证明山崎闇斋确实不满叶采集解,而将叶氏注本中的注文删除,仅以白文的形态向世人传播。
朱熹说《近思录》是学习《四书》的阶梯,而在东亚《近思录》传播历程中,《集解》又是阅读理学经典《近思录》的最佳入门阶梯,东亚朝鲜、日本社会并没有因为它存在瑕疵而唾弃,而更多地是褒扬,现存版本之多就是史上东亚社会对其肯定的有力佐证。
三、结 论
《集解》对东亚影响深远,但理解又不同于中国本土。
(一)朝鲜、日本学者理解《集解》有差异
叶采《集解》是中国《近思录》注本的代表,也是朝、日翻刻并以之构筑本土朱子学的基础文献,长期持续不断地在东亚汉字文化圈发挥着积极影响,在朝鲜、日本广受好评,极富盛名,或直接翻刻,或活字印刷,或抄录研读。他们积极吸收叶采注本的主要内容,或在叶采集解的基础上作以“详明”的注释,如朝鲜朴履坤的《近思录释义》;或依托于《集解》向求学者讲解其主要内容,如日本中村惕斋的《近思录钞说》,室鸠巢的《近思录鸠巢先生讲义》。
南宋《近思录》一直健全地活在东亚,但是在尊奉儒学的汉字文化圈下,不同的国度对于叶采《集解》却态度有别。中国本土基本谨守《集解》,不断对其进行刊刻传抄的主因则是:(1)在《近思录》传播史上,是叶采《集解》首次将朱熹的学术思想与北宋四子贯串起来,这在《近思录》诠释史上是一种创举,又弥补了《近思录》中无朱熹思想资料之缺。(2)在东亚《近思录》后续文献纲目编纂方面,《集解》不仅给后来的其他注家提供了参照之本,而且其所设置的纲目名称及其注解义理之思路,对后来其他注释本、续编本产生了积极影响。
束景南先生说:“在朱熹以后直到近代,程朱理学在很大程度上是借助于《近思录》的注释刊刻流布得到广泛传播的……因而一部《近思录》的注释传刻流布史,也就是一部宋明到近代的理学接受史。”[15]在东亚朝鲜、日本接受朱子学以及《近思录》注本时,面对朱熹血脉嫡传者叶采的《集解》,其儒者表现出的态度,也是我们考察他们思想情感的重要途径。对《近思录》的注解是各个时代的理解,又是不同人的解释,那么对《集解》的解读、诠释便烙上了时代与注解者的印迹,或深或浅,或浓或淡,或肯定主体兼而质疑不足,在东亚社会呈现出对《集解》褒扬、辨疑、批评的历史景观。
从叶采《集解》在朝鲜、日本被接受扬弃的历史考察,我们能明确地感知,他们受中国政治思想、学术传统的束缚有限,在承传中国历代注家诠释思想的同时,其学者能大胆质疑,敢于批判接受,发表己见。这些特征也印证出在其社会发展中后期,其本邦朱子学思想的逐渐成熟。
(二)朝鲜学者在吸收叶采注本主体内容的同时,敢于释疑和辨疑,从中展现自己的理解与主张
历史上的朝鲜,在思想文化方面有着深厚的中国渊源,对中国的政治、思想学术多能主动接受。宋代儒学的主流派“程朱理学”,对他们也产生了异常深远的影响。《近思录》自南宋后期传至朝鲜半岛,朱熹的“阶梯”之说、《近思录》的“入道”价值,便得到了高丽学者的肯定,随后对李氏朝鲜政治思想、学术文化产生了很大影响。流布朝鲜的《近思录》及《集解》等文献,代表的是先进、发达、文明程度较高的文化,以致李朝前期的儒学名家金宏弼、郑汝昌、赵光祖、李彦迪、李滉、李珥、金长生等,都能主动接受并加以传播,李朝在受容《集解》时又以之为基础新生出反映朝鲜朱子学的新注本,这些拥有时代意识、本邦特色的生命体态,大大推动了朝鲜理学的发展。
叶采《集解》为朱子学脉之嫡传,在朝鲜人的心目中,其内容很适用于教导求学问道者,可为程朱理学在朝鲜的发展壮大奠定基础。朝鲜在接受《集解》时,又在新创文本内容上展露兼容并蓄的思想,既将宋元明清具有代表性的理学家语录收入其中,又兼顾本邦名家语录,辑录李滉、李珥等朱子学大家的论说文字。如金长生《近思录释疑》、李瀷《近思录疾书》、林翰周《近思录叶注存疑》等文本,较多地展现出本民族学者关于《近思录》思想的别样诠释。因而,朝鲜学者在从异国他乡流布而来的《集解》这一“母体”上进行了文化增值,或增删或辨疑或校订,在再注解《集解》的过程中,其民族的主体意识,隐约之中也由面对宗主的自卑走向一种民族自尊。对中国本土相关理学文本敢于质疑或甚至批驳,反映出朝鲜儒者民族主体意识的觉醒,以致酝酿出李朝中后期对于居统治地位数百年的朱子学的不满。
(三)日本社会曾长期尊信朱子学,江户时期的日本朱子学与中国朱子学虽有共性,却也有其独立发展的一面
在受容中国历代注家诠释思想之时,即便是长期被世人诵习的叶注,日本学者也敢于批判,不一味盲从,解说时增附己见,流露出一种民族自省和自信意识。他们或将叶采《集解》吸收转化为本土文本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将中土文献为己所用。这在很大程度上与其学者不受中国政治意识、学术传统、门派之争的束缚有关,故他们在接受朱子学嫡传者叶氏《集解》时,流露出大胆的批判声音。
相较于李朝学者,日本学者对于叶采的“集解”异议更多,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1)有日本学者指出《集解》训诂考据的不足,如前文所言贝原笃信《备考》卷十第2条针对叶采《集解》引文的考证。(2)有学者不满叶采注文而将其删除,仅以白文的形态向世人传播,如《近思录》山崎嘉训点本。(3)有学者认为叶采《集解》、何基《近思录发挥》释义未尽,不能完全阐明《近思录》文理微旨,以致初学者有所困惑。如泽田希在《集解》“字义事实未尽训释,文理微旨或未阐明”的情形之下,博搜旁考“濂洛关陕全书以至诸儒百家之论说,及子史字书异端之编”,以师友之言论为佐证,进行注说,并直陈叶氏注解的不精不详,经“月订岁改,积若干年而成”《近思录说略》十四卷。[16]
(四)朝鲜、日本学者之间却有微异
在批判性接受《集解》时,朝鲜学者赞扬之余,肯定的成分远多于否定,即便有疑,仍以商榷的口吻解说,大量使用“恐”“似”“如何”等表委婉揣测之意的词语;日本学者对《集解》不盲从,解说时展示己见,为我所用的价值取向较明显。可见两国批判程度的微异,也折射出他们对程朱理学思想的认知差异。
同时,两国在重刻叶采《集解》系列文本时还存在截然不同的一面,这可从明初周公恕整理改造《集解》而成《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在朝鲜、日本的流布可窥一斑。在两国宗信中国儒家文化的时代,这类反映程朱理学思想的书籍应该很容易进入他们的视野,被当地学者读者阅读使用,但是在韩国现存藏书目录中很难找到关于《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的记录,而在日本现存汉籍与和刻汉籍中却保留有相当数量的版本,既有中国明代时期的刊本,也有日本本土的刻印本,如宽文八年(1668)石渠堂刊梓的“吴勉学校阅”本、宽文十三年(1673)吉野屋权兵卫重刻稽古斋本、贞享五年(1688)利仓屋喜兵卫改版刊本、八幡屋重兵卫据石渠堂本改版刊本等。
这一现象说明,在接受消化源自中国的理学文献时,朝鲜社会的选择趣向与同样崇尚中国儒家文化的日本并非完全一致。对于周公恕《分类经进近思录集解》,朝鲜学者可能更信奉明清之际中国理学家的评判。如明末清初的黄虞稷认为,周公恕《近思录分类集解》十四卷是“就叶采《集解》参错杂折之,非叶氏本书也”,清初江永批评周公恕“以己意别立条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细校原文,或增或复,且复脱漏讹舛,大非寒泉纂集之旧。后来刻本相仍,几不可读”[17],因而朝鲜半岛很少珍藏。然而,江户时代的日本学者已逐渐失去严格固守中国本土尊崇《集解》心态,故藏有诸如此类的文本,新创的此类本土化色彩较浓的文献要多于当时中国的属国朝鲜。
——一种可能的阐发途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