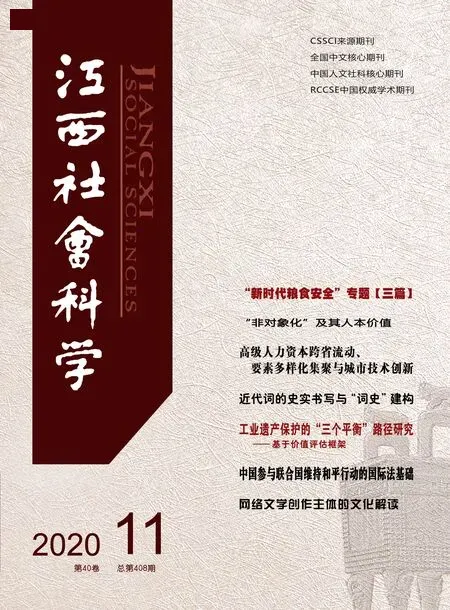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研究
《民法典》首次通过立法肯定日常家事代理制度。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与一般代理权存在差别,但这只是量的区别,不能改变日常家事代理权为法定代理权的性质。界定日常家事的范围是家事代理权制度的研究重点。决定是否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应依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例如夫妻的社会地位、职业、资产、收入、兴趣、家庭人口)及其共同生活所在地区的习惯等而定。基于社会生活的多样性及婚姻关系的复杂性,特殊情况下日常家事代理权应予以扩张与缩减,但必须符合相应条件或遵守相应规则。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以下简称《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夫妻一方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但是夫妻一方与相对人另有约定的除外。”“夫妻之间对一方可以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范围的限制,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这表明我国民事立法首次肯定了日常家事代理制度。然由于此条之规定仍过于抽象、简略,在解释与适用时不免产生歧义与困扰。立法及理论对于日常家事代理的法律性质、日常家事范围的界定、特殊情况下日常家事代理权能否扩张或者缩减规则等仍存在争议,有鉴于此,本文试图对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若干问题加以探讨。
一、日常家事代理的法律性质探讨
日常家事代理,通常是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对于日常家事夫妻之间得互为代理人,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夫或妻可以代理另一方为一定民事行为。该制度设立的目的,一方面在于让料理家务的配偶在履行义务时,对外享有必要的经济上的行动自由,但仅限于日常家事范围内,对于涉重要之家事或非共同事务则并无当然代理权,夫或妻在决定之前要征得另一方之同意或单独授权;另一方面是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有利于简化交易程序、维护交易安全、避免善意相对方权益受到损害。
对于日常家事代理的法律性质,学界认识并不统一,存在不同观点,主要可分为:(1)法定代理说。该说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基于法律规定而产生,是国家立法机关基于保护公民和维护交易秩序的特别需要而做出的关于具有特定身份的民事主体有权代理他人为民事法律行为的规定,因而其为法定代理。①(2)特殊代理说。该说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既不是法定代理,也不是委托代理,而是一种特殊类型的代理。②
日常家事代理制度源于古罗马法的委任制度,但它仅指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妻子对丈夫单方面的代理,即丈夫就日常家事代理对妻子的委任,故也被称为家事委任或默示委任。随着古罗马帝国经济社会的兴盛,原有的家长事必躬亲的制度已不再适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变化,通过古罗马元老院及大法官创设各种诉权的方式,家事代理的对象及范围得以不断扩张,最终使家属成员和奴隶代理家长或家主从事商品交易成为可能。例如,其中“奉命诉”规定,凡家属或奴隶奉家长或家主之命而与人订约的,其家长或家主应与其家属、奴隶共同对第三人负连带责任。妻子由此取得在丈夫委任之上的一定民事行为的能力,日常家事代理即包含在其中。[1](P61-62)在日耳曼法中,妻子对日常家事的代理根源于婚姻效力说,即夫妻是婚姻共同体的成员,妻子对日常家事代理是婚姻的当然效力。《瑞士民法典》以及1942年法国修订民法典时,均受到日耳曼法思想的影响,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属于婚姻的当然效力,即采用法定代理说。
从大陆法系现代各国或地区的有关立法规定来看,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的家庭法直接将家事代理定性为法定代理,如奥地利、挪威、捷克、斯洛伐克、瑞士、加泰罗尼亚均属此类。更多的国家则没有直接将家事代理通过文字“代理”表达出来,而是从夫妻一方家事代理行为的法律效力直接及于另一方的教义解释角度认为家事代理系法定代理,如比利时、法国、意大利、西班牙等。但需指出的是,也有学者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之法律性质非常特殊,不能用现有其他法律制度去解释或将其纳入现有代理制度体系中。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与众不同主要表现在:虽然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律后果可直接对合法配偶另一方发生效力,但在法律要件上并不要求行为人需要明确的代理意图,更不要求代理行为人需要向交易相对人明示代理的意思表示,此与普通代理在法律要件上存在明显不同。所以,德国法学界通说认为家事代理是特有的家庭法法权。[2](P87)[3]在英美法系国家“同居产生的代理”是源于法律的直接规定,它属于“法律自动构成代理”,因而其采取的是婚姻效力当然说。
笔者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与普通民事代理法律制度确实存在明显差异,但其主要不同仅为“量”上的差别,并无“质”的不同,我们不能据此否认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律属性。首先,日常家事代理权虽然是为了夫妻共同生活之便利而做出的规定,但其规定的目的并不限于此,夫妻双方通过日常家事代理权扩张其行为能力也不能不说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立法初衷之一,而且在客观上,这项权利也起到了这样的作用。其次,在日常家事代理中,配偶一方不需以被代理的另一方名义为法律行为,而是基于法律关于婚姻当然效力的法律规定,在日常家事范围内配偶从事法律行为,其效力自然及于配偶另一方,不需如普通代理那样通知交易相对方,此正是法定代理权之不同属性所在,而不能据此否定其代理权性质。③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律属性,决定了合法婚姻关系的存续是日常家事代理权的前提与基础。仍需进一步探讨的是,在事实婚姻或男女同居状态等非合法婚姻状态下能否享有家事代理权以及在婚姻关系破裂之后,家事代理权是否随着婚姻关系的终结而终结?
通常情况下,由家事代理权的法律属性所决定,各国民事成文法一般均规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适用范围仅局限于合法婚姻关系的配偶之间。但也有民法学者认为:“夫妻是否为事实婚姻抑或正式婚姻,外部难以认知,既知为事实婚姻,就日常家务为交易之相对人,亦系对事实上婚姻之夫妻共同体为交易,故应与法律上之婚姻为同样之待遇,事实婚姻的夫妻也应准用日常家事代理权。”[4](P323)英美法系“由于同居产生的代理”并不限于妻子的权利,也适用于同居关系的女方,因为“由于同居产生的代理”是基于同居关系产生的,并不是婚姻的法定效力,只要具备同居、家庭住所、没有剥夺妻子权利的因素等条件,同居关系的女方就应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权。笔者认为,事实婚姻属于已成立的婚姻,在未依法被撤销或被宣告无效之前,仍应受法律保护,因而事实婚姻的当事人应互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主体。但同居关系的男女因其缺乏合理合法的公示方法,不宜承认其互为日常家事代理权的主体,否则容易导致家事代理权的滥用以及对其法律属性的破坏。
夫妻在婚姻关系破裂之后,一般认为家事代理权亦随着婚姻关系的终结而终结,此为保护离婚后双方的合法权益及维护交易安全所必需。但也有学者认为:“已离婚的男女原则上彼此不再互享日常家事代理权,但在共同抚养教育等某些特殊方面仍可以保留此种代理权。”[1](P68)本文认为,既然日常家事代理权是婚姻的当然效力,而离婚导致婚姻关系的解消,因而离婚后的男女当然不再互享日常家事代理权。即使是约定离婚不离家,或是在共同抚养教育未成年子女问题上,亦如此。实际上,离婚后子女的抚养、教育等问题是通过亲权制度来解决的。
二、日常家事的判断标准
日常家事的范围决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边界。明确日常家事的范围,不仅可以避免配偶一方利用日常家事代理权强求另一方在共同生活的重要事项上接受既定事实,而且也可以避免日常家事代理权被配偶一方用来从伴侣的财产中获得扶养法上的好处,此外,也有利于保护交易的安全,维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
日常家事也称共同家计,对其范围进行界定应结合国家地域、习俗文化、社会地位、收入状况、职业状况等因素综合考量,不能一概而论,各国对于“日常家事”的界定标准各不相同。
(一)日常家事应以适当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为判断标准
如《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第1款规定:“配偶任何一方有权处理旨在适当满足家庭生活需要的、具有也有利于另一方的效力的事务。”按照该条进行解释,共同家计的范围应符合以下两项条件:(1)该事项须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即服务于共同的家庭生活,就主体而言包括夫妻双方及其未成年子女以及尚未独立生活的成年子女。就内容而言,家庭生活需要包括各家庭成员的个人需要(衣物、化妆品、子女的学费),此外还包括业余活动开支,但业余活动如果仅涉及配偶一方,则属于家庭领域之外的事务。(2)能够代理的日常家事须与该家庭的经济状况和生活习惯相符合,即应具备适当性。日常家事不仅应在类型上属于生活需要交易,在程度上还须具备适当性,不超出该家庭的经济承受能力和生活习惯。每一个家庭,夫妻习惯不同、职业不同、收入不同,由此产生生活消费的需求与消费习惯也各不相同,适当性要求所代理的日常家事在种类和范围上与其所处同等阶层或同等经济状况家庭之平均消费水平相称。
然而由于“适当满足家庭生活需要”之范围非常广泛,其包括了住房、汽车、业余活动、度假直到养老保险等各种扶养需要,为了避免该款规定的范围过于宽泛,必须通过目的考量对交易范围进行一定的限定,应限定于与共同家计密切相关的交易,如采购家庭日常用品、食物以及其他维持正常家庭生活所必需的支出。专为家务和家庭业余生活而不是为配偶一方工作需要购买轿车的,也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范围。配偶一方和电信公司签订合同,在婚姻住宅安装固定电话的,一般也属于满足家庭基本需要的交易。但若交易从根本上决定或改变了家庭及其成员的生活状况的,如出售、购买或建设房屋等,这就不属于日常家事之范围。另外,涉及财产投资和管理的措施,即使该财产措施有利于满足家庭供养,也不能适用第1357条;配偶的工作和职业领域(如签订劳动合同、加入工会合同、报名参加培训课程等)也不适用第1357条。只有当通过贷款购买特定的商品或服务是为了满足家庭生活需要时(如通过所有权保留或第三方支付的方式购买家具、在商家赊购货物),才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权交易;为获得资金的贷款行为不能适用第1357条,即使该笔贷款事实上用于满足家庭生活需要。当然,若某百货商店允许配偶一方在一定数额内借贷消费,配偶一方在总额范围内签订的多个购买合同均可适用第1357条,因为这里的贷款已经体现为一系列具体物品。子女接受医务治疗的合同毫无疑问属于第1357条第1款的适用范围,对于配偶为自己签订的医疗合同是否属于日常家事代理权交易,虽有争议,但通说认为其会产生双方的共同责任,不过在确立共同责任之前需要审查:(1)患者本人是否愿意单独承担全部义务;(2)治疗的紧迫性和选择的治疗方案之间是否存在适当性。此外,第1357条并不包括对另一方配偶所有权的支配权限,只有在非常情况下才存在例外,例如困难时期不得不以物易物时。[2](P88-93)
(二)日常家事应以维持家庭日常生活和子女教育事项为判断标准
法国民法的规定即属此种类型。《法国民法典》第220条第1款规定:“夫妻各方均有权单独订立旨在维持家庭日常生活与教育子女的合同。夫妻一方据此缔结的债务对另一方具有连带约束力。”“但是,视家庭生活状况,所进行的活动是否有益以及缔结合同的第三人是善意还是恶意,对明显过分的开支,不发生此种连带义务。”1985年12月23日法国第85-1372号法律第2条又规定:“分期付款方式进行的购买以及借贷,如未经夫妻双方同意,亦不发生连带义务;如此种借贷数量较少,属于家庭日常生活之必要,不在此限。”此外,其司法实践认为,家庭投资活动,尤其是以构建不动产财产为目的而进行的投资合同,不属于第220条当然赋予连带性质的家庭生活与子女教育活动(最高法院第一民事庭,1984年1月11日);丈夫因休闲旅游而购买机票的票款,妻子不负连带义务。因为第220条所设置的连带义务,即使不是以费用开支的紧迫性为基础,至少也是以此种开支的必要性为基础(巴黎,1989年10月11日)。[5](P207-209)
(三)日常家事应以属于经常的日常家务为主要判断标准,并应参考其他相关因素
日本民法理论及司法实践中采用此观点。日本学者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不应仅以家庭生活内容为必要,还应当以被代理配偶方的消费程度作为参考标准。”[6](P88-89)依据日本最高法院1969年12月18日判例解释,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权需考察两点:第一,考察“夫妻的内部情事和某具体法律行为之目的”,共同家计之具体范围,与家庭所拥有的财产状况及夫妻的职业、收入等因素相关,社会地位、薪酬及其他收入不同,生活习惯和消费能力也不同,日常家事的范围也应有所不同。第二,考察“该项法律行为之种类和性质”,如对于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的、与衣食住行直接相关的事务应当推定为属于“日常家事”,但如果该物品的价值过高、有悖常人理解之生活必需品除外;此外,对于家庭成员之医疗保健教育抚养、文化消费与娱乐锻炼活动等事务也应属于“日常家事”;对于借贷行为,则应考察借贷用途是否为共同家计及借贷金额是否超出必要限度进行综合判断;对于处分配偶另一方财产的行为,日本判例的态度是“不问处分目的如何”,一般认定不在“日常家事”范围之内。[7]
我国台湾地区学者持类似观点,如史尚宽认为,日常家务如“一家之食物、光热、衣着等之购买,保健、(正当)娱乐、医疗,子女之教养,家具及日常用品之购置,女仆、家庭教师之雇佣,亲朋好友之馈赠,报纸、杂志之订阅等,皆包括在内”。“其范围不独依夫妻共同生活之社会地位、职业、资产、收入等有所不同,而依该共同生活所在的地区之习惯,亦有异。此普通代理权,在特殊情形,例如有紧急情形或夫远离不在家,冠婚丧葬,得因而扩张。”[4](P284)戴炎辉和戴东雄认为:“日常家务云者,指一般家庭日常所处理之事项而言。不但客观的一般家庭妻日常所处理之事项,而且主观的在特定家庭妻日常所处理之事项,亦可谓为日常家务。保全财产之诉讼行为,不可谓为日常家务,公司之事务亦同。决定其是否属于日常家务,通说以为须以夫之实际收入额为标准。惟夫之实际收入额若何,第三人不得而知,若以实际收入额为标准,则第三人不免受不测之损害。”[8](P164-165)王泽鉴认为,日常家事“指一般家庭日常所处理的事项,例如购买食物、衣物、家用电视、冰箱,油漆住所墙壁等,应依夫妻表现生活的程度决定之”[9](P622)。陈棋炎等认为,日常家务的范围,“从日常家务之字义言,应为一般家庭日常必需事项,但社会上,家庭不一,各家庭需要也各有差别,所以除客观的一般家庭所需者外,主观的在各该家庭,妻日常所处理事项,亦可称为日常家务,较为妥当”[10](P144-145)。
我国最高人民法院在《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第17条以及《夫妻债务适用法律解释》第3条虽提到了“日常生活需要”或“家庭日常生活需要”,然对何谓“日常生活需要”或“家庭日常生活需要”并未作出明确界定。《婚姻法司法解释(一)》的起草者认为:“日常家事,顾名思义,是指日常家庭生活事务,是指夫妻双方及其共同的未成年子女日常共同生活必要的事项。一般而言,日常家事的范围,通常包括购买必要的日用品、医疗医药服务、合理的保健与锻炼、文化消费与娱乐、子女教育、家庭用工的雇佣等决定家庭共同生活必要的行为及其支付责任。当然,婚姻当事人的社会地位、资产、职业、收入等不同,日常家事范围也有所不同。”[11](P213)
国内理论界对此认识并不完全一致。如有的认为,“日常家务”的范围,包括夫妻、家庭共同生活中的一切必要事项。诸如购物、保健、衣食、娱乐、医疗、接受馈赠等等,皆包括在内。[12](P783)有的则认为,下列事务,任何情况下均不属于日常家事范围:(1)处分不动产。(2)处分具有重大价值的财产。(3)处分与婚姻当事人一方人身有密切关联的事务。如领取劳动报酬、放弃继承权等。[1](P61)
结合前述分析,日常家事的范围,应依夫妻共同生活的状态(社会地位、教育程度、财产状况、收入情况、家庭人口等)及其共同生活所在区域的文化习俗等而定。对于维持家庭共同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医疗卫生、子女教育、父母赡养支出以及必要的康体活动、文化消费等合理支出,应纳入日常家事范围。笔者认为,以下事项应属共同家计:(1)维持家庭正常生活所必需的衣食住行开支;(2)对未成年子女的教育、抚育支出;(3)对年老父母的赡养支出或其他有抚养义务家庭成员的必要支出;(4)家庭成员必要的医疗卫生服务费用;(5)必要且合理的文体活动、人际交往所需的基本支出;(6)其他为维持正常生活状态或维持与其社会地位相称的基本生活品质所必需的支出。但以下事项除非另有约定或单独授权,否则应被排除在共同家计的范围之外:(1)与其家庭生活状态及所在区域文化习俗不相称的、显著超出家庭日常生活所必需的开支;(2)对家庭不动产或价值较大的动产的处分行为或举债赊购大额资产行为;(3)合伙、项目合作、股权投资、提供担保以及其他具有较高风险的商业行为;(4)配偶一方具有人身专属性、不得代理的行为。
三、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与减缩规则
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与减缩,指原本不应属于或应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但因特殊情况的发生而被纳入日常家事或被排除在日常家事之外,夫妻双方得互为或不得互为代理人,得对外或不得对外为一定的代理行为。
(一)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
为了实现日常家事代理制度设立的宗旨,一些国家或地区的有关立法明确规定了在特殊情况下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规则。即将原本不应属于日常家事的范围,因特殊情况的发生而被纳入日常家事,夫妻双方互为代理人,得对外为一定的代理行为。
属于家事代理特别规定类型的大多数国家,虽然其家事代理的范围千差万别,但都承认被代理的夫妻一方如因缺席、患病或能力缺失而不能作出代理授权表示或无正当理由拒绝的,夫妻另一方有权对其进行代理。奥地利、比利时、捷克、丹麦、法国、立陶宛、马耳他、荷兰、波兰、葡萄牙、瑞士和加泰罗尼亚等对此均有特别规定。
各国或地区对夫妻一方在此情形下如何获得家事代理权的规定,我们可以将其分为两种:一种是自动获得。如《瑞士民法典》第116条规定:“在特别紧急的情况下,如夫或妻一方不马上行使家事代理行为就会造成不可挽回的巨大的损失时,可以由一方先进行处理,这种行为仅限于紧急且有利于夫妻共同利益的情形。”《瑞典婚姻法典》第6章第4条第1款第1句规定,夫妻一方因患病或缺席而不能自行照管其事务且缺少家庭供养物质的,夫妻另一方可以在必要的范围内使用患病或缺席夫妻一方的收入和财产收益以及取走其银行存款和其他资金。我国台湾地区“民法”对此未作规定,但其司法实践中有判例认为:“妻处分其夫之不动产,通常不属于第1003条所谓日常家事之范围,惟其夫应负家庭生活费用,而在沦陷期间侨居海外者,关于支付家庭生活之必要行为,不得谓非日常家事,如依其情形,妻非处分其夫之不动产不得维持家庭生活,而又不及待其夫之授权者,其处分不动产,自属关于支付家庭生活费用之必要行为,应解为包括于日常家事之内。”[7](P316)另一种是向司法机关申请授权。其中有的国家规定夫妻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单独处理家事,如法国《民法典》第217条和第219条规定夫妻一方不能作出表示或其反对有悖于家庭利益时,另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授权其单独处理。此外,还有国家规定夫妻一方可以向法院申请要求直接代理夫妻另一方,如波兰《家庭和监护法典》第39条规定,夫妻一方拒绝同意而给另一方行为造成不可逾越的困难时,另一方可以请求法院代为同意。[3]
我国《民法典》对此未作任何扩张性规定,属于立法漏洞,不利于特殊或紧急情形下维护家庭利益,笔者认为,对我国《民法典》自应作瑞士民法等规定之相同的解释。不过,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应符合下列条件:(1)主观要件必须是为了家庭的基本生存需要,行为人秉承善意,目的是防止家庭财产出现不必要的损失,且范围不得任意扩大。(2)客观要件之一必须是发生了紧急情况,所发生情势必须是不得延误,须即时处理。(3)客观要件之二是出现了与配偶另一方无法联络或无法获得配偶另一方同意的紧急情况(如被代理一方失踪或意识丧失等)。(4)所实施的代理行为在处分对象及处分方式等的选择上是适度的和经济的,已尽到谨慎、勤勉等注意义务。
(二)日常家事代理权的缩减
日常家事代理权虽为法定权利,但在某些情形下,如发生特定事由或者基于夫妻间的协议,这一代理权的行使也可能受到一定限制。
依我国《民法典》第1060条第2款的规定,日常家事代理权可因夫妻双方的约定而受到限制,当然,这种约定不得对抗善意第三人。但对于因一定事由的出现而导致日常家事代理权受到限制的问题,我国《民法典》并未作出规定。从比较法及各国司法实践来看,能够导致日常家事代理权缩减的情形归纳如下:
1.配偶一方存在滥用代理权情形时,相对方可限制或禁止其行使家事代理权。权利滥用将导致权利受限或权利丧失,此为通理。权利滥用包括故意(积极)滥用及消极滥用两种情形。消极滥用包括配偶一方违反代理人应尽的注意义务、善管义务以及无代理能力越权代理等。对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限制,我们应当注意的是:第一,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限制方法,应当采用向交易相对方(第三人)发出通知的方式,才能发生代理权被限制或被禁止的法律效果;如果该通知仅向配偶一方发出,为维护交易安全及善意第三人的合法利益,不能产生相应的法律效果。当然,如果有证据表明第三人存在恶意时,虽然未向其发出限制或禁止通知,也能产生日常家事代理权缩减的法律效果。第二,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限制范围,可以根据实践情形全部或者部分限制。全部限制,我们也可称其为禁止,是指配偶一方在某些情形下禁止另一方行使任何日常家事代理权。部分限制,我们也称其为日常家事代理权受限,即限制配偶一方代理某些日常家事的权限,比如禁止举债赊购或超出家庭支付能力的购物行为等。当然,在权利滥用的原因消失时,如风险认知能力及识别能力恢复或越权代理行为已消除时,其日常家事代理权可以得到恢复。第三,日常家事代理权的限制效果。无论是日常家事代理权被禁止或被限制,其效果均不及于善意第三人。正如前文所言,日常家事代理权乃婚姻之当然效力,对不知行为人家事代理被限制的交易相对人除非有证据表明其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否则不能产生代理权已被缩减的法律效果。
2.夫妻因感情不和而法定或约定分居的。婚姻以感情为纽带,夫妻分居既是共同生活状态的中断或结束,也是婚姻基础出现危机的表征。因此,有学者认为,夫妻因感情不和分居后,为方便共同生活目的而设置的法定代理权亦应自然终止,即分居状态下配偶所为法律行为仅对自己产生法律效果,对另一方不生效力。从比较法的角度来看,大陆法及英美法国家均有类似规定,但程度及标准存在差别。第一,《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第3款规定:“配偶双方分居的,不适用第1款(注:该款规定了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并且认为:“只要符合该法典第1567条第1款所规定的条件,无论分居状态(包括在婚姻住宅内的分居)和分居时间如何,日常家事代理权均会终止。分居结束后,日常家事代理权也随之恢复(包括双方为了和好而短暂的共同生活,虽然离婚法把这种短暂的共同生活计入分居时间)。分居对此前成立的日常家事代理行为不发生溯及力。”[2](P95)第二,在瑞士,依其民法典所作解释,对于裁判上之分居状态,则日常家事之代理权因此解除,配偶间不再享有家事代理权,然而夫妻一方长期有理由而不在一起生活的(例如旅游或疗养),家事代理权并不因此解除。[7](P317)第三,《日本民法典》对此问题并无明确规定,但“依据判例,在分居的情况下,如果妻子为了获得丈夫的财政援助维持生活,借了必需的款项或处分了丈夫的财产,也不属于日常生活范围之内”。[6]第四,“在法国的民法制度下,裁判之分居、离婚诉讼中之分居,共同家事已不存在,然事实上之分居,并不使家事代理权终了,除已有保障他方配偶生活之安排,应保持家事代理权,如分居,系因配偶一方之过错而失去了婚姻住所,即配偶一方不履行同居义务时,其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因而消灭”;《法国民法典》第304条规定:“除本节之各项规定外,分居之后果受上述第三章对离婚后果所定的相同规则约束。”法国的司法实践认为,夫妻事实上的分居,因婚姻产生的义务仍然存在。但是,其中一方单独缔结的合同,对另一方是否产生效力,应从具体情况分析,只有在此种债务的目的不是为了共同家计时,才能得到认定。[4](P207-208)第五,在英美法,对分居状态下之家事代理权一般也持否定立场,但非绝对。如在美国:“当夫妻双方通过法院的判决而分居时,妻子不享有缔结以其丈夫为合同义务主体的推定权限。”[13](P151)“在协议分居的情况下,夫妻双方能否享有日常家事代理权就要根据分居协议的内容来判断。”[14](P62)“如果协议中没有规定抚养的内容,而妻子又没有其他生活来源,则推定其具有日常家事代理权,但因妻子的过错而导致分居的除外。”[13](P152)
在我国,无论是《婚姻法》还是《民法典》均未确定分居制度,只是在裁判离婚认定夫妻感情是否确已破裂时用到了“分居”一词(“因感情不和分居满2年”)。从我国的司法实践来看,夫妻分居通常通过协议或裁判来实现。但无论是协议分居还是裁判分居,均因制度设置缺乏分居制度而缺失公示方法。因此,为了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应推定夫妻分居期间夫妻仍互享日常家事代理权,但夫妻之一方能举证在其夫妻之另一方代理其与第三人实施法律行为时明知其夫妻已分居者除外。
四、结语
无论是大陆法系还是英美法系国家,现代各国及地区的民事立法基于男女平等原则以及方便生活等考量,一般均规定合法婚姻之配偶双方在共同家计范围内互享代理权。对于日常家事代理行为的法律后果则存在两种不同的立法例:一是规定行使代理权的效果由配偶双方共同承担。即因日常家事所负的债务,夫妻应负连带责任。如德、瑞、日等国的民法采此立法例。④二是规定由丈夫承担,妻子负补充责任。如我国台湾地区“民法”采此立法例。⑤从我国《民法典》第1060条规定日常家事代理行为“对夫妻双方发生效力”来看,我国采用的是第一种立法例,显然第一种立法例更为公平合理,亦有利于保护善意第三人的合法权益。⑥日常家事代理权制度既事关家庭内部的和睦,也事关交易安全。因此,《民法典》虽然在我国首次以立法形式肯定了日常家事代理制度,但准确把握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法律属性,界定日常家事的范围与边界,厘定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扩张与缩减规则,对于正确理解和适用《民法典》第1060条显得十分重要。
注释:
①持法定代理说的主要有:史尚宽《亲属法论》(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315页),刘德宽《民法总则》(台湾五南图书出版公司1996年版,第309页),陈棋炎、黄宗乐、郭振恭《民法亲属新论》(台湾三民书局2004年版,第144页),佟柔主编《中国民法》(法律出版社1990年版,第203页),马忆南、杨朝《日常家事代理权研究》(《法学家》2000年第4期),王荣珍《关于日常家事代理立法的思考》(《广西社会科学》2004年第10期)。
②持特殊代理说的主要有:杨大文主编《婚姻家庭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第148页),张俊浩主编《民法学原理》(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60页),邓宏碧《完善我国婚姻家庭制度的法律思考(下)》(《现代法学》1997年第2期),杨晋玲《夫妻日常家务代理权探析》(《现代法学》2001年第1期),王歌雅《家事代理权的属性与规则》(《学术交流》2009年第9期),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李明建《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范围之界定》(《长沙大学学报》2007年第1期)。
③有学者认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是身份权的一种,是身份权中配偶权的一项内容。”参见:王丽萍《婚姻家庭法律制度研究》(山东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113-114页),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邱冬梅《论夫妻个人财产代理制度及立法构想》(《法律适用》2001年第6期)。有学者则认为,日常家事代理权之性质当属于夫妻之间的财产关系,而绝非身份权,身份行为依其性质是不能代理的。参见马特《配偶权问题探讨》(载于王利明等主编《中国民法典基本理论问题研究》,人民法院出版社2004年版,第296-297页)。笔者认为,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来源来看,其是夫妻双方依其身份依法直接取得的,或者说是婚姻的当然效力之一。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一种亲属身份权;从日常家事代理权的行使范围来看,为在日常家事范围内对外为一定财产性民事活动。从这种意义上说,它又似是一种财产权。实际上,从权利属性来看,日常家事代理权是一种亲属身份财产权。
④参见《德国民法典》第1357条、《瑞士民法典》第166条和《日本民法典》第761条。
⑤参见我国台湾地区“民法”第1026、1037和1048条。
⑥婚姻法学界通常认为,婚姻关系具有隐秘性,第三人在日常家事交易中对此通常难以知情,因此有必要通过日常家事代理规定的夫妻连带责任对第三人给予保护。参见马忆南、杨朝《日常家事代理权研究》(《法学家》2000年第4期)。保护交易安全作为民法追求的基本目标,亦不应成为以夫妻财产关系为基础的日常家事交易之例外,日常家事代理正是通过保护善意第三人进而实现交易安全。参见:史浩明《论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政治与法律》2005年第3期),熊玉梅《论交易安全视野下的夫妻日常家事代理权》(《法学杂志》2011年第3期)。然亦有学者认为,上述通说显然没有认识到日常家事代理已经全然成为债权人保护规则的事实。日常家事代理原本目的主要在于保护妻子,债权人保护仅是其客观效果。而今其已经完全成为保护债权人的工具,因为其不考虑夫妻双方是否拥有足够的经济实力,而是直接将夫妻双方捆绑成强制性债务人共同体,成为“债权人的便车”。参见王战涛《日常家事代理之批判》(《法学家》2019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