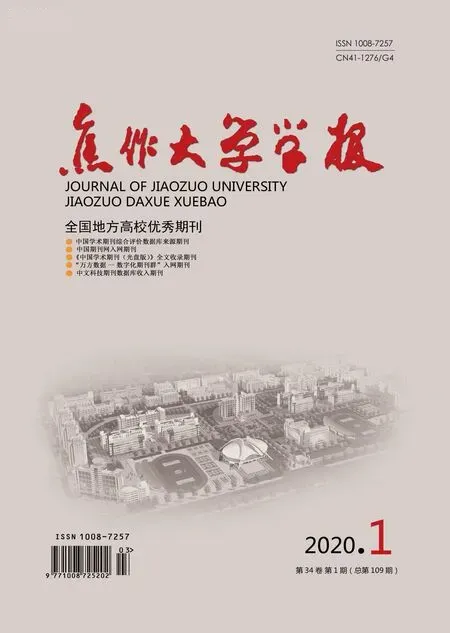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问题与路径
张艳庭
(山东师范大学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014)
新世纪以来,中国当代文学的生产取得了很多成绩,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每年出版的上千部的长篇小说,上万篇的中短篇小说,还有字数以亿计的网络文学支撑起了一个庞大的文本库。莫言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也成为中国当代文学成就的一个证明。但是,这些炫目的数字和奖项并没有掩饰当代社会审美体系中文学日渐边缘化的趋势和存在的诸多问题。文章试图就这些问题进行分析,并探讨相应的对策。
1.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问题
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并不是一个新的命题,而是长期以来诸多学者研究和热议的话题。学者吴义勤在《新世纪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现状与问题》一文中,就这一问题进行了深入的阐释。但总体而言,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进程虽然取得了一定的成果,但仍不容乐观,种种问题依然存在。由于人们对于经典含义理解的不同,对于经典产生过程中对历史和时间的过分依赖,厚古薄今的惯性思维,经典与异端的二元对峙等诸多障碍妨碍了当代文学经典化的历程。正如吴义勤所说:“无论是从汉语本身的成熟程度和文学性的实现程度来看,还是从当代作家的创造力来看,当代文学的成就都要远远超过了现代文学。现在的问题,不是中国当代文学没经典、没有大师,而是我们对于经典、大师不敢承认。”[1]虽然当代文学的经典价值今天逐渐得到了学界的认可,但当代文学经典化仍然是一个有待完成的重要问题。经典的命名、确认与完成,是一项长期的工作,有着漫长的路要走。要想实现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要突破时间和空间上的认知障碍,同时,还要突破经典与异端二元对峙的转化困境。
1.1 要突破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时间障碍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时间障碍,实际上是人们对时间上的认知障碍。在经典确立的问题上,在人们惯常思维里,总是有经典要经历时间考验的传统概念。这是对时间的一种绝对崇拜,时间在这种情况下,成为了价值的终极裁判。然而,时间并无法充当裁判。人们的时间崇拜反映了人们的历史观念。这种历史观念受黑格尔的历史哲学影响,认为历史是线性前进的,历史具有理性、具有目的、具有内在法则。许多问题需要交由时间来解决。如果说黑格尔的历史观是一种重未来而轻现在,那么中国人传统观念中的“厚古薄今”则是重过去而轻现在。中国有着悠久的历史,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诞生了众多的文学经典,这是人们厚古薄今观念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这种厚古薄今的传统,实际上也是一种时间崇拜,经典与时间长度有着直接的关系。诞生经典所需要的时间越久,这个经典也就越可靠。这与轻现在、重未来具有相似的思维逻辑:将一切交给时间。
而在克尔凯郭尔、尼采存在主义路向的历史观里,则直面各种生存性的问题, “人必须自己面对生活最根本的问题,而不能去依赖历史规律”[2]。对当代经典的确立,同样是生存性的问题之一,它意味着价值的确立,意味着当代人对自我价值进行定位的勇气。当黑格尔的历史态度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之际,对这种历史意识形态的打破就不仅需要学者的清醒意识和独立批判能力,同时,更重要的是对大众历史意识的扭转。当代文学经典化本身就是这种扭转过程的一部分,而在这个过程中,大众要更加意识到自己是经典生成中最重要的一环,而不仅仅是依靠几个学者对文学史的书写。只有这种时间认知障碍的消除,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才有可能。
1.2 要突破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空间障碍
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空间障碍,实际上是人们对空间上的认知障碍。中国自古有句谚语“外来的和尚会念经”,就是一种空间认知偏见,是对自己所属地理空间的不信任,认为其他地理空间超出自己所在地理空间。在中国现代文学经典化过程中的确有许多这样的案例。现代文学史上的许多经典作家,如沈从文、张爱玲等就是依靠夏志清等海外学者重新发现并确立其经典地位的。海外汉学对中国现代文学历史的改写,使许多遗漏的经典重新浮现。当时间抵达当代,在这个全球化的、地球已经变成平的时代,不同地理空间所承载的价值观念已不具有截然不同的属性。在这样一个时代,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不能依赖于中国之外的空间。当然,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进程中,中国之外的地理空间的确也起到了重要作用。国外奖项对中国作家作品的经典化进程起到了推动作用,如莫言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事实上,也正是自莫言获得诺奖之后,许多学者才开始确认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价值。但这种对他者的依赖,所彰显的正是主体的不自信。主体价值的确认首先应该依靠主体自身,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也不能单纯依靠国外的文学奖项和研究来确立,因为最熟悉和了解中国当代文学的, 正是中国人自己。正如吴义勤先生所言:“我觉得当代人、同时代人的命名更可靠, 更不可或缺。”[3]全球化进程已造成了思维方式中的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当下的中国并未和世界处于隔绝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异国的空间神话理应被去除,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化的空间阻碍才能被打破。
中国当代经典化的另一个空间认知障碍是对港澳台文学的他者化操作。他者的建立正是由于主体思维和眼光的存在。港台文学并未与大陆文学属于一个共同的文学谱系和评价标准,现有文学史总是在详述过中国大陆文学之后,又专辟章节对港台文学进行书写与论述,这是依据空间原则来书写的文学史。这种依据空间来划分的文学是对文学内在标准的背叛。只有将中国大陆的文学与港澳台文学置于共同的标准之下,放在一起来论述,才能保证文学研究的客观与独立,而不是政治学、地理学等学科的附庸,文学自身的主体性才能得到保障。
在这些有形的空间障碍之外,还有另一个空间认知障碍是对网络空间的认知。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网络空间已经成为一个重要的空间维度。虽然网络空间具有超空间的属性,但我们对网络空间的认知仍然延续了空间偏见。网络空间中生产的文学被命名为网络文学。现在网络空间已经不再是现实空间维度之外的一个他者,两者不断地相互渗透,网络文学也不能再是传统文学的他者。网络空间所产生文学本身拥有丰富的种类,但相关研究仍然滞后。网络空间文学的生产模式、价值模式与美学体系研究仍然不够。网络文学的他者化倾向很大程度上,其源头也在很大程度上是我们心中的空间偏见。去除这种空间偏见,网络空间文学的研究也才能步入正轨。
1.3 要突破经典与异端二元对峙的转化困境
由于语言的多义性特征,对一些词语意义的确认往往需要在相应语境中进行。许多时候,一个词语的特定语义需要靠其反义词来进行锚定。如果说在上述两个方面中,经典的反义词主要是平庸的话,那么经典的另一个反义词异端则在很多时候被有意无意忽略。事实上,异端与经典的语义对峙很多时候更加强烈。但正是这一强烈的二元对立也最容易发生相互转化。许多被某个时代的意识形态划定为异端的作品在经历意识形态变动之后,反而进入经典行列。如二十世纪当之无愧的经典《尤利西斯》刚在美国出版时曾被当作黄书查禁,成为当时的一大异端。经过一番曲折的进程,《尤利西斯》解禁,才逐渐从异端升入经典的殿堂。中国当代文学中也有许多这样的异端,其中许多有向经典转化的潜力。但这些异端书籍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完成这种转化,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相应的文学研究未能够给予足够的关注和研究。在这种情况下,文学研究者需要打破自己的意识形态偏见,从更宽泛和超越的思想视角来审视这些异端之作。如果说经典代表着一种全人类的精神财富,符合一种普世价值的规范,那么异端则包含着更多的意识形态色彩。“意识形态理论是马克思对异化的认识中一个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同时也是马克思主义对意识分析和文化分析最有独创性的贡献之一”[4]。在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之后,意识形态理论又继续发展,杰姆逊在《后现代主义与文化理论》一书中将之概括为“意识形态分析的七种模式”[5]。只有打破这些意识形态的束缚和障碍,经典的语意范围才能够涵盖异端,经典体系也才能够接纳这些异端之作。只有这样,经典才能真正具有其应有的位置和含义,经典的价值也才能够得到更多的认同,也只有这样,中国当代文学的经典化才能够真正完成。
2.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文学批评衰落的问题
勒内•韦勒克在《文学理论》中将文学研究分为三大块,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文学史”。文学批评是文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当代文学研究的活力所在,对文学史的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但新世纪以来,文学批评在整个文学研究中的地位不断降低,存在着诸多问题,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2.1 文学理论创新能力的衰弱
文学批评与文学理论的关系密切,后者是前者重要的精神资源。但新世纪以来,文学理论的供给逐渐减少,文学理论的创新更乏善可陈。这与改革开放后西方现代文艺理论的潮涌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法、荣格神话原型法、现象学方法、解释学等一大批文艺理论与方法涌入中国,极大繁荣了文学批评,促进了文学批评的发展。王岳川在《文艺方法论与本体论研究在中国》一书中,将文艺学方法论分为三个方面,即哲学—逻辑方法、一般批评模式、特殊研究方法。在论述哲学—逻辑方法时,他提到“吸收当代哲学的精神资源”[6]。事实上,在一般批评模式中,同样要借助各种哲学社会学理论。但对于各种理论的借用,不能是照搬理论来套作品。照搬理论来套作品,是文学批评中的一大顽疾,实际上也是一种理论创新能力衰弱的表现。要克服这种现象,不仅需要对文学作品有较高的领悟鉴赏能力,更需要有理论创新能力。只有这样,才能够摆脱理论与文本之间的绝缘,才能够将理论之模打破,使文学批评摆脱理论对文本规范的模式。
2.2 文学批评标准的混乱
二十世纪,形式主义理论家把文学性认定为文学研究的对象。虽然这种说法有将文学性与文学作品强行切割之嫌,但对文学性的强调依然有极大的意义,也是文学研究“向内转”的一个重要标志。新批评学派明确提出文学研究向内转之后,结构主义批评等流派将这种倾向进一步延伸。但文学研究的世界并没有一致地越来越窄,在经历了内转向之后,新历史主义批评、女性主义批评、文化研究等文艺理论流派和批评方法又把文学研究转向了外部研究。但这种转向不是像之前简单的复归,而是“在广泛地吸收了新的研究成果的螺旋式上升,有着复杂的社会文化语境变迁的历史因素”[7]。这种文化研究的转向也与哲学美学研究的转向密切相关。而中国当代文学创作与研究虽然滞后于这些文艺美学思潮,但大致能与这些文艺美学思潮相应。新时期文学时提出的“纯文学”概念,既是文学创作向内转的自觉追求,也是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标志。在纯文学的大旗之下,是先锋小说的崛起与风行,而在这之前,已有朦胧诗的风靡一时。先锋小说与朦胧诗对形式创新的迷恋与文学研究向内转的方向不谋而合,文学性成为衡量文学作品的唯一价值。但随着先锋小说对形式的穷极追求走上困境,先锋小说的没落,文学创作潮流从形式创新的胡同里走出,有了更多对社会、文化的思考。而作为新世纪的文学思潮“底层写作”,也带有更多社会学的背景。这一文学思潮与新时期文学中的“朦胧诗”“先锋小说”等文学思潮相较,有了更多社会学的意味。这个文学思潮诞生的背景,是以文学性为价值追求的纯文学衰落之后,文学研究向外转后的结果。但这种向外转,并不是吸收新研究成果后的“螺旋式上升”,而是文学研究内转向之前的社会、历史研究模式的简单复归。这种简单的复归,必然导致这个以底层文学来命名的文学思潮对文学性标准的背离。文学批评和研究放弃以文学性为首要标准之后,结果就是文学批评与研究成为其他学科如社会学等的附庸。因此,文学研究在拓展研究范畴和广度的时候,首先要保证对文学性的坚守,在吸收以往成果后进行螺旋式的上升。
2.3 文学批评主体性价值的失落
当下学院派批评文学批评主体性价值的失落是一个严重的问题。批评写作模式的僵化,语言的套路化,使批评缺少自足的价值,成为作家的轿夫和文学作品的附庸。文学批评自身主体性的确立,是有效解决这一问题的途径。文学批评在学术价值、思想价值之外,应该同样注重审美价值。在确保文学批评思想与学术价值的同时,增加文学批评语言的形象性,建立批评语言独特的美感,是文学批评主体性价值的有效途径。这不是一种增加文学批评可读性的权宜之计,而是文学批评的内在需求。后现代主义哲学家德里达对哲学、文学二元对立进行解构时指出:“哲学作品中并不仅仅是存在作为文学性象征的隐喻,用来帮助说明某些概念,相反,哲学本身是一门深深植根于隐喻的科学,假如把其中的隐喻或者说文学性清除出去, 哲学本身势将空空如也, 一无所剩。”[8]虽然德里达的论述有夸大之嫌,但仍不乏真知灼见。因为不管是哲学还是文学都是建立在语言的基础之上的,而隐喻是语言天然包含的一种属性。如果与哲学密切相关的文艺理论、文学批评试图把其中的隐喻或者文学性去除,那么它们的价值也会受损。增强文学批评中文学性语言的使用不仅不会妨碍文学批评的主体性价值,反而会增加文学批评的价值。
3.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史学化过程中当代文学研究的方向问题
学者郜元宝2017年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中的史学化趋势》中详细梳理了中国现当代文学学科的史学化转向。他指出现当代文学研究的三大块中,“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衰落,而独剩“文学史”研究一枝独秀。郜元宝在文中说:“总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现在基本就等于‘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研究’了。”[9]造成这种局面的因素有许多,文学理论与文学批评的衰落是不争的事实,但解决这种衰落需要从文学理论和文学批评自身上寻找原因和突破口,如果仅靠史学转向来赢得所谓的学术尊严,并不是好的办法。
文学史研究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文学研究“向外转”的趋势,对这一现象本身并不能简单地一味否定。在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史学研究如火如荼,取得诸多成果的同时,中国当代文学的史学研究显得滞后。面对这种情况,有些学者如程光炜教授就明确主张要“用现代文学的方式来研究当代文学史”,就是要像研究现代文学那样从历史维度平心静气重新检讨几代学人亲身经历的当代文学,“把批评的状态转型到 学术研究的状态当中, 渐渐形成一个研究当代文学史,而不是总是在那里写评论文章的风气”[10]。
当代文学的史学研究与现代文学的史学研究相比,的确不占优势。与现代文学史中的作家相比,当代作家许多都是专业作家,从事专门的创作活动,而现代作家往往与社会有较多的联系,也是社会活动家。对现代文学历史的研究,与现代社会历史的研究有更多的接壤之处,因此,史学价值似乎也就更大。但文学史的研究有本身的自足性,如果仅仅满足于与其他专门史的研究能够接壤,就不足以支撑文学史的独特价值。真正的文学史不仅仅是作品史,作家的社会活动史,更应是作家的心灵史。而后者的研究正是缺乏的,不管在现代史还是当代史中。因为这个向度的研究是困难的。这对研究者提出了挑战,而挑战正是文学研究不断向前发展进化的动力。
虽然中国当代文学研究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却有着巨大的潜力和可能。当代文学的研究者也在不断地寻找对应问题的策略与方法,并付之实施。中国当代文学的发展充满着无限的可能,这给研究者带来了挑战,需要研究者不断更新自己的理论储备,更新研究的思路与方法,不断地与当代文学一起前进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