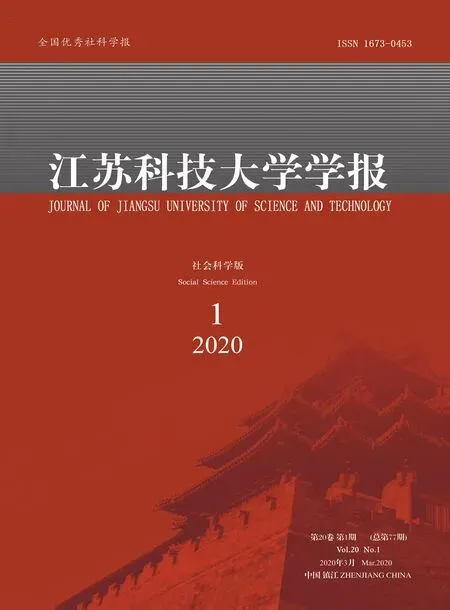黑格尔论伪善的三重形态
——兼与儒家乡愿比较
沈宝钢
(东南大学 人文学院, 江苏 南京 211189)
德国哲学家卡尔·西奥多·雅斯贝斯(Karl Theodor Jaspers)在《时代的精神状况》中写道:“人不仅生存着,而且知道自己生存着。他以充分的意识研究他的世界,并改变它以符合自己的目的……他不仅仅是尚存着的能知者,而且自己自由地决定什么将存在。人是精神,人之作为人的状况乃是一种精神状况。”[1]正如雅斯贝斯所说,人类不仅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存在。物质存在的直接表现就是肉体生命的持续,而精神存在则是通过反思、革新、创造等行为间接展现。另外,精神存在也使得人类可以自由地决定“如何去存在”。反观当下,以人工智能为代表的科学技术极大地改变了人类的生产生活。人类增强技术、基因编辑技术、人机交互技术等甚至有可能颠覆人类对生命的理解。与此同时,一系列现代“病症”也随之出现:佛系青年、犬儒主义、精神空虚、道德滑坡等。同样地,伪善作为一种常见而隐蔽的道德现象不应被忽视。两个世纪以前,晚年的黑格尔(G. W. F. Hegel)出版了著作《法哲学原理》。在其中第129-140节中,黑格尔对伪善问题进行了详尽研究。黑格尔从世界的终极目的“善”切入,展示了从善、义务、良心到伪善的逻辑进程,进而黑格尔剖析了伪善的三种形态:“盖然论”“抽象的善”与“讽刺”。
一、 伪善的生成逻辑
伪善是善的否定形式,因此在探析伪善问题前,黑格尔首先需要讨论善。何为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129节中开门见山地指出:“善就是被实现了的自由,世界的绝对最终目的。”[2]132黑格尔意指善是实现自由的开端。在抽象法、福利阶段,人的自由皆是潜在的,只有到善的阶段,自由才能实现。当然,善并不是抽象的、空洞的,而是有着丰富的规定性。善不仅包括自由的概念(自由精神),而且包括将自由呈现出来的定在(抽象法、福利)。因此,善“就是作为意志概念和特殊意志的统一的理念”[2]132。其中,理念是概念与其定在的统一。黑格尔认为:
首先,主观意志与善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一方面,对于主观意志而言,善是绝对至上的,主观意志只有服从于善,它才能够具有效力并且有价值;另一方面,对于善而言,没有落实到主观意志的善是抽象的,它必须通过主观意志的“中介”,才能得以落实。可以发现,黑格尔“善”与“主观意志”的关系类似于柏拉图“理念”与“物”的关系。物只有分有理念才可“成物”,理念也只有“成”于物中才有意义。另外,黑格尔认为,每个人的主观意志都是偶然的、任性的,只有当主观意志符合普遍性时,主体行为才可称为是善的。因此,普遍性对特殊性需要有所规定,即善对主观意志有所规定,这个规定便是义务。人作为具有自由意志的行为主体,必须通过履行义务获得普遍性,即实现善。
其次,既然“善之规定”是义务的“概念”,那么义务的“定在”又是什么呢?黑格尔说:“关于义务的规定,除了下述以外暂时还没有别的说法:行法之所是,并关怀福利——不仅自己的福利、而且普遍性质的福利,即他人的福利。”[2]136因此,对义务需要作更进一步的“特殊化”规定。原因在于,失去“特殊化”规定的义务(纯粹的抽象义务)是没有现实意义的。更严重的是,“履行抽象义务”会成为主观道德恶行的辩词。黑格尔认为,康德的道德哲学未能解决这一难题。康德提出“为义务而尽义务”,换句话说,即:当我在履行抽象义务时,不必考虑义务的客观内容,主观意志便可获得先验普遍性,即抽象义务本身便是指向善的。对此,黑格尔提出两点批评。
其一是形式主义。“固执单纯的道德观点而不使之向伦理的概念过渡,就会把这种收获贬低为空虚的形式主义,把道德科学贬低为关于为义务而尽义务的修辞或演讲。”[2]137黑格尔认为,若将抽象义务本身作为普遍原则,而不嵌入客观的经验内容,那么“固然导致对某种情况具有较具体的观念,但除了上述缺乏矛盾和形式的同一以外,其本身不包含任何其他原则”[2]137。举例而言,如果将“勿撒谎”作为义务,那么两军交战是否也应该对敌人保持诚实而将己方情况和盘托出呢?若按照康德绝对义务的理论,答案显然是肯定的,但这将导致现实情况十分危险。因此,黑格尔认为,“如果应该为义务而不是为某种内容而尽义务,这是形式的同一,正是这种形式的同一排斥一切内容和规定”[2]138。
其二是缺乏层次。黑格尔认为,“如果我们关于应该做什么已经具有确定的原则,那么,请考察你的处世格言是否可被提出作为普遍原则这一命题就很好”[2]138。黑格尔认为,在现实的、具体的情境下,主体承担的义务是多种多样、层次分明的。如上述之例,在两军交战中,既有“勿说谎”之义务,又有“赢得战争、保家卫国”的义务,那么当这两者发生矛盾或冲突时,到底是选择前者还是后者呢?由此可见,面对“道德两难”或“责任不相容”的现实问题,康德的理论是无法解决的。其原因是康德义务论并没有考虑到现实义务的复杂性、多元性与冲突性,因此必然会陷入“乌托邦”的理想境地。当然,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道德篇中并未讨论真实的义务到底是什么。直到伦理篇中,黑格尔才逐步指出,真实的义务只有落实到现实的伦理实体(家庭、市民社会、国家)中,才会获得客观的规定性。
此后,黑格尔发现,义务尽管是善落到实处的必要中介,但义务毕竟是外在于人的。因此,必须将外在义务上升为内心准则,将善的普遍性“移植”到人的主观意识中。于是,黑格尔援引了“良心”概念。黑格尔说:“由于善的抽象性状,所以理念的另一环节,即一般的特殊性,是属于主观性的,这一主观性当它达到了在自身中被反思着的普遍性时,就是它内部的绝对自我确信,是特殊性的设定者,规定者和决定者,也就是他的良心。”[2]139黑格尔认为,良心是作为世界最终目的——善的内化与特殊化,是人的主观法,是人的行动的唯一准则。外在的义务要求具有不确定性,但良心却始终“彻头彻尾地隐遁在自身之中”[2]139,要求人无条件地追求善。之后,黑格尔提出“真实的良心”一说,认为良心只有到达伦理阶段,才会获得客观规定性与固定的原则。在道德阶段,良心仅仅是形式的、抽象的且空洞的。善与恶在“道德良心”阶段是相对的,且良心取代了外在权威成为道德法庭的唯一判官。黑格尔以苏格拉底为例予以说明。当雅典的民主制度走向没落,苏格拉底固然可以在心中建立起正义、善的准则。但如果个体普遍地以内在的良心作为“在世”的唯一标准而“主观地”蔑视外在权威时,一方面,个体会把主观特殊性“抬升”为客观普遍性,造成主观的任意横行,正如每一个犯下恶行的人都可以说自己是从良心出发的;另一方面,社会有可能会陷入失序的混乱状态(由于自由意志的滥用)。正如阿兰·伍德(Allen W. Wood)所言:“良知不能避免自我崇拜的态度,再考虑到与之相伴随的欺骗和伪善的可能性,这就使良知十分接近道德邪恶。”[3]黑格尔认为,恶根源于意志的自由,而非人性。当意志追求主观的自我性而抛弃客观的普遍性时,恶便产生了。当人在反思的自我意识中把握到恶却仍然宣称自己的行为是善时,伪善便产生了。
综上所述,黑格尔完成了从善(世界的终极目的)到伪善(恶加上虚伪的形式)的完整逻辑进程。人类必须打破伪善,在现实的伦理世界与伦理生活中建构真实的良心,并履行良心的客观内容——义务,以此实现人的自由(善)。
二、 伪善的三重形态
黑格尔认为,“恶以及出于恶的意识的行为,还不是伪善。伪善须再加上虚伪的形式的规定,即首先对他人把恶主张为善,把自己在外表上一般地装成好像是善的、好心肠的、虔诚的等等”[2]148。现在的问题是,行为主体如何“伪”?即如何为自己恶的意图找到借口或辩词,甚至改头换面为善的意图?据此,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第140节中依次提出伪善的三重形态。
(一) 第一重形态:“盖然论”
第一重伪善形态是“盖然论”,即当行为人主观地采用某一权威的观点为自己恶的意图进行辩护,就可以使自己心安理得,甚至颠倒黑白。何为“盖然论”?顾名思义,理论皆具有盖然性(有可能但不是必然的)。伪善者宣称,在对某一行为进行善恶评价时,具有多种客观理由。这些理由可能是相辅的,也可能是相悖的。因此,在决定选择哪一种理由时应当完全依据人的主观性。黑格尔说:“只要行为人能替某种行为找到任何一种好的理由,无论这种理由只是某一神学家的权威,而且行为人也知道其他神学家对这一权威的判断在意见上有极大分歧,这种行为就是许可的,行为人也可感到心安理得。”[2]148意思是,如果行为人在为自己的恶的意图作“辩护”时,仅仅主观地采用某一有利于自己的理由(即使这个理由是盖然的)而忽略其他理由,那么伪善便产生了。于是问题来了。为什么人们不能用特定权威理论为恶的意识作“完全辩护”呢?理由有两点。
其一,与其说人们是信奉某一权威的理论,不如说是利用某一权威的理论。因为当人们的行为意图遭到质疑时,人们才会“拿来主义”地用某一利于自己的权威理论作辩护,而全然不管其他理论,以此获得一种主观上的“心安理得”。
其二,如果仅仅用利于自己的理由为行为意图作辩护,那么理由本身的正误善恶便显得不重要了。因为善的动机可以被说成恶,恶的动机也可被说成善。当一切动机全由人用“特定”的理论进行“任意”解释时,客观的善恶之分便不复存在。
那么,“盖然论”的伪善为什么会出现呢?黑格尔对此并没有分析。笔者认为,权威崇拜的心理导致了该伪善形态的生成。伪善者认为,自己的“恶性”动机可以通过“择取”某一权威理论进行“洗白”甚至改头换面为“行善”。这种想法是幼稚可笑的。其原因有两点。
其一,不管多么权威的理论,都有其适用的具体范围,都要受到历史背景、社会氛围、现实情况等多方面的影响。因此,如果仅仅凌空蹈虚地生搬硬套某种抽象理论来增加自己具体而现实的行为意图的“合法性”,这显然是荒谬的。
其二,如果某人在行为本身未定性前先假定行为本身就是善的,再企图搜索枯肠地用某一理论予以附会,这显然是前后颠倒的。我们需要在确定适宜的评价标准后再对行为进行具体而有效的定性。因此,上述附会行为是不合理的。
综上所述,“盖然论”是一种低级的、容易被识破的伪善,原因在于,它将伪善之可能完全寄托于外在理由,而这一伪善的根源则在于将或然性的权威理论作为判断行为意图善恶的必然性标准。
(二) 第二重形态:“抽象的善”
在论述伪善的第一重形态——“盖然论”之后,黑格尔随即提出伪善的第二重形态——“抽象的善”。黑格尔认为,“善的意志在于希求为善,对抽象的善的这种希求似乎已经足够——甚至是唯一要求——使行为成为善的”[2]149。即,如果行为人将自己的行为意图强行归结为善,且不管客观的行为内容,那么这样的行为便是伪善。在这种情境下,意图之善仅仅是抽象之善,缺乏客观内容或规定性。若人们可以任意地将内容“装入”抽象之善中,同理,人们也可以将内容“装入”抽象之恶中,那么善恶之分便被悄然模糊了。对此,黑格尔举出大量的例子。如,“为了赈济穷人而盗窃,为了对自己的生命和家庭(或许是可怜的家庭)尽其应尽的义务而盗窃和临阵脱逃,出于憎恨和复仇而杀人”[2]150。但是,问题又来了。若所有的盗窃行为都可以解释为“劫富济贫”,所有的临阵脱逃都可以解释为“敬老爱幼”,所有的杀人都可以解释为“报仇雪恨”,那么世界上就再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恶人了。当所有的恶行都可以解释为出于善的意图时,善本身便是无意义的、空洞的、抽象的。如果抽象的善的意图可以与任何行为结果(不管善恶)相联系,那么善恶的区别便消失了。由此,黑格尔牵引出一个著名命题——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如果这一命题成立,上述“抽象的善”的伪善便是真善。因此,黑格尔必须对其正面回应。黑格尔认为,上述命题不仅犯了同语反复的毛病(上述命题可以转述为“目的正当,手段也就正当”。但是,手段本身是虚无的,只有呈现为具体目的之中才有意义)。另外,服务于任何目的的手段都要“服从更高的目的,被降到次要地位,而成为手段”[2]152。举例来讲,帮助穷人是善的目的,但服从国家的法律是更高的目的,因此行为人不能为了帮助好人(善意)而做出违背法律的事情(比如偷盗富人的财产)。由此,黑格尔认为,在判断某一行为时,不能仅仅以行为人的意图和信念为标准。“无论如何,有一个绝对的要求,即任何人不得从事罪恶和犯罪的行为,人既然是人而不是禽兽,这种行为就必须作为罪恶或罪行而归责于他。”[2]153黑格尔识破了伪善的第二重形态——“抽象的善”。这种伪善形态比“盖然论”具有更大的迷惑性。原因在于,在这种伪善中,行为人是在主观内部为其恶的行为意图作掩饰,而非求助于外部权威理论。但是,行为人犯的错误在于企图用善的目的(或者信念)消解恶的手段(或恶的结果)所造成的毁损。
那么,这种伪善形态为什么会出现?黑格尔对此并没有分析。笔者认为,“不知善恶”的心理导致了该伪善形态的生成。对此,需要明晰“不知”概念。“不知”就是“不去知”,这不同于“不能知”。《孟子·梁惠王上》曰:“挟太山以超北海,语人曰:‘我不能。’是诚不能也。为长者折枝语人曰:‘我不能。’是不为也,非不能也。”[4]15对孟子“不能”与“不为”的区分关键有两点:第一,有没有实现的可能;第二,想不想去实现。借鉴孟子的观点,“不能知”善恶指的是“无法知道善恶之分的混沌状态”,而“不知”善恶指的是“知晓善恶之分却不予顾及的状态”。举例来讲,婴儿并不知道拿别人的东西是偷窃行为,因为他并没有你我之分,更不知道私有财产不可侵犯的道理。因此,他们的抓取行为只是属于“不能知”善恶的行为。换言之,在没有善恶之分时,在外在道德教化与内在先验良知未互融成主体德性时,婴儿的行为属于出自本能的“非道德行为”。对此,人们一般采取原谅的态度。反之,若一个身心健全的成年人拿取别人的东西,人们一般采取谴责的态度,因为成年人当然知道自己的行为是偷窃行为(即他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违法的)。但是,若他不以为然,依然将自己“偷窃他人财产”的目的解释为“劫富济贫”,那么这样的行为便属于“不知”善恶的伪善了。另外,这种伪装自己恶的意图的伪善本身并不能改变行为之恶。因为上述成年人已有善恶之分,暂不论他的目的是否是“劫富济贫”,单凭他始终是把自己的个别性的意图(偷窃他人财产)凌驾于普遍性的社会规范(不可侵犯他人私有财产)之上,那么这种行为本身已是恶的。由此可见,“不知”善恶是指行为主体在知晓“何为善、何为恶”的前提下对客观的“善恶之分”不以为然,将自己的主观目的“任意”解释为“善”时所呈现的心理状态。综上所述,“抽象的善”是一种较为高级的伪善。这一伪善形态的根源在于将行为动机主观地解释为“希求为善”,借以使得行为本身似乎是善的。
(三) 第三重形态:“讽刺”
在黑格尔看来,伪善的最高形态是讽刺。讽刺原是柏拉图用来描述苏格拉底反对人的一种谈话方式,即通过不断询问与诘难,使对方不断地暴露立场与动摇立场,并最终陷入两难窘境。而黑格尔将讽刺看作主观性的顶峰——“信仰”的诡辩。黑格尔认为,“如果,自我意识对着他人号称自己的行为是善的,那末这种主观性的形式是伪善。但是,如果它竟主张它的行为本身是善的,那末这是自命为绝对者的那种最高峰的主观性。对这种主观性来说,什么绝对的善和绝对的恶都消失了,它就可随心所欲,装成各种样子。这正是绝对诡辩的观念,这种诡辩俨然以立法者自居,并根据其任性来区别善恶”[2]158-159。黑格尔认为,当行为人把主观信念作为行为标准时,就不存在善恶之分了(因为对于“信念”,只有信与不信,并不关乎是非善恶)。黑格尔将此行为称为最高形式的伪善。这种伪善与上述“抽象的善”有相似之处,亦有巨大差异。相似之处在于,两种伪善形态都试图将行为意图解释为“善”的;区别之处在于,上述“抽象的善”只是强调行为意图或行为动机是善的,而这里“信仰的诡辩”不仅认为自己的行为意图是善的,还企图将行为本身也称为善的。这时,为了完成这一目的,行为人必须“援引”一个绝对者或一条绝对规律。但行为者的信仰并不是基督教似的信仰,而是“形式上的忠诚”。这种信仰并不是真诚的,而是虚伪的。对此,黑格尔批判道:“这种绝对权威的口头禅就是假借我主基督的名字,并武断地说,主居住在这些裁判官内心里。基督说(《马太福音》7、20):‘汝须凭他们的果实去认识他们’,像这种夸大的侮慢的定罪与判决,却并不是好的果实。他继续说道:‘并不是所有向我叫主呀主呀的人都可以进到天国。在那一天有许多人将向我说:主呀主呀,我们不是曾用你的名字宣道吗?我们不是曾用你的名字驱走魔鬼吗?我们不是曾用你的名字作过许多奇迹吗?我必须明白告诉你们:我还不认识你们,全离开我吧,你们这些作恶的人!’”[5]黑格尔的意思是,行为者的意图与其说是出于上帝的名义,还不如说是出于自己“理解”的(或“伪造”的)上帝的名义。由此,黑格尔认为,若行为人借助信仰的名义将自己的主观意识任意抬升为评判善恶的标准,以自我准则代替客观法则,那么这种行为便是“彻头彻尾的普遍的恶”[2]158。“事实上,如果我不能认识真理,则我之所谓确信是极其无聊而卑不足道的。”[2]155不妨以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所提到的答尔丢夫(Tartuffe)为例说明。在法国戏剧家莫里哀的喜剧《伪君子》中,宗教骗子答尔丢夫深受大家庭之主奥尔贡的信任。奥尔贡不仅想要招答尔丢夫为女婿,还取消了儿子的财产继承权,想把万贯家财全部拱手送给答尔丢夫。从奥尔贡与答尔丢夫的多次对话中可以发现,答尔丢夫多次将自己的主观动机解释为“一切都是上帝的旨意,应该遵从”[6]。由此可见,答尔丢夫借助自己的“信仰”随意“解释”主观意图。这种“信仰”的本质并不是“为了上帝”,而是“为了自己的欲望”。显然,答尔丢夫的行为是一种伪善,是一种信仰的诡辩。上述答尔丢夫的伪善不仅是伤害奥尔贡的欺瞒行为,更是对纯洁的基督教信仰的蔑视。
综上所述,讽刺形态是一种最高级的伪善。这一伪善可以看作是前两种伪善形态的综合。原因在于,“盖然论”是通过“外在理由”(权威理论)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善的,“抽象的善”是通过“主观任意”将自己的行为动机解释为善的,而讽刺形态则是通过主观、随意地“构造”利于自己的“外在理由”,以此证明自己的内在动机是善的。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完成了对伪善三重形态的披露。应该说,黑格尔的分析是严密完整、鞭辟入里的。伪善作为一种伪装为善的恶,它的道德哲学真相在于表面为善、实则为恶。因此,其生成的根源无非有两点:主观意图和客观理由。“盖然论”抓住了客观理由,即行为意图可以有多种理由的支撑。因此,行为人企图用权威理论将自己的恶意伪装为善意。“抽象的善”抓住了主观动机,即人们无法准确地知晓他者的行为意图或动机(这些属于人的主观心理范畴),因此行为者企图主观地将恶意伪装为善意。讽刺形态则是上述两者的综合,它既抓住了客观理由,又抓住了主观动机。一方面,行为者主观地构造了一个绝对者(如答尔丢夫构造了一个“仅服务于自己”的上帝);另一方面,行为者以此为依托将恶意伪装为善意。综上所述,伪善的本质是一种恶。这种恶由于戴上了善的面具,因此具有极大的隐蔽性。
三、 伪善与儒家乡愿的对比
不难发现,儒家所阐发的乡愿与黑格尔的伪善有诸多相似之处,对此不应回避,也无法回避。正如杜维明教授所指出的,21世纪需要打破“文明冲突”的“轴心时代”,进入“文明对话”的“新轴心时代”[7]。中西方文明只有在相互尊重、相互理解、求同存异的前提下才可能拓展,进而加深对彼此的理解。乡愿由孔子最先提出:“乡愿,德之贼也。”(《论语·阳货》)[8]186但是,孔子对此并未作进一步阐发,故孟子加以详细解释:
孔子曰:“过我门而不入我室,我不憾焉者,其惟乡原乎!乡原,德之贼也。”曰:“何如斯可谓之乡原矣?”曰:“何以是嘐嘐也?言不顾行,行不顾言,则曰古之人!古之人!行何为踽踽凉凉?生斯世也,为斯世也,善斯可矣。阉然媚于世也者,是乡原也。”万章曰:“一乡皆称原人焉,无所往而不为原人,孔子以为德之贼,何哉?”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乎流俗,合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悦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曰‘德之贼’也。”(《孟子·尽心下》)[4]341
孟子以孔子私淑弟子自居,应当说他的解释是详尽且中肯的。与乡愿相对的是狂者与狷者,狂者是志大而言夸但实际行动却跟不上的那一群人;而狷者是有所为有所不为、不屑于做坏事的那一群人。尽管狂狷之士都不能奉行中道,偏于一隅,但他们的处世态度是真诚、不作伪的。相反的是,乡愿是指那些表面忠厚老实、方正廉洁,且八面玲珑、不得罪他人,但背地里却逆行倒施、悖道违义的好好先生。对此,朱熹讥讽道:“狂狷是个有骨肋底人。乡原是个无骨肋底人,东倒西擂,东边去取奉人,西边去周全人,看人眉头眼尾,周遮掩蔽,惟恐伤触了人。”(《朱子语类·卷六十一》)[9]正如《论语》中出现的微生高。他自己没有醋,但当别人向他借醋时,他却向邻居借醋给别人,让自己做“老好人”。因此,孔子责怪道:“孰谓微生高直?或乞醢焉,乞诸其邻而与之。”(《论语·公冶长》)[8]51朱熹注道:“人来乞时,其家无有,故乞诸邻家以与之。夫子言此,讥其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不得为直也。”(《四书章句集注·论语集注·卷三》)[10]114何为“曲意殉物”?就是委曲己意、奉承别人,只为求得分毫利益哪怕因此而丧生;何为“掠美市恩”?就是掠夺他人的东西来为自己做人情。可以看到,孔孟对乡愿的批判只是“乱德”,即败坏道德。但是,朱熹则一下子抓住了乡愿为何要如此这般的心理动机,而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可以成为晚明东林学派批判乡愿的思想资源。东林学派对乡愿的批判不遗余力,甚至直接将其贬责为“全坏心术者”(《明儒学案·卷五十九》)[11]1436。他们深刻地揭示了乡愿对于是非善恶的模糊心态,如,邹元标曰,“乡愿一副精神,只在媚世,东也好,西也好,全在毁誉是非之中”(《明儒学案·卷二十三》)[11]545;顾宪成曰,“乡愿何以为无善无恶也?曰:其于流俗污世不为倡而为从也,即欲名之恶而不得也。其于忠信廉洁不为真而为似也,即欲名之善而不得也。是谓无善无恶”。(1)参见顾宪成《顾端文公遗书·证性编·卷三 罪言上》,泾里顾氏宗祠,清光绪三年(1877)。
笔者认为,儒家之乡愿接近于黑格尔的“抽象的善”。也就是说,乡愿不管自身行为的内容如何而始终将自己的动机定性为善。换言之,乡愿并不认为自己是伪的,而是“自以为‘是’”。何以如此?有两种可能:一是外在原因,如朱熹所言的“恐伤触了人”“曲意殉物”“掠美市恩”;二是内在原因,或许乡愿也觉得自己是善的,毕竟“众皆悦之”,即外在善意的反馈让乡愿沉浸于自我欺骗之中。对此,邓晓芒教授进一步分析道,儒家的乡愿之所以出现,是因为儒家并没有或者不敢对自己的内性进行反省,而是坚信只要持守本性、反身而诚,就有成圣成贤之可能。曾子的“三省吾身”也只是对自己是否偏离本性进行反省,而并不是对本性本身进行反省。另外,荀子强调“化性起伪”,不仅不对人之本性进行反省,还进一步强调要人为地改造、修饰本性。邓晓芒教授将儒家学说看作人格结构中的伪善虽然辛辣苦口,却实为洞见。当乡愿以“诚”为人处世之时,殊不知这样的“诚”只是他自己造就出来的“心理围城”罢了。当然儒家本意上并非想造就伪善。诚如邓晓芒教授所言:“儒家学说并不是故意伪善,要做乡愿之徒。主观上是排斥伪善,但是客观效果我们就没有想到。但上面说到的思维定势本身就是伪善,这种人格结构本身是一种结构性的伪善,是在人格结构中的伪善。不是指具体的人。”[12]
综而言之,黑格尔的伪善与儒家的乡愿都直面了一种常见的但很隐晦的道德现象。两者的相似点在于都侧重于分析伪善者行为动机之“伪”(伪装为善),而对伪善者行为结果的善恶均略显忽视。与此同时,两者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黑格尔的三重形态理性地分析了伪善者如何“伪”,即伪善者的手段或伎俩。黑格尔得出的结论是“伪”可能来自外在原因(“盖然论”)、内在原因(“抽象的善”)以及两者的合一(“讽刺”)。可见,黑格尔的贡献在于发现了伪善的潜藏性,可以帮助我们鉴别生活中的伪善。儒家的乡愿则主要集中于经验地分析伪善者对于社会风气的破坏性,其原因在于儒家有着强烈的社会忧患意识与时代使命感,他们深刻地看到了以乡愿为代表的“好好先生”对于社会道德生活与道德氛围的破坏性,即“恐其乱德也”。其原因是儒家将道德领域与政治领域直接挂钩,或者说儒家所倡导的是“伦理型政治”,人的道德品性与社会的道德氛围直接决定了国家兴衰与民生日用,即“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孟子·离娄上》)[4]167。因此,孟子才不无忧患地说:“王曰‘何以利吾国’?大夫曰‘何以利吾家’?士庶人曰‘何以利吾身’?上下交征利而国危矣。”(《孟子·梁惠王上》)[4]1在今天,伪善作为生活中一种潜藏的道德现象,对此需要借鉴黑格尔的理性分析加以甄别。另外,儒家的乡愿也警示人们,伪善可能会成为时代的“道德流感”,即伪善者可能将这种错误的道德观“传染”给他人,从而形成不好的示范效应,破坏社会的道德氛围与良善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