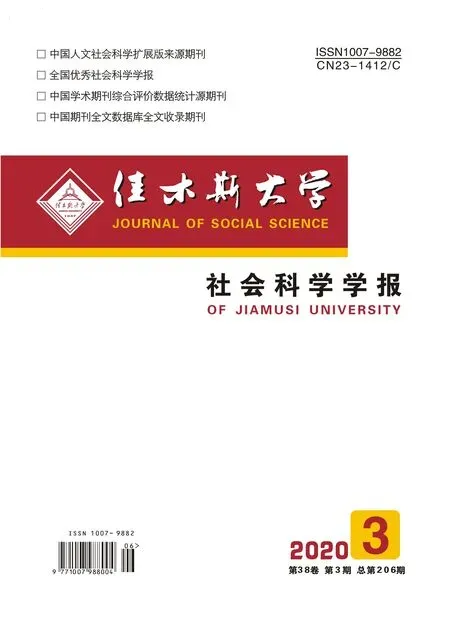魏晋玄学对阮籍文学创作风格影响研究*
韩姝婷
(黑龙江工程学院 人文与社会科学系,黑龙江 哈尔滨150000)
一、魏晋玄学的产生与发展
汉末的党锢之祸,使大一统政权最终走向崩溃。原来自董仲舒以来的儒家思想已经很难对社会起维系作用,于是“罢黜”的百家思想又活跃起来。正始年间,曹魏集团与司马集团争权越来越激烈,高平陵事变之后,依附曹爽的文士几乎全被杀害,此后司马氏取得政权。“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1]。士人们就是在这种大混乱中艰难的生存。正统的儒家信仰在此刻发生严重危及,一批知识精英跳出传统的思维方式,对宇宙、社会、人生进行反思,一种新的崇尚老庄、调和儒道的哲学——玄学应运而生。其中道家占主导地位,融合了儒家学说,可以说是道家之学的新形式,所以也称新道家。名教与自然的关系问题,是魏晋玄学贯穿不变的核心议题。名教是指封建的等级名分和道德规范,也可以理解为通过上定名分来教化天下。自然是指所谓人的本初状态或自然本性,同时也指天地万物的自然状态。
魏晋玄学的发展主要分为第一个阶段以王弼为主要代表人物。这时期是玄学的初始阶段,人们认为,整个世界“以无为本”、“以有为末”,认为“无”是世界的本体,“有”是各种具体的存在物,是本体“无”的表现。崇尚老子“无为而治”的观点,认为治理国家应该以道家的自然无为为本,以儒家的名教为末。第二阶段是以阮籍为主要代表人物。他们从道家自然无为思想出发,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的主张。同时他们又都对庄子隐士逍遥的思想非常的欣赏,并以消极的方式拒绝与司马氏政权合作,表现出一种放荡不羁的人生观。第三阶段以郭象为代表人物。其玄学思想主张为名教即自然的儒道合一说,认为逍遥世外与从事名教世务是一回事,因此逍遥游并不要遁世。第四阶段以僧肇为代表人物,核心思想是“万物是亦有亦无,有无双遣而并存的”[2]。
二、魏晋玄学对阮籍《咏怀诗》创作风格影响
在玄学思潮的影响下,名士们以率性旷达的言行引领着时代风尚。从竹林、金谷到兰亭,魏晋名士用自己的一言一行,实践着人生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性。如日本诗人大沼枕山的诗句所言“一种风流吾最爱,魏晋人物晚唐诗”。与汉朝的敦实厚重、三国的慷慨激昂、唐朝的盛世长歌、宋朝的清丽婉约不同,魏晋人物以率性不羁、旷达玄远著称。这是当时整个社会的精神时尚和审美追求。即不讲具体的道理和事物,而是追求精神上、人格上的玄远。儒家贵名教,道家重自然,玄学的特征就表现为,对儒道两家学说改造基础上而建立起关于“自然和名教”的关系之辨。
阮籍,字嗣宗,因曾做过步兵校尉,后世又称他为阮步兵。阮籍作为玄学思潮的代表人物,他才华横溢,但身处政治黑暗的年代,抱负难以实现,内心异常苦闷。在司马氏和曹魏之间,阮籍选择了一条中间道路,他一方面巧妙地和司马氏周旋,不敢明显地顶撞,另一方面又用嬉笑怒骂、利落锋利的笔调讽刺司马氏的阴险与虚伪。在思想上,阮籍是推崇道家学说的,他反对统治者利用儒家的礼教来压迫下层民众。阮籍一生从来没有放弃过对自由的追求。在他的理想中,只有内心超越时间和空间的限制,精神才能得到彻底的解脱,拥有绝对的自由。他给后世留下两笔遗产:一是他的处事方式,二是八十二首立意隐晦的《咏怀诗》。这些诗歌均收录在黄节先生所编著的《阮步兵咏怀诗注》。历来对阮籍的评价中尤以钟嵘的说法更为确切和到位。钟嵘说“厥旨渊放,归趣难求。颜延年注,怯言其志。”阮籍作为一位哲学家和文学家,他能够将自己的哲学思想和文学创作有机的结合起来,使其作品呈现出魏晋玄学的玄远和文学情感的浓烈统一,由此发散出独特魅力[3]。
钟嵘《诗品》中对阮籍做出的评价十分精炼的概括了阮籍五言《咏怀》的风格:“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无雕虫之功。”从以上的评价中我们可以看到,阮籍的诗歌多数发忧愤之气,颇似《诗经·小雅》的特点,因此我们可以说将阮籍五言《咏怀诗》的总体风格概括为:
(一)悲慨忧愤
感情是悲慨忧愤的,而语言却少雕饰,尽管阮籍的诗歌中有很多的花鸟草树的名目繁多的物象,然而这绝非是诗人在卖弄文笔,堆砌辞藻,实在是为表达的需要才出现的,和后世文人为装饰而故意雕饰的出发点和效果是绝对不同的,诗人满腹的郁愤,唯有通过诗歌才能得以疏解,所以没有修饰的必要和闲心。虽然语言质朴,字面的意思很容易理解,但诗歌表现的题旨则因为社会环境的原因而令人“归趣难求”,出现了言近旨远的特征。题旨不清,却引来众多的共鸣,千载之下仍吸引人,这和诗歌表现出的深远宏放的总体风格是分不开的,正如钟嵘的评价:“可以陶性灵,发幽思”、“使人忘其鄙近,自致远大”。悲慨忧愤,指的是诗中反映的感情。尽管诗人为远身避祸,而“口不臧否人物”,但在诗中真实的感情还是不可抑制。悲,人生的理想不能实现;慨,慨叹时光的流逝,世事的险恶;忧,国家的前途,自身的安危;愤,对曹魏政权不思进取的愤恨,对司马氏大肆杀戮的痛愤。诸种感情构成了丰满而鲜活的诗人,此种风格,正是玄学的人生态度在阮籍身上的一种特殊表现。他有一个庄子式的人生境界,却又面对着险恶的政治环境,注定了他浮诞玩世的一生。
(二)自然质朴
阮籍咏怀诗的自然质朴,并非仅指诗歌外在语言文字的质朴,而是指作诗的目的性上,阮籍的诗歌创作没有任何功利的目的,没有想通过诗歌来成就什么,他仅仅把诗歌当作是宣泄感情的唯一出口,在诗中喜悲,在诗中忧乐,诗是他的一切,他的一切“自然”乃道家思想之根本。老子云:“道法自然。”即自身不受外在的规约和引导,回归到一种淳朴天真的原始生存情态,齐同生死,无知无欲,适性自得,去追求一种精神的超脱。他所追求的正是庄子世事无所系念于心,返回自我的自然本真的人生境界。老庄之中所蕴含的自然适性之哲理也悄然进入诗歌。他想超脱于世俗,追求道家素朴的自然思想: “脩涂驰轩车,长川载轻舟。性命岂自然,势路由所有。高名令志惑,重利使心忧。亲昵怀反侧,骨肉还相雠。更希毁珠玉,可用登遨游。”(《咏怀诗 八十二首》之七十二)这种实实在在的不受约束、任情而行、悠游从容、淡薄朴野的生活的氛围,让人体会到返归自然、心与道合的美好。
(三)追求自由
庄子对个体精神自由的强烈追求对阮籍具有深远的影响。从阮籍的生活方式和人格境界上都充分地展现了庄子哲学的逍遥游精神。(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之二十三)诗人借用《庄子·逍遥游》中藐姑射之山神人的故事,营造了一个平和安谧的神仙境界。这是一种虚幻的仙境,是现实中没有的。《庄子·逍遥游》中是:“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不食五谷,吸风引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庄子描述了居于“姑射之山”上的“神人”即是得道高人,她以求与天地同在,与万物一体,而不肯苦心经营,以天下为事,故而“游乎四海之外”。这种自由不存在于现实的实践活动中,只能存在于内心之体验。罗宗强先生在《玄学与魏晋士人心态》中所说:“与其说是一种人生境界, 不如说是一种纯哲理的境界。这种境界,并不具备实践的品格,在生活中是很难实现的。若果真的进入这种境界,便会有如梦如幻之感。”[4]那么这个游心之自由逍遥就完全是精神的,是超越人间的。正所谓“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阮籍“陶性灵, 发幽思”的哲理的启迪也正是来自于他诗歌中的仙游:
“混元生两仪,四象运衡玑。曒日布炎精,素月垂景辉。晷度有昭回,哀哉人命微。飘若风尘逝,忽若庆云晞。脩龄适余愿,光宠非己威。安期步天路,松子与世违。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嗟哉尼父志,何为居九夷。”(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之四十)。“昔有神仙者,羡门及松乔。噏习九阳间,升遐叽云霄。人生乐长久,百年自言辽。白日陨隅谷,一夕不再朝。岂若遗世物,登明遂飘飖。”(阮籍《咏怀诗八十二首》之八十一)
这两首诗在对自然宇宙亘古久存、流动不居和人生“人命微”的对比哀叹中,表现了诗人“焉得凌霄翼,飘飖登云湄”,对神仙世界的渴望和期盼,流露出浓郁的超世游仙的情调。在阮籍咏怀诗中反复描绘这种境界:“天地解兮六合开,星辰霄兮日月隤,我腾而上将何怀?衣弗袭而服美,佩弗饰而自章,上下徘徊兮谁识吾常。遂去而遐浮,肆云轝,兴气盖,徜徉回翔兮漭瀁之外。”“必超世而绝群,遗俗而独往,登乎太始之前,览乎忽漠之初,虑周流于无外,志浩荡而自舒,飘飖于四运,翻翱翔乎八隅。”阮诗中的玄远境界,是纯抽象、纯哲理性的。他缺乏对理想境界笃信的热忱,时常感到它的渺不可追。但是他们的最终目标都是要获得一种无差别的精神境界,追求自我的解脱和自由。正如汤用彤先生在《魏晋玄学论稿》中所说:“魏晋人生观之新型,其期望在超世之理想,其向往为精神之境界,其追求者为玄远之绝对,而遗资生之相对。从哲理上说,所在意欲探求玄远之世界,脱离尘世之苦海,探得生存之奥秘。”[5]阮籍为了躲避祸难,不敢直指所抨击的人或事,因而采用玄学的思维方式融入其创作。如《咏怀八十二首》其一:“夜中不能寐,起坐弹鸣琴。徘徊将何见,忧思独伤心。”所写都是眼前见到的景象,却传达出诗人内心无比的苦闷、孤独!正是玄学思想的渗透,才能如此自如的运用语言,让身边的事物抒情,正是诗人的高妙之处,使诗歌最终体现出别样的风格特征[6]。
三、魏晋玄学对阮籍《大人先生传》创作影响
竹林时期的玄学家有着两个不同的走向,以阮籍为代表,诗人认为人类社会本来应和“自然”一样,是一个有序的和谐整体,但是后来的政治破坏了应有的秩序,扰乱了和谐,违背了“自然”的常态,造成了“名教”与“自然”的对立。因此,阮籍在《大人先生传》中对现实社会政治的批判非常深刻,他说:你们这些人呀,争夺高高的位置,夸耀自己的才能,用权势凌驾在别人上面,高贵了还要更加高贵,把天下国家作为争夺的对象,这样哪能不上下互相残害呢?你们把天下的东西都据为己有,供给你们无穷贪欲的要求,这哪里能养育老百姓呢?你们这些伪君子所提倡的礼法,实际上是残害天下的、使社会混乱的、国破家亡的东西,可是你们反而把它看成是美德善行不可改变的法规,着难道不太过分了吗?
照阮籍看,这样的社会政治当然是和有序和谐的“自然”相矛盾,因此他在“崇尚自然”的同时,对“名教”颇多批判。在他看来,所谓“名教”,是有违“天地之本”、“万物之性”的,“故知仁义务于理伪,非养直之要术,廉让生于争夺,非自然之所出也”(《难自然好学论》)。这种人为的“名教”只会伤害人的本性,败坏人们的德行,破坏人与人之间自然的和谐关系。由此,阮籍提出了“越名教而任自然”、“非汤武而薄周孔”,并说“老子、庄周是吾师也”。这样一种思想潮流。从当时哲学思想的发展看,走到“越名教而任自然”的境地是逻辑发展的趋势在一定条件下的现实表现。这个“一定条件”是阮籍所处当时社会风气的败坏和他们自身的种种遭遇以及性格所导致。
四、结语
本文从魏晋玄学的角度来分析阮籍文学创作,主要原因就是诗歌、散文之中抒写的个人情感和认识都是在其玄学思想的影响下产生的。由于阮籍意识到自身的价值不能在现实中实施的矛盾和苦闷。犹如阮籍自己坦言:“终身履薄冰,谁知我心焦。”所以才有钟嵘说 “厥旨渊放,归趣难求。”这种影响直体现在诗歌创作风格中。阮籍的诗歌中朦胧化抒情特点、丰富的想象空间,以及悲慨忧愤、自然质朴、追求自由的创作风格[7]。使我们相信《咏怀诗》《大人先生传》是诗人自我情感的吟咏和抒发。本文试探讨在魏晋玄学的观照下,阮籍文学创作风格特点,以期对阮籍的文学研究有所贡献。
——王弼名教思想探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