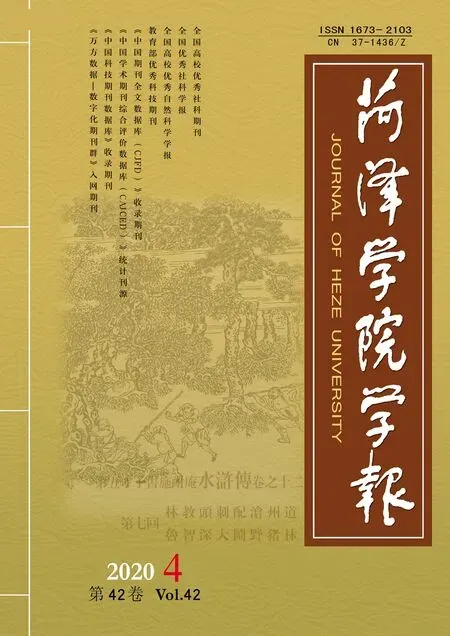“有我之境”中物我关系及“宏壮”美产生原因的辨析
范 悦
(福建师范大学文学院,福建 福州 350000)
《人间词话》中有两处关于“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的论述:
有有我之境,有无我之境。“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有我之境也。“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寒波淡淡起,白鸟悠悠下”,无我之境也。有我之境,物皆著我之色彩。无我之境,不知何者为我,何者为物。古人为词,写有我之境者为多,然非不能写无我之境,此在豪杰之士能自树立耳。(《人间词话》第三十三则)[1]
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人间词话》第三十六则)[2]
学界对于此二境争论已久,研究者各有阐发,但均难达成一致。通过阅读《人间词话》以及王国维的其他理论作品,笔者对“有我之境”中的物我关系,以及此境中“宏壮”美产生的原因有一些自己的思考。王国维有选择地接受西方哲学思想和中国传统诗词批评,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改造与创新,从而构建起自己的批评理论体系。因此,本文将立足于王国维文学批评理论之间的关联性,把这两个问题放在其批评理论体系的整体框架内探讨。
一、“有我之境”中物我关系之再探讨
叶嘉莹先生在《王国维及其批评》一书中说“王国维所说的‘有我之境’原来乃是指当吾人存有‘我’之意志,因而与外物有某种对立之利害关系时之境界。”[3]又说道:“然其所写的‘孤馆’‘春寒’‘杜鹃’‘斜阳’却似乎无一不对‘我’有所威胁,明显表现了‘我’与‘物’之间之对立与冲突。”[4]佛雏先生沿袭了叶先生的思路,并在此基础上有所发展。他认为:“‘有我之境’似可界定为:诗人在观物(审美和创作对象)中所形成的、某种激动的情绪与宁静的观照二者的对立和交错,作为一个完整的可观照的审美客体,被静观中的诗人领悟和表现出来的一种属于壮美范畴的艺术意境。”[5]佛雏先生也认为“有我之境”中是存在对立关系的,但在这一阐述中,他更强调诗人在审美活动中的“某种激动的情绪”和“宁静的观照”之间的关系,他认为这两种状态是彼此分别且对立的,不是孤立而是交错的。佛雏先生所说的“某种激动的情绪”应该就是叶先生论述中的“‘我’之意志”,从这点看,两位学者都认为在“有我之境”中应强调创作者的主观意志与情绪;而在与“我”相对立的对象的具体所指问题上,两位学者持不同看法。“‘我’之意志”或“某种激动的情绪”是诗人带入到诗歌情境中的呢,还是诗人在诗歌情境下的审美活动中产生的呢?叶先生认为的“有我之境”中物我对立关系说能否成立呢?两位学者的阐释仍有可以思考深究的地方,因此我们有必要作进一步的探讨。
解答第一个疑问,需要我们对“有我之境”的产生条件进行分析。要产生“有我之境”,诗人需先后具备两个身份:情感主体与审美主体。具有强烈的、特定的情志指向的情感主体,是诗人在进入诗歌情境之前就已经具备的身份,此身份的存在是形成“有我之境”的必不可少的前提条件。当诗人以情感主体的身份进入具体的诗歌情境中进行审美观照时,情感主体进一步成为审美主体。审美主体涵盖具有强烈的、特定的情志指向的情感主体,因此,在“有我之境”中,诗人所观之物“皆著我之色彩”。据此说,诗人作为主体,存在两个身份,并且这两个身份的产生有先后顺序,因此,与其相对应,“有我之境”的产生就需要存在两个客体对象:一个是在进入诗歌情境之前的,引起诗人情感生发的对象;另一个则是在诗歌情境下,诗人审美观照的对象。引发诗人情感的对象是先于审美活动中的审美对象存在的,诗人在第一个对象的触发下产生强烈的情感并以情感主体的身份进入到诗歌情境中,成为审美主体,对审美对象进行观照。
按此分析,我们认为,在“有我之境”中,“‘我’之意志”或“某种激动的情绪”应该是诗人在进入诗歌情境之前产生的,而并非因情境中的审美对象所引起。以“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6]此句为例,我们很难想象词中诗人所表达的极度哀怨、悲伤的情绪是其审美活动中的“孤馆”“春寒”“杜鹃”“斜阳”诸类审美客体所能引发的。《踏莎行》写于绍圣四年(1097)二月,秦观因元佑党祸连遭贬谪,在移横州编管途中写下了这首词。结合这一创作背景,此不幸的遭遇才应该是引发诗人“‘我’之意志”或“某种激动的情绪”的真正原因。解决了这一问题,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追问“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是否存在对立关系。
我们认为,分析“有我之境”中的物我关系不应该局限于具体的诗歌情境。刘熙载在《艺概·词曲概》中说:“邻人之笛,怀旧者感之;斜谷之铃,溺爱者悲之。东坡《水龙吟·和张质夫咏杨花》云:‘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亦同此意。”[7]唯有怀旧者能感邻人之笛,溺爱者能悲斜谷之铃,原因就在于感受者在感物之前内心积蓄着某种情感,因此他能深感同情景下一般人所不能感受的对象。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在产生“有我之境”的诗歌情境中,诗人是带着强烈的、特定的情志进行审美观照的。正如《蝶恋花》中因“花不语”,因“乱红飞”而伤感,《踏莎行》中因“孤馆”“春寒”“杜鹃”“斜阳”而觉不堪忍受,若非诗人之前就怀有一份情绪在心中,则他眼前所见的景物又何异于常人平日所见之自然物。正是在这份情绪的引导下,诗人作为具有主观能动性的审美主体,为了在诗中更好地表达自己的情感,他会主动地从眼前所见之景中选取外物,某些外物也因其本质特征契合诗歌情感的表达,吸引到诗人的注意,因此被选中成为审美对象,参与到诗歌的创作中。诗人在审美静观中赋予这些对象“我之色彩”,它们也将在诗歌中为“我”之情感的生发和表达积蓄能量。因此,在“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更可能存在着一种双向互动的吸引与选取关系。
王国维在《红楼梦评论》中,曾援引叔本华关于绘画雕刻中的“人类美”的一段论述:
吾人于观人类之美后,始认其美,但在真正之美术家,其认识之也,极其明速之度,而其表出之也,胜乎自然之为。此由吾人之自身即意志,而于此所判断及发见者,乃意志于最高级之完全之客观化也。唯如是,吾人斯得有美之预想。而在真正之天才,于美之预想外,更伴以非常之巧力。彼于特别之物中,认全体之理念,遂解自然之嗫嚅之言语而代言之;即以自然所百计而不能产出之美,现之于绘画及雕刻中。……此美之预想,乃自先天中所知者,即理想的也,比其现于美术也,则为实际的。何则?此与后天中所与之自然物相合故也。……唯两者于其创造之途中,必须有经验以为之补助。夫然,故其先天中所已知者,得唤起而入于明晰之意识,而后表出之事,乃可得而能也。[8]
叔本华在这段论述中提到的“美之预想”、“理念”和“补助”这三个概念值得我们重视。佛雏先生在其著作《王国维诗学研究》中解释:“理念,作为意志在某一对象上的恰当客观化,只能‘通过纯粹的静观而被掌握’。被诗人认出的理念,就内容言,是指存在于某种自然物(包括人)本身的‘内在本性’或者‘本质力量’(即意志先天地赋予该自然物的);就形式言,则指‘代表’该自然物的‘全体族类’,充分体现其内在‘本质力量’(它的这一侧面或另一侧面)之一种可观照的‘恒久的形式’,一种超时空超因果的‘单一的感性的图画’。”[9]叔本华认为,人们先天就存有“美之预想”,而诗人因为能够在审美静观中认出对象事物的“理念”,所以能在将其现于诗与绘画雕刻的创作过程中,借助自身经验对这些对象事物进行“补助”,使之与“美之预想”相契合。佛雏先生说:“在叔氏,艺术家、诗人头脑里朦胧地存在着‘美之预想’,即某种对象的理念,仿佛该对象的‘美’的理想样本;在后天的‘自然物’(包括人)中发现似乎与之相像的东西,于是‘唤起’了自己原来模糊认识的那个样本,并据以对此‘自然物’给予‘补助’,使那个朦胧的、游动于诗人眼前的样本,通过对该‘自然物’的‘补助’,而终于‘入于明晰之意识’。”[10]同时,佛雏先生又将“理念”与概念进行了区分,他认为“理念”不同于概念,概念是既定的;而“理念”却是“生发”着的,可以被不断地扩充,拥有再生产的能力。他认为:“这个‘生发’的观念颇为重要,前面所谓‘补助’(complete)只能放在‘生发’的意义下来理解。”[11]
叔本华的这番话和佛雏先生对上述几个概念的解读,对进一步阐述“有我之境”中的物我关系颇为重要。诗人带着强烈的、特定的情志进入到诗歌情境中,对对象事物进行审美观照;在审美静观中,对象事物唤起“诗人头脑里朦胧地存在着的‘美之预想’”,并以“理念”的形式呈现在诗人眼前;诗人以其生活之经验,当下之情感对这些“理念”进行取舍和“补助”,使它们的“内在本性”和“本质力量”在诗歌情境中不断“生发”,使其(某一侧面)得到更加鲜明丰富的展现。以“泪眼问花花不语,乱红飞过秋千去”[13]为例,此句将整首词的情感推向高潮。夏承焘、盛静霞在《唐宋词选讲》中说:“这首词写妇女的痛苦心情。她被关在深深的庭院里。她的丈夫却玉勒雕鞍在外游荡,她虽然登上了高楼,也望不到他。无计留春住,感叹青春消逝。”[13]在这一情感的导向下,诗人从眼前所见之景中寻找审美对象,因为“花”和“乱红”的“理念”同词中妇女的形象、妇女的情感具有关联性,因此吸引了诗人的注意;同时,为了使对象事物更加符合“美之预想”,更加有利于诗歌情境的创设和“我”之情感的表达,诗人需要对“花”和“乱红”这两个“理念”(某一侧面)进行“补助”,使它们的“内在本性”和“本质力量”得到进一步“生发”;而这一“补助”与“生发”的过程又能使词中“我”之情感得到更加完全生动的表达。暮春时节,花的凋零本身就足够引起人们的伤感与怜惜了,更何况是一位深锁闺中,丈夫成日游荡于歌楼酒馆,青春将逝的如花般的妇女呢?而当身处同样命运的“花”不能对妇女回应以理解之同情时,此时妇女的内心该有多么悲伤苦闷啊!在此情景下,妇女“问花”这一看似无理的提问也似乎具有其合理性了。
叶先生所谓的“有我之境”中物我的对立利害关系,若放在王国维所列词句的具体情境中看,似有一定的道理。无论是“问花”而“花不语”,还是“孤馆”“春寒”“杜鹃”“斜阳”,词句中所描写的诸外物都与诗人的意志相背,诗人愈是伤感,外物愈是无情,愈是给诗人以强烈的刺激和压迫感。但我们必须清楚这是具有强烈的、特定的情志指向的诗人发挥主观能动性的结果。外物本身只是作为客观事物存在于自然界,当诗人将它们带入诗歌情境中进行审美观照时,这些外物才因诗人情感的导向而获得不断的“补助”,得以“生发”。在诗歌情景中,诗人以一种有利于诗中情感表达的方式结构“我”与“物”,每首诗歌表达的情感不尽相同,诗中的“我”与“物”也相应地呈现出不同的结构方式。因此,分析“有我之境”中的物我关系,不能局限于具体的诗歌情境。
综上,我们认为,叶先生的“有我之境”中物我对立关系说可能不能成立,此境中的物我关系更可能是一种双向互动状态下的吸引、选取与补助、生发。
二、“有我之境”中“宏壮”美产生原因之再探讨
王国维曾三次在文中提及“宏壮”这一概念。前两次是在1904年发表的《〈红楼梦〉评论》和《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两篇文章上,他采用的是叔本华对“壮美”的界定:
“美之为物有二种:一曰优美、一曰壮美。……若此物大不利于吾人,而吾人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因之意志遁去,而知力得为独立之作用,以深观其物,吾人谓此物曰壮美,而谓其感情曰壮美之情。”(《〈红楼梦〉评论》)[14]若其物直接不利于吾人之意志,而意志为之破裂,唯由知识冥想其理念者,谓之曰壮美之感情。(《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15]
第三次是在1907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一文中,王国维采用的是康德的论述:
而美学上之区别美也,大率分为二种:曰优美,曰宏壮。……后者则由一对象之形式,越乎吾人智力所能驭之范围,或其形式大不利于吾人,而又觉其非人力所能抗,于是吾人保存自己之本能,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而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如自然中之高山大川、烈风雷雨,艺术中伟大之宫室,悲惨之雕刻像、历史画、戏曲、小说等皆是也。(《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16]
思想是在人不断自我否定的过程中逐渐发展成熟并最终趋于完善的,从以上引用的三则材料中我们可以看到:从1904年到1907年王国维关于“壮美”的界定是有变化的。首先,从内容上看,三则材料中对“壮美”的界定是在不断调整中具体丰富从而更加明确的;其次,从深层思想上看,在这一问题上王国维从追随叔本华转向了吸收康德的相关论述。光绪三十一年(1905)秋,王国维为其文集作序,序中写道:“癸卯春,始读汗德之《纯理批评》,苦其不可解,读几半而辍。嗣读叔本华之书而大好之。……今岁之春,复返而读汗德之书,嗣今以后,将以数年之力,研究汗德。他日稍有所进,取前说而读之,亦一快也。”[17]因此,在分析“宏壮”美产生的原因时,应该将这三则材料结合起来看。
关于“宏壮”美产生的原因,叶先生的说法是:因为“有我之境”中“我”与“物”处于一种对立的利害关系,因此对立将产生一段冲突,正因为有冲突,所以此境的美感多为“宏壮”。首先,通过上文分析,我们认为在“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不存在对立利害关系;其次,阅读《王国维及其批评》一书中的相关文字,我们会发现叶先生仅分析了1904年王国维在《叔本华哲学及其教育学说》中关于“宏壮”美的论述,因此叶先生的结论显然不太有说服力。佛雏先生补充了叶先生的说法,他认为:“完整的说法似应是:‘物我利害之冲突的克服’。因为只有这种克服,即‘强制地’驱走意志,或者‘强力挣脱这一客体跟意志之间的不利关系’,才是叔氏体系中的‘壮美’的特征。”[18]佛雏先生提出了“克服”,可以说是准确抓住了“宏壮”美产生的关键步骤,但他并未明确这一“克服”过程是诗人在什么时候经历的,是在进入具体诗歌情境中进行审美观照之前?还是之后?他也未说明该过程如何在文学创作中得以实现。因此,我们还需要继续思考。
三则材料在对“宏壮”美的界定上均说到,“物”或“对象之形式”是“不大利于吾人”或是“非人力所能抗”,我们要明确这一利害关系是在“宏壮”美产生之前存在的。更重要的是在后面的论述上,前两则材料都说到,在这种利害关系下“(吾人之)意志为之破裂”、“意志遁去”;第三则材料则更明确说“(吾人)遂超越乎利害之观念外”。这就表明,此前的利害关系只是暂时的,它会随着吾人意志的破灭而消失,此时便已不存在利害关系了。随后,吾人便可“深观其物”或是“达观其对象之形式”,唯有进入到这样的审美静观中,诗人才能创造出具有“宏壮”美的作品。综上所述,“宏壮”美也是在无利害关系的状态下产生的。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所用的“宏壮”即是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提出的“崇高”这一概念。康德认为,只能用审美的评判尺度来估量“崇高”,同时,康德又说:“每个人都必须承认,关于美的判断只要是混杂有丝毫的利害在内,就会是很有偏心的,而不是纯粹的鉴赏判断了。”[19]可见,叶先生用物我之间存在对立冲突的利害关系来解释“宏壮”美的产生,可能不能成立。那么“有我之境”表现出“宏壮”美的原因是什么呢?
解答这个问题,关键在于我们如何理解“由动之静”。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三十六则中的说:“无我之境,人惟于静中得之;有我之境,于由动之静时得之。故一优美一宏壮也。”[20]关于“由动之静”,叶先生认为:“在开始时原曾有一段我与物相对立的冲突,只有在写作时才使这种冲突得到诗人冷静观照”。[21]佛雏先生则认为:“在诗人落笔前的观照中,就已包含这个‘静’了。所谓物我之间的‘对立’与‘吸引’,就意味着‘动’(欲望、意志占主导地位)与‘静’(无意志的静观占主导地位)的交错。”[22]肖鹰先生认为:“当把所谓‘于静中得之’的‘静’与‘人心平和’联系起来,即以后者为前者的实质内涵,我们就可以相应地把‘于由动之静时得之’的‘由动之静’理解为一个自觉追求‘人心和平’的活动,故其核心在于‘动’而不是‘静’。”[23]叶先生认为,“由动之静”就是指诗人在审美活动中产生的物我冲突,在其写作时得到了冷静观照的这样一个过程。佛雏先生则认为,“静”不仅存在于诗人落笔写作时,“由动之静”的过程在诗人审美观照中就已经发生了。“动”就意味着物我“对立”,“静”就意味着物我“吸引”,“由动之静”就是从“对立”到“吸引”的过程。叶先生和佛雏先生均是以“有我之境”中物我之间存在对立利害关系的认识为基础来解释“由动之静”的,而上文通过分析认为“有我之境”中的物我对立关系说不能成立,因此,两位先生的解读虽能给人启悟,但结论仍有待商榷。肖鹰先生将此则中关于“无我”和“有我”两境的论述对照起来分析。他用“静”的实质内涵来分析“由动之静”,他认为,“由动之静”是指诗人从躁动不安、情绪难以抑制到主动追求内心平和的这样一个由动趋静的动态过程。此番解释条理清晰,说服力强,颇具启发性。我们认为,对“由动之静”这一过程的分析,是探究“有我之境”中“宏壮”美产生原因的关键步骤。
以往不少研究者在研究“优美”与“宏壮”这一问题上,只引用了王国维在1904年所写的《〈红楼梦〉评论》中笔者在上文所引的那一段,而忽视了这段文字后面的内容,即对“壮美”之情的具体描述。王氏说到:“至于地狱变相之图,决斗垂死之像,《庐江小吏》之诗,《雁门尚书》之曲,其人固氓庶之所共怜其遇,虽戾夫为之流涕,讵有子颓乐祸之心,宁无尼父反袂之戚,而吾人观之,不厌千复。格代之诗曰:‘What in life doth only grieve us. That in art we gladly see.’(凡人生中足以使人悲者,于美术中则吾人乐而观之。)此之谓也。此即所谓壮美之情。”[24]从此番论述看,首先壮美之情通常产生于悲剧中;其次,这类悲剧能深刻感染读者,又能使读者“乐而观之”。无论是具有普适性的这种生存还是死亡的终极问题,还是具有英雄性的这种为国为民的大无畏舍己情怀,它们好像时刻在提醒人们,人生就是场悲剧。这些故事和图画应该都是人人所惧怕看见的,然而为何能使“吾人乐而观之”呢?
王国维在《人间嗜好之研究》中也提到过悲剧的喜感问题,他认为,普通人嗜好悲剧的原因在于吾人能从悲剧中获得一种“势力之快乐”。在这篇文章中,王国维提出了“势力之欲”这一概念,按王国维的说法,“势力之欲”指:在生活中,人们企图通过竞争超越他人的一种生活之欲。那么吾人何以能从悲剧中获得“势力之快乐”呢?“夫人生中固无独语之事,而戏曲则以许独语,故人生中久压抑之势力独于其中筐倾而箧倒之,故虽不解美术上之趣味者,亦于此中得一种势力之快乐。”[25]“人生之运命固无以异于悲剧”[26],而当创作者将人生的悲剧以戏曲中悲剧的形式演出时,吾人观之,亦从戏曲中看到自己之人生。生活中不能言、不敢言的一种“人生中久压抑之势力”,得以在观主人公的悲剧中倾吐、宣泄。此悲剧为吾人之人生悲剧代言,而若非创作者于自己之人生中亲历过此类悲剧,则不能以真切表出之,唯有饱含真景物与真感情的作品,才能感发读者,使读者产生共鸣。
创作这类作品,对创作者而言是一种更高层次的自觉追求,唯有大诗人能够做到。“若夫真正之大诗人,则又以人类之感情为其一己之感情。彼其势力充实,不可以已,遂不以发表自己之感情为满足,更进而欲发表人类全体之感情。彼之著作,实为人类全体之喉舌,而读者于此得闻其悲欢啼笑之声,遂觉自己之势力亦为之发扬而不能自已。”[27]创作者在进行创作前,自己要先主动经历一个“由动之静”的过程。因心中存有“生活之欲”,故必与外物产生利害关系,“如果对象对于人的意志有一种敌对的关系,或是对象具有战胜一切阻碍的优势而威胁着意志”[28],此对象必使创作者内心开始激烈斗争,在沉沦与解脱之间挣扎;为克服此不利之对象,他主动选择了“苦行僧”的生活,在不断自我折磨与反思中开悟,悟到命运的不可抗性,悟到众生皆苦,悟到个人利益的不足道;随后,他从小我中超脱出来,用强力去克服此对象,使自身“生活之意志为之破裂”。他开始接受命运的安排,放下之前的执迷,主动去担荷一种更艰难宏大的人类全体之命运与事业。康德认为,当对象被视为是具有强力的东西,而我们又能通过抵抗,最终克服这种强力,这就是一种“崇高”。创作者经历的这一“由动之静”的过程,本身就是一个对自然强力的克服过程,该过程使得创作者内心激发出崇高感。当他带着这份崇高的情绪进入到审美静观中,将其经历显之为像、述之于书,这份崇高的感受必然会呈现在他的作品中,充满感发人的力量。
“由动之静”的这一过程,是对创作者而言的。但我们不能忽略“崇高”作为一种审美经验,它又是接受者的一种审美感受。创作者在其作品中呈现了他对强力的克服与解脱,并将他的那份崇高感充盈于作品中。读者往往能受此类作品的感发,产生共鸣,悲悯于作品中人物之痛苦,而暂时忘却一己之痛苦。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品让读者意识到对象带来的强力是可以被抵抗,并最终被克服的。因此,读者能从作品中寻求慰藉,从主人公与创作者身上看到解脱的希望,获得克服与超越强力的勇气和力量。康德说:“所以崇高不在任何自然物中,而只是包含在我们内心里,如果我们能够意识到我们对我们心中的自然、并因此也对我们之外的自然(只要它影响到我们)处于优势的话。这样一来,一切在我们心中激起这种情感——为此就需要召唤我们种种能力的自然强力——的东西,都称之为(尽管不是本来意义上的)崇高。”[29]
综上所述,“有我之境”之所以表现出“宏壮”美,是因为创作者带着克服强力后的崇高感进行创作,因此,其作品必然表现出“崇高”;读者阅读此类作品又能受到创作者的这一克服经历所感发,意识到自己也有力量克服具有强力的对象,遂也能因此获得一种崇高感。我们认为,这也就是“有我之境”表现出“宏壮”美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