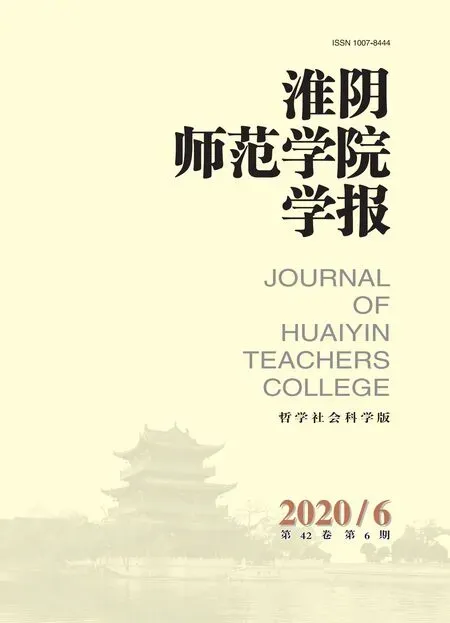学路历程:顾颉刚报刊编辑活动述论
董 娟
(肇庆学院 学报编辑部, 广东 肇庆 526061)
如果要从报刊编辑出版的视角为中国现代学者开列一个榜单,那么历史学家顾颉刚先生(1893—1980)定能名列前茅。顾先生一生创办编辑的报刊在50份以上(不完全统计),与报刊以及整个出版媒介有着深厚的渊源。顾颉刚学术版图涵盖古史辨伪、民俗学、历史地理学、民众教育等方面,他在这些领域的拓展离不开报刊媒介的推动作用,同时他又以自己的编辑出版实践丰富了近现代报刊市场。他是近现代报刊发展的受益者,又是近现代报刊发展历程的重要参与者。其报刊实践活动与学术发展轨迹颇相吻合,可以说顾颉刚的报刊实践活动既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结果,也是其学术思想发展的体现。
一、《新潮》时期:作为启蒙底色的学问
甲午战争后,国内掀起一股办报热潮,各类报刊相继涌现。正是在这一风气之下,少年时的顾颉刚接触了《新民丛报》《东方杂志》《绣像小说》《时报》《复报》《国粹学报》以及“竖三民”(《民呼日报》《民吁日报》《民立报》)。经由阅报激发起办报的渴望,中学时期的顾颉刚与叶圣陶、王伯祥等一起编辑年级级报,为校运动会出版新闻纸,并曾被邀请为《大声报》编辑,但终因与该报意见相左而辞出。少年时的办报实践,虽积累了经验,但影响范围有限。顾颉刚真正介入出版领域,以自己的编辑实践影响社会人心,是在北大《新潮》时期。
1913年,顾颉刚入读北大,与同学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等志趣相投,相处甚洽,常有对北京大学未来的畅想与规划,其中包括创办学生杂志[1]。1918年,顾颉刚休学在家,傅、罗、徐等人发起成立新潮社,同时创刊《新潮》杂志,顾颉刚成为新潮社首批社员。1919年9月返京复学后,任新潮社干事,负责杂志的推广发行等事务。后傅斯年、罗家伦等相继出国,罗将《新潮》编辑事托付于顾颉刚。1920年10月,新潮社选举第三届职员,周作人任主任编辑,顾颉刚与毛子水、陈达材、孙伏园等任编辑[2],编辑《新潮》1920年二卷五期至1922年三卷二期,之后《新潮》停刊。
虽然最初顾颉刚并未担任《新潮》编辑,后期由于多人编辑亦未能体现突出的个人风格,但他在一些通信及文章中表达了其个人的一些办刊主张。与当时一些报刊激烈的风格相对,顾颉刚希望《新潮》能取“温愉”的态度,用“真挚浓密的感情,去感动社会”[3]178。顾颉刚将这种“温愉”的态度和真挚的感情落实在学问上。在向傅斯年建议“通信”栏目的办法时,他说:“总须随时随处表明我们是研究学问的人,不是全知全能的人;是与大家同居一社会,帮助着他们进步的人,不是聪明独出看着一班人只配给我蹴骂的人”,“通信一栏,就是我们与他们知识上连络的地方,取长补短最便利的所在”[3]180。顾颉刚试图以平和的学术探讨代替凌厉的攻击对立,使编者、作者、读者三方都在学问的轨道上说话。几个月之后,顾颉刚与叶圣陶谈论办报时再次提到报刊的学问定位:“我们报纸只要避去激烈的字眼,不妨提倡激烈的意思。对于意思只要正当的从学问态度上说话,不涉谩骂态度,便不会引人惊骇。而在根本上灌输其功,尤无形而伟,于自己良心,又无对不住之处。”[3]67在顾颉刚看来,学问才是启蒙民众、改造社会的根本武器,而且深沉的学术话语才是消弭火药味的良方,其之于改造社会具有春风化雨的作用,“无形而伟”。
由于当时身为学生,深觉学问未充,见解不深,不能从根本上立论,因此顾颉刚主张一面办报,一面勤学,并勉励同道,期之以未来。“我希望我们社(新潮社)里的人,或是与本社道同志合的人,都认定了一项的学问,勉力去读书,去体察。虽则现在不过说:社会现象,可便能一步一步的引到学问上去了。过了十年二十年之后,我们的杂志,专是用学问来解决社会问题,不由得使人不信服。再我们学问渐渐的好起来,我们拿所得的学问时时由杂志发表出去,大家看了,或是有意的去研究,或是无意的受了濡染,或是间接又间接的受了同化,那便是社会的学问知识也一天一天的上去了。要说真实的新潮,真实的改革进步,都可得到用到。”[3]52可见,学生时代的顾颉刚即树立了以稳健持重的学理探讨为取向的报刊观念,反对空谈社会现象,主张以学问的充实来为报刊注入底气。
五四以后,新潮社的主将逐渐将注意力从社会政治转向读书与学问。傅斯年、罗家伦先后出国留学,希望借助西方系统的学术思想来解答自己和社会的困惑;顾颉刚则留在北大埋头整理古书,进而探索自己的学术方向。轰轰烈烈的启蒙最终落实到覆篑而进的学术耕耘。
二、整理国故运动中的报刊实践
(一)北大国学门时期
《新潮》1919年1卷5号刊登毛子水《国故和科学的精神》一文,批判刚刚创刊不久的《国故》月刊。毛子水关于“国故”的观点引起傅斯年、胡适的回应。1919年12月胡适发表《新思潮的意义》一文,正式提出“整理国故”的口号,并系统指出了“整理”的方针与计划,得到北京大学众多学者的响应,从而掀起整理国故运动。为实践“整理国故”的理念,北大研究所国学门于1922年1月成立[4]。国学门成立以后,发行《国学季刊》《歌谣周刊》《国学门周刊》作为展示“整理”成果的平台。1920年6月,顾颉刚留校任助教,初职图书馆,国学门成立后复任于国学门。顾颉刚参与了国学门的筹建,先后成为上述三个刊物的编辑。
1.《国学季刊》
1923年1月,《国学季刊》创刊,由胡适任主编。顾颉刚为该刊前两期提供了《郑樵著述考》和《郑樵传》两篇文章,同时该刊第2号刊登了胡适的《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这几篇文章致力于介绍古代的辨伪学者,颂扬他们的批评精神和科学精神,成为古史辨运动的前奏。后来,顾颉刚有意再作两篇辨论古史的文字——《禹贡作于战国考》和《尧典、皋陶谟辨伪》[3]394-397。此二文接续《读书杂志》所载《与钱玄同先生论古史书》提出的问题,试图将古史辨伪工作导向深入,但终因无暇而未能完成。
1923年12月,顾颉刚开始担任《国学季刊》校对,1924年改任编辑。进入编辑队伍之后,顾颉刚表现出负责进取的精神,一方面试图改善《国学季刊》脱期状况,使其按期出版,另一方面呼应胡适《科学的古史家崔述》一文,拟出“崔东壁专号”,开展更为精细化的批评,持续推动古籍整理与古史辨伪工作展开[3]413。然而,由于时局与经费问题,《国学季刊》在出至1925年第二卷第一号之后暂时停刊,“崔东壁专号”亦无从所出。《国学季刊》包容了整理国故的多个路向,对顾颉刚而言,它是论辨古史的一个重要平台。
2.《歌谣周刊》
《歌谣周刊》创刊于1922年12月17日,初名《歌谣》周刊,于1924年第49号更名为《歌谣周刊》。该刊由国学门歌谣研究会主编,初由常惠负责实际编辑工作,1924年4月常惠以疾乞假,顾颉刚代其编辑。顾颉刚接手编辑时正值《歌谣周刊》转型,由前期的搜集为主转向兼顾整理与研究[5],并且搜集的范围扩展到谚语、歇后语、故事、传说、童话以及风俗、方言等[6]。
为支持刊物转向,顾颉刚撰写了一系列文章。顾颉刚接编《歌谣周刊》后即以《东岳庙的七十二司》《两个出殡的导子账》《一个“全金六礼”的总礼单》《一个光绪十五年的“奁目”》《东岳庙游记》等几篇民俗研究文章刊载于“研究”“记载”栏,体现出《歌谣周刊》的民俗学转向。
也正是在这一时期,顾颉刚展开了奠定现代民俗学和故事学研究范式的孟姜女研究。为了兑现“系统的整理和具体的研究”之承诺,《歌谣周刊》自第55期开始出版专号,发布征题。顾颉刚主持“孟姜女专号”,发表《孟姜女故事的转变》一文,成为“二千五百年来一篇有价值的文章”[7]。之后又充分利用刊物的通信、按语、附记等,与读者交流,征集材料,表达观点,构筑讨论空间,保持话题的热度与生长性,使孟姜女研究刊登9期而未完结,进而延续到《国学门周刊》时期。孟姜女研究渐渐成长为现代民俗学的重要课题。孟姜女研究的成功,充分体现出现代报刊对学术发展的引导和推动,亦体现出报刊“通信”对于拓展和深化学术研究的作用。
1925年6月28日《歌谣周刊》出完第97期后并入《国学门周刊》,顾颉刚顺承为《国学门周刊》编辑。
3.《国学门周刊》
《国学门周刊》创刊于1925年10月。作为《歌谣周刊》的扩充版,包含了原《歌谣》中的民俗学研究内容;同样,随着《国学季刊》的不断脱期以至停刊,《国学门周刊》又成为《国学季刊》的补充与替代刊物,容纳了原《国学季刊》的研究内容。由此,《国学门周刊》涵盖了民俗学、历史学、语言文字学、考古学、金石学、目录学等研究方向,从高文典册、帝王圣训到俚俗歌谣、民间传说,从古史辨伪到古物发掘,皆为研究对象,体现出具有现代特质的学术平等观念。顾颉刚为《国学门周刊》所作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鲜明地表举出这一学术平等的观念:“我们要屏弃势力的成见,用平等的眼光去观察所研究的对象。我们对于政治、道德以及一切的人事不作一些主张,但我们却要把它们作为研究的对象。”[8]229这一学术平等观念正是整理国故运动的中心议题之一。胡适在《国学季刊》宣言中提出了“现在和将来研究国学的方针”,其中第一条即“扩大研究的范围”,用历史的眼光看待过去的一切历史文化[9]。因此顾颉刚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正是对整理国故运动精神的阐扬。
《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中还提到,“国学是中国的历史,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所以我们研究的主旨在于用了科学方法去驾驭中国历史的材料,不是要做成国粹论者”,研究的目的在于求取真理[8]217-229。这种科学求知与学术平等的观念成为顾颉刚学术思想的主线,不仅成为《国学门周刊》的办刊宗旨,而且也贯穿其他刊物的编辑出版活动。
《国学门周刊》亦由于时局、经费等问题而脱期,至1926年8月停刊。1926年10月,《国学门周刊》更名为《国学门月刊》,以月刊形式出版。1926年8月,顾颉刚南下,《国学门月刊》事交由冯沅君代。
(二)国学门经验的推广
1.厦门大学时期
1926年8月顾颉刚南下任教厦门大学,与林语堂、沈兼士等筹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仿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之体制,以整理国故、培养国学专门人才为宗旨[10],组织创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类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国学季刊》《国学门周刊》。其中《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季刊》创刊号虽已编好,但未能出刊[11],顾颉刚所作的发刊词也佚失。不过我们从顾颉刚为《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所作的《缘起》中可以窥见其学术主张与办刊理念。其一,顺应现代学术潮流,用现代学术方法整理国学材料。其二,实地考察与书本研究相结合,“要掘地看古人的生活,要旅行看现代一般人的生活”,因此《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中刊载了不少民俗调查类的文章,延续了北大时期开创的民俗学路向。其三,研究的目的在于求真,“在我们的学问范围之内求知识”[8]238-239。
这篇《缘起》的论点和基调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一脉相承,展现出一种崭新的学术观念。但这种观念在当时并未被社会广泛接受,因此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与《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的《缘起》两篇文章都意在向社会辨明自己的立场,其说话对象都是“一般人”,都是在向“一般人”来阐明“我们”的态度和见解。也正为此,顾颉刚才积极创办各种报刊,以造成风气,向社会灌输新的观念,为开创学术新道路扫清思想障碍。
《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由顾颉刚、容肇祖编辑,1927年1月创刊,出版3期(1927年1月5日—1月19日),第4期仅有目录,未能出版[12]。1927年2月厦大国学研究院停办,《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亦随之停刊。
2.中山大学时期
1927年4月,顾颉刚离开厦大,抵达广州,就职中山大学。1927年8月,傅斯年任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筹备主任,顾颉刚亦参与中大语史所筹备工作,议定出版《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歌谣周刊》。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所周刊》(以下简称《中大语史所周刊》)创刊于1927年11月1日,由顾颉刚与余永梁、罗常培、商承祚等负责编辑。正如刊物名称所标示的,其刊载范围以语言学、历史学为中心,并由此辐射民俗学、人类学、考古学、金石学、文艺等学科,甚至有个别文章涉及地质、数学等。如此一方面扩大了史学研究的领域与视野,另一方面又促进了民俗、考古等学科的独立发展。顾颉刚为《中大语史所周刊》所作的发刊词以“范围”“材料”“方法”“新道路”为关键词,体现出与北大研究所《国学门周刊》的《一九二六年始刊词》以及《厦门大学国学研究院周刊》的《缘起》一致的旨趣,因此张荫麟评价曰:“广东中山大学近创办语言历史研究所,其规模略仿旧日北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并印行周刊,其体例亦仿旧日北大研究所周刊。”[13]1930年11月,随着中大语史所的停办,《中大语史所周刊》停刊,而顾颉刚则于停刊之前的1929年2月离开广州返回北京,也由此结束了其在《中大语史所周刊》的编辑工作。
除了《中大语史所周刊》,中大语史所所办的另一份刊物《民间文艺》也明显体现出与北大国学门的亲缘关系。《民间文艺》初名《歌谣周刊》,显示出对北大《歌谣周刊》的承继,出版时更名为《民间文艺》[14]161,刊载歌谣、传说、谜语、神话、谚语、故事等,具有明显的文艺取向。该刊初由钟敬文、董作宾负责编辑,后董作宾请假离开中大,由钟敬文一人负责[15]45-46。《民间文艺》由于专取文艺,范围太窄,研究和发展都受到限制,因此决定“放宽范围,收及宗教风俗材料”,《民间文艺》之名不复相称,故更名《民俗》[16]。《民间文艺》创刊于1927年11月,停刊于1928年1月。
1928年3月,《民俗》创刊。顾颉刚任主编,实际编辑工作由钟敬文负责,顾颉刚亲自编辑过第25、26合期,1928年9月后由容肇祖负责编辑,后刘万章、夏廷棫亦参与《民俗》编辑事务[15]47-48。虽然顾颉刚并未太多介入具体的编辑事务,但他是《民俗》重要的指导者和支持者,是《民俗》学术质量和经费来源的重要保障。随着顾颉刚北上,《民俗》逐渐偃旗息鼓,至1930年停刊[15]48-58。由顾颉刚等人组织创办的中大民俗学会与《民俗》刊物,是发端于北大的民俗研究在南方的深化发展,也是整理国故运动在民俗领域所取得的实际成果。
在上述刊物之外,顾颉刚在中大时期还主编《国立中山大学图书馆周刊》。该刊于1928年3月创刊,由杨振声、顾颉刚、杜定友编辑。顾颉刚于1927年5月至9月前往沪杭一带为中大购书约12万册[14]161,为中大学术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图书基础。整理后的各类书目渐次在《图书馆周刊》登出。这些书目在经史子集等传统书籍之外,更有杂志、日报、家谱、账簿、日记、公文、职员录等通常不入藏书范围的资料[14]161,亦是整理国故运动所倡导的“扩大研究范围”的体现。
顾颉刚在整理国故的氛围中获得新的学术观念与科学的研究方法,在北大国学门的实践中锻炼了推动学术活动和领导学术事业的能力,从而促进了自身学术发展。当其南下时又承担起推广国学门经验的使命,而这种经验推广,实则为个人学术观念的彰显与表达。
(三)《燕京学报》:西方汉学与整理国故的相遇
1929年2月顾颉刚离开广州后,于9月任职燕京大学,成为《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委员。《燕京学报》创刊于1927年6月,得到美国霍尔基金的支持,致力于研究中国文化[17]21。1928年1月,哈佛燕京学社成立,其基本宗旨便是推动汉学以及东方学研究,并按照规定资助出版活动[17]20。因此,《燕京学报》自创刊就带有浓厚的西方汉学背景。这一背景与当时国内开展的整理国故运动有着研究对象的一致性。于是《燕京学报》的编辑与作者便在西方汉学背景下进行整理国故的实践。《燕京学报》编辑委员会主任初由容庚担任,1930年改由顾颉刚担任。中间顾颉刚经历暂时卸任、复任编委会主任过程,不过始终担任编委会委员,直到1937年离京西行。顾颉刚任职编委期间,编辑了第6—10期,第12—16期,同时编辑专号之三至六。其中第7—8期、12—15期为主编,第6、9、10、16期与容庚同编。顾颉刚担任主编后所作的重要改革就是自第8期起增设“学术界消息”和“新著评论”两个栏目,加强了与外界的信息交流,而且版面有所增加,扩大了学报的学术容量。《燕京学报》的刊载内容以历史学以及语言文字为主,兼及金石、文学、风俗、哲学、考古、宗教、数学、边疆、地理等,其中边疆地理类文章的少量出现,预示了顾颉刚下一阶段的学术转向。
三、历史地理与边疆民族研究
为了更好地研究上古史,1932年9月顾颉刚在燕京大学和北京大学开设“中国古代地理沿革史”课程,当时其弟子谭其骧在辅仁大学也开设此课程,二人有意为师生提供讨论发表的园地。适时,“九一八”之后,日本加紧侵略步伐,并造出“本部”一词离析边地,试图从地理上为其侵略寻找借口,因此顾、谭二君认为必须从学理上推翻日本的侵略理论,完善国人的地理认知和民族意识,激发爱国热情,由此,研究历史地理成为抗战的现实需要。在学术与抗战的双重契机下,《禹贡》半月刊诞生了。该刊创刊于1934年3月,顾颉刚、谭其骧负责编辑,顾廷龙、钱穆亦与其事。《禹贡》通过构筑学术平台,引导深化研究,促进了中国现代历史地理学学科的构建,可谓报刊媒介促进学科形成发展的典范。
《禹贡》的研究、刊载范围包括历史、地理、民族、边疆等几个有机不可分割的方面。1937年七七事变后,顾颉刚离京西行,《禹贡》停刊。在西部期间,顾颉刚又创办、编辑了《益世报·边疆周刊》、《中国边疆》、成都《边疆周刊》等,以继续《禹贡》时期的事业,使更多的人参与历史地理以及民族边疆问题的研究,并意识到民族边疆问题的重要性,进而为抗战提供学术支持。
四、通俗读物
除了上述历史地理与边疆民族研究方面的刊物外,顾颉刚为支持抗战而发起成立的机构还有通俗读物编刊社。该机构的前身是燕京大学抗日会所组织的三户书社,顾颉刚在抗日会中任宣传干事[14]230-235。1933年10月,三户书社易名为通俗读物编刊社,由顾颉刚所独办,并扩充工作目标,在激发民族意识、鼓励抗战之外,还致力于培养国民道德、普及工农业及医药卫生知识,激发民众向上的意志和生活的希望,真正做一个“新民”[14]237-238。也就是说,顾颉刚为通俗读物编刊社规划的目标在于启蒙与救亡并重。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编刊社出版了不少小册子和通俗读物,并创办了杂志。
1936年3月,顾颉刚在《申报》开办《通俗讲座》副刊。1936年10月,《民众周报》《大众知识》先后创刊。这些刊物,一方面以通俗浅显的语言讲述历史上的英雄事迹、爱国故事,一方面报道评论抗战时事、国内外大事,同时兼及民俗、文艺、教育、经济、化学、生物等各方面现代常识。这些刊物极受欢迎。1937年曾有《申报》读者评论:“《申报》每星期的副刊,……以每逢星期四出版的‘通俗讲座’最为精彩。……我极希望诸位有正在求学的小弟弟或小妹妹的,可以多多奖励他们去看。这不仅使他们对于我国从前的名人,多得到一些认识;而且还可以启发他们爱国的思想,真是一举数得的事。”[18]《大众知识》第一期的销量“竟超过上海最时髦的幽默杂志一倍”[19]。而《民众周报》“在开始发行的头几个月内,就在华北卖了近四五千份”[20]109。以上可以管窥上述通俗刊物受欢迎的程度,而且能够说明当时大众对这类通俗读物需求很旺。由于时局、经费、查封等问题,这几份刊物于1937年先后停刊。
这几份报刊停刊后,通俗读物编刊社依然进行民众教育工作,出版抗战小册子和通俗书刊,在战争中辗转西北西南,一直坚持启蒙与救亡的工作,直至1940年因当局压迫而解散[20]113。不过,这并未降低顾颉刚的启蒙热情。抗战胜利后,他于1946年再次组织民众读物社[14]379,1947年筹办《民众周报》(第二期更名《民众周刊》)[14]382。这些可谓通俗读物编刊社的继续,是顾颉刚学术思想在普及向度的展开。
结语
以上是根据顾颉刚学术思想发展而进行的举隅性勾勒,意在呈现顾颉刚与学术共生的编辑活动,内容主要涉及整理国故(含古史考辨、民俗学)、历史地理、通俗教育等领域,顾颉刚一生的报刊编辑出版活动基本围绕这几个领域展开。限于篇幅,还有众多刊物未能一一描述。
顾颉刚的报刊编辑活动是其学术活动的延伸,他对出版业的热情是其学术热情的映射。顾颉刚曾说:“我的创造的冲动不知何故竟这样的浓烈,心中的问题也不知何自来,竟这样的繁多,非取得一个言论机关竟无法满足我的发展”,“我自己也不懂……发展自己的心为什么会得这样的迫切”[3]87-88。为了充分发展自己,使心中的疑惑和观点得到充分表达,顾颉刚选择了报刊作为言说的空间和平台,“我在北大中肯编《歌谣周刊》及《国学门周刊》,到了厦大肯编《季刊》及《周刊》,实在要攫得言论机关来造新空气”[3]87。当然,顾颉刚编辑出版报刊,并不仅仅是为了自己。他推己及人,认为他人亦需要平台来发展个人才性,于是他特别重视出版工作。在其工作过的每一个地方,他都积极推动创办报刊、出版图书,使人尽其才、学有所用,为机构整体创造良好的学术氛围;同时,他又与多个社团交往密切,亦大力推动社团刊物的编辑出版。因此,顾颉刚编辑创办的报刊就越来越多,培养的人才也越来越多,成为现代学术史和期刊史上的重要景象。
顾颉刚的编辑出版活动贯穿其学术生涯之始终,占据了其人生中的大部分时间,研究其编辑出版活动,是接近顾颉刚的重要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