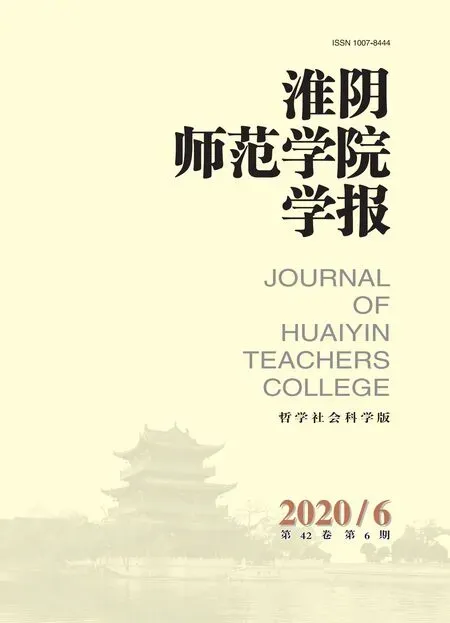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视角下的道德治理问题研究
殷 殷
(南京财经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 江苏 南京 210000)
自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提出“加强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新任务”以来,道德治理问题越来越重要。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以“人类同自然的和解以及人类本身的和解”为逻辑起点,对人、自然、社会三者关系进行了深入研究,建构了关于人与自然、人与社会、人与人和谐相处的法则,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和有效钥匙。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概述
(一)“人同自然的和解”与“人同本身的和解”是内在统一的
马克思认为,人是“自然存在物”与“社会存在物”的统一。人的基于“类存在”之上的“类意识”是人与自然环境以及人与人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结果。
1.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是彼此交织、互相制约的。一方面,人与自然的关系是人的所有关系存在的物质基础,人们正是在改造自然的生产活动中形成了人的所有关系;另一方面,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又是人与自然关系的社会前提。“一切生产都是个人在一定社会形式中并借助这种社会形式而进行的对自然的占有。”[1]
2.在人与自然和人与自身这两对矛盾中,人与自身的矛盾始终占据主导地位。马克思认为,要解决好人与自然的矛盾,首先要解决好人与人、人与社会的矛盾。马克思、恩格斯针对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指出,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生产社会化的发展和生产资料的高度集中,已经达到了同他们的资本主义外壳不能相容的地步,这个外壳就要被炸毁了”[2]。可见,只有生产方式中形成的人与人之间的对立和对抗得以化解,人类才能准确认识到自己不再是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消费者和管理者,人与自然的关系有可能和谐统一。
(二)人类主体价值与自然优先的生态统一论
1.自然界对于人类的优先存在性和本原地位
马克思提出了“自然界优先地位”的观点。他认为,人类社会的发展必须考虑环境的容量、生物圈的承受能力,而不能突破其界限。人类应当尊重自然规律,以最低的资源消耗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因为“历史本身是自然史的一个现实部分,即自然界生成为人这一过程的一个现实部分”[3]。当今时代,处于生物链顶端的人类正在主导第六次物种大灭绝。因此,人类必须改变生活方式和消费方式,不能一味地向自然界索取,而要把自身视为自然界的一部分,才能与自然和谐相处。
2.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的价值主体地位
马克思、恩格斯从来没有将人与自然的关系和人与人的关系割裂开来。他们认为,人们正是在处理与自然关系的活动中才形成了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而只有在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人类对自然界的影响[4]。虽然人总是从自身需要出发对自然界进行索取和改造,但是人在改变自然的同时,也在改变着自身。作为人和自然中介的劳动,是“人以自身的活动来引起、调整和控制人和自然之间的物质变换的过程”[5]。换言之,没有劳动,任何自然的存在也就不需要再以人的主体价值为判断尺度;而只有劳动的本性被解放出来以后,人才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实现其主体价值。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视域下的社会道德问题
自人类社会产生以来,人们对于道德的追求和向往从未间断过。道德包含了人类对于美好生活的想象和追求,也是人类过上美好生活的一种柔性制度安排,它范物规世、扬善抑恶,促使人们避恶从善。但在当下,有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的现象却时有发生,有的甚至还比较严重。
(一)对自然生态的不道德
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由于科学技术水平不高、社会生产力水平低下、人口规模相对较小,人类作用自然的行为所引起的影响似乎无关紧要。但进入资本主义社会后,被迅速激发的生产力带来的不仅仅是人的利益的扩大化,也是人与自然矛盾的扩大化。在“眼前利益”的作用下,“征服自然,为我所用”的短视行为泛滥。恩格斯针对这种行为提出了严厉的警告:“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了报复。”[6]559-560
反观当下中国社会,“良心值多少钱一斤”的发问,直接让我们感受到在利益的驱使下,人与自然、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状态。虽然保护生态环境、构建美丽中国已成为全社会认可的价值追求和生态理念,但工业化的发展、市场利润的增加似乎又在一次又一次挑战人们对环境生态平衡的考量。生态问题不论在中国,还是在全世界,都没有得到根本性解决。2020年全球新冠疫情大流行再一次证明了自然界的确在对人类进行“报复”。伴随着人类越来越多地入侵动植物的天然栖息地,那些天然寄居于动物体内的微生物也就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入侵人体的机会。“自然的报复”正在向人类袭来,而人类却还沉浸在享受现代物质文明的快乐之中。这究竟是天灾,还是人祸,值得我们深思。
(二)对人本身的不道德
自然生态问题的背后往往是令人担忧的社会生态现状。人与自然关系的不和谐映射出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紧张。在现今的生产方式中,人的主体性正在过度发挥。自从资本主义工业文明以机器化大生产将全世界裹挟其内时,人类就开始以胜利者姿态高居自然之上,滥用自然资源以满足其无法遏制的物欲,并使人本身不断物化。于是,人与人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也被践踏和否定了。“这种自我的关注实际上把德性连根拔起了,它隐含着对于公共生活和他人福祉以及个人福祉的道德替换。”[7]在当今中国,一些不道德的行为不仅发生在经济领域,并且正在一步一步地蔓延到社会其他领域。道德低下等现象不仅给人们的精神文化带来了不良的影响,也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影响社会整体的公共生活。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思想对新时代道德治理的启示
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德治建设,强化道德约束,规范社会行为,调节利益关系,协调社会关系,解决社会问题。道德治理不仅内含道德建设的具体要求,更是对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的系统性构建。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从“人同自然的和解”“人同本身的和解”出发,为新时代道德治理提供了价值指引。
(一)确立尊重自然、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紧密结合的理念
呵护自然就是呵护人本身。只有尊重自然,重视生态价值,才能保证人的价值的实现。人是自然界产物,是自然界的一部分,因此,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而不是单纯地让自然界满足自己的需要,更不是征服和破坏自然。自然界在为人类提供生存、享受和发展所必需的资料的同时,也为人类提供了巨大的经济价值。因此,优化生态环境,将生态价值与经济价值紧密结合,有助于经济的高效、持续发展,促进人类物质财富的增长。日本企业家稻盛和夫曾提出过一个企业管理理念——“敬天爱人”。“天”就是道理,合乎道理即为“敬天”;以仁慈之心关爱众人就是“爱人”。因此,我们首先应使人们敬畏自然,尊重生命,当我们能够“摆脱自己的偏见,抛弃我们对其他生命的疏远性,与我们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我们才是真正的人”[8]。
(二)道德治理的主体包括执政党、政府、社会组织和公民个人
道德问题说到底是人的问题。人是道德危机的始作俑者,也是道德危机缓解及解决的实践主体。社会道德的缺失最终伤害的是人的生存与发展权益。社会道德终究要依附于现实的经济关系和经济活动。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9],“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整个道德的基础”[10]。可见,社会道德治理要以实现好、维护好、发展好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为目标和宗旨。而解决好当前中国社会中的道德问题,不仅需要执政党和政府的高度重视,更需要亿万公民的共同参与和支持。唯有多元化的主体广泛参与和协商共治,才能解决公共规则被破坏和公共利益受损等问题。
(三)构建以公共道德为基础的制度规范体系
在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中,“人同本身的和解”除了“需要对我们的直到目前为止的生产方式”[6]561进行变革外,还需要建立能够体现公平正义的生产组织。这就需要有能够协调各利益主体之间矛盾和冲突的制度规范作为保障。这些制度规范不仅仅包括法律、法规和规章,更深层次的,则是道德。道德是一种“柔性”的社会规范,离不开相应的制度保障。因此,应当构建以公共道德为基础的制度规范体系。只有这样,才能减少善与恶、道德与非道德的冲突,道德治理的规范体系才能逐步完善。
(四)推进“文以载道”之道德文化建设
马克思主义的生态思想认为,人与自然关系紧张的背后是人与人关系的紧张,是人与人利益矛盾的冲突。因此,要实现“人同自然的和解”,就必须实现“人同本身的和解”。为此,在对利益这根“敏感的神经”进行引导时,就必须首先树立起社会普遍认可的价值观,并开展与之相应的道德文化建设。文化是人类活动的精神部分,包括意识形态、社会意识和社会心理等。道德同样也是人类精神文明的产物。千百年来,中国形成了“文以载道”的传统,文化与道德相辅相成。文化为道德的传承提供了有形和无形的载体。在当前社会主义道德文化建设中,“文以载道”须“以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以利于广大人民群众自愿接受其所负载的道德价值,潜移默化地培养公民的道德人格、规范公民的道德行为,最终规范社会秩序,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