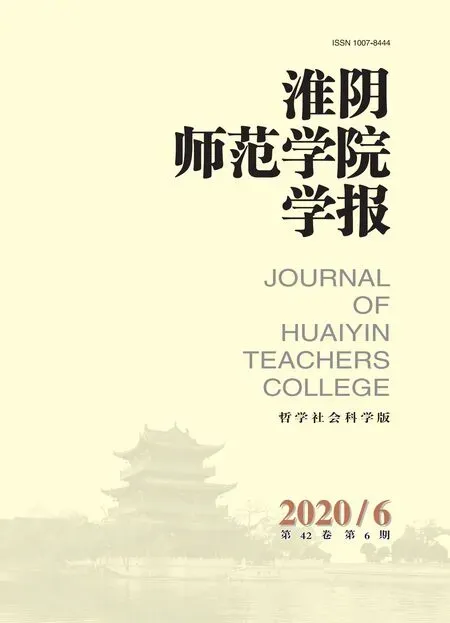修复合法性努力:晚清历史教育的政治认同书写
刘中猛
(淮阴师范学院 教师教育学院, 江苏 淮安 223300)
清军入关后,受到汉、回、苗等各族人民的强烈抵抗,国内民族关系主要表现为满族与其他民族间的冲突。清王朝建立全国政权后,建构政权合法性尤显急迫。于是清廷采取兴文教等多项措施来促进民族理解,缓和民族矛盾,消弭他族民众的抵抗,实现政治和社会稳定。
清初教化政策取得了一定的效果,“汉族始安,帝业始固。说者谓满清之命脉,全在于康熙一朝能以儒术笼络天下人之心者,非虚语也”[1],表明清初统治者成功地书写了治统与道统的合一,叙述了政权合法性,昭示民族冲突开始缓和与政治认同得到强化。诚如姚念慈所云:“清代统治者的高明之处,不仅在于满族的统治地位不可动摇,也不仅在于避免满族被汉人同化,更在于竭尽全力使主体民族,即被统治民族汉族,接受满族统治承继中原历代王朝的正朔,并承认这种统治的最大合理性与合法性。”[2]
晚清时期,政府通过康雍乾三世积累的治绩丧失殆尽。在外来入侵日益严重、国内改良和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情况下,再次遭遇政权合法性危机。
一、晚清统治合法性危机
“合法性意味着,对于某种要求作为正确的和公共的存在物而被认可的政治秩序来说,有着一些好的根据。一个合法的秩序应该得到承认。合法性意味着某种秩序被认可的价值——这个定义强调了合法性乃是某种可争论的有效性要求,统治秩序的稳定性也依赖于自身(至少)在事实上被承认。”[3]鸦片战争以降,清王朝治理国家能力逐渐式微,政府统治秩序逐渐不被认可,其“稳定性”也随着自身事实上的不被承认而失衡。
(一)政府与民众的隔阂
1840年,英国蓄意挑起了中英之间的战争,史称鸦片战争。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失败,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次抵抗外敌入侵失败。此后,在甲午战争、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清政府无一取胜。败北有着诸多原因,政府领导能力薄弱,不能强化民族意识和促进政治认同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因素。中国“政体基本上仍处于中世纪式,政府与人民各行其是”,而日本“当时已是一个现代化国家,民族主义意识使政府和人民团结成一个统一的整体”。[4]
政府与民众的隔阂并非与生俱来。鸦片战争爆发后,面临外寇初犯,家乡遭受侵袭,部分民众表现出较强的皇权认同和抵御外敌的决心,以为“英夷屡不安分,久犯天朝”,对“我皇上深仁,不忍加诛,且示怀柔”的恩赐“不知感恩”,[5]1称“我皇上体天地好生之德,容尔狗邦,通商交易”,斥其“不过贪利而来,有何知识”。[5]18但清廷告诫民众要“钦仰圣衷怀柔之至意,中外一体,方为孝子忠臣”,称抗敌活动是“贪吝无耻之士民,在此重地喧哗,横议扰众,殊属不成事体”[5]2,从而把自身推到了民众的对立面。
甲午之役中,一些民众置身于御敌之事外,甚至希望清王朝战败。英国驻天津总领事宝士德称:“我在这里经常听到中国人使用敌视朝廷的语言。就在几天前,北洋水师学堂里讨论取胜机会时,一个中国人说,我希望我们战败,那么会有一件可喜的事——朝廷寿终正寝。”[6]孙中山也有类似的回忆,“特达之士多有以清廷兵败而喜者。往年日清之战,曾亲见有海陬父老,问旅顺已失、奉天不保,雀跃欢呼者。问以其故,则曰:‘我汉人遭虏朝涂毒二百余年,无由一雪,今得日本为我大张挞伐,犁其庭扫其穴,老夫死得瞑目矣’”[7]222。这一方面体现了民众与政府的隔膜,另一方面也显示清政府在促进政治认同上的无力感,至少是成效甚微。
义和团打出“扶清灭洋”旗帜,这是“一个民族主义的口号”,“清”意指“大清国”即中国,“尽管这时候还有少数人坚持着‘反清复明’的狭隘民族认同的传统‘民族主义’,但,大多数人开始有了国家认同的意识,也就是对于‘大清国’的认同,这是下层民众的民族主义开始发轫的标志”[8]。清廷赢得了借助抵抗外敌来强化民族意识、增进政治认同、修复统治合法性的契机。但清廷轻易放弃了良机,将义和团玩弄于政治博弈之中,心怀鬼胎地把义和团推向抗敌一线,“成则可膺太上皇之位,败则抛汉人之命、割汉人之地、赔汉人之财帛而已,且汉人之力既弱,汉人之精神既疲,则驾御之之道亦易。吁!以端王等之心而言排外,其败不亦宜乎”[9]。这一败加大了清政府与民众间的裂痕,倡民族革命舆论愈盛。
(二)经济遇到寒冬
清前期财政收入以田赋为大宗,支出主要有兵饷、俸禄和河工等。鸦片战争后,财政收入以“厘金洋税为大宗”,支出主要集中于军需与赔款,赤字趋于严重。咸丰初年,“粤匪骤起,捻、回继之,国用大绌”,“府库已绌,而东南洪、杨之变,西北英法之役,掷款至巨”[10]112。同治“即位于多事之秋,军需之臣,实为前此所未有……每因军费之繁,而财用告匮焉”[10]113,加之赔款所需开支,如“拳匪祸作,赔款四百五十兆;数额之巨,为有历史以来所未见”[10]115,财政状况进一步恶化。
事实上,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财政收支已失衡。1839年,管理户部事务的大学士潘世恩领衔的奏折中提及当时财政亏空10 817万多两。[11]财政亏空已然成为晚清历史的常态。1909年,除受协不计外,各省岁入银26 321万9 700两1钱6分3厘,岁出银26 987万6 432两5钱9分6厘,亏空665万6 732两4钱3分3厘。[10]1061910年,清廷财政岁入银29 696万2 700多两,岁出33 865多万两,[10]107-108约亏空4 168万两。
为摆脱财政危机,清廷谕令开源节流。田赋作为清政府重要的传统财源,成为各省竞相逐利之场。巧立名目、过细的科则和浮收在晚清田赋征收中已属司空见惯,“各省田赋名目,最为繁琐”[12]394,“田赋科则甚繁,全省数百则或百十则,固属常事,而一县之中,亦有达数十则之多者”。冯桂芬曾谓:“再苏松各属田亩,科则繁猥,头绪纷如,苏州昆山县五十九则,元和县五十三则,长洲县五十二则,松江府虽不过四五则,却于各则内又分每若干亩准一亩,多至数等,故华亭县亦五十六则。其中有数亩一亩或数分独占一则者,万无此田必应完此粮,不可增不可减之理,徒滋书吏影射飞洒之弊。”而这种现象“不仅苏松为然,实则多处之通病”[12]354。科则如此繁多,以致“胥吏亦多不能辨其由来,明其标准”[12]397。
至于浮收,道光时“州县已有公然浮收者矣”,“漕粮之浮收,已成公开事实”,甚至各级官吏串通起来,强行征收。“浮收一事,不仅官吏利害一致,上官亦利其进奉,隐为后盾,官官相护,不虞有失,而竟以酷辣惨毒之手段,应付从事反抗之人,而浮收成为天下之通病,愈演而愈烈矣”[12]362-363。两江总督耆英也惊呼:“催科之术,则以帮费为名,捐款为词,假手书役,任意浮收,甚至每米一石,收米至三石内外,折钱至十千上下,每银一两,收钱至四五千文,小民手胼足胝,终岁勤动,所得能有几何?”[13]
晚清政府内外政策呈现出的低统治绩效,削减了其统治合法性基础,“晚清政治的腐败”和“最高统治者的昏庸无能”是民众对“政府丧失信心和信任的直接原因”,对“政府能力的置疑”促动民众“从文化和制度上寻找原因”,并影响其对政权的“政治文化合法性认同”。而“政府屡次改革的失败最终使人们彻底失去了改造传统政治文化、延续政治统治的信心”,“转而寻求革命来推翻其统治”。[14]
(三)各类运动的冲击
面对清廷统治乏力,吏治腐败,农民不断为生存而暴动反抗。1851年,洪秀全领导的太平天国运动由广西金田一隅始发,一路北上,迅疾攻克众多城池,在南京建立起与清政府对峙的政权。太平天国不但在军事上打击了清朝统治,还开展排满宣传,冲击其统治的文化根基。起事前,洪秀全就曾对洪仁玕说:“中土十八省之大,受制于满洲狗之三省,以五万万兆之花(华)人,受制于数百万之鞑妖,诚足为耻为辱之甚者。兼之每年化中国之金银几千万为烟土,收花(华)民之脂膏数百万为花粉……(犂)省或乌隆(黑龙)江或吉林为奴为隶乎!”[15]1852年,杨秀清等发布《奉天讨胡檄》,称:“予惟天下者,上帝之天下,非胡虏之天下;衣食为上帝之衣食,非胡虏之衣食;子女人民为上帝之子女人民,非胡虏之子女人民也。慨自满洲肆毒,混乱中国,以六合之大,九州之众,一任其胡行,恬不为怪,中国尚为有人乎!”[16]同时列数清朝破坏中国形象、衣冠、人伦、制度、言语的所作所为,号召汉人起来反抗。出于反抗清王朝的政治需要,太平天国重提华胡之别,藉反对民族压迫,否定了清政权统治的合法性。
随着甲午战败,民族危机进一步加深,维新才能救国逐渐成了以康梁为首新式知识分子的共识。为避免刺激清朝当权者,减轻变法阻力,改良派宣扬“满汉不分”“满汉同种”。1898年,康有为上《请君民合治满汉不分折》,指出:东西方各国之所以强盛,实因“合数千百万之人为一身,合数千百万人心为一心”,“凡语言政俗,同为国民,务合一之”,建议“立裁满汉之名,行同民之实”。他进而主张对外交往用“中华”来代表国家,“今定国号,因于外称,顺乎文史,莫若用中华二字”。[17]同年,梁启超发文提出平满汉之界,主张满汉融合,“以公天下之大义言之,则凡属国民,皆有爱国忧国之职分焉,不容有满汉君民之界也;即以家天下之理势言之,则如孪体之人,利害相共,尤不能有满汉君民之界也”,打破满汉界限是国家“自强之第一阶梯”。[18]康梁本欲表明改良并不是反对满族和清朝的统治,但将本享有特权的满族置于与他族同等之地位,实际上就是冲击了清朝统治合法性。
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认为只有推翻清朝政府,才能实现民族独立。革命派反满革命宣传主要是运用传统民族主义“夷夏”观进行的,即“合同种,异异种,以建一民族的国家”[19]。孙中山排满革命的最初表达,是兴中会入会誓词中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后同盟会章程明确了“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纲领。他对此解释道,“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中国之政治,中国人任之”,而“今之满洲,本塞外东胡。昔在明朝,屡为边患。后乘中国多事,长驱入关,灭我中国,据我政府,迫我汉人为其奴隶,有不从者,杀戮亿万。我汉人为亡国之民者二百六十年于斯。满政府穷凶极恶,今已贯盈”,所以要“覆彼政府,还我主权”,来“光复我民族的国家”。[7]296-297这番表达带有浓厚的“华夷之辨”色彩,将满人视为“夷”,排除出了中国人的范围。围绕“血缘、种族来做文章”正是革命派反满革命和民族主义表达的一大特色,[20]211在革命派中有着较大的市场,诸多革命党人皆秉持同样的思辨逻辑。如章太炎文章中充斥着“东胡”“逆胡”“满贼”“胡虏”“鞑靼”“异种”和“女真遗丑”等对满族的蔑称,提出为“中华种族”请命。[21]
从太平天国到洋务运动,再到维新变法和资产阶级革命,或以民族主义为宣传旗帜,用传统“华夷之辨”相号召,宣传“非我族类,其心必异”,或以改良为宣传旗帜,用“自强”“求富”相号召,都在某种程度上否定了清朝统治中国的主体资格,动摇了它的统治合法性根基。修复统治合法性成为清廷亟须解决的问题,而历史教育成为清朝政府重塑政权合法性、促进政治认同的支点之一。
二、清朝帝王叙述
1902年,清政府任命张百熙为管学大臣,“将学堂一切事宜,责成经理,务期端正趋向,造就通才,明体达用,庶收达人之效”[22]7。张百熙主持制定的《钦定学堂章程》,未及实施即被废止。1904年1月,张百熙、荣庆、张之洞修订了《钦定学堂章程》,对历史课程做了如下的规定:初小历史课程“要义”是“略举古来圣主贤君重大美善之事,俾知……本朝列圣德政,以养国民忠爱之本源”[22]295;高小“宜多讲本朝仁政,俾知列圣德泽之深厚,以养成国民自强之志气,忠爱之性情”[22]310;中学堂“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暨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22]321;初级师范学堂则要求“专举历代帝王之大事,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中国百年以内之大事”[22]404。
1906年3月,学部右侍郎严修代拟起草《学部奏请宣示教育宗旨折》,提出“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五项教育宗旨,获上谕批准,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由政府颁布的教育宗旨。“忠君”位列宗旨之首,称“东西各国政体虽有不同,然未有不崇敬国主,以为政治之本者”,“宜取开国以来列祖列宗缔造之艰难,创垂之宏远,以及近年之事变,圣主之忧劳,外患之所由乘,内政之所当亟,捐除忌讳,择要编辑,列入教科;务使全国学生每饭不忘忠义,仰先烈而思天地高厚之恩,睹时局而深风雨飘摇之惧,则一切犯名干义之邪说皆无自而萌”。[22]535
历史课程“要义”与教育宗旨对历史教育的规范要求十分相似,皆强调须“陈述本朝列圣之善政德泽”。究其原因,不过是晚清教育试图延续传统做法,极力赋予清朝统治者具有德性的色彩。因为德性“作为一种内化于统治者身上,而使之能够获得天命、组织政权的属性”,能够“有效的解释和论证现实政权为何具有统治权威的原因”。正因“民众相信统治者拥有超越常人的认知能力和道德自觉,并且也相信统治者会在这种德性的支配下实行对民众自身有利的行为,所以民众服膺于这样的德性统治”[23]。可见,历史教育叙述“本朝列圣德政”根本目的在于美化清朝统治,企图修复统治合法性的裂痕,强化政治认同,抵制民族革命,延续统治。初级师范学堂章程对此表述得最为直白:“尊君亲亲,人伦之首,立国之纲;必须常以忠孝大义训勉各生,使其趣向端正,心性纯良。”[22]400-401
在历史课程“要义”和“教育宗旨”规范下,历史教科书不乏赋予清代帝王神秘的天命色彩和美化其各种伟业的书写。如叙述满族祖先“为天女吞朱果所生,生而能言,体貌奇异。及长,天女锡之姓曰爱新觉罗,名之曰布库里雍顺”,太祖高皇帝“伟躯大耳,声如洪钟,长有武略,英雄盖世,国人号曰聪明贝勒”[24]151-152,努尔哈赤“龙兴于满洲”“有雄略,征服近傍诸部落,遂称帝,灭叶赫,破明军”[25]55,“聪武善用兵”[26]74。
康雍乾朝的文治武功更成为历史教科书浓墨重彩书写的内容。如描写康熙“内则削平大难,巩固统一之基础,外则战胜强敌,恢张帝国之威信,外交军事,所在奏功,而其文治亦斐然比于汉唐之盛”。面对“明室遗臣多有存者,士大夫或以逸民自居,著书言论,常慨然有故国之思”的情况,清廷“知此辈当以恩礼罗致之”。1678年,康熙“诏举博学宏儒,备顾问著作之选,令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在外督抚布按及学政,各举所知以应。于是内外诸臣疏荐送部,诏户部月给俸廪”。次年,“集诸被举者于体仁阁,试以诗赋,得士五十人,俱授为翰林院官,纂修《明史》。由是海内向化,舆论一致”。[24]225乾隆继承了康熙礼士笼络人心的做法。1736年,刚继位的乾隆就“循康熙年间故事,开第二次博学鸿词科,取刘纶以下十五人,并授翰林院官”。翌年,“又补试未预考者,得万松龄以下五人,授官如前”。1750年,再次“特旨令大学士、九卿、督抚选举潜心经学之士,得陈祖范、吴鼎、梁锡玙、顾栋高等四人,并授国子监司业。车驾巡幸所至,辄召诸生试诗赋,与以科目。朝廷所以尊礼学人者既如是其优”[24]266。
由此,历史教育完成了天命、明君、贤能、礼士和德化的帝王形象书写,传递了统治合法性的声音,以冀增强政治认同。
三、孔子及儒学叙述
汉代以后,儒学成为正统思想。历代政权对孔子及其后裔的谥封和祭孔成为一种特殊而重要的仪式,持久一贯的王朝祭祀制度,一直密切关联着“尊孔”本身与现实政权的政治“合法性”[27]。这就意味着“祭孔已转化为政治权威合法性的根源,成为统治者极力攀附、垄断的‘道统符号’”[28]。清初帝王深谙孔子的“道统”象征意义,政权建立之初就开始推行尊孔活动,因为“只有被普遍尊奉的文化规范所支持,政治支配才能成功,政府行为也才能被普遍接受,这几乎是不言而喻的道理”[29]。
对孔子及儒学的书写自然亦为晚清教育重要的内容,这主要体现于“读经讲经”和“史学”课程中。“读经讲经”课程侧重于儒学经典解读,清廷极为重视,“中小学堂宜注重读经以存圣教。外国学堂有宗教一门。中国之经书,即是中国之宗教。若学堂不读经书,则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所谓三纲五常者尽行废绝,中国必不能立国矣”[30]。因为经学已不是“一般的学术理论,而成为承载政治合法性依据的文本”,对经的解释成为“论证本朝统治合法性与阐述本朝政治理论的重要政治活动”[31]。
癸卯学制规定,初小历史“当先讲乡土历史,采本境内乡贤名宦流寓诸名人之事迹,令人敬仰叹慕,增长志气者为之解说,以动其希贤慕善之心”[22]295。中学堂和初级师范学堂除了“列圣德政”外,皆当“讲古今忠良贤哲之事迹”。当政者希冀学生做到“敦品养德,循礼奉法”,“谨言慎行,贵庄重而戒轻佻,尚和平而忌暴戾”,养成“良善高明之性情”,不“萌邪妄卑鄙之念”[22]321。教育宗旨也强调“孔孟为中国立教之宗”,教育“务须恪遵经训,阐发要义,万不可稍悖其旨,创为异说”[22]400-401。
晚清历史教科书对孔子的叙述主要集中在他的生平和思想概貌,称儒学“以仁义为道之大本,以礼乐为教,戒骄謟放纵,以躬行实践为旨”,赞孔子“博学而多能,诗书六艺,无所不通”[26]16,是“儒家之祖”,“主教育,务进化,慨周道之衰,修春秋以定名分。集弟子而讲修身治国孝悌忠信之道”,培养“弟子三千余人,通六艺者七十二”[25]7-8。并以高度评价的语言书写了孔子圣人的形象,“历代帝王奉之为先师,释奠用王者之礼,列论语于学官”,“孔孟之道,世称之为儒学,为中国政教之本”[25]8-9,“圣人之道,大而能博,因材因时,言非一端,而要归于中正。九流之精,皆圣学之所有也。九流之弊,皆圣学之所黜也。故古今言道德政教,必折衷于孔子”,孔子“教以孝悌为本,以忠恕为方,而推行仁道于天下。故其教始于修身齐家,终于治国平天下,……或谓其功贤于尧舜……孔子之道,永为中国政教之本”,“后世奉圣人之教者,号为儒家”。[32]16-17
叙述帝王崇儒亦是历史教科书的重要内容。汪荣宝的《本朝史讲义》专设“理学之表章”一目,称“圣祖既优礼儒臣,又欲统一天下之言论思想”。1685年,诏“各省督抚学政购求遗书,汇送礼部”,“谕:‘朕披阅载籍,研究义理,凡厥指归,务期于正。诸子百家,泛滥奇诡,有乖经术。今搜访藏本善本,惟以经学史乘实有关系,修齐治平助成德化者,方为有用。其他异端稗说,概不准录’。”又“宏奖理学,表章程、朱,御著《几暇余编》,其穷理尽性处,虽夙儒耆学莫能测。尝出《理学真伪论》以试词林,又刊定《性理大全》《朱子全书》等书。特命以朱子配祀十哲之列。当时如李光地、汤斌等,皆以理学耆儒跻显仕。故宋学昌明,世风醇正云”。[24]225
晚清历史教育主要配合“读经讲经”,叙述儒学的一般性内容,作为支撑经学学习的背景性知识,希冀实现“动其希贤慕善之心”的历史课程目标,尝试再造政府治统和道统合一的形象,并通过学习圣贤的修身与义理促进民众的皇权认同,泯灭民众的反抗意识。
四、祖先黄帝叙述
我国历史上汉民族建立的政权通常以大一统观念作为政治合法性基础,当遭遇少数民族威胁时,“夷夏之辨”就会抬头。少数民族建立全国政权后往往会努力消解“华夷之辨”,借用大一统观念换取正统统治地位。[20]31晚清历史教育试图通过祖先黄帝的叙述,淡化满汉畛域,重建合法性统治。
癸卯学制规定历史课程“陈述黄帝尧舜以来历朝治乱兴衰大略”[22]310,“知中国文化所由来”[22]295,向学生传递中国历史和文化源头始于黄帝尧舜,民族有着共同的祖先。在共享历史记忆中,促进民族一体认同,消弭民族隔阂,抵制民族革命。
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大都将中国历史溯及三皇五帝或者更早时期,展现了中国悠久的历史和炎黄系共同祖先的历史记忆。京师大学堂教习屠寄在他的《京师大学堂史学科讲义》中详细叙述了黄帝的治绩,“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作舟车以济不通”,“置左右大监”,“经土设井”。又“命仓颉作书,大挠作干支,容成作《盖天历》及《调历》。设灵台,立占天之官,命隶首作数,伶伦作律吕,荣猨作十二钟,大容作《咸池》之乐。染五色为文章,以表贵贱。制冕旒,垂衣裳,伐木构材,建筑宫室,上栋下宇,以辟风雨寒暑,作合宫以祀上帝。范金为货,作金刀五币,以御轻重。咨于岐伯,而作《内经》。元妃西陵氏,教民育蚕”,终“一切制作,粲然大备”,疆域“东至于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于空桐,登鸡头。南至于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屠寄还称“我四亿之人亦自认为黄帝之子孙”[24]10-12,显然这“四亿”是包括满汉在内的中国各民族。
京师大学堂另一教习王舟瑶在《京师大学堂中国通史讲义》中则叙述了黄帝治下的各种发明创造,“其史苍颉见鸟兽蹄迒之迹,初造书契。……其时史官有沮诵、苍颉,则史学亦于此始矣。正名百物,则名学之祖也。使羲和占日,常仪占月,臾区占星气,[伶]伦造律吕,大挠作甲子,隶首作算数,容成综此六术而著《调历》。垂衣裳,作舟楫,为弧矢。造指南车,制陈法,演握奇图。布九州,置十二图”。黄帝“披山通道”开拓了疆域,“大常察乎地利,奢龙辩乎东方,祝融辩乎南方,大封辩乎西方,后土辩乎北方,以及天老、力牧、太山稽、常先、大鸿,皆有专门之学、特别之技,故学术思想一时焕发,遂洗草昧之风矣”[24]64。
陈懋治的《高等小学中国历史教科书》叙述了黄帝“兵熊四方”,“大开疆土”,“东至于海,西抵崆峒,北逐獯鬻,南驱苗民于江淮。作九数,制文字,造律度量衡,定冕旒衣裳,作舟车货币,始兴蚕桑”[26]8。陈庆华的《中国历史教科书》对黄帝的叙述虽仅有两三行,但明确评说黄帝“有英姿大略”,“数征四方诸侯”后建立“一大帝国”,为“中国一统政治之始基”[32]1-2。
安东尼·D.史密斯认为族裔共同体有六个主要特质,“一个集体性的适当名称,一个关于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一个或多个与众不同的共同文化要素,与一个具体的‘祖地’的联系,在人口的主要组成部分间存在团结感”[33]。晚清中国历史教科书对祖先黄帝的叙述无意识地触及了“共同祖先的神话”“共享的历史记忆”和“具体的‘祖地’联系”等要素,成为构建中华民族族裔共同体的基础,这些叙述其意在于激发民族感情,有助于促进中国民族一体的认识,增强政治认同。
五、结语
整体言之,晚清历史教育体现了清政府“忠君”“尊孔”的办学宗旨,塑造了清代帝王德政形象,注重皇权认同。教科书编写时“谨遵教育宗旨以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为主而尤详于宪政”[34],向学生传递“我生大清国,我为大清民”[35]的观念。努力实现政府不准学生“干预国家政治及本学堂事务,妄上条陈”,“离经叛道,妄发狂言怪论,以及著书妄谈,刊布报章”的教育规条[22]482。
但历史教育并非完全秉承了晚清政府的教育精神,如对“国家”的理解,教科书编写者就相异于清政府,“清政府的‘国家’更多是指朝廷,爱国首要是维护清廷统治;而编写者显然已经脱离传统的朝廷意识,具有近代国家的意识”[36]。晚清历史教科书中既有像叙述李自成时用“窜死”和“流寇”、太平军用“长发贼”这样的词语,也有像叙述史可法时用“尽瘁”、鲁王之死用“薨”之词,称史可法“为人廉信,与下均劳苦。其督师也,行不张盖,食不兼味,寝不解衣,日夜以报仇雪耻为念。每缮疏,循环讽诵,声泪俱下,闻者无不感泣。而权奸内哄,悍将外争,凡所经画,百不一就。卒至兵顿饷竭,志决身歼。时人比诸文天祥云”。[24]179
晚清历史教育与清政府教育精神既分又合的状态,表明近代社会转型之际,历史教育在传统与现代间的困惑与选择,也表明清政府藉历史教育为支点,极力修复统治合法性中修而不复的窘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