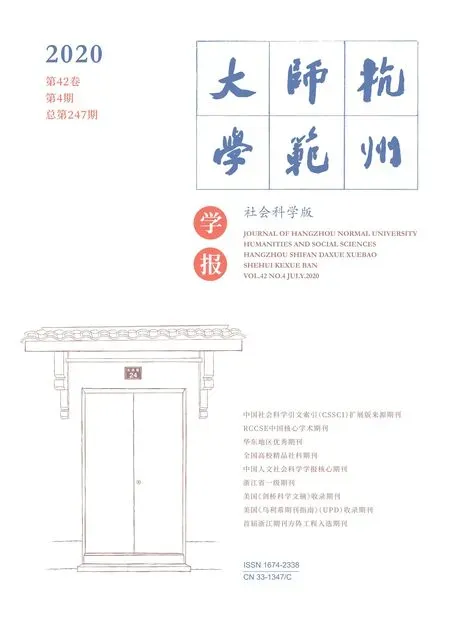儒学本体论如何统摄科学?
——以“良知坎陷”为中心
韩立坤
(南京林业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江苏 南京 210037)
科学时代,儒学何为,这是现代新儒家聚焦之主题。牟宗三试图重建形上学以处理二者之关系。他用“良知坎陷”为科学提供“儒学本体论承诺”,以此“新内圣”为科学民主之“新外王”提供超越依据。但其用“本体论之体用模型”去统摄科学,无法化解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之内在冲突。若将之修正为“价值论之体用模型”,依据良知的伦理价值逻辑,建立“儒家的科学解释学”模型,既可以保证价值选择意义上“坎陷”的合法性,又可实现儒家价值形上学对科学之“超越统摄”。
一、科学与儒学的理性向度差异:架构表现与运用表现
牟宗三认为,虽然儒、释、道三教的“共同的问题”,就是知识问题,但古人既并不关心知识及合法性问题,又轻视技术发明创造,从而认识论、知识论不发达,亦发展不出科学。通过比较,他发现中国文化关注内在德性之“内容真理”,西方文化注重经验真相之“外延真理”,二者源于“心智”(mentelity)即理性之不同运用方向:中国文化注重天人合一、物我合一、体用合一,乃“理性之运用表现”;西方文化注重天人二分、主客二分,将万物推开以做分析研究之对象,乃“理性之架构表现”。[1](P.161)而“凡是运用表现都是‘摄所归能’、‘摄物归心’。这二者皆在免去对立:它或者把对象收进自己的主体里面来,或者把自己投到对象里面去,成为彻上彻下的绝对。……这里面若强分能所而说一个关系,便是‘隶属关系’。……而架构表现则相反。它的底子是对待关系,由对待关系而成一‘对列之局’。是以架构表现便以‘对列之局’来规定。”[2](P.52)
正因理性运用不同,西方文化体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中国文化体现“综合的尽理之精神”。此“综合”乃是就中国文化“上下通彻,内外贯通”之观念说,“尽理”则是从“尽心、尽性、尽伦、尽制”说。可见,中国文化始终关注伦理道德与意义价值,而轻视经验器物。尤其受儒学影响,多基于良知仁体秉持“智的直觉”,将本该作为科学研究对象的客体“收摄”进所创造的有机主义、整体主义、道德主义的宇宙观。因而主体与客体之“对列关系”始终无法建立,经验器物无法获得独立性,而成为研究对象。相比科学以“观解理性”或“理论理性”来观察事物,中国哲学尤其是儒学惯用“实践理性”去“观照或寂照”万物,其特点如下:(一)是非经验的,既不借助耳目感官,又不受耳目感官限制;(二)非逻辑数字的,既不是以理论形态出现,不需通过辨解的推理过程,亦不需要逻辑的程序和数学的量度。此理性作用是基于“道德心灵”展开,追求“德性之感召”或“德性之智慧妙用”,“知体明觉之感应(智的直觉,德性之知)只能知物之如相(自在相),即如其为一‘物自身’而直觉之,即实现之,它并不是把物推出去,置定于外,以为对象”。[3](P.121)而既然此种特殊“心智”运用,“既不经由经验,又不经由逻辑数学,当然不能成科学知识”[2](P.50)。
如上所述,牟宗三为中西文化寻获了两种理论逻辑:体现“综合的尽理精神”之中国文化擅长“内容真理”(形而上学、道德哲学),主要受“理性的运用表现”限制;体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之西方文化擅长“外延真理”(科学、逻辑学)得益于“理性之架构表现”。两种学问本无价值高低,但中国转型急需科学,为此,思考“如何从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如何能由知体明觉开知性”,始终是中国哲学彰显合法性之重要课题。
而牟宗三虽延续晚清以来基于儒学天道心性框架统摄、安置科学之意识,且亦从形而上学之“体”“用”框架入手,但却超越前人对科学与儒学关系之外在拼凑式认识:如魏源、冯桂芬、薛福成、严复等人设定的“技”(科学)—“道”(儒学)关系。表现在,牟宗三虽同样坚持以儒家形上道德本体统摄形下科学,但他却试图“彻底反省外延真理背后那个基本精神”——科学理性[4](P.37),进而在儒家形上本体与科学理性间建立逻辑关系。
不过,他仍没能超越儒学内圣开外王之老路。事实上,在写作《理性的运用表现与架构表现》之前,牟宗三就明确:“中国要在现世界站得住立得起,必须由内圣开出外王处有一转折,绕一个弯,使能显出架构表现,以开出科学与民主,完成新外王的事业。”[5](P.97)而在《政道与治道》书中,他开始明确将科学、民主置于儒家内圣外王逻辑之中,指出:“运用表现自德性发,是属于内圣的事。讲内圣必通着外王。外王是内圣的通出去。”[2](P.54)但根本问题在于,古代外王内涵中,并不包含科学、民主这些“特殊结构”“材质条件”。为此,就需将此新“结构”、新“材质”与道德本心建立理论关联,即从理性之“运用表现”转出“架构表现”,将儒学“道德理性”转出科学“观解理性”。
二、认识心如何可能:“一心开二门”
儒家形上学乃天道心性相贯通之道德的形而上学,其观念表现为“仁智合一而以仁为笼罩者”;而“智的全幅就是逻辑、数学、科学”[6](P.144),为此,儒学必须将“仁智合一”观念“转折一下”,以开出智心(科学心、认识心)。但问题在于,作为本体之本心良知,仅具有道德规定性,而与科学理性相冲突、相违背。为此,牟宗三从佛学“一心开二门”与康德的“两层存有论”模型中,寻求理论支持。
佛教《大乘起信论》中言“一心开二门”,实质是一种形上学的本体论。一心,即本体——“如来藏清净心”;二门,即“生灭门”和“真如门”。牟宗三以此“二门”来对应现象世界和形上世界:认识现象世界的是认识心;认识形上世界的是超越心。而“生灭门”又相当于康德所说的“感触界”(phenomena),“真如门”则相当于“智思界”(noumena)。他还受康德影响,将科学称为“执的存有论”(现象界),将儒学称为“无执的存有论”(本体界)。
通过上述界定,他即将认识心或科学心与经验界或现象界,从中国哲学道德宇宙观中分列出来。但问题是,认识心是与道德心完全不同之理性能力与观念系统。具体言,“认识心的全相”包括“直觉的统觉”之心发展为“客观的心”或“逻辑的心”的过程。因此,其实际包含两个维度:一个是基于时空、范畴的“直觉的统觉之心”,其以经验现象作为对象;一个是使得千头万绪、千变万化的经验现象得以贞定,使其客观化、规律化、系统化的客观逻辑心。“直觉的统觉之心”是客观逻辑心的必要基础。[7](P.489)两维度之认识功能,共同为科学认识得以可能提供基础。
显然,上述认识心之能力绝非儒家道德心、伦理心所具备。也即是,牟宗三必须面对“道德本心实体→本心自我‘曲通’→认识心即科学理性(1)包括“直觉的统觉之心”(类似认识论意义上的感性认识)、“客观逻辑心”(类似认识论意义上的理性认识)两维度。→科学知识”的复杂逻辑。所以,“一心开二门”并非“横列之平行关系”,而是“纵贯之体用关系”。良知本心“开出”认识心之问题,亦非认识论问题,而是形而上学之问题(2)将认识心置于形而上学之中,牟宗三还使用了“两层存有论”的理论框架进行解释。认识心对应的是“执的存有论”,其理论系统表现为科学,道德本心对应“无执的存有论”,其理论系统表现为形而上学。。为此,牟宗三亦明确,对客观认识心而言,“逻辑理性不能保证之,必须有一超越形上学担任之”[8](P.419)。
但“惟精惟一”之良知本心,乃是天道心性贯通之德性范畴,认识心之“观解的”、“架构的”思维,则坚持主客对立原则,二者显然不类。牟宗三亦坦言:“德性,在其直接的道德意义中,在其作用表现中,虽不含有架构表现中的科学与民主,但道德理性,依其本性而言之,却不能不要求代表知识的科学与表现正义公道的民主政治。而内在于科学与民主而言,成就这两者的‘理性之架构表现’其本性却又与德性之道德意义与作用表现相违反,即观解理性与实践理性相违反。即在此违反上遂显出一个‘逆’的意义。它要求一个与其本性相违反的东西。这显然是一种矛盾。它所要求的东西必须由其自己之否定转而为逆其自性之反对物(即成为观解理性)始成立。”[2](P.56)这样,如何既保证儒家德性本体之超越地位,又可从道德心转出认识心,从“德性”(道德理性)“逆”着转向本与其“违反”的“知性”(科学理性),就是搭建儒学与科学内在关联的核心要义。
三、科学的“本体生成论承诺”:道德实体自我“坎陷”
儒家之良知本心,历来被视为可生化万物的无限的、绝对的、必然的道德实体。作为其彰显者与实践者,道德心亦能呈露无条件之道德意识,践行无条件之定然命令,推动无条件之道德实践。自此而言,超越实体即是道德心。而道德心之能力,即是“不虑而知、不学而能”之良知良能。还原此形上学逻辑,道德实体乃是理论上之“必然”,道德心乃是本体必然规定性之普遍现实化,是为“本然”,而良知(知体明觉)乃是必然本体之普遍属性,在具体时空中之具体呈现,是为“实然”。按照牟宗三对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之区分,道德实体是形上学本体,道德心是本体在现实世界的普遍样态,而良知则是此样态之具体能力呈现——道德理性。
在古代儒家中,对此“道德实体”→“道德心”→“良知(道德理性的仁智合一观念)↔经验”之逻辑论域尚未形成明晰之界定。尤其是古人多从良知良能去论证本心之先验性,因而在赋予良知能动性的同时,消解了其本该具有之经验面向;而儒学良知本体若要与认识心建立理论关联,就表现为以下逻辑:“道德实体”→“认识心”→“科学(观解理性的对列观念)↔经验”。这样,先验之良知实体与经验之认识心如何关联,就成为核心环节。为此,牟宗三提出良知“自我坎陷”(self-negation)。
(一)“良知”与“坎陷”的本意
不过,在阐述“良知坎陷”时,他不断论说从道德心开出认识心,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理性,因而又始终给人如下错觉:一是,道德心就是超越本体,认识心是经验产物,因而上述形而上→形而下的“必然→本然→实然”的本体现实化逻辑,就变成“必然→实然”的逻辑断裂。二是,道德心并非超越本体,而是本体现实化的普遍规定性。这样,“坎陷”说就会遭遇道德心(心的普遍道德规定性)→认识心(心的个体时空中的经验面向)的解释困境。
而欲准确厘清“良知坎陷”,首要问题是把握“坎陷”之意。事实上,在20世纪40年代末完成的《认识心之批判》一书中,他说:“理解陷于辩解中,始能成知识,而陷于辩解中必有成就其辩解之格度。是以格度之立全就理解之坎陷一相而言之。此一坎陷是吾人全部知识之形成之关键,是以论知识者皆集中于此而立言,寖假遂视此为全部理解相状之所在,而不复知其只为一坎陷之相状。”[8](P.196)此“坎陷”,仅是从认识论之维度去讨论认识何以可能的特殊概念,通过“坎陷”,理性能力开始聚焦时空、逻辑、概念、命题等科学知识系统得以可能的基本要素(3)颜炳罡也就此认为,牟宗三在《认识心之批判》中理解之坎陷,主要是理性思维之运用或起用,所以坎陷的全过程,就是知识的完成过程。参见颜炳罡《整合与重铸——牟宗三哲学思想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171-172页。。可见,“坎陷”之落脚点,正是科学知识得以可能的现实时空、经验对象。
其次,要把握能够“开出”认识心即科学理性的“良知实体”之本意。牟宗三视儒家为“德性之智”“超越之智”,而科学乃“知性之智”“分解之智”。而与科学“分解之智”相对,儒学又可谓“圆智”。他指出:“因为圆智神智是无事的。知性形态之智是有事的。唯转出知性形态,始可说智之独立发展,独具成果(逻辑、数学、科学),自成领域。圆智神智,在儒家随德走,以德为主,不以智为主。……智只是在仁义之纲维中通晓事理之分际。……一个文化生命里,如果转不出智之知性形态,则逻辑、数学、科学无由出现,分解的尽理之精神无由出现,而除德性之学之道统外,各种学问之独立的多头的发展无由可能,而学统亦无由成。”[1](P.172)也即是,作为一种道德理性的“良知”,其本是对应“仁义之纲维”之类的经验去呈现。
可见,“良知坎陷”本意是基于“道德理性”转出“科学理性”,进而开出科学经验。而本为“仁智合一之心”若要转出“认识心”,就要回答“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之逻辑关系问题。牟宗三承认,与古代由“道德理性→道德实践”之“直接实现”不同,良知本心在面对经验现实、现象世界时,要“向下曲折一下”方可转出“知性”。也即是,两种理性间之关系,并非实然的“直接实现”,而只能是“间接实现”。[9](P.33)
(二)两类“理性”冲突与“辩证发展”
显然,儒学与科学均是理性之表现,道德理性摄物归心,科学理性与物为对,自然不存在谁开出谁的可能。但为转出认识心,就必须依靠理性主体自身“把‘所’与‘物’推出去,凸显出来,与自己成一主宾对列之局”[5](P.102)。将以往消解于道德宇宙中之万事万物的个别相、差异相、生灭相凸显出来。在《现象与物自身》书中,他也说:“知体明觉之自觉地自我坎陷即是自觉地从无执转为执,自我坎陷就是执,坎陷者下落而陷于执也。不这样地坎陷则永无执,亦不能成为知性(认识的主体)。”[3](PP.122-123)
问题在于,儒家的“知体明觉”根本是作为形上本体的良知本心或道德实体的现实呈现,其本质是知善知恶知是知非的道德理性。作为“坎陷”之主体,其有且仅有道德的规定性。因此,良知(道德理性)“坎陷”出“认识心”(科学理性),哪怕是他运用了含混与模糊的“曲通”“转折”字眼,来强调道德心与科学心之关系,是“在曲通之下,其中有一种转折上的突变,而不是直接推理”,却始终无法解决两种理性能力间之理论张力。
按照牟宗三所说:“从理性之运用表现到架构表现,是转折上的突变,不是直线之推理,故虽说架构表现必以运用表现为本,但直接却推不出来。……凡直接推理可用形式逻辑之方式把握之,但转折上的突变,却是一辩证的发展。”[5](P.100)而可依据“辩证的发展”开出科学理性之主体,正是超越的良知本体。他还说:“知体明觉不能永停在明觉之感应中,它必须自觉地自我否定(亦曰自我坎陷),转而为‘知性’。此知性与物为对,始能使物成为‘对象’,从而究知其曲折之相。它必须经由这一步自我坎陷,它始能充分实现其自己,此即所谓辩证的开显。”[3](PP.122-123)可见,“坎陷”本质是形而上之实体自我发动的革命,此革命它是“在自己而又对自己”,以及“它在跃起之自觉中建立其自己,同时即在此中客观化其自己”。[8](PP.107-108)
显然,牟宗三之良知“坎陷”认识心,并非两种理性之“平列”,而是“内在贯通”意义上的形上道德实体开出形下科学功用之“客观的实现”。只是,此一实现,并非一般的“本体生成论”逻辑或“存在体用论”逻辑所能胜任。这是因为,若按上述逻辑,良知“坎陷”认识心:“德性实体”(良知)→“认识心”→“科学(观解理性的对列观念)↔经验”。这样,认识心就作为形上实体与形下经验之“逻辑中转”或“过渡环节”存在,亦符合“坎陷”乃是良知面对经验现象开出科学理性之流程。但随之遇到的问题在于,认识心从“必然”→“本然”→“实然”的本体生成逻辑中获得了“本然”地位,认识心就与道德心处于同一逻辑维度。显然,这不但直接消解了道德心对认识心之主宰、范导与统摄能力,亦凸显出儒家内圣开外王式的“本体生成论”逻辑或“存在体用论”逻辑在良知“坎陷”设定中之错位。
(三)“主体之能”
而帮助我们理解“坎陷”逻辑的,是牟宗三强调良知开出认识心,绝不是直接符合“逻辑推理”的“主观实现”,而是一种完全不同的在良知本体与科学观念间建立“曲通”关系,运用一种特殊逻辑所建立的“客观实现”。[2](P.56)在笔者看来,学界之所以围绕“良知坎陷说”聚讼不已,正是没能准确理解牟宗三所立论之特殊逻辑。而回到此说之焦点,“坎陷”一词乃是源自《周易·说卦》的“坎,陷也”。一般易学研究认为,坎卦之卦象,有上下贯通之意。显然,牟宗三正是针对百年来儒学始终遭遇科学“拒斥”与“驱逐”之困境,而试图将二者之“横列”冲突转为“纵观”之顺成,从“形而上学”之高度去建立儒学与科学之理论关联。
但是他基于儒学良知本体论之话语范式来解释良知“坎陷”,始终给人以良知本心“转生”“转出”科学知识之强为之感,让人对这种“本体生成论”逻辑以及“内圣开外王”的道德理想主义充满怀疑。余英时批评牟宗三过于依赖“超越的证悟”,将儒学变为“道德主义”。林毓生认为以科学实存为前提的“良知坎陷”只是把结论预设在前提之中的“循环定义”。傅伟勋认为“坎陷”说“仍不过是张之洞以来带有华夏优越感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这老论调的一种现代式翻版而己,仍突破不了泛道德主义的知识论框架”[10](P.448)。景海峰批评其根本是:“一种观念提纯式的运作,没有了历史真实,没有了当下情景,只剩下一大堆抽象概念的博弈和滑转。”[11]林安悟也认为“良知自我坎陷”乃是使用了“存有的发生学方法”,是采用了一种倒退论证的方式,这个方式本身是一种“理论的次序”,而非科学实践的“发生的次序”,而林安梧本人则主张放弃对理性的过度依赖,放弃对科学理性之理论建构,而是采用“学习的次序”,与科学平等对待。蒋庆批评牟宗三将良知从生命证悟的精神境界具化为认识论上的“理性概念”,将良知的“呈现”物化为“生成”,“良知坎陷”最终背离了儒家良知学。杨泽波则从体欲、认知、道德等维度去理解,将“良知坎陷”视为“道德坎陷”。
事实上,学界在讨论“良知坎陷”时,忽略了牟宗三的“主体活动之能”说。也即是,他搁置了“良知”实体的“生化”之意,而仅从道德理性之求善、求好、求真为科学之出现提供“理性的接引”,他说:“诚心求知是一种行为,故亦当为道德理性所要求,所决定。无人能说诚心求知是不正当的,是无价值的。……既要求此行为,而若落下来真地去作此行为,则从‘主体活动之能’方面说,却必须转为‘观解理性’(理论理性),即由动态的成德之道德理性转为静态的成知识之观解理性。这一步转,我们可以说是道德理性之自我坎陷(自我否定):经此坎陷,从动态转为静态,从无对转为有对,从践履上的直贯转为理解上的横列。”[2](PP.56-57)
此解释同样是一种“本体生成论”逻辑,只不过,此种生成论无需从作为形上本体的道德实体那里获得逻辑依据,而仅是从人之求好求善之理性能力立论。显然,此种角度的“坎陷”在现实维度更合理。否则,我们就无法回答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后发国家,能够学习、引进科学技术,实现社会科学化、技术化之显著成就。但是,这种“主体之能”不过是承认儒家道德理性有转换为科学理性之理论上的可能性。并且,仅有“主体之能”,不过是科学产生之“形式的必要条件”,而非“实际的充足条件”。否则亦无法解释恰恰是非儒家文明主宰与影响下之生存共同体,才率先发明科学之基本事实。
所以,从”本体生成论”与“内圣开外王”逻辑去理解“坎陷”,始终会遇到如下问题:
1.科学理性的独立性难以保证。牟宗三乐观地认为,道德理性转出科学理性后,即“暂忘”与“退隐”,以赋予科学理性独立性,但无论是经验道德观念抑或超越道德实体,均会始终笼罩在科学人格之上。受其影响,儒家道德宇宙观与科学宇宙观在“天人合一”与“物我两分”、“万物有生”与“研究实验”、“应然判断”与“实然解释”间之冲突,很难得到化解。
2.若真正保障科学与科学理性之独立性,就要真正做到各种良知观念在现实维度的“暂忘”与“退隐”。但这同时会出现如下问题:或者道德理性之内圣为确保新外王之独立性而丧失原有的普适影响,或者新外王遵照自身之“分解的尽理精神”而形成独立的理性王国,而走上与古代圣王仁政的外王学的对立道路。所以,科学时代,依然坚持儒学内圣外王之义理架构,并试图重释新内圣的做法就多此一举了。
3.即便不考虑“主体活动之能”对儒学内圣外王逻辑之消解,其问题仍在于,显然不止是儒家文明或儒化社会才具此种“主体之能”。由此,即便有此理性能力,亦与真正运用科学、认识科学、创造科学没有必然联系。所以,即便道德理性“坎陷”后具备科学理性,但仍然要承认:“有了德性,亦不能直接即有科学与民主政治。”[2](P.55)可见,“坎陷”之后,道德良知与科学本身仍处于逻辑的潜在性与可能性关系中。
四、“价值体用论” :儒学“统摄”科学的另一种选择
“良知坎陷”本意是以形上学实现儒学良知本体对科学之“超越的统摄”(林安梧语);而通过上文分析,笔者认为,“本体生成论”或“存在体用论”式的“坎陷”,并不能实现这种“超越统摄”之理想。根本上,以良知本体“保住科学知识的必然性(necessity)”,已然溢出了其解释效力之范围。为此,我们可探索从“超越性生成”转向“超越性规范”,即基于儒家一贯的“价值优位性”原则,以知识价值、行为判断维度的价值本末逻辑或价值主次逻辑,提供另一种“体用论”模式——“价值体用论”,从而既可以化解道德理性与科学理性之张力,又可以激发儒家“道德的形而上学”之时代生命力。
在此“价值体用论”中,依然可采用“体—用”框架作为形上逻辑。此“体”,依然是儒家天道心性相贯通的良知本心,此“用”依然是科学观念、科学知识、科学实践。只是,“价值体用论”范式中,并不以“先验生成”式的“本体论承诺”为主题,而是以“后验规范”式的“价值论判断”为核心。作为科学价值判断之“体”,良知本心,更类似贺麟的“逻辑意义的心”,是“理想的超经验的精神原则”与“经验行为知识以及评价的主体”。只有从此种意义,才可说此良知本心“乃为经验的统摄者,行为的主宰者,知识的组织者,价值的评判者”。[12](P.131)才可说此良知本心既是文化的创造者,又是文化的统摄者、主宰者、组织者、评判者。从此意义仍可说,此良知本心乃一切文化之“体”,一切文化乃此心之“用”。
而此“体—用”关系,乃是基于人的生存需要与生命理想展开,其二者间并非生成与被生成之逻辑,而是价值本末、主次之逻辑。正如方东美所言,一切存在均与人的“生命心灵”“生命情调”对其的“美化,善化以及其他价值化的态度与活动”有关。而包括科学、道德、艺术、文学、诗歌、音乐在内的一切文明成果、一切知识体系,既是主体理性之创造,显然亦是主体意愿之选择,主体生活之需要。这样,作为“生命情调”体现之科学,就始终服务于人类生活的实践理想、价值诉求、意义审视而被纳入到理性主体之“创造的世界”中,科学价值与科学信仰也被纳入生命多维价值诉求为标准的“立体的结构”中。[13](P.43)
显然,在此“创造的世界”中,依然可说“识心之执与科学知识是知体明觉之所自觉地要求者”,此“知体明觉”依然承担“创造实体”“创造本体”之使命。也即是,作为行为实践、知识实践之理性主体,可依据“主体之能”聚焦科学对象,培育科学理性,创造科学知识,推动科学实践。在此“立体的结构”中,道德良知、道德理性仍然具有“德行的优先性与综纲性”。在科学信仰、科学实践之“制衡”与“规范”上,以儒家擅长之“道德观念”“人文精神”依然可以作为最高原则,以对治科学的滥用、科学信仰一元化。
总之,此种“价值的体用论”,仍坚持了儒学主体性,秉承了其道德形而上学主旨;但同时,它规避了良知“坎陷”科学理性那种“生成”“转出”所带来的“先验的困境”,而建立了一种良知以道德意识、人文意识聚焦科学实践,以发挥“评价”“规范”“统会”作用的“新坎陷”效用。这样,既可在儒学与科学间建立一种“价值形而上学”的逻辑,又可在保障科学独立性之同时,通过道德良知对科学理性、科学实践之“范导作用”,始终防止科学泛化、滥用,保证道德本体对科学理性之“超越的统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