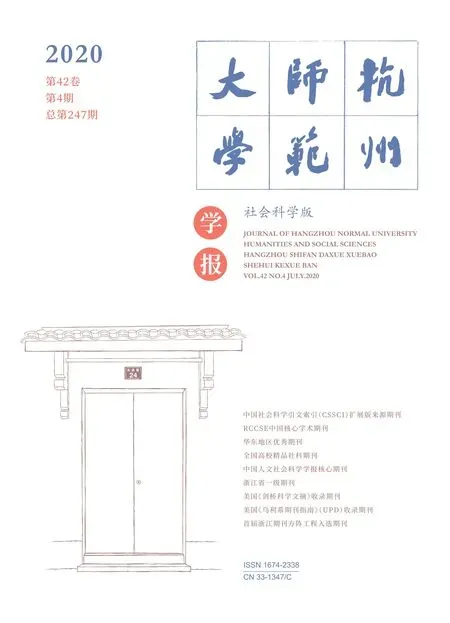清华简组诗为子夏所造魏国歌诗
张树国
(杭州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浙江 杭州 311121)
《清华大学藏战国竹简》第一册收录《耆夜》组诗,除《蟋蟀》见于《诗经·唐风》外,《乐乐旨酒》《輶乘》《=》《明明上帝》均未见传世典籍;[1]第三册收录《周公之琴舞》(下文简称《琴舞》)组诗[2],除“元内启”改编自《周颂·敬之》外,托名周公、成王所作至少9首《敬毖》组诗也未见传世典籍,笔者称之为“歌诗”,取材于《汉书·艺文志》“歌诗二十八家”如“高祖歌诗”“吴楚汝南歌诗”[3](PP.104-106)等。有学者认为歌诗抄写字体为楚文字,应该是楚人所作,但战国类似楚才晋用这种人才流动相当普遍,这两组古代歌诗虽然用楚文字抄写,但并不是楚人作品。因为组诗托名武王、周公、毕公、成王所作,对上古文学尤其是《诗经》研究来说,具有一定意义,一时之间在国内著名期刊都有相关研究文章发表,(1)如李学勤《新整理清华简六种概述》,《文物》,2012年第8期;赵敏俐《〈周公之琴舞〉的组成、命名及表演方式蠡测》,《文艺研究》,2013年第8期;姚小鸥、孟祥笑《试论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的文本性质》,《文艺研究》,2014年第6期;陈民镇、江林昌《“西伯勘黎”新证——从清华简〈耆夜〉看周人伐黎的史事》,《东岳论丛》,2011年第10期;李守奎《先秦文献中的琴瑟与〈周公之琴舞〉的成文年代》,《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4年第1期;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组诗对〈诗经〉原始形态的保存及被楚辞形式的接受》,《文学评论》,2014年第4期;徐正英《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孔子删〈诗〉相关问题》,《文学遗产》,2014年第5期;谢炳文《再议“孔子删〈诗〉”说与清华简〈周公之琴舞〉——与徐正英、刘丽文、马银琴商榷》,《学术界》,2015年第6期;李锐《清华简〈耆夜〉续探》,《中原文化研究》,2014年第2期。也出版了会议论文集,对字词以及音乐形式展开探讨。(2)会议论文集如清华大学出土文献研究与保护中心编《清华简研究》(第2辑)(上海:中西书局,2015年)、姚小鸥主编《清华简与先秦经学文献研究》(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6年)。李学勤认为《琴舞》以周公还政、成王嗣位为其内容,这不仅是佚诗的发现,也是佚乐的发现,是与周初《大武乐章》结构相仿的乐诗;赵敏俐认为《琴舞》创作于周初,“周公作多士儆毖,琴舞九絉”与“成王作儆毖,琴舞九絉”组合在一起,用于成王时的一个大型典礼活动之中;姚小鸥对其文本以及乐舞表演进行了分析,认为组诗为孔子删诗提供了证据;陈民镇、江林昌认为两篇组诗的背景为真实历史事件;徐正英将《琴舞》组诗视为《诗经》外的“逸诗”,是罕见的题目、短序以及乐章标识俱全的乐舞诗章,是演奏于宫廷的西周前期文本的原始形态,周公《敬毖》四句以及成王所作九首组诗全部为《诗经·周颂》诗篇,未经孔子删定整理过,传至战国中期的一组《诗经》作品完整形态,为孔子删诗十去其九提供了更有价值的新实证。学者们普遍关注组诗形式及演唱方式以及《诗经》学史有关问题,提出了富有启发性的见解。
孔子“删诗”是历史遗留问题,在传世文献框架内已经不可能取得一致性意见。而新出《耆夜》《琴舞》组诗为古人所未见,诸家均认为是周初先王先公所作《周颂》作品,因此自然与孔子删诗说挂起钩来。但一个重要事实不容否认:《左传》《国语》之类春秋史书频繁记载贵族行人的赋诗言志,何以自西周初直至战国七八百年间没有任何人物、任何文献称引过这些诗篇?董治安《战国文献论〈诗〉、引〈诗〉综录》《先秦文献所载古乐舞史料综录》详列战国文献对《诗经》的征引以及乐舞史料[4](PP.64-68),同时也全面列举“逸诗”[4](PP.444-460),巨细无遗,没有发现这两组歌诗题名和诗句。近年来有关《诗经》的出土文献如战国简郭店《缁衣》《五行》等篇以及上博简《孔子诗论》记录了一些上古《诗经》篇名及诗句,不出传本《诗经》范围;阜阳汉简《诗经》为汉文帝时期的隶书文本,然在这些断简残编或者竹简碎片中未见所谓《诗经》逸诗。笔者从未否认“清华简”以及近出“安大简”作为出土战国文献的真实可信性,然对学界所谓《耆夜》《琴舞》组诗产生自周初以及《诗经》“逸诗”说,不能不追问其证据的可靠性。就已出“清华简”九册来看,除《尚书》等文献为战国时期抄写外,如《楚居》《系年》等历史文献以及多篇法家文献均产生自战国时期。战国是极富文化创造力的时代,这两组歌诗也不例外,应该是战国人物所作。近期面世的“安大简”《诗经》包括《周南》《召南》《秦》《甬》《侯》《魏》,其中简本《侯风》即传本《国风·魏风》,简本《魏风》为传本《国风·唐风》,简本诗句存在着相应改动,其中虽未见到诸如《耆夜》《琴舞》诗句,但笔者注意到“安大简”《诗经》对这两组歌诗作者与时代问题具有重大启示意义。下面首先对孔子删诗问题进行学术反思,以证明清华简组诗非删诗之旧。
一、孔子删诗与《诗三百》“弦歌”文本说源于子夏
《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不见于传世典籍,有学者将其视为《诗三百》之外的“逸诗”,因此重新唤起孔子“删诗说”的讨论。司马迁《史记·孔子世家》:
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5](卷47,P.2345)
泷川资言《考证》:“孔子删诗之说始见于此。是之者,欧阳修、王应麟、郑樵、顾炎武、王崧诸人;非之者,孔颖达、朱熹、叶适、朱彝尊、王士祯、赵翼、崔述诸人。”[6](卷47,P.2913)《汉书·艺文志》:“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7](卷30,P.1708)《史记》《汉书》皆以《诗三百》定于孔子,为人所信服;但《史记》“古《诗》三千余篇”数量确实太大了,三百五篇约占十分之一,因此作为历史公案及至目前仍未止息。孔颖达《毛诗正义》在郑玄《诗谱序》“谓之变风变雅”下云:“如《史记》之言,则孔子之前诗篇多矣。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言‘古诗三千余篇’,未可信也。”[8](P.556)孔颖达在《左传·襄公二十九年》“为之歌秦”下《疏》云:“此为季札歌诗,风有十五国,其名皆与诗同,唯其次第异耳,则仲尼以前篇目先具,其所删削盖亦无多,《记》《传》引诗亡佚甚少,知本先不多也。《史记·孔子世家》云古者三千余篇,孔子去其重,取三百五篇,盖(司)马迁之谬耳。”[9](P.4357)在有关孔子删诗诸多说法中,刘操南《孔子删〈诗〉初探》认为孔子“去其重”对《诗经》进行整理定稿,孔子周游列国可能搜集到各地《诗经》藏本,如周、齐、卫、宋诸国之《诗》,这些藏本荟萃起来诗篇共计三千余篇,诗篇重复,篇目字句偶有出入,各有阙失,孔子对其补充与纠正,而成为当时较为完备定型的《诗三百》。[10]西汉末刘向、刘歆校书要参考多种本子,如《管子书录》记载,将“中外书五百六十四篇”定为“八十六篇”;《晏子叙录》记载,将“八百三十八章”定为“八篇二百一十五章”;《孙卿书录》记载,将“孙卿书凡三百二十二篇”“定著三十二篇”[11](PP.381-382)。《汉书·艺文志》“儒”类记载《晏子》八篇,《孙卿子》三十三篇;“道”类记载《管子》八十六篇。引文中多次出现“除复重”,这些“定著”本是刘向等人在诸多不同钞本基础上经过校雠而确定的,刘操南先生认为与《孔子世家》“去其重”意思一致。
孔子在搜辑“古《诗》三千篇”基础上,“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定《诗经》“四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这一“删诗说”可说是在春秋末期进行的第一次《诗经》文献整理,从此《诗经》就有了定本或“祖本”,意义非常重大。今传本《毛诗》就是在这一祖本基础上流传下来的。《经典释文·序录》记载《毛诗》传授的两条线索:
《毛诗》者,出自毛公,河间献王好之。徐整云: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仓子,薛仓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间人大毛公,毛公为《诗故训传》于家,以授赵人小毛公(一云名长。校勘云:“长”作“苌”),小毛公为河间献王博士,以不在汉朝,故不列于学。一云:子夏传曾申(字子西,鲁人,曾参之子),申传魏人李克,克传鲁人孟仲子(郑玄《诗谱》云:子思之弟子),孟仲子传根牟子,根牟子传赵人孙卿子,孙卿子传鲁人大毛公。[12](P.13)
陆玑《毛诗鸟兽草木虫鱼疏》后附毛诗传授源流,与《序录》“一云”相同[13](P.150)。子夏亲受《诗》于孔子,所传“高行子”见于《周颂·丝衣序》:“《丝衣》,绎宾尸也。高子曰:灵星之尸也”,孔疏“子夏作《序》则唯此一句而已,后世有高子者,别论他事云灵星之尸”,认为高子“必在子夏之后,毛公之前”。[8](P.1300)台湾地区学者朱冠华认为“高子”即子夏弟子高行子。[14](P.2)《周颂·维天之命》“维天之命,于穆不已”句下引孟仲子曰:“大哉天命之无极而美周之礼也”,孔疏引赵岐之语“孟仲子者,孟(轲)子之从昆弟,学于孟子者也”。[8](P.1258)据《经典释文·序录》此“孟仲子”亦为战国时期《诗经》之传人。
以上对孔子“删诗”传统说法的梳理,可知孔子通过“去其重”的古籍整理工作,确立了“诗三百”这一定本的经典地位,并奠定了《诗经》传播的“大传统”,汉初齐、鲁、韩、毛四家诗尽管存在某些异文,篇章基本上是一致的。但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存在多篇不见于传本《诗经》的所谓“逸诗”,目前学界对于组诗来源及其功用尚未有惬当解释;也有学者揪出组诗中若干词语,认为两组诗出于今人伪造,(3)如姜广辉《清华简〈耆夜〉为伪作考》(《故宫博物院院刊》,2013年第4期)、房德邻《决不能把伪简当作“中华文明的命脉”》(《湖南大学学报》,2014年第3期)等。研究方法很不科学。如何看待这些不见于《诗经》的战国竹书歌诗?需注意的是《孔子世家》提到:
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论语·子罕》记载夫子自道“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未提“弦歌”《诗三百》之事。《诗经》中《周南》《召南》诸篇可用“弦歌”,但《大雅》《周颂》主奏乐器为编钟,就不能“弦歌”。《荀子·乐论》:“故听其《雅》《颂》之声,而志意得广焉;执其干戚,习其俯仰屈伸,而容貌得庄焉;行其缀兆,要其节奏,而行列得正焉,进退得齐焉。” [15](P.252)阮元《释颂》认为“《风》《雅》则但若南宋人之歌词弹词而已,不必鼓舞以应铿锵之节也”,而“颂”即“容”即舞容,“《风》《雅》但弦歌笙间,宾主及歌者皆不必因此而为舞容,惟三《颂》各章皆是舞容,故称为《颂》”[16](卷1,PP.18-19)。王国维《说周颂》认为阮元释《颂》之本义至确,“然谓三《颂》各章皆是舞容,则恐不然”,《风》《雅》《颂》之别在“声”,“《颂》之声较《风》《雅》为缓”。[17](卷2,P.111)《颂》为仪式舞容及歌诗,其主奏乐器为编钟,其声较《风》《雅》弦乐“为缓”。然司马迁所说“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说明《雅》《颂》已经逐渐失去其仪式表演性质,经过改编而成为“弦歌”文本,此说可能源于子夏《诗序》。《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问子夏“古乐”之说,子夏云:
天下大定,然后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
孙希旦注云:“《诗》谓《风》《雅》也。德音,谓道德之声音也。”[18](卷38,PP.1015-1016)清华简《耆夜》中《蟋蟀》以及《周公之琴舞》中《敬之》分别见之于传本《唐风》及《周颂》,其章法格式与“安大简”《诗经》相似,加了诸多倚声衬词,作为阅读文本来说显得很啰嗦;而且章序复沓与传本《诗经》存在很多差异,与子夏、司马迁所谓“弦歌”接近。然若判断其时代还要着眼于两组诗的内容以及相关史实。
二、《耆夜》《周公之琴舞》均为战国魏国歌诗
《耆夜》组诗内容为周武王八年伐耆胜利以后,在文王太室举行饮至之礼,武王、周公以及毕公高相继作歌及“祝诵”互相酬酢,五首均有篇名,歌辞俱在。笔者曾撰文论证《耆夜》作为仪式乐歌的重要价值,(4)拙作《由乐歌到经典:出土文献对〈诗经〉诠释史的启迪与效用》,《浙江学刊》,2016年第2期。《新华文摘》2016年第10期摘编。然对其出处尚未作专门研究。简文云:
武王八年,征伐耆,大戡之。还,乃饮至于文王之室,毕公高为客,召公保奭为夹,周公叔旦为主,辛公甲为立(位),作册逸为东尚(堂)之客,吕上甫为司政,监饮酒。
文中记载武王“夜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乐乐旨酒》”,又“夜爵酬周公,作歌一终,曰《輶乘》”,裘锡圭先生《说“夜爵”》释“夜爵”为“举爵”,即“举相酬之爵”的意思。[19](P.536)在武王举爵酬答之后,“周公举爵酬毕公,作歌一终,曰《=》”,原释“字从賏声,疑读为央或英”,学者多从之读“英英”,但难以读通。笔者释为“婴贝”,《说文·贝部》:“賏,颈饰也,从二贝。”徐锴《系传》云:“蛮夷连贝为缨络是也,婴字从此。”[20](P.130)夏竦《古文四声韵》引《古老子》“婴”作“賏”[21](P.90),“婴”为环绕、缠绕之意。例句如《鲁颂·閟宫》“贝胄朱綅,烝徒增增”,《传》云:“贝胄,贝饰也。朱綅,以朱綅缀之。”[22](P.189)“婴贝戎服”谓以贝装饰戎装。《耆夜》歌辞云:“婴贝戎備(服),壮武赳赳。”又“举爵酬王,作《祝诵》一终,曰《明明上帝》”。这时一只蟋蟀骤降于堂,于是毕公触景生情,“作歌一终,曰《蟋蟀》”,然后文章结束。根据上下文不难判断,毕公所赋《蟋蟀》与传本《唐风·蟋蟀》字句稍有参差,大旨一致;“安大简”《诗经》将《蟋蟀》归入所谓“魏风”[23](PP.57-58),诗句与传本《唐风·蟋蟀》基本一致,《耆夜·蟋蟀》系出编选者故意改编,下文有论。
需注意的是,《耆夜》所记武王伐耆事件明显与正统史书不符。《尚书大传·西伯戡黎》云:“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勘黎》。”[24](卷10,P.374)“乘黎”之“乘”,胜义。胜古文或作“”,“胜黎”者为周文王。《今文尚书》作《西伯戡耆》。《尚书大传·康诰》:“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讼,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注引《文王世子》疏引《殷传》云:“五年之初得散宜生等献宝而释文王,文王出则克黎,六年伐崇则称王。”[25](P.66)《史记·周本纪》记西伯文王“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明年,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5](P.153),与《尚书大传》一致,可见伐耆之“西伯”当为文王而非武王,而《耆夜》则以“西伯”为武王,与传统史书记载严重不符。
《耆夜》组诗中“毕公高”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仿佛是伐耆主帅,但传世文献关于毕公高的记载不多。《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富辰论周初封建,“昔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9](P.3944),“二叔”指管叔、蔡叔之乱,分封文王十六子之国有毕、原、丰等国。《史记·魏世家》:
魏之先,毕公高之后也。毕公高与周同姓。武王之伐纣,而高封于毕,于是为毕姓。其后绝封,为庶人,或在中国,或在夷狄。其苗裔为毕万,事晋献公。
《索隐》:“《左传》富辰说文王之子十六国有毕、原、丰、郇,言毕公是文王之子。此云与周同姓,似不用《左氏》之说。马融亦云毕、毛,文王庶子。”[5](P.2219)毕公高始封于毕,是战国魏文侯的远祖,其为“文王庶子”地位并不高,而在伐耆胜利之后的盛宴中却处于“客”位,由武王、周公相继举爵敬酒,与历史记载不符。《左传·定公四年》:“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9](P.4637)《大雅·思齐》“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下,传云:“大姒,文王之妃也,大姒十子,众妾则宜百子也。”《正义》引皇甫谧云:
文王取大姒,生伯邑考、武王发,次管叔鲜,次蔡叔度,次郕叔武,次霍叔处,次周公旦,次曹叔振铎,次康叔封,次聃叔季载。
孔颖达云:“其名与《史记》皆同,其次则异,不知谧何所据而别于马迁也。” [8](P.1111) “大姒十子”中没有毕公高。皇甫谧获睹过汲冢古书,曾作《帝王世纪》,故其所说为学界所重。《史记·管蔡世家》:
武王同母兄弟十人。母曰大姒,文王正妃也。其长子曰伯邑考,次曰武王发,次曰管叔鲜,次曰周公旦,次曰蔡叔度,次曰曹叔振铎,次曰成叔武,次曰霍叔处,次曰康叔封,次曰冄季载,冄季载最少。[5](P.1891)
据《左传》《史记》以及皇甫谧之说可知“大姒十子”中没有毕公高,所以司马迁只说毕公高“与周同姓”,马融说毕公高是“文王庶子”。因为毕公高是魏文侯的远祖,于是战国魏人通过造伪,将“西伯”由文王替换为武王,所谓“在文王之室”举行饮至之礼,借武王、周公举爵献酬并赋歌诗祝诵来提升毕公高的地位,夸其祖宗以为子孙光彩,很明显出于战国魏国人的捏造,这在《周公之琴舞》中亦有体现。
(一)盛赞祖先之德,希望祖先监护自己,是所谓成王《琴舞》歌诗的主要内容。《琴舞》中“文人”反复出现,均指祖先而言,如《叁启·乱曰》“裕其文人,不逸监余”,《四启》“文文其有家,保监其有后”,《六启》“余用小心,寺(是)惟文人之若”,“文人”乃嘏辞“前文人”之省,是对祖先之尊称。
(二)谦抑自己德行,强调即位之合法性。《叁启·乱曰》“非天兴德,繄莫肯造之”,意谓若非上天兴起有德之人,则我也达不到王位这个高度;《四启》“需(孺)子王矣,不(丕)宁其有心”;《七启》“不(丕)显其有位,右(佑)帝在落”,《尔雅·释诂》:“落,始也”[27](卷1,P.19),此诗表达自己称“王”始基之义。
(三)寄望臣工敬德,拥护自己,福佑同享。《五启》“天多降德,滂滂在下,流自求之,诸尔多子,逐思忱之”,《乱曰》“恒称其有若,曰享答余一人,思辅余于艰”;《九启》“思丰其复,惟福思用,黄句(耇)惟程”,强调顺从君主意愿则带来无疆福祉。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居摄凡七年,“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5](P.1838)。《尚书大传·洛诰》:
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制礼作乐,七年致政。[25](P.68)
周公还政以后,恐成王懈怠淫佚,乃作《多士》《无逸》,以长辈身份对成王进行传统教育。《琴舞》组诗利用了《周颂·敬之》文本,加以改窜,并增益八首歌诗,而被学者误认为“《周颂》逸诗”,但其内容与史实完全不合。这些歌诗假托成王之口表达自己登基之义,周公“敬毖九絉”只有辞旨卑下的《无悔享君》一首四言诗,表示对新王的臣服。有学者遗憾地认为周公其他“八絉”没有记载,实际上根本不可能有,在传世上古文献中连影子都看不到,这篇厚诬古人的诗篇与战国晋魏禅代有直接关系。
春秋战国之际的晋国正处在被国内卿士瓜分的前夜,与当时社会剧烈变革的时代同步,旧诸侯如鲁国君权于昭、定、哀三世已旁落到“三桓”手中,而“三桓”政权又为家臣把持;宋国君权落到戴族大夫之手;姜姓齐国被新兴贵族陈(田)成子推翻而成为陈(田)姓之齐国;政权更迭最剧烈的国家莫过于晋国,公室式微,公卿大夫之间互相倾轧,由“六卿”(智、范、中行、韩、赵、魏)变为“四卿”(智、韩、赵、魏)执政。晋出公为“四卿”所逐,死于路上。出公之后继任者晋敬公为智伯所立,《史记》索隐引《纪年》:“出公二十三年奔楚,乃立昭公之孙,是为敬公。”[5](P.2031) “晋敬公”之名见于清华二《系年》简111-112:“晋敬公立十又一年,赵桓子会(诸)侯之大夫以与戉(越)令尹宋盟于鞏遂,以伐齐。”[28](P.14)韩、赵、魏杀智伯,尽并其地,敬公也成了傀儡国君。“三晋”之中,魏国最大。魏文侯在位有“三十八年”(《史记·魏世家》)、“五十年”(《竹书纪年》)两种说法,王国维、钱穆、杨宽等学者考证《纪年》“五十年”说准确,(5)参见王国维《古本竹书纪年辑校》,《王国维遗书》第7册,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第599-600页;钱穆《先秦诸子系年》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123页;杨宽《战国史料编年辑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年,第122页。魏斯始侯之年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晋敬公六年(前446)。这些新兴诸侯一方面要摧毁旧典籍,清除改革绊脚石;另一方面又大造舆论,《诗》《书》等经典曾是贵族统治秩序的保证,这时也丧失其神圣性质,通过改窜利用旧经典来树立新兴诸侯的合法性。《耆夜》假托武王、周公敬酒魏国始祖毕公高,并将《蟋蟀》著作权派给了毕公高,《周公之琴舞》改窜《周颂·敬之》“命不易哉”为“文非易师(思)”,宣扬天命不是不可以改变的,这些观念在新出“安大简”《诗经》中都得到了明显印证。
Craig和Graham并非同时自由拍摄,而是商量好了各自轮流拍摄半小时。对于拍摄全情投入格斗中的模特,Craig坦言他感觉不是很熟悉,“对我来说,拍摄动作场景是最大的挑战。因为我平时主要拍的都是静态的肖像或是风光摄影。”
三、《耆夜》《琴舞》与“安大简”《诗经》均为子夏造魏国歌诗
《耆夜》《琴舞》组诗分别收录在“清华简”第一、三两册,笔迹相同,当为同一人抄写;不仅如此,两组诗产生时代也一致,已有学者如刘立志、刘成群、曹建国等先生从多个角度论证其出于战国伪造。(6)参见刘立志《周公作诗传说的文化分析》(《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刘成群《清华简〈耆夜〉〈蟋蟀〉诗献疑》(《学术论坛》,2010年第6期)、曹建国《论清华简中的〈蟋蟀〉》(《江汉考古》,2011年第2期)等。《耆夜》组诗中的主角毕公高为战国魏文侯之始祖,组诗当与魏文侯集团有关联;《琴舞》组诗表现周公、成王变了味的禅位故事,实际上也是战国时期晋魏易代的现实投影,与魏斯称侯紧密相关。近来面世“安大简”《诗经》与“清华简”中这两组歌诗有内在关联,对此提供了新证据。
“安大简”《诗经》收录“六风”,即周南、召南、秦风、侯风、甬(鄘)风、魏风,值得注意的是,“侯风”之名仅见于该书,所收六篇为传本毛诗《魏风》;简本“魏风”则为毛诗《唐风》九篇,以《蟋蟀》为首。《诗经》传播史上从来没有类似怪异现象,整理者黄德宽先生认为“侯风”即传本毛诗《王风》之“误置”[23](P.3),这是根本不可能的。从文献上来看,《诗经》定本出自孔子,这是不容否认的。《经典释文·序录》:
孔子最先删录,既取周诗,上兼《商颂》,凡三百一十一篇,以授子夏。子夏遂作《序》焉。口以相传,未有章句。[12](P.12)
“三百一十一篇”包括笙诗六篇,有目无辞。子夏是孔门《诗》学的直系传人。上古竹书几乎都是单传,《序录》记载子夏授高行子,一直传到河间人大毛公而作《诗诂训传》,十五国风序列也就是今传本序列,虽然有个别参差之处,但并未出现某种“误置”。“安大简”《诗经》很明显是战国时人故意改动的,其原型是在《诗经》祖本即《诗三百》基础上删改选编而成。从其直接受益者来说,“侯风”之“侯”当为战国初年的魏文侯;而修改《诗经·国风》以及炮制《耆夜》《周公之琴舞》组诗之人就是子夏之流。今传本《魏风》本为古魏之风,晋献公灭古魏后封给魏文侯之高祖毕万;而文侯定都安邑即古魏之地,因此将“古魏风”移花接木重新命名为“侯风”;将本为“晋风”的《唐风》改为“魏风”,欺侮孱弱的晋国公室,为晋魏易代张本;同时选编“二南”表达“王化”始基之义;选《秦风》表达尚武精神为立国之本;选《甬(鄘)风》作为属国之风。邶鄘卫统称“卫”,《史记·卫康叔世家》:“是时三晋强,卫如小侯,属之。”《史记·六国年表》:“(前476)魏献子”栏下“卫出公辄后元年”[5](P.837),“魏”一栏中记“(前450)卫敬公元年”[5](P.848),“(前431)卫昭公元年”[5](P.852),“(前425)卫悼公亹元年”[5](P.853),可见战国时的卫国为“三晋”魏国之附庸。“安大简”《诗经》如此选编具有强烈现实政治目的,为魏文侯时期晋魏禅代大造舆论,其始作俑者当为子夏。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卜商,字子夏,少孔子四十四岁”[5](P.2676),又云“孔子既没,子夏居西河教授,为魏文侯师”[5](P.2677)。孔子生于鲁襄公二十一年(前551),殁于鲁哀公十六年(前479),由此推断子夏生于公元前507年,孔子去世时子夏二十九岁。据河南学者高培华考证,子夏出生在晋国温邑,而在为孔子守丧三年之后回到西河教授之时,温邑已属魏国,其讲学之“西河”也在温邑,地处“河济”之间。[29](P.54)《礼记·檀弓上》“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章下,孔疏引《仲尼弟子传》“子夏姓卜名商,魏人也”可证。[30](卷7,P.2778)《吕氏春秋·开春论·察贤》:“魏文侯师卜子夏,友田子方,礼段干木,国治身逸。”[31](P.586)《史记·儒林列传》记载孔子卒后“七十子”去向及儒术的传播,“七十子之徒散游诸侯,大者为师傅卿相,小者友教士大夫,或隐而不见”,其中“子夏居西河”,“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釐之属,皆受业于子夏之伦,为王者师。是时独魏文侯好学”。[5](P.3786)子夏受魏国宗室厚爱,即司马迁所称“大者为师傅卿相”之“大者”,在西河讲学,为魏文侯师,地位甚高,正如曾参所说“使西河之民疑(擬)女(汝)于夫子”(《礼记·檀弓上》)。在子夏周围聚集了诸多魏国贤士,为魏文侯时期的国之俊彦。“安大简”《诗经》与子夏之流媚附魏斯始侯之年(前446)制礼作乐而编选歌诗密切相关,而清华简组诗则为子夏之徒所造,子夏时年62岁。目前学界对魏文侯制礼作乐之事尚不清楚,下文试论。
四、魏文侯制礼作乐与魏国歌诗的编选与创作
魏文侯制礼作乐之事颇见于史书,《汉书·艺文志·诸子略》“儒家类”著录“《魏文侯》六篇”,顾实《讲疏》:“亡,文侯受经于子夏”[32](P.99),陈国庆按:“《隋》《唐志》皆不载,书亡已久。马国翰有《魏文侯》辑佚一卷”[33](P.102),马辑本见《玉函山房辑佚书·子编》“儒家类”,从《战国策》《吕氏春秋》等书辑佚凡二十四节,录为一卷,其中将《礼记·乐记》“魏文侯问乐”一节归属《魏文侯》。马云:“案刘向《别录》:《乐记》三十三篇,《魏文侯》为第十一篇,以《乐记》佚篇有《季札》《窦公》例之,《季札》篇采自《左传》,《窦公》篇取诸《周官》,知此篇为《文侯》本书,而河间献王辑入《乐记》也” [34](P.2494),马云《乐记》“三十三篇”应为二十三篇。《汉志》“《乐记》二十三篇”收录于《礼记·乐记》并传至今日者只有十一篇,名目见于《礼记·乐记》孔疏:
按郑《目录》云:名曰《乐记》者,以其记乐之义,此于《别录》属《乐记》,盖十一篇合为一篇。谓有《乐本》,有《乐论》,有《乐施》,有《乐言》,有《乐礼》,有《乐情》,有《乐化》,有《乐象》,有《宾牟贾》,有《师乙》,有《魏文侯》。[30](P.3310)
《史记·乐书》全部收录《乐记》,张守节《乐书正义》全部标注其十一篇名目。孔疏《乐记》“其余十二篇之名”云:
案《别录》十一篇,余次《奏乐》第十二,《乐器》第十三,《乐作》第十四,《意始》第十五,《乐穆》第十六,《说律》第十七,《季札》第十八,《乐道》第十九,《乐义》第二十,《昭本》第二十一,《招颂》第二十二,《窦公》第二十三是也。[30](P.3310)
“诸子”中采撷最多者为《公孙尼子》,《隋书·音乐志》引沈约之说,“窃以秦代灭学,《乐经》残亡……《乐记》取《公孙尼子》”[35](卷13,P.288),也征引了《魏文侯》及其他子书,其中《季札》《窦公》两篇均与魏文侯时事关联密切。《汉书·艺文志》云:
六国之君,魏文侯最为好古。孝文时得其乐人窦公,献其书,乃《周官·大宗伯》之《大司乐》章也。
颜师古注引桓谭《新论》“窦公百八十岁,两目皆盲,文帝奇之”。[7](P.1712)据《竹书纪年》魏文侯在位50年,杨宽考定魏文侯初立在晋敬公六年,是年为周贞定王二十三年(前446),其卒年周安王六年(前396)。[36](P.122)以魏文侯卒年算起距离汉文帝元年(前179)将近220年,“窦公”不可能是魏文侯时人物,应是战国魏国乐师,所献《大司乐》可能出自魏文侯时。《周礼·大司乐》在上古礼乐典籍中占有重要地位,从《艺文志》记载来看,窦公所献《大司乐》当为魏文侯时所作,不一定为王官旧有。“大司乐”官名未见金文著录,张亚初、刘雨《西周金文官制研究》收录“司鼓钟”“司龠”而没有“大司乐”。[37](PP.50-51)但见出土文物“令司乐作太室埙”以及“令作韶埙”,陶埙铭文见于高明先生《古陶文汇编》“西周部分”[38](P.25),杨荫浏《中国音乐史稿》上册书后附图23收录陶埙及其铭文图样,题作“周陶埙及其铭文拓本‘命司乐作太宝埙’”,“宝”当为“室”之误;[39](P.23)图24题作“周陶埙及其铭文拓本‘命作韶埙’”[39](P.24),李纯一先生以之为春秋埙[40](P.124),现藏故宫博物院。《大司乐》章内容多言王官之学,“以乐德教国子,中、和、祗、庸、孝、友”,“以乐舞教国子”,记载黄帝以来“六代大舞”;其中“凡乐圜钟为宫黄钟为角”一节记载古代降神之乐,其旋宫转调理论已超出西周时期的编钟乐水平,体现了古代以编钟为主奏乐器发展到战国以来的最高成就,通过曾侯乙墓编钟可想见其规模及乐奏形态;“以乐语教国子,兴、道、讽、诵、言、语”,孙诒让《正义》:“谓道引远古之言语,以摩切今所行之事,《乐记》子夏说古乐云‘君子于是道古’是也。”[41](卷42,P.172)此节与《乐记》“魏文侯问子夏”章颇相吻合。
马国翰推断《乐记·季札》即《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乐章,该篇与战国魏氏集团关系密切,未必不出自《魏文侯》六篇。“安大简”《诗经》“六风”《周南》《召南》《侯》(即传本“魏风”)、《魏》(即传本“唐风”)、《秦》《甬(鄘)风》,均见之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季札观周乐并发表“乐评”,论《周南》《召南》“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然勤而不怨矣”;论邶鄘卫“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论《魏风》“美哉!沨沨乎!大而婉,险而易行,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杜预注:“险当为俭字之误也。”论《唐风》“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遗民乎?不然何忧之远也?非令德之后,谁能若是?”杜注:“晋本唐国,故有尧之遗风,忧深思远,情发于声。”论秦风“此之谓夏声,夫能夏则大,大之至也,其周之旧乎”。[9](PP.4356-4358)季札用赞美语调对以上诸国之风进行正面评价,与《诗·小序》诸风多“刺”形成鲜明对比。清儒姚鼐《左传补注序》认为“《左传》非一人所成”,“盖后人屡有附益”,又云“余考其书其于魏氏事造饰尤甚,窃以为吴起为之者盖尤多”,又云:
夫魏绛在晋悼公时甫佐新军,在七人下耳,安得平郑以后赐乐独以与绛?魏献子合诸侯,干位之人而述其为政之美,词不恤其夸,此岂信史所为论本事而为传者耶?《国风》之魏至季札时亡久矣,与邶、鄘、郐等,而札胡独美之曰“以德辅此,则明主也”?此与魏“大名”“公侯子孙,必复其始”之谈,皆造饰以媚魏君者耳!又忘“明主”之称乃三晋篡位后之称,非季札时所宜有,适以见其诬焉耳。[42](PP.18-19)
姚鼐认为魏绛赐乐与季札观乐均为吴起之徒所伪造,这是很有可能的。清初顾炎武《日知录》“春秋阙疑之书”条云“《左氏》之书,成之者非一人,录之者非一世,可谓富矣” [43](卷4,P.145)。赵光贤《〈左传〉编撰考》列举多例说明“《左传》是由不同时期不同的人编成的”,编撰者有左丘明、吴起、子夏、刘歆等说法。(7)赵光贤列举《左传》作者:1.左丘明,司马迁、刘歆等;2.刘歆,刘逢禄、康有为等;3.吴起,姚鼐、郭沫若等;4.子夏,卫聚贤等;5.鲁人左氏,赵光贤认为是孔门后学,详见赵光贤《古史考辨》,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第136-187页。童书业《〈春秋左传〉作者推测》亦以吴起之作“似非妄说”,认为《左传》盖吴起及其先师后学陆续写定,惟吴起之功为多,《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吴起,卫左氏中人也”,“此《左氏传》名称之所由来邪”。[44](PP.346-347)吴起受业于子夏,为魏文侯相,在《左传》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经典释文·序录》“左丘明作《传》以授曾申,申传卫人吴起,起传其子期,期传楚人铎椒”[12](P.17),经过虞卿、荀况等人传到汉代,在传播过程中“后人屡有附益”。《左传》季札乐评对《魏》《唐》诸风极尽夸饰之辞,“安大简”《诗经》将传本《魏风》命名为“侯风”、将传本《唐风》命名为“魏风”,与子夏、吴起之流选春秋吴国贤士季札作为代言人,造饰以媚魏主密切相关,“安大简”《诗经》根本就不是经孔子手定《诗经》经典本有的样子。
《礼记·乐记》记载魏文侯与子夏谈论制礼作乐问题,子夏对雅颂“古乐”与“郑卫之音”为代表的“新乐”进行一番分析,所谓“郑音好滥淫志,宋音燕女溺志,卫音趋数烦志,齐音敖辟乔志,此四者皆淫于色而害于德,是以祭祀弗用也”,注“燕,安也”,“燕女”当作“燕安”,“女”“安”楚文字写法形近易讹。以上“郑音”“卫音”“宋音”及“齐音”均为子夏所说非“正音”的“溺音”,而雅颂古乐令魏文侯昏昏欲睡,因此子夏满足魏文侯的需要,制作所谓“德音之音”的魏国新乐,所谓“弦歌诗颂,此之谓德音,德音之谓乐”,子夏又云:
圣人作为鞉、鼓、椌、楬、埙、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后钟磬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先王之庙也,所以献酬酳酢也,所以官序贵贱各得其宜也,所以示后世有尊卑长幼之序也。[30](P.124)
《小雅·常棣序》“故作《常棣》焉”下,孔疏引郑玄答赵商云:“凡赋诗者,或造篇,或诵古”[8](P.870),“诵古”与《乐记》子夏所谓“君子于是语,于是道古”相同,即弦歌《诗经》篇章以资讽喻。“安大简”《诗经》没有选编雅颂之乐、郑卫之声、齐宋之音,却选择“二南”、《秦》《甬(鄘)》《魏》(重新命名为“侯”)、《唐》(重新命名为“魏”)等“六风”,诗篇章序及复沓手法与传世文本有很大不同,与“弦歌《诗》《颂》”之“诵古”功用密切相关;而“造篇”则体现为《耆夜》《琴舞》等新体歌诗的创作,子夏论古乐“弦、匏、笙、簧会守拊鼓,始奏以文,止乱以武,治乱以相,讯疾以雅”,以琴瑟等弹拨乐为主的弦乐作为主打乐器,结合匏、笙、簧等吹奏乐以及鼓乐,在《琴舞》歌诗创作中“启”“乱”相配,即《孔子世家》所谓“三百五篇皆弦歌之”以及子夏“弦歌《诗》《颂》”;其中《耆夜》中《蟋蟀》以及《琴舞》中的《敬之》句式及章序与传本不同,皆与“弦歌”有关。《乐记》子夏说“德音”之功用为“献酬酳酢”“官序贵贱”,清华简组诗与“安大简”《诗经》均体现了子夏之流在魏文侯时期的礼乐实践。
综上所论,司马迁《孔子世家》所谓孔子将“古者《诗》三千篇”定著“三百五篇”之后,“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之说当源于子夏《诗序》。清华简《耆夜》《周公之琴舞》两组歌诗并非孔子“删诗”之余,其创作与子夏在战国初年魏国的礼乐实践有关;除“造篇”外,“安大简”《诗经》为子夏在西河讲学、为魏文侯师时在孔子《诗经》定本即“祖本”基础上选抄而成,即所谓“弦歌《诗》《颂》”的底本,为配合魏斯始侯之岁(前446)制作“德音之音”的需要,做了相应改动以媚附魏文侯。由于《汉志》“《魏文侯》六篇”已亡,关于魏文侯制礼作乐之事已久不为学者所知,笔者利用有限传世资料结合出土清华简、安大简进行初探,希望得到方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