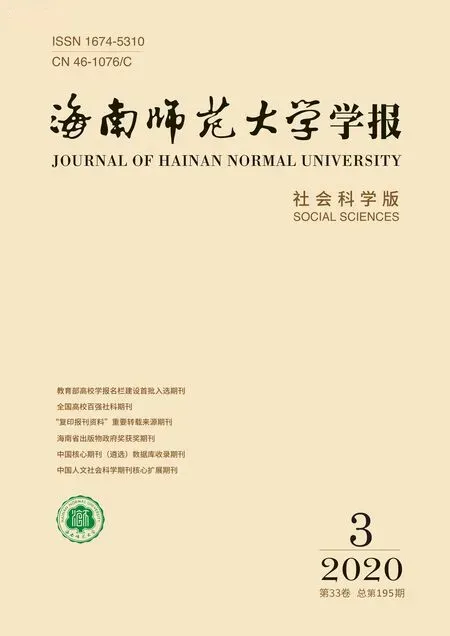旧日的幽灵:论鲁迅的“太平天国”书写
周楷棋
(中山大学 中文系(珠海),广东 珠海 519082)
作为一次重要的政治运动,太平天国是中国近代历史抹不去的集体记忆。出生在19世纪80年代的鲁迅虽然并未亲身经历太平天国,在他的作品中却并不缺乏对太平天国的书写。对于鲁迅来说,太平天国本身已经是“过去式”,但其影响仍然在他生活的年代中荡漾。在对太平天国的书写中,鲁迅呈现出隐秘的焦虑,在回避对运动本身进行描写的同时通过真假难辨、模棱两可的语境去解读其背后的意义。在这个过程中,鲁迅看到的是一个来自旧日的“幽灵”,虽然其无法被现实和当下语境所呈现,但却通过潜伏在个体和集体的无意识中而无形地威胁着当下与后世。在对太平天国的书写中,鲁迅除了展示自身出对此运动的态度外,更将其作为一个参照的“他者”去呈现、反思他一贯关照的诸如“革命”“国民性”等命题。本文在梳理鲁迅与太平天国关系的情况下,通过分析其笔下对太平天国的书写方式,结合鲁迅个人思想变化的脉络去辨析对太平天国书写的意义所在。
一、认识与态度:鲁迅对太平天国的接受概述
在现实层面对太平天国的接受对鲁迅日后的书写具有深刻的影响。生于1881年的鲁迅无法亲历太平天国,但他早年即已从各方面对其进行了认识。太平天国曾经短期地席卷了鲁迅的故乡绍兴,并留下了一些实际的遗迹。鲁迅属于周家覆盆房的一支,这一支又分为致、中、和三房,除了致房的鲁迅童年居住的新台门外,还有属于其他家系的过桥台门和老台门两处住宅。周作人在《鲁迅的家世》中提到,老台门住宅中曾被太平军征为公馆,并在墙上绘上了龙形图案。(1)无名(周作人):《鲁迅的家世》,《文艺阵地》1939年第4卷第1期,第1221页。这一点得到了罗尔纲的实证,他在实地考察确认周家老台门的太平天国遗迹的同时,通过采访许广平得到了鲁迅对这组遗迹的认识:“鲁迅先生在平常家庭谈话中,讲过老台门住过太平军,墙上都绘有龙,天阴时隐约可见……”(2)罗尔纲:《绍兴太平天国壁画调查记》,《历史研究》1956年第2期。可知鲁迅已经在早年生活中实际接触过太平天国的物事。除此之外,鲁迅曾提到,生在僻乡的自己在尚无“满汉”之辩的时候听得最多的故事就是“打长毛”(3)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92页。。故事的讲述者包括鲁迅的母亲、长妈妈等他身边的人,《阿长与山海经》中即描写过长妈妈讲述太平天国的事迹。周作人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也提到,鲁迅《怀旧》中有关太平天国的内容并非独立虚构,而是从母亲和佣工口中听来的。虽然鲁迅也自述曾通过阅读县志的方式去认识太平天国,但总体来看,他对太平天国的认识和接受更多地是来自“民间”话语的传述。
另外,鲁迅也是站在民间的立场上对太平天国建立了总体性的认识。这一点显著地体现在他对太平天国的称呼上。在所有的文体中,鲁迅对太平天国使用得最多的称谓是“长毛”。在今天看来,太平天国无疑更是一个带有官方色彩的正式称谓,但在鲁迅笔下,其若非只作为专有名词的一部分而出现于书信和日记中——比如《太平天国野史》或“太平天国玉玺印本”,便有在《中国小说史略》这样相对正式的论著中出现。“长毛”一词并非包含着贬义,其更多地代表着一种直接的民间态度。有学者考辨关于“长毛”一词的蕴意时指出,长毛是当时民众对太平军的主要称呼,但并不带有污蔑性,而与民间善以借代修辞为外号的习惯有关。更具有污蔑性的称呼则是清廷冠以的“贼”“寇”“匪”之类的名号。(4)史式:《太平天国文书史料中的词语诠释问题》,《社会科学研究》1981年第6期。从民间角度接受太平天国的鲁迅听得最多的大抵就是“长毛”,而对该词进行沿用也体现出鲁迅从民间立场审视太平天国的态度。这种民间的态度使鲁迅在文学文本的创作中,在回避预设的政治立场和宏大叙事的同时,尽量通过对个人经验进行艺术再造和从民间视角去呈现、审视太平天国。一个最突出的例证在于,他基本以王翁或阿长这类普通民众作为叙述者,从文本个体的角度去回顾太平天国,这和作者本人对太平天国的总体接受角度也是接近的。
未能直接与太平天国发生关系的鲁迅,在书写太平天国时的态度总体上是批判的,但批判并不仅在于或止于太平天国本身。在鲁迅笔下,太平天国经常被作为一个参照物的“他者”而被书写,鲁迅亦得以透过其展开更有深度的批判。这种思辨是更多的是围绕着对当下精神的批判性认识,但广阔的历史视野又能使他往往能“借古释今”,将过往的史实、史事化为己用。《病后杂谈之余》是鲁迅写于1935年的一篇杂论,内容大致围绕自己对满清政权的“愤懑”展开。在第三节中,鲁迅即借助太平天国阐释他对辫子问题中有关奴性的思考。在提到阿长讲述长毛故事时他提到:“她并无正邪之分,只说最可怕的东西有三种,一种自然是‘长毛’,一种是‘短毛’,还有一种是‘花绿头’。到得后来,我才明白后两种其实是官兵,但在愚民的经验上,是和长毛并无区别的。”(5)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92页。在此处,鲁迅着重批判的对象是两相勾结的清兵和外国兵,而长毛显然是一个“他者”。鲁迅接着提到,自己曾经从县志中的“烈士烈女”认识到太平天国的残酷而认定其可恶,但久而久之,他自己也分不清造成这些“烈士烈女”的究竟是长毛还是“短毛”和“花绿头”。之后鲁迅又写到“辫子”,认为其是最初提醒他满汉之别的东西。他这样说:“这辫子,是砍了我们古人的许多头,这才种定了的,到得我有知识的时候,大家早忘却了血史,反以为全留乃是长毛,全剃好像和尚,必须剃一点,留一点,才可以算是一个正经人了。而且还要从辫子上玩出花样来……”(6)鲁迅:《病后杂谈之余》,《鲁迅全集》第6卷,第193页。在批判辫子加诸在民众身上的奴性时,长毛再度成为批判话语中的“他者”,在受辫子精神影响下的庸众心理的一角中被呈现。
从这篇鲁迅晚年对太平天国具有相对集中论述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将太平天国作为“他者”进行关照的态度:太平天国虽然是反清的运动,但鲁迅并未对其有所嘉许,反而更倾向于将之作为“反面教材”,进一步衬托他更着重批判的统治阶级的“恶”和民众的愚昧。往更深处说,县志中的“烈子烈女”使鲁迅初步认识了长毛的“恶”,但后来他也分不清“恶”的根源究竟来自何处。是以,长毛、“短毛”和“花绿头”从某种程度上说实则是同类。在文学文本中,鲁迅进一步将太平天国作为暴露国民性的参照物进书写,从形式和内容出发,鲁迅通过经营太平天国的书写呈现出他对这段运动背后所蕴含着的,关乎历史和国民层面的批判,并从这个角度侧面回答了他晚年的思考。
二、太平天国文学书写的形式解读
在鲁迅的小说和散文中,提及太平天国的有《怀旧》《头发的故事》《风波》《长明灯》以及《阿长与山海经》等,而内容相对重要的则是《怀旧》《风波》和《阿长与山海经》三篇。在这些篇目中,鲁迅对太平天国的书写在形式上具有许多相似之处。“太平天国”被表述为一种缥缈的存在,其本身并未实际发生在文本时间中,但却因他人的提及而对文本中的人物产生了影响,正似死于过去但徘徊于当下的“幽灵”。透过这个虚无的幽灵,立足于现代视点的鲁迅从对太平天国看似戏谑、荒诞的书写中展开了对历史和国民性的另类批判。
纵观文本可以发现,太平天国由始至终都是被文本中的人物“讲述”而非被潜在作者所“呈现”的。即便在只提到过一次的《头发的故事》和《长明灯》中,“长毛”这个词也都来自N先生和庄七光的口中,从未被作为潜在作者的叙述者所书写。“长毛”在这里被呈现为不同文本的个体所共有的一个集体记忆。这种书写方式和鲁迅更多地作为听者,从他人的口述中认识、理解太平天国的方式是一致的,可以说鲁迅是在将自身对太平天国的经验从亲历者体验国的“旧事”文学地再现为被接受的“故事”。黄子平认为,“旧事”是个人的亲历,而一旦为了解释当前而将旧事反复重提,使之成为现实的一项注解,旧事也就“故事化”“寓言化”了。(7)黄子平:《〈故事新编〉时间与叙述》,《中国文化》1990第1期,第123-124页。在鲁迅的文本中,太平天国的事迹首先是被如王翁、九斤老太或是阿长之类的亲历者所讲述的“旧事”,再于文本中的听者所接受的过程中被“故事化”。而被讲述的“旧事”本身的特征在于,文本中的听者乃至文本外的读者,都无法判断其真假,而只能将之转化为表象的“故事”,既着重于接受事件的发展过程而非对其真假的合法性进行判断。
除了被“故事”化,太平天国的事迹还会进一步被“流言”化。强调受众对事件发展过程而非其背后的逻辑进行接受的“故事”,自然可以成为流言的温床。
可以发现,鲁迅在对太平天国的书写中设置了不少的“流言”,而这主要包含着两种形态。一种是对文本的现实时空产生切实影响的“当下”的“流言”,另一种则是存在于叙述者讲述的“旧事”中的流言。在对太平天国的书写中无不充斥着真假难辨的“流言”,无论是《怀旧》中的“长毛将至”,《风波》中的“皇帝坐龙庭”,还是《阿长与山海经》中“脱裤挡大炮”的荒诞言论。“流言”本身是一种没有根据乃至真实性的话语,但恰恰是这种“假”的话语,成为了暴露太平天国书写意图的重要工具。有学者谈到流言“并非是单纯关于个体、人事的琐碎八卦,而也包含了对文化、现实、历史等层面的非常规表达”(8)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2期。,鲁迅正是将太平天国置于真假难辨的“流言”中去考察民众的反应,由此开启了他国民性及思想批判的独特路径。在《怀旧》与《阿长与山海经》中,鲁迅反复表达了类似的书写内容,但同样的内容在不同的语境中起到了不同的表达效果。在《风波》中,“长毛”也只是被作为对照当下“皇帝坐龙庭”的局势而被短暂地提起。鲁迅在书写太平天国时并不过分在意其内容的表达,重点更在于人们对“流言”这一形式的反映。在这里,太平天国再度被赋予了“他者”的参照意义,其不存在于文本当下的叙事时空中,而只是离散在不同人物所讲述的“故事”之中。但当这些“故事”以“流言”的形式对此在的叙事时空产生影响时,旧日的幽灵才逐渐清晰起来。是以,鲁迅以流言的形式书写太平天国的目的也绝非仅在于太平天国本身,而在于传递流言呈现出的现象背后的思考。
在《怀旧》中,“长毛将至”的流言最早由金耀宗——一个无能的纨绔子弟带入文本视野。《风波》中“皇帝坐龙庭”的流言则由少了辫子的七斤自己带来,但这两个消息也是他们从其他处听来的,前者来自三大人,后者可能来自“城里”。而从《怀旧》后文分析,三大人也不是真正的消息源,是以两个流言都无法找到真正的源头。两则流言的形式也很类似,都和旧日被推翻政权的疑似复归有关。《怀旧》发生在革命前夜,太平天国早已被镇压;《风波》发生在民元革命后的某个时间,清廷也已被推翻。而通过这种“前朝复归”式的流言,长毛又在各人心中被唤醒,引发了各种各样的反应。长毛并不会真正地在现实中复归,却因“流言”化所幻化,从而唤醒了民众集体心中的政治无意识。而从这种无意识的特征可以看出,太平天国的“幻觉”引发的是大多数民众的负面情绪,但鲁迅并不是单纯借民众之口批判太平天国,更多的是借由太平天国非在场的“幻觉”形态来批判民众通过集体无意识展示出的种种劣性。在流言的形式中,民众的行为在表面的戏谑中被予以深刻的批判,揭示出了“集体无聊、琐碎、卑微、伪善”(9)朱崇科:《论鲁迅小说中的流言话语》,《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第2期。等种种劣根性。在《怀旧》中,“长毛将至”的流言引发了秃先生坐立不安的虚伪,金耀宗“箪食壶浆以迎王师”(10)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27-230页。的家训,以及王翁关于太平天国往事中残酷片段的戏谑追忆;在《风波》中,赵七爷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危言恐吓七斤,对当年的太平天国却也抱着畏惧;唯独九斤老太不露惧意,借长毛继续阐发其“一代不如一代”的价值观。在这些文本中,萦绕在各人心中的太平天国不约而同地激发了他们对这一旧日政权的恐惧,也由此暴露出了各种各样的国民劣根性。
鲁迅又设置了“孩子”这一类特殊的听者以增加批判和省察的多面性。《怀旧》中的“吾”和《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我”都是孩子的形象。在《风波》中,赵七爷和九斤老太在饭桌前谈及长毛时,饭桌前也存在着女童六斤这样一个形象。这类孩子有一个共同的特征,就是完全不为长毛的残酷行径所动。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听闻长毛杀门房的暴行时“我”并不觉得害怕,因为“我觉得这些事和我毫不相干的,我不是一个门房”(11)鲁迅:《阿长和山海经》,《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52页。;《怀旧》中在“长毛将至”的流言笼罩村镇,道上“人人悉函惧意”时,作为主人公的孩子则“不暇问长毛事”(12)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7卷,第229页。,自顾扑蝇弄蚁,在听闻长毛砍杀赵五叔的暴行时不为所动,反而在想:“思倘长毛来,能以秃先生头掷李媪怀中者,余可日日灌蚁穴,弗读《论语》矣。”(13)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7卷,第230页。以儿童作为太平天国事迹的接受者有其意义所在。有学者从儿童的角度出发,认为儿童不大能理会成人眼中的恐怖,而《阿长与山海经》中的“我”的解释也带有戏谑性。(14)费东梅:《〈怀旧〉的主题与形式——对普实克论文的再讨论》,《现代中文学刊》2015年第2期。而还有学者注意到:“‘儿童’是鲁迅‘回忆’或‘观看’的对象,却不是发声者甚至被预设的读者”。(15)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7卷,第228页。结合两种观点可以认为,鲁迅笔下的儿童更多地是作为被表现的对象,在天真的一面被突出之余自身并不承担理性认识或批判的任务,更在无形中消解了“长毛”带来的种种恐惧。在《阿长与山海经》中,少不经事的“我”并不会去判断“脱裤挡大炮”一事到底是真是假,但却由此对阿长产生了敬意。这种看似荒诞的反应实则正是鲁迅想要表达的:相比于因为太平天国的流言而恐惧的成人,只有在儿童那里,太平天国的往事才能真正地被“故事”化。从“时予已九龄”的文法来看,《怀旧》实际上是成长之后的“吾”的回忆,和《阿长与山海经》以“我”讲述童年故事的叙事视角是接近的,而《风波》则明显是由文本外的叙述者所建构的故事。作者主体明确介入文本的现象表明鲁迅在有意地使用儿童视角,以儿童的回忆锚定太平天国的“过去”意义的同时也试图以之消解这些“过去”对于文本现实的意义。儿童无法成为批判的主体,但未经世事的他们也暂时免疫了对暴行的认知,而完全从天性出发去理解这些“故事”,才得以带着戏谑的观点在文本层面消解了因长毛引发的集体无意识的恐惧。
从上述对太平天国书写的形式特征可以看出,鲁迅希望将太平天国塑造为集体无意识中的“幻觉”,在虚假中真实地暴露国民的劣根性。与此同时,儿童作为一个独特的存在,本身既未真实经历过太平天国,其精神又尚未被纳入为集体无意识中,其态度反而这类事件的虚无特性,从而在加深了对国民性反讽的同时又揭露了太平天国书写作为“幻觉”的本质。从作为个体的儿童和群体的民众对长毛的不同反应,可以看出鲁迅书写太平天国的一部分内涵。但在更广阔的意义上,对太平天国的书写还和鲁迅文艺思想从“反抗”到“暴露”的整体性变革中,对中西时间观差异的把握有关。
三、书写的内蕴:启蒙视点下对循环时间观的批判
鲁迅对太平天国的态度是批判的,他在杂文中明确地对长毛作出了“恶”的评价,甚至将《怀旧》中有关长毛的残酷事迹复刻到了《阿长与山海经》之中。但若从由此直接理解其书写意图还是过于浅薄,鲁迅绝不仅仅是将太平天国作为工具性的“他者”而使之服务于文本的批判,而更关乎在历史关照和文学创作的双重前提下对文艺思想的艺术呈现。是以,在通过鲁迅文艺思想的发展、变化轨迹之中寻找太平天国书写的多重内在意义的同时,也能将后者作为照见其部分变化变化轨迹的一种视角。
不妨以写作时间最早的《怀旧》作为切入点。鲁迅在晚年的书信中曾提及《怀旧》的创作,但其回忆多有错漏。(16)参见鲁迅:《340506 致杨霁云》,《鲁迅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92-94页。而周作人对《怀旧》的回忆是:
他写小说其实并不始于《狂人日记》,辛亥冬天在家里的时候曾经写过一片,以东邻的富翁为“模特儿”,写革命的前夜的事,性质不明的革命军将要进城,富翁与清客闲汉商议迎降,颇富于讽刺的色彩。(17)周作人:《关于童二树》,《瓜豆集》,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12年,第156-157页。
若采用周作人的说法,那么《怀旧》的现实背景即是革命军将要进城引发了城内诸人投降的众议。对“投降”举动的讽刺自然已由金耀宗、秃先生等角色承担,但为什么鲁迅要把革命军替换成“长毛”呢?这里首先涉及到鲁迅对革命的态度问题。鲁迅在1911年曾为以宣传革命为目的而新成立的“越社”编辑刊物,并参与修改、圈断由周作人起草的,强调小学教育对共和自治之重要性的《维持小学之意见》一文,再有就是于1912年应蔡元培邀请赴南京任职时自觉“中国将来很有希望”(18)鲁迅:《两地书 第一集 北京 八》,《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1页。。从上述诸事可以看出,辛亥年前后的鲁迅对革命的态度是积极且认可的,但在辛亥年末创作的《怀旧》一文中,革命军不仅由长毛所取代,整篇文章也未见高昂的精神格调,反而在沉郁中显出几分荒诞。笔者认为,这可能是反映鲁迅文艺观从早年的“反抗”向“五四”时期着力于国民性批判转变的一个侧面。在这种转变中埋藏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一种视点。
留日时期的鲁迅以“反抗”为旨归,译介了许多被压迫民族的文学作品。对此他自述:“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论,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19)鲁迅:《我怎么做起小说来》,《鲁迅全集》第4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5页。。虽然鲁迅并不像章太炎那样高扬“排满”等直白的革命口号,但其立意仍在“反抗”这一基于个体自觉并带有革命色彩的行为上。而自“五四”以降,鲁迅在《呐喊》《彷徨》和一系列杂文中着重对国民性展开了深刻的批判。他自己的观点是:“最初的革命是排满,容易做到的,其次的改革是国民改革自己的坏根性,于是就不肯了。所以此后最要要紧的是改革国民性,否则,无论是专制,是共和,是什么什么,招牌虽换,货色照旧,全不行的。”(20)鲁迅:《两地书 第一集 北京 八》,《鲁迅全集》第11卷,第31-32页。相比于政治革命,在思想上革去国民的劣根性尤其重要,是以经历了二次革命失败等事件的鲁迅,在“五四”转向国民性批判自然顺理成章。但从《怀旧》来看,鲁迅对国民性批判的思考也许在民国前夜就已经萌芽。若最终来到镇上并得到款待的是革命军,则难以表达对秃先生、金耀宗乃至王翁等人的讽刺,作品本身的艺术和思想格调也可能受到影响。虽然鲁迅在《杂忆》中批判过革命军进城后的一些劣迹,但在文本语境中,革命军和“长毛”的意义显然存在着差别。与新政权相联系的革命军相比,与“短毛”“花绿头”分有着类似之“恶”的“长毛”,更易于成为鲁迅发掘国民性批判资源的载体。作为一次反清的政治运动,其未能得到留日后同样热衷于民族革命的鲁迅认可的原因即在于其分有着往昔政权的“恶”的共性。这种“恶”并不是某个政权所独有,而是和中国的历史、文化传统有关。作为“他者”的太平天国被鲁迅反复置于“过去”这一文本语境中进行书写,其即暗示着鲁迅站在启蒙立场上发现了国民性批判的一个角度——时间。
中国古代遵行的是往复的循环时间观,鲁迅也意识到了这种循环时间观的特点,并曾将整个历史表述为“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和“暂且坐稳了奴隶的时代”的反复。而在西方启蒙现代性思想中,时间是向前线性发展的。这种不同的时间视点成为了鲁迅赋予太平天国书写以批判意义的角度。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数千年未有的共和政权,理应成为时间的新起点。但从鲁迅作品中一以贯之的国民性批判来看,他担心的正是无法与政权同步更新的国民性的遗祸。这种在数千年的礼教思想中成形的国民性包含了旧日权威的恐惧和崇拜,并由此散发出诸如奴性、内斗等更多的具体恶质。九斤老太口中的“一代不如一代”,就暗示着对“过去”的崇拜。她口中的长毛并无善恶之分,唯独因为其属于“过去”而被反复提及;赵七爷对七斤说:“长毛时候,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21)鲁迅:《风波》,《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495页。但实际上这句话是满清入关时对汉人的恐吓。赵七爷在恐吓七斤时混淆了清廷和长毛,这不仅意味着“皇帝坐龙庭”这样的政治事件对他的影响不外乎将辫子重新扎起,重要的是他能够借助旧的权威来攻讦七斤。在民众混沌的政治无意识中,鲁迅发掘到了某种实质:无论是清廷还是“长毛”,都是历史循环的一部分,其给民众的苦难带来的苦难是一致的。
在《长明灯》中,鲁迅曾借庄七光之口点出,长明灯“连长毛造反的时候也没有熄过……”(22)鲁迅:《长明灯》,《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9页。,这暗示着长毛也可能是鲁迅长久批判的传统礼教和吃人秩序的受众。《怀旧》中的秃先生固然迂腐,但却在无意间点破了“长毛”和“官兵”的共性。当金耀宗希望他书“顺民”二字以彰身份时,秃先生这样说:“昔髪逆反时,户贴顺民字样者,间亦无效;贼退后,又窘于官军”(23)鲁迅:《怀旧》,《鲁迅全集》第7卷,第228页。,长毛固然反清,但在此之余对民众同样施以杀戮,不服者如赵五房等同样要被砍头。是以,长毛和清廷实际上都代表着传统的循环时间观中,以暴力使民众成为奴隶的奴隶主政权。鲁迅早年推崇强力的“反抗”,但强力并不等于暴力,这使他将长毛也定性为“恶”的最主要原因。通过太平天国书写,鲁迅将这种“恶”在“过去”这一独特的时间话语中进行表现,表达出了他对革命发展的忧思与期待。推翻帝制,实施共和固然是当时接受了现代启蒙思想的知识分子的共同愿望,但鲁迅更从太平天国的书写中发出了深刻警惕:倘若不改革国民性,这类看似已经被推翻的奴隶主政权和一系列属于过去循环的旧日幽灵,就可能被国民的集体无意识所“复活”。
最后,鲁迅着重通过回忆的儿童视角去书写太平天国的举措,即和他站在“立人”的立场上对儿童的认识有关,这和《狂人日记》中的“救救孩子”也是有关系的。未被旧思想支配的孩子不仅对太平天国往昔的愚昧和暴行产生了消解,更是鲁迅在“立人”的思想关照下为打破这种历史循环所安置的希望。孩子们并未亲身经历太平天国,长毛对他们来说也是确凿地只是“故事”。他们的思想一方面未被传统礼教扭曲,更尚未被将个体拉向“过去”的国民集体无意识所俘获,其成长的历程指向了充满可能性的未来。是以,“没吃过人”的孩子才而具备着出离幻觉、冲破循环的可能,从而被鲁迅赋予了消解与建构的意义符码。
四、结语
在从“反抗”走向“批判”的思想转变中,作为启蒙者的鲁迅将太平天国作为一个历史的“他者”展开书写,最终发现其历史局限性的同时,亦借其对国民性展开了深刻的批判。鲁迅将批判的最终目的指向对国民性的再造上:太平天国是局限于历史循环中的一个“幽灵”,但其仍可能由于集体无意识的劣性而被“招魂”甚至复归。基于从留日到“五四”时期一直延续着的“立人”观点,鲁迅从孩子的角度出发,暗示着启蒙对破除这种历史循环所造就的集体无意识的可能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