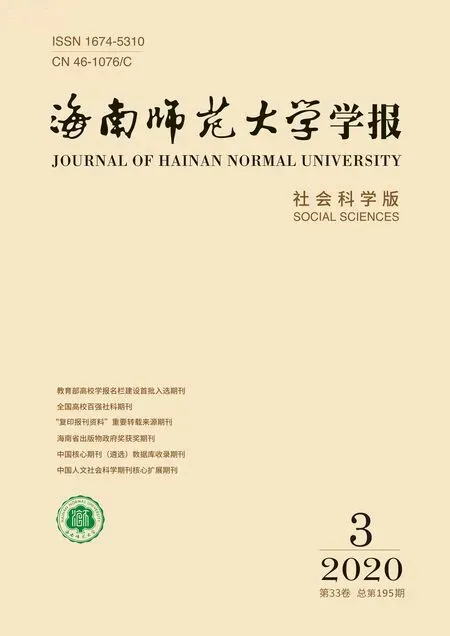“五四”的观看之道
——以瞿秋白为中心
傅修海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东 广州 510642)
“五四”百年,无论回望与展望,都是人们基于当下语境和心境,以“五四”为起点的一种情境化的自我思考。这个意义上的“五四”名与实,短而言之是百年前那一天的历史故实,综而观之则是以那一天为中心的前后漫溯及其相关体认与总结。无论是“短而言之”,还是“综而观之”,“如何说”和“说什么”固然重要,更重要的却是“由此观之”的当下情境与试图从此而“再出发”的未来之思。
瞿秋白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事业的早期领导人,是变革时代潮流中成长起来的“五四”一代,也是“五四”与“五四时期”的亲历者,更是有生之年不绝如缕地自觉对“五四”不断进行回望与反思的先驱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探究瞿秋白对“五四”的“观看之道”(1)约翰·伯格认为:“注视是一种选择行为。注视的结果是,将我们看见的事物纳入我们能及——虽然未必伸手可及——的范围内。触摸事物,就是把自己置于与它的关系之中。”(参见[英]约翰·伯格:《观看之道》,戴行钺译,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第2页。)在这种意义上,我认为瞿秋白的“五四”之思,恰恰体现出了一种“观看”。,即他的“五四”言说与历次“五四”回望之心路历程,而不仅仅局限为柄谷行人所说的“装置”性质的“风景”(2)[日]柄谷行人:《日本现代文学的起源》,赵京华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14页。,也不妨是百年“五四”思索的一种题中之意。所谓“看风景的人”及其眼中的风景,本身也是一种风景。
一、旁流杂出的欧化:瞿秋白的“五四”现场
瞿秋白于1909年秋天开始接受新式中等教育,他回忆自己“受欧化的中学教育时候,正值江南文学思想破产的机会”(3)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23页。。瞿秋白对这段新式中学教育的印象很糟,认为所谓的“欧化”是“死的科学教育”,而且“敌不过现实的政治恶象的激刺,流动的文学思潮的堕落”(4)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3页。。于是,他“处同样的环境,大家不期然而然同时‘名士化’,始而研究诗古文词,继而讨究经籍;大家还以‘性灵’相尚”,“和社会隔离”。(5)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4页。
瞿秋白1917年暮春到北京闯生活,曾旁听过北大中文系陈独秀、胡适等先生的课程(6)参见《党史资料》丛刊总第4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75页。,本想“能够考进北大,研究中国文学,将来做教员度过这一世”(7)瞿秋白:《多余的话》,《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695页。。然而迫于生计,他首选了参加北京文官考试,未果。然后他又于1917年9月考进北洋政府外交部设立的俄文专修馆习俄文,以期在短平快的学习模式中迅速取得独自谋生的资格。
1919年5月4日,五四运动爆发。然而,这一俨然划分时代的大事件,对当时沉浸于日常生活中的许多人而言,不过是“陡然”爆发的。即便如瞿秋白这种对代际感觉较为敏锐的新学生,他也只说自己是“卷入漩涡”,“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8)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这一说法显然与许多同代人的后世记忆大异其趣,其间的被动感超过了主动参与意识。对于后世仰之弥高的“五四”,瞿秋白的回忆与描述简直算得上过于朴素,真切呈现穷学生在大时代中更为常态的被动和激情。而真实情况也是如此。毕竟“五四”时期的思潮纷乱混杂,不定一尊,没有哪种思潮主义能够独大或独霸一方:
从孔教问题,妇女问题一直到劳动问题,社会改造问题;从文字上的文学问题一直到人生观的哲学问题;都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9)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
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其时一般的社会思想大半都是如此。(10)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6页。
卷入漩涡的瞿秋白,自然成了历史潮流中的一员,甚至是干将。此后,瞿秋白与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许地山等人组织创办《新社会》旬刊。后来《新社会》被封,他们继而创办《人道》月刊,直到1920年10月,瞿秋白赴俄考察成行。至此,因“五四”而提前入社会的瞿秋白,弯道超车般地冲到了“五四”时代的最前面。
从“死的科学教育”的“欧化”,到“正如久壅的水闸,一旦开放,旁流杂出”的“欧化”,截至赴俄考察之前,瞿秋白对“五四”前后的“五四”认知,都是“欧化”的定位,不过前期是教育知识模式和教育训练思维上的向西方看齐,后期则是思想启蒙和主义选择上的向西方取经、取西方思潮为宗。变化当然也是显而易见的,那就是此前是西化“科学教育”的“死”反感与拒绝,后期则是“在这一时期兴起,萦绕着新时代的中国社会思想”的“旁流杂出,虽是喷沫鸣溅,究不曾自定出流的方向”的活力四射的现代倾慕与向往。
二、以俄为师的现代:瞿秋白的“后五四”生长
在历史拐点的旁流杂出的诸多选择里,瞿秋白“没有办法”且“不得不”地被“阴影”领入了彼时世人所恐怖的“黑甜乡”——苏维埃俄国——去了。迄今仍令人讶异的是,他居然曾经是那么顿挫抑扬地表述自己当初选择“俄化”的一番心态:
我既挣扎着起来,跟着我的“阴影”,舍弃了黑甜乡里的美食甘寝,想必大家都以为我是疯子了。那还有什么话可说!我知道,乌沉沉甘食美衣的所在——是黑甜乡;红艳艳光明鲜丽的所在——是你们罚疯子住的地方,这就当然是冰天雪窖饥寒交迫的去处(却还不十分酷虐),我且叫他“饿乡”。我没有法想了。“阴影”领我去,我不得不去。你们罚我这个疯子,我不得不受罚,我决不忘记你们,我总想为大家辟一条光明的路。我愿去,我不得不去。我现在挣扎起来了,我往饿乡去了!(11)瞿秋白:《饿乡纪程·绪言》,《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5页。
选择以俄为师的现代,这既是瞿秋白“后五四”时代的生长,当然也是瞿秋白式的现代中国与当代中国的“五四”式的第一次链接。这也是一种摩登,另一种现代,所谓革命的现代。
就文学向度而言的观察,瞿秋白的“后五四”生长的逻辑转向也是很清晰的。两年的旅俄考察期(1921—1922),瞿秋白系统梳理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学史,并根据自己对俄国革命的现实经验和理解写成了《俄国文学史》。这是瞿秋白第一次以现代意味的“文学史”名目来表述其对俄国文学史的系统观照。在这部《俄国文学史》中,瞿秋白根据社会历史进程,梳理了俄国十月革命之前的文学潮流更替、思想变迁与历史进程转换的关系,初步体现了瞿秋白对一些现代文艺思想基本观念的理解和运用。尽管全书采用的是专题式随感,另加读书心得式记述,不像是一部有着自己独立文学史思想的通观性著作,更像是俄国文学史自学笔记综述。在一定意义上,这种习得模式,事实上与当代高等教育自学如出一辙,更与中国当代高教发展的工农阶段里的现学现教、教中学、学中教的方式高度一致。自力更生的成长固然见出勤苦与勇敢,但夹生与交缠、误解与正解的辩证交错带来的后遗症也是相伴相生的应有之义。
经李大钊推荐,1923年7月20日,在考察与被考察中成长的瞿秋白出任上海大学教务长兼社会学系系主任,讲授《社会学概论》和《社会哲学》。这些课程中,有内容论及关于艺术的社会学理解和哲学把握。本来,对知识进行现代体系的梳理和建构,是现代社会科学的一大特征。但瞿秋白通过俄文专修馆里的学习和在俄考察期间的翻译式、编校式自学,接受了现代社会科学的思想方法和梳理体系的同时,思想上也带上了强烈的俄化色彩。1923年10月,瞿秋白从俄国文学史的十月革命化理解的学习体会中现学现用俄苏式现代革命的文学史观,写下了《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以下简称《荒漠里》)。
《荒漠里》分为两部分。正文前面缀有一篇“小叙”(12)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312页。。“小叙”的开篇表明瞿秋白对1923年中国文学状况的感觉——“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13)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1页。,新文学仍然是“霞影里的屋楼,是我孤独凄凉的旅客之唯一的安慰。然而他解不得渴”(14)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1页。。彼时瞿秋白对“五四”文学革命有一比喻,“文学革命的胜利,好一似武昌的革命军旗;革命胜利了,军旗便隐藏在军营里去了,——反而是圣皇神武的朝衣黼黻和着元妙真人的五方定向之青黄赤白黑的旗帜,招展在市侩的门庭”(15)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2页。。现在“‘文学的自话,白话的文学’都还没有着落”(16)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2页。,中国的拉丁文“废了,中国的现代文还没有成就”(17)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2页。。瞿秋白继而严厉指出“五四”文学革命后的翻译文学没有“丝毫现实性和民族性”(18)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2页。,是一种“外古典主义”(19)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3页。,进而呼唤“中国新文学”这个“好妹妹”“从云端里下落,脚踏实地”,因为“许多奋发热烈的群众,正等着普通的文字工具和情感的导师”,如此文学世界才能真正有“劳工的诗人”的“劳作之声”(20)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4页。。
此文思维逻辑简单。但瞿秋白这种以“革命”起点切割文学史的思路却从此蔚为壮观,成为后世现代文学史重新叙述的固有思路模式。正如在1927年2月17日的《〈瞿秋白论文集〉自序》里强调的:“革命的理论永不能和革命的实践相离。”(21)瞿秋白:《〈瞿秋白论文集〉自序》,瞿勃,杜魏华整理:《瞿秋白论文集》:重庆:重庆出版社,1995年,第 1页。事实上,在“五四”之后,“五四”就不再是、也不可能再是一个人的“五四”,它已经成为了一个起点,一面旗帜,是应该有、也必须有一种理论与之相随的一段实践。
两年的俄国实地考察走访与调研,瞿秋白从“黑甜乡”里确认了当初领着他去俄国的“阴影”,并在此红光照耀下返回到“五四”文学现场。彼时那个曾经把他卷入的“漩涡”地、他曾经“抱着不可思议的‘热烈’参与学生运动”(22)瞿秋白:《饿乡纪程·四》,《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25页。的“五四”文学现场,而今却是“好个荒凉的沙漠,无边无际的”(23)瞿秋白:《荒漠里——一九二三年之中国文学》,《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311页。。革命需要野蛮生长,文学现场既然如此,革命当然就英雄大有用武之地。倘若说“五四”时代是主义的火星四溅,那“后五四”时代则是开荒播火的准备期。无独有偶,瞿秋白“荒漠里”的心碎感与激愤情绪,恰好与另外一位战士诗人闻一多1925年的“一场空喜”“噩梦”的“发现”(24)闻一多:《死水》,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第29页。异曲同工。发现也好,荒漠也罢,总而言之,时间开始了,只不过不是“五四”时间,而是“五卅”开启的另一种关于五月的时间理解——“红五月”(25)“红五月”的强调是中国共产党对“五四”记忆的改造与革命放大叙述,类似的文章在中央苏区时期的宣传品尤其突出。相关讨论可参见杨会清:《“红五月运动”的兴起及其运作模式(1921—1935) 》,《中共党史研究》2008年第6期;梁化奎:《“红色的五月”与瞿秋白的“革命”叙事》,《山西大同大学学报(社科版)》2017年第2期。。
三、本土化与大众化:瞿秋白的红“五四”锻造
“红五月”的苏区塑造不仅是革命宣传,更是实际政治与革命斗争的一部分。因此,在真刀真枪的语境里,思想比重为主、文学文化底色为辅的“五四”元素在“红五月”里当然并不是主要的。“红五四”的文学言说与文艺思想史嵌入,仍旧是从瞿秋白开始的。
1931年4月,因被排除出政治中心而回返文学园地的瞿秋白,开始以一名有着丰富实践斗争经验的战士心态来领导文艺战线。此时,瞿秋白的现代文学史观不仅更加成熟,也更加清楚意识到在“话语霸权”锻造意味上的革命工作的重要性。这既是瞿秋白为自己量身定做的、退而求其次的革命工作自觉,更是他作为中国共产主义革命先驱者在思想上的远见卓识之处。(26)参见傅修海:《时代觅渡的丰富与痛苦——瞿秋白文艺思想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第51页。
“红五四”的锻造、整理与叙述,在瞿秋白以及“左联”等主持和参与的一系列文艺论战中开始了。自然,这也正是瞿秋白所说的——为“五四”文学实践寻找理论伴侣的工作。瞿秋白“红”化“五四”的第一响,便是力作《鬼门关以外的战争》,名称就透露出置之死地而后生的“反击”力度和“战争”志趣,时为1931年5月30日。文中,瞿秋白提出要进行“第三次文学革命”——“文腔革命”来开辟新的文艺战线和提出新的革命任务,把“五四”文学革命定为第二次文学革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是“真正的文学革命”“的确形成了一种新的言语”,其历史意义首先在于“明白的树起建设‘国语的文学’的旗帜,以及推翻礼教主义的共同倾向”。而要实行“文腔革命”,必须建立“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27)瞿秋白:《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64页。。
在随后的《学阀万岁!》里,瞿秋白再次详细讨论了“五四”运动的“光荣”所在。瞿秋白说:“‘五四’的‘光荣’多得很。现在我们只讲‘五四’的文学革命的成绩。固然,‘五四’的文学革命和当时的一切种种运动:爱国运动,社会运动,妇女运动,反对礼教运动等等,都是密切相关的,仿佛留声机和唱片的关系一样。”(28)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74页。瞿秋白也以反语方式指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白费,认为“这次文学革命,和国民革命‘大不相同’,差不多等于白革”,同时强调说“所说的是‘差不多’,并不是说完全白革。中国的文学革命,产生了一个怪胎——象马和驴子交堵,生出一匹骡子一样,命里注定是要绝种的了”(29)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76页。。这就是瞿秋白著名的“五四”乃“骡子文学”说。瞿秋白认为“五四”文学革命不彻底的原因,“除出中国社会实际生活里面的许多原因之外,还有一个‘次要的’原因,就是‘文学革命党’自己的机会主义”(30)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76页。。瞿秋白说:
文学革命本来首先是要用文学上的新主义推翻旧主义,用新的艺术推翻旧的艺术。但是,在二十世纪的中国,要实行这种“文艺革命”,就不能够不实行所谓“文腔革命”——就是用现代人说话的腔调,来推翻古代鬼说话的腔调,专用白话写文章,不用文言写文章。而且,要彻底的用“人腔”白话来代替“鬼腔”文言,还必须废除汉字,改用拼音文字,就是实行“文字革命”。这在所谓“五千年持续不断的”古文化国,是多么严重艰苦的革命斗争。而“文学革命党”,却用那么妥协的机会主义策略来对付!自然,文学革命弄到现在,还是非驴非马的骡子文学了!(31)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78-179页。
除了从革命彻底性的高度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外,瞿秋白还分别对“五四”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分别进行检讨和批判,认为由于“五四”文学革命的不彻底性,革命文学的“三大主义”的光荣都变质了。(32)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98页。
在《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中,瞿秋白第一次从两个方面彻底否定“五四”文学成就的两方面:一是“五四式的半文言”(33)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45页。——“这种假白话文是五四式的白话文的正统”(34)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88-289页。,“五四式的新文言,是中国文言文法,欧洲文法,日本文法和现代白话以及古代白话杂凑起来的一种文字,根本是口头上读不出来的文字”(35)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16页。;二是“五四”的文学革命“等于政治上的国民革命,就是变成了最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反革命”(36)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45页。。此文甚至第一次出现瞿秋白对汉字的激烈的完全否定,把汉字说成“真正是世界上最龌龊最恶劣最混蛋的中世纪的毛坑! ”(37)瞿秋白:《普通中国话的字眼的研究》,《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47页。
然而,当重点从“五四”文学革命转移到“五四”白话的时候,瞿秋白已不仅是在讨论“五四”的文学意义,而是讨论“‘五四’文学”的“语言”意义了。瞿秋白转向从语言变革的贡献反过来评价“五四”文学革命的功绩。他说:“‘五四’的白话运动当然有它的功绩。它打倒了文言的威权。但是,它的使命已经完结,再顺着它的路线发展下去,就是——用改良主义的假面具,掩护事实上的反动,扛着‘白话文’的招牌,偷卖新文言的私货,维持汉字和文言的威权,巩固它们的统治地位。”(38)瞿秋白:《新中国的文字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92页。
至此,瞿秋白的“五四”叙述史清理,走过了从文学革命到文学语言革命,再到文学革命的回路。其中,无产阶级革命彻底性是总评价标准。在1931年春的《致新兄》中,瞿秋白甚至把“‘五四’的文学革命是半路上失败了,现在需要第二次的文学革命”(39)瞿秋白:《致新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339页。的总体判断认为是个“原则上的问题”。(40)瞿秋白:《致新兄》,《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339页。
彻底性的探求正是瞿秋白“红五四”锻造工程的基因转化酶。此后,瞿秋白的“红五四”叙述,都是根据实现文学革命和语言革命彻底性的具体化目标——文艺大众化和现代普通话展开的。1931年10月25日,瞿秋白作《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正式提出“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41)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465页。。其实,这也就是在瞿秋白代拟的中央文化工作委员会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里提到的:“革命的文化运动的大众化,就是目前最重要的中心问题”(42)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31页。,“苏维埃的文化革命,是在文化战线上彻底完成民权革命的任务,为着社会主义而斗争”(43)瞿秋白:《苏维埃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第232页。。
从《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为发动“第三次文学革命”而提倡“文腔革命”,到《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呼吁“中国需要再来一次文字革命”(44)瞿秋白:《普洛大众文艺的现实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第465页。,再到《“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的大声疾呼;从“无产阶级革命”到“文学革命”“文腔革命”,从“文字革命”到“文化革命”,从“文艺大众化”到“汉字拉丁化”“现代普通话”。围绕着“红五四”的完形,瞿秋白的论述逻辑趋于极端:一则偏于语言文字问题,一则偏于民族文化问题。“偏”的好处固然有深刻,但弊病则是有所废弃,不得圆通。1932年5月18日,瞿秋白写《“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源和〈文化评论〉》,涉及“五四”文学革命精神继承人的资格,“问题的中心”是阶级立场。瞿秋白明确指出:“而‘自由人’的立场,‘智识阶级的特殊使命论’的立场,正是‘五四’的衣衫,‘五四’的皮,‘五四’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的遗毒。‘五四’的民权革命的任务是应当澈底完成的,而‘五四’的自由主义的遗毒却应当肃清!”(45)瞿秋白:《“自由人”的文化运动——答覆胡秋源和〈文化评论〉》,《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年,第501-502页。瞿秋白牢牢地把握住了“五四”革命立场与革命领导权的“话语权”。
在革命政治斗争异常激烈的大时代,革命立场是所有问题最后和唯一的标杆。既然“五四”成了历史合理性叙述的重要资源,那就不是论争和局部重构的问题,而须系统化建构。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堪称个中力作。该文同时被收入《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和政治理论编第7卷(46)收入《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7卷时题目稍有出入,“五四”没有引号,题为《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其它内容完全一致。,也说明其意义非同寻常。文中,瞿秋白主要阐述“只有无产阶级,才是真正能够继续伟大的‘五四’精神的社会力量!”(47)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第23页。的核心观点,从革命领导权的转移系统论述了从“五四”到“红五四”的必然之路:
“五四”是中国的资产阶级的文化革命运动。……新的文化革命已经在无产阶级领导之下发动起来,这是几万万劳动民众自己的文化革命,它的前途是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前途。(48)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2页。
“红五四”当然是“五四”的历史和逻辑的必然。瞿秋白因此强调“无产阶级决不放弃‘五四’的宝贵的遗产”(49)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3页。,并对“‘五四’的遗产是什么”(50)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3页。的问题进行界定,倡导“来一个无产阶级的‘五四’”(51)瞿秋白:《大众文艺的问题》,《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3页。。至此,瞿秋白的“红五四”观基本定型。
1932年3月5日,瞿秋白重写《大众文艺的问题》。6月10日该文在《文学月报》第一期发表,也就在这天,瞿秋白给鲁迅写了一封名为《关于整理中国文学史的问题》(52)这是瞿秋白1932年6月10日写给鲁迅的信,1950年上海鲁迅纪念馆整理鲁迅藏书时发现手稿,题目为1953年辑入八卷本《瞿秋白文集》第3卷时编者所加。的信。这是自《荒漠里》之后,瞿秋白再一次观照中国文学史。显然,这一次的梳理,不仅对象阔大——它不再是对某一年的文坛现场的瞭望,而是涉及到对中国文学史的整体放观与设计。然而最根本的变化是,在这一封信里,“红五四”正式凝聚为瞿秋白“革命”化整理中国文学史的一盏“闪闪红灯”。
岳飞的《满江红·写怀》词云:“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该词句中家国情怀的豪迈,其实与闺阁情调中“头未梳成不许看”的顾虑,颇有相通之处,那就是历史现场中的人事,事前、事中与事后的心态和情态都在变动。历史事件与历史书写的关系,哪怕是恢弘如“五四”者,大凡亦如此,都存在着整理和叙述的诸多微妙之处。而历史与现场的张力,形形色色的回望、叙述与辩护,也就往往融化在这诸多角度、高度、深度各异的观看之道中。瞿秋白曾有云:“‘五四’的娘家是洋场”。(53)瞿秋白:《学阀万岁!》,《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190页。比喻总是跛脚的。瞿秋白此一精警比喻的言下之意,不仅传达了他从“欧化”到“俄化”,再从“俄化”到“红化”(即本土化、大众化)的“五四”观看之道的变迁,也永远回荡着对“‘五四’的遗产是什么”(54)瞿秋白:《“五四”和新的文化革命》,《瞿秋白文集》(文学编)第3卷,第23页。的追问与思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