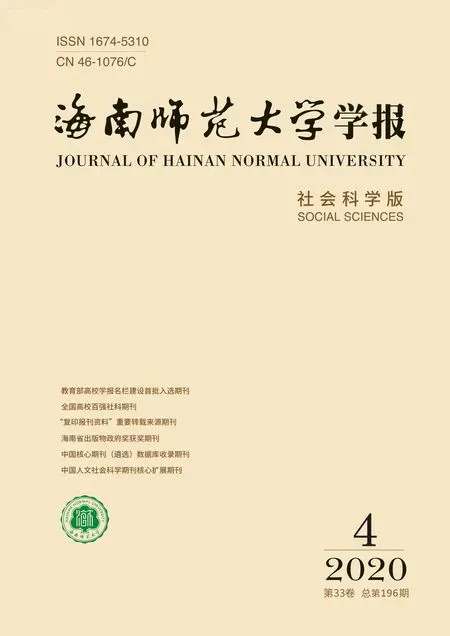“智者”教育之旅的“迷雾”:“五四”时期杜威访华若干问题之厘清
李 永,周洪宇
(1.中南民族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2.华中师范大学 教育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1915年9月15日,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成为新文化运动兴起的标志。在新文化运动注重民主启蒙的背景下,以哥伦比亚大学(以下简称“哥大”)师范学院归国留学生为核心的一批新知识分子群体,力邀“美国教育大家”“世界思想领袖”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以下简称“杜威”)来华讲学,希望借助杜威的学说建设新教育,并通过教育实现“人”的现代化、“人”的启蒙,进而实现国民性的改造。访华期间,杜威的学说也在一定程度上呼应了“五四”运动所倡导的爱国、进步、民主、科学的时代精神。
1919年4月30日杜威到达上海,4天后“五四”运动爆发。这是一场以先进青年知识分子为先锋,广大人民群众参加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伟大爱国革命运动。李泽厚认为:“在一个短暂时期内,启蒙借救亡运动而声势大张,不胫而走。”(1)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上海:东方出版社,1987年,第15页。从这种意义来说,“五四”运动扩大了杜威在中国的影响,加深了杜威与中国的情谊,并戏剧性地改变了杜威的短期访华之旅。杜威所宣传的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因内容精深、适合所需、易于接受而颇为流行。知识分子与普通民众倾听了杜威的演讲,阅读了杜威的报道,讨论了杜威的思想。杜威在当时被誉为“德先生”与“赛先生”的化身,获得了极高的声誉。1921年8月2日,杜威返美以后,有关此行的探讨虽时涨时落,但却从未停止。当前有关杜威访华之行的初衷、组织、经费、续假、往返时间等问题,在学界或尚未关注,或存有异议,或谬误频出。通过对上述问题的释读,有助于还原一个真实的访华之行,并以此纪念杜威访华一百周年。(2)20世纪80年代,黎洁华发表了《杜威在华活动年表》(上中下)(《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1985年第1-3期)。该文粗略勾勒了杜威在华期间的主要讲学活动,但是在杜威女儿露茜到达时间、杜威返美时间上存有纰漏。王剑和陈文彬分别在《“杜威中国之行”若干史实考释》(《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3期),《邀请美国教育家杜威访华的台前幕后》(《兰州学刊》2006年第7期)中对杜威访华的细节做了补充与修正,但是尚缺少对杜威访华始末的整体解读。2019年,时值杜威来华讲学一百周年,中国教育学界为纪念这个特殊的历史事件,相继在权威杂志《教育研究》以及《北京大学教育评论》《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教育科学研究》《宁波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等期刊发表专题论文。但是上述文章的部分作者对杜威访华的若干记述,依然沿用旧有观点,导致史实疏漏,影响事实本身。
一、东亚之行的初衷
就杜威而言,1919-1921年的访华之旅,在情理之中,又在意料之外,偶然性与必然性并存。杜威访华肇始于日本之行。1918-1919学年是杜威在哥大的休假年,当时杜威客座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授课。杜威对东方国家怀有兴趣,一直期待能到东方进行一次旅行。1918年12月9日,他给友人的信中写道:“照现在的情形,我们度假最远所能到达的地方只能是日本了。”(3)[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9年,第294页。
杜威休假期间只有一半薪水,如果开始日本之行,经费从何而来。杜威的好友阿尔伯特·C·巴恩斯(Albert C.Barnes)慷慨提议:每月给予杜威一笔津贴,但需要完成一份《未来国际形势的一个主要因素:日本》的报告作为回报。《新共和》(TheNewRepublic)杂志也承诺每月就杜威发表的有关日本政治、文化的文章给予津贴。再加上定期收到的版税,杜威将会有四五个月的经济保障,足以担负这次旅行。(4)Jay Martin,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2,p304.此外,杜威还得到了日本工业银行副总裁小野荣二郎的大力支持。小野留学密歇根大学期间与杜威相识并成为好友。(5)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0年,第172页。作为联络人的小野博士找到当时日本财经界和慈善界的风云人物涉泽荣一男爵提供资助,并在东京帝国大学支持下在该校设立一项讲座基金(6)[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第294页。,从而妥善解决了杜威访日的经费问题。
上述条件虽然说明了杜威具备了访日的经济能力,但是为什么选择日本,为什么此时出行,则是另外一个问题。答案要从他的家庭说起。1886年杜威与艾丽丝·奇普曼(Alice Chipman)结婚后共生育了6个孩子,分别为长子弗雷德里克·阿奇博尔德(Frederick Archibald,1887年生)、长女伊芙琳(Evelyn,1889年生)、次子莫里斯(Morris,1892年生)、三子戈登·奇普曼(Gordon Chipman,1896年生)、次女露茜·艾丽丝(Lucy Alice,1897年生)、三女简·玛丽(Jane Mary,1900年生)。但是非常不幸,1895年3月,杜威一家在欧洲旅行时,2岁半的莫里斯因患白喉癌在意大利米兰去世。(7)[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第23页。1904年9月,再次赴欧旅行时,戈登在去爱尔兰途中因伤寒病复发而亡。(8)[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第34页。此行逗留意大利期间,杜威夫妇收养了一名与戈登年龄相仿的8岁意大利男孩萨比诺(Sabino)。1918年秋,5个孩子都已经长大。长子弗雷德里克参军了,长女伊芙琳定居纽约,次女露茜将于1918年12月从巴纳德学院毕业,三女简在1918年秋天成为了伯克利大学的新生,养子萨比诺找到了工作。(9)Jay Martin,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p305.
杜威夫妇终于可以自由地离开哥大、离开纽约、离开美国,离开战后混乱的政治局面以及战争带给杜威的希望与失望。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杜威由起初反战转变为支持参战。“如果能在美国本土之外弘扬推进民主制度,又能在美国本土之内深化理想主义,那么杜威则选择支持他曾为之担忧的战争。”(10)Jay Martin,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p305.但是,杜威对参战的支持却遭到了以伦道夫·S·伯恩(Randolph S. Bourne)为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猛烈批评,从而削弱了他在学术界的领导地位。(11)Shanshan Peng,‘A Journey to Mars:John Dewey’s Lectures and Inquiry in China’,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12,no.1,2018.此外,战事的进展也让杜威越来越失望。为了战争动员,美国政府肆意压制言论自由,许多持不同政见的教师被解聘,许多人受到政治迫害。杜威寄予很大希望的国际民主前景也堪忧。威尔逊总统的“十四点和平计划”在巴黎和会上基本落空,唯一的成果“国际联盟”又因欧洲战胜国拒绝德国和新生苏联的加入,埋下了新的战争隐患。(12)涂诗万:《杜威教育思想的形成》,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14年,第110页。
再者,杜威从内心深处希望这次旅行有助于治疗艾丽丝长期抑郁的情绪。十年间两次遭遇丧子之痛,加之1904年戈登逝世前,艾丽丝倾注心力经营8年之久的芝加哥大学实验学校被迫关闭。家庭与事业的双重打击,使艾丽丝的精神和身体每况愈下,再也没有能恢复从前的活力。最后,在私人方面,杜威在访华前的两三年都处于消沉的境地:参战言论导致事业上的攻击;身体方面脖子僵硬,患有眼疾,极度疲劳甚至无法写作;私生活方面与犹太女作家安西娅·耶泽尔斯卡(Anzia Yezierska)有染。这些事件都导致杜威身心疲惫。在此情形下,好友巴恩斯建议他访问日本。(13)Shanshan Peng,‘A Journey to Mars:John Dewey’s Lectures and Inquiry in China’,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12,no.1,2018.另外,杜威同意日本之行也可能是为了逃避两次欧洲之旅的伤痛回忆。
1919年1月22日,杜威夫妇乘坐日轮“春洋丸”(14)学界有学者误写为“春秋丸”。查阅1919年2月前后国内报刊涉及赴美的报道,使用均为“春洋丸”。《时报》1918年12月13日第3版《马尼剌电曰菲律宾上院议长克爱宋氏带有该岛独立运动之使命于去九日搭春洋丸赴美》的标题涉及“春洋丸”;《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7日第5版《陶履恭教授致校长函》记载“孑民先生鉴,春洋丸于十二日到神户”,也是使用的是“春洋丸”。离美赴日,于2月9日抵达横滨港。杜威夫妇受到了此次筹备工作负责人小野荣二郎博士、东京帝国大学负责人姊崎宏教授、友枝孝彦教授以及众多记者的欢迎。(15)[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第295页。江勇振认为:“杜威夫妇还在加州时,就计划在1919年5月份从日本到中国旅游几个星期”。(16)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第77页。鉴于中日距离较近,且中国也有不少哥大弟子,杜威既可以了解中国情形,又可以传播学说,一举多得,所以这个观点基本是成立的。
二、邀请来华的详情
在近代留学史上,哥大师范学院因为培养了众多留美教育学者而对民国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大影响。1904年杜威来到哥大任教。他虽属哲学系,但与师范学院亦十分密切。师范学院教育部成立时,他是首批被聘任的七位教授之一,(17)陈竞蓉:《教育交流与社会变迁:哥伦比亚大学与现代中国教育》,武汉: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42页。当时杜威每周在师范学院讲课2小时(18)[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第34页。,主讲《学校与社会》。
杜威顺道来华的设想,能否成行充满变数,具有偶然性。不过细细分析,来华却也有必然性因素。纵观杜威一生,东亚之行之后,他又访问了土耳其(1924年)、墨西哥(1926年)、苏联(1928年)、南非(1934年),从事国民外交。所以,即使日本之行未能到访,杜威来华也是早晚的事。就民国教育界而言,杜威访华前后,师范学院毕业生郭秉文执掌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南京高师”),李蒸、李建勋先后执掌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下简称“北京高师”),蒋梦麟代理北大校长,张伯苓执掌南开大学,他们与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张耀翔、欧元怀、汪懋祖、刘湛恩等一批教育科系的主任、教授成为了蔚为壮观的“哥伦比亚派教育家群体”的早期代表。他们求学哥大期间直接或间接受到杜威学说的影响,杜威可视为他们的业师。以这批杜氏弟子在民国教育界的影响,邀请杜威访华也是或早或晚而已。正如陶行知所言:“我两三年后所要做的事体,倒是日本先做去了”。(19)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书信)》,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5年,第2页。
1919年2月,1915-1917年就读哥大哲学系并师承杜威的胡适致函陶行知,告知杜威到访日本。陶行知立即将此事告知郭秉文,决定由郭秉文赴欧美考察战后教育途经日本时当面邀请杜威。1919年3月12日,陶行知回函胡适,动议“南北统一起来打个公司合办”,邀请杜威来华。(20)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书信)》,第2页。
1919年3月13日,郭秉文与北京大学教授陶履恭途径日本时,到东京专门拜访了杜威。陶履恭致胡适的信中写道,杜威夫妇“拟先到广东,然后到南京、北京,可在三处讲演。”“惟今年恐不能在华久留,以九月间拟回美授课也。”(21)《陶履恭教授致胡适之教授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3月27日第6版。杜威家书也记载了拜访之事:“他们希望知道是否可以跟哥伦比亚大学商量,让我明年留在中国一年,在北大以及另外一间大学教书。妈妈很有兴趣,我也差不了多少。我不置可否地说可以。这能不能成还不知道。他们显然想跟哥大提出一个交换的计划,让哥大付我的薪水,中国方面则付他们派去哥大的教授的薪水。如果哥大不让我留职留薪,他们就会付我薪水。”(22)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77页。
1919年3月27日,三位日本大学教授拜访杜威,希望安排好杜威在日本的每一处细节。但杜威深知三位日本学者不能明白,因为“一直到动身去中国之前,我们没法针对行程中的每一件事都给出一个完全准确的信息。”(23)[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刘幸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74-75页。换言之,至迟在此时,杜威已经确定访华。
1919年3月28日,杜威致函胡适,表示只要两边的大学商量好,愿意做一年的讲学。(24)《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译稿)》,《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8日第5版。当时面见杜威之后,郭秉文将其答应来华以及行程打算致函陶行知。1919年3月31日,接信当天陶行知就致函胡适商量接洽事宜。杜威“说四月中就可到中国,打算游历上海、南京、扬子江流域,一直到北京。”(2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第34页。陶行知还在信中建议,由北京大学、江苏省教育会、南京高师三个机关各举1名代表负责接洽事宜,陶行知已获南京高师推定担任此职。同时,陶行知还附上南京高师所拟接洽办法数条,请胡适与蔡元培等人磋商。
1919年4月15日,蒋梦麟致胡适函言及,虽然杜威尚未到来,但是南京、上海,以至于教育部都希望杜威讲演与教育有关的话题,(26)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36-37页。同时还告知自己已确定为欢迎代表。1919年4月28日,杜威夫妇搭载“熊野丸”轮离开日本前往中国。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到达上海。北京大学、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代表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到码头欢迎他们,并送入沧州别墅居住。1919年5月1日《时报》有云:“杜威博士,美国大思想家大教育家,久为吾国学界所钦佩。兹已于昨日下午到沪。”(27)《美国杜威博士到沪》,《时报》1919年5月1日第9版。1919年5月2日,杜威家书记载:“有一个欢迎委员会来迎接我们。这个委员会由几位中国绅士组成,他们大多数都是归国的美国留学生。”(28)[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第146页。
杜威访华是中美教育交流史上的一桩美谈。由于能否邀请成功尚不确定,所以初级目标比较简单,正如陶行知所言:“或者暑假的时候可以请先生到中国来玩玩,否则就到日本去看看他也是好的。”如果邀请成功,则希望杜威能“帮助东方的人建设新教育”,并将杜威的学说“传得广些”。(29)华中师范学院教育科学所编:《陶行知全集(第5卷书信)》,第2页。其实际结果却远超预期。胡适夸赞道:“没有一个外国学者在中国思想界的影响有杜威先生这样大的。”(30)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第2版。汪懋祖评价:“杜威博士来华,予吾人以新教育之概念与其途辙。”(31)蔡元培,黄炎培,郭秉文,汪懋祖:《第一次年会日刊发刊词》,《新教育》1922年第3期。
三、筹集经费的困境
“五四运动”爆发后,曾力劝学生不要上街的北大校长蔡元培联合北京各校校长保释学生,此举得罪了当权亲日派。蔡元培于1919年5月9日被迫辞职,悄然离京,使得北京大学一时无人主持,直接影响了杜威访华的接待经费。
1919年4月初蔡元培曾致电哥大校长巴特勒,敦聘杜威主讲于北京大学一年。此事从侧面反映了虽然提出邀请的是胡适等人,但官方层面蔡元培的支持才是杜威旅华讲学的关键。1919年4月29日,蔡元培致赴上海迎接杜威的胡适:“哥伦比亚大学如有复电,请转上。”(32)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412页。1919年5月12日,因为学生运动胡适返回北京。1919年5月13日,胡适收到巴特勒的电报,说给杜威假一年,但5月15日的第二封电报又补充说,所给的是无薪俸的假。(33)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25-26页。此处需要补充的是,作为知名学者,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后期年薪达5,000美元,哥伦比亚大学后期年薪达7,000美元。鉴于当时中美消费力的巨大差距,按照美国水准筹资对中方而言可谓一笔巨款。此时恰逢蔡元培请辞,这使得胡适、陶行知、蒋梦麟作为访学实际运作者焦虑万分,三人频繁联系、募集经费。
1919年5月22日,黄炎培、蒋梦麟致函胡适:“哥仑比亚已允给假,大学如散,上海同人当集万金聘之。”同时还提出了南方的预备方案,比如“杜威如在沪演讲,则可兼授新大学”等。(34)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47-48页。1919年5月26日,蒋梦麟致函胡适:“杜威留中国,其俸已由省教育会担保。任之与弟又要做和尚募化万余金。”(35)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0页。1919年6月1日,杜威北京家书有云:“我们昨天都达成了共识。”(36)[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第194页。估计与上述蒋梦麟信件提及的杜威薪俸以及后期安排有关。
1919年6月,胡适与范源濂商量杜威的讲学费用,范源濂主张利用社会上私人组织的力量。后经范胡两人联系,尚志学会担任六千元,清华学校担任三干元,“新学会”也加入筹款。(37)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26页。胡适日后回忆也提及,除了北大、南京高师、江苏省教育会最初三家之外,我们乃商请“北京一个基金会叫做尚志学会,筹集基金邀请杜威来华讲学,并分担全部费用”。(38)胡适口述:《胡适口述自传》,唐德刚译,北京:华文出版社,1992年,第109页。1919年6 月17日,杜威家书呼应了上述胡适等人的努力。“北大的情况仍然极不明朗。所以他们上星期对我说,他们了解我们对这悬宕的情况一定感到不安。如果北大的情况到秋天还不明朗,有一个私人的团体——我不太清楚是什么性质的——会承担我的所有费用,并负责安排一切。如果是这样的话,我们会在这里待到明年二月。二月开始往南移动,在接下去的四个月里,根据当时的情况,去南京、上海和广东。”(39)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87页。根据这封家书,似乎杜威不太清楚或不太关心经费来源。
1919年6月22日,胡适致函蔡元培抱怨杜威之事以及其他事情。“(二)是他(胡适)手里订了五年、七年的契约同杜威的事,忽然一拋,是对他(胡适)不住。”(40)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22页。1919年6月24日,陶行知、蒋梦麟致函胡适,“徒威(杜威)留一年,甚好。南京、上海方面准合筹四千元。”(41)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组编:《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8页。他们还对胡适来信所谈计划,估计为邀请社会组织加入杜威的接待问题表示赞成。1919年6月28日,蒋梦麟致胡适函中转达了即使蔡元培辞职,北大依然有履行契约以解决杜威薪酬之事的责任,即胡适“手里订的五年、七年的与杜威的契约,是替北京大学校长订的”。(42)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22页。
纵观1919-1921年间的胡适日记或日程,只有一处提及与杜威的经济往来,即1920年2月5日写道“杜威信,附$500”。(43)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19-192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82页。虽然不知道中方具体支付杜威薪水的数额,但是根据上文记录,尚志学会、清华学校、新学会的筹款至少9,000元以上,再有南京、上海方面(估计为南京高师与江苏省教育会)合筹4,000千元,所以至少有13,000元。这还不包括北京大学所需支付的一年讲座教授费用。1919年6月28日,蒋梦麟提及蔡元培的观点,“中国对待外国教习,是特别优待。”(44)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22页。由此可知,北大给杜威设定的待遇必然是高规格的。
综合分析,邀请杜威来华起初可视为弟子邀请老师之举,但从正式角度而言,则是北京大学、南京高师和江苏省教育会三个团体的组织行为,并分别得到所在机构负责人蔡元培、郭秉文和黄炎培的大力支持。其后由于经费问题以及宣传鼓吹,杜威之行吸引了多个团体加入。以随后两次代表性宴请为例:1920年5月29日新教育共进社、江苏省教育会、中华职业教育社三团体在上海聚餐欢迎杜威及家人;(45)《三团体欢迎杜威记》,《时报》1920年5月30日第5版。1921年6月30日北京大学、男女两高师、尚志学会、新学会五团体在北京公饯杜威及家人。(46)《五团体公饯杜威席上之言论》,《晨报》1921年7月1日第3版。多个团体参与杜威访华的组织安排以及经费筹集,缓解了组织者的接待焦虑,并提供了讲学交流的平台。
四、来华讲学的焦虑
目前学界少有关注的是杜威访华抉择的“焦虑”。先从两则事例说起:其一,1919年3月28日杜威致函胡适:“我们的行程还不曾十分确定,大约五月中旬可到上海,在中国可稍住几时,到七月或天太热的时候我们仍旧回日本乡间住几个星期然后回美国。”“你问我能否在中国讲演,这是很荣耀的事,又可借此遇着一些有趣的人物,我想我可以讲演几次,也许不至于我的游历行程有大妨碍。”杜威接着又说同意做一年的演讲,“我觉得几个月的旅行实在看不出什么道理。要是能加上一年的工夫,也许我能有点观察了。”(47)《杜威博士致胡适教授函(译稿)》,《北京大学日刊附张》1919年3月28日第5版。
其二,1919年4月 7日,杜威收到了北大讲学邀请函,北大表示将替杜威征得哥大校长意见。1919年4月14日,蒋梦麟撰文:“杜威博士将来华游历,特请其在大学讲学一年,已得博士允许,并专电哥仑比亚大学校长求同意矣。”(48)蒋梦麟:《杜威先生将讲学北京大学》,《时报》1919年4月14日第16版。1919年4月15日,哥大秘书通知杜威,巴特勒收到蔡元培的电报并同意杜威在北大讲课。“巴特勒很高兴知道你有这样的机会,并确信你在该校将能留下长远的良好影响。”(49)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钟沛君译,台北:猫头鹰出版社,2018年,第285-286页。
综合以上两则事例,一方面杜威只希望做短暂的游玩,即使有讲演也不要耽误游历;另一方面,杜威在还没有抵达中国之前,就表示愿意做长期讲学。对于杜威秉持的看似矛盾的态度,可以从两个方面加以理解。
第一,杜威对于做事的严肃态度。杜威不善言辞。哥大时期“许多学生都认为他的课讲得枯燥无味。他讲课极慢,一个字一个字的慢慢的说下去。”但是胡适认为这反映了他“讲课时选择用字的严肃态度”。(50)胡适口述:《胡适口述自传》,第103页。如果将这种态度迁移到事务抉择上,则反映了杜威做事的严肃态度。尽管杜威收到了哥大批准休假的通知,但他并没有承诺在中国停留一年。因为他需要亲自到中国,需要评估中国的前景,才能做出明智的决定。而后面的经历,也佐证了杜威的顾虑是有必要的。
据1919年4月15日家书:“东京的朋友私下提醒我们,说如果明年在中国,对薪水一事得格外小心。因为对方可以说得天花乱坠,但也很能赖得一干二净。这使我每隔一天就想打消这件事情。”(51)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79页。1919年4月22日家书提及:“以前的中国学生似乎正在精心制作访问计划,以使我享受这里的接待。唯一问题是,我得一直演讲来平衡这个计划。”(52)Jessica Ching-Sze Wang,John Dewey in China:To Teach and to Learn,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7,p4.最后,杜威夫妇打定主意,到了中国再看,并听取美国大使建议,走一步算一步。
1919年5月3日,受到热烈欢迎的杜威致信巴特勒:“目前是中国教育和思想发展的一个关键时刻”,“这可以让我了解东方的思想和情况”,而争取留在中国一年。(53)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79页。但过了不久又有些动摇,1919年5月26日艾丽丝在家书中说:“今天早上,一切都在未定之数。这些年轻人不太了解美国人按部就班处理事情的态度。我想他们压根儿没想到我们还有家要顾,还有其他事要考虑。”(54)江勇振:《舍我其谁:胡适第2部(日正当中:1917-1927)》,第80页。不知道杜威是否萌生去意,因为1919年6月25日有报道称:“杜威博士现拟于下月上旬前往日本避暑,在日本停留至九月首返回美国。(55)《杜威赴日避暑》,《顺天日报》1919年6月25日第5版。
第二,杜威对于金钱的务实态度。杜威有经济上的顾虑,因为当时他还不确定在中国讲课的薪资或待遇。虽然杜威早已饮誉海内外,但家大口阔,花费较多,此时他们的家境仍不宽裕。这可以从杜威的前半生说起。
1879年,杜威在佛蒙特大学毕业之后到一所高中教书,月薪仅为40美元。(56)[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59页。由于这个工作没能积攒多少积蓄,为了攻读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的研究生,他接受了一位姑妈500美元的借款才得以入学。1884年杜威博士毕业后进入密歇根大学,起初年薪900美元。(57)[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19页。1894年前往芝加哥大学时,他与校长哈珀通信交流,希望谈到年薪5,000美元,但未果。在芝加哥大学时期,大儿子想买一辆自行车,这几乎导致一场“家庭危机”,经过大家反复辩论,才最后通过此项动议。(58)郭小平:《杜威》,香港:香港中华书局,1994年,第44页。另外,很长一段时间,杜威家甚至连电话都没有。
1904年进入哥大以后,由于五个孩子都正在读书,杜威夫妇甚至感到财政上有些入不敷出。(59)郭小平:《杜威》,第48页。由于纽约消费较高,杜威花了十年的时间才恢复到相当于他在芝加哥的工资水平。为了找一个便宜点的地方住,1905年到1914年间,他们居然搬了九次家。(60)郭小平:《杜威》,第48-49页。由于对加薪感到焦虑,就职哥大期间传出杜威可能前往斯坦福大学任教的说法可能也不是巧合。(61)徐国琦:《中国人和美国人》,第286页。
总之,出于对陌生国度未知行程的担忧,出于对开展长期中国之行经济负担的考虑,在日本决定未来中国的计划,可能对杜威而言是一个不太容易下的决定,这才有了上述抉择的“焦虑”。在这一点上,杜威这位大牌教授与常人的心理无异。
五、再次请假的动因
1920年4月杜威一年期讲学即将结束之时,先是北大打电报给哥大请求批准杜威再任哲学教授一年。1920年4月22日报道:“杜威夫人得哥仑比亚大学校长白特老(巴特勒)博士复电,已允杜威博士续假一年。”(62)《杜威博士继续在本校讲演一年已得哥仑比亚大学同意》,《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4月24日第2版。相较第一次请假的“焦虑”,杜威二次续假可谓干脆利落,这其中更是有着多方面的原因。
第一,“五四运动”的爆发及中国知识分子为建立独立统一的民主国家而进行的斗争深深地吸引了杜威,此为关键因素。“五四运动”唤起了民族的觉醒,作为旁观者,杜威感受到中国公众觉醒的巨大力量,也看到了民主理念付诸实践的巨大可能。实际上,杜威还不自觉地成为了参与者。杜威的演讲以及传播的学说成为“五四”思潮的组成部分,直接影响了一大批知识分子和年轻学生。杜威评价五四运动是辛亥革命的扩展,是从政治革命向思想启蒙的深入发展。他曾说:“民国之造成,不在于改头换面,而在于改革内容也。”(63)《南高师欢迎杜威博士记》,《时报》1920年4月9日第6版。杜威还在《新共和》和《亚细亚》等刊物连续发文报道“五四运动”,传递中国民意。郭秉文曾评论:“自外交言之,博士考察山东等问题,甚为精确。当发抒言论,揭载美国各大杂志。以造成美国人对于中国正确之舆论。”(64)《欢迎杜威博士聚餐会纪略》,《江苏省教育会月报》1920年第5期。上述文章是杜威运用实用主义哲学,观察思考中国现实问题的尝试,部分文章被译为中文国内刊发,引发了民国学者的思考,丰富了“五四”的话语。1920年3月杜威讲学时曾说:“这次运动于我做讲演文稿时的观念很有影响。”(65)杜威讲演,敬轩笔记:《教育哲学(十六)(五续)》,《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8日第2版。
第二,民国教育界的盛情。杜威初到后蒋梦麟发文欢迎:“先生是一颗思想界、教育界的大明星。先生来,我们大家都欢迎你。”(66)蒋梦麟:《欢迎杜威先生》,《时报》1919年5月5日第15版。杜威讲学第一年哥大学子常伴左右,北方有胡适、蒋梦麟、张伯苓、李建勋等人,南方有郭秉文、陶行知、郑晓沧、陈鹤琴等人。他们陪同游览、讲演翻译、组织考察、参与会议,还多次举行宴会以显示学界的盛情。由于杜威60岁大寿与孔子农历生日同为一天,在1919年10月19日晚上的庆祝会上,蔡元培致生日祝词,赞誉杜威为“当代的孔子”,“我觉得孔子的理想,与杜威博士的学术,很有相同的点。”(67)《杜威博土六十生日晚餐会的盛况》,《广益杂志》1919年第6期。
第三,杜威中日体验的反差。虽然杜威在日本受到了很好的款待,也在东京帝国大学举行了8次《哲学的改造》系列演讲,但“并没有造成重大的影响”。(68)[美]乔治·戴克威曾:《杜威的日本之行》,[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294页。系列讲座的听众从开始约1000人减少到30-40人。(69)[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单中惠编译,第296-297页。当时日本一些年纪稍大的哲学家以德国哲学为主要研究对象,他们对杜威经验的、具体的、实践的哲学不感兴趣,少数哲学家还表示反对。(70)关松林:《日本学习借鉴外国教育之研究:“和魂洋才”的建构与嬗变》,第175页。杜威初到中国后,“闻杜威博士每次讲演,听讲演者非幸踊跃,无不座为之满云。”(71)《杜威博士来华讲演纪闻》,《教育潮》1919年第2期。杜威第一年的讲学产生了轰动效应,上至《晨报》《时报》《新闻报》《民国日报》等全国性报刊,下至地方小报、学生刊物等,不仅报道杜威的动态,还连续刊载杜威的演说内容。
第四,旅行疗法奏效及家庭团聚。根据杜威夫妇家书记载,他们在日本参观了博物馆、寺庙、神社、学校,体验了戏剧、节日、艺伎表演、花园聚会、饮食等。到达中国后,杜威夫妇共同致力于演讲和讨论活动,也享受着一段美妙的异乡体验。(72)[美]约翰·杜威,[美]爱丽丝·杜威:《杜威家书:1919年所见中国与日本》,序第2页。艾丽丝曾在密歇根大学接受高等教育,又曾将杜威倡导的“试验主义”学说,“悉运用于此校(实验学校)组织之各部。”(73)[美]杜威:《学校与社会》,刘衡如译,上海:中华书局,1928年,自序第2页。作为具有实践经验且热衷公共事务的新女性,艾丽丝在华时也受各地女性团体邀请发表教育讲演。在兴奋多彩的日子里,旅行疗法开始奏效,“艾丽丝的抑郁在这些激动人心的新经历和她有意义的活动中消失了”。(74)Jay Martin,The Education of John Dewey:A Biography,p321.另外,1919年7月25日次女露茜,1920年2月24日长女伊芙琳先后来到北京,尤其是露茜到来后的家庭团聚可能从心理层面对杜威的续假有所支持。
第五,1920年前后美国的动荡局势,也是让杜威留下来的重要原因。1919年2月6日至2月11日,美国工人在华盛顿州西雅图市举行了总罢工。这导致了1919年初的红色恐慌。种族冲突、劳工起义、美国共产党的建立和左翼势力的增长进一步加速了红色恐慌的发展。美国政府采取抓捕和逮捕激进分子的措施,更是扩大了红色恐慌。在红色恐慌期间,《新共和》被列为革命杂志,杜威被认定为“对年轻人最危险的人”。1920年2月红色恐慌的顶峰,胡适曾警告杜威,如果他返回美国,他将被驱逐出境。(75)Shanshan Peng,‘A Journey to Mars:John Dewey’s Lectures and Inquiry in China’,Journal of Modern Chinese History,vol.12,no.1,2018.
六、访华往返的时间
在杜威来华若干问题中,有关杜威到达及返回时间的谬误最多。
第一,杜威1919年5月1日到沪的时间错误,杜威实际到达时间为1919年4月30日。此种谬误主要归因于胡适以及杜威二人。胡适在《杜威先生与中国》一文中写到,“杜威先生于民国八年五月一日——‘五四’的前三天——到上海。”(76)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第2版。此后胡适口述自传也采用这一说法。1919年7月5日,蔡元培对胡适“因任杜威君演讲的译述,将离去大学”,表示很可惜,希望胡适“一面同杜威做‘教育运动’,一面仍在大学实施教育。”(77)高平叔,王世儒编注:《蔡元培书信集(上)》,第424页。此信足见胡适与杜威之亲密关系,甘愿放弃北大教职。由于胡适在民国学界的影响及与杜威的师徒关系,胡适错误的记忆直接掩盖了事实真相。其实,胡适起初的记忆是正确的。1919年5月3日,胡适致函蔡元培介绍接待情况:“杜威博士夫妇于三十日午到上海。蒋陶与我三人,在码头接他们。”(78)《胡适教授致校长函》,《北京大学日刊》1919年5月8日第3版。
回头再看杜威,经常写家书的杜威不知道是不是受到胡适影响而采用了错误日期。1920年3月杜威在北大讲授《教育哲学》时说:“我到中国来的时候,是去年五月初一,不数日而有五四学生运动发生。”(79)杜威讲演,敬轩笔记:《教育哲学(十六)(五续)》,《北京大学日刊》1920年3月8日第2版。1920年4月6日,杜威在南京高师发言:“回忆去年予至中国时为五月一日,未几而爱国运动起矣。”(80)《南高师欢迎杜威博士记》,《时报》1920年4月9日第6版。此为两例。作为亲历者的杜威与胡适有如此的误记,实在不可思议。事实是,1919年5月1日,杜威由胡适、陶行知、蒋梦麟等人陪同参观申报馆,并合影留念。此外,有学者认为,1919年4月30日杜威夫妇偕次女露茜抵上海,实则有误。
第二,杜威1921年7月11日离京返美的时间错误。真实的情况是杜威一家离开北京后,又在山东进行二十多天的游历和讲演,1921年8月2日从青岛经日本返回美国。
1921年7月11日胡适日记记载,“杜威先生今天走了。车站上送别的人甚多。”(81)胡适:《胡适文集》,北京:北京燕山出版社,1995年,第121页。同日,胡适又在《晨报》发文:“我们对于杜威先生一家的归国,都感觉很深挚的别意。”(82)胡适:《杜威先生与中国》,《晨报》1921年7月11日第2版。胡适的记述,一定程度也成为了大家“信服”的杜威回国的佐证,而少有关注后续来自山东的报道。
1921年7月3日《京报》报道:“杜威博士将于七月初旬返国。现闻博士取道青岛,由青岛往日本,在日本小游之后,于八月初旬,再由横滨买船回国。”(83)《杜威博士将离华时之贡献》,《京报》1921年7月3日第2版。1921年7月4日《时报》报道:“杜威博士约八九日出京,赴鲁演讲,取道青岛回国。”(84)《杜威博士约八九日出京》,《时报》1921年7月4日第5版。虽然上述报道介绍了杜威的未来行程,但是也有些报道具有迷惑性,让人以为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京即为归国。比如,《来复》发表的《杜威罗素两先生于七月十一日先后出京返国》(85)《杜威罗素两先生于七月十一日先后出京返国》,《来复》1921年第164期。。此前,山东教育厅拟组织夏季讲习会,获悉“博士道出山东,以为机不可失”,立即向杜威发出了讲演邀请,并请王卓然担任翻译。1921年7月2日,“山东教育厅长谭寿堃(应为覃寿堃)到京,将正式聘请的公函两份带来,已交与杜威与王君(王卓然)。”1921年7月4日为美国独立纪念日,“在京美侨,皆须到该国公使馆参与庆祝典礼,博士行期因之受阻,否者出京当较早。”(86)《杜威博士将离华时之贡献》,《京报》1921年7月3日第2版。1921年7月6-7日,杜威作为证婚人,先后参加了陆志韦(南京高师)与刘文瑞,徐淑希(香港大学)和刘文庄的婚礼。(87)《两起新人物的新式结婚》,《晨报》1921年7月9日第6版。离开北京前一天,1921年7月10日,胡适与杜威一家到容光照相馆照相。(88)胡适:《胡适日记全集第3册(1919-1922)》,第367页。
1921年7月11日杜威离京后的行程如下:11日晚10时,杜威一行到济南,当晚住于中西旅馆;12日,各界人士二十余人公宴杜威一行于石泰岩饭店,午后游览大明湖;13日,杜威一行往游曲阜;14日,游览孔庙、孔林、周公庙、少昊陵、衍圣公府等地;15日,赴泰安;16日,登泰山,在玉皇阁住一夜;17日,下山回济南,住于石泰岩旅馆。(89)《杜威博士之消息(济南特信)》,《京报》1921年7月21日第2版。
1921年7月18日-23日,杜威在济南开始讲演,其总题目为“教育者的事业”,分6天讲完,具体为《教育者的工作》《教育之社会的要素》《学校科目与社会之关系》《学校的行政和组织与社会之关系》《教育之心理的要素》《学校与社会的关系》。艾丽丝分别讲演《女子教育提高的必要》和《女子教育之过去现在和将来》。1921年7月25日,杜威一行离开济南并于当天抵达青岛,在与当地人士交谈并参观风景名胜后,于8月2日赴日本。(90)王剑:《“杜威中国之行”若干史实考释》,《教育史研究》2002年第3期。至此,从1919年4月30日到达上海至1921年8月2日离开青岛,杜威2年3个月又3天的访华行程到此结束。
结语
基于大历史的视野,“约翰·杜威与现代中国的相遇,是20世纪中国知识界历史上最为迷人的一个篇章。”(91)Barry Keenan,The Dewey Experiment in China:Educational Reform and Political Power in the Early Republic,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77,pPreface 1.在两年多时光中,由于一战以后中美社会乃至世界格局的变动,杜威与中国之间产生了一种交互的经验。康德认为交互范畴的原理是:“一切实体,在其能被知觉为在空间中共同存在者,都在一贯的交互作用中。”交互作用包含互相联系、互为因果等内容,它的时间构架是“同时共存”。(92)[德]伊曼努尔·康德:《康德的批判哲学》,唐译编译,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3年,第94页。
杜威访华以来的一百年,有关此人此行的探讨、研究虽时涨时落,却从未停止。杜威访华于中国而言,塑造了中外教育交流的典范,淋漓尽致地阐发了实用主义教育学说,成为“五四”新思潮的重要组成部分,给当时和其后的中国思想文化界留下了深刻而长久的印迹。(93)周洪宇,李永:《五四时期杜威访华与南京高师的关系考察》,《南京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3期。反向观之,访华之行对杜威具有重大的和长远的影响。首先,增进了杜威对中国的认识。杜威认为访华之行是一次绝对超值的体验,“与其说学习到了什么新鲜事物,不如说获得了崭新的看待事物的视角与侧面。”(94)[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362页。在长期的旅居生活中,杜威了解了中国社会心理学和人生哲学,“杜威学会了以自己的方式理解和尊重中国。”(95)Jessica Ching-Sze Wang,John Dewey in China:To Teach and to Learn,p74.其次,“杜威从美国到中国,环境的变化如此之大,以至对他的学术上的热情起了复兴的作用。”(96)[美]简·杜威等著:《杜威传(修订版)》,第363页。尽管杜威不懂中文,并受到了胡适等人的影响,但是不能由此假设杜威没有自己的判断,毕竟杜威是一个带着实用主义思想工具的大学者。最后,中国之行成为杜威作为一个公共知识分子的人生转折点。由于杜威对中国的访问及他帮助中国学校实现现代化的努力得到了广泛的报道和认可,导致许多外国政府邀请杜威前去考察他们的教育系统。杜威由此成为了一名“跨国哲学家”。(97)Jessica Ching-Sze Wang,John Dewey in China:To Teach and to Learn,p85.
古语有云“有心栽花花不开,无心插柳柳成荫”,从微观视角探寻杜威访华的史实细节,既可以看到此行中必然与偶然的相互交织,又有助于回归历史场景,更为客观、全面和深切地看待一位“智者”的教育旅行史。另外,鉴于实用主义教育学说对教育问题的洞察力和影响力,可以说杜威对中国的影响在过去是重大深刻的,在今天是值得思考的,在未来是可资借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