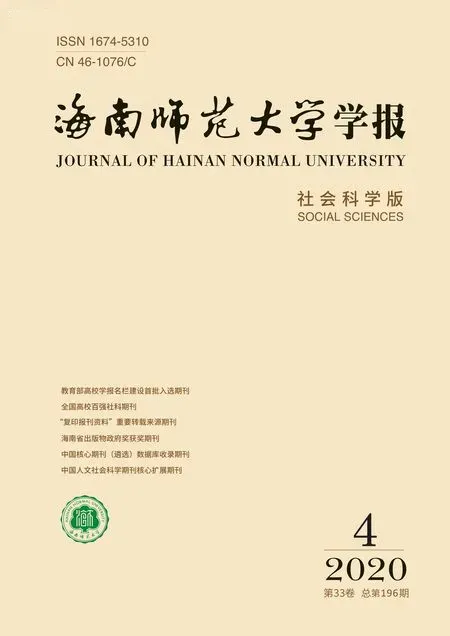回到文学的“五四”:由平民文学论争探析周作人思想的内倾性
杨高强
(上海师范大学 人文学院,上海 200234)
在新文学历史的百年回望中,“五四”作为起点之意义和价值的再述再评成为近年来现代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和视域。如何命名“五四”?这是从1919年以来就纷纭不一的历史命题。“五四”的身份夹杂在文学与历史、文化与政治、个人与群体之间,在各种各样的叙述、阐释和想象的场域中被不断拆解或重组为不同的话语类型。况且,众多话语在逻辑上又都各自辩述出难驳的合理逻辑,愈发使得“五四”成为一个宏阔而混沌的“意象”空间,仿若意外地具备了文学化的机制。然而,这种文学化“意象”的营造,却客观地对重回“五四”之路造成了某些阻隔,尤其是“五四”及其一代文人自身的复杂性经由反复的取舍和演绎,不仅会造成认识和评价的失之偏颇,甚至可能导致历史的缺漏错讹之憾。李怡教授就曾经作出颇具学术反思深意的“谁的五四”(1)李怡:《谁的五四?——论“五四文化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9年第3期。之发问。事实上,无论是参与“五四”发生的在场者,还是追述“五四”历史的后继者,都对“五四”的生产充满热情的“设计”执念,在某种程度上,历史本身都客观地具有个体性意识和个人化色彩。因而,面对命名和回到“五四”的问题,忠实于对彼时个体的人和事的详察深探,无疑是重述历史的重要方法之维。
“五四”新文学的滥觞时期,平民文学之主张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作为一种文艺口号,其贯彻了新文学从理论思想到艺术实践的整体过程;作为一种思潮形态,它关涉着新文化运动对于“人的发现”之人道主义精神和重塑国民意识、升举“人”的地位的民主政治理想。然而,平民文学运动的推进,却经历了从高昂的理论口号、高涨的文学潮流到步调不一的创作追求、歧路纷争的艺术主张之流变,尽管平民文学所内蕴的文学精神在此后的新文学发展中,尤其是乡土文学、现代市民文学、左翼革命文学、工农兵文学中得以部分地转化承续为文学传统,然而作为当时文学革命的重要运动之一,却在不了了之的收场后成为文学史书写中难以重视的尴尬事件。正如首倡者周作人的命运一样,充满含混模糊的悲情色彩。
客观地讲,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系其前半生文学生涯的成果化产出之一,既是他文艺思想的具体体现和主要内容,也是“五四”时期文学革命的重要理论收获。周作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与同时期“人”的观念和新文学发展之间实际存在差异,在当时及后人评议的双重认识视域中呈现出前褒后贬的复杂语义。对这一问题的认识,离不开对当时平民主义思潮背景下胡适、陈独秀、李大钊等人的平民论进行比较分析,也需要重新梳理和阐释周作人“平民文学”思想的缘起和内涵,尤为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对文学和艺术审美的个人化主张与其思想的内倾性构成了内在一致的精神特质,进而影响并决定其在新文学道路上与众别异的立场、追求和坚守。周作人作为“五四”一代的成员,应该说在周作人的情感中也存在一个“五四”的构想。在某种意义上,正是这种构想与历史发生之间的悖歧,才造成了个体在历史言说中的隔膜和尴尬。而将个人的“五四”和历史言说中的“五四”进行差异化比较,也是一种追述历史的方式。
一
对“五四”时期平民文学的认识,前人多有所论。一般认为,“平民文学”一词由周作人在1918年5月发表的《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中最先提用;在此之前,梁启超、裘廷梁、陈天华等人分别通过对小说地位的推崇、白话语言的倡导、民间歌谣和戏曲的重视等方面,共同营构了文学平民化的风气;而陈独秀则是明确文学平民化道路的最早主张者,甚至是最早实践者:他于1904年发表了用口语写成的《论戏曲》一文,内容是谈论戏曲对于平民百姓的启蒙教育功用,后来的文学革命檄文《文学革命论》中更是把“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放在“三大主义”的首位。继之而起的是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建设的文学革命论》和周作人的《人的文学》《平民的文学》,胡适的文章中包含着文学走向平民化的期望,而周作人的文章则具有新文学建设性的“宣言”意义。
同时期对“平民文学”提出动议的,还有毛泽东于1919年7月为《湘江评论》撰写的创刊宣言,他从“世界革命”潮流“自文艺复兴”以来的成就中总结出“对抗强权”的“根本主义”即是“平民主义”,认为合理的革命道路即是“一些学者倡之,大多民众和之,就成功或将要成功许多方面的改革。”而改革的成果,“见于文学方面,由贵族的文学,古典的文学,死形的文学,变为平民的文学,现代的文学,有生命的文学”。(2)陆学艺,王处辉主编:《中国社会思想史资料选辑(民国卷)下》,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151-153页。毛泽东援引欧洲文艺复兴的经验,对中国革命道路的论证颇富有前瞻性和科学性。
几乎在一众论者畅谈平民文学理想的同时,文坛上悄然涌出了平民化的文学潮流。最早在白话诗群的探索性写作中,胡适的《蝴蝶》、以及与沈尹默同名的诗作《鸽子》《人力车夫》等,刘半农的《学徒工》、刘大白的《卖布谣》、康白情的《草儿》等,不仅在语言和形式上追求“破旧立新”的文体实验,而且在题材内容和思想情感上呈现出进入底层社会、表现平民生活的自觉意识。《新青年》杂志于1918年6月推出的“易卜生专号”,也随即启悟小说界找到了表现和反映社会问题这一写作方向。1919年创刊的《新潮》杂志接连发表了《一个勤学的学生》《渔家》《是爱情还是痛苦》《这也是一个人》等作品,拉开了新文学史上“问题小说”的序幕。随后,俞平伯、冰心、王统照、许地山、庐隐等文学研究会作家的加盟,形成了声势浩大的文学潮流,成为“五四”时期最重要的文学现象之一。
从发生的时间来看,陈独秀、胡适、周作人的文章与当时的平民文学创作几乎是同时出现,二者之间存在合理化的证论关系,但是至于影响及其程度应许商榷。尽管批评家阿英认为,周作人的《平民的文学》等三篇文章“不仅表明了他个人的文学上的主张,对于当时的运动,也发生了很广大的影响”(3)阿英:《阿英文集》,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1年,第112页。,但是,周作人连同鲁迅、郑伯奇等却表达了与此不同的态度,对当时的“平民文学”实践或不满或否定,某种意义上揭示了新文学理论建设与文学创作之间确实存在步调不一的嫌隙。郑伯奇、鲁迅都指出当时所谓的“平民文学”名不副实,“假托平民底口吻”,“故意做了些同情于贫民的诗或小说”(4)郑伯奇:《郑伯奇文集》,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8年,第34-59页。,有情感作伪之嫌。
平民文学的作家们也对写作问题开始了思考,集中在1922年间形成了一场关于平民文学的讨论。讨论的缘起是1921年11月俞平伯写出《诗底进化的还原论》一文,朱自清看完之后以《民众文学谈》作回应,对俞平伯提出的“文学部分地民族化”表达看法,俞平伯又很快写出《与佩弦讨论民众文学》进行反驳。随后,《文学旬刊》在1922年总第26、27期上开辟“民众文学的讨论”专栏,由俞平伯、朱自清、沈雁冰、许昂若共同撰文讨论,总第28、29期又发表许昂若的《文学上的贵族与民众》、路易的《文学与民众》等文章。这场讨论主要的观点是朱自清提出的“为民众的文学”和俞平伯倡导的“文学的民众化”。前者强调文学要以服务于民众为目的,主张尊重写作者的独立性,但所写内容要面向民众生活,形式上要采用通俗化的语言,也即是朱自清所言的“旧瓶装新酒”。后者认为白话应该是文学的最初形貌,白话文学革命就是一种形貌还原,要严格的使用“听的语言”“句句可以听得懂的白话”(5)朱自清:《朱自清全集》第4卷,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6年,第24页。,甚至是方言,文学的民众化追求就是“借作者的心灵”去“渗过民众的生活”(6)俞平伯.《俞平伯全集》第3卷,石家庄:花山文艺出版社,1997年,第36页。。这两种观念虽然有侧重角度的差别,但基本主张大同小异。
在这场平民文学的讨论中,作为首倡者的周作人于同年发表了被后学认为表现出“思想有了改变”(7)尹康庄:《二十世纪中国平民文学的研究与实践》,《山西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年第9期。的《贵族的与平民的》一文,意在对文坛作跟踪式回应。与《平民的文学》相比,后作对平民文学的内涵确有延伸和补充,但可谈不上所谓的“重新诠释”,不过无疑对当时平民文学及他人的论见主张有所不满。周作人仍然贯彻否定和批判“贵族文学”的立场,再次强调前作所主张的“普遍”和“真挚”为平民文学应该具有的精神。他提出的“平民的贵族化”,针对的是当时平民文学运动中表现出的偏离和局限,认为平民化的追求不在于作者和读者的阶级身份和文学形式,而在于文学表现怎样的人生观。文学不宜过于苛求现实的关切,这样会造成人的精神和艺术理想的退化。
通过比较可见,前后作中对平民文学内涵的阐释和原则的构想并无背离和冲突,更像是一种对症式的强化说明。这其实体现的是周作人对文学精神和艺术旨趣的个人化观念,客观来看,这种宽泛的人性论和理性的艺术主张有尊崇文艺主体地位的合理化方面,具有独特的认识价值。如果据此理解周作人思想发生改变,从而判定其“舍弃了”当初平民文学的立场、甚至是彻底否定“平民文学”,则实属不当。
二
为什么平民文学会在创作实践中产生意见的纷争?周作人作为这一文学主张的首倡者,为什么会步入先褒后贬的岐境?事实上,在文学革命的理论建设阶段,平民文学是作为主要贡献来进行倡导实践的,尽管论者们对平民文学的具体构想和内涵阐释有所不同,但由于都站在反对旧文学的立场上,整体地被冠以新文学构建者的身份,所以人们更注重从发生学意义上进行概念化的接受。从当时的情形来看,陈独秀等人是以战斗和进攻的姿态发动文学革命,胡适后来非常贴切地评价陈独秀为“急先锋”,而对于胡适提出的“讨论,征集意见”的改良方案,则被陈独秀以“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气势给挡回了。不过,这份果断确也为后来的“口水仗”埋下了伏笔。周作人所倡导的平民文学理想与新文学发生实际之间的嫌隙,正出于个人的“私见”,先是草率地纳为“一朝一夕”间“一二人”之所定,后又因试图“匡正”而不容于“绝对之是”(8)周月峰编:《新青年通信集》,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38页。。当然,说到底,矛盾的产生仍然要归结于平民文学论者们不同的理解和构想。
分歧首要源于对“平民”的意涵存在不同的认识和界定。“平民”一词较早见于晚清报纸中的对外事件报道,如《万国公报》《知新报》《翻译世界》等,多论及欧洲“近事”所发生的平民主义。1907年《东方杂志》第4卷第8期上发表社论《论平民主义与国家主义之废兴》,1908年《河南》第4期发表旒其(许寿裳)的文章《绅士为平民之公敌》,表明平民主义开始为近代革命思想所吸纳。随后,国内的平民论逐渐流行起来,论说“平民教育”“平民政治”主题的文章层出不穷,进而从民初到“五四”时期形成了广泛的平民主义思潮。平民主义思想在当时国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政论辩说中都有重要的参与度,由此延伸出的相关概念如“庶民主义”“民本主义”“民主主义”等都与“五四”核心思想中的“民主”即“德先生”关系密切。而在具体的词语使用中,“平民”要么与“庶民”几无区分地相互代用,指称下层民众;要么与“国民”在一定语境中互为替用,跟封建贵族阶级相对立,是现代国家和民族相依附的群体。而对平民意涵的不同理解则关系着民主观建构的不同道路选择。
在早期社会学视野中,平民问题又等同于劳工问题。事实上,中国早期社会学的发生与平民主义思想存在着影响关系,“劳工”作为当时所理解的平民阶层的主要群体,在世界“劳工革命”的潮流中得到政治地位的凸显,“劳工政治”也被视为重要的革命路线,而本身即是工业革命产物的社会学,在中国发生伊始即把目光首先投向了劳工问题。从清末民初开始,文学中就出现了劳工题材,柳亚子(署名“侠少年”)在《醒狮》杂志1905年第3期上发表的社会小说《劳动狱》,可称之为现代劳工文学的首作。但是,文学中将劳动等同于苦力、劳动者等同于劳工的现象非常普遍,反映了当时缺乏对这些概念主动澄清厘定的意识。
1918年11月16日,蔡元培为庆祝一战胜利发表了题为“劳工神圣”的著名演讲,以“此后的世界,全是劳工的世界”之宏论喻示了革命潮流的历史动向,此后演变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现代政治和思想话语之一。演讲中对“劳工”的意涵的界定虽然宽泛,但实际上是将传统的“士农工商”阶层概念进行现代性转换,涵括了“平民”所指,应该说是自晚清以来平民主义思潮中首次较为明确的平民意涵之界说。然而,当时“劳工神圣”引发了广泛影响,概念本身所激起的感性激情显然冲淡了对其内涵的关注。李大钊随后发表了《庶民的胜利》等文章,进一步强调劳工阶层的社会地位和革命价值。从平民、庶民到劳工的词语迁变,至“五四”前夕已经普遍而具体地形成了倾向于下层民众的认识论。在民主革命的主流观念中,平民主义即是追求庶民的、劳工的解放,成为了普遍意义上的合法化诠释。在这种背景下,田汉在《少年中国》1920年第1卷第8期上发表的《诗人与劳动问题》一文,对“劳动”概念做出拨冗化繁的辩证思考,表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理性精神,遗憾的是未引起重视。
以胡适为代表的平民文学倡导者,显然倾向于将阶级化的平民认识论作为建构文学理想的基础。胡适的平民文学观的逻辑起点在于从写作主体方面打破传统文学的专制和专权,即1916年7月13日的日记中所述:“以为文学在今日不当为少数文人之私产,而当以能普及最大多数之国人为一大能事。”(9)胡适著:《觐庄对余新文学主张之非难》,曹伯言整理:《胡适日记全编·2》,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428页。这不仅确立了文学创作服务于平民百姓的要求,还导引出关于文学创作主体的范畴问题。1917年1月,胡适发表《文学改良刍议》,其中提出的“八事”主张,即是针对文学创作的要求;而一年后发表的《建设的文学革命论》,以及1921年的讲义《国语文学史》中,又都同时对文学范畴进行主张。在胡适看来,平民文学是描写下层人民且与之共享的文学,一定程度上也即是民间文学。他在《国语文学史》中对文学范畴做出了划分:“庙堂的文学之外,还有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之外,还有平民的文学”,并且评价庙堂文学“达不出小百姓的悲欢哀怨”,不能引出“小百姓的一滴眼泪”和“普通人的开口一笑”,是没有“生气”和“人的意味”的文学。(10)胡适:《国语文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8),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2-23页。胡适对平民文学的界定不仅宽泛,而且更倾向于以“通俗”和“写实”为主,显然跟周作人的观念中不能废弃文学的“雅趣”有所不同。
胡适的主张涵括了1922年平民文学论争中的两方观点,如前所述,所谓的论争只是侧重的角度问题,关于文学形式和内容的主张,意见基本相同。但这些无疑都与首倡者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想法存在背离。在周作人的理想中,平民文学比古文更通晓简明,但不等于通俗;他主张文学反映真实的生活、表达真挚的情感,但反对完全贴近平民生活、迎合平民要求的文学观;他提出“人生的艺术”观念,既不赞成艺术的唯美派,也不认同“为人生”的功利化。“平民的贵族化”其实既包含了对平民生活的尊重,也表达了对艺术超越的理想坚守。
应该说,周作人对平民文学的构想,是着眼于文学自身的。他在对“平民”概念进行解说时表示,“中国现在成了民国,大家都是公民”,虽然社会身份、阶级地位“大有高下”,然而“思想趣味,毫无不同,所以在人物一方面,分不出什么区别。”(11)周作人:《平民的文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02页。言下之意,周作人对平民的理解,是从文学本位的思想、趣味出发,至于文学中的“人”的问题,无论写作的人是谁、还是所写的人是谁,都不必做阶级化区分。这种理想化的文学观,无疑存在着时代语境下的局限,但他从文学艺术的本体角度对当时平民文学创作提出的批评,也具有客观理性的价值意义。而在“五四”时期理想与现实互搏交缠的情形下,周作人的平民文学观处于个体和他人所构建的双重认识视域中,在个人坚守和他人称论之间不为调和的纠葛下,纷争和歧路在所难免。穷究其间的深刻矛盾,一方面关涉到周作人平民文学观的早期认识和表现,另一方面则需要注意到周作人思想的缘起和内涵对其艺术审美的个人化立场所产生的影响。
三
自近代的“新小说”等文学革新运动,到“五四”时期的文学革命,新文学的理想始终背负着沉重的“镣铐”,或为社会维新需要,或被政体变革征用,或任文化重兴先锋。从文学的多重使命反过来审思文学家们的身份,也大多都不是单一而纯粹的。许寿裳回忆创办《新生》杂志时说道:“学文学的,除周氏兄弟外,根本没有一人。”(12)许寿裳:《许寿裳回忆鲁迅全编》,上海:上海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4-26页。革命家多于文学家的情形,在“五四”以前较为普遍,某种意义上折射出早期的文学革新活动带有一定的革命“投机”色彩。不过,历史经验又肯定了当时“革命家”的重要性,胡适后来讲道:“当日若没有陈独秀‘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的精神,文学革命的运动决不能引起那样大的注意。”(13)胡适:《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3),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第255页。并且,陈独秀当时对胡适主张“商讨”的犹豫态度“不以为然”,很能说明革命家与文学家的区别。所以后来因由胡适在新旧文化阵营间的“周旋”和“宽容”,造成了新文化团体的一个内在裂痕。
在“五四”群星闪耀的学人群体中,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与众不同地呈现出较为纯粹而专一的文人化色彩。从书斋少年步入群英殿堂,从拟古仿文的书生士子成长为立言治学的大家文豪,他的前半生功业之路更彰显了传统文人转变为现代文人的一种内部探索。
少年时期的周作人,度过一段颇为正统的书斋生涯,读书问学,吟诗作文,参考应试,经历了传统社会的科举末路。1901年,他继鲁迅之后也踏上了“走异路,逃异地”之途,去南京水师学堂就读。居南京期间,周作人接受了近代文化新风的启蒙,但一时间中西、新旧思想混杂影响的状态,让他深感苦闷迷茫。直到南京生活的后期,这种思想状态开始发生转折。彼时,为留学之事奔走经营,家人不许参加“乱党”的管束,祖父去世代父兄“承重”,让他深觉“前此之种种为大谬,为自苦”,发出“吾身虽死,自由不死”之慨叹,并在日记中写道:“近来我之思想大变,昔主强权,今主悲悯;昔主欧化,今主国粹,其不同如是。”(14)钱理群:《周作人传》,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年,第79页。由此可见,周作人后来思想中传统的雅趣情志和现代的悲悯人道正是从此时埋下了种子。
1906年,周作人考取赴日留学,终于实现了“得乘长风,破万里浪,做海外游也”(15)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 1885—1967》,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2页。的愿望。到东京后,在鲁迅的引导下,他通过大量阅读增长了文学知识和社会见闻,特别培养了研究希腊神话的兴趣。1907年,鲁迅认为章太炎编的《民报》等刊物过于偏重政治和学术,无法完成文艺上的任务,于是邀约许寿裳等人筹办《新生》杂志。周作人从事协助工作,并兴致高昂地为该刊创作《三辰神话》。原本计划学习建筑学的周作人,在鲁迅“弃医从文”志向的影响和带动下,转而将文学作为了矢志不渝的主业。
在东京生活初期,周作人与鲁迅同住“付见馆”时,曾与一些政客有过接触,但很快就搬迁至“中越馆”,因为所见之人“目的是专在升官发财的”“语言很是无味”。志不在政治的周作人,潜心于翻译和写作,逐渐开拓和形成自己的文学领地和文艺观念。1908年《河南》杂志第4、5期,周作人发表了署名独应的文章《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16)周作人:《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1),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7-115页。,此系其首篇正式表达文学见解的论作,表现出自觉秉持个人化立场和理性批评精神的文艺家之性情。这篇文章所阐明的文学观主张,与其后来的平民文学、“为艺术而人生”等观念应是一脉相承。
1910年,周作人归国回到绍兴,适值辛亥革命爆发,他后来回忆道:“一直躲在家里,虽是遇着革命这样的大事件,也没有出去看过”,之后所做的事情“大约只是每日抄书,便是帮鲁迅翻看古书类书,抄录《古小说钩沉》和《会稽郡故书杂集》的材料,还有整本的如刘义庆的《幽明录》之类”(17)钱理群:《周作人传》,第162页。。潜居绍兴的七年间,周作人的生活更像是传统读书人和现代学人的结合,除发表几篇时论文章外,主要工作是童话研究、小说研究、翻译和创作,社会活动是从事地方中学教育、主编教育杂志。周作人的文字和生活,反映出的性情和志趣更多地倾向于文艺和学术。
1917年9月,周作人应邀赴京,被聘为北京大学文科教授,这意味着他从此正式以现代学人的身份走到时代前台。北大作为新文化运动主战场和文学革命的策源地,近代以来的学人们有相当一部分在这里完成了现代思想观念和现代知识分子身份的最后转换。这自然也包括步入中年的周作人。受邀到北大任教,颇有点“出山”“出世”的意味,但此时周作人在思想观念和文化学养上已有丰厚的积淀,在治学、写作上也趋于成熟,虽处在新文化运动的风潮中心,迎于文学革命的狂流拍岸,但传统文人的散淡隐逸性情和成熟现代学人的严谨理性,使得他并未完全融入“五四”的狂飙突进气质。
当时北大在文科之外,还设立文科研究所,分哲学、中文及英文三门,由教员拟定题目供师生共同研究。周作人选择了“改良文学问题”和“文章”类第五的小说组两项。如今看来,他后来的许多论作及文学观的思考,正是从这里开始系统产出,包括《日本近三十年小说之发达》一文。这篇文章中首次提用“平民文学”一词,主要谈到日本文学中对中国文学的创造性转化,目的在于提请新文学界对这种转化经验的注意。虽然该文与平民文学观并无实质关联,但日本文学确实对周作人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尤其日本白桦派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发起的新村运动及其倡导的人生的文学,让他对这种文艺理想和乌托邦的社会实验非常向往和推崇。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6号发表《人的文学》一文,同期还刊出他翻译的日本作家江马修的小说《小小的一个人》,有意为“人的文学”主张佐以说明和形象化阐释。周作人特别强调:“我所说的人道主义,并非世间所谓‘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乃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18)周作人:《人的文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88页。随后发表的《平民的文学》,则是对“人的文学”观念作进一步阐释和具体化主张,指出“平民的文学与贵族的文学相反”,而相反的地方“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即“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并再次强调“平民文学绝不单是通俗文学”,“平民文学绝不是慈善主义的文学”(19)周作人:《人的文学》,钟叔河编订:《周作人散文全集》(2),第93页。。以《人的文学》和《平民的文学》这两篇文章为主述,周作人建构并阐明了他的平民文学观。之后,周作人又接连发表了《新文学的研究》《个性的文学》《美文》《自己的园地》《贵族的与平民的》等文章,虽然在角度和内容上各有侧重之别,但对平民文学观的主张从未发生原则性的更变。
不仅如此,在周作人的文学创作中,亦有不少闪耀平民性色彩的作品,比如小说《杀儿的母》,新诗《两个扫雪的人》《北风》《背枪的人》《京奉车中》《苦人》《劳动的歌六首》等。其中,《京奉车中》和《背枪的人》在《新潮》1卷5号上转载时,傅斯年特别写了“附记”郑重推荐:“我们应该制造主义和艺术一贯的诗,不宜常常在新体裁里放进旧灵魂……所以现在把《每周评论》里这两首诗选入,作个榜样。”(20)傅斯年:《仲密〈背枪的人〉和〈京奉车中〉两诗附语(诗)》,欧阳哲生编:《傅斯年全集》第1卷,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283页。周作人的诗文,用通俗、清淡的语言表达对劳动人民和现实生活的关切,蕴含着个人化的情感和思考,也即是对其坚守的文学观念和理想的躬身实践。正如其不断所强调的:以平民的精神为基调,用艺术的方法表现个人的情感,代表人类的意志,有影响于人间生活幸福的“人生的文学”——或称“真正的人的文学”。
通过上述对周作人早期平民文学观的形成道路及其思想情状的探查,不难发现,他对文学艺术有着纯粹的情感投入和理想追求。在周作人身上,有机地统一了传统书斋式文人的性情和现代学人的理性,这注定他在新文学潮流中的站位,既不同于激进的为启蒙而文学者,也不同于为求文学之新的盲目实践派。集文人和学人于一体的周作人,在狂飙突进的“五四”浪潮中更像是一位特立独行的“文学学家”,其“平民文学”观的酝酿和形成,早于辛亥革命后兴起的平民主义思潮,并在“五四”时期的平民文学热潮中保持着理性的个人化立场和主张,既与“五四”前后胡适等人的观念相异,也不像后人所认为的存在着前后矛盾的变化,谈不上据此证为“中庸”之风的体现。如此种种,揭示了周作人的早期思想中,于看似散淡隐逸之间包蕴着刚毅执著的品格,在独善自守的性情另一面张扬着坚持为文艺发声的热情理想和学思理性,构成了他作为文艺家思想的内倾姿态。这种内倾性思想,既表现为对文艺由外而内的“出世”性情,也表现为在文艺内部寻求审美超拔的“入世”精神。具体而言,就是对传统文人的痴恋情结内化为对文学的专一,又以现代学人的谨严理性追求对文学内在的超越和突破。看似充满矛盾,但在纷纭复杂的“五四”同代人中,却又凸显出某种纯粹的可贵风格,而周作人对平民文学观的主张和坚守,正是其思想内倾性的自然表现,与“文学学家”的特殊身份、视野和追求存在着一体联结、互为表征的关系。至于周作人在新文学道路上步入“岐境”的困惑,则反映了“五四”文学革命时期个人方案和群体而治之间不可避免的客观矛盾和冲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