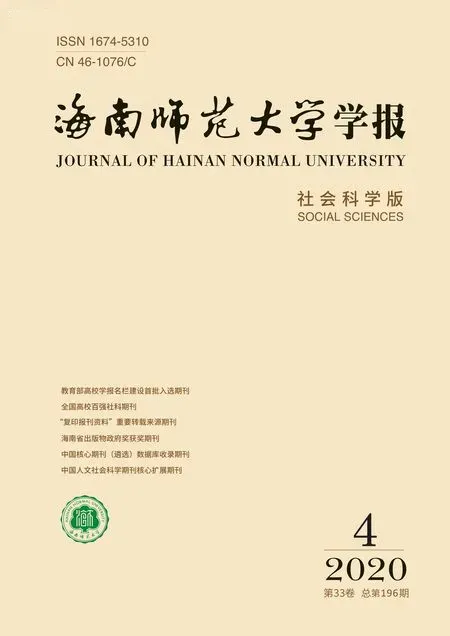论郭沫若旧体诗中的国家意识
吴 辰
(海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海南 海口 571158)
一、引言
中国现代文学中的旧体文学如何入史?此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长期处于一种悬而未决的状态,学界常常理所当然地将这类与新文学共生的旧体文学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这种现象背后的原因是复杂的:一方面,对旧体文学的轻视源自于新文学的繁盛。20世纪以来,新文学以其新的精神和新的形式迅速占领了曾经属于旧体文学的文化空间,将这些原先被视为正统的文学体式挤出了公共视野,旧体文学变成了一种文人创作的余兴或者自我言说的空间,对文学的发展和演进的影响力相对较小;另一方面,中国现代文学以现代性为核心的史观构建特征也必然会使一些现代性色彩不那么明显的文学作品和现象被摒除在文学史书写之外。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虽然求全责备是不可能的,也是没有必要的,但是如果明知在新文学之外还有旧体文学这样一个广阔的空间却不去正视它,则不能不说是一种缺憾。无怪乎当年范伯群先生曾经以“俗文学”为例,痛心疾首地感叹到:“现有的中国现代文学史是一部残缺不全的文学史”,“这‘残缺’的程度严重到我们过去只研究了半部中国现代文学史。”(1)范伯群主编:《中国近现代通俗文学史》,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1999年,第1页。
对于中国现代文学中的一些作家而言,旧体文学的创作有时还是其人生中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例如郭沫若的旧体诗(2)本文在论述过程中所使用的“旧体诗”概念相对较宽,将楹联等传统文学形式也纳入“旧体诗”范畴之内。创作。有研究者认为:“现代文学史没有对于旧体诗创作的研究,是文学史的一块缺失。郭沫若旧体诗创作的研究,几乎没有进入到郭沫若研究的视野中,当然也是郭沫若研究的一个缺失。”(3)蔡震:《“坐见春风入棘篱”——郭沫若流亡期间旧体诗创作论》,《中国社会科学论坛文集——郭沫若与文化中国》,2013年。这一论点对于郭沫若研究而言是十分客观的:首先,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持续时间极长,从其少年时代至其晚年,一直有作品问世,只有将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纳入研究视野,才能推进郭沫若的整体研究;其次,郭沫若作为中国现代新诗的代表人物,却在新诗创作之外坚持以旧体诗写作,这本身就是一个颇为耐人寻味的问题;第三,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和新诗创作从传播角度来看并不是在一个维度上,其形式本身就具有政治实践和文化实践的意味(4)刘奎:《诗人革命家:抗战时期的郭沫若》,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9年,第105页。。旧体诗为郭沫若开拓了一个新的话语空间,这对郭沫若研究而言也是十分重要的。
在郭沫若的旧体诗创作中,国家意识作为一个较为核心的观念一直贯穿其中,而随着20世纪中国政治文化的发展,以及郭沫若本人思想的转变,其国家意识也有一个产生、演变到定型的过程。对郭沫若旧体诗中的国家意识进行研究和辨析是对郭沫若进行整体研究过程中一个重要的切入点。
二、辛亥革命前后国家意识的混杂
辛亥革命是20世纪中国历史上的大事件,它意味着中国帝制王朝的终结。靠着惯性维持下来的王朝统治终于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土崩瓦解,而中国在现代政体领域的实践也随之展开。在一般的表述中,辛亥革命时“中国政治及人民生活方式走向近代化之路的一个划时代的起点”,也是“近代中国人民追求民主和国家独立富强的一个里程碑”。(5)林家有:《辛亥革命的社会影响及其历史启示》,《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第4期。就较为宏观的社会层面而言,这种表述是十分准确的,但是如果将观察的镜头推进至每一个具体的个人,其思想的转变往往与政治体制的变革并不总是保持同步。
而辛亥革命前后的郭沫若正是这样。虽然他早在清末赵尔巽主政四川时期就曾经积极地参加学生运动,也对国会“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管国家的大事,让我们一切的老百姓都要来说话”(6)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13-214页。的设立目的有着感性的理解,但是长期以来皇权统治的烙印并不是说消除就能立即消除的。尽管郭沫若盼望着有一个“老百姓”都能参与到国家事务中的新型政体,但实际上此时的郭沫若尚未对所谓现代意义上的国家形成一种清晰的认识。这集中体现在郭沫若在辛亥前后所写的旧体诗中对一些基本政治概念使用混杂。
郭沫若在1911年春节至1912年春节这一年间,曾留下了不少楹联题词,其中大部分的题材都是围绕着立宪派国会、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成立等题材而展开的。然而,如果通观郭沫若这一时期创作的全部楹联就会发现,实际上郭沫若对民主和帝制之间的认识并不总是那么清晰,在一些文字中,他自觉不自觉地就会混入一些与民主相背离的词语。在1911年春节的楹联中,郭沫若的笔下曾经出现过一些与帝制相关的词语,例如在“诏书颁下九重来,国会缩短三年,要与列强争优胜;峨眉耸立青天外,山势蜿蜒万里,飞临当户作画屏”(7)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2年,第144页。和“吾年已近古稀,惟愿后生中人,镳驰千里;今日竞行新政,私祝圣朝前路,雄长万邦”(8)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46页。两幅颂赞立宪的对联中,均出现了“诏书”“圣朝”等与帝制相关的词语。词语的出现本身并不会对楹联的意义造成什么影响,但是考虑到郭沫若在书写这些楹联之时,曾经作为学生代表参与到立宪斗争中,诸如“诏书”“圣朝”一类词语的出现在其这一时期所有楹联当中就显得十分突兀。事实上,这些词语在郭沫若楹联中的闪现次数非常有限,但正是由于其有限,才反映出郭沫若此时对国家认知的驳杂。
两种政体之间的交叠并不仅仅是宏观层面上的事情,更意味着话语体系的更迭。在这个时期,民主和帝制两套话语体系正在争夺着中国未来的方向,而在大多数时候,这两套话语体系却是不兼容的,与民主相关的词语往往意味着先进,而与帝制相关的词语则往往意味着落后。而有关民主和帝制之间的更迭在清末一系列民主革命运动中都处于中心位置。早在20世纪初,就有人详细地对这一问题进行了阐发:“今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君乎?曰可。民主国之总统,不得谓之君,招之来则来,挥之去则去,是无所谓君也。又试问一国之中,可以无民乎?曰不可。民也者,纳其财以为国养,输其力以为国防,一国无民则一国为丘墟,天下无民则天下为丘墟。故国者民之国,天下之国即为天下之民之国。”(9)《说国民》,《国民报》1901年第2期。在20世纪初叶,虽然深处中国内陆的四川信息交流并不像东部省份那样便利,但也时时与其他省份的民主革命运动声气互通。这样看来,郭沫若倾心民主而言语之间又不时出现对帝制时代话语体系的留恋,就不能仅仅被视作是巧合或表述上的不当了。
郭沫若的另一幅楹联将其心中混杂的国家意识表现得更为明显:“力挽狂澜,旰食宵衣新主业;忧先天下,江湖廊庙小臣心。”(10)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44页。不难看出,在郭沫若心中,即使是在准备立宪之后,刚登基的溥仪皇帝仍是国家的“新主”,而面对这位“新主”,包括自己在内的民主政体的支持者仍然是“小臣”。这幅楹联中所折射出的郭沫若对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认知实际上并未超出封建王朝“君君臣臣”的纲常,这甚至与其同时期的诸如“古圣人智不惑,仁不忧,勇不惧;新国体,民为贵,土为次,君为轻”(11)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44页。等其他有关立宪的楹联是相互冲突的。
造成郭沫若这一时期国家意识混杂的原因是多方面的。首先,20世纪以来,全国各地普遍有一种“一蹴而就”的社会革命发展观,四川也不例外。在郭沫若的回忆中,请愿最开始的设想是非常理想化的:“1.要求在明年便开设国会;2.要求四川总督代奏;3.一律罢课,不达到目的,誓不复课。”(12)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211页。在这种观念的驱使下,包括立宪情愿等社会革命运动的参与者们顾不上认真考虑革命之后所要面对的种种问题,便迫不及待地加入到了成功之后的狂欢队伍当中,其对革命的理解自然也会流于浅薄。其次,20世纪以降,四川省内的教育仍是相对陈旧,在教学方面相对落后,常出现“以旧喻新”的现象,所学历史“差不多就只是一个历代帝王的世系表和改元的年表号”(13)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180页。。在这种教育之下,郭沫若在国家意识方面的混杂就几乎是在所难免的了。而除了以上两点之外,更重要因素则在于郭沫若此时对“国家”这一概念的关注重点。郭沫若对“国”的认知更多地在于“国土”而非“国体”。对于郭沫若而言,此时对于“国”的观念是十分保守的。在自传中,郭沫若声称“中国的不富不强就因为清政府的存在,只要把清政府一推翻了,中国便立地可以由第四等的弱国一跃而成为世界第一等的国家。这是支配着当时青年脑中的最有力的中心思想。”(14)郭沫若:《反正前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1卷,第203页。然而,这是出自于郭沫若反观自己人生经历时的一种后设,如果回到历史现场就会发现其所关心的核心问题实际上还是与“国土”有关,这一问题从立宪请愿时期一直延续到了辛亥革命时期。郭沫若的一幅对联写到:“光复事殊难,花旗矗树,华盛顿铜像如生,祖国丘墟,哥修孤英魂罔吊。于瞻于仰,或败或成,人力固攸关,良亦天心有眷顾;边维氛未靖,东胡逐去,旧山河完璧以还,宝藏丰繁,碧眼儿垂津久注,而后而今,载兴载励,匹夫岂无责,要将铁血购和平。”(15)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5页。这是一幅篇幅较大的长联,字里行间,郭沫若以美国和波兰在独立斗争之后的不同境遇传达了对辛亥革命之后中国命运的隐忧,而这忧虑的焦点则是国土。较之国体问题,郭沫若更担心是“边维氛未靖”“碧眼儿垂津久注”等问题。虽然在辛亥革命之后一段时间内,郭沫若对国土的担忧常以“排满”的形式呈现出来,但是如果联系郭沫若在立宪时期所写的文字,就会发现这种排满反清的情绪中更多是一种对清末山河破碎的愤怒和怨恨,而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由大汉族中心意识而产生的狭隘民族情绪。郭沫若之所以在一年之间由甘为“小臣”到反清排满,其思维转变的内在逻辑则在于清朝政府已经无力守住国土,倒不如将“旧山河完璧以还”,移交给新政权。
在辛亥革命前后,郭沫若的国家意识刚刚开始萌芽,他积极地以行动参与到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之中。而就郭沫若自身而言,其国家意识是颇为混杂的。他将国土这一民族国家想象中重要的一部分当成了民族国家的全部,而对诸如国家政体等其他方面的元素并未加以重视。故而,在国土受到威胁的时候,郭沫若的国家意识也随之摇摆不定,“国民”“臣民”“立宪”“排满”等一系列相互对立的元素也因之纠缠在了一起。
三、从国土到强权:转型中的国家意识
1912年,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在中国的版图上,第一次建立起了现代意义上民族国家。郭沫若对中华民国也抱有很大的希望,在这一年的春节前后,他创作了大量歌颂中华民国的楹联和诗句。这之中不仅包括诸如“春色翻成新世界;晴光煊染旧中华”(16)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9页。和“竹报桃符更岁月;鹦簧蝶板庆共和”(17)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34页。等这种结构上比较简单的楹联,甚至还有“欲铭勒恢复事功于昆仑,千秋景仰;喜摆脱专制政体之羁绊,万代共和”(18)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36页。或“故国同春色归来,歌唱凯旋,都邑声宫占乐岁;民权如海潮爆发,肃清夷虏,壶觞飞羽醉共和”(19)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47页。,这样有意识地将专制与共和、民权与共和并置的情况。这说明了在民国建立前后,郭沫若实际上对这个现代民族国家在政体方面的构建是有着较为明晰的认知的,只不过由于其在国家意识层面上的混杂,这些有着丰富内涵的政治词语在郭沫若所撰写的诗文中常常仅作为一般意义上的词语出现,而就郭沫若的本意而言,也并没有将这些概念拓展开来的意图。
与此同时,郭沫若对于国土问题仍是十分关心,面对新生的中华民国以及环伺于国家周边的列强们,郭沫若不由得心怀忧虑。在一首代友人作答的诗中,郭沫若写到:“拂霄振逸翮,国基伤未坚。胡马骈西北,郑羊势见牵。巢破无完卵,编声非弱弦。我愿学归来,仍见国旗鲜。”(20)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11页。而在稍后另一首与友人唱和的诗歌中,郭沫若更是直接用杜甫《春望》“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的韵脚,写道:“烽火连西北,登埤动客心。茱萸山插少,荆棘路埋深。惊见归飞雁,愁听断续砧。一声河满子,落泪不成吟。”(21)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12页。从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出,郭沫若清楚地知道民国肇始,在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下,却是危机四伏。在郭沫若眼中,伤而未坚的国势还可以通过时间来慢慢恢复,而边疆烽火却是摆在民国政府面前不得不去直面的现实问题。在这种语境下,对国土尤为关注的郭沫若无暇顾及政体方面的问题,而频兴“国破山河在”的嗟叹。
伴随着时间的推移,新兴的民国在内忧外患下呈现出颓败的迹象,西北边疆战事未休,国内原本共同参与革命的各家势力却因利益相互攻讦,这使郭沫若尤为心焦。此时郭沫若的诗作中常常弥漫着狼烟烽火:“群鹜趋逐势纷纭,肝胆竟同楚越分。煮豆燃箕惟有泣,吠尧桀犬厌闻狺。阋墙长用相鸣鼓,边地于今已动鼖。敢是瓜分非惨祸,波兰遗事不堪。”(22)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15页。中华民国的建立确实给郭沫若带来了很大的希望,而民国成立之后,并没有改变晚清丧权割地的命运,这又使郭沫若陷入了极大的痛苦之中。而通过民国与晚清的对比,郭沫若渐渐地意识到,要想救亡图存,其根本不在于对国土的坚守,而在于政治体制的革新,在旧的政治体制下,所谓公侯将相其心中关心的只有自己的名利,而对民国之民与民国之国,他们是一点也不在乎的。郭沫若借助《感时》的诗句将这一事实生动地展示了出来:“冠盖嵯峨满玉京,一般年少尽知名。经营人爵羊头烂,罗掘民膏鼠角生。腾说曹邱三寸舌,争传娄护五侯鲭。鼎镬覆公终折足,滥竽还自误齐民。”“劫燧初经尚未稣,丛祠夜火复鸣狐。奔林战象衡驰突,窜穴阵蛇恣毒痡。极望疮痍千井满,不闻号泣一家无。司戎毕竟司何事,双方罪恶讵胜诛。”(23)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16-117页。郭沫若意识到,那些在中华民国建立初期崭露头角的青年政治家们,实际上也只不过求名图利的不学无术之辈,国家和土地在他们手里只不过是利益交换的筹码而已。民国甫立,根基未稳,外患未除,而新进一班权贵却因为蝇头小利而同室操戈,彼此攻讦,毫无正义感可言,这样的民国实际上只是清政府的借尸还魂。1912年年尾,武昌起义刚刚胜利了一年,而周边强国却丝毫不给民国以喘息的余地,这更加重了郭沫若对时局的担忧。他曾经绝望地写道:“欲把清流葬浊流,党人碑勒澄千秋。驴鸣厖吠争相诮,螳黯蝉痴漫不忧。胜国衣冠惊老大,汉家车马病轻浮。穿篱已自招群盗,屋社由来岂用秋。”(24)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34页。诗句里集中出现了“胜国”“穿篱”“屋社”等亡国的意象,中华民国在郭沫若眼中已经是风雨飘摇。
中华民国的建立未能转变晚清以来中国不断割地丧权的现状,这也让曾经将对国家的认知集中于国土层面的郭沫若的国家意识有了新的发展。郭沫若此时有诗写到:“抽绎俄蒙协约词,我心如醉复如痴。追念极边思缅越,难忘近事失高丽。覆车俱在宁仍蹈,殷鉴犹悬敢受欺。伤心国势飘摇甚,中流砥柱仗阿谁?”(25)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21页。惨痛的时局让郭沫若明确了一个事实,即如果不从根本上来改变“国势”,那么以国土建立起来的一套国家认知就是非常不可靠的,因为曾经认为是国土的部分很可能转瞬之间就被拱手让与他人。郭沫若将其注意力从国土转移到了政体上来,而颇为耐人寻味的是,此时的郭沫若常常将政体捆绑于某一位政治人物身上,他期待着一个能够充当“中流砥柱”的“阿谁”。
郭沫若将对国家的希望寄托在某一政治人物身上,这其实体现了他对“强权”的倾心,造成这一现象的根源在于晚清以来川内纷繁错乱的局势,而在革命过程中,川内各方势力更是走马灯一般,你方唱罢我登场。在四川响应武昌起义建立大汉军政府之后,事实上首义的蒲殿俊等人并没有能力整合川内各方政治力量,以至于其仅仅做了十日都督就被迫下台。这段时间的四川局势其实是十分混乱的,郭沫若在诗中写道:“甲保街头夜鼓鼙,满城烟火月轮西。兵骄将悍杜陵泪,象走蛇奔庾信悽。社鼠缘经成市虎,惩羹敢不慎吹齑。茫茫大祸知何日,深夜牙牌费卜稽。”(26)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37页。而郭沫若把这一系列动乱的根源归结于当权者的无能,他曾多次在诗句中流露出对当政者的不满:“汉祖虚传三侯歌,嗟无猛士奈如何”“还怜帷幄纡筹者,惩令欲行不敢行。”(27)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38-139页。郭沫若苦于国中没有一个完全强势的政治人物能够一统政令,将此时相对松散的各种势力整合起来,并对目前执政者迫于各种压力而对自己颁布的发令也不敢执行的窘态颇有嘲讽之意。国内事务已是如此,面对国际争端时,新政府也自然无力应对,在外交方面常显得软弱不堪。郭沫若曾在诗中描绘民国初建时沙俄对国土的虎视眈眈:“贺兰山外动妖氛,漠北洮南作战云。夜舞剑光挥白雪,时期颈血染沙殷。筹边岂仗和戎策,报国须传净虏勋。已见请缨争击虏,何如议事徒纷纷。”(28)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35页。面对外敌,已有仁人志士主动请缨,而民国政府却畏首畏尾,凡事只论“从长计议”,而迟迟未曾有所行动,这令郭沫若十分不满。在郭沫若心中,中华民国应该是那个能够代替清朝来守卫疆土的政权;是那个“武装作和平,维持人道;铁血为资本,购买自由”(29)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32页。的国家;是能够带领中华民族“汉字旗翻,国光辉耀,祝我神明胄裔,从兹振刷,用为东亚雄狮”(30)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6页。的政权。由于曾经亲自参加过四川省内的革命运动,郭沫若也深信这一新生国家有能力做到这一点。至于理想和现实之间的差距,此时的郭沫若则将其简单地归结于政治人物的软弱。
中华民国成立后,郭沫若对国家的认知发生了重大的转变,其关注点也从单纯国土转变为了政体。在此时的郭沫若看来,国土固然重要,但是只有一个稳固的政体才能真正维护国土的长治久安。而民国肇始时的动荡与川内长期的混乱又使郭沫若对政体的认知从一开始就和强权捆绑在了一起,在“铁血”“富国强兵”等一类颇具蛊惑性的国家主义口号下(31)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65页。,此时的郭沫若将国家的希望维系在一个特定的政治领袖的身上,这也是其在这一时期思想上的局限性。但是,由国土到政体,则意味着郭沫若的国家意识正在由传统向着现代转型,其对国家的认知不再仅停留于客观现实中的土地,而是开始想象一种涵盖面更为广阔的政治共同体。
四、反思强权:现代国家意识的确立
在一段时期里,郭沫若对强权十分迷恋,这甚至影响了他对于时局的判断。郭沫若曾经一度错误地相信袁世凯政权能够为中国带来新生,其理由也很简单,就是因为在活跃在当时中国的各路政治力量中的实力占据绝对优势。郭沫若曾经在一封致父母的信件中写到:“正式大总统业已举定袁世凯,欧美各国俱各承认矣。似此则吾中华民国尚有一线生机矣,无任庆幸。”(32)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76页。而对于那些反对袁世凯的政治势力,郭沫若大多对其嗤之以鼻:“中国自反正来,一般得志青年,糊涂捣蛋,蠹国病民,禽荒沉湎,忘却兄台贵姓。”而袁世凯则成为了郭沫若心中扶大厦于将倾的不二人选:“袁氏此次振救,颇快人意,一棒当头,喝醒痴顽亦复不少也。”(33)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81页。郭沫若在这段时间里对袁世凯的支持实际上还是其对四川反正前后社会境况的反映。在辛亥革命之后,四川省内政局的反复无常使郭沫若特别希望看到有一个力量能够迅速将各派力量整合,稳定国内形势,进而使中国足以与周边其他国家相抗衡,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仅就实力而言,袁世凯显然有着他人所难以企及的优势,这使在当时寻找政治上强权的郭沫若多少有点“病急乱投医”,被袁氏当政的假象所迷惑,甚至在袁世凯称帝后,云南方面通电讨袁,郭沫若尚有“云南变故家中想受影响,然吾家深居山僻,或者当无可虞。现在中央军队已陆续进发,想小小变故,亦不难荡平也”(34)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26页。这样的文字存焉,这不能不说是郭沫若在此时思想上的局限。
而事实上,早在1915年,郭沫若就开始对袁世凯政府的所作所为有所反思,在那首成于留日期间的著名《七律》中,郭沫若愤慨地写道:“哀的美顿书已西,冲冠有怒与天齐。问谁牧马侵长塞,我欲屠蛟上大堤。此日九天成醉梦,当头一棒破痴迷。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35)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2卷,第41页。从1915年初开始,面对日本提出的“二十一条”,袁世凯政府采取了较为消极的应对策略,一再拖延。遂至该年5月7日,日本向中国下最后通牒,也就是诗中的“哀的美顿书”,其背后虽然有袁世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具体考虑,但是就民国的外交行为以及最后结果来看,此举却令曾经以袁氏为强权之代表的郭沫若等人倍感失望。出于对强权的信任,在面对外来压迫时,郭沫若一直希望中国能与之公开较量。虽然当时还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并不想看到中日之间发生战争,但是对于袁世凯政府的软弱,郭沫若也并不以为然。郭沫若曾经对中日之间因为“二十一条”而发生战争后的种种可能性做过一番分析:“设使我国万一而出于战也,亦未必便不能制胜。即以吾国古兵法言之,所谓兵骄必败。日本鬼国,其骄横可谓绝顶矣,天其真无眼以临鉴之耶?今次吾国上下一心,虽前日之革命党人今亦多输诚返国者,此则人和之征也。鬼国近日政争甚烈,内顾多所掣肘,敌我相权,未见便输于彼小鬼也。”(36)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08页。可见,类似诗中所云“男儿投笔寻常事,归作沙场一片泥”也并非是一时凭着意气而作,其背后有着郭沫若对于时局的观察。
虽然在袁氏签订“二十一条”后,郭沫若仍是有意为其辩解,但是如果细究其中语句,就会发现,此时郭沫若的态度立场与之前有着天壤之别。“此次交涉之得和平解决,国家之损失属实不少。然处此均势破裂之际,复无强力足供御卫,至是数百年积弱之蔽有致。近日,过激者流竟欲归罪政府,思图破坏,殊属失当。将来尚望天保不替,民自图强,则国其庶可救也。”(37)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213页。郭沫若在言语之间,失望之意尽显。虽然他将中国签订丧权辱国条约的原因归结于“数百年积弱之蔽”,还劝家人不要过多地责备政府,但是袁世凯在其心中政治强人的形象也随之瓦解了。而更进一步,郭沫若在国家意识领域也逐渐将国家从强权之上松绑,转而寄希望于“民自图强”,这之于郭沫若对国家的认知而言,可以说是一个长足的进步。
“民自图强”四个字,其重点有两个,即“民”和“自”,“民”则不必赘述,指的是包括郭沫若在内的中华民国国民,而“自”却显得意味深长。在此前郭沫若所创作的大量楹联和诗文中,无论是颂扬还是嗟叹,国家、政权实际上都是以一种客体的姿态呈现的。例如:“桃花春水遍天涯,寄语武陵人,于今可改秦衣服;铁马干戈回地轴,吟诗锦城客,此后休嗟蜀道难”(38)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43页。,或是“五族共和岂易哉,百年根蒂费深培。理财已少计然数,和狄偏无魏绛才。西北旧蕃行瓯脱,中央深疚弗虺催。请看肉食公余后,尚向花丛醉酒杯。”(39)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18页。即使是情之所至,也不过是“屈指韶华二十年,茫茫心绪总如烟。故人相对无长物,一弹剑铗一呼天。”(40)郭沫若著,郭平英、秦川编注:《敝帚集与游学家书》,第125页。纵使弹铗而歌,而终究无可奈何。随着中华民国的成立,郭沫若认为革命已经毕其功于一役,作为国民,其所要做的只是随着国家的安排亦步亦趋,而自己如何参与到国家的建构中,则并没有被纳入郭沫若的思考范畴。就郭沫若的国家意识而言,仅仅将注意力放在国土之上,或者仅仅将注意力放在某一强权人物身上都会面临着同一个问题,即无法很好地处理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在很大程度上,两者都会使国家这一涵盖面极其丰富的范畴大大缩水,成为某一个人或者某一政治团体所应该思考的问题,而个人却只有旁观的权利。随着郭沫若对强权反思的深入,这一问题得到了解决。他意识到,无论是政治团体,还是个人,都不能成为国家和民族的最终解释者,而个人作为中华民国的“国民”,是有权利也有义务参与到国家建构之中的。于是,就有了以下这首著名的诗作:“少年忧患深苍海,血浪排胸泪欲流。万事请从隗始耳,神州是我我神州。”(41)郭开贞:《同文同种辩》,《黑潮》1919年第1卷第2期。在这首诗里,郭沫若明确地传达出了自己要担负起国家社稷的抱负,既然“神州”就是“我”,而“我”也正是“神州”,那么与“神州”相关的事务“我”自然都有参与其中的权利和义务。这首诗中所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一种家国情怀,更是一种在现代民族国家意识关照下的个人与国家关系的重构。
而此后在郭沫若的一些旧体诗作中,这种基于对强权的反思而进行的个人与国家之间关系的重构就更加地自觉了。在《暴虎辞》中,郭沫若借着李广之孙李禹之口痛斥“一世雄”的汉武帝,称“穷兵黩武汉天子,汝是天下万世仇!生民何罪复何尤,被汝趋走寊荒陬”。而郭沫若对《暴虎辞》的一番解释更是耐人寻味:“诸位!我在此处不免又要谈说一番历史了。李禹底祖父李广本是弓箭底名手,他与当时的匈奴大小七十余战,可终莫有甚么大功。后来到了六十多岁,跟随着大将军卫青出征,卫青不信用他,是他纡回远道。他因此迷失路途,误了军势,遂至到头自杀了。他的第三个儿子李敢,便是李禹的父亲,因为替他父亲报仇,曾经把卫青打伤;他也就因此被人暗杀了。卫青和暗杀李敢的人都是些外戚权贵,所以李禹说父遭暗箭祖自残,都是权贵之人中作蛊呢。”(42)郭沫若:《暴虎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343-344页。这哪里是在讲古,分明是在讽今,而在这“讽”的过程中,郭沫若也对自己曾经深深信赖的政治强权做出了深刻的反思。在另一首《哀时古调》中,郭沫若更是明言:“神州原来是赤县,会看赤帜满神州。朋友,朋友。努力事耕耰。”(43)郭沫若:《暴虎辞》,《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卷,第350页。这一时期的郭沫若已经清楚地认识到,要想重振华夏,需要包括自己在内的每一位公民的参与,只有国民才是中华民国的主人。
正如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所言,“现代民族国家是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它是想象的,因为即使是最小的民族的成员,也不可能认识他们大多数的同胞,和他们相遇,或者甚至听说过他们,然而,他们相互联结的意象却活在每一位成员的心中。”(44)[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6页。经由对强权的反思,郭沫若认识到了曾经对国家在国土层面上的片面理解与对政治强权的迷恋使其忽视了一个最为强劲有力的现代民族国家建构的力量,即包括郭沫若自己在内的国民;而中华民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其发展的根本也在于要建立国民对政治体制的认同,并在这个政体制度下形成一种有关群体的想象。及至后来,随着郭沫若的思想转向马克思主义,国民的概念也渐为人民所代替,这种经由反思而来的国家观念深刻地影响着郭沫若的一生。1926年,郭沫若在北伐途中经过湖南汨罗江,留下了《过汨罗江感怀》一诗,诗中有两联写到:“揽辔忧天下,投鞭问汨罗:楚犹有三户,怀石理则那?”(45)郭沫若:《北伐途次》,《郭沫若全集·文学编·第1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第14页。屈原失去的只是怀王的信任,而只要楚国的人民还在,楚国就总还是有收复失地的一天,既然是这样,又何必要投江自杀呢?这也正是郭沫若转型后的国家意识的真实写照。
五、结语
通过对郭沫若旧体诗的梳理和研究,可以看到一条国家意识从萌芽到定型的线索。从单纯对国土的认同到对强权政治的倾心,再到心中“国民”意识的觉醒,郭沫若每一次国家意识转变的背后实际上都是个人境遇与宏观历史之间的对话。而就旧体诗文体而言,由于其高度凝练的格式,在很多内容背后都有着微言大义,尤其是以郭沫若为代表的这些曾经深受传统文化熏陶的现代作家,其旧体诗创作中的典故、情绪,乃至于韵脚等方面都尚存在很大的解读空间,值得研究者们持续进行关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