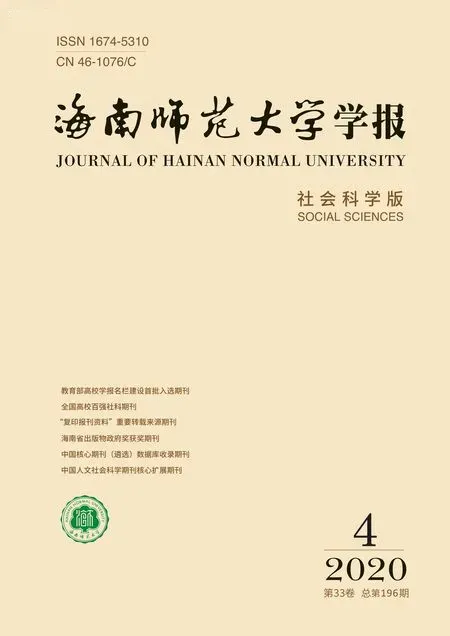作为方法的“新旧时间意识”
——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论
赵 斌
(衡阳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南 衡阳 421002;江西省社会科学院 文化研究所,江西 南昌 330077)
现代时间暗含人类进步发展的密码,规约着我们的思考与实践。现代时间意识是一种新旧时间观念,其在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小说现代转型中的新旧时间问题很复杂,因为,进化过程中的小说嬗变“往往包孕着冲突、断裂、转折和飞跃,它甚至不局限于单线承递,却要在共时与历时各条线路的协同作用下交织成一幅多向分化与综合的复杂图景。”(1)陈伯海:《关于文学史进化的探讨》,《文学评论》1993年第6期。晚清、“五四”小说中的新旧时间问题也具有这种复杂性,但这并不影响我们沿着新旧时间这条线索考察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问题。鉴于新旧时间问题的复杂性,我们大致从进化论与作家的新旧时间意识、新旧时间的过去-现代-未来、晚清小说中的“白日梦”与分离式的新旧时间、“五四”小说中的“梦醒了无路可走”与残缺的新旧时间等问题进行阐述,其他问题只是略有涉及。
一般来说,进化理论下的线性时间(新旧时间)意识是一种认为社会发展是直线前进的直奔终极目标的时间观念。在今天看来,这是一种偏执的时间观念,其认同性不高,但近代的进步知识分子却认为是“时间公理”,他们普遍“以新胜过旧的逻辑将‘新’置于经典之上,甚至将‘新’神圣化、经典化。”(2)②耿传明:《〈天演论〉的回声:清末民初知识群体的心态转换与价值翻转》,《天津社会科学》2007年第5期。这是符合当时思想界的认知心理的。概而言之,近代伊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的天道循环时间转向了天演进化时间,形成了线性新旧时间。
线性新旧时间“不仅成为这个民族近代以来种种历史行动的理由和依据”,也成了“革命家的行动理由,实际上也是普通人忍受种种苦难,却对未来不完全失去信心的潜意识根据。”(3)[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13页。线性新旧时间把“进步”绑架在直线向前的时间轨道上,把事物是否“发展”看成社会历史进步与落后的标志,而一旦发展受阻,便会产生种种关于转折时期新旧转换的焦虑,而“求新”似乎是唯一可靠的行动,否则,只能埋葬在“旧”的时间中。
一、进化论:作家的新旧时间意识
在中国小说现代转型中,进化论起着不容忽视的作用,其对中国作家的新旧时间观的形成也有着重要的促进作用,这有其时代驱动力的原因所在。正如黄开发所言,“从戊戌变法到20年代中期”的“传统向现代的转型”“并非中国文学内部发展的结果,而是由民族危难激发的”,有其“救亡图存的外在动力。”(4)黄开发:《新民之道——梁启超的文学功用观及其对“五四”文学观念的影响》,《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99年第4期。在这种“外在动力”下,国人亟需一种新的思想理论来解决现实问题。而1898年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犹如雪中送炭,革新了一代人的时间观念。正如曹聚仁总结的那样,在《天演论》熏陶下,“如胡适……以‘适’为名,即从《天演论》的‘适者生存’……陈炯明,名‘陈竞存’,即从《天演论》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5)曹聚仁:《中国学术思想史随笔(修订本)》,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371-372页。这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R.韦勒克曾经指出,只有当“进化论使用了诸如‘适者生存’……等概念时,它才能被称为达尔文的进化论。”(6)[美]R.韦勒克:《批评的诸种概念》,丁泓等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8年,第48页。实际上,进化论这种语言学接受史在《天演论》早期传播史上十分常见。蔡元培曾说严复译的《天演论》出版后,“‘物竞’、‘争存’、‘优胜劣败’等词,成为人人的口头禅。”(7)蔡元培:《蔡元培全集》第4卷,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352页。这些进化论词汇也成了晚清、“五四”小说中常见的词汇。例如,包天笑的《空中战争未来记》有“世界文化日进,生民智慧日睿”等等。进化论也是小说评论的理论依据。有人评论吴趼人的《新石头记》时认为小说中的“文明”“千奇百怪,花样翻新”都有很重要的现实意义,其“循天演之公例……为极文明极进化之20世纪所未有”。(8)报痴:《说小说》,《月月小说》1906年第2期。这也是当时的肺腑之言。
在新旧时间转换的过程中,进化论是其理论依据。杜赞奇对此做过富有创建性的回答:“线性历史……最重要的手段便是进化的叙述结构,它通过历史主体为未来增加了一层稳定感:进化的事物在变化中保持不变。历史主体是一个形而上的统一体,用来对付线性时间经验的困境,即过去与现在的分离以及流动的时间与永恒的时间之间的脱节。”(9)[美]杜赞奇:《从民族国家拯救历史——民族主义话语与中国现代史研究》,王宪明等译,第29页。我们知道现代性概念来源于欧洲,现代性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时间观念,是一种面向未来的执念。中国原初的天道循环时间几乎没有“现代性”的质素。“人生代代无穷已,江月年年只相似”“青山依旧在,几度夕阳红”,时间反复循环,很难与“进步”的新旧时间意识关联起来。
晚清、“五四”是重要的转折时期,政治、经济、文化等接连不断的危机冲击着传统的天道轮回时间观,孕育出新旧进化时间观,其中严复翻译的《天演论》贡献最大。《天演论》是西方的文明成果,代表西方的“先进时间”“新旧”有“时、空”上的差异,前者以“现在”为标尺,“过去”为旧而“未来”为新;后者则以中方为旧、西方为新,“吾国今日新旧之争,实犹是欧化派与国粹派之争”(10)管豹:《新旧之冲突与调和》,《东方杂志》1920年第1期。,基本属于空间意义的新旧。近代先进知识分子把探寻与学习的目标瞄准了代表“先进时间”的西方,即完成了对“时间的空间化”的体认,“中西方的空间性差异开始转换成时间性的历史阶段差异。”(11)耿传明:《时间意识、现代性与中国文学的古今之变》,《文艺争鸣》2015年第6期。而《天演论》在这场时空意识转变的革新运动中起着关键作用。
受时代意识的影响,晚清、“五四”两代小说家大都接受过进化论思想的洗礼。梁启超曾经说过:“竞争也,进化也,务为优强,勿为劣弱也,凡此诸论……莫不口习之而心营之”(12)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三),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12页。,《天演论》以“世道必进,后胜于今”的进化时间观替换了“天不变,道亦不变”的传统轮回时间观,建立起面向未来的新旧时间观。《天演论》犹如一场“及时雨”,为现代新旧时间观的形成提供了思想动力,它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展示了一种统摄历史目的与自然规律于一体的现代时间-历史观”,也为民族国家这个历史主体“提供了以线型进步时间——历史大势”(13)尤西林:《心体与时间:二十世纪中国美学与现代性》,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28页。。作为本体根据的价值定位,新旧时间成了判断进步/落后的标准。这样,进化的新旧时间观就遮掩了社会演进过程中退化、循环、交错的历史复杂现象,而且有将新与旧、现代与传统简单对峙起来的弊端,但是进化论必定构建起一种新的时代视野和时间意识,促进了中国小说的现代变革。
晚清、“五四”时期,进化论影响深远。“‘进化论’在新旧时间观的转换中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它不仅是摧毁传统文化时间观的利器,也是新时间观形成的内在依据。”(14)唐晓渡:《时间神话的终结》,《文艺争鸣》1995年第2期。晚清、“五四”时期的小说也是在进化维度中展开其变革行动的。“欲新一国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国之小说。”(15)梁启超:《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陈平原,夏晓虹编:《20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1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第33页。晚清“小说革命”的宣言,句句落实在“新”字上,即使是谴责类的小说,也能够依照一种对旧现实彻底否定和批判的精神来表达对“新”的追逐。民初小说家大多是期刊编辑,他们也有新旧时间意识。如《小说新报》发刊词有“爱情读新装简册,伦理讽旧日文章”之语;《香艳杂志》声称“本编无新旧之偏见”;王蕴章主编的《小说月报》抱着以“缀述旧闻,灌输新理,增进常识”作为刊物宗旨;包天笑在《妇女时报》声称该刊“责任”在于“改良恶风俗、发扬旧道德、灌输新知识”,其在另一个刊物《小说画报》的“短引”中更是提出了“借材异域求群治之进化”(16)期刊发刊词、编辑声明等。如李定夷:《〈小说新报〉发刊词》,《小说新报》1915年第1期;均卿:《新彤史》,《香艳杂志》1915年第6期;《编辑室之谈话》,《妇女时报》1916年第18期;包天笑:《〈小说画报〉短引》,《小说画报》1917年第1期。的呼喊声。当然,清末民初时期的知识分子的时间观还残留着传统的时间意识。
“五四”时期的知识分子对新旧进化时间都有深刻的认知。陈独秀认为在进化论的时间链条上,欧洲文学思潮由“理想主义再变而为写实主义(Realism),更进而为自然主义(Naturalism)。”(17)陈独秀:《现代欧洲文艺史谭》,《青年杂志》第一卷第三号。实际上,“五四”文学的“新”是一个社会历史时间的概念,它与古代文学的“旧”是相对的。并且,“‘新’与‘旧’以历时性的方式(diachronically)结合在一起,而且前者看起来总像是在向死者召唤一种暧昧的祝福。”(18)[美]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象的共同体: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吴叡人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183页。鲁迅也曾经“一有闲空,就照例地吃侉饼、花生米、辣椒,看《天演论》”,“一口气读下去,‘物竞’‘天择’也出来了,苏格拉第,柏拉图也出来了,斯多噶也出来了。”(19)鲁迅:《琐记》,《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306页。总之,转折时期的知识分子都有“求新”意识,具有“唯新主义”思想,在“进化论框架下”推演出“‘新’与‘旧’,已经由两个原本中性的词演变为具有鲜明价值评判色彩的语汇,表达着进化与进步的意义指向。”(20)张宝明,褚金勇:《“唯新主义”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河北学刊》2011年第4期。处在现代转折阶段的晚清、“五四”知识分子对进化论却深信不疑,他们大都有很强烈的新旧时间意识。
二、新旧时间:过去、现在和未来
新旧时间是以“进化”为人类社会的发展维度,将历史划分为过去、现在和未来三个连续的时间段,过去负载着落后和黑暗,反叛过去也就是“斥旧迎新”;未来代表光明和希望,面向未来也就是“求新”。正因为如此,“理解时间意义的全部困难就在于理解过去、现在和未来的关系。”(21)[英]埃利奥特·贾克斯:《时间之谜》,[英]约翰·哈萨德编:《时间社会学》,朱红文,李捷译,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4页。新旧时间观的问题很复杂,与时代密切关联,也与人们心中的现代化焦虑密切相关,政治革新、文化革新、思想革新,处于转折时期的人们在焦躁不安中、迟疑不决中迎接一个个“新时代”。奥斯本认为:“有意识的弃绝历史性现在本身,把它当作不断变化的过去和仍不确定的未来之间的永恒过渡这样一个正在消逝的点,换句话说,现在就是持续和永恒的同一。”(22)[英]彼得·奥斯本:《时间的政治——现代性与先锋》,王志宏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31页。奥斯本把“现在”作为“过去”与“未来”之间的中介点,并且突出“现在”时间的独立意义,这样很自然地把“过去”的“旧”与“将来”的“新”做以区分。
王一川认为:“进化论为新,为未来许诺和提供了价值、权力、崇拜与合法性。”(23)王一川:《文学革命:进化文学史观》,《涪陵师专学报》1999年第4期。这一“未来性时间取向”与传统“过去性时间取向”截然不同。因为“过去”是传统时间的核心,人类一直从“过去”时间获取生存的意义,也以“过去”来评判社会发展的程度。在农耕社会里,老人比青年更有优势,老人身上蕴藏着“祖先所遗留的智慧与经验的库藏”,因此“权威常在老人手中”,近代以前的“中国成为一‘老人取向’的社会”。(24)金耀基:《从传统到现代》,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第12页。黑格尔则认为:“这个时代是一个新时期的降生和过渡的时代……成长着的精神也是慢慢地静悄悄地向着它新的形态发展,一块一块地拆除了它旧有的世界结构。”(25)[德]黑格尔:《精神现象学》上卷,贺麟,王玖兴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年,第6-7页。这个时代正处于过去已经过去、未来尚未到来的过渡时期,但无论如何,具有现代品格的新旧时间已经到来,并且人们也在不断地从“未来”时间挖掘意义,去构建人类新的时间体验。
现代时间“不同于古代一般意义上的新变,而是明确设定了时间的前方模式”,其“重心在于‘未来’”,“现在是对于将来的一种开创,历史因为可以展示将来而具有了新的意义。”(26)詹冬华,占淑荣:《中国古代趋新派文变观中的时间之维——兼与现代进化论文学史观之比较》,《江西师范大学学报》2005年第4期。现在是为未来的进步打基础,现在的价值意义必须经由对未来的超前想象才能得到确证,这就是现代的新旧时间意识。随着科技的发展进步,人们对“未来”的预测更为乐观,人都在憧憬美好的未来。
新旧时间是一种现代性时间。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或者说是一种直线向前、不可重复的历史时间意识”。(27)王晓明:《批评空间的开创》,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年,第2页。现代性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时间感知方式:以西历为时间的标准,包含着时间向未来无限伸展的认知。当然,面向未来的生活并不是同质性的无限延伸,但是,在中国现代社会转型时期的晚清、“五四”,先觉者们对这种未来趋向的时间观念的进步性充满着无限的信任,并由此建构了一种过去、现在、未来的目的论史观。
上文论述了晚清、“五四”小说家都有进化论思想,有新旧时间意识。根据刘永文编的《晚清小说目录》统计的数据显示:发现第一篇以“新”命名的小说是署名“饮冰室主人”撰写的小说《新罗马传奇》,发表在《新民丛报》第十号至第五十六号上,首载时间是1902年6月20日,而1902年到1910年期间《晚清小说目录》收录了以“新”命名的小说多达170篇,这一数字仅仅包括很少的几篇译文小说。(28)刘永文:《晚清小说目录》,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第7-391页。这一数据说明了在进化理念下的《新中国未来记》《新石头记》《新纪元》《新年梦》等“新式小说”书写着小说家们对未来时间的热情与渴望,但是受时代环境及文学自身演变的局限,以至于小说家的新旧时间意识与文本表述出现了悖离。具体言之:一、时代没有给小说家提供足够“面向未来”的驱动力,小说家看不到希望,即使意识到危机重重,也无法突围“铁屋子”;二、小说新旧时间书写一定程度上借鉴了外国未来小说的写法,但中外境况明显不同,照搬照抄肯定不行,而中国古典小说又无法提供多少可供借鉴的写作资源。所以,作为过渡时期的晚清、“五四”小说对新旧时间的书写都不成熟,还处于摸索阶段。一般来说,小说现代转型中的新旧时间观念主要有两个时间面向,一个时间面向是晚清、“五四”小说作者或书中人物所持的进步时间观念,另一个时间面向是小说叙事艺术层面上的进步时间意识,两个时间面向有一定程度上的视域融合。
三、晚清小说:“白日梦”与分离式的新旧时间
从小说的时间结构上看,晚清小说的过去时间与未来时间往往相互分离、单独呈现,没有过程感,只是出现一个“过去”或“未来”的空间,“时间的河谷出现了断裂,人们恰恰被抛弃在无可依傍的断层空间。”(29)许纪霖:《无穷的困惑:黄炎培、张君劢与现代中国》,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年,第1页。处在一个新旧杂陈、中外对峙时代的晚清小说家都有求新的意识,但他们在小说中的新旧时间的表述却截然不同。谴责小说家痛快淋漓地暴露晚清官员的虚伪无耻和道德沦丧,控诉的是旧文化价值观失落的现实,面对的是罪恶的过去或现在;政治小说家则抛弃陈旧的过去或现在,迎接崭新的未来。简而言之,晚清小说家都很难把新旧放置在时间线上做出符合现实和逻辑的推演,即使稍有过程感也只是顿悟式的新旧转换,显得突兀而又牵强附会。
(一)从野蛮到文明的新旧转化
在线性时间链条上,晚清先觉者们大都把新旧进化时间看成从野蛮到文明的转化。早在义和团时期,麦孟华在《清议报》上就说过:“排外之道有二,野蛮人之排外,排以腕力;文明人之排外;排以心力”(30)麦孟华:《排外平议》,梁启超编:《清议报全编》第一集卷二,日本横滨:新民社,1901年,第1-4页。,这与《警世钟》《革命军》中的“野蛮排外”“文明排外”所作的区分是一样的。另外,《东欧女豪杰》《文明小史》《苦学生》《乌托邦游记》《虞初今语·人肉楼》《新石头记》《中国进化小史》等小说也都提出“野蛮”“文明”的界分,“论那天演公理”“使尽把世界上文明的大敌都扫清了”,以至于“野蛮政府,在今日开明之世,是有一无二的了。”(岭南羽衣女士《东欧女豪杰》)可见,文明和野蛮既是二元对立,也是新旧时间转化的依据。
野蛮/文明是一种空间上的时间界分,中国人在时间上是落后于西方的,但是也深信中国人在时间上是可以追赶上西方的。如仅有两回的“未竟之作”《中国进化小史》论述了文明与野蛮的“人民”与“国度”是可以随着时间“进化”的,“世界上没有不进化的人民,就是没有不进化的国度……要晓得进步是由野蛮而之文明,进化是由今天到了明天。”(燕市狗屠《中国进化小史》)最终,黄种人战胜了白种人,比西方更文明、更进步,因为“新年了,到新世界了”。(31)蔡元培:《蔡元培全集》,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第242页。
但在当时,晚清谴责小说家对中国的现状却不乐观,他们通过比较认为,“我汉族对于蒙古、满洲、苗、瑶自然是文明的,对于欧美各国又是野蛮”的,如果“不力求进步,使文明与欧美并驾齐驱”,肯定会亡国“灭种”,因为“中国,一大死海也……自甲午以来,创深痛巨,二、三志士奔走号呼,亦已口瘏心瘁矣。”(陈天华《猛回头》)《文明小史》的开头写的湖南永顺府是“野蛮”的——“苗汉杂处,民俗浑噩”,“虽说军兴以来,勋臣阀阅,焜耀一时,却都散布在长沙、岳州几府之间,永顺僻处边陲,却未沾染得到。”所以,姚老先生认为:“民风保守,已到极点,不能革旧,焉望生新?”改革只能够多用些“水磨工夫……断不可操切从事,以致打草惊蛇,反为不美……以愚兄所见,我们中国大局,将来有得反复哩!”小说第一回批注者也认为:“书曰文明,却从极顽固地方下手,以见变野蛮为文明,甚非易事。”(李伯元《文明小史》)这些观点在亟需变革的时代确实有些不合时宜,结合中国近现代以来的改革史、革命史,也许是一种深远的预见。一方面,处于“千年所未有之巨劫奇变”的危险时刻,各类人物都意识到中国必须除旧布新,进行改革。如李伯元意识到他处在“黑暗和光明的交替处”和“动乱的时代”,所以,他要把现实“无情的揭露出来,希望能为改进的一助”,从“朴陋”的湖南开场,是为了“要先写一个守旧的地方,以与维新的湖北、上海各处相对照。”(32)阿英:《晚清小说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15页。这样看来,李氏有依据进化论思想来构置小说的潜意识。安德鲁·琼斯认为进化论虽然还不是“一个精确的术语”,还“不足矣表述发生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那不均衡的、复杂的并精微如毛细血管般的对社会科学与大众话语的渗透现象……这种思想的关键,便是其对于发展式叙事的确信。在这种叙事中……个人与国家一样,都被假定为是沿着一条连续的线索从‘野蛮’向‘文明’前进着。”(33)[美]安德鲁·琼斯:《鲁迅及其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王敦,李之华译,《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2期。也许,在今天我们会对这种从野蛮到文明的新旧时间转化提出种种质疑,但当时的小说家们是深信不疑的。
当然有些晚清小说家对野蛮、文明的理解有自己的看法,甚至对“假文明者”充满愤慨。《乌托邦游记》有言:“看见英国名士赫胥黎的《天演论》,也提起‘乌托邦’三字……哪知这文明国民,所作为的都是野蛮,不过能够行他的诈伪手段,强硬手段,就从此得了个文明的名声……能够侵夺别人欺悔别人的,都是文明;被人家侵夺,被人家欺侮的,都是野蛮。”(萧然郁生《乌托邦游记》)小说家是按照《天演论》的进化时间来思考社会发展的,而社会、历史进化是依据野蛮到文明的新旧转化的,他们在寻找“乌托邦”——一个理想中的“文明”天堂。《新石头记》的贾宝玉是从“野蛮社会”进入了“文明境界”的,贾宝玉通过深入研究后发现,晚清的中国已有种种“文明”的表象,却仍然是那样的野蛮。问题的症结是官场的极其腐败。于是,贾宝玉下决心要寻找真正的“文明境界”。在新旧时间转化的过程中,腐败的官场是新旧历史转化的障碍,而改造好官场,野蛮的官场变成了文明的官场,社会也自然就进步了。这一朴素的新旧进化思想是当时救治民族国家的一种方法。
根治官场、深化政治改革是当时提出的野蛮变文明的一条路径,“教育兴国”也同样是野蛮变文明的一条变革路径。教育小说表达了“教育兴国”的进化理念,把新旧时间的转化寄托于教育界的改革。例如,“乘此学务方兴之际为营私图利之地,演出种种怪现象……喜我中国尚有人在,求真学问、扫怪现象,大放学界光明。急起直追竟能慑服列强,使中国能有富强之一日。”(老林《学堂笑话》)很显然,作者把学界也当成“官场”加以谴责了,并且也影射到社会进化的时间方向。教育小说集中于中国传统的旧观念和新思想的矛盾。可惜的是,他们对新的政治走向还不太清晰,只能通过小说描绘种种“怪现状”,“为着暴露,为着寻找出路而出现的新与旧的矛盾斗争关系”,其中最主要的是,“为着有话说,要说话,中国要亡了,有爱国心肠的人,不能不大声疾呼。”(34)阿英:《小说三谈》,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第19页。《学究新谈》《未来教育史》《学界镜》等小说都描述了从野蛮到文明这一新旧时间转换主题。
(二)“白日梦”对新旧时间的缓冲
在晚清小说中的新旧时间的链条上,小说家对中国的过去(旧)认识得很清楚,对民族国家的未来(新)却是模糊的。谴责小说重在暴露中国的“旧”,对中国的“新”没有提出多少未来预设;政治小说与谴责小说形成补充,重在想象中国的“新”(乌托邦)。而政治小说对民族国家“新”的想象是依据西方发达国家为模板而进行的科学幻想,有现实的基础,但缺少推理演绎的逻辑性。野蛮落后的旧中国如何能够踏进文明进步的“乌托邦”?似乎很难找到一个合理的解释。面对这种野蛮与文明、旧与新的时间断裂,晚清小说家找到了“白日梦”这个时间中介。处在过去(旧)时间的主人公会“黄粱一梦”,然后进入到未来(新)的时间轨道上。
“白日梦”是虚幻的,但也有一定的现实依据,“日有所思”才能“夜有所梦”。“白日梦是故意做的清醒梦,也就是梦想”,“梦想是对某种现实的不认可,它表达的不是‘世界是这样的’,而是‘世界必须是这样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世界不应该是那样的’,这样它就成为一个引导社会行为的政治规划”,也可以说“社会理想、乌托邦或者社会制度设计就是最大的梦想。”(35)赵汀阳:《美国梦,欧洲梦和中国梦》,乐黛云:《跨文化对话》第18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43-161页。在小说中出现梦境是很正常的,中国古代小说就有大量梦境的描绘,这些梦境对于情节设置、人物心理以及小说艺术的构造等都具有调适功能。随着中国小说的现代转型,小说逐渐“向内转”,“梦”在小说中的表现更加丰富多彩。在晚清的小说中,“梦的社会性,则是对未来社会建制的一种理想性表达……文学中的‘乌托邦’被认为是典型的‘白日梦’,其幻想性常常是推动社会和历史前进的一种力量。”(36)高鸿:《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学海》2013年第5期。但不可忘记“白日梦”的虚幻性,因为“梦是一个(受压制的或被压抑的)欲望的(伪装的)满足。”(37)[奥]弗洛伊德:《释梦》,孙名之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年,第157-158页所以晚清政治小说用梦链接过去与未来、“旧”与“新”所展现的时间的虚幻性,也就是从野蛮到文明、从“旧”到“新”的时间进化过程中所展现出的虚幻性,其“白日梦”书写的现实依据不充分。
晚清“白日梦”小说叙事模式可能是借鉴了美国作家爱德华·贝拉米的出版于1888年的小说《回顾:2000—1887》的写法。例如,1891年在《万国公报》连载的《回头看纪略》,在当时极受欢迎,其“很大程度上与19世纪末叶深受经济危机频繁震荡的人们企盼社会变革的愿望有关。”(38)宋师亮:《论晚清政治小说中的乌托邦叙事》,《渤海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1期。晚清小说家被《百年一觉》中的乌托邦意象所吸引。这样的理想社会正是晚清先觉者们所梦寐以求的,借鉴其“白日梦”写法成了很自然的事情。晚清乌托邦小说有这样相似的情节:“我”“忽然瞪目一看,自己恰睡在李医生家的床上,外面已经天亮了,我方才知道回到十九世纪的,恰是一梦,这二十世纪恰是真的。”(39)爱德华·贝拉米:《回头看》,上海:商务印书馆,1914年,第144页。小说在时间中穿越,一个“白日梦”链接了时间的过去与未来,使新旧时间的过渡顺其自然,增强了小说情节设置的合理性,同时也给故事增添了虚幻感,必定是一个“白日梦”而已。晚清政治小说多采用这种“白日梦”的写法叙述未来,铺展故事。李伯元《官场现形记》、梁启超《新中国未来记》、吴汝澄《痴人说梦》、陆士谔《新中国》、碧荷馆主的《新纪元》等小说都多多少少受到《百年一觉》的影响。
晚清的政治小说确实给焦灼无助的先觉者提供了想象未来的动力。“政治小说综述关乎未来。即使它批评当下,也总是包含着对未来的憧憬。它预设了一个国家的发展方向。”(40)季进:《“政治小说”的跨界研究———叶凯蒂访谈录》,《另一种声音:海外汉学访谈录》,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58页。《新中国未来记》是对60年后的社会乌托邦想象,预示了中国前进的新的时间方向,小说“在叙事时间上呈现了一种‘跨越式’的表现,文本叙事上‘半途而废’的《新中国未来记》,在故事时间上有过去、有未来,但在完成的过程却来了个‘紧急刹车’,‘丢失’了由旧转新这个重要过程。”(41)高鸿:《探寻晚清的“中国梦”——晚清政治小说〈新中国未来记〉的法律想象和审美价值》,《学海》2013年第5期。这是问题的关键,乌托邦小说在想象未来的时候必须处理好新旧时间的转化。那么如何转化呢?答案是:引入“白日梦”。很多晚清小说(包括谴责小说)借鉴了这种写法。
遂在椅上睡去了……原来此山有一只大狮,睡了多年,因此虎狼横行;被我这一号,遂号醒来了,翻身起来大吼一声。那些虎狼,不要命的走了……转眼又不是山中,乃是一个极大都会……讲不尽富贵繁华,……又到一个大会场,大书“光复五十年纪念会”。《狮子吼》
(“我”)刚合上眼……到马路上一瞧,不觉大惊,但见世界换了个样子……女士笑道:“你怎么一睡就睡得糊涂了!现在,治外法权已经收回……”我道:“我与你不是都在梦里么?”女士道:“你疑是梦,你才在梦里呢!”(《新中国》)
我想游乌托邦的心愈热……不觉昏昏睡去。忽而背后术了一人,把我的肩上一拍道:“你要到乌托邦去么?你除非到何有乡乘船,方才好去。”我听了吓了一跳。我就信步出门,从那人同去。(《乌托邦游记》
上文所摘要《狮子吼》《新中国》和《乌托邦游记》里面的“白日梦”片段都是新旧时间的过渡情节,人物由过去走向未来。正如陆贞雄(陆士谔之孙)说:“在《新中国》这部小说内,我的祖父以‘梦’为载体,描绘了自己所憧憬的理想社会。”
《新石头记》也有“白日梦”的写法。贾宝玉在大荒山青埂峰下,“不知过了几世几劫,总是心如槁木死灰,视千百年如一日”;焙茗在一座道观里,一睡不醒;薛蟠则是和朋友们逛陶然亭,吃醉了酒,就在那里睡到了二十世纪。小说借助“白日梦”进行快速地时间转换。到了小说最后一回,宝玉借助“白日梦”重返上海,崭新的未来世界呈现眼前:中国摆脱了帝国主义的侵略,收回了“治外法权”,经济繁荣,各地大力开办商场,建设了无数的工厂……如果说吴研人在《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里只是罗列了种种“怪现状”,没有谋划出救亡图存的方案,那么《新石头记》则在前半部描述了过去的中国旧社会,后半部畅想了几十年后的未来世界,用“白日梦”链接起了新旧时间,还是有积极意义的。换句话说:“前半部是作者认识到的当时的社会现实,后半部是作者想象中的理想世界的刍形,它集中地展现了吴趼人对救亡图存的考虑。”因此,“《新石头记》对于研究吴趼人的政治理想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和意义。”(42)[韩国]南敏洙:《〈新石头记〉初探》,《东岳论丛》1999年第1期。无独有偶,小说《学究新谈》通过夏仰西的一个梦境想象了一幅理想的图景:在泰平乡里全面实行了义务教育,办起了小学堂,“一里地内,随便那家的小孩子,都可以进去读得书,不要学费。”“学生早半天放牛,下半天去读书”(第四回)。在小学堂里,操场上活跃着学生打秋千、盘杆子的身影,科学馆里,有各种供学生进行机械、电学、声学先进设备。这部小说用“白日梦”暂时实现了“教育救国”的乌托邦想象。
“白日梦”载渡新旧时间的写法只能有限缓解新旧时间的断裂,因为“乌托邦式的科学幻想,可把一个失败的国族空间投置在乌有乡中,重新构建其合法与合理性”(43)王德威:《被压抑的现代性——晚清小说新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309页。,其难度是很大的。“吴趼人的小说围绕着进化思想的核心悖论,特别是围绕着关于‘文明’与‘野蛮’的时空二元进行建构,他的文本试图在历史必然性的铁律之外幻想出另一个未来,但却被自己叙事逻辑的形式矛盾所粗暴地惊醒。”(44)[美]安德鲁·琼斯:《鲁迅及其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王敦,李之华译,《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2期。这些叙事倾向仍然无法逍遥于历史因果律的线索之外。作者固然能轻易通过制造叙事断裂来炮制一个截然不同的未来,“这个断裂……确保了新乌托邦的激进的与现存社会的不同”,但“悖论在于,如何解释作者是身在现存的社会资源里想象出如此迥异的乌托邦来?”如何才可能做到既成功达成了一个历史转型的完成,又成功挑衅,或至少搁置了那被认为是统驭历史转变的进化论式法则和详细过程?这个逻辑上的死胡同,常常导致不完整或断裂的叙事,或导致乌托邦叙事自身走向土崩瓦解——它无法承受自身的形式及意识形态上的断裂。(45)[美]安德鲁·琼斯:《鲁迅及其晚清进化模式的历险小说》,王敦,李之华译,《现代中文学刊》2012年第2期。所以晚清小说的新旧时间叙事仍然是分离式的,无法完成新旧时间的现代转型。
四、“五四”小说:“梦醒了无路可走”与残缺的新旧时间
学界一般会把清末民初连在一起加以论述,但实际上,在新旧时间的意识上民初小说家与 “五四”新文学家更接近。民初小说家相对于晚清新小说家有某种历史的退步,但民初小说家的新旧认识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一直以来,辛亥革命在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中的作用被学界有所忽视,事实上辛亥革命在中国文学转型中所起的作用,特别是在中国小说的新旧时间叙事形成、转化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并不比“五四”新文化运动的作用小。因为晚清“新小说”家们面对民族危机四伏时仍然怀着极大政治热情去畅想未来,而民初、“五四”小说家们面对新建立的民国,越来越陷入时间的困境,无路可走。不可否认的是,受时代变迁的影响,民初、“五四”作家的思想越来越现代,但辛亥革命在最终结果上的失败却带来了新的创伤,使他们对时代更加焦虑,故而他们在小说中的新旧时间意识与晚清作家呈现出明显不同。
晚清到民初、“五四”,新旧时间叙事有了新的转化:一、从社会的新旧变迁到人的新旧成长;二、新旧时间叙事模式更加完整,只是对未来的想象不足;三、新旧时间意识更明确和强烈。而“五四”和民初的新旧时间叙事也有些区别,大致来说,“五四”的新旧时间意识更强烈。更为重要的是,虽然两个时期都是从民族国家的新旧时间转向到人的新旧时间上来,但是民初小说回到世俗言情中,人的现代性很大程度上被消解掉了,甚至沦落到退步的境地。相对来说,“五四”新文学家要比民初小说家进步和积极得多。其实从深层次上看,民初小说世俗的“人”的发现是“五四”“人学”的基础,有不可否认的文学史意义。当然“五四”的新旧时间叙事比民初更典型。
“五四”小说的新旧时间叙事根源于辛亥革命所带来的历史困境。因为中华民国建立之后,新生的“民族国家”并没有按照晚清“乌托邦”设想发展,希望很快破灭了,人们对政治现状极度失望。如果说晚清先觉者们还可以满腔热情设计各种“乌托邦”建国方案,完成各种形形色色的“梦想”,那么辛亥革命之后,面对如此复杂的民国现实,想要改弦更张、重新筹划未来,几乎没有可能。基于此,李大钊在《隐忧篇》中展露了他对新民国的“忧心忡忡”:“其扶摇飘荡,如敝舟深泛溟洋,上有风雨之摧淋,下有狂涛之荡激,尺移寸度,原望其有彼岸之可达,乃迟迟数月,固犹在惶恐滩中也。”(46)李大钊:《李大钊文集》(上),北京:人民出版社,1984年,第1页。鲁迅也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试将记五代,南宋,明末的事情的,和现今的状况一比较……现在的中华民国也还是五代,是宋末,是明季。”(47)鲁迅:《忽然想到·四》,《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17页。鲁迅似乎有点偏执,却不无道理;鲁迅把民国看成旧历史的轮回稍显过分,却符合他非常复杂的“五四情绪”——梦醒了无路可走。
如果说晚清小说是用“白日梦”链接新旧时间,缝合“过去”与“未来”,以便形成一个看似连贯的进化时间线,那么“五四”小说却无法呈现新的时间——未来,只有用“梦”迷醉自己,却又是醒着的,因为“五四”先觉者对新旧时间的体悟更为强烈。茅盾说:“新文学就是进化的文学。”(48)冰(茅盾):《新旧文学平议之评议》,《小说月报》1920年第1期。此言可谓一针见血。“五四”小说家坚信不断进化的时间的前方必然有光明的未来,只是这种新未来被复杂的现实“搁浅”,暂时还找不到新的时间方向。他们知道在进化的新旧时间向度上,过去代表着“落后”,将来代表着“进步”。这种新旧时间意识在鲁迅早期的《中国地质略论》《人之历史》等文中已经有所表述。在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鲁迅说:“大学无甚事,新旧冲突事。”(49)鲁迅所说是指:1919年3月18日,《公言报》刊出《请看北京学界思潮变迁之近状》污蔑革新派,同时发表林纾的《致蔡鹤卿书》,蔡元培有《答林琴南书》进行反击,等等。这句话表明:一、“五四”时期的鲁迅是用新旧观念看待问题的;二、大学中的知识分子也都有界限分明的新旧观念。问题是具有强烈新旧时间意识的鲁迅在思想中偶尔也会有消极情绪,但他直对未来还有信心,他说:“‘将来’这回事,虽然不能知道情形怎样,但有是一定会有的,就是一定会到来的,所虑者到了那时,就成了那时的‘现在’。然而人们也不必这样悲观,只要‘那时的现在’比‘现在的现在’好一点,就很好了,这就是进步。”(50)鲁迅:《两地书·四》,《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21页。茅盾说:《新青年》到底是一个文化批判的刊物,而新青年社的主要人物也大多数是文化批判者,他们的文学理论的出发点是“新旧思想的冲突”。并且“新旧思想的冲突,确是现在重大而耐人焦虑的问题。现在创作中描写新旧思想冲突的作品,虽都是短篇的,却也已经不少。”(51)雁冰(茅盾):《创作的前途》,《小说月报》1921年第7期。可见,“五四”新文学家有更强烈的新旧时间意识。
颓废的现实不可能给“五四”知识分子提供晚清小说那种走向富强的“乌托邦”想象力,因为“五四”新文学家对于辛亥革命后建立的民国是悲观失望的。“五四”小说也用新旧时间来结构小说的,写法却不同。晚清政治小说家对未来是乐观的,“五四”新文学家却是悲观、犹疑不定的。“五四”新文化中的“感情的成分多于思想的成分。其中还伴随着夸张和混乱,未能消化掉的智慧与荒谬的杂合,等等。一切都告诉我们,这场运动的开始阶段是太急功近利了。”(52)[美]维拉·施瓦支:《中国的启蒙运动——知识分子与五四遗产》,李国英等译,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第10页。另外,新文学家们对“五四”新文化思想遗产的接纳需要一个吸纳的过程。所以冰心小说在预设的新旧叙事框架中装上的却是很旧的理想;庐隐小说在新旧现实的矛盾中宣泻纷乱复杂的情感;凌叔华小说在“新”“旧”之间摇摆,不再有“新”与“旧”的对立,而是半“新”半“旧”间的尴尬与难堪。
“五四”新文学家在新旧之间摇摆,他们也喜欢写梦,写“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彷徨”与沮丧。鲁迅《在酒楼上》写“五四”梦醒、梦破。在小说中,吕纬甫的过去找不到了,未来也不知道在哪里?吕纬甫说:“以后?——我不知道……现在什么也不知道,连明天怎样也不知道……”吕纬甫的“现在”是毫无意义的时间向度,承担不了“中间物”新旧转换的作用。李欧梵说“现在”“是不稳定的”,它“因叙事结束而消失,它并没有隐含向将来前瞻的意义。”(53)李欧梵:《现代性的追求》,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0年,第147页。由此,梦醒后的吕纬甫的过去、现在与未来是断裂的,也就是新旧时间之间是断裂的,因此吕纬甫不能在新旧转换中完成自我成长,只有在梦中死亡。其他小说《白光》《伤逝》《孤独者》等作品也都揭示了“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时间主题。
郭沫若和郁达夫等创造社同人也写“梦醒之后无路可走”这个时代主题。郭沫若的小说《残春》借用意识手法编织了主人公爱牟、S小姐相会的梦境。“梦”是小说的线索,展现了人物在现实生活中觉醒而又“无路可走”,便在梦境中获得里比多的满足。在小说《南迁》中,伊人的梦境中出现两个女人,代表了灵与肉的冲突,以梦境的形式表现了封建专制对青年人的迫害。“五四”青年无法获得自由,只有在梦中追求一种精神的慰籍,但梦醒之后更加失落。在这一主题上,郁达夫的《沉沦》更能够表现人醒后在现实压迫下的虚无感,也是觉醒后“零余者”的沉沦。所以说,梦醒后的“五四”青年无法进入新的历史时间。
概而言之,在新旧时间的转换中,鲁迅等创作“五四”小说的人物大都处在“梦醒之后无路可走”的时间困境。只有到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左翼革命小说《少年漂泊者》《流亡》等作品才把进化论的时间叙事结构补全,小说人物才有新的时间方向——革命。如左翼作家叶紫1936年发表的《星》中,主人公梅春经历了大革命失败、情人被杀、孩子夭折等种种不幸,最终离家出走,向着北斗星指引的“那里明天就有太阳”的东方走去,走向光明,走向了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