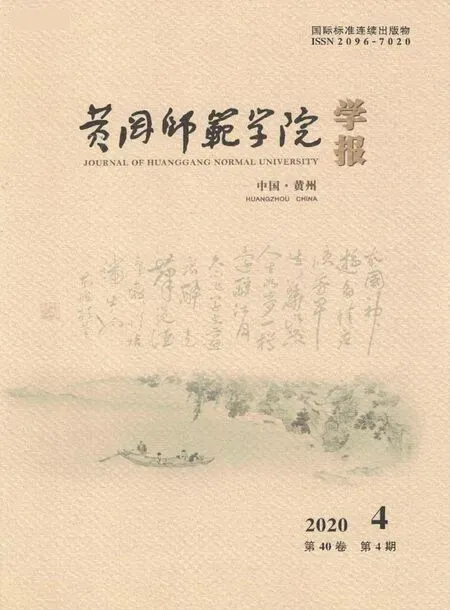1990年代以来小说价值论研究
周新民
(华中科技大学 人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1990年代初期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确立,此后,中国社会生活面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随之,小说理论所关注的话题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小说理论不再聚焦小说的现实功利价值、审美价值。通过梳理1990年代以来小说理论的变迁过程,我们可以发现,告别形式实验转而关注伦理问题、对普通大众的真切关注和召唤小说的道德价值,成为小说理论最为关注的理论命题。小说理论的上述变化,为中国当代小说理论的价值论注入了崭新的内涵。本文拟对此做一些探讨。
肇始:告别虚伪的形式
1980年年代中期,先锋小说实验开始批评家和小说家关注的核心。作为一种完全不同于现实主义小说的小说形态,先锋小说推崇小说形式的探索。小说形式也随之成为小说家和批评家所关注重要内容。但是,把小说形式推为小说全部的小说形式本体论潮流,也遭受到质疑。早在先锋小说风头正健的1988年,叶兆言就已经开始反思中国的先锋小说创作:“我们已经陷入了小说实验室的囹圄,面对灿烂的世界文学之林,小说家惭愧而且手足无措。新的配方也许永远诞生不了。文学的选择实在艰难,大家在实验室里瞎忙一气。不是抱残守缺,便是靠贩卖文学最新的国际流行色”,“小说的实验室很可能就是小说最后的坟墓。障碍重重,左右为难,除了实验的尝试和尝试的实验,小说家很难创造出自身以外的任何新鲜事。”[1]除此之外,先锋小说家马原的反思也极其深刻。马原被称之为最有代表性的先锋小说家,他的小说实验之路,是在小说家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芙等影响下开展的。事实上,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芙等被先锋小说家尊称为教父。不过,进入到1990年代后,马原对“教父们”不再毕恭毕敬,言辞之中多有嘲弄:“小说变成了一种叫人云里雾里的东西,玄深莫测,不知所以,一批创造了这种文字的人成了小说大师 ,被整个世界的小说家尊为圣贤。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芙,乌纳穆诺,莫名其妙。”[2]405马原对乔伊斯、普鲁斯特、伍尔芙等“嘲弄”,动摇了1980年代中国小说实验的根基。不仅如此,马原还彻底否定了小说实验的价值和意义:“以为精神分析学是向前进了,以为打破时空观念是向前进了,以为采用意识流手法是向前进了。结果呢? 小说成了需要连篇累牍的注释的著述,需要开设专门学科由专家学者们组成班子研究讲授,小说家本人则成了玄学家,成了要人膜拜的偶像。”[2]405马原的反思不可谓不彻底。马原和叶兆言、余华等一道,开始了反思先锋小说创作。这些先锋小说家的反思,拉开了中国小说理论转向的序幕。叶兆言、马原代表了1980年代末期先锋小说理论的反思,也代表了一种小说理论的萌芽。它意味着小说不能再一味地在形式实验上兜圈子,应该有所调整。事实上,在1990代初期开始,先锋小说家要么如叶兆言、余华、苏童,开始走上了否定先前小说实验,走上了“先锋小说”转向的创作道路;要么如马原、洪峰,在小说创作道路上沉寂了。除了这些处于小说创作风头的小说家,日后在中国小说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小说家们,也开始走上了小说观念转折之路。
1990年代初期,中国发生了一场关于人文精神的大讨论,让中国小说理论的价值之维推向了伦理价值的建构上。这场讨论有着深厚的社会现实背景。1990年代初期,中国文学面临的社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让中国作家一度无所适从,文学创作乱象环生。基于对文学出现的崭新状况,一些批评家提出自己的看法。这其中由王晓明、张宏、徐麟、张柠、崔宜明的对话《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的影响最大。王晓明等认为,“今天,文学的危机已经非常明显,文学杂志纷纷转向,新作品的质量普遍下降,有鉴赏力的读者日益减少,作家和批评家当中发现自己选错了行当,于是踊跃’下海’的人,倒越来越多。”[3]由《旷野上的废墟———文学和人文精神的危机》引发的这场关乎到中国文学价值的讨论,被称之为“人文精神大讨论”。中国当时重要的小说家,如王蒙、王朔、史铁生、张承志、张炜等,都有参与过“人文精神大讨论”。尤其是张承志、张炜的一些观点,成为其时颇具影响力。他们的观点从一个角度展示了中国小说家的精神追求,显示了中国当代小说抵抗市场经济的努力,也是中国当代小说试图建构精神价值的一次尝试。张承志在市场经济时代的文学潮流中做出了自己的选择:“我不愿无视文化的低潮和堕落。我只是一个流行时代的异端,我不爱随波逐流。哪怕他们炮制一亿种文学,我也只相信这种文学的意味。这种文学……它具有的,是信仰。”[4]张炜认为“文学已经进入了普遍的操作和制作状态,一会儿筐满仓盈,就是不包含一滴血泪心计。完全地专业化了,匠人成了榜样,连血气方刚的少年也有滋有味地咀嚼起酸腐。在这种状态下精神必然枯萎,它的制品——垃圾——包装得再好也仍然只是垃圾。”因此,张炜呼唤作家起来抵抗,“诗人为什么不愤怒? 你还要忍耐多久? 快放开喉咙,快领受原本属于你的那一份光荣! 你害怕了吗? 你既然不怕牺牲,又怎么能怕殉道?我不单痴迷于你的吟哦,我还要和你同行!”[5]
先锋小说非常看重形式创新,但是不免过于强调小说形式,极端者甚至视作小说艺术的唯一标准,由此而产生了“小叙事 ”、“形式至上”等艺术哲学[6]。社会的发展,贫富悬殊的客观存在,让有良知的小说家,不能闭上双眼。他们从社会精神现状出发,发出了针砭时弊的呼声:“穷人在如今依然是一个庞大的、触目惊心的群体。我认为,怜悯,仍然是作家的美德之一。……总会有一些作家,自觉或不自觉地承担着某一部分平衡我们时代精神走向的责任,并且努力弥合和修复我们社会的裂痕,唤醒我们的良知和同情心,难道这有什么错吗?”[7]
由此可见, 小说创作的焦点首先是对人类灵魂的关注:“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必须以笔为家面对遍地流浪的世界,用自己的良知去营造那笔尖大小的精神家园,为那一个个无家可归的灵魂开拓出一片栖息地,提供一双安抚的手。”[8]作家谈歌也意识到,小说创作不能忽视现实社会生活中的种种乱象,作家必须担负起责任来:近些年来,当男男女女都跌入了气功的陷阱,我们又看到了什么呢? 光芒万丈的当代中国,集儒、道、释与当代最新科学技第4期周新民:1990年代以来小说价值论研究术于一身的气功大师们横空出世,给中国人注入了鲜活的丹田之气,心灵果真是繁荣了嘛? 气功果真是万能的嘛? 它如果真将宗教、艺术、科学、饮食男女统统升华到一个极乐的神秘境界了嘛?
如果真是如此,那么我们跨世纪之后,我们老去的是民族的心脏,长存的是那副不老的皮囊。但愿这不是一句谶言。[9]
告别形式实验,承担社会责任,聚焦社会精神状态成为1990年代以来小说理论的重要命题。小说理论转折已经发生,中国当代小说理论即将迎来崭新的一页。
延展:关注普通大众
告别形式实验,小说家和批评家把目光聚聚在普通劳动者的现实生活状况上来。从1990年代中期的“现实主义冲击波”,到新世纪的底层写作,中国小说自始至终贯穿着一条红线:关注普通劳动群众的切身利益,关心普通劳动者的疾苦。这些小说在艺术形式上的成就可能不是太大,在生活描写的深度上可能不是太令人满意,在意识到的历史内容的发掘上,也许还达不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提出来的高度。但是,有一点是值得肯定的,这些作家在创作态度上是虔诚的,他们的作品从情感上的确能打动人。总体上看来,刘醒龙、关仁山、何申、谈歌这些作家“决不游戏生活,决不草率轻狂地玩弄艺术,无意奢求脱离生活背叛现实的自以为是的个人价值与自我,而只是甘愿做芸芸众生中的一员,与他们休戚与共、为他们代言。”[10]对大众的命运的关切让小说家们自觉地以人道主义的视野来关注中国社会发展,“我觉得现实生活本身就鲜活、复杂、立体、深刻。文学不应该是一曲颂歌,文学的内涵应该是广博的。小说应该背负这沉重,表达善意的人间情怀个人情怀人道主义内容,对社群祈愿、期待与寓言”[11]。在小说家看来,众多的普通劳动者是我们共同家园里的平等一份子。关仁山小说集《大雪无乡》后记中写到:“在我们国家,普普通通的劳动者是社会发展的主体,在这个主体中,最多的还是八亿农民。作为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文学,理应关注和表现这些底层的老百姓生活。”[12]把普通劳动者看作是我们共同家园的一份子,关心他们,为他们的权益鼓呼,为他们的命运而焦虑。这种人道主义情怀构成了“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的一个共同的价值立场:“工人农民不比我们,他们现在干得很累。我们应该把小说的聚焦对向他们。……我觉得这应该是我的使命。”[13]
1990年代的刘醒龙、关仁山这些小说家们自觉地坚持人道主义①价值立场,继承了自五四时期中国现实主义的人道主义传统。应该说,五四时期中国现实主义之所以产生,其主要原因是中国作家的人道主义精神的觉醒。先哲们意识到中国积贫积弱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国民众得不到关注,劳苦大众的利益得不到有效的保障。如何叙述一个中国老百姓真实的生活现状,构成了五四文学一个重要的目标,为此,人道主义立场产生。同样,在中国改革开放之交,人道主义仍然是中国小说的内在的价值标准。无论是对旧有生活的否定,还是对新生活的向往还是追求,无不是建立在人道主义立场上的,以至于有论者把新时期之初的文学潮流看作是人道主义文学潮流。只是到了1980年代中期,中国小说过于追捧西方文学,陷入到现代派文学实验的陷阱过深,小说才开始成为精英话语。普通大众的声音,人道主义情怀才再次被中断。一直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潮流再次兴起,人道主义才再次成为重要的价值标准。
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发展和市场经济持续推进,中国社会各个阶层均衡的发展局面开始瓦解。中国社会发展不平衡的现象呈现出愈演愈烈的局面。加之社会变革速度加快,一些社会群体难免出现不适应日益发展迅速的社会,于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一个具有相当规模的弱势群体开始在我们的社会中形成,他们主要由以下几个部分构成:贫困的农民,进城的农民工;城市中以下岗工人为主体的贫困阶层。”[14]这些贫困阶层的出现,使中国小说家面临着崭新的书写领域,不得不再次调整价值立场。随着作家的价值立场的转变,底层小说应运而生:“底层小说其实是从2004年才开始讨论的一种文学现象。最早是在《天涯》杂志上发表过关于‘底层与底层的表述’这样一组文章,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从《那儿》开始之后,然后《天涯》杂志,后来的《上海文学》、《小说选刊》、《北京文学》,文学刊物不断地参与到讨论中来,还有文艺理论刊物,像《文学评论》、《文艺理论与批评》,全国最重要的一些理论和文学刊物都在关注这个话题。”[15]底层小说关注的是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处于弱势的群体。面对着这样一群弱势群体,作家的担当自然显得特别重要。中国小说历经“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洗礼,已经在表现社会民众生存取得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因此,面对弱势群体之时,小说家已经获得了相当的表现能力。尤其在小说的价值上,已经开始自觉地维护底层民众的利益,自觉地充当底层民众的代言人。曹征路、陈应松、刘庆邦、刘继明等小说家,抱着维护弱势群体利益的态度,表现出了对于社会公平、正义的热切呼吁。底层小说正是在这个逻辑基础上出现的:“我们今天为什么要重新叙述底层,是为了唤起道德的同情和怜悯? 当然不是。是为了重新接续某种‘苦难’叙事? 也不完全是……就我个人而言,在非文学的意义上,重新叙述底层,只是为了确立一种公正、平等和正义的社会原则。”[16]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最初所倡导的现实主义理论,其现实主义规范就是从倡导公平与正义的角度确立的。同样,像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等现实主义经典作家,也是从呼喊社会公平与正义的角度来批判资本主义的罪恶。这一套思想体系,后来被命名为人道主义。事实上,陈应松的《马嘶岭血案》(《人民文学》2004年第3期)、刘庆邦的《卧底》(《十月》2005年第1期)、胡学文的《命案高悬》(《当代》2006年第3期),都堪称这方面的优秀作品。这说明,人道主义———这种被认为早已“过时”的价值系统仍然是中国作家最普遍也最深厚的精神资源,虽然以之面对今天中国复杂的社会现状,必然又一些难以解决的问题,但文学的任务毕竟不是“找出路”、“给说法”,而是写伤痛。在这个意义上,这种产生与欧洲资本主义初期的价值立场在中国的当下乃至以后相当长一短时间内都仍然有着很大的发挥空间。[17]
人道主义是小说家们面对社会弱势群体时所持有的基本价值立场,也是中国小说所追求的社会价值的重要体现。值得注意的是,中国改革历史进程中出现了相对弱势的老百姓。可贵的是,作家不是居高临下地面对社会普通民众。一方面,作家以人道主义的立场来关注社会普通民众,关心弱势群体的利益;另一方面,作家们也从社会民众包括底层民众那里也得到了灵魂的深化,从这些在历史变革时代大潮里普通民众命运那里,受到了心灵的洗礼和灵魂的净化。
普通民众之所以能产生出值得称道的精神品格,和特殊的历史情形分不开。“在物质利益膨胀的时候,我们这个家的每个成员,如何搀扶、体贴、鼓励度过眼前的难关,这个过程,是人民群众的伟大实践,劳动人民高贵的精神品格,推动历史前进。”[18]关仁山道出了在历史转型时期中国民众的精神格局、精神气度,这是作家在社会实践中所受到的活生生的教育。面对着艰难的生活,面对着从艰难生活中升华出来的优秀品质,作家能不动心么? 能不把笔触对准这这些普通民众么? 正如关仁山所说,历史变革,无形之中激发了中国民众优秀品质:“农村改革大潮大大解放了生产力,同时也带来各种问题。乡村的淳朴、坚韧和荣光,充满着悲怆的情调,但是人与土地的美质熠熠生辉。”[19]与关仁山一样,刘醒龙也把关注历史变革时期百姓所表现出来的精神品格作为书写的重点内容。刘醒龙的小说《分享艰难》是一篇被称之为“现实主义冲击波”的代表性作品。这篇小说也引起了比较大的争议。其中一位代表性的观点是认为《分享艰难》代表了“现实主义冲击波”这一类现实主义小说典型地缺乏人文关怀,是价值混乱的一种表现,是“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呈现高度紧张与冲突情况下,以责任伦理为重,而抑制自己的信念伦理。说得更直白一些就是:昧著良心(可憎)不择手段(可怕)发展所谓‘经济’。虽然小说也表现了他们这样做的时候内心的某种暂时的 ‘痛苦’,但他们必须、也只能‘分享艰难’。”[20]对《分享艰难》的批评的对错,暂时可以不论。但是,这种批评性意见源于所秉持的价值观是启蒙思想。然而,对于刘醒龙等小说家来说,作家和民众的关系不再是启蒙与被启蒙的关系,相反,在普通民众身上有着太多值得礼赞的精神、品格。对于为何倡导“分享艰难”,刘醒龙坦陈:“分享幸福是一种善,它昭示作为人的无私,而分享艰难则是一种大善,它是生命中的理想和爱、宽广与容纳,任何一种有关人与社会的进步,其过程必定少不了艰难的分享。”[21]显然,刘醒龙着眼的是这个时代人的优良精神,他发现了普通人身上的优秀品质,而不是一味地居高临下,以启蒙的态度来评判普通人身上的劣根性。刘醒龙要表现的是普通民众身上的“优根性”。他认为,优根性才是中华民族延续绵长历史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愿意为此去表现,去发掘:“人在社会中需要的更多是崇高与善良,没有谁是天生为了恶才来到这个世界的。‘现实主义’的精神之力正是取之于这一点,相对于劣根性,优根性是个客观存在。”[22]
与刘醒龙一样,很多作家着力去表现在历史变动中的普通人的高贵品质。“当前现实主义文学对历史的进步和道德进步的统一的执着追求,深刻表现在他对深重生活的一切有价值、有生命力的东西的开掘上。尤其是它在最底层的小人物中开掘真善美,这无疑是接过了19世纪俄国现实主义文学的精神火种。”[23]在民众身上开掘真善美,应该是“现实主义冲击波”的最为重要的特质。
自1990年代以来,从 “现实主义冲击波”到“底层叙事”代表了中国文学的一股流脉,它显示中国小说在叙述价值上的一种坚守。现实主义作为一种文学精神,是中国作家对中国社会发展的一种关注,也是在现代化日益迅猛发展的今天,中国作家寻找民族精神的一种重要的方式。
深化:建构道德修辞
小说家的理论倡导和创作实践,丰富了小说建构资源。以李建军为代表的小小说理论家,开始吸收1990年代小说创作实践和理论成果,建构了小说修辞学。
进入20世纪后,小说更是散发出迷人的光辉,继续影响了人们的精神生活。小说是在现代社会开始发挥出巨大的影响力,虽然小说的源头可以追溯到比较久远的历史。因此,在一定意义上说,小说这一文体属于现代社会的。不仅在现代社会形成之初,涌现了巴尔扎克、司汤达、托尔斯泰等小说巨匠,在现代社会深入发展的 21 世纪,小说仍然繁荣与发展,福克纳、普鲁斯特、陀思妥耶夫斯基等现代小说家,得到了各国作家的追捧。小说在现代社会发展有其内在的原因。其中最为根本性的原因和小说的文体特征分不开。现代社会的形成是和传统社会价值观的崩溃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现代人的物质世界极大丰富,而精神世界相对荒芜,寄情于小说,在小说徐徐展开的丰富世界里寻找精神寄托,是读者喜欢小说最为重要的原因。“小说也许是与伦理道德问题联系最紧密、最广泛的文学样式了……小说所叙之事,往往是处于特定的伦理关系和道德情境之中的人的‘事’,而这些‘事’里不仅包含着小说中人物的道德反映,也反映着作家的道德态度和道德立场。”[24]311现代社会物质的高度发展,也必然引起了传统价值观与伦理道德的变化,为作家提供丰富的能量。小说家根治于社会变化,写出了在现代社会人心、人性的变化,小说这种文体,为小说家提供了便利。
因此,在李建军看来,小说这一文体的本质规定特征就是“与伦理道德问题联系最紧密”。那么,小说修辞的本质也就天然“与伦理道德问题联系最紧密”,超出了简单的技巧层面的内涵,因为“修辞并不只是一个简单的技巧问题。根本上讲,修辞问题乃是一个意义问题,它决定于作者的价值观和世界观。”[24]334因而,我们便可以明白,李建军所建立的小说修辞理论系统的支点是“伦理道德”。“伦理道德”也因此成了李建军构建小说修辞的基本出发点。
首先,李建军找回了小说创作的主体,且给主体赋予必要的思想立场。他说:“一个没有深刻‘观点’的作家,一个没有成熟的世界观的作家,是不可能深刻地认识生活、了解人的内心世界的。”[24]335-336在李建军看来,无论形式主义怎么排斥作者,甚至宣扬“作者之死”,但是,无可否认的是,主体是小说价值的根本源泉。基于这种考虑,李建军提出了创作主体必须要有成熟的世界观。以此为标准,李建军对于1990年代风靡一时的《废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废都》是一部大胆的小说,但也是一部失败的小说,它赋予颓废、堕落以感伤的诗意和风流名士的浪漫情调,却没有真实地写出来中国作家内心深处的困惑、焦虑、无奈甚至绝望,没有真实地写出他们与自我、与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和冲突,没有为人们了解和认识特殊时期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存状态提供可靠的信息。”[24]372
召唤回作家,强调了作家的伦理道德对于小说创作的重要性之后,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的各个层面上,围绕小说如何贯彻道德立场做出了有效的理论构建。李建军在召回创作主体之后,进一步对于形式主义文论所倚重的隐含作者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形式主义文论为了建构一套规避创作主体的理论体系,不承认主体的作用,认为小说并非是由作家创作的,而是由隐含作者创作的。隐含作者向叙述者发出指令,叙述者创造了小说文本。同时,小说叙述创作了一个和创作主体不相关的叙述者、隐含作者。对此,李建军并不认可,他认为,隐含作者是“真实作者在小说中表现出来的自我形象的一部分”[24]41。李建军之所以提出隐含作者是主体的“自我形象”这一论断,是为了让创作主体的思想、道德、精神、信仰成为关注小说文本的源头,从而树立起小说是道德与信仰的旗帜的理论主张。
关于作者和人物的关系,有两种理论观点,一种是布斯所代表的,强调主体的绝对重要价值,把小说人物也看作是主体主宰的对象,人物是作者主体价值的体现。另外一种观点是巴赫金所倡导的对话性关系,把人物看作和作者平等的对话关系。不过,李建军认为,巴赫金的理论观点有些陷入到相对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桎梏。相反,布斯的观点更加切合创作实际。他认为,只有通过作者的修辞性介入,也就是说,只有作者通过各种修辞方式,把自己的思想、情感、道德投射到人物身上时,各具个性和思想特色的人物才具有意义和价值,小说浑然天成的思想境界才能形成,读者才能从人物身上受到教益。
至于距离在小说修辞中所体现的道德、价值立场就更明显了。他发现“现代小说的一个突出倾向就是摒弃‘思想’因素,而侧重于对对象的近距离的直接描写。他们倾向于追求形象化展示所带来的直接而真实的印象和戏剧化效果,强调缩短读者于人物等形式因素的距离”[24]134。李建军注意到,作者的信念、道德、思想、情感,决定了小说距离的远近的控制:
问题在于,即使我们把文学当作文学来欣赏而不是当作宣传来欣赏,也必然会涉及信念问题,而且我们对这个问题的回答是不可避免的。一个人“此前或此后”读过同一部小说,当他抛弃了小说的观念之时,不论是关于宗教还是党派,抑或是对于进步、虚无主义、存在主义或其他什么主义的信仰,他会发现小说的表现力量丧失了。这时他就会了解,即使我们对纯智力的信念,也不可避免地影响我们的文学反应。[25]
调控距离的方法大概有场景描写和概括讲述两种。场景描写给人身临其境的感觉,给人的距离远;而概述则给读者的距离近,便于赋予意义。优秀的小说需要在场景描写和概述的有机处理上,体现自己的价值立场与伦理态度。
至于宏观修辞讲述与展示,无疑也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伦理立场。讲述体现的是作者的价值立场,展示则是客观地展现社会生活。小说既不能完全彻头彻尾地自然展现社会生活,也不能从头至尾体现自己的价值立场。李建军认为,小说的艺术是如何调配展示和讲述之间的关系,而不是一味地宣扬展示的价值,让小说陷入一堆没有精神的物质之阵中。
微观修辞层面李建军比较看重反讽、象征的修辞效果。反讽被看作是小说修辞中不可或缺的修辞技巧,他被看作是小说意义形成的不可或缺的因素。反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反讽“可以避免作者以过于武断、直接的方式,把自己的态度和观点强加给读者,而是以一种曲径通幽、暗香浮动的方式,更为智慧、更有诗意地将作者的态度隐含于曲折的陈述中,让读者自己心领神会”[24]217。在李建军看来,象征是现代小说最为常用的修辞方式。它是作者直接性介入被取消后最为重要最有价值的修辞方式。因此,在李建军眼里,象征是作者价值立场、道德、信仰表达的一种非常有效的方式。
李建军在小说修辞的各个关系层次———作者与读者、作者与人物、作者与隐含作者等———上,在小说的宏观修辞和微观修辞层面上,都围绕建立理想的道德效果来展开。判断小说的价修辞标准是,除了给人带来消遣快感之外,小说必须“带来道德上的升华和伦理上的净化体验”[24]315。李建军提出这样的一个价值标准,显然是有针对性的。中国当代小说在发展过程中,日渐陷入到“美”的桎梏。其表现有二。其一是追求所谓的人性复杂性、人性的深度,从而放弃了应该有的道德基准。小说打着“化丑为美”的旗号,陷入到写丑的狂欢之中。一些在道德上低劣、甚至恶心的内容,被升华为艺术美,堂而皇之地进入到小说的表现领域。阅读这些作品,自然无法得到灵魂上的净化与道德的升华。其二是宣扬所谓的 “纯文学”。所谓的“纯文学”,是把“为艺术而艺术”作为文学创作的指南,沉溺于小说创作的形式实验之中,在所谓“叙述圈套”中彰显小说的艺术价值。这样的不及物的写作,成为先锋文学的圭臬。李建军的小说修辞围绕小说要提升的道德境界这样一个终极目的,建立起来的小说理论系统无疑具有极其重要的历史价值。
自1990年代开始,中国小说理论在小说价值论上的探究,是以张扬伦理精神为核心的。当代小说理论发展过程中,一度偏执地建立现实功利价值,在小说的反映现实的历史深度上深入开掘。而到了1980年代小说理论在小说的审美价值上,开始了深入的探索。而进入到1990年代以后,当代小说理论进入到了开掘小说的伦理价值的历史阶段。小说伦理价值的探求,丰富和发展了中国当代小说的价值理论,体现了重要的理论价值和意义。
注释:
①人道主义在不同的语境里含义各有侧重。这里所谈的人道主义所取的含义是对人的尊重与关怀的价值尺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