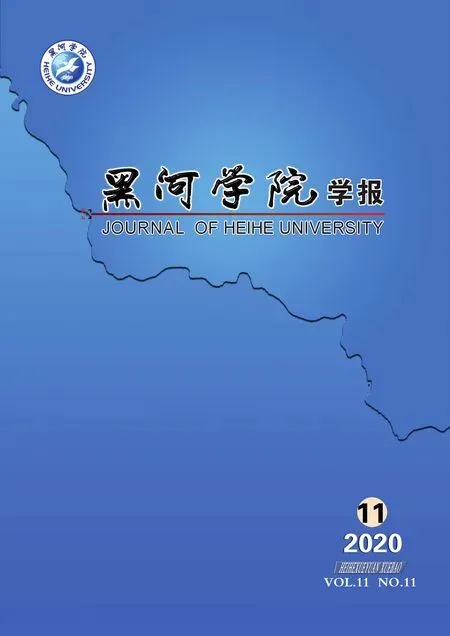从 “天使” 到 “魔鬼”:荒岛文学中女性形象的蜕变
——析《鲁滨逊漂流记》和《蝇王》中的女性形象
李向云
(四川大学 外国语学院,四川 成都 610225)
荒岛文学主要是讲述荒岛生活的一种文学。以荒凉,偏僻,未开发为主要特点的荒岛往往是故事设置的主要地点,主人公在岛上历险构成荒岛文学故事的主线。英国岛屿众多的地理特征及对外征服的历史,使荒岛文学成为英国文学的传统。而女性主体的缺失又构成了荒岛文学的一大特色和传统。尽管女性主体缺失,但作者却通过其他母性意象传达了对女性的态度和当时社会中女性的地位。《鲁滨逊漂流记》讲述了鲁滨逊遭遇船难,在荒岛漂流的过程中建立一个海外帝国的故事,探讨了18世纪英国新型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社会风貌。《蝇王》讲述的是一群孩子遭遇机难,流落荒岛求生的故事,探讨了人性在缺乏监督时的本质。两篇小说自问世以来,就引起不小轰动,受到国内外批评家的广泛关注,并从历史、社会背景、心理、基督文化及男性沙文主义等方面对作品进行了解读。也有批评家对女性的缺失作了分析,认为这是男权话语体系下,女性命运的写照,男权社会通过对女性的压制来实现自己的权利。本文通过对荒岛文学传统的剖析和女性形象的解读,阐释女性角色从 “天使” 到 “魔鬼” 的蜕变之路及其原因。
一、女性主体的缺失与污化——荒岛文学的传统
荒岛母题一直伴随着英国文学的发展,各个时期都用自己的方式书写荒岛小说。英国独特的地理特征和海外扩张是造成这种传统的原因。英国地处大西洋海岸的东北部,由众多岛屿构成,据统计,在英国有近920个岛屿。因此,岛屿的概念深深影响了人们,包括作家群体,其生于岛屿,育于岛屿,悟于岛屿,自然对岛屿有着更深地的见解和情感。因为 “从他出生之日起,他生活于其中的风俗就在塑造着他的经验和行为,而当他长大成人并能参与这种文化活动时,其文化习惯就是他的文化习惯,其文化信仰就是他的文化信仰”[1]。由此岛屿文化促成了英国海洋文化的兴盛,进而文学不可避免地与航海、海盗、海船、海上战争、海外贸易海外扩张和殖民贸易等相关[2]。而这些要素也构成了荒岛小说的素材库,也是直接导致女性缺席荒岛小说的客观原因。女性由于身体特征,力量问题,缺席与以探险为主的荒岛小说中,似乎合乎常理。
此外,荒岛小说中,女性主体向来都是缺失的,即使有部分女性形象出现,作者不是以寥寥数语带过,就是把女性刻画成为思想狭隘,没有主见,依附于男权社会的群体。在《鲁滨逊漂流记》中,鲁滨逊建立海外帝国的生涯中,没有一个女性参与,文中涉及到的女性有其母亲以及在逃亡中救了其性命的土著女性。在笛福笔下,鲁滨逊的母亲是个言听计从,依赖于丈夫,连儿子的秘密都无法保守的女性;而土著女人只是理所应当提供服务的路人。在《格列佛游记》中,对性的讽刺更为裸露:格列弗结婚只是为了妻子的财产;当女王的皇宫着火时,他骄傲于用自己的小便轻而易举地解决了火灾,在斯威夫特笔下,女王也被看作是狭隘的女性。在《珊瑚岛》中,出现了温柔善良的土著女性,救了冒险的主人公。相比于之前的作品,女性的形象有所改变,但对其描写更多地突出服务性与依赖性,而土著女性的存在也是三个男孩荒岛生存能力的体现,这时候的女性仍然是无足轻重。在《蝇王》中,戈尔丁笔下女性的缺失走向了极端。女性的身影几乎没有,唯一一个被提到的是猪仔的姑妈,而姑妈的教育观念却遭到了大伙的反对,最终猪仔也死在了伙伴的残忍杀戮下。
因此,纵观整个荒岛文学,女性的主体地位是被有意遮盖的。在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中,其命运取决于男性。解构主义人物雅克·德里达认为:在传统的二元对立中,“在场” 与 “缺席” 其实是相对的[3]。也就是说,“在场” 和 “缺席” 其实是作为关系反义词而存在,他们必须处在一个相互关联的语境中,才会有所谓的 “在” 与 “不在”。因此,对于文中女性的 “缺失” 其实与男性的 “在场” 是二元对立的,也正是这种二元对立,使得读者意识到男权文化中女性的失语状态,更加强化了女性的存在状态。
二、女性形象的显性存在:“天使” 与 “魔鬼”
在《鲁滨逊漂流记》和《蝇王》中,女性并没有作为主体而出现,但这并不意味着女性在这两部作品中完全失语,相反,女性形象的动物代表了女性,传达了当时时代下的女性观及女性的社会地位。《鲁滨逊漂流记》中是一只被驯养在羊圈的母山羊;《蝇王》中是被孩子猎杀的母猪。这两个带有女性特征的动物,被赋予了和女性一样的命运。
《鲁滨逊漂流记》以荒岛冒险著称,所以,全文并没有女性参与到男性建立帝国的伟业之中。但读者不难发现书中对于女性意象的母山羊却有多次提及。在第十三章 “考察全岛” 中,鲁滨逊表明自己 “宁愿打只母山羊”;“长期以来,我一直想活捉一两只小山羊饲养,让他们成长繁衍为一个种群,以便火药和子弹耗尽后我仍然有鲜肉吃。”;“由于饥饿,它已经变得相当温驯,根本没必要栓住它,一路上像狗一样追随着我,……从那往后,它成了我饲养的家畜之一,而且从来不离我左右”。荒岛中的母山羊对于鲁滨逊而言,是女性的代表。从鲁滨逊对于母山羊的行为态度来看,可以看到女性所扮演的两种角色:“房屋中的天使” 和 “生产的工具”。
“房屋中的天使” 生性温驯、善良,对于男性的话语呈现服从态度,没有过多的激情与欲望,是男权社会下典型的女性角色。鲁滨逊所圈养的那只山羊也是如此,“温驯” 地尾随于主人之后,依赖于鲁滨逊的饲养,生活于鲁滨逊给其建立的栅栏中。寥寥数语,便描摹出一幅笛福时代女性的生活图景。很难说这只是一个简单的母山羊的生活图景,这似乎也影射出女性们的生活现状:安守于家庭便是一个值得称赞的女性。“生产的工具” 是这群 “天使” 存在的主要价值。缔结婚姻,只是“天使” 为传宗接代的一个契约任务,无关爱情。正如母山羊对鲁滨逊而言一样,可以繁衍,保证主人断粮时的温饱,除此以外,它都不是荒岛中的一个伴侣。在鲁滨逊的认知中,鹦鹉才是他的伴侣,而山羊似乎理所应当的提供其该有的价值。这又何尝不是当时女性的命运呢?
《蝇王》中女学童与母亲角色并没有按照读者的常规思维出现,只有被孩子追赶的那头母猪,是作者提到的唯一的女性意象。猪的意象在文中多次提及,每次出现都是以被追赶杀戮的,但戈尔丁总是以简单的描写带过。唯独对于母猪的残忍杀戮,作者花费笔墨来进行描写,其中包含着作者对于女性的态度。在《献给黑暗的礼物》这一个章节中,着重描写了对于母猪的猎杀。“离开猪群不远,躺着一只肥大的母猪,它沉浸于当妈妈的幸福之中。它的躯体,一半是黑色,一半是粉红色;它那鼓鼓囊囊的肚子旁边有一排小猪仔,有的仔睡觉,有的仔扒土,有的载吱吱叫”[4]148。这幸福的图景在孩子到来后便荡然无存了。读者再次听到的是母猪 “痉挛地尖叫”,此刻它的腹肚已经插入两根标枪,而猪仔死的死,伤的伤,四处逃窜,之前安逸的幸福之景已完全不复存在。而被命运选中的母猪,标枪的刺中只是悲惨命运的开始。一路逃窜,一路被追赶。
它 “经不起炎热的打击,在这里倒了下来。猎手们向它猛扑过去,……罗杰围着人群团团转,寻找空隙,一见猪就用标枪刺去。杰克压在母猪身上,刀子往下猛戳。罗杰找到一个下手的部位,使劲一桶,将全身压在标枪上。标枪步步深入,恐怖的尖叫变成了高声地嚎叫。随后,杰克刺中了喉咙,热血直喷出来,洒遍他的双手。母猪在他们身边瘫了下来。他们沉沉的压在它身上,感到心满意足[4]150。
母猪被杀,她的肉可以用来饱腹,她的血可以用来祭拜,驱赶森林中邪恶的魔鬼。读者在这里看到的母猪,不像鲁滨逊圈养起来的山羊那般温驯与服帖,相反,母猪生性狂野,顽强,不服从约束与管制,像极了 “阁楼上的疯女人”,热情、狂放、疯癫有着自己的想法。一路逃离,相要脱离男孩的追杀。她越是寻求独立,越刺激了男孩好胜的心。而在男权社会下,此类型的女性形象归属于 “魔鬼” 形象,在男性看来威胁着社会的发展。正如母猪一般,会威胁到岛上孩子的安危。男权社会对于女性的压制正如孩子们对母猪的杀戮,是一场没有同情与人性的压制。再也不是 “圈养+玉米” 可以哄好的女性了,惶恐与畏惧着的男性只能采取暴力压制。此外,母猪尽管是 “魔鬼”,但仍难逃 “生产工具” 的厄运。母猪旁边的猪仔,无不在提醒着女性,其职责与任务是生产。
波伏娃说,“一个女人之为女人,与其说是‘天生’ 的,不如说是‘形成’的”[5]23,在男性主导的社会下,女性命运和形象被男性牢牢掌握。被规训的天使和生产工具,无一不是来自男性社会对于女性的 “期待” 与塑造。因此,男性执笔的作品下,女性的形象是由男性所控制的,并通过男性表现出来。
三、女性形象的蜕变:从 “天使” 到 “魔鬼”
在《鲁滨逊漂流记》中,母山羊被刻画为 “天使” 一般的女性,是当时男权社会下标准的女性形象。圈在栅栏中的山羊就如同 “房间里的天使”,没有话语权,受到男性和社会的压制,依附于男性的权利。在鲁滨逊生活的荒岛,鲁滨逊用 “玉米+羊圈” 来对付所捕获的母山羊,这是富有征服欲和处于强势地位中男性所惯用的手法——刚柔并用。尽管鲁滨逊为母山羊提供了食物,但最终把它圈养在了羊圈。而且山羊的存在主要是为了解决鲁滨逊的温饱而存在的。在这个过程中,可以看出男性的霸权地位,而母山羊被赶入羊圈和最终被吃掉的命运意味着女性无法摆脱男性的控制。此外,山羊作为鲁滨逊的食物来源之一,其地位是可以被取代的,在鲁滨逊找到下一个代替品或食物充裕时,山羊是随时可以被丢弃的。正如笛福时代的女性,除了生育的责任以外,也是随时可以被男权社会抛弃。
而在《蝇王》中,作者刻画了一个野猪的形象。她具有慈母般的柔和,沉浸于初为人母的幸福之中。没有压制的母猪是安静和温和的。但当孩子的来临搅乱这一切时,她凌厉地喊声似乎在对压制进行控诉。即使被刺进木棍,她仍选择逃离。最终在猎手的 “合作” 之下,她被控制了。在这一过程中,猎手用 “假脸+刀+木棍+血祭” 最终制服了令其害怕的“魔鬼”。这个 “魔鬼” 有着自己的意志和求生欲,她不甘于被压制,尽一切可能进行反抗。在屠杀母猪的过程中,人们看到的是男性对于 “魔鬼” 的一种畏惧,再也没有了鲁滨逊控制山羊时的闲适淡然。而母猪似乎也并不是可以被取代的,因为她的肉可以用来饱腹,这也是男孩们最后分裂的最直接原因,而且母猪的血可以用来祭拜,从而驱赶岛上的魔鬼,使孩子处于安全之中。“魔鬼” 价值得到了孩子的关注和认可。正如戈尔丁作品末尾提到的那样:“即使孩子们在成年人的战争中再次幸免于难,但在一个没有女性无法繁衍后代的纯男性的世界里又能挣扎多久呢?” 这在一定程度上反应了女性存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一个理想的世界应该是男女和谐相处的世界。戈尔丁以此肯定了女性在社会中的价值。
《鲁滨逊漂流记》和《蝇王》中对于女性缺失的处理,显示出了两位作者对于不同时代女性的态度。笛福时代,女性集体处于 “沉默温驯” 的状态,是男性生存的有利工具,对于男性生活构不成威胁;而在戈尔丁生活的年代,女性不满于自己的待遇,对于权利的呼声高涨。戈尔丁陷入了对于女性认知的一种两难境地之中,并且认识到女性对于社会的重要作用,但是碍于男性执笔,又不愿意在文中赋予女性声音。这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体现出女性权利和地位的斗进化史。
四、女性形象变迁的 “孵化器”
笛福生活在17世纪末期至18世纪初期,其思想主要受启蒙运动的影响。启蒙运动中 “自由、平等、博爱” 的口号,强调民主和个人平等。在这场民主和人权平等的呼声下,女性的价值首次得到洗礼。伏尔泰(Voltaire)谴责女性命运的不公;孔多塞(Condorcet)强调男女教育平等从而实现性别平等;狄德罗(Diderot)更是把女性和男性放到同一位置上来讨论[2]。笛福自身也反对这种男尊女卑的思想,在其《评论报》创办的9年时间里,常常提到妇女的问题。认为妇女应该接受教育来摆脱目前的地位,强烈反对把女性作为性欲的对象,他哀叹法律对妇女婚后财产的不公正分配,她强调婚姻生活应以感情为基础。但新的思想仅局限于少数哲学家。大部分人仍认为女性是性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生养工具,属于男人的附属。“对于男人而言,女人在他们眼中,只是一个性感的动物,她就是性,其它什么也没有”[5]6。更为重要的是,笛福时代的女性,因为没有经济方面的独立性,其生存不得不依赖男性,所以,无论是在文学领域还是其他领域,都没有杰出的女性。虽然有相关女性压制意识的觉醒,但当事人却 “无能为力” 参与其中,所以,女性仍旧活在男权社会下。而笛福,除了是一个作家,还是一个商人,其写作的初衷也是为了求生。所以,作品先是满足商业价值,其次才是文学价值,女性自然而然成为了男性所期待的 “天使”。
相对于笛福,戈尔丁生活于20世纪,两次工业革命,战争、女权运动无一不是女性成长的 “孵化器”。两次工业革命的结果之一就是 “女人打进了工厂,成了生产的劳力”[5]12。此时,女性基本可以不依赖于男性而生存,认识到了自己的独立性与价值。此外,战争也加速了女性对于自己的认知。男性国外参战,而国内家庭事务及工厂生产便由女性负责,在这个过程中,女性的能力和独立性日益增长,加速了女性意识的觉醒及女权运动的兴起。在女权运动的影响下,在20世纪初女性相继在财产、选举等领域获得了平等权利,使女性在各方面获得了自信。同时,女性作家也侵入了向来由男性主导的文学领域,在其笔下,女性则是具备 “天使” 和 “魔鬼” 特性的新形象,这些女性形象纯洁美丽,洋溢着热情和勇气。女性的崛起,使得男性权威受到了挑战,这种挑战也体现在文学领域。这时的男性作家,笔下出现了受伤或是失势的无能男性形象,如《太阳照样升起》中的杰克;《阿尔弗雷德·普罗弗洛克的情歌》中的普罗弗洛克。这些男性形象由于受到 “新女性” 挑战和困扰,表现出精神上和心理上的忧虑。《蝇王》中女性的缺席,对于母猪的疯狂屠杀,同样也体现了男性在女性崛起时的焦虑。无疑,这也是戈尔丁在女性缺席时对人性自身及人类命运严肃思考后的反思。
五、结语
《鲁滨逊漂流记》和《蝇王》中,女性主体隐性缺失,而女性形象显性存在,巧妙地传达出当时的女性观以及女性地位。通过《鲁滨逊漂流记》,笛福时代的女性受独立性影响,不得不成为男性笔下的 “天使”;而《蝇王》中,戈尔丁笔下的女性追求独立,渴望自由,女性阶层的兴起使男性权威受到威胁,所以不得不成为男性笔下的 “魔鬼”。而20世纪女性笔下那些兼具 “天使” 与 “魔鬼” 特征的女性形象,无一不在传达着女性的意识的崛起及女性对自己价值的重新认知。而在当代思考男女社会性别时,更应该提倡:女性既不是 “天使”,也不是 “魔鬼”,是独特的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