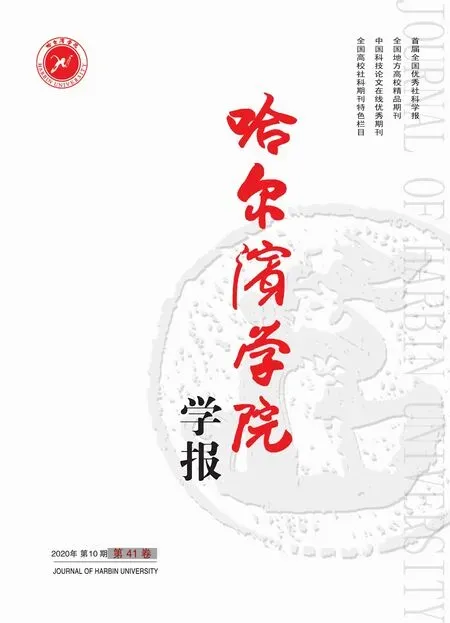辽代契丹族人的忠诚观念探究
徐世康
(上海师范大学 旅游学院,上海 200234)
通常来说,夷狄较之于诸夏,是野蛮而无礼的,如《论语·八佾》以为“夷狄之有君,不如诸夏之亡也”。[1](P2466)故而理论上,作为中国之人,绝不可能忠于由异族统治者建立的政权。不过,正如美国学者狄宇宙“所有关于‘道德的考量’与国家的‘理性选择’相比,都是居于第二位的”一语所言,[2](P147)从历史上看,中国之人效忠于异族统治者甚至帮助异族统治者“对付”同胞的事例屡见不鲜。如早在春秋时期,各诸侯国便已与夷狄政权建立了密切的联系,联合夷狄以进攻诸夏国家的事例并不罕见。因此,《论语·八佾》中的论述更多只是表达了一种理想化的状态。
公元10世纪前后,由于李唐王朝的灭亡,中国再次进入分裂时期,而这一时期内,除汉人势力之外,党项、女真、契丹等民族也相继建立了政权。本文正是以辽代契丹族人为对象,考察中国传统社会中忠诚观念对其人的影响。截至目前,学界对相关话题已有了一些论著,[3-4]但对于契丹本族人的忠诚观念研究仍显不足,故笔者不揣浅陋,将就这一问题展开分析和探索。
一、辽朝建立初年契丹族人的忠诚观念
早期的契丹社会中并无忠诚观念,如《资治通鉴》载开元间契丹王李过折被杀后,新国王涅礼在向唐廷上书中,毫不掩饰自己以“过折用刑残虐,众情不安”而将其杀之的行为。唐玄宗虽然默认此结果,但在致书新国王涅礼的书信中明确提出了“卿之蕃法多无义于君长,自昔如此,朕亦知之。然过折是卿之王,有恶辄杀之,为此王者,不亦难乎”的批评。[5](P6812-6813)从引文看,臣僚弑杀君主之事在契丹族人看来似乎并未引起多大反响,足见此时契丹人并无甚忠诚的观念。
阿保机建立政权后,辽代社会中的忠君观念亦较淡薄。从辽太祖即位后至辽穆宗遇害期间,内部叛乱时有发生,对于许多契丹族人而言,也并不了解阿保机即位称帝的真实含义,如耶律辖底谋反失败后,曾对阿保机明言:“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臣曾奏事心动,始有窥觎之意。度陛下英武,必不可取;诸弟懦弱,得则易图也。事若成,岂容诸弟乎。”[6](P1648)其中“始臣不知天子之贵,及陛下即位,卫从甚严,与凡庶不同”一句是问题的关键所在。此时作为皇帝的阿保机已经与以前世选时期的可汗有了根本区别,而思维依然停留在世选可汗时期的耶律辖底等人至此方认识到“皇帝”这一职位的与众不同,从而产生了觊觎之心。不过,从另一角度来看,阿保机称帝并改变以往的世选制度,也可视为是对传统的背叛,因而诸弟的行为也是一种对部落传统的“忠诚”。故而阿保机虽然明知其人“不忠”,对于参与叛乱的各方势力仍采取了较为宽大的措施。但需要指出的是,在辽代初年,也依然有一些大臣始终站在阿保机这边,保持对阿保机个人及其家族的“忠诚”。如耶律欲隐,其人曾受太祖之命,“典司近部,以遏诸族窥觊之想”,后在太祖“置宫分以自卫”时,又“率门客首附宫籍。帝益嘉其忠,诏以台押配享庙廷”。[6](P1352)另有耶律曷鲁,自小便与太祖交好,先后参与平定小黄室韦、讨越兀与乌古部、劝说奚部归降、征讨黑车子室韦、平定诸弟之乱等重大行动,并劝说太祖承继帝位等。[6](P1348)但总体上,遍检史籍,在辽代初年,此类“忠臣”并不多见。
二、辽朝契丹族人的“忠臣”理念
(一)以“忠”为谥
辽朝建立后,中原传统的忠诚观念开始逐渐为契丹统治者所接受,并在全国范围内推行,辽代赐予臣僚以“忠”为谥的做法,便是宣扬这一理念的行动之一。在唐代,那些谥号中带“忠”字者,一般会有军事上的功绩,而一个人在明知会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仍秉公执事也会被谥为“忠”,不过也有因为其他原因谥号为“忠”者,如忠孝楷模、不为人知的美德、拒绝侍奉他主等。[7](P69)有些人物即便没有在死后拥有“忠”为谥号,但其言行也被帝王称赞,认为其“忠”。唐代的这一惯例也为辽人沿袭,如从辽代的谥号中看,死后谥“忠诚”的耶律良,在听闻兴宗弟重元与涅鲁古意图谋反后,不顾自身安危,明言“臣若妄言,甘伏斧锧”,最终使兴宗躲过一劫。[6](P1539)而谥为“文忠”的耶律隆运,则主要表现为军功,如击败宋军的入侵及讨伐高丽等。[6](P1422-1423)一些契丹人虽然并无军功,但是长期担任武职,并坐镇地方,如耶律宗政,谥号“忠懿”,其人为景宗次子,生前曾坐镇平、滦、营等州,还担任过南院大王,执掌四十万兵马。[8](P306-307)而另一被谥为“忠懿”的是汉臣梁援,其人能得到这个谥号,最关键的事迹和其在耶律乙辛陷害太子时不畏强权、果断上书有关,即其墓志所载“值贼臣耶律英弼等。畏东宫之英断,肆巧言以构之。公欲冒死上奏,潜作二书,一以致父母,一以示子孙,用史馆印识之。遂奏状曰,皇太子年小,事理暗昧,不同凡庶,及陈故事,用启上心”。[8](P521)当时乙辛及其党羽权势熏天,梁援此奏可说是冒着极大风险,但其依然决定“秉公执法”,体现了“忠”的原则。
(二)忠诚表现
除谥号为“忠”外,史籍所见辽人的忠诚表现,则既有泛泛而谈其人尽忠于国,也有举出具体事例以表现其人忠诚的。前者如卫国王沙姑墓志载其先祖“蕴忠贞而匡佐□□,布恩威而励安士庶”;[8](P27)后者如耶律延宁墓志载其担任景宗近侍,“尽忠尽节,竭力竭身”,在景宗去世后,愿随从死,即位的圣宗以为“赤忠”。[8](P85)同样在圣宗朝参与东征高丽的耶律元宁,其墓志也载“公躬率锐旅,首为前锋,始遇敌于建安之南,贼卒向三千余众,猗角才□,剪戮殆尽。我一贾于余勇,□累公于降书。□为藩臣,永事天阙。故高丽岁时之贡,不绝于此,由公之力也”等。[9](P44)“拒绝侍奉他主”而被认为是忠诚的例子在辽代也可见,如圣宗朝只剌里奉使高丽,因为不屈而被扣留长达六年,表现出了对契丹王朝的绝对忠诚。[6](P209)
(三)忠诚与孝
忠与孝的冲突,是古代社会常见的现象,在二者发生冲突时,是否选择忠于国家是衡量一个人忠诚观的重要标准。那些能选择忠于国家者往往会在史籍中得到凸显,如《辽史》载令稳援里得之长子耶律海里在“察割之乱”时,他的母亲的鲁参与其中,并派人来召唤他一起作乱,但海里的反应却是选择忠于国家。正是这一正确的选择最终也救了其母亲的性命,“察割之乱”平定后,其母“以子故获免”。[6](P1443)
(四)敌方的“忠”
嘉奖或惩罚属于“敌方人物”的“忠”或“不忠”行为,也可视为是契丹人忠诚观念的体现。如后晋将领高行周、符彦卿曾经打败过辽太宗,但当其人在归降后,面对太宗的责难,以“臣当时惟知为晋主竭力,今日死生惟命”作答时,太宗只是“笑而释之”。[5](P9324)另如后晋将领宋彦筠,开运二年“从元帅杜公(即杜重威)拒戎王于滹川”,由于契丹势大,且“滹水泛溢,王师不得渡,粮运俱绝”,在作为元帅的杜重威投降后,宋彦筠“犹力战,戎王慕其忠节”等。[10](P612)有奖赏自然也有惩罚。在辽代初年,一些在中原王朝与契丹之间的投机者,其行为不但为中原王朝所不耻,亦为契丹人所鄙视,典型如阿保机妻述律后在接见反复无常的赵德钧父子时,当面数落其人曰:“……汝欲为天子,何不先击退吾儿,徐图亦未晚。汝为人臣,既负其主,不能击敌,又欲乘乱邀利,所为如此,何面目复求生乎?”德钧俛首不能对。[11](P184-185)
(五)“忠”与“不忠”
辽代还有一些被谥为“忠”者,则似乎并不那么忠诚,其中一位是谥号为“忠懿”的耶律俨。遍观其本人的列传,最值得称颂的唯有入宋调解宋夏纠纷与完成《皇朝实录》七十卷,这些均很难与“忠”挂钩。其之所以能得到“忠”的谥号,恐怕和其人“善伺人主意”,因而得到辽主宠信有关。[6](P1558)另一位死后被谥为“忠肃”的萧孝先,其人得谥的理由则更显离奇。从《辽史》看,其人先是参与了兴宗母萧耨斤谋害圣宗仁德皇后的行动,一度“权倾人主”,后又参与兴宗母萧耨斤意图以兴宗弟耶律重元取代兴宗为帝的谋反活动,所幸被兴宗以“先发制人”的手段终结,[6](P1468)可谓处处“不忠”。但若站在兴宗母萧耨斤的角度,则或可被认为是“忠诚”的,其能得到“忠肃”的谥号,当是出于兴宗与其母妥协的结果。
(六)忠诚标准
契丹人对于何为“忠臣”,也产生了自己的判断标准,如辽道宗曾谓大臣曰:“今之忠直,耶律玦、刘伸而已!”从两人的传记看,《辽史》认为刘伸的功绩在于“三为大理,民无冤抑;一登户部,上下兼裕”,还有面对奸臣耶律乙辛的擅权而毫不畏惧,同时在为民请命时,面对兴宗的忽视而敢于直言“臣闻自古帝王必重民命,愿陛下省臣之奏”。[6](P1559)似乎后两点更符合上文所说的“明知会身陷囹圄的情况下仍秉公执事”。另一臣僚耶律玦,重熙间入见太后时,太后曾言“先皇谓玦必为伟人,果然”,然而先皇在何种情况下说出这样的话语不得而知。从传记内容看,其本传中最为突出的事例为“岁中狱空者三”,但道宗却认为“然熟察之,玦优于伸”。[6](P1502)目前耶律玦的墓志已有发现,从已经释读的部分看,主要罗列墓主的祖先以及其为官历程。不过值得注意的是,其契丹小字墓志亦有意为“大家可汗子伟人善成为□郎君□谓”的类似记录,《辽史》本传“先皇谓玦必为伟人”应是出于此。[12](P22)
三、辽代末年契丹族人的忠诚选择
辽末,面对女真人的反叛,契丹族人的忠诚观念受到了空前的考验。与辽代初年是选择忠于部落传统还是忠于阿保机个人及其家族的不同,天祚帝时期,整个契丹族人面对的首要问题是选择忠于辽帝国,还是选择忠于女真人,或者趁机独立。同时在选择忠于辽帝国的人中,还要区别是忠于天祚帝本人,还是忠于契丹王朝的不同。
关于契丹何以灭亡,目前学者已经给出了较为详细的论述,归纳起来主要有享乐主义盛行、好逸恶劳、贪污腐败、贫富差距扩大、统治阶级矛盾激化、崇尚佛教、与北宋和女真的战争等。[13](P161)不过,考虑到天祚帝是辽代灭亡前的最高统治者,其个人的行为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整个帝国的命运,而天祚帝本人的性格与其童年的命运有很大的关系。在天祚帝出生后不到七个月,祖母萧观音便被权臣耶律乙辛诬陷与伶官赵惟一私通而被杀。此后不到两年,其父耶律浚与其母均被乙辛所害。虽然之后认识到问题严重性的辽道宗本人在大康六年封其为梁王并加以保护,但直到大康八年才诏“化哥傅导梁王延禧”。[6](P325)可以说,在八周岁之前,天祚帝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与教育,而这段时间正是幼儿智力、语言、情绪、人格与道德发展的关键时期。当代心理学研究也表明,幼儿如果没有得到合适的照料,便无法从成人的认同处取得安全感和安定感,也无法取得内心的充分自信。[14](P80)弗洛伊德认为,所谓儿童“纯洁的天性”实由学习而得,不然他们都会顺其自然地暴露自己的兽性,[15](P249)但“兽性”的具体表现并不一致。就天祚帝而言,选择“耽于田猎”或正是其选择满足“兽性”的一种方式。而从另一方面看,天祚朝的一些典型事件,如任用奸臣萧奉先、罢免耿直的萧兀纳与杀害其子晋王等,也与天祚帝的成长环境有关。对于前者,以往的研究将其归纳为用人不当,但对于为何会用人不当没有过多解释。一般而言“缺乏父母关爱的儿童会产生焦虑、自卑、耽于幻想,缺少安全感和对挫折的耐受力”,[14](P88)而对于作为君主的天祚帝来说,则表现为对一些直言劝谏的言行感到反感,因为这在本质上与其“本我”所遵循的“快乐原则”相冲突,而更愿意接受那些阿谀奉承之语。
据有关学者统计,辽末契丹人的政治动向中,降金是主流,占比约六成,反叛者约占两成,守节者仅占一成多,而隐逸与投机擅权者各一人。[16](P145-146)考虑到契丹人毕竟是王朝的建立者与统治者,故其“忠诚”选择的具体情况还更为复杂,以降金的契丹贵族为例,又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是一直忠于辽王朝直至天祚被擒方降的,如萧仲恭,其人在天祚逃亡中一直追随,“时大雪,寒甚,辽主乏食,仲恭进衣并进糒。辽主困,仲恭伏冰雪中,辽主藉之以憩。”此后与天祚一并被俘后才被迫为金人效力,其对辽帝的忠诚,甚至金太宗也予以了赞扬。[17](P1849)第二类是在仓猝之下无可奈何只能降金的,如辽主在应州期间,宗望、娄室、银术可等人曾在向导带领下直扑辽主营地,辽太叔胡卢瓦妃、国王捏里次妃等多名宗室贵族在惊骇中被俘投降。[17](P1702)第三类是由于对天祚帝不满愤而降金的,代表为耶律余睹。因为天祚听信谗言,误杀文妃,而作为文妃妹夫的余睹“惧不能自明被诛,即引兵千余,并骨肉军帐叛归女直”。但女真人并不信任他,其在女直“就不调,意不自安”,最后逃往西夏。[6](P1589)《孟子》认为,“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1](P2680)从耶律余睹的事例来看,契丹人对于天祚帝的不满而做出反叛的行为恰恰可以用此解释,其“不忠”的背后实则是另一种对于王朝和本民族的忠诚。
除此之外,金人对于降者的政策,既吸引着汉人,也吸引着契丹人。例如,在收国二年(1116),金太祖即下诏:“自今契丹、奚、汉、渤海、系辽籍女直、韦室、达鲁古、兀惹、铁骊诸部官民,已降或为军所俘获,逃遁而还者,勿以为罪,其酋长仍官之,且使从宜居处。”[17](P29)而从实际上来看,这一政令也并非泛泛而谈,如萧仲恭后来进拜尚书右丞相,拜太傅、领三省事并封曹王等。[17](P1849)
四、结语
本文的研究可以发现,除宗教以外,辽代统治者亦积极利用儒家思想以达到巩固皇权的目的。在辽代建国前,契丹族人本无忠诚观念,故阿保机“变家为国”的做法因与契丹社会的部族传统相背离而导致了一系列的变乱。不过,至辽代中后期,在契丹族人中,遵循并践行忠诚观念已是一种常态,辽人对臣僚诸如敢于“犯颜直谏”等忠诚行为亦予以褒扬。发展至辽末,在面对崛起的女真贵族时,大部分契丹族人选择了站在本民族这一边,但其人同时又需要面对是忠于天祚帝本人亦或是忠于整个王朝的艰难抉择。由于随着时间流逝,女真政权取代契丹已成定势,加之女真统治者的招诱,最终,大部分契丹族人归顺了女真。
通过研究契丹族人的忠诚观念演变,还可看出,对于入主中原的契丹族人而言,其人接受中华传统文化中的忠诚观念,并不是为了接受而接受,更是考虑这一观念的实用性以及对于其人统治是否有利,而这也正是忠诚观念得以被以契丹为代表的少数民族政权接纳并吸收的真正原因。姚从吾所言:“中华文化的成立、扩大继续依靠的是适合人性,而不是武力与政治。中华文化富于人情味,有关各民族都乐于采用”,[18](P257-271)可谓一语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