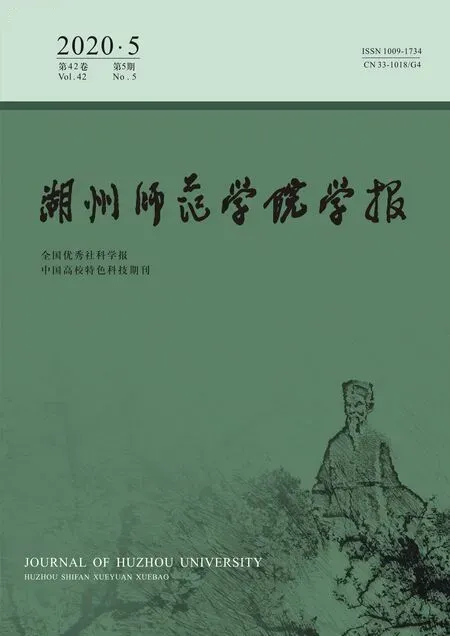气氛营造与民国上海遗民的园林诗文书写*
朱银花,刘红麟
(湖南理工学院 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湖南 岳阳 414006)
民国时期,沈曾植、郑孝胥、樊增祥、陈三立等一批清遗民纷纷选择避居上海。然而,上海租界虽给清遗民提供了一个“于朝廷无所负,于革命党亦无所忤”[1]1358的生存空间,但有着十里洋场之称的上海,其城市化的环境,无疑对他们形成了强力的冲击。王国维在《疆村校词图序》中道:“然二地皆湫隘卑湿,又中外互市之所,土薄而俗偷,奸商傀民,鳞萃鸟集,妖言巫风,胥于是乎出,士大夫寄居者,非徒不知尊亲,又加以老侮焉。”[2]722由此可知,避居海上虽是清遗民基于现实处境的抉择,但上海对于清遗民来说实非理想隐居之所。值得注意的是,类似王国维这样对上海生存环境的直笔描写,在清遗民的诗文中并不多见,反之,清遗民在寄居期间创作了不少园林隐居诗文,学界对此至今关注不多。这些园林诗文背后,实是缘于自我边缘化的清遗民,在“新”与“旧”的冲突中,通过园林营造了传统遗民的隐居气氛。感知这样的气氛,上海租界的清遗民才得以维持原有遗民体系中的生活方式以及书写方式。
一、营造气氛
“气氛”在美学上的运用分析最早由德国学者格诺特·波默提出。在波默的气氛美学中,他将“气氛”界定为:“某种独特的居间现象,某种介于主、客体之间的东西。”[3]91从客体属性与气氛之间相对固定的对应关系出发,他进一步提出了气氛的可营造性,即人们可以通过对客体条件的设定、加工,从而将其所需要的某种气氛进行场景化,这一审美过程便是气氛的营造过程。上海的环境对于商人以及推崇新文化的人士来说,可谓自由徜徉的新世界,但对于寄居于此的清遗民来说,实是“内则无父老子弟谈宴之乐,外则乏名山大川奇伟之观”[2]722的逼仄之地,上海与传统遗民山林隐居环境的异质性,使得他们与上海之间产生了难以消磨的隔阂。为了避免城市新文化、新气氛对其遗民身份记忆的削弱,遗民们有意识地通过园林营造传统遗民生活的隐居气氛,其中包括私家园林以及经营性私园。
(一)私家园林
私家园林自中唐时期开始兴盛,当时的士大夫文人多以此为远离尘嚣的修身养性之所,经过长期的发展演变,到了民国时期,租界遗民赋予了私家园林更深层次的含义,即避世之地。经济宽裕的清遗民在避居上海时,便购买或租赁寓园。鉴于上海的现实生存环境,此时的寓园(寓楼)已不同于传统意义上的园林,西方的建筑设计理念以及一些现代化的设施,更是使得上海园林与传统遗民的隐居园林相去甚远,清遗民希冀寓园成为夷市上的一方净土,则需要通过条件的设定。沈曾植在移居麦根路时,以《离骚》中“揽木根以结茝兮”之意,将麦根路改为“木根路”,并以“汇万象以庄严吾楼资吾诗”[4]696之思,将寓所命名为“海日楼”。郑孝胥“海藏楼”的命名,取自苏轼“万人如海一身藏”的诗意。除此二人外,其他遗民的寓园命名多窃比古逸民。如若仅仅是命名取意,在上海这一城市化之地,遗民们似乎不足以完成隐逸场景的设置,故而园中的自然景物、文化事物便成为营造气氛的关键。
樊增祥避居上海时的诗文写作大多以寓园(号樊园)为主,其寓园虽几经迁移,但每一处寓园的选择及其景物布置都包含了个人情怀,他在《后园居诗九首》中写道:“辟地植花卉,纵横二丈可”[5]1766,可见其对寓园中花草的经营。樊园在他的布置下“万木绿成阴,百卉芳心纵”[5]1767、“十亩绿茸茵,织成翠无缝”[5]1767。置身樊园,夜晚可倚栏赏月,清晨可闻风露飘香。樊园更是因自然景观之盛,成为了遗民们遣心散性的常聚地,他们的诗文中也有不少关于樊园景物的描写。倾心布置寓园自然景物的清遗民,除樊增祥外,郑孝胥亦是如此。郑孝胥于辛亥革命后避居上海,其海藏楼虽不是民国后所置,但亡国后其遗民的身份才赋予了海藏楼真正的含义。郑逸梅曾对海藏楼的景观有过记载:“门前有大柳数株,楼为三层,环莳花木,楼前为广场,春樱秋菊发荣时,主客常游赏期间。后于场南筑盟欧榭,为饮酒论诗之处。场西又有一小亭,署名思鹤,其弟子朱莲垞拟购双鹤贻之,以郑北上而罢。”[6]17从这段文字中可略观郑孝胥对其寓园的用心,在避居初期,他甚至寓居不下楼,这一期间他多倾心于海藏楼的布置,其在日记中写道:“移植樱花、垂柳”[1]1377,“复种橘二株,买盆梅八头”[1]1380。海藏楼虽属西式洋楼,但在郑孝胥的经营下,与传统遗民园林隐居的自然环境颇为贴近,遗民们多留恋于此。
寓园中的自然景观在经遗民们有意识地培育后,园中的场景与上海的现代化形成了强烈反差,而在这一基础上,遗民们在园中布置的文化事物、进行的文化活动又进一步推进了气氛的营造。在有限的条件下,遗民们虽渴望山林隐居生活,但实不能如愿,这就使得他们对历来的隐逸文人心慕手追。沈曾植在避居上海期间不仅在精神层面上,常以自身比附陶渊明、白居易等前代隐士,亦有意识地对他们的作品进行吸收内化,在诗歌创作中多处化用。其海日楼虽处城市喧闹处,但沈曾植在楼中作《山居图》寓意,“诵陶公云鹤有奇翼八表须臾还之句”[4]696,城市楼居便具有了随地山居的气氛。这是因为沈增植在诵读隐士作品时,“它并非只是告诉我们某个其他地方曾笼罩着某种气氛,而是召唤来了这个气氛本身,使其现身”[3]26。另外,与前代遗民分散避居的情况不同,上海清遗民群体性特征突出,这一群体无论是内在的文化思想还是外在的服饰装扮,都不同于上海其他居民,这就促进了其成员内部的交流,他们常在寓园中邀好友游园赏花、诗词题咏,其中颇具规模性的文化活动便有超社、逸社等遗民诗社,这些分期举行的社集活动多带有模仿前代遗民雅集的痕迹,如题咏前代遗民图画、三月三仿兰亭俢禊等。这些文化活动在加强群体联系的同时,更是促进了园中隐居气氛的营造。
(二)经营性私园
游园、赏园一直以来都是颇受士大夫文人青睐的交游休闲方式,避居上海郁郁无聊的清遗民亦是如此。而与前代文人略为不同,其所游历的园林除了自家园林或他人私园外,还出现了经营性私园。清遗民多不喜时人趋之若鹜的现代化娱乐场所,“醉中惟觉灯光热”[7]265、“同游肮脏应相许”[7]265,从郑孝胥记游新世界所作诗歌中,可见遗民们对这类场所的排斥态度。经营性私园由原本封闭的私家园林转向公众开放,这些园林占地面积大、布景繁多,满足了他们这一群体的休闲需求,成了私家园林之外,遗民们营造隐居气氛的另一场所。经营性私园与私家园林在气氛营造上不尽相同,在私家园林中,遗民们可以根据自身需要对园林进行场景化设置,而经营性私园的构造及布置并不受清遗民控制,其本意并非为遗民隐居气氛的营造服务,这就产生了园中气氛与遗民自身气氛的差异,这一差异的存在使得遗民们需要通过自身气氛的营造,达到两者间的融合。
自光绪年间开始,在租界公园禁止华人进入的刺激下,为了满足沪人的休闲娱乐,上海陆续出现了一批经营性私园。这些园林有的纯是西洋风格,如张园,园主在对旧园扩张重建时多吸收租界公园的元素,园中建筑物都是英文名。有的是中式传统园林风味,如徐园、豫园,园中景致颇胜。出于盈利的目的,为了吸引游客,园主在园中添加了很多娱乐性的项目,如弹子房、照相馆、动物园等。在投入运营后,沪人多争相前往,一时间张园、徐园、愚园等,成为了上海时髦、洋气的象征。到了民国时期,因为经营性园林彼此之间的恶性竞争,再加上真正娱乐场的出现,这些园林的经营状况有所衰落,但这并未影响其原有的娱乐性、营利性特征。在郑逸梅的文集中有一则为《已往之园林》,其中对民国时期经营性私园的情况有着详细的记载,如写张园,不仅是妓女招揽熟客、商人茗茶休憩的场所,全国铁路大会、南北议和大会亦在此处召开,此处亦是文艺新剧社表演新剧的地方。写徐园,“有兰花会、菊花会、杜鹃花会、昆曲会、书画会,每逢开会,群屐联翩,颇极一时之盛。”[6]661-662总之,作为开放性的公众场所,经营性园林聚集着不同类型的游客,从这些文字记载中便能感知园中的娱乐气氛或者说是经济气氛。而同是游园,在清遗民的园林诗文中,其笔下的经营性私园,并未让人感受到这样的气氛,这就在于其自身隐居气氛的营造。
虽然多数清遗民在晚清时曾到过这些园林,但此时与彼时气氛不同,此前他们多是前清官员,友朋在园中不期而遇,或茗坐观剧,或体验新鲜事物,他们与园中的气氛颇为融洽。而在民国后,清遗民的自我定位是亡国之人,是旧体制文化的守护者,这就使之与园中气氛出现了背离。从他们的视角出发,园中的娱乐项目已不再具有吸引力,游客的醉语嘈杂亦多令其不适,他们所倾心的是园中得以满足山水之思的自然景物。陈三立避居上海期间并未置办园林产业,其寓所处楼馆喧嚣之地,逼仄的楼居生活常让他有鸡著笼、鸟著笼之感,经营性私园是他常游之处,有时甚至夜半驱车前往。而“以我观物,则物皆着我之色彩”[8]26,因为自身气氛的营造,他自觉地避开游客众多之地,特寻幽辟之处无人之径。这些景物在经其发掘后,为其气氛的营造服务,由此主客之间相互融合。不仅是陈三立,郑孝胥亦留恋经营性私园,感叹“却羡愚园好怀抱,能将余事做诗人”[7]268。除了独游或友朋偕游,遗民们大型的群体性活动亦多选址于此,愚园曾聚集二十多位遗民举行文化活动。虽然这些园林可以是新式婚礼的举行地,可以是新思想新文化的宣讲地,柳亚子还将愚园称为南社的大本营,但清遗民在游园时通过他们的在场规定了园中的气氛,从而使得经营性私园成为了他们展露隐居情怀的一方天地。
二、进入气氛
气氛既不属于客体,亦不属于主体,但却具有整体性的特征。所谓气氛的整体性即是指气氛生成后既作用于客体,给客体着色定调,亦作用于主体,侵袭主体的心境感受,“这样一种力量并不登台亮相,而是在无意识中发挥其作用”[3]27。就清遗民在园林中所营造的隐居气氛而言,当他们以自身的心境状况,通过身体性在场进入规定的气氛时,上海园林与传统遗民隐居环境之间的差异便不复存在。这一点从他们的园林诗文中可以得到印证,如陈三立将郑孝胥的海藏楼称为远离尘嚣的幽宅、泬漻,称樊增祥的寓园为“人境辟仙源”[9]347。因为有了隐居气氛这一先决条件,沈曾植在海日楼中更是萌生幻想之景,“以途人为鱼鸟,阛阓为峰崎,广衢为大川,而高囱为窣堵波”[4]453,都市楼居俨然成了隐逸山居。由此,进入这样的气氛,作为审美主体的清遗民,其园林诗文书写多不见其与上海现实生存环境之间的隔阂,而是延续着传统遗民的书写方式,主要表现在对隐居之乐与亡国之哀的表达上。
(一)隐居之乐
出于对外界环境的排斥,多数清遗民平日除与同人交游外,基本闭门不出,或坐于花下赏园,或登楼与诗卷相依。纵然上海与前代遗民的生活环境相去甚远,但置身园林,感知园中营造的气氛,他们便不由地自比前代遗民的山林隐居生活,其园林诗文中的隐逸之乐不难寻觅。樊增祥在避居上海时,闭门著述不问世事,其在《清波引》小序中写道:“每日平明,娇鸟哢睛,千啁百啭,绿烟始泮,天宇空濛。正于此时得乾坤清气,特尘梦中人不知耳。余自居海滨,夜常不寐,目娱鼂景,耳熟好音,在官时无此乐也。”[5]1937此则小序颇能体现樊增祥园居生活的心境体验。在此期间他写下了大量园林隐逸诗文,独乐则高吟“老坡亦买塘桥宅,何必还山定故乡”[5]1813、“精庐亦与人相似,太傅曾言小者佳”[5]1881,众乐则招饮群贤,比拟魏晋风流、兰亭集会。试读《采绿吟》:
上巳日小园桃花犹盛,柬招伯严、石甫、午诒、公倩小集。
曲水流觞日,想绮陌草暖云香。吾庐可爱,蒨红庭院,新绿池塘。素心人未远,青笺去,几经马肆鸡坊。待羊求开三径,桃花含笑相望。 低咏丽人行,谁曾为罗衣珠衱惆怅。隔竹听跫音,且笑抚斜阳。念人生对酒当歌,还摹写兰亭两三行。江南乐,今夕斗茶,明朝乞浆。[5]1931
上巳日自魏晋起定为三月三日,按照习俗人们多在这一节日水边宴饮、郊外游春,称之为俢禊,寓意消灾祈福,后来成为了文人雅集的范式,兰亭俢禊是颇具盛名的集会之一。避居初期,樊增祥在这一日召集三五好友相聚寓园,饮酒赏花,颇有进行俢禊雅集的意味。词上阕描写樊园中的自然风光,“蒨红庭院,新绿池塘”、“桃花含笑相望”,不仅极写园中景色之美,含笑二字亦流露出园中人的心境。下阕写聚会场景,此时此景虽不及前人兰亭俢禊的山水盛景,但感知园中所营造的隐逸气氛,园中人眼前所见之景以及心中所生发的情感则与前人别无二致。樊增祥与友朋在园中把酒言欢,摹写《兰亭集序》,园中洋溢着欢声笑语,亦是一番乐趣。末句言“今夕斗茶,明朝乞浆”,表明了樊增祥的处境感受,整首词隐居之乐溢满辞章。
沈曾植的海日楼虽地处尘嚣,不及樊园景致,但其在进入气氛后,吾亦爱吾庐的隐居乐趣油然而生,其在楼居期间所作诗歌,多体现了其怡然自得的心境。试读沈曾植《散原六十寿诗》其一:
久客谙吴语,行吟是晋年。壶中真岁月,市上隐神仙。会有骑驴唤,相期梦蝶眠,大槐何戏剧,瞥过大椿前。[4]496
沈曾植这首诗虽是为陈三立祝寿而作,但与常见的祝寿诗不同,篇中皆是写自身客居上海避世楼中的情感体验。首句“久客谙吴语”表明,沈曾植在上海时日之久,已能知晓当地语言,此处读来似乎让人觉得他已经融入了上海的生活,但从“行吟是晋年”可知,其以陶渊明不欲出仕新朝,所著文章均书晋氏年号的典故,表明了自己如陶渊明般隐居不仕,不用民国纪年的遗民心迹。不仅仅是日常生活上比拟隐士,论其客居心境,亦颇有“心远地自偏”之感。对于诗人而言,气氛的存在将楼内外分离成两种不同的世界,虽寓居洋楼,日常用品离不开洋货,当其感知到气氛时,现实生存环境便无碍于诗人对隐逸之思的表达,诗中“壶中真岁月,市上隐神仙”的描写,正是诗人对自我心境体验的记录。在这样气氛中,其作为审美主体更是将自身比拟为隐居城市的神仙,因而才会生发庄周梦蝶、南柯一梦般的如幻如梦之感。整首诗不见其避居城市的凄清惨淡,不见其昔日为官时的励精图治,唯见其藏身隐庐,随地山居的精神飞跃。不仅仅是这首,他在寓居上海时所写的作品多通过化用以及典故的运用,描写幻境仙境,从而形成了与其前期作品相异的风格,颇有前代隐者风范。
(二)亡国之哀
寓居上海的清遗民几乎没有上海原籍,此前他们多在它处安置寓所,如陈三立于金陵建有散原别墅,朱祖谋于苏州置有听枫园,他们去国离家聚集上海,则是缘于这一国中之国的政治独立性。易顺鼎曾言:“无宁入裸国,而不居危邦”[10]1092,表明了当时对民国的排斥态度,郑孝胥更是直言民国乃敌国也。出于此,清遗民将“辟世欲何往?飘然海上逃”[7]248,视为保全身份的方法。然而在实际层面上,上海对其而言既非桑梓之地,又无山水之美,且清亡后他们不再出仕,多数清遗民失去了经济来源,有的依靠卖画鬻字为生,有的完全依靠友朋的接济,现实的困境使得他们无不追忆昔日前朝的生活,“然当春秋佳日,命俦啸侣,促坐分笺,壹握为笑,伤时怨生,追往悲来之意,往往见于言表。”[2]723虽然他们在此处过着隐居生活,但在进入气氛后,除抒发隐居之乐外,作为海上寓公的寄居者,其亡国之哀亦是如影随形。试读陈三立《秋日愚园西楼茗坐》:
层叠秋阴染鬓丝,翠槐列幕盖园池。小楼把茗寒阳外,远海来愁薄醉时。奇服自将孤往意,零花犹恋旧栽枝。吟虫啅鹊如相讯,此客凭栏却为谁。[9]335
陈三立在上海期间的园林诗文多是以经营性私园为背景,常见之笔端的便是对园中的幽静景色描写。他或是在园中假山石上观夕阳,或是看海棠花开、赏绝美雪景。然而,因为受自身气氛的影响,这些写张园、徐园等经营性私园的作品在书写其闲适生活的同时,亦将其作为亡国之人的隐痛不自觉地流露出来。这首诗是陈三立在游愚园后所作,诗人独自在园中西楼茗坐,看秋阴层层,看寒阳点点,起初从陈三立的视角出发,可以感知到园中秋景正好,但在赏景之余诗人的万千愁绪悄然而至,由此,这些景在其影响下不可避免地沾染上了哀伤的色彩。“奇服自将孤往意,零花犹恋旧栽枝”,道出了诗人感伤的原因,其中的“奇服”出自《楚辞·九章》:“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王夫之在《楚辞通释》中解释为:“奇服,喻其志行之美,即所谓修能也。”[11]70诗人在此处化用无疑别有深意,接着其以“零花犹恋旧栽枝”,抒发了自己对故国的怀恋。陈三立虽置有散原别墅,但在战乱四起的民国,为了保全身份只能怀着亡国之愤恨寄居夷市,最后其写吟虫啅鹊的欢娱问询,更突显自身凭栏远眺的孤寂。不仅是陈三立,其好友郑孝胥的诗文更是多笼罩着亡国之痛。试看《答陈伯严同登海藏楼之作》:
恐是人间干净土,偶留二老对斜阳。违天苌叔天将厌,弃世君平世亦忘。自信宿心难变易,少卑高论莫张皇。危楼轻命能同倚,北望相看便断肠。[7]225
这首诗是郑孝胥与陈三立二人在登海藏楼后的赠答之作,虽同为遗民,但郑孝胥与陈三立略有不同。陈三立在晚清戊戌年间已被革职,此后便无意仕途,郑孝胥则一直负有功名之心。辛亥革命爆发后,郑孝胥避居上海,在海藏楼中他多留心局势,苦于在这乱世间他不能掌握实权规划大计。民国的建立推翻了几千年来的封建体制,同时也破碎了他的政治理想,其对民国一直恨之入骨。在避居期间其内心颇多愤慨,意欲恢复旧制,在海藏楼中他布置着清朝的黄旗,寓楼对他而言便具有了象征意义。因此,其作品中的亡国之痛较于陈三立则更为悲戚,更具有政治意味。他与陈三立同登海藏楼把话斜阳,最初身处海藏楼这一“干净土”中,郑孝胥不禁感叹二老在乱世中幸得存活于世,似乎真应弃世、忘世。然而,楼中的气氛在激发其闲适之意的同时,更是唤醒了其内心深处的遗民情结,其对旧体制的依恋以及对这一体制下用世之心的重视,又使得他难以改变对清王朝的忠心,难以像陈三立一样成为“神州袖手人”。因此,深怀如此沉重的情感,郑孝胥即便只是不自觉地向北眺望,便已是肝肠寸断,其“北望相看便断肠”句,真切地写出了其作为亡国臣子的悲痛。
三、结语
租界不受民国政权管辖,相较于前代遗民为保全身份隐居山林、不入城市的生活方式,租界的存在给清遗民提供了一个全身远祸之所,多数清遗民纷纷选择寓居租界。上海作为最早开放的租界,因其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以及生活条件备受遗民青睐。在租界中,他们可以不剪辫、不易服,可以继续使用宣统纪年,如此自由之地,对于清遗民来说,应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方净土,但置身于此的他们并未有如鱼得水之感。因为上海的城市化环境与传统遗民山林隐逸环境的异质性,避居于此,这一批有着特殊身份的文人士子,无不深感压抑苦闷。出于对外界环境的排斥以及对前代遗民山林隐居的向往,清遗民有意识通过私家园林以及经营性私园营造隐居气氛,其园林诗文中的隐逸情怀与前代遗民相差无几,如若仅将这一现象归因于清遗民的凭空想象,似乎并不全面,因为其在生发山林想象时正是处在自我营造的气氛中。正是因为气氛的营造,缓解了他们在上海现实生存环境中的不适之感,感受这样的隐居气氛,才使得他们能延续前代遗民园林诗文的书写传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