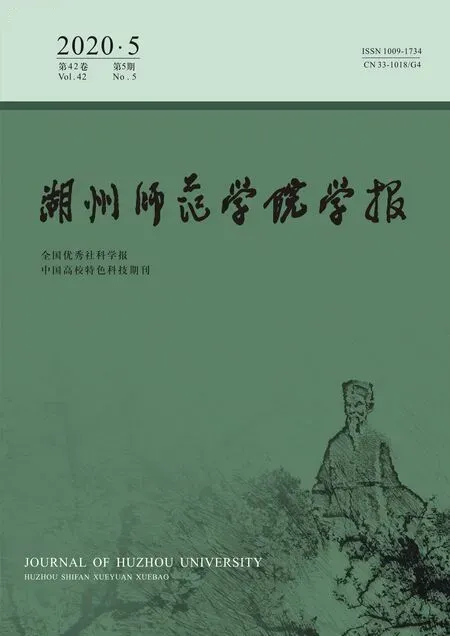南华意象禅家诗*
——浅谈皎然诗中的庄子意象
韩焕忠
(苏州大学 宗教研究所,江苏 苏州215123)
一、引言
中唐时期的高僧、诗人、诗歌理论家皎然非常喜欢《庄子》,因此他在诗歌创作中运用了大量来自《庄子》的意象。
皎然,俗姓谢,名昼(又说名清昼、如昼),东晋诗人谢灵运十世孙,湖州长城(今湖州长兴)人,出家后从守直律师受具足戒,听讲戒律,并开始留心于诗歌创作。后来游历京师(长安)与地方诸郡,诗文深得当朝公卿及地方官员的欣赏和重视。中年之后曾参访禅宗祖师,究明心地法门。晚年居湖州杼山,所著诗文多有亡佚,今尚有《诗集》七卷、《诗式》五卷存世。其所唱和者,如颜真卿、韦应物、陆鸿渐等,皆有声于当代,垂名于后世,故而时人有“释门伟器”之誉。皎然尝于诗中自述其学行云:“我祖传六经,精义思朝彻。方舟颇周览,逸书亦备阅。墨家伤刻薄,儒氏知优劣。……中年慕仙术,永愿传其诀。岁驻若木景,日餐琼禾屑。婵娟羡门子,斯语岂徒设。天上生白榆,葳蕤信好折。实可返柔颜,花堪养玄发。求之性分外,业弃金亦竭。药化成白云,形彫辞肃穴。一闻西天旨,初禅已无热。涓子非我宗,然公有真诀,却寻丘壑趣,始与缨绂别。野饭敌膏粱,山楹代藻棁。……境清觉神王,道胜知机灭。”(1)皎然:《妙喜寺达公禅斋寄李司直公孙房都曹德裕从事方舟颜武康士骋四十二韵》,《皎然诗集》,扬州:广陵书社,丙申(2016)春日据清康熙四十六年(1707)扬州诗局刻本影印,卷一,第5页。下文皎然诗歌皆出于此,故下文不再标注出版社等信息。这里皎然将儒家的六经视为祖传家学,自谓对之有非常深入的研究和理解,已能够把握其精髓,对于儒墨百家之书,也是无所不读;步入中年之后,开始修学神仙养生之术,为此不惜抛家舍业;后来接触到佛教,为佛教的修行及境界所折服,遂辞舍世荣,出家为僧。皎然这里虽然没有提到《庄子》,但既已“周览”“备阅”各种逸书,又于中年修学道家,而且此处“朝彻”一词也来自《庄子·大宗师》,其为精于《庄子》者,自是不待赘言。
意象也者,寓有某种特定含义之具体形象也。庄子首先用之,后世奉以为则,我们因此称之为“庄子意象”。如逍遥、无名、虚舟、郢人、骊珠等,皆为庄子所营造,也是皎然经常运用的意象。
二、逍遥
逍遥是《庄子·逍遥游》所极力塑造的一种意象,集中体现了庄子和道家对自由境界的追求和向往。皎然将这一意象运用于对佛教僧人生活状况的描述中,展现了出家僧人超然世外的潇洒和自在。
与官员忙于公务相比,出家为僧的生活确实要显得逍遥很多。在某个春天的夜里,皎然与一位叫裴济的朋友约定集会于某座寺院,但是这位朋友由于公务在身,不能如约而至。在经过漫长而徒劳的等待后,皎然吟咏道:“东林期隐吏,日月为虚盈。远望浮云隔,空恋定水清。逍遥方外侣,荏苒府中情。渐听寒鞞发,渊渊在郡城。”(2)皎然:《春夜期裴都曹济集心上人院不至》,《皎然诗集》卷二,第8页。东林,即庐山东林寺,乃东晋高僧慧远所居之处,皎然用以指代他与裴济约集的地方,兼有赞誉寺主之意。皎然就在这样一座住有高僧大德的著名寺院里,等待着与他的朋友裴济相会。裴济虽然出仕为官吏,但不过是以当官吏作为一种归隐的方式罢了,因此皎然称他为“隐吏”,即隐于吏者也。皎然从金乌西坠,一直等到玉兔东升,都不见这位朋友的踪影。皎然远望从郡城进山的来路,视野却被片片浮云阻隔,只能看到那一汪可爱的非常平静的水面。由此我们也可以体会到皎然的心中对于朋友的到来虽然充满了期盼,但仍然还是非常平静的。皎然及在座的僧人,既已削发出家,自然都属方外之侣,而那位朋友还必须在官府中以处理公务的名义消磨时间。想到这里,皎然似乎听到了在郡城的寒风中传来的蓬蓬鼓声,那可是约束着官员们按时上下班的号令啊!从这几句诗文中,我们可以看到,皎然实际上是以一种得大自在的心情悲悯着在世俗中劳碌不已的这位当官的朋友。
在皎然看来,逍遥并不是僧道的专利,那些能力超群、志趣高雅的官吏们,在处理完自己承担的公务之后,也是可以享受到逍遥的乐趣的。皎然在一首和诗中称赞一位叫袁高的地方官员说:“置亭隐城堞,事简迹易幽。公性崇俭素,雅才非广求。傍檐竹雨清,拂案杉风秋。不移府中步,登兹如远游。坐觉诗思高,俯知物役休。虚寂偶禅子,逍遥亲道流。更闻临川作,下节安能酬。”(3)皎然:《奉和袁使君高郡中新亭会张炼师昼会二上人》,《皎然诗集》卷三,第3页。这位官员在城墙边建筑了一座亭子,不仅造型十分简洁,而且还比较幽静,属于人迹罕至之处。推崇节俭朴素本来就是这位官员的特性,因此对所谓的雅致并不刻意地加以营求。靠近亭檐的竹叶上滴沥的雨水清澈透明,从杉林中吹拂过来的轻风带来了秋天的感觉。这里离官署很近,因此从官署出来,走不了几步,就能登上此亭,远眺美景,如同到很远的地方游览一般。坐在亭中,可以感觉到诗思灵感极为活跃;俯视亭下,可以体会到世间尘劳的休止。在此陪同那些禅僧释子,可以共同领悟清虚寂静的滋味;在此亲近道冠羽客,可以一起欣赏逍遥放达的美妙。而且这位官员还能像谢灵运那样吟咏出美妙的诗篇,这就更不是那些随从们所能附和应酬的了。此处皎然以虚寂属禅子,以逍遥归道流,固宜,但从修辞上讲,却为互文,其意谓政府大吏于公务之暇,如肯亲近禅子道流,亦可享受到虚寂逍遥的那种乐趣,从而与一般俗吏区别开来。事实上讲,这也是历代士大夫亲近禅子道流的根本原因,我们于此还可以隐然看出皎然思想中有一种以出家为高尚其事的自得之心和自足之意。
那些喜欢亲近禅子道流的政府官员们,在思想言行上逐渐具有了逍遥放达的旨趣,因而也使他们主持的官署变得雅致起来。皎然曾经参与过这些官员们的聚会,他在诗中记录了自己参加这种集会的感受:“府中自清远,六月高梧间。寥亮泛雅瑟,逍遥扣玄关。岭云与人净,庭鹤随公闲。动息谅兼遂,兹情即东山。”(4)皎然:《夏日奉陪陆使君长源公堂集》,《皎然诗集》卷三,第3页。阴历的六月,正是酷暑时节,在高大而茂盛的梧桐树掩映之下,高大宽敞的官署显得非常的清静幽远,一阵阵优雅的琴瑟之声泛起其间,到此集会的士大夫们都在探讨着玄言妙理的关键,无不显得逍遥自在。从山岭上飘来的白云给人一种极其洁净的感觉,而庭院里的仙鹤也跟随太守一起过着悠闲自在的生活。在这里工作和休息都获得了充分的实现,诗人推想,这大概就是当年谢安石居住于东山时的情形吧。玄关,此处既可以理解为进入玄妙境界的门户,也可以理解为玄妙义理的关键之处,本来是道家术语,但是隋唐佛教诸宗的祖师,也将佛教经典所阐发的思想义理称之为“玄”。如天台宗的智者大师有《法华玄义》和《维摩诘经玄疏》,章安灌顶有《涅槃玄疏》等注疏;华严宗的至相智俨有《华严经搜玄记》,贤首法藏有《华严经探玄记》等著述,并以“十玄无碍”作为本宗的最高境界;而禅宗也将参悟禅理称之为“参玄”。因此我们认为,结合当时的语境,作为出家僧人的皎然所说的“逍遥扣玄关”,就是自由自在地探讨佛道两家的经典义理,体味佛道两家的思想境界。也就是说,皎然此处所说的逍遥,其主体虽然是供职于官府的士大夫,但其获得,却仍然需要通过探索佛道两家的玄言妙理。
古来释逍遥之义者多矣,而皎然最佩服的,则是东晋时期隐居于浙东剡溪沃洲山中的支道林。皎然除了多次在不同诗作中表达自己对支道林的敬仰之情外,还有专门赞颂支道林的诗作:“支公养马复养鹤,率性无机多脱略。天生支公与凡异,凡情不到支公地。得道由来天上仙,为僧却下人间寺(一作世)。道家诸子论自然,此公唯许逍遥篇。山阴诗友喧四座,佳句纵横不废禅。”(5)皎然:《支公诗》,《皎然诗集》卷六,第10-11页。支公,即东晋高僧支遁,字道林。道林隐居于剡溪山水之间,重马之神骏,喜鹤之冲举,因而过着放马养鹤的生活。道林性情真率,毫无心机,脱略于名利之表。在皎然看来,这正是道林天生不同于凡夫俗子的地方,而凡夫俗子也根本体会不到道林的思想和境界。道林精通老庄,本有仙风道骨,如果修道的话,本可以成仙而上天的,但他偏偏出家为僧,来到人世间,居住在简陋的佛寺之中。道家诸子,如老子、列子、庄子等,都非常推崇自然,而道林精通道家典籍,最为推崇的却是《庄子·逍遥游》。向秀、郭象等以注解《庄子》出名,他们以适性为逍遥,道林不许此意,而以至人解脱尘劳所达到的心灵境界为逍遥,时人皆以其说为“拔理于向郭之外”。道林深受名士们的喜爱,经常以诗文会友,但仍然保持了僧人的特色,并没有废弃禅定修行。在这首诗中,皎然充分表达了他对支道林的倾慕和推崇,其中特别提到道林对《庄子·逍遥游》的欣赏和赞许。
我们说,作为具有深厚文化修养的佛教高僧,皎然喜欢《庄子》,推崇将逍遥理解成佛菩萨超脱凡俗尘劳状态的支道林,因此可以对《庄子》中的逍遥意象有深刻的理解和切身的体验,这也是那些在名利中奔忙的士大夫们非常愿意与他接近的主要原因。
三、无名
无名是老庄道家对天然之道的描摹,包含对修道的强调和悟道的体会。《庄子·逍遥游》云:“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这就是说,只有达到了无己、无功、无名的得道状态,才能像至人、神人、圣人那样于天地之间实现真正的逍遥游。皎然在自己的诗作中运用这一意象,既展现了得道高人的境界,又指示出修道入门的关键所在。
自古以来,大凡得道的高人,都已打破世俗名利的束缚,其行事往往超越人们的意料,因此无不处于一种“无名”的状态。正如皎然在一首诗中所说的那样:“不住东林寺,云泉处处行。近臣那得识,禅客本无名。”(6)皎然:《酬李补阙纾》,《皎然诗集》卷一,第14页。东林寺因东晋高僧慧远的驻锡而名闻天下,成为高僧得道的渊薮,因此之故,为僧而出于东林寺者,莫不受到天下的崇重。但盛名之下,往往是其实难副,多有欺世之徒盗其名而用之,以求名闻广大与供养丰饶。李纾官居补缺,职虽卑微,但由于是天子近侍之臣,因而在官场上很受重视。皎然则明确告诉他,自己并不住在东林寺那样的名山大刹中,而是像天上的云彩和地上的泉水一般,随顺各种因缘,到处游方行脚。作为一心追求参禅悟道的人,也就难怪像阁下这样的近侍之臣不认识了。此处虽然只有寥寥数语,却生动而鲜明刻画出一位世外高人远尘离俗的形象来,其中“禅客本无名”一语正是作者以道自居的体现,故而包含着某种矜持和自信的情愫。
无名既然是得道的体现,那么不近名或者避名,自然也就成了修道的捷径。皎然在写给自己的好友郑方回的诗中说:“思君处虚空,一操不可更。时美城北徐,家承谷口郑。轩车未有辙,蒿兰且同径。庄生诫近名,夫子罕言命。是以耕楚田,旷然殊独行。……逸翮思冥冥,潜鳞乐游泳。”(7)皎然:《答郑方回》,《皎然诗集》卷一,第4-5页。皎然非常思念这位朋友,他虽然独自生活在远离城市的空旷之地,但却依然保持着高尚节操而无所改变。他不仅体貌像古人称赞的城北徐公一样英俊伟岸,而且还门第高贵,家世显赫,出身于荥阳谷口的郑氏大族。他不肯俯首结交达官,因此门前没有车马通过的辙迹,经行的小路也长满了蒿草和兰花。他遵从庄子的告诫,为善无近名;他也信守孔夫子的格言,从来不觉得命运对自己有什么不公平。因此他耕种在长满荆棘的瘠田上,行走在孤独的旷野中。而在皎然的心目中,这位郑姓朋友就是飞翔在高空的鸿鹄,就是潜泳在深水的游鱼,过的是一种逍遥自在的生活。在这里,皎然揭示出自己这位好友修行的关键就是不近名。
不近名,所以无名。无名,也就意味着不受名闻利养的干扰,可以保持自己独特的性格和节操,保留事物自身的天然状态。皎然另一位姓郑的朋友得到一段带着枝丫的木头,他没有做任何加工,就直接拿过来当木机(茶几一类的桌案)用。皎然对此极为欣赏,特地写诗赞扬他:“万物贵天然,天然不可得。浑朴无劳剞劂工,幽姿自可蛟龙质。欲腾未去何翩翩,扬袂争前谁敢拂。可中风雨一朝至,还应不是池中物。苍山万重采一枝,形如器车生意奇。风号雨喷心不折,众木千丛君独知。高人心,多越格。有时就月吟春风,持来座右惊神客。爱君开合江之滨,白云黄鹤长相亲。南郭子綦我不识,非君独是是何人。”(8)皎然:《郑容全成蛟形木机歌》,《皎然诗集》卷七,第5页。皎然认为,万物的可贵,就在于其保留了极其难得的天然状态。很显然,皎然的这一观点来自道家特别是《庄子》,此处且不细论。皎然指出,这段带着枝丫的木头,浑然朴拙,用不着任何的加工雕刻,就可以呈现出一副腾云欲飞的蛟龙姿态来,人们虽然争相前来观看,但却不敢加以拂拭。皎然甚至突发奇想,觉得这段像蛟龙一样的木头绝不是池中之物,万一哪天风雨降临,它就会冲天飞走。这位朋友从万重大山之中采来这段木头,其外形如同车辆一样,可谓是出乎意料的奇特,这段木头虽然经历过无数次的风吹雨淋,但其内心依然是无比的坚硬,只有这位朋友,从千万丛木料中发现了这段木头的独特性,这也正是他作为高人见地时常迥出常人的突出体现。就在这条利用天然木头做成的木机旁边,这位朋友吟咏风月之诗并与朋友们一起玩味,使大家都惊讶赞叹他的神来之笔。皎然对这位朋友隐居在江边的生活本来就非常欣赏,对他长时间亲近大自然中的白云黄鹤充满了羡慕之情。如今看到这位朋友的天然木机,使他想起了《庄子·齐物论》开篇所说的得道高人南郭子綦。皎然承认自己并没有见过南郭子綦,但却觉得这位郑姓朋友就是南郭子綦一样的人。皎然尊敬和赞叹这位郑姓朋友,是因为在他身上感受到了天然无名的朴实之美,于此我们也可以看出皎然对于《庄子》中这一意象所怀有的无比喜好之情。
皎然对于无名的推崇,还来自他对突破名利限制之后自由自在境界的向往和追求。他在诗中说:“乞我百万金,封我异姓王。不如独悟时,大笑放清狂。”(9)皎然:《戏作》,《皎然诗集》卷六,第13页。在皎然看来,获得百万金的富有,受封异姓王的尊崇,还不如独自悟道的时候,可以纵声大笑,自由地展现自己的清高和狂放姿态。《庄子·秋水》载有庄子却聘之事:“庄子钓于秋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愿以境内累矣。’庄子持竿不顾,曰:‘吾闻楚国有神龟,死已三千岁矣。王巾笥而藏之庙堂之上。此龟者,宁其死为留骨而贵乎?宁其生而曳尾于涂中乎?’二大夫曰:‘宁生而曳尾涂中。’庄子曰:‘往矣,吾将曳尾于涂中。’”《庄子·列御寇》也记有此事,只是说法稍有不同:“或聘于庄子,庄子应其使曰:‘子见夫牺牛乎?衣以文绣,食以刍菽。及其牵而入于太庙,虽欲为孤犊,其可得乎!’”而《史记·庄子列传》将此事坐实为楚威王所使。庄子有受聘之事,自然是为声名所累。但他毕竟是得道之人,故而在名利面前仍能保持其块然复朴的状态。皎然的这首诗无疑是受到了庄子却聘的启发,也是他对自己出家之后过着无名朴素的生活感到满意和自足的体现。
从皎然对无名天然的推崇中,我们可以非常明显地感受到,庄子道家对他的思想观念所产生的深刻影响。因此我们说,皎然作为谢灵运的后裔和一代诗僧,其艺术思想和创作风格既深受儒道等中国固有传统文化影响,也久为佛教所浸染,是儒道佛三家的思想文化在唐朝中期的历史形势下综合创新的结果。
四、虚舟
在《庄子·山木》中,市南宜僚对鲁侯说:“吾愿去君之累,除君之忧,而独与道游于大莫之国。方舟而济于河,有虚船来触舟,虽有惼心之人不怒。有一人在其上,则呼张歙之。一呼而不闻,再呼而不闻,于是三呼邪,则必以恶声随之。向也不怒而今也怒,向也虚而今也实。人能虚己以游世,其孰能害之!”市南子从虚船触舟而人不怒的现象中受到启发,提出虚己以游世的主张,由此形成了“虚舟”的意象。虚舟泛于湖海之上,既无人操作,又无所系属,因此又称为随波逐流的“不系舟”。皎然运用这一意象,表达了一位禅僧无所用心、无所追求、随缘任运的人生态度。
在皎然看来,作为禅僧,既可以隐于深山,又可以游于市朝,但当随缘,不必拘执。他在一首诗中明确表示了自己“反招隐”的态度:“禅子方外期,梦想山中路。艰难亲稼穑,晨夕苦烟雾。曷若孟尝门,日荣国士遇。铿锵聆绮瑟,攀折迩琼树。幽践随鹿麋,久期怨蟾兔。情同不系舟,有迹道所恶。”(10)皎然:《奉和薛员外谊赠汤评事衡反招隐之迹(一作“作”)兼见寄十二韵》,《皎然诗集》卷一,第3页。出家为僧,涉身方外,希望与二三同道好友隐身于山林之中,以便于悟道参禅。殊不知自耕自食极其艰难,自炊自饮也是非常劳苦。从修道的方便上考虑,还不如找一个像孟尝君那样热情好客的功德主或者供养人,每天都享受着国士的待遇,可以聆听着铿锵悦耳的琴瑟之音,可以随手攀折近在身边的玉树琼枝,可以在放养着麋鹿的幽静园林里经行散步,可以在明亮的月光下与好友聚会。真正的修行就应该像没有缆绳系属的船儿一样,如果执著于山林,执著于某一种方式,反为不美。这里皎然以不系舟的意象表达了自己反对执著隐修山林的立场和观点。比皎然稍早一些的禅宗僧人永嘉玄觉,在回复好友左溪玄朗招他同隐山林的回信中,也表达了大致相同的观点,提出修行的关键在于自心,而不在都市或者山林。由此可见,皎然运用庄子意象所表达的这一主张还是非常符合禅宗的思想传统的。
皎然虽然主张随缘修道,不拘山林和市朝,但他毕竟是出家僧人,而且天性上也厌喧喜静,因此有时还是禁不住表达出对归隐山林的羡慕和向往。如他在写给友僧的诗中说:“未到无为岸,空恋不系舟。东山白云意,岁晚尚悠悠。”(11)皎然:《湖南兰若示大乘诸公》,《皎然诗集》卷一,第14页。无为岸,即涅槃岸、彼岸之意。早期译经,找不到涅槃在汉语中的对应词,就用道家的无为这一范畴表达涅槃之意。东山,即东晋谢安石未出仕时的隐居之所,后世以之为高才硕德隐居地的象征。皎然坦承自己还在修行的路上,还没有到达涅槃的彼岸,因而对那艘“不系舟”,即随缘任运的修行方式,还有着万分的留恋。虽然如此,每当想起白云飘荡的东山,那是他先祖归隐之所,都不禁要心驰神往,此心此意,即便是到了他的晚岁,都没有丝毫的改变。随缘任运,说起来虽然非常好听,也很符合佛教特别是禅宗自觉觉他、随方利物的思想观念,特别是对那些修行已经达到很高境界的人,确实能够起到弘扬佛法、利益众生的目标,但是如果本人修行不足,也就成了某些资佛自活之辈贪恋城市繁华的借口而已。因此,那些有道高僧在表示要随缘利物的同时,无不特别强调要努力加强自身的修行,提高自己的造诣。皎然晚年放弃诗歌创作和理论探讨的主要原因,也是基于佛法修行一定要逮得己利方面的考虑。因此我们也可以这样讲,在皎然的思想意识中,真实的佛法修行是实现像不系舟泛乎江海那样随缘利物的基础和前提。
皎然还用江湖虚舟的意象解释了自己的居住情况。皎然长期居住的草堂,位于南池之中充满诗情画意的一座小岛上,“左右云山满目,一坐遂有终焉之志”(12)皎然:《南池杂咏五首·序》,《皎然诗集》卷六,第5页。。不仅景色幽美,而且具有丰富的人文内涵,当年吴兴刺史柳恽就在这座小岛上写下过“汀州采白蘋”的名句。皎然很喜欢这里,在这里咏有《南池杂咏五首》,其三即以“虚舟”为题。其诗云:“虚舟动又静,忽似去逢时。触物知无忤,为梁幸见遗。因风到此岸,非有济川期。”(13)皎然:《南池杂咏五首·其三·虚舟》,《皎然诗集》卷六,第6页。江湖上飘浮着一艘虚舟,无所系属,无人操作,动了动,又静了下来,想要离开,又好像逢到了适宜的得风顺水的好时机。即便是触碰了什么,对方也知道不是有意的要来冲撞和冒犯。令这艘虚舟倍感幸运的是当年造桥的时候,把它给落下了。它只是顺风来到这里而已,并不是有目标地穿过江河来到这里。皎然将自己随顺世间的因缘,很自然地生活修行在一个风景幽美、文化资源丰富的场所,比喻为虚舟无所用心的随缘停泊,对于像他这样深受士大夫敬重的出家高僧来讲,应当说还是非常贴切的。
庄子所说的虚舟,更多强调的是“虚己以游世”,从而获得与物无忤的效果。皎然将其借用过来,转化成了佛教特别是禅宗的随缘任运。就其破除主体自心的某种执著而言,二者确实具有相当的一致性。但庄子本意不过在苟合取容而已,皎然所强调的则是随缘任运之后的弘法利物。如此来看,皎然借用庄子虚舟这一意象的同时也将其改造得更富有主动精神和建设意义。
五、郢客
郢客这一意象出自《庄子·徐无鬼》:“郢人垩漫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垩而鼻不伤,郢人立不失容。”从此之后,郢人或者郢客,就成为能够虚心接受别人批评和指正的高明作家的代名词。皎然将这一意象运用在朋友创作的评说之中,同时也使自己的相关诗作具有了运斤成风的意义。
如裴刺史在听陈山人弹奏白雪之曲后,很是欣赏,为之作诗称赞,同集之人都纷纷作诗相和,皎然也和了一首:“春宵凝丽思,闲坐开南围。郢客弹白雪,纷纶发金徽。散从天上至,集向琼台飞。弦上疑飒飒,虚中想霏霏。通幽鬼神骇,合道精鉴稀。变态风更入,含情月初归。方知阮太守,一听识其微。”(14)皎然:《奉和裴使君青春夜南堂听陈山人弹白雪》,《皎然诗集》卷一,第13页。春天的夜晚,大家闲坐在南堂之内,凝神静思,听一位陈山人弹奏白雪之曲,那纷纭整齐的音节发出金属鸣击的声音。大家仿佛看到了散乱的白雪从天上纷纷飘下,飞落集合在洁白无瑕的琼台之上。分明是弦上弹奏出的飒飒之声,却被听众想象成了空中雪落的霏霏之音。这位陈山人真是弹奏的高手,他的音声不仅能够通向幽暗的地府,使鬼神感到惊慌害怕,而且还能够直接与道相合,很少有人能够欣赏其精微神妙。其声调变换就像风卷雪入,其脉脉含情就如同新月初升。听众们更从裴刺史的赞诗之中,体会到他像西晋的阮咸一样非常精通音律。皎然这里运用“郢客”这一意象,既表扬了陈山人弹奏白雪之曲的美妙,又称赞了裴刺史赞诗的贴切恰当。
又如袁刺史到鹡鸰峰兰若春游,在所写诗中表达了对皎然的思念之情,这令皎然非常感动,因此特地作诗致谢:“鹡鸰中峰近,高奇古人遗。常欲乞此地,养松挂藤丝。昨闻双旌出,一川花满时。恨无翔云步,远赴关山期。跻险与谁赏,折芳应自怡。遥知忘归趣,喜得春景迟。已见郢人唱,新题石门诗。”(15)皎然:《奉酬袁使君高春游鹡鸰峰兰若见怀》,《皎然诗集》卷二,第1页。鹡鸰中峰虽然离郡城很近,但却高峻、奇险,有很多古人的遗迹。皎然早就想向有关部门提出申请,想在这里结庵隐修,种植松树和丝藤。昨天听说袁刺史出来游玩,这可正是满山谷中鲜花盛开的好时节啊!皎然深恨自己没有腾云驾雾的本领,不能飞过关山赶到鹡鸰中峰陪同袁刺史,不知袁刺史与哪位一道攀越险峻的山峰。他猜想着并无人与袁刺史一起欣赏折来的还带着春天芬芳的山花;他想象着袁刺史春游的兴趣盎然,流连忘返,尽情欣赏着山上迟来的春色和美景。皎然看到了袁刺史为此所写的纪游之诗,他感到很有自己先祖谢灵运《游石门诗》的清新旨趣。皎然将袁刺史的诗作称为“郢人唱”,显然是一种极高的推崇和赞誉。
再如他曾写诗表达自己阅读张九龄文集的感受:“体正力已全,理精识何妙。昔年歌阳春,徒推郢中调。今朝听鸾凤,岂独羡门啸。”(16)皎然:《读张曲江集》,《皎然诗集》卷五,第6页。张九龄是皎然比较佩服的一位政治家,因此读他文集时肯定是充满了敬仰之情的。在皎然看来,张九龄的诗文不但文体很正,力道很足,而且说理精微,见识高妙。皎然以地望尊张九龄为张曲江,其所留下的阳春之歌,皎然推崇为“郢中调”,即郢人所创的高雅之作,这自然属于对张九龄诗文的赞扬之辞。今朝再读,如听鸾凤的鸣叫一样悦耳动听,作者是对《张曲江集》怀有深深的敬意的,因此他在这首诗中称其为“郢中调”,其中很显然蕴含着郢客或郢人的意象,不仅是表达自己的羡慕而已。
被皎然推许郢客或者郢人的,虽然也有工匠,如其诗中有“楚山有石郢人琢,琢成长枕知是玉”(17)皎然:《花石长枕歌答章居士赠》,《皎然诗集》卷七,第10页。的说法,但主要还是指那些擅长作诗的士大夫们。众所周知,唐朝是中国诗歌的全盛时期,许多士大夫都是因擅诗而得第,皎然推许他们为郢客或者郢人,实际上也是他具有卓越文艺鉴赏能力的反映。
六、骊珠
骊珠这一意象出自《庄子·列御寇》:“河上有家贫恃纬萧而食者,其子没于渊,得千金之珠。其父谓其子曰:‘取石来锻之!夫千金之珠,必在九重之渊而骊龙颔下。自能得珠者,必遭其睡也。使骊龙而寤,子尚奚微之有哉!’”骊珠至贵,而贫子之父竟取而锻之,此亦遵守道家“不贵难得之货”之所致也。后世之用此典者,则多反庄子之意,必就其奇其贵其难得而为言,皎然也是如此。
皎然曾以骊珠的意象夸奖朝廷大吏于頔的诗作。于頔身为朝廷重臣,以御史中丞刺史湖州,不意罹患疾病,静养署斋,闲中赋诗一首,举示皎然。皎然酬诗中有云:“比闻朝端名,今贻郡斋作。真思凝瑶瑟,高情属云鹤。抉得骊龙珠,光彩耀掌握。若作诗中友,君为谢康乐。”(18)皎然:《奉酬于中丞使君郡斋卧病见示一首》,《皎然诗集》卷一,第1页。皎然首先大力赞扬于頔的佛学造诣,然后表示自己很早就听说过中丞的大名,而今竟然获得了中丞从郡斋寄来的大作。皎然拜读之后,觉得这首诗真情凝聚,如聆瑶琴玉瑟,像冲天飞起的仙鹤一般将读者的心情带入高高的云端。他捧读之际,如捡到了一颗骊龙宝珠,在他的手掌上放出了耀眼的光彩。皎然认为,如果在诗人之中寻找可以与于頔不相上下的人物的话,那么只有他的十世祖康乐公谢灵运可以相比了。我们知道,谢灵运自晋宋以来诗名甚盛,李白、杜甫等都对他极为钦佩,皎然因为与之有血脉传承的关系更是对其敬重万分,因此他将于頔比之于谢灵运,自然是一种高度的推崇。而于頔对皎然也是非常欣赏,后来他入朝拜相,将皎然诗文集奏上,遂得敕入秘阁,成为那个时代的荣宠。
皎然曾以骊珠的意象鼓励年轻人的诗赋创作。一位叫裴集的年轻人和另一位叫阳伯明的年轻人,二人也许是久慕皎然的大名,分别将自己的诗作呈上,皎然作了一首诗,同时回复他们两人,其中有云:“知音如琼枝,天生为予有。攀折若无阶,何殊天上柳。裴生清通嗣,阳子盛德后。诗名比元长(二子诗比王融,为俱少年著名),赋体凌延寿(赋如文考亦俱盛年)。珠生骊龙颔,或生灵蛇口。何似双琼章,英英耀吾手。”(19)皎然:《答裴集阳伯明二贤各垂赠二十韵今以一章用酬两作》,《皎然诗集》卷二,第4页。这两位年轻人的诗中,可能对皎然的诗作有所称誉,因此皎然将他们视为知音,认为他们像上天恩赐给自己的玉树琼枝一样。皎然表示非常乐意与他们结交,只是他们出身高贵,自己苦于缺少台阶,因而只能像仰望天上的柳树一样无缘攀折。因为裴生先世多位居清通显要之职,阳生先人也有盛德于国家,而且二人擅长诗赋,以至当世比之于晋代竹林七贤之一的王融和汉代弱年即能作赋的王延寿。皎然认为,他们呈给自己的诗文就像骊龙颔下或者灵蛇所羡的宝珠一样珍贵,因此他们那两篇如美玉一样的诗篇,在自己的手中散发出耀眼的光辉。作为诗名甚深的前辈,对后世有如此的赞扬,自然可以对他们产生无穷的精神激励作用。
如果说皎然运用郢客或郢人的意象称赞的是诗文创作主体的话,那么他运用骊珠的意象所表扬的主要就是诗文作品。这既是他作为诗人具有丰富创作体验的表现,也是他作为《诗式》的作者,具有极高的诗文鉴赏水平和理论概括能力的反映,更是他作为一代高僧非常注重广结善缘的表现。
七、余论
皎然虽然在自己的诗文创作中大量运用了逍遥、无名、虚舟、郢客、骊珠等来自《庄子》的意象,对道家的思想也有所接受和欣赏,但他毕竟是佛教的高僧,因而有时也会站在佛教的立场上对道家的思想观念提出不同看法。
皎然对道家将无或者道作为天地根源的说法深为不满。他在《禅诗》中说:“万法出无门,纷纷使智昏。徒称谁氏子,独立天地元。实际且何有,物先安可存!须知不动念,照出万重源。”(20)皎然:《禅诗》,《皎然诗集》卷六,第9页。道家认为,万物都是来源于无,以无为门,从无而生。皎然认为这种说法会让人的心智产生混乱,因为万物众多,各有因缘,不可能从一个原因产生和形成。因此老子所说的“不知谁氏之子,在象帝之先”的道,在皎然看来实际上就是不可能存在的东西。皎然指出,主体自我只有在无思无念的寂然状态下,才可以照见,或者说直观地感受到万事万物的根源。众所周知,道家非常重视对世界事物产生根源和发展规律的探讨,而皎然的这种思考,则将人们的思路拉回到对主体自心的关注上,体现的是中国佛教特别是禅宗的思想特点。
皎然对道家将事物的发展变化视为自然运行的结果也很不满意。他在《禅思》中说:“真我性无主,谁为尘识昏?奈何求其本,若拔大木根。妄以一念东,势如千波翻。伤哉子桑扈,虫臂徒虚言。神威兴外论,宗邪生异源。空何妨色在,妙岂废身存。寂灭本非寂,喧哗曾未喧。嗟嗟世上禅,不共智者论。”(21)皎然:《禅思》,《皎然诗集》卷六,第10页。真我即自性,空无所主,因此外界的事物并不能昏蔽人们的认识。人们一旦认识到了这一点,就等于拔出了无明的根本。但是妄念不守自性,随境流转,其势如同江河东流一般,波涛翻滚,滔滔不绝。《庄子·大宗师》中的子桑户等人自称无论是变成鼠肝,还是化为虫臂,他们都会顺从自然的运行和变化。皎然认为他们的这种观念非常可悲,将某种事物奉为神威是外道的标志,而对外道的尊崇就是各种邪门歪道的来源。皎然站在佛教的立场上,认为空不妨碍事物的存在,妙也不废弃人身的存在,寂灭并不是消除各种声响,喧哗也不是产生各种噪音。世间所谓的各种禅定,是无法获得智者的欣赏和赞同的。很显然,在皎然看来,道家特别是《庄子》中的那些随顺自然的观点就是一种不足与论世间禅,是佛教所要批判的外道之论。
皎然虽然对道家和庄子的思想观点并不完全认同,但他在诗作中大量运用了来自《庄子》的意象,从而使他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一定的庄子道家色彩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