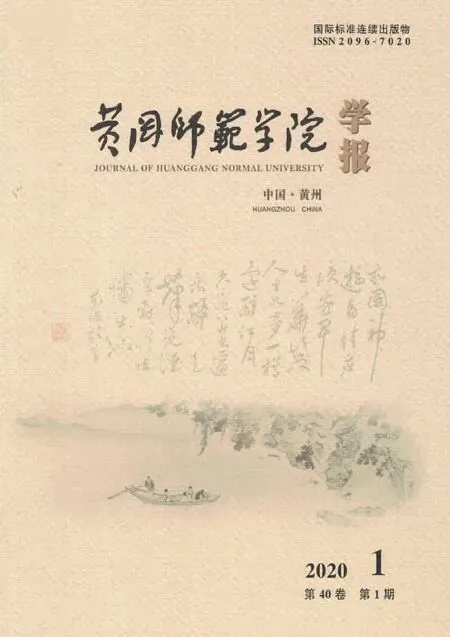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的民间叙事
陈 瑶
(黄冈师范学院 文学院,湖北 黄冈 438000)
湖北作家晓苏,本是华中师范大学教授,大约是源于兴趣,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创作,成为一名成果丰硕的作家。晓苏小说朴质生动,善良温暖,有一股浓郁的生活气息。他的小说大致有两个系列:油菜坡系列和大学校园系列。这与他的生活经历是息息相关的,他的老家在湖北一个偏远的乡村,离开家乡后成为一名大学教授,他所写的是他自己再熟悉不过的生活。他笔下的油菜坡,有纯净的自然环境,生动的乡村生活,活泼的乡亲乡民,寄托着他难以掩饰的深情。所以,油菜坡既是晓苏的物质家园,也成为他的精神故乡。晓苏离开家乡多年,但是小说中的乡村乡野味还是那么纯正,我想,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他的民间叙事。笔者认为,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的民间叙事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平民立场:普通老百姓叙述的普通生活
任何一种叙事形态,首先都取决于叙事立场。叙事立场是叙事形态得以形成的先决性因素。因此,我们研究晓苏小说的民间叙事形态,就必须先从它的叙事立场入手。平民立场是晓苏民间叙事立场的重要体现,也是民间叙事的主要策略。平民立场要求作家拒绝知识分子的精英立场,把老百姓作为叙事的主体,从情感立场上与老百姓保持一致,用老百姓的眼光看,用老百姓的耳朵看,用老百姓的嘴巴说,力求真实反映老百姓的生存状态,原汁原味地呈现老百姓生活的原生形态。油菜坡系列小说的叙事立场就是这样的平民立场,它们所叙述的都是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作家隐藏在这些普通百姓中间,与他们融为一体,一同喜怒哀乐。莫言曾经说过:“我认为真正的民间写作,就是作为老百姓的写作”[1],而不是“为老百姓的写作”,这句话精辟地揭示了平民立场的内核。油菜坡系列小说的叙述者多半是乡村普通的老百姓。比如村里的光棍寡妇、相依为命时而拌嘴吵架的夫妻、关系微妙的婆媳、生活艰难的老人、远离故土的打工者、留守农村的农村妇女……等等,都是乡村极其常见的各色普通百姓,仿佛就是你我身边的乡里乡亲。
晓苏擅长从这些普通人物的伦理关系入手,真实地反映老百姓的日常生活本相。他们的家庭关系如夫妻关系、婆媳关系、兄弟姐妹关系及姑嫂叔嫂关系等等几乎所有乡村伦理关系都在作品中得到体现。《我们的隐私》写的是夫妻关系,《花被窝》写的是婆媳关系,《侯己的汇款单》写的是公媳关系和邻里关系,《姑嫂树》写的是姑嫂关系,《嫂子改嫁》写的是叔嫂关系,《我的三个堂兄弟》《坐下席的人》写的是兄弟关系,《桃花桥》写的是兄妹关系……晓苏的小说几乎涉及到家庭关系的方方面面。其次,还有各种社会关系,如师生关系、邻里关系、朋友关系、上下级关系,甚至两性关系。晓苏通过这些普通人物的伦理关系多侧面地透视了普通百姓的真实生存境况。
这些普通人叙述着他们同样极其普通的生活:吃饭睡觉、拌嘴吵架、偷情出轨、外出打工、皮肉生意、回乡做房等等,他们行走在平淡无奇的日常生活中,体味着生活的那一份酸甜苦辣与喜怒哀乐。这些普通老百姓的普通生活在晓苏小说里得到充分展现。
反映底层生活的磨难。如《我们的隐私》中,我们的隐私既有“我”和麦穗这一对临时夫妻的隐私,也有留守在家的我老婆的隐私,而这些隐私是不便明说却又彼此心知肚明的。无论是外出打工一族还是留守农村一族,都面临着性饥渴性压抑的生理和心理问题,在情感上同样渴望得到家庭和社会的关爱。《陈仁投井》、《幸福的曲跛子》、《侯己的汇款单》等写的都是底层农民的苦难,那苦难背后的努力与挣扎直抵人心深处,触动心灵。
讲述家庭生活的摩擦与温馨。《花被窝》讲述的是婆媳之间的故事。婆媳关系本是最微妙最难处理的,一床花被窝所暗示的性事反而让婆媳间达成难得的谅解。无论是婆媳关系,还是乡村女性的性爱关系,都是民间重要的伦理关系。这种谅解是对乡村女性生存状态的同情。《看稀奇》中,三位吵过架的老人因为看到一对青年男女热烈亲嘴受到触动,尽释前嫌,传达出普通百姓内心蕴藏着的亲情、友情和温情。《幸福的曲跛子》中,曲跛子夫妻终于如愿以偿地盖起了两层高的小楼房,但是曲跛子为此付出了一只脚的代价,让妻子又心疼又无奈。《麦芽糖》中的“我”只能每天给爹抓背,相比同村的成功人士显得毫无出息,“我”却很享受这种幸福。“我”留守村庄的生活就如同农家最常见又最不值钱的麦芽糖,普普通通又甜甜蜜蜜,小说写出了普通百姓最朴实简单的幸福生活。
有的作品批判乡村的物欲主义。张大凤盖三层楼的愿望,是利用自己的姿色欺骗三个男人的感情才得以实现(《三层楼》)。余勒回乡给丈母娘祝寿,却因为赌博输光了本金和礼金而打架斗殴被警车带走(《给丈母祝寿》);钱眼一心钻到钱眼里去了,最后反而丢了性命(《有个女人叫钱眼》);《姑嫂树》中的小姑子刘贝不管嫂子的坚决反对,执意离开贫瘠的家乡去城市做皮肉生意赚钱;《侄儿请客》中漂泊半生回到故乡的老人却难以接受世风日下的现实,温暖的故乡只剩下苦涩的记忆。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坍塌让曾经民风淳朴的乡村蜕变成物质欲望的利益场,晓苏表达出了对乡土伦理的丧失满含痛惜,透露出作家对于现代都市文明的入侵所导致乡土传统文化消逝的反思。
凸显乡村弱势群体生存的艰难。《陈仁投井》里,女儿因为谣言上吊自尽;陈仁与儿子儿媳关系不和,善良的陈仁最终没有报复仇人们而选择了静静死在自己的井里。作家通过陈仁的遭遇展现出农村贫困人口老无所依的现状;《无孔之乡》里,文香的六十岁生日十分惨淡,刚刚因为婆媳关系不和而分家;儿子儿媳不但没有回家祝寿,托人带回的一百块钱最后也被儿子收回了。文香老人的生活陷入困境。无孔之乡,也暗示着儒家伦理道德的逝去;道德模范刘春水之所以拒绝道德模范的光荣称号,实在难以承担一个家庭里两个老人和一个病人的生存压力和没老婆的苦楚(《道德模范刘春水》)。《侯己的汇款单》中,年过半百的侯己为那会属于自己的血汗钱——五百块钱的汇款单,绞尽脑汁,数次被无理盘剥,最后只剩下一张空无分文的汇款单。这些作品叙述的是底层百姓尤其是农村孤寡老人老无所依的现实生存本相,提出了令人深思的严峻的社会问题。
有研究者认为:“晓苏对人性的拷问选择了苦难做为人性的试验场,而叙述的视角则直接来自社会的底层”[2]。这些普通老百姓叙述的普通生活展现出俗世众生的痛苦和现状。晓苏拒绝了政治化叙事和知识分子叙事,而是采用民间化叙事体验乡土,言说乡土,实践了“作为老百姓的写作”的平民立场。
二、人性立场:民间化的伦理叙事
与以血缘宗法为纽带的儒家伦理体系不同,民间伦理受到地域风俗民情的影响,形成了具有民间特色的伦理观念。与传统的儒家伦理观念相比,民间化的伦理观不刻板,不严厉,不是戒律清规,不是存天理灭人欲,不是男女授受不亲,它存在于乡野之中,以一种更加自在舒适的方式顺应了人们的生活。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中的伦理观是民间化的,不同于传统文化的伦理观念,这种伦理观是顺乎人性的,充满着一种相互理解的温情和宽容,体现了作家的人性立场。
对于性的宽容和理解,突出地体现了晓苏小说民间化的伦理叙事。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以降,性描写越来越频繁地出现在中国当代文坛,甚至形成了一股强劲的欲望化叙事潮流。作家们纷纷通过欲望叙事来探讨人性。贾平凹的《废都》中性描写体现了转型时期知识分子的精神危机与人格迷失;余华苏童们通过写性探索人类的生存状态;王安忆的“三恋”、铁凝的“三垛”借助性揭示女性的生存本相;迟子建通过性叙事展现人与自然的和谐;林白陈染们通过性探索女性的成长秘密和自我价值……作家们看起来是写性,实则通过性描写或者反叛传统,或者揭示人性之恶,或者批判现代文明,或者宣扬女权主义等等,不一而论,使性描写具有形而上的意义。晓苏油菜坡系列小说的性叙事则体现了民间的伦理观念。
文学评论家金立群认为:“晓苏的小说,往往有着表面的情节的趣,而且取材往往带点‘色’,既令人啼笑皆非,又可使人想入非非”[3]。《钟点房》就讲述了一个带着“趣”带点“色”的故事,让读者忍俊不禁。40多岁的表哥杨官还是个单身汉,没尝过女人的滋味,因为偷看赵必为老婆屙尿,被赵必为打破了额头。“我”不但没有批评表哥 “有伤风化”的恶劣行径,反而大骂赵必为“饱汉不知饿汉饥,连起码的同情心都没有!”[4]真是让人又好气又好笑。晓苏给荒诞的行为配上义正言辞的辩解更增添了小说的“有意思”。 最有代表性的小说是《光棍们的太阳》,这篇小说的情节其实就是出轨和偷情,最有意思之处就在于作家并没有站在道德制高点批评谴责他们,反而以一种戏谑幽默的语调寄予同情甚至理解。小说开篇坦言:“假如没有黄娘,油菜坡的光棍们真不知道该怎么活下去”,既令人惊愕,心生疑虑,又活泼有趣,哑然失笑。这样有悖常理的行为,读者自然也想看个究竟,弄个明白。原来黄娘出轨偷情的背后是出于对光棍汉们同情。甚至在丈夫死后,黄娘表示立志不嫁,不是出于对丈夫的忠贞,真实的原因是:“我嫁人了,油菜坡这么多光棍怎么办?” 黄娘就这样成了光棍们的公共情人。这情节既荒唐又实在,在看起来荒诞不经的背后隐藏着人性的善良与宽厚。这样一种在传统伦理体系中不被接受和理解的生活,对于黄娘和光棍们来说,却是那样的简单自然、善良快乐,是失去了人性禁锢后无拘无束的生活状态。与此类似的小说还有《松油灯》、《送一个光棍上天堂》等,讲述的都是光棍们的性苦闷与女人们的性同情,在艰难生存的底色中抹上了一点人与人之间相互慰藉的温暖和人性的光亮。《打飞机》中,“我”花费五百块钱,促成傻哥哥和黑耳之间的性交易,才真正使哥哥四十八年来第一次有了性经验,使得这个娶不上老婆的傻哥哥开心不已。这场违背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性交易背后,却蕴藏着人和人之间的同情关注,以及对于人性复杂性的普遍观照。韩修竹之所以能够原谅甚至怂恿丈夫与朱碧红的私情,也是亲眼见识了守活寡的朱碧红艰难度日后,产生了怜悯之心(《养驴的女人》)。《松毛床》里,老碗一生风流成性,竟引以为豪;甚至在她六十岁生日的时候,无上光荣地邀请她的三位情人到场讲述她和他们在松毛床上的故事,旧梦重温。小说情节令人啼笑皆非,故事性与趣味性融为一体,并无道德审视和批判。
晓苏写性不为性,而是为了写人性,通过直击心灵的性描写,晓苏想探寻的是性背后的心理基础——人性的力量,比如温暖、同情、宽容,尤其是打破伦理道德桎梏后人性的自然率真。正如晓苏在接受采访时说:“文学是人学,作家纯粹的写作立场应该是人性立场。”[4]晓苏本着人性立场,将同情的目光投向了乡村的弱势群体, 在否定物欲主义的同时他对于性的宽容和理解,折射出作家的人性立场和人性反思的光芒,也体现出作家的悲悯情怀和底层关怀。
三、小说叙述的可读性
小说叙述的可读性,是民间化叙事小说的重要特征。小说的“可读性”看似浅显,但要真正实践起来确非易事。可读性既包含但又并不完全等同于通俗性、故事性,可读性还应该包含意趣的成分,也就是晓苏一直倡导的“有意思”。关于这个问题,晓苏有过细致的阐述:“好读并不完全等于可读,它只是可读性的一个方面。可读性的另一个方面还要耐读,即耐人寻味、发人深省、常读常新、百读不厌等。因此,可读性实际上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好读,二是耐读。只有即好读又耐读,小说才具有真正的可读性,即对读者既有暂时的吸引力又有长久的诱惑力。”[8]晓苏的小说创作实现了他的“可读性”理想,他的油菜坡系列民间化叙事小说非常融洽地处理好了好读与耐读的关系。
晓苏的小说叙述充满了通俗性、故事性,保证了小说的好读。小说的通俗性、故事性,本是中国古典小说的传统。但一直以来深受老百姓的青睐,为小说这种文体增添了更广泛的读者和听众,小说也具有了更普遍的群众基础。晓苏小说通俗易懂。作家既拒绝了政治权利阶层的话语权力,也没有了知识精英阶层的启蒙精神,从平民立场出发,贴近百姓生活,叙述的都是油菜坡普通老百姓喜怒哀乐的日常生活,描绘出了一个原汁原味的民间世界。
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故事性很强,他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里“讲故事”的手法,巧设环扣,引人入胜,常常让读者爱不释手欲罢不能。首先是他善于在情节模式上制造出峰回路转跌宕起伏的效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桠杈打兔》里的毛洞生年满六十岁,本来可以领取养老金,但身份证上只有五十五岁,这就使他的养老金领取之路一波三折。先是因为没有证明和原始证据,派出所不肯更改;接下来为要寻找原始证据还得找到当年的集体户口本,甚至给姜广财100块钱只为借手机拍下他出生时石洞上的生辰八字。就在即将大功告成的时候,毛洞生却出乎意料地突然放弃了。《侯己的汇款单》, 侯己五十岁了却依然靠煤矿打工艰难度日。干的最苦的活儿,吃的最差的伙食,省事俭用攒下五百块钱。为保险起见,他以自己为收款人汇款回家,结果还是被儿媳妇、邻居等以各种名目敲诈得一干二净,最终还是落了个一文不名。《嫂子改嫁》中,围绕嫂子和哥哥、小叔子之间的关系从扑朔迷离到真相大白,最后出人意料,情节扣人心弦。这些作品情节模式的峰回路转跌宕起伏,无疑形成了晓苏小说的故事性。其次,晓苏善于处理小说的结尾,常常是看起来出人意料,细细想来却又在情理之中,让读者禁不住拍案叫绝。《桠杈打兔》的毛洞生为领取养老金更正自己的真实年龄,四处奔波,大费周章,结局却出人意料:他放弃领取养老金放弃更正自己的年龄。原因却也在情理之中:如果他的养老金手续办成了,估计也跟姜广财一起在领取养老金的路上骑摩托车摔死了。陈仁投井之前一直宣称要投仇人家的井,最后却死在自家的浅井里,是因为陈仁本性的善良所致(《陈仁投井》)。余勒专程回乡给丈母娘祝寿,却连丈母娘的面都没见着,因为他在丈母娘家赌博斗殴被警车带走了(《给丈母祝寿》)。邹少芸为寻找失踪的小姑子刘贝,历尽艰辛找到后却发现刘贝根本不愿意回到穷困的家里;她牺牲自己的身体拼命保护刘贝不遭受匪徒的蹂躏,殊不知刘贝早已失去了少女的贞操(《姑嫂树》)。《养驴的女人》韩修竹最后主动把自己的丈夫推向了她曾经最痛恨的守活寡的朱碧红,恰恰是源于女性生存艰难的恻隐之心。谷婶越是反对谷珍去骗色的谢去病那里除癣,谷珍反而真的与谢去病有了私情(《除癣记》)。《等冯欠欠离婚》里,杨耕田等了冯欠欠五年,为冯欠欠作出了巨大的付出,而临近结婚的时候,冯欠欠却投入了别人的怀抱。仔细读来,作家早就草灰蛇线:冯欠欠是一个“物质主义”者。《回忆一双绣花鞋》的真相大白后出乎所有人的意料:原来是在她看来最不可能与温九有私情的妇女主任秋红送的!晓苏很擅长运用这样惊人的结局来解开谜底,既意外有意内,在你想不到的地方展现生活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
晓苏的油菜坡系列小说叙述的是普通生活,但就是这些平淡无奇感性具体的日常生活在晓苏的笔下变得饶有趣味。这样的生活趣味,看上去没有什么深奥之处,但仔细琢磨,却无不透出生活本来的原汁原味,充分保证了小说的好读。
如何葆有作家的创作个性与风格,晓苏有自己的思考。晓苏一直倡导 “有意思的阅读”[6],这源于晓苏本身就是一位“有意思的”作家。这种“有意思”渗透在晓苏的民间化叙述中集中表现为小说的耐读:耐人寻味、发人深省。
晓苏小说大体上写出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意思和意义。
一是写人性的,既有人性的复杂、冷漠,也有人性的单纯与温暖。《花被窝》、《养驴的女人》《花嫂抗旱》等写出了人性的矛盾、渴望与温暖。《看稀奇》写到了人性的激活和沟通。晓苏很多作品是写性的,如《光棍们的太阳》《打飞机》《风流老婆》《回忆一双绣花鞋》《松油灯》等等。写性也是为了写人性,晓苏为此专门谈论过写性的意义所在:“性是人生的重要内容,作为反映人生的文学,不可能不涉及性。……我觉得性是人性中最幽深、最诡谲、最迷人的部分,如果要让自己的作品具有人性的深度,闪烁人性的光芒,那你就得直面性这个敏感的话题,大胆地写性,严肃地写性,艺术地写性。”[4]
二是传达对于传统乡村和人伦情感的认同与眷念。如《麦芽糖》虽然没出息却十分孝顺;《卖糖记》中的“我”设法弥补自己的过错,最终获得了他人的谅解。岁岁最终嫁给卖卤菜的李学乖是因为他的忠厚善良(《卖卤菜的李学乖》)。在伦理失范的乡土文化中,传统的美德才是晓苏无比怀念的道德规范,才能获得晓苏的认同和眷恋。
三是对于传统乡村伦理失范的审视与忧虑。在乡村的现代化进程中,现实的乡村面临着传统伦理秩序的全面崩塌,新的伦理关系已经取代了传统的伦理关系。乡村已然成为新的利益场,充斥着金钱的铜臭,满溢着物质的欲望。记忆中关于乡村的美德:孝道、亲情、勤劳、诚信全都荡然无存,昔日情同父子的师生关系如今也难逃权势与功利的侵蚀,人情亲情转化为物质金钱关系,面对这一切,作者的痛心与无奈溢于字里行间,读者也禁不住会扼腕叹息。
小说源于生活,晓苏小说的意义就是发源于生活的纷繁复杂。“正是生活中的暧昧、含混、矛盾、神秘引发了我写作的欲望和冲动。这样,意义便是从题材中自然生成的,而不是由外部强加的。它是生成的,我怎么真实怎么写,怎么人性怎么写,怎么舒畅怎么写。”[7]这是晓苏的夫子自道,我们也由此体会出小说意义的产生。而这些意义的阐述又充满通俗性、故事性,既保证了小说的好读,又凸显了小说的耐读,也就是说,晓苏小说既有意思也注重意义的建构,二者浑然一体、水乳交融:“意思中有意义,意义中有意思”[8]。
於可训曾经这样评论晓苏的作品:“他的小说的故事不纯粹源于他的个人才能,而是民间精神在小说创作中的一个突出表现。”[9]晓苏教授生在农村,长在农村,丰富绚丽的民间文化滋养了他,并且成为他的文化底色,于是民间叙事便成了他小说创作最浑然天成的叙述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