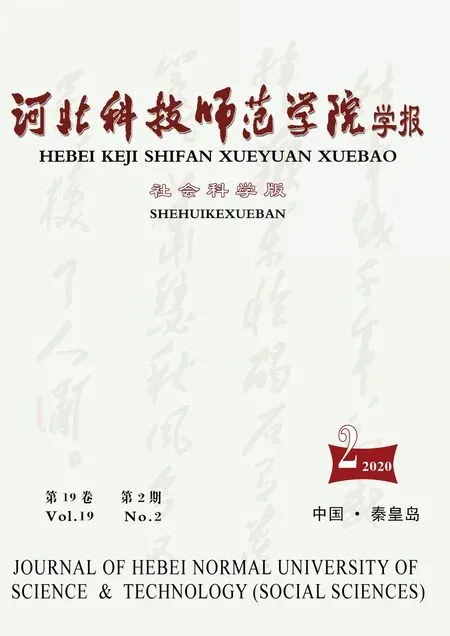《伤逝》作为悲剧艺术的张力书写
李梦莹
(安徽大学 文学院,安徽 合肥 230039)
《伤逝》是鲁迅唯一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自问世以来一直受到学界的关注。在《伤逝》的解读中,研究者多从爱情悲剧的角度入手,探究其爱情失败的原因;或者从文章的叙事角度进行分析,探讨涓生作为第一人称叙述者而引发的关于两性关系的思考;亦或联系作者的生平,将其视作兄弟之情或与其伴侣关系的隐喻描写,以上的论文观点却忽略了文章作为悲剧艺术本身所具有的美学意义。 “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在黑格尔看来,矛盾不仅使事物充满生机,而且还是其前进发展的动力,在悲剧中,正是由于不同伦理力量之间的较量和冲突,其情节才得以展开。而悲剧人物之所以具有悲剧性,不在于他被恶统治着,而在于他们各自坚持自己所代表的具有片面性的伦理力量时,一方为了实现自己所代表的伦理力量而要毁灭另外一方。《伤逝》中借涓生爱情的幻灭过程来书写特定时代下知识分子建构理想世界所面临的来自外部以及内部伦理力量的矛盾冲突,在表现新一代知识分子为实现自己的欲求遭致来自社会、文化传统以及主体精神世界的压抑而惆怅痛苦时,又彰显了人的生命意志在进退维谷的矛盾冲突中所迸发的生命欲求和进取精神。正因为如此,《伤逝》作为悲剧艺术在内涵与外延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
一、永不破灭的希望:在现实中的求存
在《伤逝》中,造成新一代知识分子精神困境的首先来自于理想与现实之间矛盾。鲁迅在《伤逝》中以涓生爱情的发展轨迹来诉说时代困境下知识分子的挣扎和彷徨,在理想与现实不断交叠下,他们成了两难处境中的悲剧式人物,一方面是新思想滋养下不断涌现的美好理想,一方面是来自现实的严酷打击。
从涓生的精神世界来看,他反对家庭专制、倡导男女平等、婚姻自由,是当时时代影响下先进思想的代表,然而他的悲剧性也源于此。具体来说,要实现历史的必然要求和这个要求实际上不可能实现的悲剧冲突之间构成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生活其中的“涓生”们作为时代的先锋者,一方面受到来自现实环境的重重阻碍,萨特的存在主义观点就将“他人”与环境当成各种各样的“异化”,其是对个人的压抑性力量,一种令人讨厌的“粘液”,并处处限制人的自由的“他者”……想要摆脱它、却又无法脱身[1]。涓生与他所生活的现实环境便处于这样一种境况,即他与现实已融为一体,但目标的理想性却又要求他摆脱现实环境,而现实又时时缠绕着自己,阻饶着自己,最终成为实现理想的一种压抑性力量;另一方面,以涓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企图改变现状的理想本身就带有悲剧性。“在黑格尔看来,真正悲剧的灾难,却完全作为本人行动的后果,落在积极参与者的头上,他们本身既是悲哀的制造者。”[2]112黑格尔将社会性的普遍意义寓于个体体验当中,以具体的人的体验来揭示抽象的悲剧命题,而涓生的艺术形象则是当时普遍状态下知识分子悲剧的缩影,从“涓生”作为个体的生存悲剧中窥探人类悲剧性的根源。他们是时代的先觉者,虽看到了未来新希望的曙光,但通过一番挣扎后,却发现无力改变现状的残酷事实,由此造成了知识分子苦闷的精神困境。
在涓生的会馆处所里挂着雪莱最美的一张半身像,代表浪漫主义思想的雪莱形象是涓生对新生活充满无限希望的化身,而渴望实现自由浪漫的爱情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理想世界中一个象征性存在。涓生的手记中,我们看到的是知识青年涓生在失去爱情后的内心独白,他在手记的开头讲到:“如果我能够,我要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3]109涓生在追求爱情失败后只剩下寂静和空虚,而为爱情出走的子君则走进了“连墓碑也没有的坟墓”,这是双方在憧憬美好爱情时所不曾料到的,然而却不能由于当事人的主观意愿而避免这种悲剧性的结局。在恩格斯看来,任何悲剧都是社会的、历史的,只有从当时的具体历史条件和社会生活出发,才能予以说明。
涓生的爱情理想遭到失败,是由特定的历史环境和个体主体两部分,即外部冲突和内部冲突两方面造成的。一方面,新思想的传入并未给国人带来思想上的大变革,而接受者多为在新环境成长下的知识分子、留学生,而文中出现的“雪花膏”、子君的叔父等都是旧思想的代表,这也说明构成实现理想的现实阻力之大;另一方面,悲剧人物在实现理想过程中所暴露的个人局限性形成了人物悲剧命运的内因,涓生虽受新思想的洗礼,然而对于爱情却难以有清醒的认识,从而暴露出其思想上的片面性。在浪漫主义知识分子那里,“他们往往只是按照他们对爱情和生活的单方面期待及幻想来面对他人,要求他人,成为自我欲望的满足,从而失去了与他人之间的相互性关系”[4],思想上的片面性使得涓生的爱情理想在与现实发生冲突时,形成两人悲剧性的结局。“而较之单纯地由他人所给予的灾难,由于自身原因而引起的重大的不幸才是更深刻的悲剧”[2]114,涓生在手记的末尾写道:“却不过是写下我的悔恨和悲哀,为子君,为自己”,涓生虽然逃离了“吉兆胡同”,却陷入了更大的悲哀当中。在叔本华看来,任何人都无法逃脱由自身编织的罗网,而破坏幸福和生命的力量无处不在、无时不有,每个人随时都可能同时充当悲剧的制造者和悲剧的承担者,涓生的逃离以及逃离之后的空虚便带有这种叔本华式的悲剧色彩。
《伤逝》作为悲剧艺术作品,一方面,作者借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幻灭揭示了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由于现实与理想间难以调和的矛盾所造成的人物悲剧;另一方面,作者通过矛盾冲突为文本意义的解读创造了更大的阐释空间。在艾伦·退特《论诗的张力》中指出:“我所说的诗的意义就是指它的张力,即我们在诗中所能发现的全部外展和内包的有机整体”[5],而《伤逝》则透过两人的爱情揭示出在故事深层一场理想与现实矛盾的双重交叠。在严酷的现实中,涓生带着知识分子对未来的希望,带着子君,逃离会馆,逃离寂寞和空虚;在与子君组建新的家庭时后,当知识分子涓生为奔向新生活而扇动翅子时,每一次都以失败告终,但是作为悲剧的主人公,却依旧向往着新的希望,涓生在手记中写道:“我活着,我总得向着新的生路跨出去。”[3]130在现实与理想这对矛盾因素中,“我”没有就此向残酷的现实低头,而是在经过现实的洗礼后,重新整装出发,继续前行。
二、 两种声音的对抗:传统与现代
在易卜生的《娜拉》被翻译到中国之后,鲁迅等人关于“娜拉出走之后”进行了大范围的讨论,鲁迅认为接受了新思想而出走的女性“不是堕落,就是回来”,来自外部世界的压力以及自身思想的局限性成为新一代女性难以摆脱悲剧命运的重要因素。可以说,在新旧交替的时代背景下,女性的生存境况是带有悲剧色彩的。五四运动后新思想随之在中国掀起热潮,中国传统文化面临着挑战,几千年来处于正统地位的儒家文化成为新一代知识分子批评的对象,而这时鲁迅却在新思想热潮中进行了“冷”思考:即对待中国传统文化遗留物是否要一味舍弃,对待新思想是否要全盘接受,在《伤逝》这篇爱情题材的小说中,子君和涓生的爱情悲剧便是鲁迅对于那个时代思考的缩影。
《伤逝》中子君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所诞生的悲剧人物。子君在遭到涓生的遗弃后走向了死亡,构成子君悲剧性的源于现代与传统两种力量在子君思想中的冲突所构成的张力。“在黑格尔看来,这种冲突中对立的双方各有它那一方面的辩护的理由,而同时每一方拿来作为自己所坚持的那种目的和性格的真正内容的却只能把同样有辩护理由的对方否定掉或破坏掉。”[6]子君是深受传统与现代两种思想影响的人,一方面她生长在有着根深蒂固的中国传统思想的土地上,另一方面,她又受到新思想的熏陶,强烈要求摆脱现实生存环境,因此子君身上体现出传统与现代两种思想的对抗和冲突。
首先,子君作为不彻底的思想革命者和不彻底的传统拥护者本身就是悲剧。在子君的性格形成中她始终被现代性和传统性这两种声音所支配,在与涓生聊男女平等、家庭专制时,她说:“我是我自己的,他们谁也没有干涉我的权利”,涓生作为浪漫主义知识分子自然是欣喜的,因为他看到了中国女性在接受新思想、反专制方面是极有希望的,解放封建下的中国是“要看见辉煌的曙色的”,这正与他们在五四时期进行思想启蒙的愿望相契合。然而,同居后的涓生并没有如他所愿逃离寂静和空虚,而是陷入了更加异样的寂寞和空虚。通过文本细读,可以发现,回归家庭的子君与涓生在生活中出现了分歧,涓生喜欢带有浪漫气息的花花草草,而子君更钟意于有生活气息的油鸡和叭儿狗;子君为叭儿狗取名“阿随”,其中这个“随”字有跟随、依附的意思,表明她并没未从依赖他人的思想中独立出来,暴露出思想革命的不彻底性。正是由于子君思想上的不彻底性,造成了她在从私人的家庭空间走向社会公众空间时,自我身份转变的失败,即靠着旁人走出“父权”之家的子君,凭着自己却难以走出“夫权”的家。
其次,涓生所导向的思想启蒙与子君所导向的生活启蒙之间的矛盾冲突形成了两人之间真正的隔膜,并最终导致了子君的死亡。与文章《娜拉走后怎样》相同的是,鲁迅在《伤逝》中所关注的并非是爱情如何发生,而是爱情发生后会如何的问题,出走后的子君也如娜拉一样,等待她的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的悲剧命运。 “划分一个社会制度、一个阶级、一个事变或一个人物是悲剧阶段,还是喜剧阶段,最根本的标志是历史存在的‘合理性’。”[2] 110-111显然,在新旧交替的特定历史下,无论是传统思想还是受西方影响的新思想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当两者交织在一起时,企图改变对方而单方面服从自我意愿的尝试注定是失败的。一方面要认识到涓生所导向的思想启蒙者试图将子君改造为新历史时期下的“新人”的进步性,即“从传统的礼法道德、风俗习惯等层层束缚解放出来,成为西方现代文化标准下所定义的‘人’”[7];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子君身体力行用生活启蒙的方式追寻爱情的合理性。与涓生完全受西方思想影响而展现出的过度理想主义、自私、缺乏责任感相比,子君身上则呈现出带有传统色彩的一面。她专注于对生活的营造,更加务实和关注眼前,她辛勤操持家务,虽没有为家庭带来直接的经济补贴,但她却力所能及地为家庭付出,甚至在即将离开时仍在努力维持对方较长的生活。涓生的不理解使子君的死亡成了必然,子君用生活启蒙来维持两人较长爱情的努力在涓生这里却形成了两人真正的隔膜:“子君的功业,仿佛就完全建立在这吃饭中。吃了筹钱,筹来吃饭……”[3]118
子君的悲剧是五四新思潮退潮后鲁迅对关于现代与传统思想冲突的反思。在去往“新的生路”上,涓生所代表的处于西方文化视野下的新一代知识分子企图用思想启蒙的方式解放国人,但在他们呼吁男女平等、女性独立时,并未能认清社会发展的特殊性所在,一方面中国传统思想在新的历史环境下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在西方民主自由思想传入中国后,应对中国传统持相互融合、取长补短的态度;另一方面他们忽略了人所赖以生存的实际社会状况,即对于女性解放而言,她们是否具备独立的条件和地位、出走后的女性如何重新确立身份等。子君自身性格上两面性以及与涓生所代表的新思想的悲剧冲突构成了一种张力效果,即子君的悲剧命运所唤起的国人对传统与现代的深刻反思以及关于传统的时代意义和价值的思考。
三、未来之路的抉择:埋葬真实
是否要告知民众冲破铁屋子的问题常常使鲁迅陷于真实与谎言的矛盾之中,因此,是将残酷而没有希望的现实告知民众还是继续让其在沉睡中死亡成为鲁迅小说探讨的另一个重要主题。在《药》《祝福》《孤独者》等小说中展现了鲁迅内心的艰难选择,彷徨和犹疑构成了知识分子精神上的困境,对于那个特定时代而言如何选择都将构成一出悲剧,正如在《死火》中所说,被惊醒的死火倘若继续留在冰谷必将冻死,而要将其带出,则会燃尽。
面对种种矛盾的对立与冲突,黑格尔提出,当矛盾的双方由于陷入片面性而各执一端时,唯有通过他们的毁灭才能否定各自的片面性,使冲突得以解除,从而体现出普遍意义的伦理力量的胜利。在涓生与子君的爱情幻灭过程中,子君的结局宣告了在两人所代表的不同的思想观念相互碰撞时,一方以死亡的形式暂时缓解了矛盾冲突,但对于涓生来说并却未达到真正意义上的矛盾和解,真正的和解则来源于自我思想层面上。具体来说,再次回到会馆时的涓生其时并未摆脱静寂与空虚,反而由此陷入了更深的精神危机之中,子君的死使得涓生看到深层的矛盾来自于自身精神世界中对未来的犹疑和彷徨。在《伤逝》中,这种矛盾的化解体现在知识分子涓生对“真实”的认识上以及在得到“真实”后却选择用“谎言”来继续负重前行的思想升华。
首先是在对“真实”本身的理解上。伴随着爱情的幻灭,涓生对“真实”的理解逐渐清晰,两人刚交往时涓生虽处在寂静和空虚中,然而却是常含期待的,涓生在子君身上看到了在不远的将来中新希望的曙光,然而他逐渐意识到两人同居并非想象中那么完美,不过三星期,涓生在手记中写道:“我也渐渐清醒地读遍了她的身体,她的灵魂”[3]119,子君从偶像的位置中跌落,成了涓生眼中真实的凡人,子君不停地做着家务,操持着饭食,同涓生心中的反家庭专制、雪莱、易卜生等浪漫主义理想背道而驰。此时,他的精神世界是痛苦的,在理想遭到外部因素的破坏后,他写道:“这是真的,爱情必须时时更新,生长,创造”,在遭遇偶像破灭后,他的思想逐渐成熟。被浪漫主义驱动的知识分子在这里遭到了现实打击,随着对现实的不断认识,他开始理性对待与子君的爱情。从另一方面来看,涓生在意识到必须将真实说给子君后,却没有对眼前的困境指出一条明确的出路,从而直接导致了子君负着空虚的重担走向死亡,这也暴露出新的革命力量在诞生之初思想上不成熟、不理智的特点。
其次是在对“真实”态度的转变上。涓生在生的路上,却选择以遗忘和说谎为向导,继续前行,这与鲁迅之前在小说中对真实的态度形成了反差。总的来说,鲁迅的态度经历了一个从坚定真实到徘徊于真实与谎言之中再到选择带着谎言“走”出去的变化过程。鲁迅在《呐喊》自序中曾说道:“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绝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8],此时的鲁迅坚定地站在了真实的一面。在《药》中鲁迅通过乌鸦“铁铸一般站着”的姿态表达了对谎言的否定,而在面对祥林嫂是否有灵魂与地狱的疑问时,“我”却选择了用“说不清”来回答她,他说:“人生最苦痛的是梦醒了无路可走。……倘没有看出可走的路,最要紧的是不要去惊醒他。”[9]显然在经历了“冲破”铁屋子的呐喊之后,鲁迅在未来之路的选择中陷入了彷徨和犹疑。
面对“真实”与“谎言”的两难之境,鲁迅最终在寻找自由之路中选择了虚无。萨特在《存在与虚无》中认为,真正自由的人,在他所能实现的个人存在中,必须尽可能寻求一切机会使自身的意识“虚无化”,因为意识的虚无意味着它不受任何限制,它要做什么就做什么。与之前的文章相比,鲁迅对于真实的理解更加趋向理性和复杂,他既看到了真实的必要性,同时又意识到其存在的局限性,在理想与现实、传统与现代、真实与谎言等种种矛盾交织中,鲁迅并未在客体环境中寻找到真正的解药,而是通过以主体思想上的虚无来摆脱困境、寻求自由。与萨特所不同的是,鲁迅的虚无之路是被动的、别无他法的。在《伤逝》的结尾处,鲁迅借涓生之口坚定了人活着必须跨出去的目标,而跨出去的第一步却要将真实埋葬,将谎言作为前导。
结 语
《伤逝》虽是以爱情为题材的小说,但其主旨并没有局限于描写知识分子的爱情幻灭,第一人称下的忏悔性自述,揭示了涓生等知识分子从幼稚逐渐走向成熟的思想历程,在理想与现实、现代与传统、真实与谎言等矛盾的交织下,彰显了其作为悲剧艺术的张力之美。在理想遭到幻灭后,以涓生为代表的知识分子选择向着空虚和寂静的前方继续前行;当现代知识分子决定与传统彻底诀别时,却发现在传统中仍有其合理性的一面;在与谎言不断的抗争中,鲁迅看到人活着就必须向前迈进的残酷事实,而谎言却是通向前路的向导。在时代与理想不可调和的矛盾中,首先觉醒的人必是痛苦的,他们生活在新旧交替的时代下,其精神上的痛苦和彷徨不仅展现出个体主体的悲剧性,更显示出人在悲剧面前顽强向上的斗争精神,而悲剧的美学意义也在于此,它既包含着人受到历史环境而感受到的痛苦的精神体验,同时又显示出人在困境的迷雾中所迸发出的积极向上的进取意识,能够在充满张力的内外矛盾中彰显出悲剧艺术本身独特的美学价值和时代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