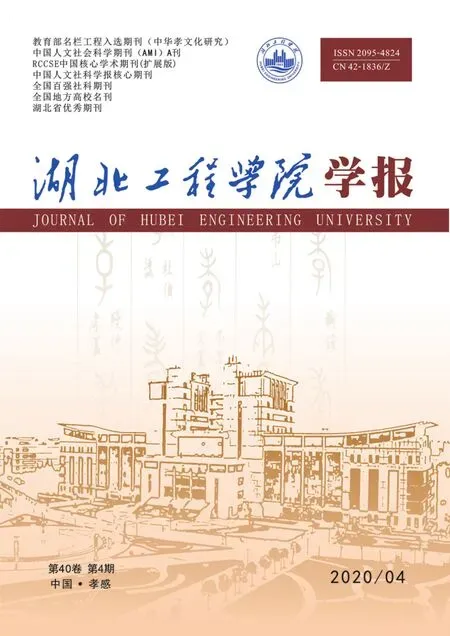《红楼梦》对才子佳人小说中“艳遇”模式的超越
李玉箫
(中南民族大学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4)
爱情故事一向是古代戏曲的常见题材之一,明代更是出现了《紫钗记》《玉簪记》《娇红记》等一系列以才子佳人为主角的传奇剧目。自《金瓶梅》流行开来之后,一系列由文人创作的世情小说纷纷问世,这些作品所叙,“则大率才子佳人之事,而以文雅风流缀其间,功名遇合为之主,始或乖违,终多如意,故当时或亦称为‘佳话’”[1]。“才子佳人”遂成为古代小说戏曲的一个常见题材,这类故事在表达上形成了固有的模式,为后来的作品所承袭。《红楼梦》中,不论是占去较大篇幅的“宝黛爱情”,还是其他角色的情爱纠葛,在表现上都多少受到旧有模式的影响。
探讨《红楼梦》与传统才子佳人小说的关系的作品已经有很多。刘雪莲认为,《红楼梦》在小说开端和故事演进中,都应用了才子佳人小说中“一见钟情”的相见模式,并将其转化为一种叙事策略。[2]蔚然认为,《红楼梦》中存在着大量才子佳人小说中爱情符号形式,如赋诗、赠物、 感梦、交谈以及婚礼仪式等,并在吸收这些元素的同时有所创新。[3]王颖认为,对大团圆结局的摈弃使得《红楼梦》完成了对传统小说思维、民族文化心理、审美习惯和欣赏情趣的突破。[4]
“艳遇”是一般才子佳人故事中的一个固定模式。在《红楼梦》中,曹雪芹完成了对“艳遇”模式的超越,使得它完全脱离了“才子佳人”的窠臼。
一、从“完成的”到“未完成的”:“艳遇”模式的演化
对“艳遇”的想象本来不止文人所有,民间故事中也有不少“花园会”“楼台会”“书房会”的桥段。不同的是,民间故事往往以节夫义妇终得善果或者淫乱不节之人遭到现世报应的结局完成劝诫的目的,而文人在写作中着力于“艳遇”本身,“终成眷属”不过是例行公事的大团圆结局,重头戏实则在“琴挑”和“佳期”。
小说戏曲中的“艳遇”本身是不合礼法的。民间故事一面热衷于大肆渲染艳情的情节,一面又以现世报应惩罚男女主角——尤其是女主角,如《玉蜻蜓》《阴阳河》《大劈棺》等。文人则在作品中有意地暂时忽略礼法,专心风月,先令男主角在“真空”的环境中完成一次“艳遇”,在故事结束的时候给男主角安排一个功名,就可以掩去之前的一切不道德从而堂堂正正地迎娶佳人。
“真空”环境中的女主角一定是孤独的,或者待字闺中——身边唯一的侍女还是男主角的盟友,比如崔莺莺;或者就是尼姑,如陈妙常。女主角绝不会见到男主角之外的第二个男人,她的父亲一定不在场。这些发生在“真空”中的艳遇是极其不牢靠的。在这些故事中,艳遇是属于男主角的一次经验,并且把女主角变成男主角全部经验的一部分。女主角本身是没有独立的经验的,在遭遇男主角之前,她的人生是静止的,在遭遇男主角之后,她的人生就仅仅是男主角经验的一部分。男主角在离开这一个佳人之后,还可以遇见下一个佳人,假使赶考的路途足够遥远,他可以遭遇无数个类似的艳遇,他也可以将其中那些孤女一般的佳人忘在脑后而不必承担任何责任。一个特定的男主角匹配一个特定的女主角,“艳遇”发生且仅发生一次,这一存在于《西厢记》《玉簪记》等才子佳人故事中的“大前提”其实是站不住脚的。
之后的文人作者显然意识到了这一漏洞,所以他们在故事中强调“一见钟情”,并努力地将其上升到“精神”层面。在一些平庸的故事里,男女主角即便处在符合发生艳遇的“真空”环境里,物理事实上的“艳遇”却被取消了,男女主角仅仅简单地交换信物,通常是诗文、扇子、首饰、佩剑等,且不一定由本人出面,就实现了终身的约定。这一约定将成为全书中男女主角之间唯一的情感纽带。
囿于礼教,文人不能同民间艺人一般直白地表露自己对于情爱的想象。“艳遇”在文人笔下最终演变成一个极为奇异的模式,即“未完成的艳遇”,它的出现来自于原始冲动,而它在文本的呈现中又刻意回避着原始冲动。由于小说没有必须搬上舞台、博人眼球的需要,故而“未完成的艳遇”更多地出现在小说当中,最终使其彻底成为了僵化的案头之作。
二、反复出现的“艳遇”:承袭之下的突破
“满纸潘安子建、西子文君,不过作者要写出自己的那两首情诗艳赋来”[5]3,《红楼梦》开篇就一语道破才子佳人小说作者的心事。然而“艳遇”模式的起源并非完全不合人情,种种叙事模式的确立也表明,长篇白话小说的创作技法已经成熟。曹雪芹选取小说这一体裁,就意味着他不得不受制于创作中的既定规则,“艳遇”也就成为他在叙事中不可规避的情节。在对男主角贾宝玉的塑造上,曹雪芹一面承袭了“艳遇”模式,一面又故意在具体呈现上打破其中的既有规范,使贾宝玉的形象有别于一般意义上的“才子”。
首先,贾宝玉遭遇过不止一个“艳遇”对象,譬如梦境中的秦可卿,现实中的袭人、秦钟、蒋玉菡、金钏、晴雯等人。这就打破了才子佳人小说中,才子在“一见钟情”之后便毫无二心的规律。不仅如此,贾宝玉和理应是“佳人”的林黛玉之间却始终没有发生“艳遇”。
其次,单独看待贾宝玉的每一次“艳遇”,仍能看到曹雪芹对既有规范的嘲弄。比如,“梦会”本来是才子佳人小说中主角才能够享有的“特权”,但在第五回里,贾宝玉梦中欢会的对象却是秦可卿。纵观《红楼梦》前八十回,曹雪芹都没有直接描写宝黛的“梦会”。又如,在现实中与贾宝玉“初试云雨情”的,恰恰是在价值观上与他极其不相合的袭人。再如,与蒋玉菡、金钏的“艳遇”,都因外界的突然干预而中断,并最终给贾宝玉带去灾祸。
再次,这些“艳遇”是属于贾宝玉的,但“艳遇”的对象却不是贾宝玉经验的一部分,也不是林黛玉的陪衬,而是独立的个体。对于现实中的秦可卿而言,贾宝玉只是同自己兄弟年纪相近的孩童;对于袭人而言,贾宝玉则是生存的倚靠;在金钏和晴雯的心目中,对贾宝玉的好感远远不及人格尊严重要。曹雪芹通过这些人物的塑造,揭示并消解了“艳遇”模式中所隐藏的具有男权色彩的想象。
三、“木石之盟”的订立:对“艳遇”模式的超越
全书的女主角林黛玉,自然不是贾宝玉的附属品,她有自己独立的经验。作为贾宝玉的爱人,她无依无靠,行动范围狭窄,除去贾宝玉几乎对异性没有认识,符合成为才子佳人故事中“佳人”的所有客观条件,却从来没有成为贾宝玉“艳遇”的对象。在第三十二回宝黛互相剖白心迹之前,曹雪芹不止一次将两人置于“真空”的环境里,细细描摹两人独处时的情状,丝毫不回避两人间有逾礼数的行为,尤其是贾宝玉面对林黛玉时情不自禁的举动。通过这些宝黛独处的情节,“木石之盟”在现世中一步一步结成的过程就呈现在纸上。
宝黛虽然于第三回中一见如故,但那时两人之间的感情尚且与爱情无关。第十九回中,贾宝玉趁林黛玉独自午歇时前去打搅,两人说笑嬉闹,举止亲昵,林黛玉“将自己枕的推与宝玉,又起身将自己的再拿了一个来,自己枕了。二人对面倒下”[5]158,后“因看见宝玉左边腮上有纽扣大小的一块血渍,便欠身凑近前来,以手抚之细看”,“便用自己的帕子替他揩拭了”[5]158-159,这其中并没有显出丝毫男女之间的暧昧之意,全然一副两小无猜的天然亲密之态。
及至第二十三回,宝黛二人于沁芳桥畔一同读《西厢》,葬落花。这一段情节是最可能演变成一次“艳遇”的,两人不但独处,贾宝玉还带着《西厢记》这一道具——恰如戏曲中“琴挑”一折里的琴,但曹雪芹依然巧妙地把握住了平衡,一面以《西厢记》完成了两人间对于情爱的启蒙,一面又使两人在精神上产生共鸣,令其意识到,在整个大观园甚至整个世界中,他们互相是对方唯一的知己。“读《西厢》” 作为一份宝黛共同拥有的经验,把两人间的感情从两小无猜的童年状态转入真正的爱情中去。这和将佳人变为才子的附属品的“艳遇”是截然不同的。
在此之后,林黛玉的状态就已经从“无性”转入“有性”,其形象也就随之变得更为丰富。她唯有进入“有性”的状态,才能被《牡丹亭》中的唱词深深打动,才能对着满地落红吟出“未若锦囊收艳骨,一掊净土掩风流”[5]228的诗句。此时,她的丰神终于不再仅仅为贾宝玉所欣赏,第二十五回中,曹雪芹借薛蟠之眼展现了林黛玉作为女人的风姿:薛蟠在一片慌乱中“忽一眼瞥见了林黛玉,风流婉转,已酥倒在那里”[5]209。宝黛二人间的关系也随之完全发生了变化。第二十六回中,贾宝玉信步来至潇湘馆,偶然听见林黛玉睡起时不自觉地吟咏《西厢记》中的句子,“不觉心内痒将起来”[5]216,便进去打搅,同样是打搅睡眠,两人相对的情状已经全然不同于第十九回的天真,贾宝玉化用自《西厢记》的玩笑话也就果真惹恼了林黛玉。第二十七至第二十九回间两人的纠葛,就不再是出于孩童的使气任性,而是源于恋人间的反复试探和误解。
有了之前如此细致的铺垫,待到第三十二回,宝黛二人终于互相剖白心迹,现实中的“木石之盟”就水到渠成地完全订立起来。曹雪芹通过将“一见钟情”与“私定终身”之间的时间间隔拉长,填充其中的细节,描绘男女主角之间牢不可破的爱情的具体形成过程,使得宝黛二人彻底摆脱了一般意义上“才子佳人”形象,同时也完全取消了两人间发生“艳遇”的必要性,从而完成了对“艳遇”模式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