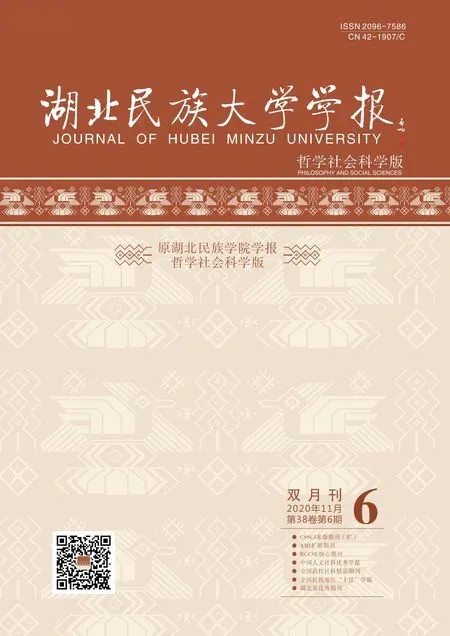“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
——以吴泽霖、林惠祥为中心的考察
张福强 高 红
随着近年来构建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呼声日渐高涨,迫切要求我们要重新回顾和反思民族学在中国的百年发展历程。其中田野调查的开展、本土化理论的提出及学科制度化的推进等,固然是学科史回顾的重点内容。但除民族志书写与理论构拟外,还存在一种可称之为“采集民族志”的学科表现形式,它与表现于文本的民族志或影像的民族志一样,同样表达着学者的理论意图及文化多样性等主题,构筑着有关民族的知识。对此类民族志形式的研究理应得到重视,并需要把它与学科发展的整体进程联系在一起。而论及民族文物标本的采集、展示等,吴泽霖与林惠祥是绝不能避开的人物,他们“南北相映”,为中国民族标本采集、展览作出了重大贡献,被誉为“民族博物馆学”的创始人和奠基人。以他们二人为中心来分析中国民族学史上“采集民族志”的演变与特征,不仅可行,而且极有意义,对于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理解中国民族学史的发展将会有所帮助,同时对于今天民族学人类学“中国学派”的构建也有裨益。
对于中国民族学史上采集实践的梳理讨论,学界已有一些成果。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胡鸿保《中国人类学史》对此多有论述,以事实呈现与贡献评价为主。以“民族博物馆”为主题的回顾展望类文章对此亦有涉及,但同样集中于事实考梳层面,此类论著为本文研究奠定了坚实的材料基础。(1)参见雍继荣:《中国大陆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历史发展》,《中国博物馆》2006年第2期;秦晋庭:《20世纪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兴建与发展》,《中国博物馆》2004年第1期;唐冬兰:《中国民族博物馆的历史回顾与现状分析》,《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等。对本文有思想启发性的文章多系近年发表。安琪以“器物民族志”的表述来分析民族博物馆中西南形象的演变,她侧重族群的社会政治背景,对于民族学史讨论并不多。(2)安琪:《器物民族志:中国西南民族博物馆与族群叙事》,《贵州社会科学》2010年第2期。张先清更进一步,把对民族文物的采集展览置于学科史中来探讨,开创性意义很大,但由于主题限制在林惠祥身上,对有些论题的分析难以全面呈现,延展性略弱。(3)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民族学刊》2016年第1期。本文即是在此基础上进行的继续拓展。此外,学界对吴泽霖采集实践与理论的研究,多数集中于事迹考梳及思想总结上,学者们更多把思想放置在个人的逻辑理路或学术背景中去考察,探寻其思想发展过程,凸显其学术贡献与学术地位,思想史意味浓厚。(4)参见温世贤、彭文斌:《传译民族文化与平等——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博物馆思想》,《民族学刊》2010年第3期;秦晋庭:《中国民族文博事业的拓荒者》,《中国民族文博》2010年第3辑;钟年:《吴泽霖民族博物馆思想管窥》,《民俗研究》1993年第1期。而对林惠祥的研究,则偏重知识社会学的范畴。学者们从博物馆人类学的角度出发,把博物馆收藏、展示视为实践活动以及具有持续性的科学与社会文化过程,探究博物馆的本质及其暗含在实践活动中的逻辑与策略。重点讨论了林惠祥的博物馆民族志书写及标本展示背后所隐藏的理论意图,还有通过林惠祥的个案揭示了标本、采集活动与采集者之间的复杂关系,等等。(5)参见杜慧、熊佩:《从民族志物品收集到东南海洋系文化构建——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1929-1958)》,《民族学刊》2016年第6期;尹凯:《林惠祥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浙江自然博物馆编:《自然博物》第2卷,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尹凯:《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1966年)为例》,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北京民俗论丛》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8页。
一、“贯穿一生”:吴泽霖和林惠祥的采集经历
吴泽霖与林惠祥作为中国第一代民族学与人类学家,他们二人对民族文物标本采集、展览的热情与执着,贯穿其学术生命的始终。在他们的学术理想中,民族文物事业须占据一席之地,文物标本的采集与展览并非拒斥在其学术体系之外,而是其中极为重要的一环,是实现他们社会理想的一个重要手段。
先从吴泽霖谈起。“吴老为我国少数民族文物事业的发展,灌注了心血和汗水,他走到哪里,就把这专业的种子撒在哪里。他是我国当之无愧的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创始人和最有权威的民族博物馆专家。”(6)费孝通:《在人生的天平上——纪念吴泽霖先生》,《读书》1990年第12期。这是费孝通借用别人的话来评价吴泽霖的民族文物事业。诚如费孝通所言,吴泽霖一生所涉学科甚广,但对文物收集的偏爱,并没有因研究的数度转向而有所废止。
吴泽霖在美国留学时对博物馆便产生了兴趣,他经常参观各大博物馆,博厄斯的博物馆理念对他也有一定的影响。1927年回国后,他的博物馆实践正式开始。在大夏大学任教时,他就在学校群贤楼二楼研究室中展览各种收集的标本。全面抗战爆发后随校入黔,对民族文物的收集成为其主要工作之一,建立了苗夷文物陈列室,三年多征集各类文物两千多件。仅1941-1942年,就举办了三次文物展览。在西南联大工作期间,吴泽霖继续致力于文物征集及展览工作。他创立的墨江和丽江边胞服务站,除日常工作外,搜集当地的民族文物也是其主要任务之一,共搜集纳西族、傈僳族和藏族文物及图片等二百多件。1948年4月29日,在吴泽霖的主持下成立了清华大学民族文物陈列室,“公开展览,使校内外人士得随时观摩。”(7)陈梦家:《清华大学文物室成立经过》,《大公报》(天津)1948年4月1日,第3版。1949年后,吴泽霖的民族文物事业进入一个新阶段。清华大学筹备组建文物馆时,吴泽霖负责少数民族组工作。在参加中央民族访问团贵州分团时,在紧张工作期间,他也搜集了大量文物,并在贵阳举行了展览活动。其后,他又被推举为中国民族博物馆筹备组主任,但筹建工作半路夭折。吴泽霖改赴西南,参加西南民族工作视察组,文物收集工作亦同步开展,工作结束后,他留在西南民族学院工作,创建了该校的民族文物室。1982年8月,吴泽霖应邀支援中南民族学院建设,并建立了“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该馆是国内第一所民族学博物馆。
吴泽霖对民族文物事业的热情,从一些小事中也可看出。西南民族学院筹建文物室时,他把珍藏的价值超千元的文物毫不声张地捐献给学校。1990年患重病在病榻上,还写信给潘乃谷,向其叔潘光迥借钱购买工作人员在湘西发现的古床。他对民族文物工作终其一生都保持饱满的热情,经常废寝忘食地工作,在《吴泽霖执教60年暨90诞辰纪念文集》一书中,有许多同事、弟子对此多有回忆,在此不再赘述。
林惠祥出生于1901年,福建晋江人氏,1926年毕业于私立厦门大学,留校任教一年后,赴菲律宾师从美国导师拜耶(H. Otly Beyer)学习人类学,拜耶在菲主要讲授美国人类学理论与方法。林惠祥回国后担任中研院民族学组助理研究员。1929年,林父逝于台湾,林氏赴台处理丧事,其后深入高山族地区开展调查,搜集文物标本,所集文物涉及台湾“番族”生活的方方面面,(8)林惠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第41-47页。1934年,林惠祥在家中设立文物标本室,称之为“厦门市人类学博物馆筹备处”,藏品达三四百件。但为进一步充实内容,林氏于1935年冒险再入台湾,采买标本。全面抗战爆发后,他避难新加坡,带走大部分文物,在新期间亦着力搜集各类文物。1947年,林惠祥自南洋归来任教厦门大学,在学校举办了人类学标本展览会。1951年,他专门写信给当时厦门大学校长,建议成立人类学博物馆,并把自己数年来收集的一千多件文物全数捐献给学校,以作博物馆建设之用。1953年,厦门大学人类学博物馆正式对外开放,实现了他数年来的愿望。1958年,林惠祥突发脑溢血逝世。
林惠祥为民族文物事业疲心竭虑、呕心沥血的精神,在一些小事中体现得淋漓尽致。抗战胜利后,林携家眷及文物回国。据林夫人回忆,其他华侨回国时,大箱大笼皆是细软之物,而林惠祥的行李装的却是他认为比他生命更重要的文物和图书。(9)蒋炳钊:《怀念林师》,汪毅夫、郭志超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13页。又据其子林华明回忆,林惠祥在筹办博物馆时以馆为家,没有节假日,“我记得父亲塑造从猿到人的模型,自己脱光上衣,双手举着木棒,张着大嘴,模仿山顶洞人的样子,给工作人员当模特。”(10)林华明:《永远的怀念》,汪毅夫、郭志超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1页。
二、民族学博物馆:“采集民族志”的理论意涵
吴、林二人贯穿一生的采集实践仅是其宗师地位一个层次的体现,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对民族文物标本的采集提出了诸多较为一致的理论主张。从现有材料看,吴、林二人并无密切交往,思想的相互影响不大可能,学术实践双线并行,(11)具体参见哈正利、张福强:《吴泽霖年谱》,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2018年,第67-72页。但在理论探索中却体现出诸多一致性,绝非偶然性所能解释,而应该是学科自觉发展使然。提炼他们理论主张中的共性,实际在昭示中国民族学中的“采集民族志”有着丰富而深刻的理论意涵。抛开细枝末节的论述不谈,他们最终的学术理想是要建立一座带有人类学民族学旨趣的民族学博物馆,它为人类学学科发展服务,同样也离不开学科理论的哺育,这类民族学博物馆实际上蕴含着他们的民族志理想。“吴泽霖与林惠祥,一南一北,前者孜孜不倦、辛苦积累‘民族文物陈列室’实际上掩盖着一张关于民族学博物馆的规划蓝图。”(12)郑茜:《民族博物馆?民族学博物馆?——对一种独特的中国博物馆现象的理解与阐释》,顾群主编:《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2014上)》,北京:民族出版社,2014年,第7页。在他们的学术视野中,民族学博物馆能够超越政治对立、文化区隔,它是通过采集的形式,用“物象”来展现文化多样性,表达“美美与共”的理念,最终实现文化的相互沟通与交流,这与表现于文本的民族志只是路向不同,目的却系一致。实际上,这种“采集民族志”虽然立足的是专业知识,但面向却是人类普同的人文关怀。此种努力在当时遭到了部分学者的非议,但放置到今天博物馆面临的各种后现代解构性话语时,却显示出独有的价值。
按照吴泽霖的想法,民族学系、民族研究所与民族学博物馆是一体,缺一不可,共同推动民族学学科的发展。民族学博物馆的建立依托系、所的人才培养和科学研究,而系、所发展也需要民族学博物馆的支持。(13)吴泽霖:《有关博物馆方面的资料(二)》,年代不详,笔者藏。在吴氏的民族博物馆思想中,他一直想把体现政治性的民族博物馆和体现学科性的民族学博物馆进行区分。民族博物馆主要是为政治服务,其功能有六点,如介绍兄弟民族历史、介绍少数民族对中华民族的贡献、介绍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介绍少数民族的在解放前后的历史变化、展望近景与远景等。而民族学博物馆主要为科学服务,也即为民族学学科服务,它建立在民族学基础上,同样也需要开展田野调查,它们的关系与化学或物理与其实验室的关系一样,相互依赖、相互促进,处于一种共生状态,实际上,民族学博物馆就是民族学的一种间接的田野调查基地。(14)吴泽霖:《论博物馆、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年第3期。
1949年前,吴泽霖在各高校建立的民族文物陈列室,属于他所说“民族学博物馆”类型的早期形态。“民族学博物馆性质的机构也只是在30年代后在诸如华西大学、厦门大学,抗日战争时期由上海内迁贵阳的大夏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浙江大学等少数学校内播下了种,发出了幼苗。”(15)吴泽霖:《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中国博物馆》1986年第1期。其中大夏大学和清华大学的文物陈列室都系吴泽霖亲自创建,在其论述中均属民族学博物馆。1949年后,虽然他多次参与或主持了带有意识形态色彩的“民族博物馆”性质的展览,但把博物馆拉向民族学学科的努力始终没有放弃。宋兆麟回忆,在一次民族博物馆筹备工作会议中,多数人主张应该定名为中国民族博物馆,“唯独吴老提出异议,认为应该定名为中国民族学博物馆,后来他多次坚持自己的看法。”(16)宋兆麟:《我国民族博物馆事业的开创者》,赵培中主编:《吴泽霖执教60周年暨90寿辰纪念文集》,武汉:湖北科技出版社,1988年,第137页。1982年,吴泽霖到中南民族学院后建立了民族学博物馆,最终实现了他梦寐以求的理想。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讲求学科属性的民族学博物馆才是他毕生所愿,而非在各类“物”的装饰下被“意识形态”填充的民族博物馆。
与吴泽霖略有差异,林惠祥对民族类博物馆并没有作出细致的区分,但他对强调学科性质的人类学博物馆的坚持,从其学术研究之初便已生根。就林惠祥建立的文物机构的性质来看,一直未脱离学科的关怀。1934年,他建立了第一所民族文物机构,便命名为“人类学标本陈列室”,该机构主要目的是为学科建设服务。1951年,他在原有基础上筹建了“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该馆虽在名称上作了调整,但其人类学的学科立场依然未有改变,在展示内容、展示秩序等方面,都有学科理论的指导,“本馆的陈列设计也颇具学科特点。与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相适应。”(17)唐星煌:《林惠祥与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汪毅夫、郭志超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66页。
从其学科建设的思想看,林惠祥一直坚持认为博物馆是人类学学科不可缺失的一部分。“博物馆是研究和教学不可缺的工作,其重要性不输于图书馆。而高等学校和研究机关必须附设。”(18)林惠祥:《厦门大学设立人类博物馆筹备计划书》,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94页。1949年,解放军进驻厦门大学不久,林惠祥便向上级机关申请开设人类学系、人类学所和建立人类学博物馆。在报告中,他反复申明,人类学的研究须采集标本和设立博物馆。人类学者必定兼习博物馆学。在其开设的课程中,博物馆学是必修课程。在报告的结论中,他再次强调“以上所提的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和人类博物馆并设,是为三者有密切联系。教人类学不能无标本,而教员不能不做研究,研究的结果所得到的标本也一定陈列于博物馆内,所以三者不可分离,设一种便可设三种。”(19)林惠祥:《厦门大学应设立“人类学系”、“人类学研究所”及“人类博物馆”的倡议书》,蒋炳钊、吴春明主编:《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12年,第617页。博物馆与研究所应该相通,这是林氏的一个基本认识。可以说,在林惠祥的学术思想和学术设想中,博物馆应时刻置于学科背景中,它依托学科而发展,为学科服务,是为其学术理论的论证提供一个试炼场。宋伯胤恰如其分地概括了林惠祥的博物馆思想,“林惠祥力求找寻文化人类学、历史学和博物馆学三者之间的连接点。在有机统一体中建立一座新型的融合历史与哲学、艺术与人种学、人与群体、古与今为一体的人类学博物馆。”(20)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汪毅夫、郭志超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7-369页。
吴泽霖和林惠祥作为中国民族学的先驱式人物,为什么都不约而同地钟情于他们所谓的民族学博物馆呢?其理论意义到底何在呢?早期的博物馆都是奇珍异宝的“储藏室”。地理大发现后,人们热衷收集初民社会的生活用具等,人类学博物馆作为一种类型从此产生。如何处理、解释从世界各地征集来的各式各样的器物,成为博物馆专业人员关心的核心命题之一。人类学的各种理论,为他们如何“展示秩序”指明了方向。各种理论依次出现,在博物馆中体现为物品展示秩序的变更。进化论盛行时,人类学博物馆中物品秩序的展示以社会进化的阶序顺次排列;传播论主导理论界时,器物展示以地理区域为划分标准,并对同类型、同功能的器物进行类比,得出人类文化的宏观历史。这种相互依存关系伴随着人类学的发展,走过了很长的一段时期。正如学者所说的“人类学博物馆赖以生存的基础——展品和藏品的知识建构与信息传播,依赖人类学的民族志研究和诠释。人类学博物馆的发展需要人类学学科理念与研究成果的支撑。”(21)桂榕:《博物馆人类学刍议》,《青海民族研究》2012年第1期。可以说,人类学是人类学或民族学博物馆不断保持生机盎然、活力四现的最重要依托,同时民族学博物馆也以一种物化的形态来表达、阐发着早期的人类学理论。此类表述与吴、林二人对民族学博物馆的定义如出一辙。这反映出,实际上他们对博物馆的本质属性早已有清醒的认识,认识到人类学的“缺席”将会使得民族学博物馆变成无源之水。按照潘守永所言:“人类学的缺席,使得民族学博物馆游离于应有规范之外,自身也难以得到应有的学术影响和社会地位,甚至连最起码的尊重也得不到。”(22)潘守永:《民族博物馆是什么?》,《中国民族报》2010年10月29日,第9版。从这点出发,或许可以回答为什么1949年后,他们用民族文物展览的形式来宣传党的民族政策的同时,心中依然怀有民族学博物馆的梦想,并在众人的异议声中,依然不断倡议筹建民族学博物馆。
吴、林二人对民族博物馆与民族学博物馆的区分,结合今天博物馆人类学的潮流来看,依然具有很重要的意义。20世纪80年代以来,人类学进入到一个批判和反思的时代,其中诗学与政治学成为这次解构性风潮最重要的武器之一,民族学博物馆也深深陷入到后现代的泥潭中,“突然间人们开始讨论博物馆,并将关于它的争论置于中心,”(23)麦夏兰:《人类学视野中的民族博物馆》,《中国博物馆》2012年第3期。甚至成为各种思想角逐的前线。他们对民族学博物馆的殖民地属性、展品的本真性、表述主体、权力本质等等都开展了质疑与讨论。而今学界多处于解构风潮之后理性平静的重建时代,更多思考博物馆的未来走向,其中一些学者对民族志博物馆(24)民族志博物馆又叫做民族学博物馆、人类学博物馆等,它把民族志博物馆与民族志文本、民族志电影置于一个同等地位,都是作为对异文化的表达、呈现与阐释的“文体”,吴泽霖所谈的民族学博物馆与民族志博物馆实质上是同一类型。给予了厚望,认为它能在当今人类学学科与当代博物馆在遭遇到本体论与知识论的危机时,或能扮演“救世主”的角色,“民族志博物馆根深蒂固的跨科学本质和人文主义精神不仅值得博物馆学界予以重视,而且还为整个博物馆世界的发展提供了可供选择的路径。”(25)尹凯:《重思民族志博物馆:历史、秩序与方法》,《青海民族研究》2018年第1期。
他们不论个人或学科处境多么艰难,始终坚守着民族学博物馆梦想。而他们所处的那个时代,后现代潮流尚没有把博物馆的各种权力本质识别与暴露出来。我们不能说他们对学术潮流有着超乎常人的先知先觉,但至少从中可以看出,甫一开始,对博物馆在表达文化的真实性或价值无涉方面,他们始终保持一种审慎的心态,对民族学博物馆未来如何更好地发展,也有自己的看法。也正是如此,在经过长时期的博物馆实践后,才会在晚年抛出区别政治属性的民族博物馆与学科属性的民族学博物馆这样一个重要命题。
三、文化史构建与平等的“物化”:“采集民族志”的两种取向
“采集民族志”所追求的是与人类学民族学学科互为支撑的“民族学博物馆”,它是学者学术实践的具体组成部分,一方面体现着学者学术研究的旨趣与风格,另一方面为学者学术思想体系的构建、学术观点的表达提供支撑。吴泽霖与林惠祥虽然都受美国文化批评学派的影响,但学术研究的分异十分巨大,在他们采集实践中也有着充分体现,表现为两种截然不同的取向。苏珊·皮尔斯在论述欧洲传统的“收藏品”时,除其本身的实体意义外,更重要的是把它看作想象和建构的产物,认为“收藏品”经过组合以隐喻的方式制造着意义。(26)Susan M. Pearce, On Collecting: An Investigation into Collecting in the European Tradition, New York: Routledge, 1995, P. 25.也就是说,收藏品的意义与实践者的认识有着密切关联。吴、林二人在他们的学术道路上,各自逐步形成了对中国的民族构成等的系统认识,这种认识上的差异性在收藏品意义赋予与秩序的重构方面也有体现。这种分异实际代表着中国民族学史中“采集民族志”的两个不同发展方向,关于此点,容后再议。首先从二人的具体差异谈起。
林惠祥在菲律宾学习期间更多继承了美国学派的特征,研究范围相对广泛,涉及考古、体质、文化等领域。他不仅以文化人类学家著称,更多的是以考古学家和民族史学家而闻名于世。在此研究旨趣之上,他在文物标本的征集展览方面多偏重历史、考古与体质资料。“从一定意义上说,林惠祥是一个以民族史为目的的考古学者、博物馆学者。”(27)尹凯:《林惠祥的博物馆理论与实践》,浙江自然博物馆编:《自然博物》第2卷,杭州: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2015年,第191页。从林惠祥亲手建立的人类博物馆的陈列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种倾向。该博物馆陈列主题有三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史前遗物及模型,包括新旧石器时代的考古遗物、古人类的遗骨及复原模型、从猿到人的进化线路等;第二部分为历史时代的古物及模型,比较特别的是铜器、玉器、陶器;第三类为民族标本和人种模型,内含国内民族标本(主要是台湾少数民族)、南洋民族标本、印度民族标本、日本民族标本和世界民族标本等。(28)宋伯胤:《林惠祥与人类博物馆》,汪毅夫、郭志超编:《纪念林惠祥文集》,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367-369页。从林惠祥的学术研究历程看,他多次在台湾开展过田野调查,并参与了数次考古发掘,还对世界人种有过系统研究,撰写了《世界人种志》一书。在此研究基础上,他的民族文物标本的收集展览自然偏重考古材料及人种材料。
分析林惠祥文物标本采集背后所展示的知识建构性则更有意义。张先清认为林惠祥1929和1935年两次台湾文物标本采集工作,带有很明显的进化论思想,但摒弃了“心理一致”说,且受到美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带有抢救民族志的性质。(29)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民族学刊》2016年第1期。尹凯主要关注林惠祥20世纪50-60年代人类博物馆的标本陈列,指出其藏品展示是在进化论、历史特殊论和传播论三种知识体系指导下的实践活动。(30)尹凯:《博物馆的民族志书写——以林惠祥的厦门大学人类博物馆(1953-1966年)为例》,北京民俗博物馆编:《北京民俗论丛》(第2辑),北京:学苑出版社,2014年,第8页。从林惠祥整个民族文物事业来看,其标本陈列中蕴含着进化论、美国历史学派等因素是不可否认的,并且体现出他的诸多学术意图。“他试图从人类学、考古学、历史学、民族学等多个维度还原这一区域的文化特质,探寻文化起源、变迁和传播的规律,”(31)杜辉、熊佩:《从民族志物品收藏到东南海洋系文化构建——林惠祥先生收藏与展示实践(1928—1958)》,《民族学刊》2016年第6期。最终在人类博物馆这个知识话语空间内建构东南海洋系文化的学术理想。上述论述虽然各有差异,但总体表达的含义较为一致,都强调林惠祥的博物馆实践侧重通过考古、体质等文化特征的搜集分类组合,来重建东南海洋文化区,试图通过文化特质的接触展示“汉”与“非汉”亲缘关系的目的,最终完成文化史构建的目的。从林惠祥的论述中看更为明显,他特别关注台湾与大陆的一体关系,他通过对考古、体质、文化等特质的发掘与组合,最终得出结论“台湾的新石器时代的文化虽有一点地方特征,但从大体上看,却是属于祖国大陆东南一带的系统。”(32)林惠祥:《林惠祥人类学论著》,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1年,第194页。他还通过对有段石锛的调查研究,判断东南文化区的范围、特征及民族交往交流的历史,通过空间的分布来构建历史的发展序列。因此,我们可以说,林惠祥的“采集民族志”背后所蕴含的知识建构与其学术研究保持一致,即通过东南文化史的构建,来证明中华民族的联系性、整体性与一致性。
吴泽霖的“采集民族志”背后所蕴含的意义则是另外一番景象。与林惠祥不同,吴泽霖对考古和语言两个学科的研究较少涉猎,他一生的学术旨趣多集中在体质和文化两个方面。而在文物标本的搜集、展览方面,他比较注重物质文化材料的搜集,尤其是语言、服饰、民族工艺品等。在吴的遗稿中,有一篇名为《博物馆陈列》的文章,他对中南民族学院民族学博物馆的陈列作出了设想,其主要陈列有六方面内容,分别为中南地区概况、语言文字、工艺、乐器、住宅、服饰。(33)吴泽霖:《博物馆陈列》,年代不详,笔者藏。从间接材料来分析,1982年吴氏支援中南民族学院建设,对学院原有的民族文物陈列作出调整,调整后设有民族服饰、民俗、民族工艺品、民族文化等展厅。(34)石建中:《民族博物馆学教程》,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0页。
吴氏的展示特征与其田野经历有着密切联系,他的田野足迹多在西南少数民族地区,他对西南民族本质的把握多从婚姻、家庭等文化要素入手,在文物标本搜集方面自然而然会有所偏好。在学术研究中,他侧重文化多样性的呈现,而贵州民族多样性最为直观的体现则是在民族服饰的差异性上,由此,吴泽霖的文物标本采集中注重服饰,便不难理解了。
吴泽霖在文物标本展示所透露出的意义则比较纯粹,他的核心诉求在于通过“物化”的文化特质来向观众传递一种民族平等的理念。可以说吴泽霖的民族博物馆思想是对其早期学术关怀——种族平等问题的延续。(35)温世贤、彭文斌:《传译民族文化与平等——吴泽霖先生的民族博物馆思想》,《民族学刊》2011年第3期。在民族文物事业的实践及民族学博物馆的研究中,他以另外一种方式践行并倡导着他的“平等”理念。“他这种崇尚民族平等的思想贯穿在他一生的事业里。民族博物馆的创建,只是为实现他这个理想的一项具体措施。他热爱民族文物是从他心底认识到民族平等、共同发展的表现。”(36)吴泽霖:《美国人对黑人、犹太人、东方人的态度》,北京:中央民族出版社,1992年,“费孝通序”,第3页。在展示秩序方面,他更多继承了博厄斯在博物馆展示方面的经验。博厄斯十分反对按照进化论序列的器物展示方式,同时指出相关陈列必须兼顾自然与人文,这是唯一能展现某一现象的特征与周边环境的方法。(37)弗朗兹·博厄斯:《民族博物馆与其分类方式》,吴洁译,《中国民族博物馆研究》编辑部:《中国民族博物馆2015》,北京:民族出版社,2016年,第4页。在吴泽霖的文物展示中,很少看到按照进化论式的排列,他不太注重从历时角度还原民族的发展序列,更多的是以器物为中心的同心圆式的铺陈展开。同时,他还特别主张“文物标本的展示应该放置在活的背景中”。(38)吴泽霖:《民族文物工作的三部曲》,年代不详,笔者藏。可以说,博厄斯关于博物馆的秩序展示思想对吴泽霖的影响很大。
另一方面,吴泽霖文物标本所采集与展示的重点在于“美学”特征突出的文化特质,如工艺品、服饰等,希望通过美学特征突出的文物展览,来唤起观众对少数民族的重新认识,这些艺术品所体现出的含义,实际上都可归置到李亦园所说的“不可观察的文化”的类型,“它就已不再是一种工具,而成为一套分类的符号,一套任何文明不分轩轾的精巧设计。”(39)李亦园:《人类学家与他的博物馆》,吕理政主编:《人类学家的博物馆》,“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8年,第9页。在艺术品面前,民族没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先进后进之别,都处于一个平等地位。这是吴泽霖在文物展示中试图想要表达,并期望达成的目的。一言以敝之,吴泽霖的博物馆实践背后有着艺术学与美国博厄斯式的文化人类学的双重依托,其最重要的意指是对平等的表达与追求。
综合而言,吴泽霖和林惠祥“采集民族志”背后所体现的知识建构差异,前者强调用“物化”形式表达平等理念与诉求,后者试图通过文化特质的组合来完成东南文化史构建,最终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和内部各部分的联系性。然而,从思想来源看,差异中也蕴含着某种关联。他们二人都是美国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都是在继承博厄斯人类学思想基础上结合中国实际开展的学术研究。吴泽霖20世纪20年代留学于美国,对美国种族问题有切身感受,博厄斯种族问题研究与平等主张对他影响很大,归国后更多从事社会学研究,关注社会问题,民族“平等”的理念与主张蕴含着更多的现实关怀;而林惠祥在菲律宾师从拜耶学习人类学,间接领会和吸收了博厄斯的人类学思想,他更多继承了博厄斯人类学的方法论,偏重于文化史的构建。可以说,他们在“采集民族志”中所表现的差异,是对博厄斯不同思想的继承和中国化处理,表现为“同源异流”的关系。把视域扩展到中国民族学发展的总体历程中来考察,他们的分野实际代表着中国民族学中“采集民族志”的不同取向。
四、中国民族学史上的“采集民族志”
从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发展的整体而言,重视文物标本的采集,并把民族学或人类学博物馆的建设与人才培养、民族志书写等联系起来的思路,并不是吴、林二人独有的特点。与民族学专业建设有关的民族文物或民族学人类学器物和标本的搜集、整理,在中国民族学的发展史中始终占据重要的位置。(40)王建民:《中国民族学史(上)》,昆明:云南教育出版社,1997年,第203页。然而,这其中又有诸多具体差异性。美国文化学派和德奥、法国等欧陆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特别强调用器物的搜集展示来表达学术思想,建构相关的民族知识,而英国功能学派的代表人物对此并不热衷。
美国学派中的吴泽霖、林惠祥在此不作多议。杨成志虽系求学法国,但归国后更多体现了美国学派的特征,他在民族文物标本的采集展览方面也开展了诸多实践,颇有心得,发表了《学院与博物馆》《现代博物馆》等文章,在云南、粤北等地调查的同时也特别注重文物的搜集与整理。(41)赖雪芳:《杨成志的博物馆思想与实践》,《中国博物馆》2014年第4期。他的“采集民族志”所体现的知识建构性与林惠祥的十分相似,都试图通过相似特征来构建文化区,从而证明中国民族在历史上长期交往交流的亲缘关系。他在设计云南民族研究的计划时谈到:“我特注重技术上的学习,在民族志博物馆学习如何整理、分类、陈列、保藏民族物的方法”,最终目的是“推出我国古代文化的遗迹及寻出中华民族迁移的遗迹。如此,对于外国人的西南民族著作上的许多错误可加以严格的批判和纠正。”(42)杨成志:《我对于云南罗罗族的研究计划》,《杨成志民族学人类学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年,第230页。
欧陆学派在中国的代表人物对文物标本的采集展览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中央研究院人类学及民族学组在成立之初,便设专人负责搜集标本,后来成立了民族学标本室,准备时机成熟时建立民族学博物馆。1929年凌纯声、商承祖等开展东北满-通古斯语族调查,历时三月,除有民族志报告问世外,所得标本材料亦颇多;金陵大学柯象峰、徐益棠于1938年对西康的社会文化进行调查,为期两月,其后出版了《西康记行》,同时收集文物52件,拍摄照片283张。他们的“采集民族志”背后所体现出的知识建构特点,与他们的学术研究旨趣保持一致,都体现着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南派”风格,“比较倾向于从事边疆民族的调查,不同民族文化类缘关系的探讨,以及中华民族发展形成过程的追踪探索。”(43)陈其南:《四十年来台湾人类学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人类学研究与社会科学中国化》,杨圣敏、良警予主编:《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建设百年文选》,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08年,第301页。
英国功能学派在中国,以吴文藻为首的燕京学派最具代表性,他们对文物搜集展览并没有投入太多精力。不论在采集实践方面还是理论阐释方面都乏善可陈。吴文藻一生论述多为学理演绎,少有调查实践;李安宅、费孝通、林耀华等田野经历丰富,但在调查中对文物标本的采集并不重视,其后也没有举办有规模、有影响的民族文物展览。费孝通虽有若干相关文字发表,但在文中自己也承认自己“并不是民族博物馆的工作者,对民族博物馆没有什么经验,”(44)费孝通:《关于建立中央民族博物馆的意见》,《费孝通民族研究文集》,北京:民族出版社,1988年,第111页。且文中论述的要义与吴泽霖、林惠祥所着力倡导的民族志博物馆相去甚远。可以说,中国民族学的“北派”或中国功能学派,在“采集民族志”的实践与理论阐释中发声不多。但这并不是说,他们学术研究有何缺失,而是由于学术研究路向不同导致关注点有所差异。
总的来看,“采集民族志”在中国的实践,至少有两种不同取向:一种以林惠祥、杨成志、凌纯声等人为代表,倡导通过民族文物与标本的采集展览,来构建文化的区域类型,从而构拟民族的历史互动过程与亲缘关系,最终目的在于论证中华民族的整体性,主要以中央研究院、中山大学、厦门大学为主要阵地;另一类是以吴泽霖为代表,试图通过文物的展示来表达文化的多样性,用物化的形式来体现民族“平等”的理念,从而推动跨文化的交流,主要以清华大学为主要阵地,带有很强的实用性。
但不管是哪种类型,他们通过“物”的展示来表达各自学术理念的方法却是一致的。因此,从广泛意义上说,民国时期中国民族学人类学学科的发展,除了介绍西方理论、构建中国民族学的体系、开展田野调查之外,还存在一种可以称之为“田野采集志”(45)张先清:《物件的文化:中国学者的早期田野采集志反思》,《民族学刊》2016年第1期。的学科表现形式,它是以器物展示的方式来表达学者们诸如文化多样性、中华民族一体性、文化亲缘关系等主张,用物象化的文物展览来切实贯彻他们在学术研究中得出的结论,在最终指向上与表现在文本上的“民族志”并无太大差别,只不过是各自的方式有所不同而已。它与表现在影像上的民族志一样,用一种特殊的手段建构着有关民族的知识,是对学者学术思想记录的一种方式。(46)张先清、张云鹤:《人类学、影像民族志与族群景观——林惠祥的早期“原住民”田野摄影》,《西北民族研究》2019年第2期。同时,也应该看到,在早期大部分学者思想中,“采集民族志”与“文本民族志”、人才培养是一体的,共同构成民族学人类学发展的基本要素。反观我们今天的学科发展,民族学博物馆或者更多地称之为民族博物馆,在规模、建制方面与1949年前相比,有了长足进步,甚至有学者不断提出“民族博物馆学”的构建。但从整个民族学人类学学科体系中的地位来看,“采集民族志”在促进人类学知识的增长与理论的更新上,或在专业人才培养所发挥的功能上,都尚有较大拓展的空间。关于这一点是今天“中国学派”构建中所要重视的内容之一,同时也是我们重新回顾老一辈学者“采集民族志”实践的意义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