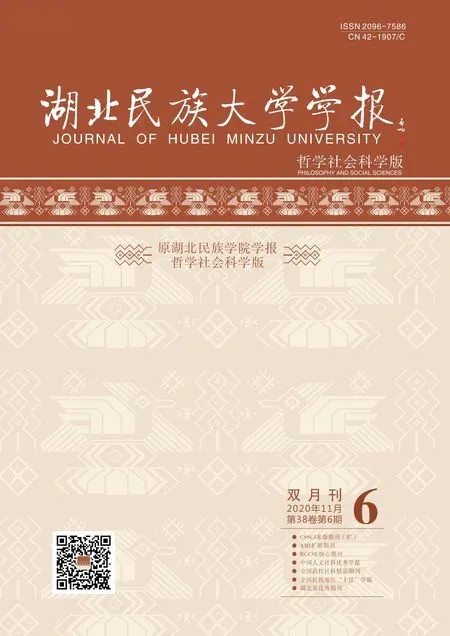在穗经营型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的形成及其社会融入
杨小柳
一、问题的提出
改革开放以后,中国进入城市化加速发展时期,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以城市为中心的全国性人口迁移潮流的出现和持续,少数民族是人口迁移群体的重要组成部分。广州作为珠三角的核心城市,是全国少数民族人口增长最快、增幅最大的城市之一。根据广州市政府官网的数据,目前全市有少数民族人口82.7万人,分属55个少数民族。其中,户籍少数民族人口约11.8万人,非户籍少数民族人口70.9万人。(1)《广州概况之人口民族》,2020年3月13日,http://www.gz.gov.cn/zlgz/gzgk/rkmz/index.html,2020年9月10日。
与一般外来移民群体不同,少数民族迁移人口由于特定的民族文化特点,其迁移流动、城市适应、期望需求均具有一定的特殊性。特别是不少民族迁移人口进入大城市后,并不以务工为生,而是从事各类极具民族特色的工商业活动,成为城市的经营型移民。少数民族经营型移民通过链式迁移,围绕这些工商业活动迁移形成了聚集区。这类聚集区与周边社会在空间形态、社会结构、文化表象等方面都存在着明显的差异性和边界性,使中国移民城市的文化景观呈现出马赛克一般的多样性和混杂性。这类移民聚集区已经引起了国内不少学者的关注。学者们一方面从少数民族移民的角度,讨论了其聚集区形成的内在机制,并认为这是其城市适应的重要手段;(2)张继焦:《城市民族的多样化——以少数民族人口迁移对城市的影响为例》,《思想战线》2004年第2期。另一方面则是从城市的角度,讨论了移民聚集区对城市社会构成的影响。(3)靳薇:《少数民族移民与城市其他民族居民的互动及调适》,《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3期;陈云:《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城市融入中的排斥与内卷》,《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第3期。
2014年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指出城市民族工作要立足于社区,通过构建相互嵌入式的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来促进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为在城市管理中如何应对和处理各类民族事务和民族问题提供了指导思想。那么,从互嵌型社会构建的角度来看,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引导和管理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呢?围绕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环境,国内学者重点对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的内涵、意义、构建路径及问题挑战展开了一系列研究。在这些研究中,学者们关注到了居住空间与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构建的紧密关系。(4)杨鹍飞:《居住空间与民族关系再造:民族互嵌型社区的文献评述与研究展望》,《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2期;卢爱国、陈洪江:《空间视角下城市多民族社区互嵌式治理研究》,《内蒙古社会科学》2016年第6期。除了空间要素外,学者们还关注互嵌式社区构建中的关系网络和精神网络的建设。(5)马晓玲:《关于城市“民族互嵌式”社区的内涵思考》,《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上述研究主要是从处理城市民族事务的现实层面出发开展的应用与理论结合的探索。笔者认为,需要进一步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将“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的思想与学界特别是西方学界已有相关理论进行比较和对话,由此明确中国城市多族群社会构建的主要机制和特点,才能更好地引导现实中构建互嵌式社会结构和社区的实践。
围绕少数族裔的工商业活动而形成的移民聚集区在欧美的移民社会中同样存在,其在学术研究中被称为族裔聚集区(Ethnic Enclave)。族裔聚集区形成的基础在于族裔经济,即同一文化/语言的少数族裔拥有和经营的企业聚集在一个可识别的地理区域,彼此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并雇佣大量的同族裔成员。不同时期的欧美学者对作为经济和文化实体的族裔聚集区进行了大量研究。族裔聚集区之所以成为研究热点,与西方学界对空间聚集可能带来社会隔离的担忧紧密相关,认为族裔聚集区的形成来源于外界的隔阂与不平等,因此社会融入一直是这一领域研究的理论出发点。围绕社会融入这一核心问题,学者们的观点大致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芝加哥学派发端,在社会同化的理论框架中,将其作为移民同化过程的过渡阶段,认为随着移民对主流社会的融入,这种具有明确边界的族裔聚集区将逐渐消亡。帕克把移民聚居区称为族际交往的“前沿地带”,比较和竞争以族群为界限展开,但随着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和族际双方不断的调适、权益的斗争和协商,最终会达成社会融合。(6)Nathan Glazer and Daniel P. Moynihan, Beyond the Melting Pot (second edition), Cambridge: The M.I.T. Press,1970, pp. 22-34.第二种观点是基于对第一种单一同化理论反思的基础上,关注到聚集区族裔经济对移民多元融入的重要影响力,认为族裔经济带来了族裔聚集区内部多样的阶层划分,通过凝聚同族群群体的社会资本,为移民的经济和阶层流动创造了机会。(7)狄金华、周敏:《族裔聚居区的经济与社会:对聚居区族裔经济理论的检视与反思》,《社会学研究》2016年第4期。
两类观点对族裔聚集区在社会融入上的意义和价值判断完全不一样,由此导致引导族裔聚集区社会融入的不同思路。在第一种观点来看,族裔聚集区作为社会融入的过渡阶段,是一种社会隔阂存在的标志,那么移民离开聚集区,聚集区消解就是其发展的方向。就第二种观点来看,族裔聚集区是各类少数族裔主动开展社会融入的重要场域,其中族裔经济作为推动移民聚集区的核心动力,其形态和机制成为研究的热点,不少学者将聚集区族裔经济作为少数族裔实现主流社会融入的有效路径,认为其具有强大的凝聚力,使族裔聚集区内部围绕族裔经济形成多样的阶层结构,涵盖了企业主和雇员、新移民和老移民,为移民提供了一个内部阶层流动的渠道。(8)Portes and Alejandro, Economic Sociology: A Systematic Inquiry,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0, pp. 162-186; José A.Cobas, “Ethnic Enclaves and Middleman Minorities: Alternative Strategies of Immigrant Adaptation?” Sociological Perspectives, vol. 30, no. 2.1987, pp. 143-161.
上述有关族裔聚集区的研究,是欧美学者在移民输入国存在着明显的族群等级结构的语境中对跨国移民聚集区形态开展的研究。因此,不能将中国城市中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简单等同于族裔集聚区,其相关假设和观点也无法直接移植用以解释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移民的社会融入。但上述研究却可为我们理解城市各类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提供理论启发和研究参照。由于我国不存在等级化的族群结构,那么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形成和维系的机制是什么?围绕移民经济形成的聚集区代表了何种融入趋向?我们应该如何看待和引导城市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的发展?这些问题均需要我们突破仅从现状问题出发的研究局限,遵循一定的理论研究路径,围绕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社会融入这一问题,深层次挖掘少数民族移民聚居区内部的整合方式及其与迁入地社会的互嵌机制,并通过深入的调查了解关心少数民族移民的真实需求和生活问题,切实为推动民族交流与互融做出贡献。
本文以在穗朝鲜族、藏族经营型移民及其所构成的空间集聚为研究对象,通过结构性访谈和田野调查的方式,尝试对朝鲜族、藏族经营型移民的聚集区形成机制及其社会融入状况进行分析,在此基础上形成与国外有关移民融入理论的回应和对话,并就如何推动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的社会结构和社区,实现各民族的交流交往交融提出思考。
在穗朝鲜族和藏族移民群体在城市生活中均围绕具有民族特色的移民经济,形成了极具文化标示性的移民聚集区。其中,在穗朝鲜族与韩国移民生活在一起,主要为韩国人饮食起居、生意交往、沟通联络提供服务,典型聚集点为广州远景路。在穗藏族移民以流动小贩和店铺经营为主要生计方式,聚集在广州荔湾区中和街道的坦尾村。本文的调查和数据来自笔者带领的课题组于2016年在上述地点开展的田野调查,共收集到访谈个案49例,其中朝鲜族移民21例、藏族移民28例。
二、在穗朝鲜族经营型移民——韩国人族裔聚集区的有机组成
在穗朝鲜族经营型移民的聚集形成与在穗韩国商人群体紧密相关。在穗韩国人总规模在两万五千人左右,其中三分之二从事经营和贸易,主要经营服装、皮革、鞋子和布匹等;另外三分之一的韩国人主要在集中在领事馆、政府派出机构以及学校里。课题组重点调查的远景路、机场路片区,因为交通、物流、运输以及服装皮革等贸易集散地均分布在附近,小区设施相对成熟,是最早形成的韩国人聚居区,也是多数新来韩国人的落脚地,聚集着上万从事商贸活动的韩国人。
在穗韩国人采取一种“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的文化适应策略,表现为一种基于生存和发展需要而实践的浅层融入,同时出于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优越感,强调群体的排他性和封闭性,与周边社会保持“深度区隔”。而这套文化适应策略的维系机制则是韩国人与朝鲜族经营型移民的互补共生关系。(9)周大鸣、杨小柳:《浅层融入与深度区隔:广州韩国人的文化适应》,《民族研究》2014年第2期。
朝鲜族经营型移民因与韩国人同宗同源,语言相通、文化相似,是韩国人与其周边文化沟通的桥梁。远景路韩国人聚居区汇聚了一大批为韩国人日常生活、饮食起居、生意交往、沟通联络而服务的中国朝鲜族经营型移民。朝鲜族经营型移民为在穗韩国人提供的服务主要有四大类。
一是开韩国料理、韩国餐厅。广州的韩国餐厅八成以上是朝鲜族人开办的。韩国人特别忠于自己的饮食习惯,为了提供地道的韩国菜,不少老板自己和厨师都会前往韩国学习地道韩国菜的做法。
二是开办家庭旅馆,为初到的韩国人及经常从事贸易往来的韩国人提供服务。朝鲜族开设的韩国家庭旅馆集中在远景路附近的小区,他们会在小区内租下几间房,按照韩国人的习俗设计家庭装修摆设。在家庭旅馆里,朝鲜族人与韩国人生活在一起,朝鲜族人为韩国人提供饮食、洗衣、翻译、生活指引以及必要时协助贸易的服务。浓厚的家庭氛围可以让韩国人虽然身在中国也有一种在家乡的感觉,不少居住过的韩国人会与朝鲜族房东成为好朋友,继续为房东介绍新租客。一位韩国受访者表示,他刚来中国的时候,就是由朋友介绍在远景路的一家朝鲜族家庭旅馆住了一个多月。在这一个多月时间里,他生活得非常轻松,在家里可以用韩语自由地交流与沟通,房东可以给他们做家务包括提供韩式早餐,使用韩国的日用品,从而大大减少了与当地的社区、各种机构打交道的不便。
三是在各领域提供翻译以及中介服务。当一些生意人与朝鲜族人的交往次数增多,彼此之间熟悉和信任以后,有些韩国人便不再亲自来广州进货,而是交给朝鲜族人代为办理,他们将产品需求及进货的资金交给朝鲜族人,由朝鲜族人进完货后通过国际物流的方式发往韩国,朝鲜族人从中赚取一定的佣金。
四是开设美容美发店、韩国商品店以及从事家政、代办签证等服务。受访的韩国商人郑先生表示,对他们来说,中国政府办事机构多,办事程序复杂,很多事情只能让熟悉中国情况的朝鲜族人代办。他特别提到了自己办理签证续签的经历,第一次跑错了公安局,第二次资料不全且沟通不畅,第三次只好求助一个朝鲜族代理帮忙,才把事情办妥。从此之后,他就会把这类需要与本地部门打交道的事情交给朝鲜族朋友去办,然后支付一定的费用,以节省自己的时间和精力。
可见,围绕韩国移民在华生意和生活的需求,在穗朝鲜族形成了一个极为活跃的移民经济体系,这个移民经济体系不但是凝聚朝鲜族移民的纽带,更是韩国人族裔聚集区维系和发展的经济基础。因此,韩国人的族裔聚集区不仅仅指的是由韩国移民形成的空间上的聚集,其在功能上还应该涵括与韩国人互补共生的朝鲜族移民的聚集。作为韩国人族裔聚集区的有机组成部分,朝鲜族经营型移民还界定了韩国人族裔聚集区与周边社会互动的性质,使韩国人族裔聚集区成为一个在文化景观上极具族裔特点,在结构上又与主流社会融合共处的存在,缓解了韩国移民与周边社会的隔阂及其在互动中潜在的各类矛盾和冲突,在社会融入的层面上展现了族裔聚集区形成和发展的一种路径和可能性。
因此,朝鲜族经营型移民作为韩国移民文化适应的媒介和桥梁,在与周边社会的适应上表现出非常显著的开放性。朝鲜族经营型移民以家庭迁移为主,以家庭为单位从事各类服务于韩国移民的行业。绝大多数朝鲜族经营型移民来自吉林,地缘和亲缘是他们迁移和聚集的主要机制。这些移民的文化水平相对较高,一半以上的受访者受过高等教育。大部分调查对象都在广州居住了3年以上,访谈对象中有13位受访者表示已经在广州购买了房产,实现了入户定居。调查对象开店资金来源最多的是自费,向亲戚朋友借款或合资也较多。从多方面考察情况来看,在穗朝鲜族在经济、社会交往和生活方式等方面,都体现出对于城市生活深度融入的特征。如调查对象所经营的生意顾客群体多样,韩国人、朝鲜族占47%,其余的则是以汉族和其他少数民族为主,广州本地人也在朝鲜族的顾客群体中占有一定比例。而在社会交往方面,调查对象的社交圈也颇为广泛,没有特别依赖某一群体。受访对象最要好的朋友除了朝鲜族,还包括韩国人以及周边社会的各类群体。而调查对象中近六成希望自己的孩子与广州本地人交往,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明其对广州有着较强的融入意愿。在生活方式上,朝鲜族经营型移民平时的休闲娱乐方式较为多样化,看书和看电影是最多的方式,与广州本地人的娱乐方式已经颇为接近,不会体现出明显的民族特色。调查对象对于休闲娱乐的消费也呈现多样化的层次,整体经济、文化消费水平较高,他们中的大多数去过广州较为著名的旅游景点,包括自然生态景观长隆野生动物园、人文历史景观陈家祠、广州地标小蛮腰和省博物馆等。而陪同他们去的朋友,除了本民族以外,汉族和广州本地朋友也较为多见,休闲娱乐时的同伴较为多样化。
朝鲜族移民社会融入的案例清晰地表明,经济因素固然是移民社会融入的重要因素,但文化的相似性则是促进社会融入的根本动力,在穗朝鲜族的生存之道最初是作为沟通韩国移民与汉族的桥梁,从中赚取一定的利益作为自己扎根城市的资本。桥梁的链接不仅增加了韩国移民在广州生活的便利度,对于朝鲜族移民来说,一开始的生存策略也成为他们融入本地社会的一种文化迫力。他们必须对迁入地的社会规则和文化熟悉才能够更进一步地积累资本,这促进了在穗朝鲜人的文化适应。所以,从目前的情况看来,在穗韩国人因聚居区明确与本地社会形成了浅层融入和深度区隔,反而为朝鲜族提供了与广州这座城市“互嵌”与“融入”的机会。
三、在穗藏族经营型移民——底层边缘的隔阂群体
在穗藏族经营型移民大都来自四川省阿坝州黑水县木苏乡,来到广州后集中居住在荔湾区桥中街道坦尾村。坦尾村是一个典型的城中村,以其低廉的房租吸引了众多的外来人口。这些藏族经营型移民人数不足百人,集中租住在村里的几栋房子里,相互之间交流、找人都非常方便。
迁移之前,这些藏族经营型移民在老家以农牧业为主要生计方式,在家乡时收入极低,调查对象中没有收入的占到71%,收入1001~2000元之间的占28.57%,只能维持最基本的温饱,在同乡或者亲人的介绍下来到广州寻求挣钱的机会。整个迁移群体的学历层次较低,82%的受访者没上过学或只有小学学历。
藏族移民进入广州后首先从流动商贩做起,其中的一位访谈对象表示这是他们的无奈选择:“刚刚来广州的时候,也想进到厂里面打工,但是我们以前没读过书,不认识字,而且刚来也不会讲普通话,根本就找不到工作,而且那些老板看到我们是藏族的,就不肯要我们,所以就只好摆摊卖一些从老家带过来的藏族小东西,有些时候为了方便进货就卖一些能在广州进到货的东西。”一部分人因为居住时间长,有了一定的资金积累,就会与汉族人合租一个小店铺卖些小东西。其中的一个访谈对象表示:“这几年城管管得严,出去摆摊容易被城管收东西,我们家今年开始开店,就是和汉族人一起合租店面,面积很小,只有3~5个平方(米)。虽然租的是最便宜的,但是店租也要每个月2000多呢,太贵了。要是外面给摆摊,我肯定出去摆摊,卖的东西也和之前摆摊差不多。我们老乡也都在摆摊,只有几个开店了,租铺子太贵了。”在笔者的调查对象中,仅有一人固定在多宝街贩卖商品,其他的受访者都是流动摊贩,经常更换售货地点,为了逃避城管处罚,很多人会去番禺、滘口、南海等地摆摊。这些藏族经营型移民来到广州之后,收入有了一定的提高,78.57%的受访者月收入在1001~2000元之间,有17.86%的人月收入在2001~3000元之间,有一人月收入达到5000元以上。
在穗藏族经营型移民保留着非常显著的民族文化特点。他们以贩卖自己民族的货品为生,常常身穿藏族服饰。他们全部信仰藏传佛教,来到广州后仍保持着一定的宗教习俗。大多数(92.86%)调查对象表示会说普通话,但主要是应付生意上的交流和日常生活;同时大家又表示在广州存在语言沟通问题,其中几乎听不懂当地人说话的占50%,认为存在一点语言沟通问题的占21.43%,只有7.14%的人认为自己没有这一问题。
藏族经营型移民以家庭为单位迁移,年长父母、年轻夫妻和孩子一起出来。绝大多数的受访者在广州居留超过3年,有的甚至长达12年。年轻夫妇是家庭生计的主力,每天早出晚归,父母尤其是母亲通常会待在家里照顾小孩。除了家庭,亲属网络是藏族经营型移民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虽然大家都以摆摊为生,之间难免会有竞争,但面对更加艰难的城市生活大家会分享彼此的相关知识和经验,在哪里摆摊查得没有那么严,哪里摆摊会卖得比较好,到哪里进货或者谁要进货了能不能帮忙带货,等等。尤其是对那些新来的移民,会有居住时间较长的长辈帮助他们安排住宿、传授给他们摆摊的知识经验。由于出租屋居住空间狭小,无法存放各类货品,于是大家在坦尾村外围公共厕所的旁边租了一间空房子作为共同的仓库,租金由大家平摊,并且由几个长辈共同管理协调。他们还在坦尾村外围的空地上搭建了简陋的“西藏聊天室”用作他们日常交流信息和感情的公共空间。在家的老人们白天会聚在这些空地上聊聊天,互相帮忙照顾家里的小孩,而年轻人晚上摆摊回来后也会聚到一起坐一坐,分享信息,有问题的会提出来一起帮忙出出主意。调查对象在广州经常接触的群体,最多的是同乡,占96.43%;其次是自己的亲人,占10.71%;工友、同事、老板和其他加起来只占7%。在广州遇到困难的时候主要会找亲人(67.86%)、同乡(50%)、警察(57.14%)和政府(50%)寻求帮忙。因为居住在一起而时常交流,互帮互助,这些亲戚、老乡之间形成了很强的连接纽带。
子女教育是藏族经营型移民最大的权益诉求。除了个别调查对象的孩子辍学或在老家上学之外,几乎所有的调查对象都遇到了子女入学难的问题。调查对象子女每年的入学费用都非常高,每年花费在5001~10 000元的占46.43%,10 000万元以上的占25%,只有3.57%费用在1000元以下,另有25%费用在1001~5000元之间。
另外,90%的调查对象表示在广州不同程度地遇到过“三拒”(酒店旅馆拒住,出租屋拒租,出租车拒载)的情况,其中租房被拒尤其普遍,特别是社会上出现有关藏族负面新闻的时候,拒租问题更为突出。遇到这种情况,久居在此的同乡长辈就会出面和房东协商,帮助他们解决租房问题。因此,为了防止出现中途回乡再出来找不到房子租或被拒租的情况,藏族移民们表示只要家里没事一般都不回去。一位访谈对象还谈到城市人在眼神和行为上不知不觉的关注带给自己的不适:“我有一次摆摊回来拉着我的货坐公交,旁边几个人看我穿着藏族衣服,看我的眼神就好像我做了坏事一样,马上往旁边站。一个小朋友可能没见过我的衣服,一直看着我,她妈妈使劲拽她,让我很难受,也很生气。”
从对周边居民的调查中我们也可看到,人们与这些藏族移民的交往极为有限。一位将房子出租给藏族移民居住的街坊表示,他们与租住自己房子的藏族移民并无交集,租房事宜都是通过他们群体中固定的话事人来对接安排的。房东表示,虽然听不懂这些藏族移民的语言,也不太理解他们的生活习惯,但把房子租给他们的这些年里,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情,房租也能按时缴纳,所以就放心地把房子一直租给了他们。
在穗藏族移民有着与朝鲜族迥然不同的生活状态,对于广州本地生活的融入度也较低,即使生活在广州,日常生活和社会交际网络也多局限于本民族的聚居区之内。藏族文化与广州本土文化上的巨大差异,一方面为藏族移民带来了赖以生存的“商机”,另一方面却在使藏族移民不断地遭遇到误解,导致他们在文化上的不适应;更进一步,也使得他们的“商机”难以从收入较低的小商品经济发展到系统化的资本积累阶段。语言隔阂、风俗差异以及遭遇到的一些偏见,造成了在穗藏族移民的文化不适应,也进一步阻碍了他们的社会融入程度。从藏族移民的案例中可以看出,经济因素固然是移民融入的一个重要方面,但经济收入背后的文化适应,则更应得到关注。在穗的藏族移民,虽然遭遇着种种的困难与不适应,但也一直在尝试扎根在广州,成为这个城市真正的居民。目前来说,藏族聚居区为他们的居留和生存提供了一个基本的依靠,但要走出聚居区,真正地融入到迁入地社会,还是依赖于优惠的民族政策与政府实践的帮助与驱动。
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因为疫情防控需要,人们的日常经济活动受到了极大影响,一部分在穗藏族经营型移民在新年离开广州后并未返回。随着国家层面对地摊经济的放开和推动,2020年7月广州市出台了《广州市流动商贩疏导区管理办法》《广州市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设置手册》,在部分区域划定临时摆卖点,允许流动商贩在规定时段进行摆卖,有序引导流动商贩入场入室入点经营,解决部分无业人员的就业问题。目前,广州市已建成流动商贩临时疏导区和临时摆卖点60多个,设置摊位8400多个。在笔者的追踪调查中,只有极少数的在穗藏族移民听说过地摊经济,他们不了解广州市的相关规定和做法,也没有人通过申请入市做生意。
四、分析及讨论
从在穗朝鲜族和藏族经营型移民的案例研究,我们可以看到推动中国城市少数民族移民形成聚集区的主要机制与国外的族裔聚集区有较大的差别。
从西方学者的研究来看,发达国家中族裔聚集区的形成来自于外部和内部两种机制的作用。从外部来看,不平等的族群等级导致了移民与主流文化的隔阂;从内部来看,移民为了实现在新环境中的适应有内部凝聚和自我保护的需求。内外两种机制的作用,共同推动了族裔集聚区的形成和发展。
而在中国移民城市的研究个案中,各民族移民都处于一律平等的社会大环境中,不存在由不平等的族群等级划分所导致的各民族在收入分配、教育程度、社会阶层、文化发展等方面的差异,因此并不存在导致移民聚集区的外部文化隔阂压力。在此种语境下,影响移民聚集区形成的外部机制主要是由城乡二元结构衍生出来的一系列本地人—外地人在社会公共服务和福利分配制度上的差异,也就是说少数民族移民群体的社会融入和适应首先是其作为外地人身份而存在的,这是其面对的首要和关键的适应问题,然后才是其作为一个与周边社会存在文化差异的族群而产生的文化适应问题。
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出现的主要动力在于移民群体内部。除了少数民族移民需要通过内部凝聚,实现城市适应这一普遍性的内部因素外,更重要在于其具有民族特色的移民经济,而移民经济与城市经济融合程度的差异,又直接导致了不同民族移民社会融入效果的差别。具体说来,移民经济作为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形成和发展的基础,其与城市经济的融合度高,成为城市经济结构中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那么其移民群体就能因此实现有效的社会融入,移民群体完全有可能被涵盖到国家、省市在新型城镇化进程中有关农民工市民化的一系列措施内,享受在子女教育、就业经营、社保、居住、积分入户等各方面的政策福利,甚至有机会突破本地人—外地人的结构界限,实现入户、购房和定居。而这种有效社会融入的实现,完全可以在移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与保留自身的文化及移民聚集区的延续同时发生。反之,如果移民经济与城市经济有较大隔阂,游离于城市经济的边缘甚至体系之外,那么移民群体在城市的生活就会表现出较为明显的隔阂性。相应的,移民群体不但难以纳入各项城市福利的政策范围中,更有可能与城市社会体系的运作存在对立性的矛盾。
从朝鲜族和藏族移民的个案来看,两个移民群体体现了两种不同的移民经济的融入模式。朝鲜族移民作为韩国人与中国城市的桥梁,其移民经济极具活力,链接着双方的信息和生活资源,既让朝鲜族移民在经济上取得了不错的收益,又产生了使其深度融入城市生活的文化推动力。其移民经济与城市社会的融合度较高,很大一部分朝鲜族移民是从事合法工作和经营,能定期纳税、缴纳社保,迁移趋势相对稳定的人群。其移民聚集区表现出来的文化特色不但不是难以融入的表现,反而是其移民经济活跃发展的重要因素,并获得了周边社会的认可和接受。而就藏族移民来讲,多数藏族摊贩无合法经营场所和手续,流动摆摊是其不得已的生计选择,其移民经济与城市管理体系存在着根本性矛盾,难以为城市社会所接受。因此,藏族移民群体不但难以被纳入市民化的政策范围中,更是成为城市管理的“问题”,再加上藏族移民在宗教、语言等方面与周边社会的显著差异,其移民聚集区就会表现出明显的经济边缘、文化隔阂的特点。因此,聚集区对于在穗的藏族移民来说,既是保护伞,也是进一步隔离藏族移民文化与广州城市文化的“透明墙”。
可见,我国城市少数民族移民聚集区形成的机制及其社会融入方面的效果与西方族裔聚集区理论论及的情况有所不同。其中最大的差别在于,我国不存在驱动移民聚集区形成的族群等级体系,移民聚集区的形成与移民经济有关。移民经济与城市体系的融合程度,影响了移民聚集区的社会融入效果,同时经济适应又为移民的文化和心理适应奠定了基础。
从两种不同类型移民聚居区的分析中引发出笔者对于打造互嵌式社区的一些思考。有关互嵌式社区的思想及其实践是城市少数民族移民服务和管理工作的一个突破性尝试,其积极意义不言而喻。然而,移民居住的空间隔离并不一定是互嵌式社区实践的障碍。笔者认为,互嵌式社区的打造应该在充分借鉴和批判西方族裔聚居区相关理论的基础上,做到因地制宜,灵活建设,尊重聚集区特色,首先做到经济融入,继而推动文化适应。
在穗朝鲜族和藏族两个少数民族的移民聚集区呈现出了不同的状态,针对依存于韩国人聚居区而形成聚落的朝鲜族移民来说,在穗韩国人“浅层融入,深度区隔”的背后,是朝鲜族移民完成资本积累真正贡献于城市建设,深度融入本土文化的积极策略。韩国人与朝鲜族的聚居区,已经成为人民安居乐业的城市社区,而且因为其突出的文化特征,已经成为城市多样性的象征。针对这样的民族聚居区,互嵌式社区的打造不应以打破空间上的隔离为出发点,而应该着重于积极引导,支持朝鲜族移民的正当生意,保护移民产业,让其扮演好外国移民和周边社会交流的桥梁。
对于空间隔离明确的藏族聚居点,目前表现出难以融入城市生活、文化不适应和经济边缘的状态,这说明移民聚居区的存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移民的融入。针对此类型聚居区的互嵌式社区打造,可以遵循打破“透明墙”,加强“保护伞”的原则。一方面,积极在空间上打破隔离,加强相关宣传与教育,让少数民族与周边社区居民彼此熟悉和尊重对方文化,促进不同民族间的友好交融,减轻因文化隔阂带来的不适应与“阵痛”;另一方面,也是最关键的,在于推动其生计方式与城市社会的适应。特别要利用当前国家层面鼓励发展地摊经济的机会,专门针对藏族移民宣传广州市实施地摊经济的政策和做法,帮助他们了解申请入市的程序和要求,为其入市经营提供便利。对其进行免费培训,建立藏族移民摊贩的管理档案,引导他们合法合规地开展经营,并在此基础上,推动其从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地摊式小商品经济向充满民族特色但更系统化的商业经营模式转变。而对已经有转型趋势的经营个体,则需要通过实施一些便利政策和帮扶机制,促使藏族移民提高收入水平,完成移民到城市的初期资本积累,成为真正的经营型移民,让城市成为他们真正可以扎根的地方,也让他们能够真正为城市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