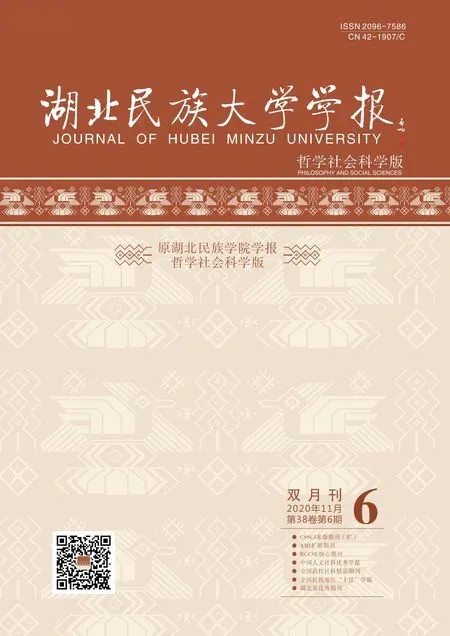“活在脚下”:重庆F区街头修脚女工的自我认同建构
王文涛
一、引言
修脚在我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传统老行当,早在商朝甲骨文中便有关于足病的记载。而关于修脚人的记载最早出现在明代《外科启玄》(卷七)中,至清代,修脚业才开始繁荣。清末民初,修脚业逐渐发展起来,但主要以街头修脚为主,形成了带有明显区域和地方文化特色的传统老行当。随着经济的发展、社会的变迁和政治制度的更迭,社会转型过程中的结构性矛盾、收入差距、社会不平等不仅使原有的底层群体出现了一些新的特征,而且不断有新的群体纳入底层中,加速了新兴底层群体的形成。(1)秦洁:《关于“底层”研究的相关概念分析》,《华南理工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0年第6期。时至今日,在中国南方的某些城市依然存在着传统的街头修脚形式。但是,现代街头修脚形式在从业者的性别构成、生存处境等方面相比于传统的街头修脚有了很大的变化。在法律层面,“贱民”的概念虽已消失,但在大众的观念里,修脚行当一直以来都被社会“污名化”,是“下九流”的低贱行当,街头修脚工身份地位低下,属于典型的底层职业群体。
底层职业群体的生存状况与社会心态是社会稳定的映射,是学术界历来深耕的领域。对底层职业群体的研究大致可以分为企业体制内劳工和流动散工两个方面。在企业体制劳工研究方面,打工妹是在社会深刻变革、跨国资本以及家庭三重社会压力下创造出的一个以阶层、性别和城乡差别为基础的特殊劳动者群体。(2)潘毅、黎婉薇:《失语者的呼声:中国打工妹口述》,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第8页。为了证明个体存在的价值,寻求现代性的生活体验,她们以“逃亡”的心态进入城市。作为都市里的农家女,她们的进城选择看似积极主动,实则是被动卷入现代化进程的无奈之举,且在劳动权利表达中普遍存在失语的状态。(3)杰华:《都市里的农家女:性别、流动与社会变迁》,吴小英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3-14页。然而,她们充分调动机灵而反叛的身体,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对父权制文化提出挑战,展演工厂中支配与抗争的复杂劳资关系,进而开创了一种新的抗争理论:“抗争次文体”。(4)潘毅:《中国女工:新兴打工者主体的形成》,北京:九州出版社,2011年,第193-195页。在浴场劳工研究中,刘博全景式描绘了浴场劳工在城市社会生活中的日常经历与个人情感,借助隐喻提供了一个具体的、微观的社会底层从业者群体研究与反思的文本,为理解当代中国情境下社会阶层普遍存在的主体焦虑提供了一个分析视角。(5)刘博:《浴场劳工:服务者的生活世界与身体实践》,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2013年,第5-10页。在流动散工研究方面,秦洁通过“都市感知”对重庆“棒棒”开展民族志研究,专注于城市融入过程中“乡土性”的主题,探讨了以“棒棒”为代表的城市流散农民工在城市化过程中如何选择性地坚守“乡土性”、选择性地适应“都市性”的问题。(6)秦洁:《重庆“棒棒”:都市感知与乡土性》,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14页。而三和青年在面对不公正的待遇时选择了一种新的抗争模式:为了避免持续的“剥削”,他们纷纷逃离工厂,出现了一种“干一天玩三天”、做日结、跑路的“反工厂文化”,在大都市里“混吃等死”。(7)田丰、林凯玄:《岂不怀归:三和青年调查》,北京:海豚出版社,2020年,第7页。
可以说,进城农民工构成了底层职业群体的主体,他们离开了乡村却又不属于城市,过着“流而不迁”的“钟摆”生活。(8)周大鸣:《渴望生存:农民工流动的人类学考察》,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222页。底层职业群体在城乡空间置换中面临着城市适应和角色转换困境,容易引发身份认同危机。在学术研究中,人们往往专注于社会结构与社会变迁带来的社会不公,忧心于社会底层群体的生活境况与艰难生计,较少挖掘他们在艰难处境下积极主动面对生活的社会心态。
“在大众主义消费盛行的今天,人们似乎把太多的目光留给了消费和消费者,而忽视了服务于身体的劳动和劳动者是怎样的事实。”(9)陈龙:《身体的劳动与劳动者——以足疗店青年女技师为例》,《青年研究》2016年第2期。在本文中,我们将街头修脚女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利用滚雪球式访谈、体验式观察等调查方法,对分散于重庆市F区街头巷尾的27位修脚工展开实地调查,探究现代化背景下街头修脚女工的自我认同建构。具体的样本分布情况是:兴华中路(XHZL)5人,罗家花园(LJHY)4人,马鞍新区(MA)4人,易家坝(YJB)1人,南门山(NMS)4人,重百(CB)9人。本研究并不是对底层职业群体生存处境的“诉苦式”描述和“情景式”展现,以谴责社会不公以博取社会同情,而是以街头修脚女工为主体,关注其在艰难处境中所呈现出的积极主动的自我调适的社会心态与自我认同建构。街头修脚具有明显的地域文化特色,对街头修脚女工自我认同的研究可以窥视当代中国情境下社会底层职业群体的生存处境和社会心态,有助于理解街头文化和地方性知识,引发和培育社会对底层职业群体的人文关怀。
二、现代社会下的街头修脚:认同危机与生存处境
早在古希腊时期,西方哲人就提出了“认识你自己”的哲学命题,并把它视为人类活动的重要任务。在高度现代化的情境中,吉登斯将自我认同置于现代性的视域下。他认为,一个人的自我认同不是个体与生俱来的自然特质或特质组合,而是个体通过自身所经历的社会事件,不断地进行自我反思与总结,最终在内心形成一种“我是谁”的自我意识和总体认识。(10)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与自我认同——晚期现代中的自我与社会》,夏璐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6年,第87页。吉登斯对“自我认同”的理解具有显著的唯心主义倾向,即强调自我认同是自我反思性的结果。所以,有学者对“自我认同”的概念进一步阐释和扩展,认为“认同最根本的涵义是对自我的界定,即自我认同,而自我只能在社会关系当中完成自我界定。”(11)张海波、童星:《被动城市化群体城市适应性与现代性获得中的自我认同——基于南京市561位失地农民的实证研究》,《社会学研究》2006年第2期。也就是说,自我的认知和定位产生于一个人在社会中的角色位置、自身资源的多寡、社会处境、社会中的互动和交流等。
(一)社会角色定位:社会底层从业者和底边群体
中国台湾学者乔健提出了“底边阶级”的概念,他认为,“底边阶级”是中国传统社会中的一个特定阶级,游离在“士农工商”四民之外,处于社会底层和边缘,且社会地位低贱,一般是从事日常服务类行业的群体。(12)乔健:《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一些概念、方法与理论的说明》,宋文薰等编:《石璋如院士百岁祝寿论文集:考古·历史·文化》,台北:南天书局有限公司,2002年,第429页。以乔健、岳永逸为代表的学者,通过对中国传统社会中存在的诸如乐户、堕民、剃头匠、杂耍艺人、疍民等“贱业”从业者的调查研究发现,他们社会地位卑微,并被抛离出主流社会,由他们所组成的社会便是“底边社会”。(13)乔健:《底边阶级与边缘社会——传统与现代》,台北:台北立绪文化公司,2007年,第15页。新中国成立后,经过社会主义改造、公私合营、改革开放等政策措施,“底边阶级”虽然已经不复存在,但是社会结构化调整所积累下来的、生活于社会底层的底边群体依然存在。
从群体特点、社会地位和经济收入等方面看,街头修脚女工属于典型的底边群体。她们在经济上往往是贫困的,并且难以通过自身的努力实现地位提升。由于自身所掌控的经济资源欠缺、社会支持网络薄弱,加之身体劣势,街头修脚女工在社会生活中往往面临来自社会各方面的歧视与市场的挤压,她们为生存抗争并进行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的建构。
(二)身份迷失:城乡空间置换中的认同危机
街头修脚女工来自于农村或城市郊区,内心充满了基于乡土生活经验和文化观念的都市生活想象。她们认为在城市修脚市场需求大、生存机会多、赚钱容易,而且城市生活丰富多彩,此种对城市生活的想象正是她们的入行动机。(14)秦洁:《“棒棒”的生计方式与就业空间研究》,《社会工作与管理》2015年第4期。但是,在她们顺利进入城市工作之后,她们对于自身却仍处于一种模糊的认知状态,乡村与城市存在着极大的反差,农村人的“礼俗性”特质与城市人所体现的“法理性”特质形成鲜明的对比。(15)谭翔鹏:《重庆“棒棒”的身份认同和归宿研究》,《文存阅刊》2018年第17期。
在从农村到城市的空间置换过程中,街头修脚女工容易出现身份迷失,即她们既脱离了农村,又不属于城市。脱离了农村意味着缺少了乡土社会中血缘宗族、风土人情等赋予她们的身份认同,而生活在城市她们又无法建立起新的社会支持网络和族群共同体。面对城市的排挤、社会的不公正待遇所造成的人际冲突,她们的身份认同面临重构。她们在城市生活中往往通过延续一定的乡土社会文化特质,坚守自由的生活等方式来缓解和避免城市生活节奏的影响和规章制度的束缚。(16)秦洁:《农民工的都市想象——基于对重庆“棒棒”入城动机的人类学考察》,《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年第3期。也可以说,街头修脚女工的城市生活体现出了“文化变迁与文化固守并存、文化认同与边界意识明显、文化寻根与文化重构交融的重要特征。”(17)王希辉、莫代山:《武陵走廊散杂居民族的文化特征与研究价值述论》,《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年第5期。
(三)生活方式转变:养生保健风潮兴起
生活在现代社会,人们一直用各种方式不断追寻健康的生活方式和美丽的外貌。“20世纪70年代出现的所有实践活动(身体疗法、健身、慢跑)发展到极端,使个体成为其身体的产物。想要改变生活只需改变身体。”(18)帕斯卡尔·迪雷、佩吉·鲁塞尔:《身体及其社会学》,马锐译,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17年,第45页。一方面,环境污染和生态破坏导致生存风险,加之激烈的社会竞争,人们普遍经受着生存环境恶化、心理压力过大和身体亚健康的困扰;另一方面,生活水平的提升增强了人们的养生保健意识,经济收入的增加使人们有了消费养生服务和购买保健产品的经济实力,在物质生活得到极大满足的条件下,人们更加注重生活质量和个体的健康美丽。
此外,随着社会舆论和传播媒介对健康、审美等铺天盖地的宣传,人们越来越关注自己的身体健康和体型的美感,足疗店、养生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在经济结构调整和优化的大潮下,政策倾向和市场前景驱动着养生保健行业迅猛发展,养生保健俨然成为一种关注身体、改造身体的时代潮流。现代化生活方式为修脚行业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遇。
(四)生存空间压缩:现代化专业修脚店的兴起
丹尼尔·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呈现出明显的时代特征:农业和制造业因为机械化和信息化的普及致使对劳动力的需求日渐减少,而服务业吸纳了社会上的大部分劳动力,服务型经济得以创立。(19)丹尼尔·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高铦、王宏周、魏章玲译,北京:新华出版社,1997年,第14页。后工业社会所带来的现代化冲击着传统的政治体系、经济体系、文化体系。高楼大厦侵占了窄巷小院,机械流水线生产超越了手工作业,那些历史悠久的民间传统手工艺和牵系着平民百姓日常生活点滴的老行当,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街头修脚面对现代性的冲击并没有像其他老行当一样彻底淡出人们的视野,而是实现了现代化的转型,即修脚店的兴起。修脚店相对于街头修脚来说专业卫生、服务周到,它一方面满足了人们追求安逸舒适的服务体验的需求,另一方面也压缩了街头修脚的生存空间,加剧了其生存困境。
自我认同的建构往往对应的是自我认同危机,而这种认同危机来源于社会转型、生活方式转变、生存空间转换等因素的影响与冲击。目前对社会底层行当从业者身份认同的研究凤毛麟角,仅有的少量学术研究成果多集中在底层行当从业者自我认同迷失、传统文化传承视域下的身份确认与认同再造等方面,其间充斥的社会心态往往是消极无奈与自我保护性顺从。
三、自我认同建构:身份调适与主体性强化
街头修脚女工是社会底层职业群体的典型代表,她们自我雇佣,进行着自主自立的劳动生产。此外,现代机械流水线生产以及人们生活方式的改变挤压着街头修脚行当的生存空间。街头修脚虽然是底层活路,从业者却可以借此维持生计,她们能够理智地看待并接受自我以及客观处境,可以长久坚守而不会轻易离开,从而建构起了较高的自我认同。
(一)满足收入预期,获得生存保障
在现代化背景下,社会身份的界定已经不再完全遵照和取决于恒定不变的世袭头衔,而一个人在发展迅速、变幻莫测的经济体系中的表现成为市场经济下个人身份认同的重要影响因素。(20)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88页。也就是说,市场经济视域下人们对自我价值的追求可以简单地解释为对财富的追求,经济因素成为衡量一个人身份地位和自我认同的重要因素。
首先,街头修脚女工的自我认同建构与经济收入紧密勾连,其从业动机和职业选择遵循“经济理性”原则,较少考虑晋升机会、职业发展前景、空间环境以及社会评价。53岁的修脚工李阿姨表示,修脚仅仅是一个工作,对于未来她没有太多的期待和规划。
现在还在乎被人看不起干吗啊!这是一项工作,而且我能够挣到钱就行了啊。别人说就去说,我不在乎。说什么自己又不痛不痒,挣到钱才是最实在的噻。有钱你的生活就有保障噻!被人看得起能当饭吃啊。(LJHY2-20190922)
其次,街头修脚的经济所得虽然不多,但是对于一个底层家庭来说却是不可或缺的。她们利用街头修脚的收入足以支付“柴米油盐”等家庭日常生活开支,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家庭经济负担。所以,修脚女工虽然从事底层的街头修脚行当,但总会得到家人的鼓励和支持。65岁的王大娘,从业3年,女儿离婚在家待业,生活的压力让她和丈夫不得不拖着年迈的身体外出讨生活。
现在孩子们的压力都很大,平时我男人挑着扁担在街上卖海椒(辣椒),我摆摊修脚,我们老了,能自己赚点就赚点,不给孩子们添负担。如果能攒下点钱,我们还可以给孙子买点零食啥的。(CB4-20181113)
最后,街头修脚所用工具简单,投资少,大部分底层群体都可承担;此外,街头修脚是一个“即时性的付薪”行当,劳动付出收获即时的经济回报,不存在拖欠工资的现象。余阿姨,52岁,2000年不幸遭遇车祸截肢后,就一直在兴华中路摆摊修脚。
我这里最贵的就是这一套修脚刀具,孩子帮我从网上买的,两百多(元)。其他的都是从家里带过来的。修脚这个基本是没有什么成本的,修一双脚赚一双脚的钱,而且当时就能见到钱。(XHZL1-20190709)
经济基础决定一个人的社会地位与自我认同,底层群体的生活有了保证,社会地位必然会提高。(21)王文涛:《“脚下”的人生:修脚工身份地位变迁的社会史考察》,《青海民族研究》2019年第3期。街头修脚的“即时性”经济收入不仅让修脚工生活自给自足,还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这是吸引社会底层中老年女性的最主要动力,也是获得较高自我认同的决定性因素。
(二)工作时间自由,兼顾家庭责任
在现代社会,自由的工作时间成为职业选择的重要参考因素,表明了个体对自主性和个性化的发展诉求,以及现代企业制度下对人身自由控制的逃避与违抗。街头修脚工自由的工作时间不同于现代企业或单位中所流行的固定工作时间,它是一种个人对工作时间的自由选择。
首先,街头修脚是一种自我雇佣的劳动形式。工作时间具有多变性、灵活性和选择性,身体不受权力和制度的约束,能够随时来,又可以随时去。在我们的访谈中,有4人是60岁以上的老年修脚工,她们年迈体弱,不能高强度长时间修脚,由她们自行决定出工时间。马鞍新区修脚工张大娘,62岁,身患糖尿病等多种慢性病,自由的修脚时间可以有效地缓解身体劳累。
修脚这个工作并不累,比较自由,出来不出来自己说了算,累的时候可以早回去,少修几双脚,身体得行的时候,就多修几双脚。(MA3-20190826)
其次,自由的修脚时间。修脚女工一方面可以履行对孙辈的看护抚养义务,另一方面可以使她们在工作之余照顾家中的老人或病人。在我们访谈的27位街头修脚女工中,有14人家中有老人需要赡养,12人需要协助子女看护孙辈,有5人既要赡养老人又要照看孙辈。兴华中路一位55岁、从业6年的修脚工,家中不仅有年迈的公公婆婆,还有生病的丈夫,自由的修脚时间对她来说十分重要。
我公公婆婆年纪大了,丈夫又有病,我哪能走得开?我挺愿意出去打工的,但是像我这样的家庭,时不时的需要回家一趟,看看家里的病人和老人。在外面上班都是按点的,去晚了和走早了都不行噻!(XHZL3-20191109)
在当代中国,“男主外女主内”的社会传统依然延续。女性在家庭中承担着抚养后代、照看老人和从事家务劳动的职责。街头修脚女工之所以对自由的工作时间如此看重,主要基于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她们来自农村,日常的农业生产和田间劳作对出工的时间要求并不严格,所以传统的农民身份使她们很难适应现代企业制度下严格的时间制度以及行为规范;二是她们大多家境贫寒,家庭成员众多,特别是在当下年龄(50~60岁),家中一般都有高龄老人需要赡养,或有幼小的孙辈需要照顾。街头修脚虽然作为一个不为人所看好的底层行当,但是因为它工作时间自由,使从业者具有较高的职业倾向性。
(三)选择参考群体,寻求自我安慰
参考群体(亦称参照群体,或重要他人)提供了一个个体用来评价自我以及与他者的比较框架。1942年海曼最先提出“参考群体”这一术语,他认为人的主观地位应该定义为与他人群体对比后得出的自我社会地位认知,其中他人群体指的是人们的参考群体。在形成行为和评价方面,人们常常使自己取向于他们自身之外的群体。然而,重点方面的转移会很容易被误解为只有非隶属群体对于参考群体行为才具有重要性;这是一个不能很快被消除的误解;参考群体几乎是无数的,个人是其成员之一的所有群体和那些个人并非其成员之一的群体都可以构成某人态度、自我评价及行为的参考点。(22)罗伯特·K.默顿:《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唐少杰、齐心译,北京:译林出版社,2015年,第405页。街头修脚女工通过与参考群体的比较来获得一定意义上的自我认同。
首先,街头修脚女工选择隶属群体内的个体作为参照,进行比较。隶属群体内的参考群体主要包括两类:一类是由擦鞋匠转行来的修脚工(11人),她们入行时间较短且“自学成才”,没有经过正规的培训,修脚手艺较差;另一类是入行时间较长,接受过专门培训的“专业修脚工”(16人)。然而,街头修脚女工往往选择不如自己手艺、低于自己收入的修脚工进行比较,从而进行自我认同建构。于大娘在南门山街头修脚行业中从业时间长,修脚手艺好,她经常拿周围从业时间短的修脚工来作比较。
你看那些擦鞋转来的,她们没有专门学过啊,根本就是在乱修,有的是直接把别人的脚修出血了。和她们相比,我修脚算好的,我的顾客比她们多,收入肯定也比她们多。(NMS4-20191103)
需要指出的是,擦鞋匠与修脚工同处一块工作场地,通过日常的工作观察和收入比较,促使部分擦鞋匠毅然投身街头修脚行当,在日常的身体实践中一边擦鞋,一边磨炼修脚技术,她们期待未来某日既可以擦好鞋,又可以修好脚。高阿姨55岁,从擦鞋匠转为修脚工仅半年时间,其修脚技术还在自我学习和熟练的过程中。
我们擦一双鞋才3块钱、5块钱,她们修一双脚要10块钱。其实我们擦鞋费的功夫并不比修脚少,而且修脚不难学。我以后就想既可以擦鞋,又可以修脚,这样就可以有更多的生意。(NMS2-20191103)
其次,街头修脚摊位周围存在许多“伴生群体”,他们包括擦鞋匠、修理匠以及小商贩等,街头修脚女工对非隶属群体内参考群体的选择不仅包括以上几种伴生群体,还包括环卫工人、门卫等群体。52岁的街头修脚工张阿姨对自己现在的修脚职业很满足。
她们那些擦鞋的、打扫卫生的、扫大街的不仅比不上我们自由,而且收入也不比我们多。小贩需要往里投钱,搞不好就会赔钱,我们修脚就不需要什么投入。门卫、扫大街的是按月发工资,我们修一双脚就有一双脚的钱。现在干这个修脚我就很知足。(CB2-20191117)
个人若想获得成功的感觉、建构较高的自我认同,其最佳途径莫过于选择一个与自己同质性强且稍逊于己的个人或群体作对比。街头修脚女工自我认同的建构和自我价值的感知与实现,一方面通过与周围群体的参考和对比来获得,另一方面来自于自我安慰。如果仅仅看重别人的评价,缺少自我调适与自我安慰,就会容易形成自我焦虑。在日常生活中,我们对事物所形成的种种期待、评价和判断必然有一个参考群体作为比对,只有和与自己同质性强、具有相似人生经历的他人做比较,我们才能确定合适的、理性的和容易达成的个人期待和愿景。(23)阿兰·德波顿:《身份的焦虑》,陈广兴、南治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7年,第38、49页。街头修脚女工通过与参考群体比对,感知自我在隶属群体或非隶属群体内的身份地位和角色位置,从而获得清晰的自我认知,降低自我期待。
(四)清晰的自我认知,合理的自我期待
现代社会激发了人们无限的期望,人们之所以感受到自我价值难以实现,重要原因在于我们的能力和需求之间、现实地位和理想地位之间存在着难以填补的鸿沟。德波顿认为,人生在世,一个人的自尊不仅受制于我们日思夜想所要达成的理想和为了理想而付出的所有努力和行动,还取决于个体当前的现状处境与自我期待之间的比率。①所以,要想获得崇高的自尊,一个重要的途径是拥有清晰的自我认知,建构合理的自我期待。
街头修脚工群体由年老体衰、文化水平低的中老年妇女组成。在27位修脚工中,60~65岁的有4人,50~59岁的有16人,50岁以下的仅有7人,其中初中文化程度仅有9人,大部分是小学文化程度(15人),甚至是无受教育经历(3人)。她们已超过了外出打工的黄金年龄,她们能够比较理性地看待自身条件以及自我所能够支配的社会资源,认为能够有一比较稳定的谋生手段或是稳定的经济收入,便会拥有很高的自我满足感。
像我们这个年纪的人,身上不是这里不舒服,就是那里不舒服,干重活干不了。你看我,平时修脚能挣个生活费,不拖孩子们的后腿,多好啊!修脚是名声不太好,但是到我这个年纪还能在乎这些?(MA3-20190826)
街头修脚女工这种清晰的自我认知还来自于家人,甚至是社会对其恰当的角色期待。刘大娘57岁,从业5年,在谈到家人对自己工作的态度时显得特别欣慰。
他们对我没什么要求,人慢慢地老了,只要身体健康,他们说就很知足。我愿意做这个修脚,他们就支持我,挣多挣少无所谓,只要我开心就好。(NMS3-20191103)
街头修脚女工的自我认同与自我安慰紧密相关,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参考他者的看法和评价。她们的自我认知、自我期待并没有超出自身条件和能力,因此,身体与期待之间并未发生断裂。自我身处底层世界,身体劣势、家庭牵绊、生活处境等客观现实增强了她们的职业认同感,而这种职业认同感是她们建构自我价值、增强自我认同的重要来源。
现代社会“对我们的生活世界所造成的最大的紧张与焦虑,并不是经济与技术发展的问题,而是价值认同的问题,是克服对本体的安全和存在性焦虑,在充满冲突和断裂的多元社会中对自我重新定位。”(24)赵静蓉:《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5年,第3页。对于街头修脚女工等底层职业群体而言,自身所具有的发展资本不足以满足和应对现代社会市场对劳动力的基本要求。由于不具备心智、年龄、性别以及体力优势,只能选择地位较低、工作收入微薄的街头修脚行当。身体上的劣势和能力上的不足产生了相应的身份认同,由此,街头修脚女工才会在街头修脚行当中待得长久。
四、自我认同背后的社会价值再生产
“人的自我认同与主体性建构不是给定的,而是自我反思的结果。它们发生在自我意识之中,但又不是孤独主体的自我反思,不可能由自己独立完成,它们的形成、实现与个体的社会归属感密切关联,是个体与社会互动的结果。”(25)刘传霞、石成城:《集体主义时期城市底层家庭妇女的自我认同与主体建构》,《妇女研究论丛》2018年第3期。人是社会性的动物,街头修脚女工自我认同建构的背后蕴含着丰富的社会价值再生产。
(一)性别分工与主体性建构
现代社会的发展日渐解放劳动的性别约束,但是自古形成的“男主外女主内”的劳动分工理念依然存在。在男性主导的家庭权力模式下,生活中的成年女性往往存在个人与家庭的结构性冲突,而这种冲突在“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妇女中尤为突出,其外在表现为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以及女性个体在家内、家外的角色冲突。(26)宋少鹏:《中国女性身份认同的历史与现实》,《文化纵横》2015年第1期。传统文化所形成的“女主内”的思维定势牵制着女性,将中老年妇女禁锢于家庭之内。
首先,在男性主导的家庭权力模式下,女性处于从属地位,特别在底层社会,中老年妇女的经济权力、生活话语权严重依附于男性。她们一旦步入老年,由于身体劣势,家庭牵扯,加之年老体衰,中老年女性的生活选择非常有限;同时,一旦获得工作机会,她们便会具有较高的职业认同。此外,中国有句俗语:男做女工,越做越穷。街头修脚特有的职业形象和工作性质,在男性看来并不体面,所以男性极少从事街头修脚行当。
我家里他(丈夫)说了算,我们老了不容易找钱,我跟他说咱俩一起出去修脚。他不干,他觉得丢人。(CB7-20191120)
其次,风险社会背景下,年轻人面临着巨大的职场压力和家庭负担。作为家庭中的一份子,老年人有责任且有意愿分担家庭发展过程中的职责和义务。一方面,承担日常的家务劳动与孙辈看护;另一方面,通过自身的劳动力和手艺,补充家庭的经济收入。街头修脚女工呈现出乐观积极的生活样态,积极主动地开展自我主体性建构,积极融入到家庭的经济生活之中,有限度地参与家庭建设,没有因为家庭的结构性排斥和主流价值观的脱离而走向“自我边缘化”。56岁的林阿姨,家中两个儿子,面临着娶妻成家的经济压力,她尽力分担家庭的生活负担。
现在年轻人压力多大啊,起早贪黑也挣不了几个钱。做父母的能白看着孩子受累?我们现在还爬得动,得分担孩子们的负担噻,在家里不能光吃不干活。(LJHY3-20191103)
最后,老年人的晚年生活可以通过劳动、工作实现经济独立;保持身体健康、生活自理、避免失能;维持独立人格和精神自强。(27)穆光宗、淦宇杰:《给岁月以生命:自我养老之精神和智慧》,《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自我养老不仅体现在老年人的经济独立上,还在于日常生活和精神层面的独立。街头修脚女工从事修脚行当是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积累养老后备资源、培养自我养老意识的有效方式。她们通过修脚获取生活来源,实现一定的经济独立,从而根据自我喜好安排自己的生活。
现在孩子们挣钱难,我们老年人能出来挣一点是一点,存点钱,走不动了也少跟年轻的要点钱。(MA4-20190826)
底层社会家庭妇女依附于男性的突出表现是经济难以独立,所以,街头修脚工的职业收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使其在老年生活中掌握经济主动。街头修脚女工的主体性建构既有社会现实的推力,也有自我内心的拉力:一方面是家庭发展压力促使其发挥余热,继续为家庭建设贡献力量;另一方面积累自我养老储备,实现自我独立。
(二)街头公共空间与再社会化
一方面,街头商贩在过去经常被定义为影响市容市貌的重要因素,为了改善城市街头景观,基层政府对街头商贩实行简单直接的严厉管制,压缩了他们的生存空间。(28)胡俊修:《流动商贩与中国近代城市社会》,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年,第312页。时至今日,基层社会治理更加体现以民为本,民生与市政冲突大为缓解,底层群体不断涌入街头公共空间谋求生计。另一方面,社会发展日新月异,老年人传统观念依然延续,且随着年龄的增长,身份角色发生巨大变化;他们淡出家庭决策,在现代化背景下与社会主流价值容易发生“断裂”,成为边缘群体。此外,他们禁锢于家庭,从事简单繁杂的家务,自我价值和自我认同严重依赖于家庭。街头修脚可以帮助底层中老年妇女走出家庭,并且提供了一个再社会化的情境。
首先,随着基层政府行政职能的不断转变,以民为本的服务理念渗透进基层社会治理的方方面面,街头流动小贩的生存空间更具有弹性。从街头路面严禁摆摊到有序发展地摊经济,街头修脚工的身份地位得到认可,自我身份得以重建。一位从业7年的修脚工回忆了过去与现在街头摆摊的不同。
以前城管是不让我们在这里摆摊修脚的,后来开始收取摊位费,一个月40块钱。现在政策放宽了,他们给我们指定一个位置,然后登记一下我们的信息,不花钱就可以在这里修脚了。(CB9-20191120)
其次,街头是城市最重要的公共空间,它们不仅担负着城市的交通,而且还是日常生活和经济行为的载体。一个相对独立的场域代表了一个社会小世界,(29)布尔迪厄、华康德:《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5年,第123页。街头巷尾就是一个特定的场域,它聚集了众多商贩和行人,为修脚工提供了一个再社会化的有效场所。修脚工走上街头,摆摊修脚,她们主动参与到社会分工中来。在街头的特定场域里,她们与修脚顾客、周围摊贩、过往行人闲聊,感知人间冷暖与社会发展。一位48岁、从业4年的修脚工对此很满意。
我们这地方每天经过的人非常多,什么人都有。你看他们穿的衣服就知道现在流行穿什么。我们没活的时候,我们在一起摆摊的有说有笑,说说家长里短,比窝在家里开心多了。(CB3-20191108)
通过街头摆摊,修脚女工可以重新定位社会角色,建立新的社会关系,感知社会发展,认知社会秩序。街头修脚行当是中老年女性走出家庭,参与社会化劳动,主动融入公共生活的一种选择。
(三)街头文化与地方性知识
街头是城市中最受注目和使用率最高的公共空间,它是地方文化最有力的体现,在中国城市生活中总是扮演着一个中心角色,城市民众利用街头空间参与经济、文化、社会和政治活动。(30)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4页。街头修脚工是街头空间和社会关系网络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身体实践与人生百态塑造了特有的街头文化,使街头空间深深地打上了地方性知识的烙印。
修脚行当在特殊的自然环境和社会氛围中孕育,它深深地嵌入到地方社会结构和文化传统中。F区特有的地形和气候促进了街头修脚行业的发育:首先,地形崎岖不平,上坡下坡台阶众多,脚部容易经受挤压和磨损;再次,F区无风无雪无霜冻的气候可以使人们比较舒适地将自己的脚部外露接受修脚服务。此外,修脚是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作为传统老行当的街头修脚在现代社会中仍然占据着职业空间,因价格低廉、随到随修以及流动性强的特点,其服务对象往往是城市底层群体,特别是老年人和以体力劳动为主的低收入者。街头修脚女工来自于底层社会,同时也服务于底层群体,底层群体的修脚需求延续着街头修脚的生存空间。
修脚是从中国传统社会流传至今的“老行当”和民间手艺,在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和“非遗”保护的背景下,街头修脚是一种重要的地方文化载体和产业资源,它是理解地方文化的一个重要文本。政府可以通过“购买服务”的方式,将其纳入到城市文化建设的总体规划中来,采用“生产性保护思路”,定期组织街头修脚工为社会弱势群体进行修脚服务,发挥民间传统手艺服务社会、奉献社会的作用;规范修脚摊位,提高服务的质量和水平;对街头修脚文化进行挖掘,通过多种途径进行宣传,努力将街头修脚发展为地方旅游和城市文化的名片,促进修脚技艺的保护与发展。
总之,需要给予街头修脚女工足够的人文关怀,不断提升其职业认同和自我价值;赋予她们新的社会身份,使修脚手艺成为社会底层群体脱贫的重要方式,使她们成为传承民间文化的重要载体。保护和发展街头修脚文化,对留存集体文化记忆和传承民间文化具有重要的价值。
五、小结
街头修脚女工自我认同体现的是风险社会背景下底层职业群体的生存处境与社会心态。她们的自我认同建构一方面体现出“他者化”特点,另一方面,自我认同建构的背后也蕴含着社会价值的再生产。通过街头修脚行当,她们既获得了工作权,实现了自我经济地位的提升,又保留了原有的传统生活样态。当然,传统修脚行业也面临风险社会的冲击和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不同的底层职业群体体现出不同的社会心态和社会情绪。
社会发展过程中的结构性问题容易制造矛盾。首先,贫富差距悬殊,容易引发民众利益被剥夺的社会心态;其次,社会保障不到位,个人需求难以满足;最后,公共权力缺乏强有力的监督和限制,不时造成“合法性伤害”。(31)成伯清:《从嫉妒到怨恨——论中国社会情绪氛围的一个侧面》,《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10期。结构性的社会问题可能催生扭曲的社会心态,容易引发底层职业群体的厌世情绪,从而蓄意报复社会。将社会转型所引发的问题纳入到底层职业群体社会情感的角度进行考量,展演现代化浪潮中底层职业群体的生存处境、生存逻辑以及社会心态,从而引发和培育社会对底层职业群体的人文关怀,这是街头修脚女工自我认同研究的终极学术关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