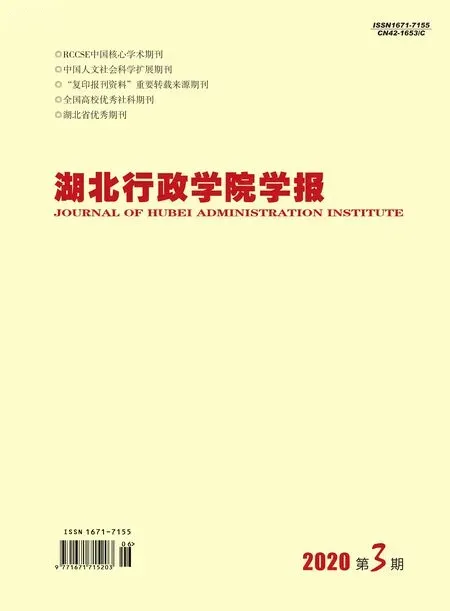武昌首义“第一枪”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郭国祥,王欣欣
(武汉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湖北 武汉430070)
辛亥革命是中国由封建专制社会走向民主共和过程中的重大历史事件。揭开这场巨变大幕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由谁打响,一直是史学界争论不休的话题,也涌现了不少的学术成果。本文拟从狭义和广义两个角度对相关研究进行梳理和点评,并对今后研究提出展望。
一、狭义的“第一枪”
狭义的“第一枪”也就是指时间先后上的第一声枪响。曹忠生曾对“第一枪”的概念作过说明,即武昌首义“第一枪”特指1911 年10 月10 日晚时间顺序上的第一声实实在在的枪响。他还特别强调,只要这一枪是在约定的起义条件下打响的,且在客观上取得了众人响应的效果,那么无论这一枪打响的主观目的为何,也“不管是自行走火,还是蓄意放射”[1],都必须承认其为首义的“第一枪”。那么到底是谁打响的第一枪呢?目前学术界主要有以下几种观点:
(一)金兆龙打响“第一枪”说
万耀煌先生在《辛亥首义答客问》一文中提到首先开枪的是金兆龙。黎澍在《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政治》一书中说:“夜晚七点钟,工程第八营后队的一个排长巡查营房,与该排士兵程正瀛及该排副目金兆龙发生冲突,排长被猛击倒地。”[2](P34)一些首义人士的回忆文章也证实了10 月10 日晚是金兆龙第一个直接与清兵进行生死对垒的,如熊秉坤的《金兆龙事略》对当天起义谋划经过有较为详细的说明:“翌日,龙遂与陈振武、程正瀛、钟士杰三君会议,各给子弹三颗……令钟士杰刺本队队长,程正瀛刺二排排长,陈振武刺三排排长,龙与王忠威在后援助。”[3](P70)胡石庵的《湖北革命实见记》也引用了朱思武对当晚起义情形的具体描述:“陶启胜巡查各处营房,窥见金兆龙皮盒内有真子弹数排,呵斥其是否准备谋反,金大怒,回答道‘反!反!即反矣!’,即扑向陶启胜,双方开始扭打起来。”[4](P12)贺觉非、冯天瑜根据熊秉坤等亲历者早期文献的具体描述,认为金兆龙应该是10 月10 日晚第一个和清兵扭打的人,说是“第一打”应该是可以的,但并非是开“第一枪”的人[5](P176)。
(二)程正瀛打响“第一枪”说
冯天瑜在《谁打响“辛亥首义第一枪”》一文中搜集整理了很多首义亲历者的早期文献,特别是熊秉坤本人的早期文献,以翔实的材料说明程正瀛打响“第一枪”才是真实的历史,并对“熊一枪”说流行的缘由提出了自己的解释。他指出熊秉坤在1912-1913 年间曾为当时的湖北革命实录馆撰写过《前清工兵八营革命实录》、《前工兵八营革军各执事暨各会员事略》等4 篇文稿,对起义功勋人物及其事迹都有较为鲜活的记载,这些文稿无一例外都承认是程正瀛打响的“第一枪”。只是后来因为这批原始文献长期湮没,程正瀛因为背叛革命而被人逐渐遗忘,孙中山对“熊一枪”的倡议,熊秉坤本人的记忆变化及其各种名位利益的考虑,“熊一枪”说才逐渐成为主流观点[6]。白雉山在《到底是谁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一文中特别强调,面对程正瀛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铁证如山的史实,必须尊重历史,拂去“历史的灰尘”,恢复“程一枪”的本来面目。范荧亦认为,武昌首义“第一枪”是客观存在的历史事实,不会因人的忠良贤愚而改变,不能因为程正瀛的晚节不保就抹去他打响“第一枪”的历史功劳。
(三)熊秉坤打响“第一枪”说
目前的教科书和主流媒体都坚持这一观点。“熊一枪”说得力于几位重要历史人物如黎元洪、袁世凯、孙中山、居正等人的坚持。1913 年1 月,袁世凯政府根据黎元洪的报告授予当时陆军少将熊秉坤勋五位证书,中有“盖闻时逢走鹿,难每发于一夫;势等连鸡,功莫先于首”这样的溢美之词。孙中山考虑到熊秉坤是革命党在新军工程第八营的正式党代表,为了争“革命党人推翻满清之功”,自然力推“熊一枪”说。1914 年,熊秉坤陪孙中山到日本,在一次聚会中,孙中山向在座客人隆重介绍熊秉坤,说:“这就是武昌首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7](P553)1918 年双十节,孙中山又在《晨报》撰文,称“今日何日,此非我革命同志熊秉坤以一枪起义之日乎!”[8](P248)1919 年双十节,孙中山在《八年今日》中再次提及:“今日何日,乃革命党员熊秉坤开枪发难,清朝协统黎元洪被迫效顺而起革命军于武昌之日也。”[9](P131)同一时期,孙中山在撰写《建国方略之一》时,在《有志竟成》一章中写到“为自存计,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10](P243)孙中山作为革命领袖对熊秉坤打响“第一枪”可以说是不遗余力地肯定和宣传,这自然让熊秉坤声名鹊起,再加上革命元勋居正等人也力倡“熊一枪”说,“熊一枪”说便逐渐成为史学界的正统观点。
(四)罗金玉打响“第一枪”说
竺柏松指出,10 月10 日晚,城外辎重队李鹏升燃草引火示警,罗金玉鸣枪示威为号,在时间上首先发难。辎重队革命代表李鹏升在其回忆文中描述:“万分紧张之际,罗金玉发一信号枪,全营同志蜂拥集合。”[11](P55)章开沅、林增平主编的《辛亥革命史》也采纳了这一说法,“届时,罗金玉首发一枪,辎重队的革命者即将马草房点燃,举火起义。”[12](P958)首义人士胡祖舜在《武昌开国实录》中更是大谈罗金玉“第一枪”的历史贡献,“城外起义总指挥李鸿(鹏)升指挥罗金玉打响了武昌首义第一枪,时间是10 月10 日晚上6 时零5 分,‘幸是一枪,而民国从此声一响而专政倒矣’。”[13](P40)笔者认为,胡祖舜的评价未免有点言过其实,另一位首义人士邵百昌的说法倒是比较符合实际,“七时许,由李鹏升等前往马厩,燃草引火,同志罗金玉鸣枪示威。此枪实系辛亥武昌首义第一枪。因该营距其他营房过远,未引起大作用,故各书鲜少提及。”[14]很多史料也证实,罗金玉打响的“第一枪”的确比程正瀛的时间更早,只不过,罗金玉在发枪为号后,仅有该营士兵进入军装房抢出子弹一箱,城外驻扎的其他两队的人响应不多,最终因其力量薄弱又无后续重大行动,其在武昌起义中所起的实际作用和影响不大,导致此枪既不为外界所知,也少有著作记载。
(五)吕中秋打响“第一枪”说
伍立杨著《中国1911》提及吕中秋曾在1946 年的首义同志会上爆粗口骂人,自称自己打响“第一枪”,但功劳却被别人领了去。此书出版后,引起了史学界对吕中秋打响“第一枪”的探讨与争论。目前,可以肯定的是吕中秋的确是武昌首义当晚工程营的发难士兵,他也确实开枪打死了黄坤荣、张文涛两名队官,只不过按照时间的先后顺序,他打响的并非是“第一枪”。《辛亥首义回忆录》中载有吕中秋口述的《辛亥回忆一则》,他自己说道:“程正瀛、金兆龙枪杀陶启胜,我亦枪杀黄坤荣、张文涛。”[15](P67)首义人士邵百昌的回忆文中有“右队队官黄坤庸(荣)阻止本队士兵参加,吕中秋击杀之,弹贯穿黄身而出,该队司务长(张文涛)立于旁,亦中弹而死。”[14]裴高才详查史实,认为吕中秋打响的应该是继罗金玉、程正瀛等人之后的第三枪或者第四枪(如果熊秉坤在他之前放枪的话)。根据现存的史料判断,第三枪或者第四枪的说法较为可信,比较熊秉坤、周全胜、金兆龙、程正瀛等人的回忆文章以及胡绳武、杨玉如、章开沅等辛亥革命史家的专著,极有可能的情况是,武昌首义当晚程正瀛先以一枪击伤清兵排长陶启胜,“熊秉坤闻声放枪为号,右队队官黄坤荣挽本队兵士暂留房内,吕中秋击之,坤荣死,弹贯司务长张文涛亦死。”[16](P46)如果是这样的话,吕中秋应是在熊秉坤信号枪响之后开的枪,他应该也知道自己打响的不是“第一枪”。因此,吕中秋打响“第一枪”说很难成立。
谁打响的“第一枪”仍是一个历史之谜。尹呈辅在《参与辛亥武昌首义之回忆》中讲道:“武昌首义‘第一枪’到底是谁放的?这可能还是一个历史之谜”。郭国祥、朱喆对此也持相同看法,他们认为武昌首义是一场仓促之间由恐慌引起的基层士兵发动的兵变,兵变不是一处两处,又是混乱情形之下,那么打响“第一枪”的人、准确时间和确切地点实在难以考证。就时间而言,当时只有排长以上的军官才有怀表,普通士兵没有表也就说不清楚具体时间,因此各自放枪的准确时间就不是很确定;就地点而言,有人在工兵营放枪,有人在辎重队放枪,有人在炮兵营放枪,但到底谁先谁后很难考证。因此,是谁实际打响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在今天只能是一个历史之谜[17](P65)。
二、广义的“第一枪”
狭义的“第一枪”特指揭开武昌首义序幕的第一声枪响,但这个“第一枪”具有太多的局限性。首先,开“第一枪”具有太多的偶然性,一个恐慌引起的兵变,谁开的“第一枪”,当事人恐怕也不太清楚,也没有那么重要。我们更应该从发动这次起义的历史必然性去考虑“第一枪”的问题,如果是发动起义的标志性的信号枪就更有意义。其次,既然是恐慌引起的兵变,放枪肯定就不是一处两处,缘由也就多种多样,有人在工八营因应对突发检查向清兵开枪,有人为发动起义鸣枪为号,还有人在没有放枪之前就打了起来。有人在辎重队燃草引火示警,有人鸣枪示威为号,有人在炮兵营放炮为号。这些人谁的时间早,谁的功劳大,就很难说清楚。再次,“第一枪”不能拘泥于有形的第一声枪响,“第一爆”“第一打”“第一把火”“第一炮”等难道就不是揭开起义序幕的重大历史事件吗?既然如此,那就应该把“第一枪”这个问题泛化,提出无形的“第一枪”。最后,历史研究从来就不是一个单纯的史实问题,还涉及到后人对历史事件进行分析的立场、视角、方法和理论问题,如把“第一枪”可以看成是一个群体行为。这样关于“第一枪”的研究就更加精彩纷呈,观点多样。目前,主要的观点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起义信号的“第一枪”和实际打响的“第一枪”
郭国祥、朱喆认为武昌首义的发生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第一枪”既有程正瀛在紧急状态下戏剧性和偶然性地实际打响的“第一枪”,也有熊秉坤按照预定计划打响的标志起义信号的“第一枪”。两个“第一枪”都有其独特的历史价值,不能轻易抹杀其中的任意一个,但熊秉坤的“第一枪”更符合历史的必然法则,更有象征意义和历史意义[17](P65-70)。
贺觉非在《辛亥武昌首义人物传》中多次强调了熊秉坤打响标志起义信号的三枪,在《熊秉坤》篇中记:“熊走到本队……听到楼上有扭打声,即取枪实弹。方拟上楼,见排长陶启胜狼狈跑下,即开枪击中陶小腹,陶捧腹而逃。随即对空放了三枪,表示已经发难。”[18](P250)在《金兆龙》篇中记:“熊向天鸣枪三声,才是发难讯号。”[18](P257)吴剑杰在《熊秉坤与辛亥武昌首义》一文中指出,从微观、狭义上来说,“第一枪”确实不是熊秉坤打响的,但如果没有工程营党代表熊秉坤在发难前卓有成效的串联、策划、动员和组织,如果没有他的“鸣枪三声”和之后的临机指挥,那么武昌首义也许就熄火了,也许就不可能出现现在我们所熟悉的重大历史事件了。因此,从宏观、广义上来说,熊秉坤荣膺首难“一枪之功”是当之无愧的[19]。严昌洪对此表示赞同,认为如果从发出正式起义号令这个广义的角度来看“第一枪”,熊秉坤可以说是名副其实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的功臣。
陈家琪认为“熊一枪”更符合革命叙事,更利于革命神话的塑造。他认为孙中山对于“熊一枪”的强调就是一种宏大的革命叙事,是革命者争“推翻满清第一功”的自然反应,是渲染革命道统和法统的必然之举。黄逸梅、郑一奇、武云溥等学者也提出了相似的观点。黄逸梅认为罗金玉虽然打响了武昌城外的“第一枪”,但是在事后竟人间蒸发,程正瀛虽打响了城内的“第一枪”,但他不知珍惜荣誉,在武昌起义后不久叛变革命,投靠了袁世凯,唯有熊秉坤在武昌起义后再接再厉,因此,承认他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更具正面意义。郑一奇认为整个发难过程中熊秉坤自始至终都是革命的领导者,他开的三枪具有特别的意义,是工程八营正式起义的信号,再加上程正瀛后来堕落为军阀爪牙,承认“熊一枪”的说法更能服众,也是对首批发难的革命士兵的赞誉。武云溥亦认为熊秉坤是革命党人的代表性人物,也是10 月10 日群龙无首时发难的实际组织者和领导者,加上还有孙中山等人对他的褒奖,将他视为广义的“第一枪”有其合理性。
(二)城内“第一枪”与城外“第一枪”
武昌起义当晚的发难单位,既有城外李鹏升带领的辎重队,又有城内熊秉坤带领的工程八营,两个发难单位谁是“第一枪”,如何评价他们当晚的行动,这在学术界也是争论很大的一个问题,代表性观点如下:
1.城外辎重队首义说
张绍春根据塘角党人、城内党人、湖南党人、立宪党人等四类人的回忆,提出是“辎重十一营放火在先,工八营鸣枪在后”。竺柏松也力主此说,并引当时领导辎重队发难的李鹏升自述和其他目击者的记述,证明是“塘角辎重队比城内早发难一小时左右”。胡祖舜在《中西报》上质疑“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时,公开提出辎重队发难在10 月10 日下午6 时许,而工程营则在8 时左右,且从辎重队放火,又经武胜门,绕至通湘门,最后从中和门进城到楚望台会师的路程来看,可以推算出辎重队发难在先,胡祖舜还曾举出章炳麟所作黎元洪墓碑初稿作为佐证。
2.工程八营首先发难说
《辛亥革命史稿》第3 卷《1911 年的大起义》中详细列举了工程八营在10 月10 日晚担当率先发难任务的几个有利条件,其一,楚望台军械库由工程八营负责防守;其二,工程八营驻扎城内,又独守紫阳桥,行动便利;其三,工程八营组织基础良好,工程八营内的革命党人占该营士兵人数的十分之四。学者黄逸梅认为,人们在谈论是谁打响武昌首义“第一枪”时,往往特指武昌城内发难,鲜少提及城外发难,因此,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是特指工程八营打响“第一枪”。肖承勇认为,虽然程正瀛的一枪事出偶然,但他这一枪在客观上取得了众人响应的效果,城内步兵中几乎所有革命党人闻声起义,继而夺取了对起义成败具有关键作用的楚望台军械库。因此,城内程正瀛打响的“第一枪”的地位和作用是城外罗金玉所打响的“第一枪”所无法比拟的,武昌首义“第一枪”就是特指城内“程一枪”。
3.城内城外两相宜说
张玉田、陈崇桥认为,1911 年10 月10 日晚7 时左右,驻武昌城内的工程八营和驻武昌城外的工程、辎重两队首先起义,各标营基本上仍按原作战计划同时行动,武昌首义的成功是城内、城外两个发难单位协同作战的历史成果。著名史学家章开沅、林增平在《辛亥革命史》中认为:“武胜门外塘角辎重队,……差不多与工程八营同时举起了义旗。”[12](P40)贺觉非、冯天瑜合著的《辛亥武昌首义史》也认为:“就发难时间而言,应以城外第二十一协辎重队为最先,但工八营地处城内,打响第一枪,影响最大,该营又是首先抢占楚望台军械库的。因此,城外辎重队和城内工八营均可视为武昌起义的发难单位。”[5](P188)吴剑杰认为抛开武昌首义及其开创的辛亥革命全局去计较两个发难单位的轻重之分是没有多少实际意义的,历史事件之所以被大家铭记,就在于该事件对当时及今后其他事件产生重大影响,从这个意义上说,将首难之功归诸工程营,是当之无愧的,承认辎重队纵火在先,也丝毫不会减少工程营首难的光彩[20]。裴高才也持相似观点,既肯定城外辎重队先行发难的史实,又认为城内城外两相宜,两个发难单位的历史功绩不分上下,各有千秋,应承认两个“第一枪”的合理存在。
(三)有形的“第一枪”和无形的“第一枪”
有形的“第一枪”就是实体的“第一枪”,就是真正的第一声枪响,不管它是起义信号还是偶然之间的擦枪走火。无形的“第一枪”则是广泛意义上同清军展开战斗的第一个行动。单从10 月10 日晚的发难来看,金兆龙是和清兵展开生死对垒的第一人,他的“第一打”揭开了当晚革命的风暴,就是“第一枪”。郭国祥、王欣欣在《武昌首义“第一枪”新探》中提出,我们理解“第一枪”不要局限于实际开的第一声枪响,而应该从宽泛的意义上来理解“第一枪”,即无形的“第一枪”,也就是和清兵进行的直接的尖锐对垒的标志性事件,如“第一把火”“第一声炮”也是“第一枪”,甚至“第一爆”“第一炸”“第一打”也是“第一枪”。无形的“第一枪”更符合特定状态下的语义,也更有利于分析首义志士们敢为人先的先锋作用。
也有人纠结于武昌首义的发动到底是“第一枪”在先还是“第一把火”在先,谁在先谁就更具历史意义,因此提出武昌首义不是“第一枪”,而是“第一把火”揭开起义大幕的。金冲及在《辛亥革命的前前后后》一文中认为,武昌起义是以城外辎重队李鹏升首先点燃草料库为发难信号的,因此不应该叫武昌首义“第一枪”,应该叫“第一把火”,承认城外首先发难的历史地位。实际上“第一把火”也好,“第一枪”也好,它们都是强调哪个事件是揭开这次起义大幕的标志,也就是一个符号和象征,都统称为“第一枪”也未尝不可。
(四)将工程八营发难一事整体视为起义的“第一枪”
罗华庆在《武昌首义第一枪》一文中指出,武昌起义是工程八营的革命党人率先发难,而组织、领导发难的熊秉坤又是工八营革命党人的总代表,将工八营发难之事整体视为起义的“第一枪”,更能渲染革命的合理性和必然性。冯天瑜先生在其专著《辛亥首义史》与《辛亥武昌首义史》当中,分别以“1911 年10 月10 日夜,城内工程第八营率先打响起义枪声”和“1911 年10月10 夜城内工程第八营打响起义第一枪”作为段落小标题,详细讲述了武昌首义当晚工程第八营革命士兵与清兵战斗的英勇事迹,并以“是夜,城内工程第八营率先打响第一枪”作为最后总结。王天奖、刘望龄也认为工程八营打响了起义的“第一枪”,随后,熊秉坤“即命令整队猛扑楚望台军械库,以求一举夺取军事”。毛磊、毛传清等人认为,“以熊秉坤为党代表的工程八营的革命者打响了武昌首义的第一枪”这个说法强调了集体的作用,更符合历史的发展规律。伍立杨亦认为熊秉坤是辛亥革命武昌首义事发时的实际领导组织者,他率领工程八营“冒险发难”,打响的是“首义的第一枪”。
(五)将推动武昌首义走向胜利的关键性行动都看作是“第一枪”
武昌首义,既是一场恐慌之中由基层士兵发起的兵变,也是一场由共进会和文学社两大革命组织经过精心准备、精心策划发动的起义。从历史的必然法则和历史的合力理论来思考,我们更应该把“第一枪”的标准放宽,即推动武昌首义走向胜利的关键性行动都可被看作是某种意义上的“第一枪”,而这些关键性行动的领导者、发起者都可以享有这一殊荣。郭国祥、王欣欣在《武昌首义“第一枪”新探》中认为,武昌首义,出现了一个英雄群体,他们在不同的时间段都有其不可磨灭的历史贡献,如第一策划者蒋翊武,不仅是起义的直接策划者,也是首义当晚制定行动计划的总指挥;第一试爆者孙武,既是共进会的首领,更是身体力行,试爆炸弹,点燃熊熊革命烈火的先驱;第一个向清兵扔炸弹者杨洪胜、第一个和清兵扭打者金兆龙、第一个点火为号者李鹏升、第一个向清兵开枪者程正瀛、第一个吹响起义哨子者熊秉坤,这些人都是革命党人的精英和先驱,他们不但参与了起义前期的各项准备工作,而且在正式起事过程中各自作出了开创性的历史贡献。这些革命先驱,在重大历史转折关头都发挥了特殊的开路先锋的作用,毫无疑问都暗合广义“第一枪”的内在含义。而且,这个群体的无形的“第一枪”比个体的有形的“第一枪”更具历史意义,也更能反映历史发展的人民性、客观性和必然性[21]。
综上所述,学术界有关武昌首义“第一枪”的研究已经从狭义的单一史实性研究逐渐发展到了多层次理论研究以及系统性的群体研究,总体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在具体研究方面,还存在着许多可以突破的地方,例如,如何从有形和无形、个体和群体、历史必然性和偶然性、历史事实和历史评价相结合等多角度来看待“第一枪”,就还有大量的工作可做。特别是历史已经远去,而当事者留下的各种回忆性史料并非尽善尽美,有的道听途说,有的局促一隅、管中窥豹,有的自说自话、自相矛盾,有的“是非颠倒,贪天之功”,要对这样一些史料抽丝剥茧,还原历史的本真,揭示这样一个英雄群体的具体的历史贡献,还有很长的一段路要走。
——武汉市武昌首义中学校本课程文化建设的探索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