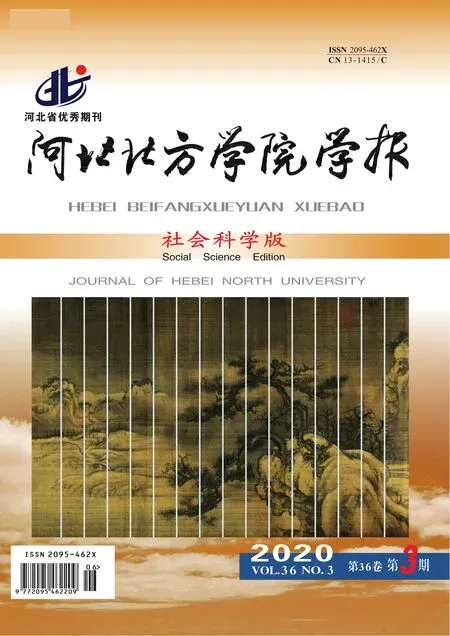论非虚构写作的文体与文类归属
刘 栋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自2010年《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并启动“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以来,“非虚构”逐渐成为一种写作潮流,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但至今,仍难以理清非虚构写作的概念与边界等,对于其究竟是文体还是文类依然存在争议。随着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发展,其大有向外转的趋势。因此,理清非虚构写作的归属既有利于厘清非虚构写作的概念和边界,也为非虚构写作在国内的长期发展奠定基础。
一、文类与文体的区分
非虚构写作的文体与文类的归属问题难以理清与文体和文类概念的模糊有很大的关系。长期以来,文体和文类被人们混用,仅被当作文学体裁。实际上,文类和文体是一对十分复杂的概念,是不同层次的术语,既相互关联,又相互交叉。
文类,即文学类型。“文类”在英语中对应“genre”,但该词在西方并没有明确的解释。英国文艺理论家罗吉·福勒在《现代西方批评术语词典》中指出:“在英国文学批评语汇中,此术语没有一个众所承认的等义词。‘种’、‘类’、‘样式’和‘体裁’等术语常被混杂地使用着。”[1]而M·H·艾布拉姆斯在《欧美文学术语词典》中写道:“‘文类’(genre)为法文词,在文学批评里表示文学作品的类型与种类,或者是我们现在常采用的叫法——‘文学形式’。文学作品可以划分为多种类型,而划分的标准也是五花八门。”[2]“genre”被该书译为文类,并被指出有现在常用的“文学形式”即文学体裁的含义。由此可知,“genre”一词有文类和体裁两种含义,但这并不表示文类就相当于体裁。韦勒克与沃伦在《文学理论》中提出:“我们认为文学类型应视为一种对文学作品的分类编组,在理论上,这种编组是建立在两个根据之上的:一个是外在形式(如特殊的格律或结构等),一个是内在形式(如态度、情感、目的等以及较为粗糙的题材和读者观众范围等)。”[3]可以看出,韦勒克和沃伦将文学类型总体分为内容和形式两种。因此,文类的划分有多种方式,并非仅有体裁的划分。且划分的标准不同,文类自然也就不同。
相比文类,文体的概念更加复杂。申丹在《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指出:“文体有广狭两义,狭义上的文学文体包括文学语言的艺术特征、作品的语言特色或表现风格、作者的语言习惯以及特定创作流派或文学发展阶段的语言风格等。广义上的文体指一种语言中的各种语言变种。”[4]73文体不仅涉及文学语言领域,也涉及非文学领域,如新闻语体、法律语体及宗教语体,甚至应用场合的不同也会引起文体的变化。而在文学领域,文体也不仅是文学体裁上的区别,“它可泛指所有对文学文本进行分析的文体派别,也可特指以阐释文学文本的主题意义和美学效果为终极目的的文体学派”[4]73。不论中国古代还是西方,对文体的理解都没有局限在文学体裁上。曹丕在《典论·论文》中就写道:“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这里的“体”不仅指奏议、书论、铭诔与诗赋4科,也指雅、理、实和丽4种风格。而在西方,文体对应的英语为“style”,可译为类型、方式、语体及文体等多种含义。人们常用“stlye”表明书写或说话的表达方式、具有特色的用词风格或作家独特的行文风格等。对比发现,中西方对文体的理解虽不完全相同,但都有体裁和风格两个含义。因此,文体并不等同于文学体裁。
综上所述,文体和文类都不仅指文学体裁。文类的划分多种多样,文体也有体裁和风格两方面含义。只有当文体和文类都指文学体裁时,文体才相当于文类。
二、作为叙事策略的非虚构写作
在20世纪中期以前,“非虚构”原是美国书商分类图书的方式。他们将小说归为“虚构类”,小说以外的图书归为“非虚构类”。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一种介于新闻和文学之间的文体在美国兴起,被称为非虚构小说或新新闻报道。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的概念传入中国。王晖和南平在《美国非虚构文学浪潮:背景与价值》一文中将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兴起的非虚构小说与新新闻报道等纪实体裁统称为非虚构文学。这是国内“非虚构文学”一词的首次亮相。随后,两人在《对于新时期非虚构文学的反思》和《1977-1986中国非虚构文学描述——非虚构文学批评文学批评之二》等文章中,将中国的报告文学、口述实录体、纪实小说、文学传记以及回忆录等纪实类体裁统称为非虚构文学,其中报告文学是非虚构文学最主要的文学体裁。实际上,王晖和南平是借非虚构文学之名来彰显报告文学的重要性。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报告文学的文体逐渐僵化,非虚构文学的概念并没有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总而言之,从20世纪80年代“非虚构”的概念传入中国起,王晖和南平等人是把非虚构文学当成文类来对待的。
2010年2月,《人民文学》开辟“非虚构”专栏。之后,慕容雪村《中国,少了一味药》、萧相风《词典:南方工业生活》及梁鸿《梁庄》等作品相继在“非虚构”专栏发表并引起热议。同年10月《人民文学》召开了“非虚构:新文学的可能性”研讨会。时任主编李敬泽在会上发布“人民大地·行动者”非虚构写作计划,面向全国征集12个非虚构写作项目。随后《人民文学》发表了李娟《羊道》系列、贾平凹《定西笔记》、乔叶《盖楼记》和《拆楼记》、郑小琼《女工记》、于坚《印度记》以及孙惠芬《生死十日谈》等。这些非虚构作品引起张文东、张柠、张莉、林秀琴和李云雷等学者的注意,他们发现《人民文学》所发表的非虚构作品与以往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作品相比有很大不同,并呈现出独特的特征。例如,张文东较早地察觉出《人民文学》所刊发非虚构作品的独特之处:“一是用‘生活的在场’营造出的再现性,二是用第一人称所形成的抒情性。”[5]李云雷又在《我们能否理解这个世界?——“非虚构”与文学的可能性》中,将2010年《人民文学》发表的十几篇“非虚构”作品按常规体裁分为自传、回忆录、历史散文、社会调查与大散文等,并发现作品“内部并未有文体自身的‘规定性’”,但也有“相同之处”,都具有“真实性”,都是从个人的“小世界”出发来表达对世界的看法[6]。至此,非虚构写作倡导作家走出书斋,书写“吾土吾民”,并将个人叙事与宏大叙事联系在一起,强调作品的真实性,却并不绝对真实,在当时形成一种独特的叙事特征,大有成为一种独特文体的趋势。但非虚构写作是否可以成为一种新的文体,学界对此一直都存在严重的分歧。对于《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存在以下3种观点:1.王晖延续以往观点,在《别样的在场与书写——论近年女性非虚构文学写作》和《现实与历史:非虚构文学的独特叙述》等文章中将报告文学、口述实录与人物自传等纪实类体裁统称为非虚构文学。这仍是将非虚构文学当作文类来理解。2.梁鸿作为非虚构写作的主要领军人物之一,把非虚构写作视为一种和报告文学并列的文体,并认为它和报告文学最大的区别在于,“‘非虚构’是允许有个人的犹疑的,是允许有个人的痕迹存在的”[7]。3.洪治纲等人认为,“‘非虚构’与其说是一种文体概念,还不如说是一种写作姿态,是作家面对历史或现实的介入性写作姿态”[8]。
李敬泽曾谈到设立“非虚构”专栏的初衷:“当时我要发韩石山的自传《既贱且辱此一生》,然后就有一个难题:把它放在哪个栏目里呢?你知道,文学期刊大致是几大块:小说、散文、诗,有时还有报告文学,像韩这样的作品,当然不是小说,是报告文学吗?是散文吗?都不很对;中药柜子抽屉不够用了,我也想过临时做个抽屉,比如就叫自传,但我又没打算发很多自传,做个抽屉难道用一次就让它闲着?最后,就叫‘非虚构’吧,看上去是个乾坤袋,什么都可以装。”[9]由此可见,《人民文学》之所以设立“非虚构”专栏,是因为传统的文学体裁不能涵盖当时所有的文学形式,需要增加“新抽屉”。“非虚构”是与诗歌、小说、散文以及报告文学等文学体裁并列的“乾坤袋”,可存放自传、田野调查、回忆录与非虚构小说等体裁,唯独不能放传统的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传统的文学有诗歌、散文、小说、戏剧与报告文学等几种体裁或类型,而《人民文学》设立“非虚构”专栏打破了传统文学的划分方法,将文学分为诗歌、小说、散文、报告文学和“非虚构”等类型。此外,《人民文学》在设立“非虚构”专栏时也表明:“不能肯定地为‘非虚构’划出界限”[10],但只是觉得当下的文学不能局限于“传统的文类秩序”。它所倡导的“非虚构”包括叙事史、人物自传、非虚构小说以及“具有个人观点和情感的社会调查”[10]等。
由此可知,《人民文学》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包含自传、回忆录与非虚构小说等多种纪实类体裁。《人民文学》对“非虚构”的划分方法与王晖和南平在20世纪80年代所提出的非虚构文学类似,都包含多种纪实类体裁。不同的是,非虚构写作不包含报告文学和纪实文学,具有独特的叙事特征。若延续王晖和南平以往的观点,将非虚构写作看成一种文类,就会遮蔽其特有的写作姿态。因此,简单地将非虚构写作当成文体或文类都不合适。事实上,非虚构写作处于文体与文类之间,是一种以“在场”和“行动”的姿态书写“吾土吾民”的叙事策略。
三、非虚构写作的“向外转”趋势
《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潮流最初并没有明确的界限,一切都只是在探索中。随着各大期刊“非虚构”或相关专栏的开辟以及新媒体上各种非虚构写作平台的推出,近几年非虚构写作在中国蓬勃发展。但作为叙事策略的非虚构写作却大有向外转的趋势,主要体现在以下4个方面。
第一,《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作倡导力度的弱化。作为倡导者的《人民文学》近几年发表的非虚构作品越来越少,“报告文学”专栏也没有消失。统计发现,《人民文学》在2010-2019年间发表“非虚构”作品共46篇,前5年发表作品共33篇,后5年发表作品共13篇。尤其在2017-2019年间,所发非虚构作品只有《纸上》《何处不青山》《天下第一渠》和《我的二本学生》4篇。此外,“留言”或“卷首”一直是《人民文学》表达文艺理念、倡导文学思潮、推广作家和介绍文学作品的重要阵地。10年来,《人民文学》通过“卷首”或“留言”倡导非虚构写作潮流,但2017年以来,《人民文学》很少在“卷首”或“留言”上提及非虚构写作。由此可见,作为倡导者的《人民文学》对非虚构写作的关注越来越少,对非虚构写作的倡导力度已明显减弱。
第二,其他文学期刊“非虚构”及相关专栏的开辟。除《人民文学》外,《收获》推出“非虚构”“说吧记忆”与“亲历历史”等专栏,《花城》推出“家族记忆”专栏,《钟山》推出“非虚构文本”“栏杆拍遍”专栏和“非虚构副刊”,《小说界》推出“非虚构写作”专栏,《山东文学》推出“非虚构中国”专栏,《山西文学》推出“叙事史”和“非虚构”专栏,还有《当代》《十月》《青年作家》《萌芽》《山花》《解放军文艺》《安徽文学》《西部》《北方作家》《雨花》《江南》《清明》《西湖》《中国工人》以及《边疆文学》等40多种文学期刊先后推出“非虚构”或与之相关的专栏。如《解放军文艺》从2016年第一期改版后,在原有小说、诗歌与散文等栏目基础上又增加评论和访谈等专栏,原来的“报告文学”专栏变为“非虚构”专栏。从“征稿启事”可见《解放军文艺》对“非虚构”的定位:“选发以军事历史、战争人物与事件为主要题材的纪实作品,可以宏阔叙事,亦可微观铺陈。首重文学品质,同时要求资料翔实,角度独特,生动可读。”[11]改版后的《解放军文艺》,其“非虚构”专栏涵盖以往的报告文学,是一个范围更大的“文类”专栏。虽然其他文学期刊“非虚构”及相关专栏的开辟使“非虚构”写作迅速发展,但由于各刊办刊理念不同,对“非虚构”的理解也各不相同,这导致“非虚构”专栏呈现出不同的形态。
第三,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平台的设立。随着微博和微信等新媒体的发展,网上出现很多“非虚构写作”平台,如网易的“人间”“真实故事计划”“我从新疆来”“湃客工坊”“三明治”和“正午故事”以及腾讯的“谷雨实验室”等。新媒体的非虚构写作平台企图将非虚构写作大众化,倡导普通大众写自己的故事并以不同的形态将“非虚构”推到更广阔的天地。但由于“非虚构”写作者大多没有文学创作的经验,文学素养参差不齐,这导致新媒体上的“非虚构”作品数量虽多,但精品极少,作品整体文学性不强。所以,新媒体平台虽然使非虚构写作更加大众化,但也给非虚构写作带来更大的争议——非虚构写作更加泛滥,更加没有边界。
第四,学界对“非虚构”研究的扩大化。起初,学界对“非虚构”的研究仅停留在《人民文学》的“非虚构”系列作品上,主要对其概念、兴起原因、意义以及作品特征进行探讨。但由于学界对“非虚构”概念的理解不同,对“非虚构”的研究也逐渐扩大化。一方面,不少学者将报告文学纳入“非虚构”的研究范围。如丁晓原的《非虚构文学:时代与文体的“互文”》与何建明的《创意写作理念与实践:中国非虚构文学的新契机》等文章,将报告文学作为“非虚构文学”的主要文体,以“非虚构文学”的名义探讨报告文学。另一方面,学界对“非虚构”的研究由文学领域扩充到社会学、历史学、传播学与新闻学等多个学科。“非虚构”也不仅指文学写作,还包含一些以“非虚构”为核心特征的艺术形式,如照片和纪录片等。2019年1月,《当代文坛》开辟“非虚构写作”研究专栏,洪治纲在《主持人语》中说道:“‘非虚构’写作在强调‘真实感’和‘现场感’的同时,逐渐呈现出一种开放性的文化姿态。它不仅囊括了中国类型的文学实践,产生了一系列别有意味的典型作品,还延伸到当下的新闻写作和‘口述史’写作等领域之中。”[12]由于学界对“非虚构”研究不再局限于《人民文学》,甚至不再局限于文学领域,导致“非虚构”再难成为一种文体。
综上所述,《人民文学》所倡导的非虚构写作处于文体与文类之间,是一种以“在场”和“行动”为姿态,书写“吾土吾民”的叙事策略。随着《人民文学》自身倡导力度的减弱、其他文学期刊对“非虚构”的推广、新媒体“非虚构”写作平台的兴起以及学界对“非虚构”研究的扩大化,非虚构写作大有向外转的趋势。因此,作为叙事策略的非虚构写作构成一种文体的可能性越来越小,最终只能是一种文类的划分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