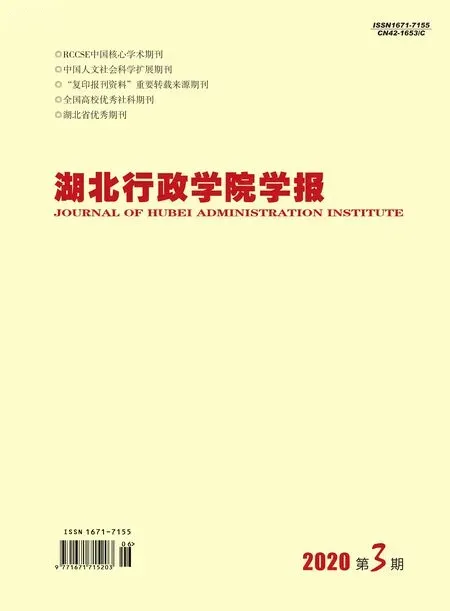当代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成因分析
袁婷婷
(郑州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南 郑州450000)
自2016 年“黑天鹅事件”惊现以来,西方民粹主义愈演愈烈,2019 年法国“黄马甲运动”此起彼伏,特朗普相继推出反全球化等诸多政策……西方民粹主义至今毫无消退之象,并且与贸易保护主义、排外主义、极端主义思潮的耦合之势愈发强烈。新一轮西方民粹主义持续时间更久、波及范围更广、影响程度更深、潜在威胁加大,持续的肆行给西方社会带来了深刻变动,使欧美国家逆全球化的势头不减,也极大增加了世界全球化进程的不确定性。究竟为何新一轮西方民粹主义如此顽固?到底是哪些深层次因素引发了如此肆行的西方民粹主义?廓清以上问题成为解读当前西方民粹主义大规模爆发的关键。本文认为,当代西方民粹主义的兴起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多方面因素合力促成的。
一、全球化的深化与经济不平等状况的加剧是其经济根源
在上个世纪70 年代,世界性经济危机使西方各国陷入经济滞涨与低速发展的困境,社会收入不平等状况开始显现。面对这一经济形势,里根和撒切尔夫人奉行自由主义主张,强化市场作用,弱化政府干预,使西方社会经济在全球化的助推下重现活力。然而,经济全球化给西方发达国家带来繁荣的背后并不是“全员受益”,而仅仅是“部分成员受益”,经济全球化深刻改变了西方社会的经济结构。一方面,大量跨国公司觊觎发展中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与原材料并在各地选址建厂,西方本土主要保留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另一方面,广大发展中国家的商品大量涌入西方市场,给西方部分产业带来了冲击。诸多公司的外迁必然导致西方社会工作岗位锐减,大量蓝领工人不得不面临失业窘境,而本土的互联网等高新技术产业与金融行业对劳动者素质的要求较高,使得蓝领工人的再就业相当困难。也就是说,在经济全球化中,西方社会部分成员非但没有从中受益,反而利益受损,甚至要面临随时失业的威胁。曾任职于世界银行的美籍经济学者米兰诺维奇(Branko Milanovic)指出,自1988 年以来,新一轮的全球化在缩小国家之间贫富差距的同时,却加剧了国内阶层的不平等,就西方国家中产阶级而言,在全球衡量标准中他们被定位于高收入阶层,但在近30 年间他们的收入增幅却极其不明显,然而,全球收入最高的前1%人群收入增幅在40%以上[1]。对于西方富人群体而言,依托全球化中廉价的原材料、劳动力与广阔的世界市场,他们必然能从中攫取巨额利润而变得更富有;而对于西方中产阶级而言,全球化给他们带来的是日益恶化的工作形势,虽然他们的收入可能没有下降,但与收入增幅较大的富人群体相比,中产阶级与富人群体之间的收入鸿沟愈发明显。换言之,经济全球化加剧了西方社会的收入不平等状况。进入21 世纪,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广泛应用,各国的经济交往愈发密切,经济全球化日益深化,与之相对应,全球化所带来的收入不平等必然进一步加剧。
受2008 年金融危机的巨大冲击,西方社会长期存在的经济痼疾被集中放大,收入不平等问题被“台面化”。据美国权威部门统计,“2010 年,美国的人口贫困率为15%,比金融危机前的高出2.5 个百分点”[2](P146)。据美国相关部门统计,2015 年,美国5%最富裕家庭的总收入,是收入最低的20%家庭总收入的7 倍[3]。事实上,在1893 年美国经济危机爆发之时,也正是民粹主义崛起的高峰时期。在2008 年金融危机以后,由全球化所引发的收入不平等出现进一步扩大的趋向。诸多经济问题的集中暴露很容易强化民众尤其是社会中下层群体对建制派的不满情绪,从而为民粹主义的酿发埋下诱因。面对巨大的收入差距、恶化的就业形势,西方社会的中下层群体对现有体制的疑虑与不满迅猛激增。然而,传统政党长期以来根本无力改变他们的境况,长此以往的期望落空让社会中下层群体深感失望,“希望巨变的发生成为社会非精英阶层的普遍心态”[4]。
在代议制民主政治中,这种心态对选举或投票行为产生了直接影响。一方面,国家经济形势的低迷、公民生活境况的恶化和社会成员被剥夺感的强化,很容易使建制派遭受选民的报复性投票惩罚。在2016 年美国大选中,许多人之所以支持特朗普,是因为他们用投票行为对难以忍受的现状进行反抗,强烈表达对希拉里及其所代表的建制派的失望;另一方面,民众对巨变的渴望、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对建制派的不满,恰恰给长期被边缘化的政党尤其民粹政党营造了崛起契机。事实上,民粹政党在西方国家长期存在,但长期以来均遭到不同程度的忽视而处于被边缘化境地。当利益问题引发民众对建制派强烈不满时,以推崇“人民”与批判建制派精英为导向的民粹政党所推行的反建制派与反“政治正确”等主张,就很容易引发大范围的选民共鸣,使得民粹政党的支持率迅速提升,如法国国民阵线、德国选择党等。民粹政党的崛起,必然会掀起民粹主义浪潮,这是西方民粹主义兴起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代议民主政治的衰败与政党最大限度争取认同的迫切需求是其政治诱因
近年来,关于西方民主政治衰败的呼声不绝于耳。国内外学者、媒体纷纷针对西方民主的隐患刊发文章,其中不乏以福山为主要代表的西方学者和以《经济学人》为代表的知名媒体,也包括张维为、陈曙光等一批国内学者。当前西方民粹主义的集中迸发既暴露了代议民主政治的病症,又恰恰从侧面印证了代议民主政治的衰败状况。因此,为廓清民粹主义的成因,必须首先对西方代议政治的“病灶”予以深刻剖析。
事实上,西方所标榜的民主制度存在不容忽视的内在“基因缺陷”,这种缺陷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人是理性的;二是权利是绝对的;三是程序是万能的[5]。这些内在“基因缺陷”虽看不见、摸不着,但却是西方民主走向衰败的重要“元凶”。
首先,“人是理性的”即公民基于自己的理性思考投下神圣庄严的选票。然而,人既有理性的一面,也有非理性一面,其认知受教育水平、知识结构、具体环境等复杂因素的影响。在政治层面,被预设为理性的选民往往难以理性权衡眼前利益与长远利益、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他们所坚持的观点通常只是一种“偏见”。与之相对应,投票行为也带有“偏见”。这种“偏见”为特定政党或政客争取认同提供了风向标,在政党或政客的支持下,这种“偏见”很容易将社会发展引入歧途。比如,选民怀有社会高福利的固有“偏见”,政客投其所好大打“福利牌”,结果很容易将国家带入高福利债务危机的泥潭。近年来,随着新媒体崛起,受新媒体舆论的诱导、政党或政客巧言花语的蛊惑、自身对现状的不满等因素的影响,公民通常无法理性控制自己言行,其非理性的面相得到进一步强化。比如,英国脱欧公投刚结束,就有280 多万选民联名为“二次公投”请愿,相当一部分选民表示后悔脱欧,这是非理性投票行为的鲜明例证。多重复杂因素的叠加使公民投票行为往往表现出非理性的一面,其结果是“既可让天使当选,也可能让恶魔上台”[6],很容易使国家发展陷入泥潭。然而,选民不会从自身找原因,而是将责任转嫁给政府,以至于陷入对政府更加不满的恶性循环。
其次,“权利是绝对的”即个体权利至上。绝对的权利意味着追求权利而缺乏妥协、强调权利而回避义务。在多元主义占据主流的西方社会,价值取向的多元导致权利诉求千差万别。倘若权利诉求之间不容妥协、互不相让,必然会难以达成社会共识,甚至会导致社会冲突与对抗。对于政党而言,不同政党皆追求代表自身利益的绝对权利,以至于将自身权利置于其他政党利益甚至国家利益之上。在政治领域,绝对的权利主要表现为“党派政治”的极化即政党恶斗,在两大政党之间,无论其中一个政党所持的主张合理与否,往往都会被另一个政党所否定或反对。在政党轮替中,执政党往往将“前朝”政策议程推倒重来。比如,特朗普上台后就宣布推翻“TPP”协议和奥巴马政府的移民政策。在此形势下,政党议题似乎变得不重要,“为了反对而反对”成为政党竞争的惯用规则,政治博弈中的妥协与理性精神丧失殆尽,政治共识无从谈起。不仅如此,执政党的改弦更张使国家政策缺乏持续性,一些斥巨资在建或酝酿成熟的项目不得不被迫中止,从而造成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正基于此,西方代议民主长期陷入囿于“私利”、浮于“当下”的政治困境。
最后,“程序是万能的”即将民主简化为一种选举程序。只要符合选举程序,任何行为都被视为民主的。然而,选举程序潜藏着被“解码”的风险。一方面,进入选举程序是昂贵的。大力的宣传、全国范围的巡回演讲等公开活动是选举获胜的重要因素,而开展这些活动需要大量金钱。据统计,1988 年的美国大选花费3.24 亿美元,2004 年花费高达8.81 亿美元,2008 年甚至耗资24 亿美元。这些数据充分证明,西方民主已扭曲为有钱人的游戏。在政客与财团“钱权联姻”的背后,政客所代表的必然是财团利益,而非广大选民的根本利益。对此,福山直接指出,利益集团的膨胀和游说集团的影响扭曲了民主的进程[7]。另一方面,与中规中矩的政治博弈手段相比,娱乐化与游戏化的竞选表演往往更能引发大范围关注。于是,“竞选程序又被简化为政治营销”[8]。政治人物扮演着营销者的形象,他们为了营销自己、为了吸引更多选民为其投票,从而卖力地表演、浮夸地宣传、油腻地煽情。除了娱乐的快感,选民从中一无所获。
质言之,西方民主体制越来越难以维护广大选民的根本利益,而是过度代表利益集团的利益。选民在政治衰败中愈发焦虑,对传统政党愈发失望。2012 年,对七个欧洲国家的调查结果显示,超过半数的选民表示“根本不信任政府”[9]。在此形势下,部分政党的支持率持续下滑,传统政党皆面临认同危机。而普通民众在选举政治中规模巨大的数量意义,决定了政党或政客操纵民粹主义的行为动机[10]。为最大限度获取政治认同,不少政党开始寻求“药方”,转向民粹主义,并主张反全球化、反移民等政策。概言之,政党为争取更多的选票,在与民众的互动中助推了民粹主义的集中生成。
三、外来移民的涌入所导致的白人身份认同危机是其文化根源
2016 年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获胜,是美国民粹主义崛起的代表性事件之一。据统计数据显示,在大多数女性和非白人支持希拉里的情况下,58%的白人和53%的男性投票给特朗普[11]。投票选民中白人占比70%,在选民中处于绝对主体地位。白人和男性选民,是把特朗普送进白宫当之无愧的“功臣”。再看英国脱欧公投事件,英国脱欧的支持者大多也是白人,也包括年长者、低学历等群体,与美国大选中特朗普的支持群体类似。可见,民粹主义主体构成的白人种族性较为显著。白人群体对民粹主义的助推,无疑受政党或政客所操纵的反全球化、反移民等议题的煽动,而又恰恰反过来深刻呈现了这一群体本土保护主义的倾向。白人群体对反移民、反全球化议题的关切与附和,对民粹主义的兴起起了推波助澜作用。那么,为何英美国家民粹主义的主体构成主要是白人群体?白人群体又为何对移民政策等主题表示排斥?为深刻剖析民粹主义的成因,我们必须解开这些谜团。
最早到北美的定居者—英国新教徒,将英国新教文化镶嵌在北美大地,生成了美国主流文化即盎格鲁—新教文化。1789 年,美国第一任首席法官约翰·杰伊总结了美国特性,即共同祖先、语言、宗教信仰、治理原则、风俗习惯、战争经历,构成了盎格鲁—新教文化的基本范畴。美国学者亨廷顿指出,“在美国历史上,凡是不属于盎格鲁-撒克逊新教白人的人,都被要求接受美国的盎格鲁-新教文化及其政治价值观,而成为美国人”[12](P47)。也就是说,白人及其所代表的主流文化在很长时间内构成了美国文化的核心。与之相对应,白人必然会形成一种主导性身份认同。少数族裔则在白人群体构建的“文化帝国主义”中承受着身份、地位、待遇的不平等。到了19 世纪60 年代,随着外来移民人数的逐渐增多,感受到强烈不平等的黑人等少数种族集聚起来,发起了以平等与公正为诉求的平权运动。迫于压力,联邦政府不得不保障黑人和少数族裔的平等权利。
声势浩大的平权运动,直接推动了多元文化主义的兴起,并改写了盎格鲁—新教文化在美国一元主导的局面。多元文化主义强调多元文化之间的平等与包容,并主张没有一种文明能以主流态势自居并歧视或庖代其他文明。确切地讲,多元文化主义肯定了少数种族在语言、风俗习惯、宗教信仰等方面的文化传统,瓦解了白人种族的“文化帝国主义”,是对美国传统主流文化(盎格鲁-新教文化)的批判。然而,在过度批判中,“多元文化主义刺激了‘族裔崇拜’现象的增长”[13]。在现实生活中,多元文化主义更像是一种政治口号,往往在实践中被价值错置而走向“极化政治正确”的理路,并促使社会原有资源分配程序被颠倒重置、既有的利益格局被深刻调整。比如,在教育领域,许多高校刻意招录少数族裔学生,学生身份的多元化逐渐成为评判学校办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准。在白人和少数族裔成绩相同的情况下,大多数学校会优先选择少数族裔。从而导致白人群体的社会地位相对下降,而非白人群体的社会地位却明显上升。更严峻的是,据美国相关部门预测,“到21 世纪中叶,现在被称为‘少数民族’(minorities)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多数,而现在属于‘白人’(whites)范畴的美国人将成为美国人口的少数”[14]。在此形势下,以主流自居的白人群体的恐慌感加剧。亨廷顿在《谁是美国人?美国国民特性面临的挑战》一书中发出的“who are we”呼声,说出了美国白人的内心自白,是白人身份认同危机的集中写照。面对非白人群体社会地位的提升,白人群体在身份认同的危机中愈发迷茫、愤懑,并逐渐滋生了对外来移民及其相关政策的抵触心态。
身份认同同样也是欧洲民众较为关注的议题。近些年来,受国际政治的影响,大量北非和中东的穆斯林涌入欧洲。2011 年的利比亚战争促使更多战争难民流向欧洲,其中,大部分难民是穆斯林群体。大多数穆斯林处于欧洲社会的最底层,由于人口猛增、暴力倾向显著、犯罪率上升,他们逐渐引发了欧洲本土民众的厌恶与排斥。然而,在穆斯林人口出生率逐渐上升的同时,欧洲本土人口出生率却不断下降。长此以往,穆斯林人口将取代本土民众成为欧洲“主人”。但是,“西欧主流社会与穆斯林‘我国’和‘他教’的不对称性对立却普遍存在”[15]。倘若穆斯林群体成为欧洲“主人”,与穆斯林格格不入的基督教文明必然走向衰落,那时,西方人该将如何自处?又将走向何处?在此形势下,欧洲本土民众逐渐产生种族危机感与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对外来移民的排斥情绪不断强化。
总的来看,外来移民及其引发社会格局的深刻变动,导致了部分白人身份认同的危机感不断强化。政府无力解决各种移民问题,也难以安抚民众的焦虑心理。而西方左翼政党对移民的支持态度,进一步加剧了西方民众的身份认同危机。他们在迷茫、愤懑中发出“Who Are We”的呐喊,并极力渴望捍卫白人群体的“主人翁”身份。这种社会氛围刺激了西方右翼势力的崛起,从而为以反移民为主题的民粹主义的酿发埋下了诱因。
四、金融危机后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是其重要温床
特定时期利益格局的深刻变动,通常容易激化社会矛盾,因而民粹主义往往容易在社会转型或发生经济危机等特定时期沉渣泛起。在20 世纪中叶,经历现代化转型的拉丁美洲就曾见证了民粹主义的集中爆发。近些年来,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西方国家虽取得了巨大发展,同时也催生了各种社会问题,如经济不平等、民主政治衰败、多元文化冲突等。但是,很多社会问题并没有在社会治理中得到妥善解决,反而像滚雪球一般越滚越大。2008 的金融危机集中暴露了这些问题,经济问题带来的巨大生活压力促使各种社会矛盾集聚性爆发。这些矛盾主要表现在:民众对提高收入的渴望与愈发加剧的经济不平等,保障选民权利的承诺与名不副实的施政方针,社会对移民的依赖与白人群体的身份焦虑,等等。除了要面对就业、医疗、教育等领域的直接压力,多数西方民众还不得不承受社会枪击事件、恐怖袭击的冲击,这使得民众对社会安全与外来移民问题倍感不安与焦虑。政党之间、民众之间、民众与政党之间的冲突对立愈发激烈,执政党与在野党的分歧难以调和,白人群体与非白人群体的隔阂持续深化,社会撕裂与社会两极分化现象愈演愈烈。比如,在2011 年,美国爆发“占领华尔街”行动,抗争行动迅速由纽约华尔街地区蔓延至华盛顿、旧金山等50多个大城市,其中,大多数具有相似利益诉求的社会中下层民众集聚成群,围绕就业、医疗等领域的问题向执政党提出抗议,并强烈呼吁社会公正。
社会矛盾集聚的严峻形势,既暴露了西方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危机,又进一步彰显了西方社会治理的乏力。倘若西方各国适时运用有效的社会治理手段将社会矛盾的火苗摁灭,反而会增加西方政治的合法性。然而,事实却恰恰相反。在欧裔产生身份焦虑的同时,欧洲各国政府不断接收难民,却无法处理难民对社会安全、文化冲突等各个方面带来的治理难题,也无法安抚欧裔因难民问题所产生的焦虑情绪,从而导致欧裔的身份焦虑更加焦灼。在社会福利问题上,为迎合多数民众增加福利的要求并以此获取选票,西方政党大打福利牌,以至于国家财政承受能力不堪重负出现福利赤字。由于选民不同意削减福利、不愿意增加劳动时间、不愿意增加税收,为了防止选票流失,多数政党并不敢根治福利赤字的毒瘤,而只能将债务问题“击鼓传花”留给下一任当政者解决。长此以往,由高福利政策导致的债务危机必然会引发周期性经济危机。就此而言,“西方精英长期没有对积压的矛盾做出有力回应,迟迟拿不出调整社会再分配、缓解国内安全危机”[16]的有效方案,一方面无力破解经济复苏乏力、社会福利危机、精英腐败、暴力恐怖袭击等治理困境,另一方面对民众的经济焦虑感与身份迷茫感却无力舒缓。由此而导致经济不平等日益扩大、社会不安全局势日益严峻、部分民众对精英政治越来越失望,社会矛盾像气球一样被越吹越大,最终必然走向难以控制的局面。
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二者相互助推,愈发强化了民众对精英政治的抗拒心理。在此形势下,选民对建制派精英充满质疑,同时对传统政党的左右之争倍感厌烦。作为第三方势力的政党或政客所操纵的民粹主义恰恰契合了选民的心声与诉求,从而作为一股强大力量强势崛起。由此西方社会矛盾的集聚与社会治理的乏力为民粹主义的兴起提供了温床。
五、结语
新一轮西方民粹主义长时间、大规模的兴起,是西方国家各种复杂因素叠加催化的必然结果,暴露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深层次痼疾。在经济层面,随着全球化进程的推进,西方国家经济不平等状况持续加剧;在政治领域,代议民主政治的衰败,政党轮替退化为政党倾轧的否决性政治,民众对传统政党政治倍感不信任;在文化层面,外来移民的涌入引发一系列问题,白人群体身份认同危机感愈发强烈;在社会层面,金融危机后西方国家社会矛盾交织集聚,社会治理的乏力使得选民对建制派愈发不满,这些因素持续发酵,最终导致西方民粹主义大规模兴起。倘若西方国家无法在实质性变革和制度反思的基础上,重塑西方代议制度、平衡利益格局、优化社会治理、调和社会矛盾,民粹主义愈演愈烈的趋势将难以扭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