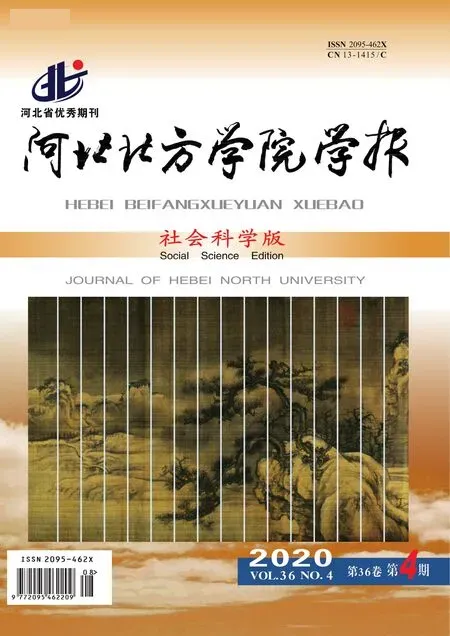《金楼子》编撰动因谫论
李 聪 聪
(河南大学 文学院,河南 开封 475001)
萧绎的《金楼子》是梁代重要的文学典籍。该书内容宏富,援引周秦古籍,历载君臣治国安邦之例,囊括古今乱亡之君,还记录了萧绎的家庭琐事及其聚书藏书之举,更有梁代逸闻志怪等。《金楼子》既是萧绎读书笔记的展现,也是他个人思想的汇集。学界对《金楼子》的研究多集中于其文本内容、文艺思想与文学价值,但未充分重视《金楼子》的编撰动因。文章厘清萧绎编撰《金楼子》的前因后果,以期对萧绎及《金楼子》有进一步的认识。
一、著书立言,以求不朽
作为梁王朝秉权执政的皇亲贵族,萧氏家族深受文艺熏染,雅爱辞章。四萧①的文学成就也是中国文学史上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张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魏武帝题辞》载曰:“帝王之家,文章瑰玮,前有曹魏,后有萧梁。”[1]如张溥所言,魏时曹氏父子3人在建安文坛慷慨多气,流风余韵令后世文人追慕不已。至于齐梁,梁武帝萧衍以帝王之尊博览群书,推崇文艺,奖掖后进,为梁王朝营造了良好的文艺氛围;昭明太子萧统温文尔雅,引纳文士,由萧统主持编撰的《文选》一书收录文章菁华,流芳百世而不坠;简文帝萧纲勤学好文,追新求变,对文艺精雕细琢,倡导宫体,引领一时风气。梁元帝萧绎是梁武帝萧衍的第七个儿子,一生自修典籍,著述尤勤。《梁书·元帝纪》记载萧绎年少能诵《曲礼》,聪颖好学,受家庭环境的影响,能够较为便利地接触到较多优秀的书籍。《金楼子·聚书篇》载曰:“初出阁,在西省,蒙敕旨賚《五经》正副本。为琅琊郡时,蒙敕给书,并私有缮写。为东洲时,写得《史》《汉》《三国志》《晋书》……”[2]366-367
萧绎将“著书立言,以求扬名不朽”的人生信仰作为编撰《金楼子》的目的之一。他在《金楼子·序》中言:“先生曰:余於天下为不贱焉。窃念臧文仲既没,其立言於世,曹子恒云‘立德著书,可以不朽’,杜元凯言‘德者非所企及,立言或可庶几’,故户牗悬刀笔,而有述作之志矣。”[2]1可见,萧绎渴望通过著书立言和笔耕不辍而扬名后世。他在《金楼子·序》中提及的臧文仲、曹丕及杜预3人都是通过立言扬名后世的历史人物。《国语》卷十四《晋语八·叔孙穆子论死而不朽》中记载鲁国公派叔孙穆子即叔孙豹到晋国出使访问,被范宣子询问“死而不朽”的含义。叔孙豹回答:“鲁先大夫臧文仲,其身殁矣,其立言于后世,此之所谓不朽。”[3]由此可知,叔孙豹将臧文仲视为死而不朽的典范。臧文仲是春秋时期鲁国的重臣,历经鲁庄公、闵公、僖公与文公4位国君,且在鲁国危难之际屡次谏言,为国家作出了重大贡献。如鲁庄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66),鲁国发生饥荒。臧文仲出谋划策并主动请缨去齐国游说,用钟鼎宝器作抵押向齐国求购粮食,从而帮助鲁国度过难关。叔孙豹以臧文仲“长于辞令,死而不朽”为例,阐释了“死而不朽”是一种超越生死的人生价值观。臧文仲声名播迁于世,其个体生命也具有了永恒的价值。三国时期,曹丕在《与王朗书》亦曰:“生有七尺之形,死唯一棺之土,唯立德扬名,可以不朽,其次莫如著篇籍。”[4]109曹丕在此思考人生归宿的问题,旨在说明人固有一死,而立德著书可使人死而不朽。曹丕在《又与吴质书》中言:“观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而伟长独怀文抱质,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谓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论》二十余篇,成一家之言。辞义典雅,足传於后,此子为不朽矣。”[4]110他认为文人徐幹既有文采,亦有人品名节,是一个文质兼备的君子,其政论性著作《中论》是一部阐发圣贤之道的子书。曹丕评论该书辞义典雅足以流传后世,正指出了著书立言对于扬名后世的重要性。杜预是魏晋时期著名的政治家和学者,著有《春秋左氏经传集解》等。《晋书·杜预传》载曰:“杜预,字元凯,京兆杜陵人也……预博学多通,明于兴废之道,常言:‘德者非所企及,立功立言可庶几也。’”[5]可见,杜预也认为通过立言立功可以使自己留名历史。
显然,萧绎所列举的臧文仲、曹丕及杜预3人都有宏大的人生诉求。其中,臧文仲被认为是死而不朽的典范。臧文仲的“立言”,实指因他对春秋时期鲁国的贡献,被后人追忆而不朽。萧绎很认同臧文仲的作法,即“立言”可以使个人的完节美行传于后世。曹丕与杜预的不朽则是基于儒家思想的浸染,着眼于修身和人格的完善。萧绎也很赞赏他们的行为,即通过“立言”进一步完善自己,从而以盛德名世。因此,萧绎将立言不朽视为一种自觉的个人追求。他在《金楼子·序》中写道:“常笑淮南之假手,每蚩不韦之托。由是年在志学,躬自搜纂,以为一家之言。”[2]2萧绎特意指出,不同于淮南王刘安使人代笔完成《淮南子》,也异于吕不韦招揽门客代为著述《吕氏春秋》,他是亲自著述完成《金楼子》。由此可见,萧绎希望通过著书立言实现个人的永恒价值,并借此为后世留下精神财富且扬名于后世,从而达到名利双收的目的。因而,《金楼子》熔铸了萧绎强烈的自我表述与鲜明的个人情感色彩。
二、雅谈人世,宏论政术
《金楼子》一书多为体制短小的篇幅,语言典雅凝练,内容琐碎驳杂。余嘉锡在《古书通例》中言:“杂家者兼儒墨,合名法,知国体之有此,见王治之无不贯,故必杂取各家之长,如《吕览》《鸿烈》而后可。后世杂家,若《抱朴子·外篇》《刘子新论》之兼道家,《金楼子》《颜氏家训》之兼释家……此特於儒家之外,有所兼涉耳,未尝博综以成一家之学也。”[6]余嘉锡详细论述了汉魏子书体制的变迁与分类的沿革,并指出《金楼子》博综杂家与体兼释家的思想特点。萧绎秉承“著书立言,以求不朽”的人生追求,且躬身力行,坚持原创的著作动机,继承并深化了前贤“立言不朽”的人生价值观。他将《金楼子》视为承载思想与语言的文本载体,并渴望流誉千载,这亦是萧绎创作《金楼子》的主观因素。从该书的内容考察,萧绎的文人气质与内在修养使得他撰作《金楼子》旨在雅谈人世,宏论政术。
萧绎在《金楼子·序》中写道:“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2]4在此,萧绎称自己企慕像管仲那样有高雅的言谈,像诸葛亮那样有见识高明的言论。而管仲和诸葛亮都是辅佐朝政的有功之臣。“尝谓人曰:‘诸葛武侯、桓宣武并翼赞王室,宣威遐外,此鄙夫之所以慕也;董仲舒、刘子政深精《洪范》,妙达《公羊》,鄙夫之所以希也;荣启期击磬,纵酒行歌,斯为至乐,鄙夫之所以重也。’”[2]611-612萧绎阐明了自己对3个层面的追求,其一为政术。无论诸葛亮、管仲还是桓温,都曾身居要职,悉力尽智,尊王攘夷,有辅佐之功。且萧绎的母亲阮修容也曾勉励萧绎留心政术,如《金楼子·杂记篇》云:“余好为诗赋及著书,宣修容敕旨曰:‘夫政也者,生民之本也,尔其勖之。’余每留心此处,恒举烛理事,夜分而寝。”[2]1127萧绎论及母亲阮修容对自己的谆谆教导,言语中充满敬畏。因此,他废寝忘食并勤于著述,除满足自已修身养德的需要外,还有不辜负母亲期望之意。其二为学术。董仲舒“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思想主张是西汉长期奉行的正统思想,影响极大并延及后世。刘向覃思经术,校订皇家藏书,成为一代经学大师。萧绎曰:“及仲舒之学术,子政之探微,见重元光之初,声高建始之末,通宵忘寐,终日下帏,不有学术,何以成器?川溜决石,可不勉乎!驰光不留,逝川倏忽。尺日为宝,寸阴可惜。文武二途,并得俦匹。”[2]612从中可知,萧绎对董仲舒和刘向学术成就的肯定。而萧绎也非常勤奋,通宵达旦,卷不辍手,并希望自己文修武备,成为一个庶几两全的人。其三即萧绎个人情志与日常生活的展露。他所列举的荣启期是春秋时的隐士,行年90,纵酒行歌,知足常乐。这种豁达乐观的人生态度成为萧绎欣赏与向往的生活方式。他在《立言篇》中所阐述的对政术与学术的感慨以及对生活的感悟,成为贯穿《金楼子》一书的核心内容。
“今纂开辟已来,至乎耳目所接,即以先生为号,名曰《金楼子》。盖士安之《玄宴》,稚川之《抱朴》者焉!”[2]12萧绎指出,《金楼子》是类似皇甫谧《玄晏春秋》与葛洪《抱朴子》的著作。皇甫谧一生以著述为务,自号“书淫”,其《玄晏春秋》在《隋书·经籍志》与《旧唐书》中有著录,是一部记载个人所见所闻的子书。葛洪《抱朴子·内篇》论述道教炼丹术,涉及葛洪对社会现象的思考,传达了其个体的人生价值观念,也是汉魏时期的一部子书。萧绎自比皇甫谧与葛洪,旨在强调《金楼子》的子书性质及其著书不辍的人生追求。“开辟已来,至乎耳目所接”即《金楼子》的内容属性,该书的类目纵横上古3代,下迄齐梁,开篇《兴王篇》罗列从上古时代的帝王至梁萧衍的治国安邦之例,《箴戒篇》则囊括古今乱亡之君。这种篇目间对立统一的内在逻辑关系旨在劝诫,也与萧绎追慕先贤宏论政术的创作主旨环环相扣。此外,《金楼子》的部分篇目是萧绎的个人创作。萧绎将古今见闻载录,再附以议论,这些篇目主要雅谈人世。如《立言篇》即萧绎将读书见闻与日常所感记录在册,传达他的人生观与文学观;《戒子篇》是萧绎对子孙的家训之语;《终制篇》涉及萧绎对丧葬礼制的看法;《著书篇》记录了萧绎生平著述的书目;《聚书篇》则是萧绎自述私家藏书与聚书之迹等。
综上所述,萧绎将《金楼子》作为个人立言扬名的文本载体,用典雅简洁的语言议论人世与宏论政治。相较于前代子书,《金楼子》的性质并非对某一家思想的传承转述,而是杂糅多家思想。萧绎历时30余年独立完成《金楼子》,将个体价值观念进行延展,并熔铸个人的思考与智慧,使得《金楼子》成为子书创作的个性化展示。
三、游书释典,寄托性情
萧氏家族热衷文艺,以儒道治国持家,贯以仁孝,这是其鲜明的文化特征。萧绎身处良好的文艺氛围,上有父兄为榜样,旁有文士可切磋商讨,还有触手可及的文化典籍可阅览,这都为萧绎日后的文学创作提供了丰厚的积淀。萧绎在《金楼子·兴王篇》曰:“梁高祖武皇帝,生而灵异,有圣德……始在髫发,便爱琴书,容止进退,自然合礼……每读《孝子传》,未曾终轴辄辍书悲痛。由是家门爱重,不使垂堂。”[2]146可见,梁武帝萧衍从童年起便热爱读书,推崇孝道,举止合乎礼仪。在梁武帝重视孝道的情感态度影响下,萧绎也非常注重对道德品质的修炼和提升。因此,他编撰《金楼子》是希望通过著书立言的方式以求生命不朽,并将宏论政术与雅谈人世的内容主旨贯穿《金楼子》全书,近而使该书呈现出萧绎勤学上进、才学与品德兼备的正面形象。值得注意的是,《金楼子》是萧绎寄托性情的载体,却也离不开与世俗生活的天然联系。除了是萧绎个人化色彩的展现之外,还是他寄托性情与娱乐消遣的文本载体。
萧绎处在南朝政治安定的大环境下。梁武帝统治时期,上至帝王皇室贵族,下至民间普罗文士,都勤学好进,爱好文艺并将文艺视为消遣娱乐。罗宗强曾论道:“南朝一些最重要的作家,虽然与萧梁君臣用文学于娱乐不同。但是,他们主要也是用文学于抒一已情怀,而与儒家政教目的了无关系。这一时期的文学批评家们提出来一些文学的功利主张,如裴子野与刘勰等人,但对其时之创作实际影响很少,没有能改变文学的社会位置。文学的社会角色依然是抒一己情怀、消闲、娱乐。”[7]罗宗强指出,萧梁君臣的文学创作带动了一时的文学风气,且他们的创作多为娱乐和抒情,无关儒家政教的功利性。一方面,萧氏父子爱好文学是为了修身养性与陶冶性情。另一方面,萧氏父子招揽贤士,朝野之上君臣的聚众赋诗与对答唱和也体现出将文学视为娱乐消遣的倾向。《梁书·武帝本纪》曰:“竟陵王子开西邸,招文学,高祖与沈约、谢朓、王融、萧琛、范云、任昉、陆倕等并游焉,号曰‘八友’。”[8]萧衍早年是竟陵王西邸文学集团中的一员,这些文士通过结友聚会与赋诗唱和的方式展示个人才华,互相鉴赏评定,碰撞思想,将娱乐功能巧妙融会其中。“竟陵八友”的文学活动引领了一时崇尚文学之风气,促进了南朝文学的彬彬之盛。萧绎在《金楼子·兴王篇》载曰:“登于晚年,探赜索隐,穷理尽性,究览坟籍,神悟知机。读书不待温故,一阅皆能诵意,所以驰骋古今,备该内外,辨解连环,论精坚白。沛国刘瓛,当时马、郑,上每析疑义,雅相推揖。深沉静默,不杂交游,所与往来,一时才隽,至于得人,门称多士。”[2]148-149可知,梁武帝晚年仍广泛阅读各种典籍,读书诵意,学识渊博。萧衍与当时才隽文士交游并探讨义理,日常中的文学探讨就是一种消遣娱乐方式。由此,梁武帝萧衍为萧绎树立了爱好文艺与礼贤下士的榜样。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记载:“孝元初出会稽,精选寮寀,绮以才华,为国常侍兼记室。殊蒙礼遇,终于金紫光禄。义阳朱詹,世居江陵,后出扬都,好学,家贫无资……卒成学士,官至镇南录事参军,为孝元所礼。”[9]由此可见,萧绎在出任会稽太守时礼贤下士,选任贤能,身边聚集了一批文士,如朱詹、张瓒、刘显及裴子野等。义阳(今河南信阳)的朱詹家境贫寒,但勤学刻苦,不废学业,最终学成入仕,受到萧绎的礼遇。萧绎与这些文士相互往来,切磋文艺。如裴子野在萧绎任丹阳尹时,著《丹阳尹湘东王善政碑》歌颂萧绎在任时的政绩,而当裴子野去世时,萧绎为其作《散骑常侍裴子野墓志铭》,以示悼念。
萧绎在《金楼子·序》中写道:“盖以《金楼子》为文也,气不遂文,文常使气,材不值运,必欲师心。霞(暇)闲得语,莫非抚臆;松石能言,必解其趣。风云玄感,傥获见知。”[2]12由此可见,《金楼子》是萧绎在闲暇时写就的出自肺腑且发抒性情之语。《金楼子》还有一些篇目并非正统的叙事,如《金楼子·捷对篇》记载萧绎听闻所得的对话以及带有嘲谑意味的典故;《志怪篇》则记录神奇鬼怪与逸闻趣事等,这些篇目都是萧绎的消遣之作。张峰屹《逞才游艺与魏晋南朝诗歌与诗学》一文指出:“综观魏晋南朝诗坛,总的倾向是不断远离现实的社会人生,而流行逞才游艺的优雅娱乐。”[10]显然,视文学为消遣娱乐是南朝时期社会的创作风气。萧绎的诗赋中亦有不少游戏娱乐之作,如他的题名诗将描写对象的名称镶嵌在诗里,构思奇特,这在《宫殿名诗》《将军名诗》《车名诗》和《药名诗》等诗中有显著体现;再如萧绎写《宴清言殿作柏梁体》即是他在清言殿宴请群臣时君臣之间以七言诗句唱和的范例。
《金楼子》是萧绎出于著书立言和以求不朽的人生信念,将读书见闻载录在册的一部子书。该书辑录了自上古3代至齐梁的圣贤之君与昏庸无道的反面帝王的人物群像,旨在观王道兴衰,揭恶扬善,劝诫兼资。同时,萧绎将《金楼子》视为抒一己之情的文本载体,他在闲暇自由时记录的所观所感构成了《金楼子》一书雅谈人世的内容。《金楼子》中除了萧绎的雅谈与宏论,还有诸如《志怪篇》《捷对篇》以及《杂记篇》这样的非正统之论,这些是萧绎将文学视为娱乐消遣的重要体现。
注 释:
① 四萧指萧衍、萧统、萧纲与箫绎。
——以《金楼子》为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