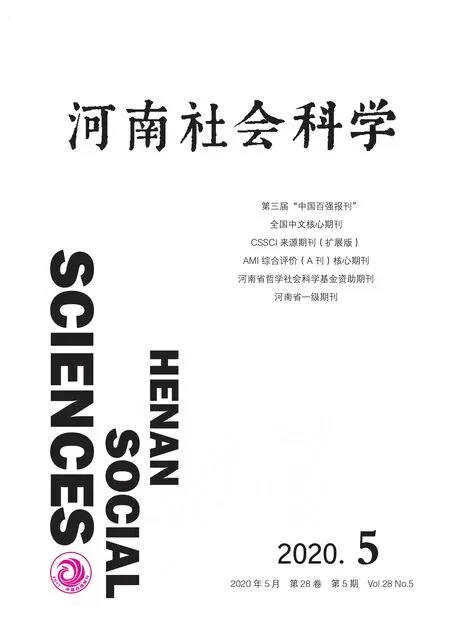扶手椅哲学
蒂莫西·威廉姆森 著王洪光 译
(1.牛津大学 哲学系,英国 伦敦 OX13BN;2.北京大学 哲学系,北京 100871)
“扶手椅哲学”一词通常带有贬义,用来形容以所谓传统先验方式完成的哲学,与之形成对比的是从真实实验中获得的哲学,这些实验由自然科学家或哲学家亲自完成。一个支持x-phi(即“实验哲学”)运动的网站展示了一段燃烧扶手椅的视频,建议哲学家别再坐在扶手椅上发表这个世界应该如何的理论,相反,应该去观察这个世界实际上如何。特别是,实验哲学的一些支持者认为,如果哲学家想要主张“我们”对思想实验中各种假设的情景有何看法,那么他们应该首先去查明统计数量显著的外行对那些情景实际上有何看法。这呼应了挪威哲学家阿恩·纳斯(Arne Næss)早前一项基于调查的研究,他调查研究了外行对日常语言中哲学术语的理解,之后将其用作对日常语言哲学的指责。
令人困惑的是,扶手椅成为一个话题,可追溯到牛津哲学家奥斯汀支持日常语言哲学的经典例子,他将日常语言哲学与根基较不扎实的、在扶手椅上自己动手完成的理论建构做对比:
我们共同的词语储备,体现了人们一代又一代所发现的值得做出的区分和值得建立的联系:与你或我坐在午后的扶手椅上构想(这是传统上最受哲学家青睐的方法)出来的相比,它们很可能在数量上更多,由于经受了优胜劣汰的长期考验而更可靠,并且至少在所有日常及合理的实际问题上更微妙。
这种对待日常语言中区分的方法论态度,可以从奥斯汀追溯到牛津实在论者约翰·库克·威尔逊(John Cook Wilson),后者写道:“永远都无法不出差错地忽视语言中的现行区分。”
在奥斯汀看来,日常语言中的区分虽然可以在扶手椅上获得,却是由数百年来扶手椅之外的经验所塑造、修正和检验,而扶手椅哲学家忽视了这一点。在持实验哲学立场的批评者看来,扶手椅哲学家使用了那些区分,但并未检查他们这样做是否带有种族、性别或其他偏见。不过,许多实验哲学家并不赞同这种“消极方案”。他们认为,实验哲学是扶手椅哲学的一个有价值的补充,而非竞争对手。根据实验方法的改进标准,支持指控种族偏见和性别偏见的早期实验结果,普遍没有得到重复。在这个有限的范围内,日常语言哲学的方法论得到了维护。当然,即使某个思想实验的一个特有判定对人类而言是普遍的——例如在知觉哲学中,如果每个人都同意在某情况下受试者看到一棵树——那也不表明这个判定就是正确的。某些固有的人类偏见可能会促成错误的判定。
这种担忧可能会沦为一种更一般的怀疑论。因为我们对思想实验的判定,其实只是关于假设情景的判断,实际上就是反事实条件句:“假如存在这种情况,那么受试者将(不会)看到树。”对这类条件句的非反思性评估使用的认知机制,我们没有理由认为与评估哲学之外的类似反事实条件句所使用的有所不同。从演化的角度看,我们常常需要对条件句做出可靠的评估,否则进行选择时就会犯太多错误。(“假如我选择A,结果会比选择B 更好吗?”)思想实验的认识论是反事实条件句认识论的一个意外的副产品。
条件判断可以存在于先验判断范例与后验判断范例之间的谱系上。例如,“如果你要透过我的卧室窗户看,你就会看到一棵树”显然是后验的,而“如果你往森林中间看,你就会看到一棵树”则更多是先验的。至于“如果你望向没有障碍物的n 米开外的一棵树,你就会看到它”,从扶手椅上判断它是先验还是后验的难易程度,依赖于“n”的取值而变化。这种连续变化使得在先验知识与后验知识之间,区分的进深成为问题。充当背景知识的不仅是变化,甚至遗忘已久的经验,也会对形成和修正我们(包括在假设的情景中)大致上准确运用词汇的能力起作用。考虑这些情况时,扶手椅上的哲学家在所想象的可能性上运用模式识别能力,他们仍然可从这种“前-扶手椅”经验中获益。扶手椅思维远不是一个“单纯的”方法。
越来越少有人相信:哲学绝不应当依赖非扶手椅式方法。知觉哲学家们常常从知觉心理学的实验结果中学习,不这样做则是愚蠢的。研究空间和时间的哲学家必须考虑物理学理论,显而易见,最需要考虑的就是爱因斯坦的狭义相对论。当然,有些哲学家坚持认为,他们的兴趣在于我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经验或概念,而非物理的空间和时间。但避免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互动,并没有得到很好的结果。即使他们能够避开物理学,又怎能忽视实验心理学家关于人类时间经验的非扶手椅式工作,或语言学家关于不同自然语言中时态语义的非扶手椅式工作?至于哲学的“概念性”问题与科学的“经验性”问题之间的所谓天壤之别,则依赖的是某种行不通的概念理论。无论如何,当代形而上学家更感兴趣的是空间和时间自身的真实本质,而不是我们关于空间和时间的经验或概念。
这种压力可能暗示:只有采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经验”方法,哲学才能成为完全严格的。但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因为它忽视了最为严格的科学——数学,其方法就是典型的扶手椅式。数学家无需依赖实验即可证明其定理。逻辑学既是数学也是哲学的分支,它采用扶手椅方法。模仿物理学并不会帮助逻辑学家回答他们的问题。
一个自然而然的异议是,逻辑学是特例:在哲学的大多数分支中,我们都不能指望用数学证明来回答问题。数学先例与那些分支有什么关系呢?
该异议的缺点在于,数学方法并不是纯粹演绎的。数学证明逐步进行,这些步骤最终都是第一原理的实例,数学家接受这些原理而不用进一步证明。就目前而言,我们无需担心这些第一原理是否逻辑规律、集合论公理或者其他东西。重要的是,它们的认识论地位亟待说明。一些数学家和哲学家曾希望第一原理不存在认识论问题,因为它们是“根据定义”而有效的。可是这个回答不起作用:定义仅仅将证明责任从被定义项转移到定义项,定义并不会使证明责任消失。数学的第一原理也并非不容置疑。离经叛道的逻辑学家理解这些第一原理的内容却仍未被说服,所有第一原理都被质疑过。
伯特兰·罗素在一个多世纪前就面临这个问题,他曾计划将数学建立在纯逻辑规律的坚实基础上,但他发现所需要的原理并不完全自明。他由此断定:支撑原理的是归纳,而非演绎。他在一篇首发于1907年的论文中说:
……我们是因为能够知道后承为真,才倾向于相信前提,而非因为知道前提为真,才相信其后承。但是,从后承推断前提是归纳的本质。因此,研究数学原理所用的,其实是一种归纳的方法,这与其他科学领域发现一般规律的方法基本相同。
即便到今天,罗素的说法也仍符合研究者在数学基础领域的实践。当然,罗素心中所想的并不是简单枚举归纳,因为那只会让我们用描述数据的术语同样去阐述概括,而数学基础理论一般要引入新的基本术语。现在我们更倾向于用皮尔士的“溯因”(abduction)一词来指称罗素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称其为“最佳解释推论”,但条件是数学中的相关解释不是因果的。确切地说,研究者从少数更普遍的原理推导出许多具体的、看似完全不同的数学事实。这些原理始终有信息量,简单、优雅,那些数学事实也借此被统一起来。如罗素所见,科学家也可用同样的方式来主张物理学的基础理论。数学这个例子表明,溯因方法可在非扶手椅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外使用。数学这门扶手椅科学就需要它。
溯因方法对哲学也有意义。清晰明确的哲学理论可能会包含一些始终有信息量的简单、优雅的普遍原理。那么,哲学家想要主张一个理论,就可以去证明它能够为许多具体的、看似完全不同的事情提供统一的解释。20 世纪后期重要的分析形而上学家大卫·刘易斯(David Lewis)就明确以这种方式主张具有其鲜明特征的理论。我在逻辑学和形而上学中都曾使用过溯因方法,并且为这种使用而辩护。在这些情况下,在扶手椅上可能已经有足够多的约束性材料了:我们通常只需要去寻找使原理无效的反例。于是,数学成为在构建哲学理论时运用扶手椅式溯因方法的相关先例。
许多哲学分支,例如认识论、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以及心智哲学、语言哲学和艺术哲学,它们主要处理杂乱且难以控制的人类世界,其中有信息量且无例外的普遍概括并不多。可能有人会好奇,溯因方法在这样的情况下能让我们走多远。
杂乱且难以控制的复杂性问题并非哲学特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也要处理这种问题。大多数宏观系统如此,许多微观系统也是如此。例如,生物学家已经认识到,不要期待能对生物系统给出有信息量且无例外的普遍概括。科学家开发出一种应对这种情况的建模方法。模型实际上是对那类复杂系统中高度简化的假设示例做精确描述,描述通常由定义了系统如何随时间变化的数学方程构成。可以通过严格的数学方法研究模型的特性,来帮助科学家理解在真实系统所观察到的特性。在许多科学领域,进步并不在于发现了新的、无例外的普遍自然律,而在于开发出越来越好的模型。
模型的意义有时在于做出定量准确的预测,但并非所有情况都是如此。例如,有些生物学家想要知道物种为何倾向于通过两性而非三性繁殖。回答这个问题的好方法,就是探究三性繁殖的模型:首先制定三性繁殖将如何运作的合理规则,然后通过数学计算或计算机模拟来跟踪这个系统随时间推移的发展,希望能发现是什么地方出现问题——或许由于该物种缺乏多样性,所以容易受到环境变化的影响。这些将有助于解释为何缺乏三性繁殖的物种。这种情况就与定量准确的预测无关,相反,是模型的定性作用。我们可以不带贬义地称之为扶手椅生物学。
模型也能在哲学中发挥定性作用(Williamson 2017b)——它们已经在一些领域发挥这样的作用了:形式知识论专家使用贝叶斯概率论和认知逻辑框架来研究涉及知识和不确定性情境的数学模型。例如,“约翰知道玛丽知道约翰知道玛丽知道约翰不忠”这样的陈述很容易将我们搞晕。对这类陈述进行严谨推理,最好的办法是使用扶手椅哲学家提出的知识与无知的数学模型(Hintikka 1962)。计算机科学和理论经济学中已广泛使用这种模型(Fagin et al. 1995)。同样,扶手椅语言哲学家使用来自逻辑学的精确方法,已经发展出通过语句构成词的字面意义来计算语句的字面意义的形式语义框架。语言学中广泛地使用这些方法来研究自然语言的意义(Heim and Kratzer 1998)。尽管大大简化了语言现象,但其关于语言结构性基础的深刻见解,对恰当理解更复杂的现象是不可或缺的。道德哲学和政治哲学领域已经用博弈论和决策理论的数学方法来构建复杂选择的模型。例如,用这些模型帮助解释:为什么人人都依据理性行动,结果有时候却对所有人而言都更糟?
常见的刻板印象认为,自然科学取得了进步,而哲学却没有进步。此反差依赖于“科学进步在于发现普遍规律”这个过时观点。至少在逻辑学之外,哲学家并没有发现很多这种规律。然而,一旦我们意识到许多科学进步在于提出更好的模型,我们就应该意识到哲学也取得了不少同样的进步。可用于知识论和语言哲学的形式模型,比1950年时要好得多。因为这些模型为知识和意义的底层结构提供了更深入、更精细的见解,它们几乎完全是在扶手椅上提出来的。但是大多数哲学家,甚至许多实际做建模工作的人,却没有用那些术语来思考他们的方法。结果,他们严重低估了自己学科所取得的进步。
哲学与其他探究之间的差异,远没有许多哲学家认为的那么大。哲学在很大程度上与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中最具理论性的部分更加相似,而非其最具实验性和观察性的部分。但我们不应该期待哲学与那些科学之间存在一个逐渐趋同的方法,因为哲学与数学的基础部分也有许多共同之处,数学是最具有扶手椅特征的科学。只要有扶手椅,它们就会是思考的好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