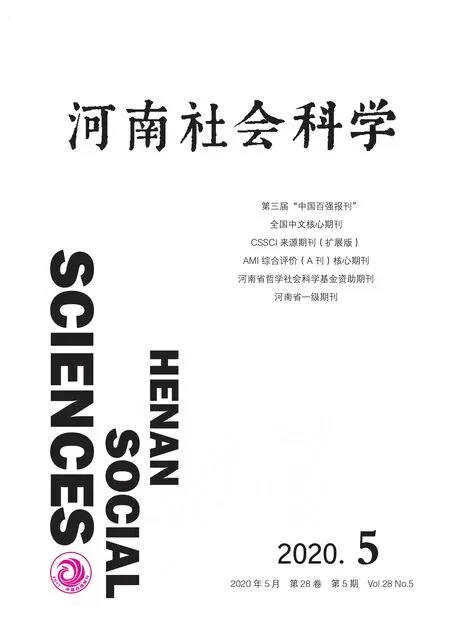论《诗经》在《中庸》叙事中的结构性意义
张红翠
(大连大学 文学院,辽宁 大连 116622)
很少有人在《中庸》研究中指出《诗经》的使用问题,其中《诗经》在《中庸》文本中的反复出现毫无疑问构成《中庸》说理叙事的重要特征。《诗经》在《中庸》文本中的出现不能被认为是简单的修辞性引用。《诗经》的反复出现,对于《中庸》说理具有重要的叙事性作用和根本性意义:修辞性意义、阐释性意义以及结构叙事的功能性意义。《诗经》之所以能够在《中庸》中反复出现并使《中庸》呈现特有的叙事性局面,有许多内在原因,其中有三个原因尤为重要:一是《诗经》之于中国文化思想具有经典性意义和地位,这决定了《诗经》对于《中庸》具有“原型”性价值;二是中国文化“述而不作”与崇古宗经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促使《中庸》不断回到《诗经》的古代现场;三是中国古典思想文化的口语文化本质导致了以《诗经》为代表的文化经典在《中庸》文本中反复出现的叙事方式。
一、《诗经》之于《中庸》文本的三重叙事性意义
在查找《诗经》之于《中庸》文本叙事作用的内在原因之前,我们先以现代叙事学理论为基点对《诗经》在《中庸》叙事中结构性作用的具体表现进行梳理。《诗经》在《中庸》叙事中的作用可以从修辞、阐释和结构性三个方面展开分析。
(一)引用:修辞性意义
《诗经》在《中庸》中的出现,首先是以被引用的方式呈现的,并且通常是在一个章节主文之后,作为补充、说明和证据被引用。如第13、14、15、16、17、20章,全部是在孔子语录之后引用一段《诗经》,而结尾的第34 章则整章以引用六段《诗经》为内容而结束。这种行文表明《诗经》占据了《中庸》叙事的重要地位,总是作为重要的文献传统和思想依据被引用。作为一种修辞方式,“引用”指的是,写文章时有意引用成语、诗句、格言、典故等,以表达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说明自己对所讨论问题和道理的见解。这种修辞的目的是运用各种语文材料或各种表现手法修饰文章词句,以便增强语言表达的效果,使表达更准确、鲜明和生动。这是修辞学的定义和解释。而就现代叙事学而言,“引用”所呈现的不仅是一种修辞关系,更是一种内在的文本关系,即引文和正文之间的文本关系,因此,现代叙事学理论将修辞的意义拓展为哲学品格和文本理论的问题。《诗经》在《中庸》文本中的反复被引用,使《诗经》文本超出了一般文学经典的意义表达,而成为《中庸》文本的一个重要的意象,这个意象不是单纯的文学意象,而是一个精神和传统的意象。这一意象保存着《中庸》思想在叙事和生存哲学层面的某种整体性意念。所以,《诗经》在《中庸》中的出现,既是一种修辞的表现,又超越了单纯的修辞性意义。
(二)互文关系:阐释性意义
在现代叙事学理论的目光下,《诗经》在《中庸》文本中的反复出现,客观上造成了《中庸》文本叙事的一种结构性局面,这种局面便是:相应于《中庸》思想叙事的文本表达层面而言,《诗经》构成潜存于《中庸》文本深层的阐释性结构层面。这两个层面构成一种关系,即表层向深层的不断“回访”和“追寻”,这种结构性局面,用现代叙事学的理论表达,即是一种文本内部的“互文性”结构关系。“互文性”这一概念最早由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者茱莉亚·克利斯蒂娃提出,她指出“任何作品的文本都是像许多行文的镶嵌品那样构成,任何文本都是其他文本的吸收和转化”①。因此没有单独的文本,任何文本之间都是互相指涉的,构成了绵延不断的文本群体。后来,叙事学理论家热奈特对“互文性”这一概念“做了决定性的工作”,他在《隐迹稿本》中指出,“互文性”表现为“一文本在另一文本中的实际出现”,如引用。热奈特突出了“互文性”理论的思想意图,即搭建一种现代生命与传统之间的历史关系,并借“源文件”“元典”这样的概念将历史、传统甚至一个更终极的世界意象、起源时刻纳入现代自我的精神领会当中。
对于《中庸》文本而言,《诗经》就是这种“典故式”和“源文件式的”的存在,是沉淀在中华文化中被抽象和被提出来的一种纯粹的形式。它好像一个文化及其传统中的谚语、古老的哲学命题,以及格言片段。“典故”以及“源文件”保存着子文件的基因、密码,具有解释子文件的权威性意义和可能。从这个意义上说,《诗经》在《中庸》的文本中复出再现,就构成了《中庸》叙事及其意义的“源头”。因而,从叙事功能和作用而言,作为源文件的《诗经》,是推动叙事的结构性动机,是意义生成的原始结构,是叙事意义生成的源头,暗含着对后来文本的解释和意义规定。因而,《中庸》叙事对《诗经》的不断提及,甚至思考都是对文化源文件智慧的“回忆”和阐释,而《中庸》思想的阐释和理解也需要借助《诗经》的巨大内涵才能完成。
(三)结构叙事:功能性意义
《诗经》的反复出现,使《诗经》还具有结构《中庸》文本的功能。这种判断是从结构主义的理论视角做出来的。根据结构的理论,一个文化(文本)意义的产生与再创造透过作为表意系统的各种实践现象与活动,这种现象和活动连接着文化(文本)意义被制造与再制造的深层结构。因而,正如霍克斯所说,“在任何既定的情境里,一种因素的本质就其本身而言是没有意义的,它的意义事实上在它和既定情境中”。对于《中庸》文本而言,《诗经》的反复出现使其具有之于《中庸》文本而言的永恒性结构的意义,是《中庸》叙事展开的动力装置。首先,《诗经》在《中庸》中被引用,但不是被动的被引用,也不是文本的附属部分,而是具有主动性功能的主体性部分,对于理解《中庸》具有决定性意义。因而,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并不是写作者在掌控叙事,而是《诗经》在结构叙事。其次,《中庸》与《诗经》构成了一种双向的结构关系,《中庸》因为《诗经》而实现,《诗经》因为《中庸》而得以完成。因而,《诗经》作为中华文化的典故、原型、母题成为《中庸》叙事内在的结构性动力,成为《中庸》的深层“信仰”。之于《中庸》,《诗经》像神秘的原始力量保存着世界的秘密,为存在者提供母题性参照,规定了人类存在的本质和根源,使生命形式最终都在遵从“一个早在人类发展反省意识前就已经建立的模式”②。可以说,《诗经》作为文化典故是《中庸》理解存在、建构叙事的重要依据和基础,也是推动叙事、阐释叙事的重要根源。作为《中庸》文本的深层结构,《诗经》之于《中庸》而言具有古老命题的意义,这些古老命题在时间的开端便存有对时间长流中当下生命状态的寓言般的先在指认。它们作为更高的抽象掌控着生命的痕迹、存在的样式,不断在未来的生命文本中反复出现,《诗经》在《中庸》中的不断复现就带有这种结构性特征。因而,《中庸》不断在叙事中提及具有古老的谚语和命题意义的《诗经》,并始终与之保持紧密关联。所以,从《诗经》在《中庸》中的文本表现,我们可以认定,这种现象不仅仅是一种叙事方式和逻辑表现,更是一种生命哲学和生存信念的体现。《中庸》以这种方式将《诗经》的意义提示给我们,相应地,《中庸》的叙事也实现了对《诗经》所包含的古老生命经验的模仿、阐释和再现。在《诗经》强大的原型性意象世界中,《中庸》的叙事让阅读者领略到《诗经》作为生命“典故”的意义、“原型”的意义,这深刻地透露出《中庸》深层的世界观与存在观,即当下(现代)生命与传统生命之间的“一以贯之”。
二、《中庸》叙事特征的结构性动因
为什么《中庸》会有这样的叙事局面和文本结构?有几个重要的原因在起作用。我们将从《诗经》之于中国文化思想具有经典性意义和地位、中国文化“述而不作”与崇古宗经的中国传统文化基因,以及口语文化时期的技术惯性三个方面来进一步探究。
(一)《诗经》的双重“身份”决定了《诗经》在《中庸》中的突出地位
在中国文化中,《诗经》具有经典性意义,既是文学经典,又是文化经典,因而,具有双重身份。这双重身份尤其是后者,决定了《诗经》在中国文化表达过程中的地位、作用和出现方式。
1.“诗”的身份
就文学意义而言,《诗经》被誉为中国诗歌的源头,中国诗歌的生命起点,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无可撼动的地位。和《离骚》一样,《诗经》被认定为中国诗歌、文学的两大传统之一。魏晋时期钟嵘的文艺论著《诗品》,就是在《诗经》和《离骚》两大传统中梳理魏晋南北朝之前的诗歌发展。钟嵘认为:“古诗,其体源出于《国风》。”③“汉都尉李陵其源出于《楚辞》。”④“魏陈思王植其源出于《国风》。”⑤“晋步兵阮籍其源出于《小雅》。”⑥可见,以诗歌身份出现的《诗经》是后来诗歌的典范,为后世诗歌创作提供了传统:体裁的传统、朴实苍劲的文学风格的传统、现实主义精神的传统。到宋代朱熹的《诗经集注》,尤其注重《诗经》文本的文学性,着力于以《诗经》文本为中心的文学研究,突出《诗经》的文学意义。但是在人们注意《诗经》的文学意义和价值之前或者同时,人们一直或者主要是把《诗经》作为更具有普遍性意义的文化经典来对待的。所以,在中国文化中,《诗经》还有一种身份似乎比“诗”的身份更重要,这就是“经”的身份,即文化经典的身份。
2.“经”的身份
什么是“经”?《说文解字》解释为:“织纵丝也。”⑦本义是织布机上供纬线穿梭交织、等列布设、纵向绷紧的丝线。段玉裁做了进一步的解释:“织之纵丝谓之经。必先有经而后有纬。是故三纲五常六艺谓之天地之常经。”⑧显然,经过这种引申,“经”就有了典范的意义,表示作为思想、道德、行为等标准的书。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文化经典,作为儒家六经之一的《诗经》无疑就具有这种文化意义,某种程度上构成中华文化及华夏民族生命的源头之一。那么,《诗经》作为文化源头的经典性地位是如何确立的呢?是通过不断经典化的过程被赋予的。在《诗经》经典化的过程中,孔子的认定无疑具有奠基性意义。孔子不仅在删诗制礼作乐的过程中将《诗》三百列入儒家“六经”,而且总是在教育活动中惯例性引用《诗经》诗句、惯例性以《诗经》为标准对事件或者人物品性与行动进行评价和判断,给出建议和训示。《论语》中,孔子和弟子们经常以《诗经》为基准来讨论问题,并将《诗经》中的很多句子引申为人生哲理或者道德信条。《论语·学而》中有:“子贡曰:‘《诗》云:“如切如磋,如琢如磨”,其斯之谓与?’子曰:‘赐也,始可与言《诗》已矣,告诸往而知来者。’”⑨《论语·为政》中有:“《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⑩《论语·八佾》中有,子夏问曰:“‘巧笑倩兮,美目盼兮,素以为绚兮。’何谓也?”子曰:“绘事后素。”⑪《论语·泰伯》中有:“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⑫《论语·季氏》中有:“不学《诗》,无以言。”⑬《论语·阳货》中有:“小子何莫学夫《诗》?诗,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迩之事父,远之事君;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⑭《论语·子罕》:“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⑮《史记·孔子世家》进一步引申:“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于《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这些不完全的片段非常明显地表明,《诗经》在孔子礼义传习过程中的地位。在这个经典化的过程中,《诗经》被赋予礼乐文化重要载体的地位,具有了不同于文学身份的功能,这个功能是:它是文化本质的呈现,其作用则是让百姓学习以后提高道德修养,最终达到平天下的目的。所以,《诗经》几乎成了社会文化生活的核心内容,它是学习、修养的主要内容,是学问的主要标准,能够谈论《诗经》是一种有学问修养和文化的标志。可见,孔子对《诗经》的看法、评价和认定不断赋予《诗经》以“文化母体性”地位,以及中华生命原始基因的地位。
后来,汉代设立五经博士,专修儒家经典,作为五经之一,《诗经》是汉代官学研究的一个重要科目。儒生的《诗经》研究延续了孔子开创的《诗经》社会教化的经学传统,继续将《诗经》文化经典化。在他们的研究中,尽管《诗经》的文学性也同时被讨论,但通常是被放在其政教功能之后被认知的。自汉代起,关于《诗经》的主要研究有毛诗、郑玄笺、孔颖达注等。《毛诗序》开篇即点出:“《关雎》,后妃之德也,风之始也,所以风天下而正夫妇也。故用之乡人焉,用之邦国焉。风,风也,教也,风以动之,教以化之。”⑰《诗谱序》中有:“《虞书》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然则诗之道……何者?论功颂德。所以将顺其美,刺过讥失;所以匡救其恶……遂为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⑱鲜明地指出《诗经》的功能和本质。这种观点虽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点,但是在客观上确实固化和强化了《诗经》的经典性地位。因此,在汉及其后的《诗经》研究中,《诗经》不断被赋予坚实的文化经典的神圣性地位。而且,后世对《诗经》的阐释基本是在我注“六经”的路数上展开,这意味着,每一次阐释都在加固《诗经》的经典性地位,这就不断使《诗经》被符号化和经典化。可见,就文化的意义而言,《诗经》俨然被赋予中国文化精神以及生命源头的地位和价值。而这种地位的作用就不仅仅是诗学的和文化的,它还被抽象化为一种纯粹的形式,包含着中国传统文化的母题、原型和内核,进入到对文化的影响之中,并不断被古人指认为生命法则的原始表征,而古人的文化生命也因此得到衍生,并得到揭示,所以,《诗经》对于中国传统文化而言,具有文化根源和精神出处的意义。因而也不难理解,《诗经》之于今天文化的意义与其之于古代文化的意义是不同的。而《诗经》之于《中庸》的方式、作用和价值就体现了这种不同。
(二)中国古人“述而不作”的文化传统和遵古的意志,潜在地影响了《中庸》叙事的文本形式
“述而不作”出于《论语·述而》:“述而不作,信而好古。”朱熹集注指出:“述,传旧而已;作,则创始也。”《北史·袁翻传》:“皇代既乘乾统历,得一御宸,自宜稽古则天,宪章文武,追纵周孔,述而不作。”清朱彝尊《刘永之传》:“其自称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夫岂以其圣而傲当世哉!”三家注《史记·孔子世家》中有“孔子以四教”,南朝宋裴骃的集解指出:“何晏曰:‘论古而不自作,处群萃而不自异,唯道是从,故不有其身。’”这种以“古”为“经”的意志赋予《诗经》与其他古代典籍一样的“经”的地位,这些经典被奉为后来社会发展的“法则”“典章制度”以及社会文化的依据和来源。这是人类文明早期赋予自我合法化的一种文化努力和方式。在这种传统下,《诗经》便具有了特殊的意义,它是在漫长的文明之河中逐渐成为中华文化的生命寓言,给予中国古人以生命的启示,似乎是天启般的存在。《诗经》正是以后一种身份进入对《中庸》的叙事意识中的。正是《诗经》的这种特定身份,才使得《诗经》对于《中庸》而言具有复杂的结构性意义。“述而不作”的传统又与宗经原道思想相关。《文心雕龙》总论详细论述了原道、征圣以及宗经的总体观念。这种观念不应该被单纯地理解为是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而产生的,也不是纯粹的文学本体论的理论,其背后隐藏的实质是中国古人不同于今人的世界观和宇宙观:生命大一统、天地人共在之观念。
(三)口语文化时期——习惯性表达方式
美国学者沃尔特·翁在《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中对口语文化进行了界定,并对口语文化和书面文化之间的逻辑性差异做了到目前为止较为全面的和非常有价值的探讨,这为我们提供了理解《中庸》文本特质和叙事结构的又一个理论可能。
沃尔特·翁指出,“无文字或者印刷术浸染的文化称为‘原生口语文化’”⑲。口语文化时期的思维和语言表达方式,与书面文化、印刷文化的线性以及理性方式不同,主要有九个方面的主要特征。在这九个特征中,有三个特征尤其为我们理解《诗经》在《中庸》中的文本表现提供了有效的解释。我们逐一进行对照理解。(1)附加的而不是附属的。口语文化经常用“和”(and)来连接上下文,而不是书面话语经常使用的“然后”(then)、“当什么时候”(when)、“因此”(thus)等线性顺承的连接词。若此,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之间的逻辑方式就有明显的区别,前者是并列或者并置关系的,后者是线性向前的⑳。《中庸》文本中《诗经》诗句的叠放以及以“子曰”以及“诗曰”为起始的《诗经》引入在《中庸》文本中所起到的作用与“和”(and)所起到的作用是一致的。(2)聚合的而不是分析的。口语文化喜欢说的不是一般的抽象的事物而是具体的事物,比如,不说一般的公主,而是美丽的公主。因此,口语文化里承载着大量的具体而非抽象的称号(这些称号也是事物的呈现)㉑。《诗经》诗句在《中庸》中的并列,也是一种聚合而非分析的文本表现。(3)冗余的或“丰裕”的。口语文化中的冗余,即重复刚刚说过的话。因为没有文字的固定,没有广泛的书籍文字作为传播媒介,为了便于传播和记忆,就反复重复固有的套语;要想保证前后内容的连贯且不被快速忘记,就需要不断提起之前说过的话。《中庸》中《诗经》以及“子曰”的内容都是传统沉淀下来的不断被说起的“话”,沃尔特·翁称之为说理的一种套式,冗余的套式。沃尔特·翁所提出的“套话”概念,某种程度上对应了现代叙事中“互文性”理论提出的关键词:谚语、典故以及固定短语等,二者是具有相似功能的叙事要素。所以,《诗经》在《中庸》中的反复出现,还是口语文化表达习惯中对“套话”的一种自动性技术习惯。诗句片段被单个抽离出来之后,就变成了箴言警语。从某种程度而言,作为套语、谚语和俗语,《诗经》扮演了口语文化表达中的固定成分,链接和固定口语表达内容,从而固定口语文化资源的记忆和传播。这在客观上也加固了《诗经》或者套语在文化传播过程中的固定地位和影响。但是沃尔特·翁的分析并不止于此,他更深入地指出,在口口相传的文化中,谚语和俗语不是偶一为之的手法,“它们在我们的生活中绵延不断,它们构成思想自身的内容。没有它们,任何引申的思想都不可能存在,因为思想就存在于这些表达方式之中”㉒。所以,口语文化里的人必然花费很大的精力,反复吟诵世世代代辛辛苦苦学到的东西。这就慢慢确立一种高度传统或者保守的心态。所以,《中庸》对于《诗经》和“子曰”语录的重复,从技术上来说,就是口语文化表达习惯的体现。
在沃尔特·翁的研究中,我们不仅获得了理解《中庸》叙事方式的宝贵视角,获得了了解口语文化与现代文字印刷文化之间的差异和历史演变,也获得了反思现代文化思维特征的重要而有效的途径。
三、意义——构建生命连续统,串起时间的碎片
《诗经》在《中庸》文本中的反复出现,无论是出于《诗经》的文化原型身份,还是出于中国古人遵古宗经与“述而不作”的文化传统,抑或口语文化时期表达习惯和叙事技术,都使得《中庸》在其文本格局、形式结构的背后透露出完全不同于现代文化的气息。这种气息的深层实质是古人有别于今人的宇宙观和生命体验。
在《中庸》不断回溯《诗经》的过程中,透露出一种深刻的观点,即人的存在意义在时间之初就已经完成了,人的存在密码早已被保存在先在的“世界形式”中,这种形式以文化典故、谚语或者诗歌的诗句等形式载体具体呈现出来。它们是暗示的、隐迹的,是绝对命令,是决定叙事、结构叙事、建构世界的终极力量。它们作为原始样态对当前的存在、意义和叙事构成阐释系统,提供意义。若此,叙事不是孤立的——过去、现在和未来构成了一个统一体,一个不断生成的系统;生命也不是孤立的,因为生命与世界背后的终极参照取得联系,而生存只有在世界的参照中才能获得意义。若此,叙事成为对古老生命、古老意义的重复。《中庸》对《诗经》的不断重复无疑是这种世界观念的模仿和再现。在这样“回环往复”的世界中,存在延续了古老的生命传统,延续了世界本身。而且,这个获得意义的过程就是对终极纯粹形式的重复性动作,是生命的出现和生命的绵延。同时,这种世界观念和存在观念又时刻坐落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大背景之中。这个大的文化背景为《中庸》文本提供了天人合一、天地人同体同源的宇宙观和生命观。在漫长的华夏历史中,这种观念演化为多种表现形式,而《中庸》在叙事形式上对《诗经》的运用就是中国古人大文化思想与生命观念的表现。《中庸》的叙事表现串联起了生命的碎片,呈现了生命连续统的生命景观,而这个景观之于现代之后不断碎裂的现代生命景观无疑是一种提示和反衬。
注释:
①Julia Kristeva. The Kristeva Reader[M].Oxford:blackwell publishers Ltd.,1986:36.
②[瑞士]卡尔·荣格等著:《人类及其象征》,张举文、荣文库译,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48页。
③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2页。
④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4页。
⑤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37页。
⑥钟嵘著,周振甫译注:《诗品译注》,中华书局1998年版,第41页。
⑦《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4页。
⑧《说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版,第644页。
⑨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0页。
⑩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61页。
⑪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71页。
⑫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19页。
⑬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97页。
⑭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202页。
⑮朱熹:《四书集注》,岳麓书社2004年版,第128页。
⑯司马迁:《史记》,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 年版,第1515页。
⑰黄霖、蒋凡主编:《中国历代文论选新编》,上海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第23页。
⑱孔颖达:《毛诗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3页。
⑲[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6页。
⑳[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7—29页。
㉑[美]沃尔特·翁:《口语文化与书面文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29页。
㉒[美]尼尔波兹曼:《娱乐至死》,章艳译,中信出版社2016年版,第2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