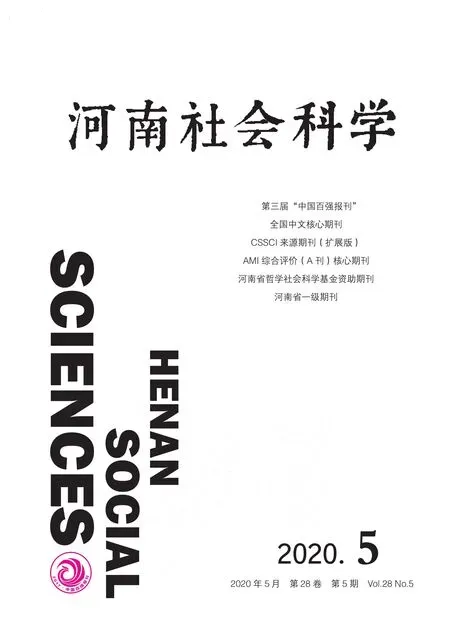原始-神话思维的元思维性
——以中原盘古神话为例
雷 娜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神话之所以是民族文化的瑰宝,不仅在于其绚丽的想象、朴实的文字等文学价值,更为重要的是神话是原始初民以朴素而神秘的主观精神观察外在世界的语言表达形式,由此而积淀形成的民族文化基因影响深远。卡西尔说:“一个民族的神话不是由它的历史确定的,相反它的历史是由它的神话决定的——或不如说,一个民族的神话并不决定而是这个民族从一开始就注定了的命运。印度、希腊等民族的全部历史都暗含于他们的神明中。因而,个人如同整个人类,没有自由的选择权使他们能够取舍既定的神话观念。”[1]6
一、原始思维与盘古神话
列维-布留尔通过研究神话和人类学家在非洲地中海沿岸等地对原始居民的考察资料,并吸收借鉴泰勒的“万物有灵论”,认真思考神话与原始思维的联系,他得出了如下结论:在原始思维中没有纯客体的东西,一切事物连同它周遭的环境、气候等都具有神秘性,最后作为神秘性的整体存在,“客体和存在物的神秘属性构成了那个在任何场所与时刻都显示出复杂整体的原始人的表象的组成部分”[2]40。所以原始思维中不存在主客体差别,没有物质与精神的对立,更没有物与物之间的区分,甚至我们逻辑思维下所认为的时空观也是不存在的。这种元逻辑思维是同时在集体中思维个体、在个体中思维集体;在主观中包含了主体、客体还有主观本身,即人、物、心统一的综合性思维。在列维-布留尔看来,这种互渗是灵魂与灵魂的对话,是各种力场之间的交融与作用,这种互渗不仅将神秘的力场赋予每个客观实在物,也赋予在彼此之间的复杂作用和关系之中。
盘古神话是中华民族的起源神话,包含着祖先对宇宙之始和万物起源的思考,在久远的历史长河中经由一代代人民的口头和文学传承,出现了盘古神话的各种异文,呈现出一定程度上区域性和文化性的差异。因此通过历史文献考证和口头田野考察的方式确定盘古神话的原型是盘古神话研究必不可少的一步。张振犁教授经过多年广泛的文献考证和田野考察,认为中原盘古神话不仅属于中原古典神话,而且因其与洪水神话、英雄神话等神话的关联在中原地区拥有现实的历史和地理基础,很可能是盘古神话的原型。因此对中原盘古神话的研究有助于发现人类思维发展早期的特点。借鉴列维-布留尔对原始-神话思维的研究成果,本文试图对中原盘古神话中的原始思维进行研究,随之发现中原盘古神话包含的神秘因果联系、大胆的空间想象以及持续的转生观念,这些呈现都体现出元思维性所具有的互渗性、整体性、直观性、形象性的特征。另外,中原盘古神话因其独特的地域性也体现了中原文化独有的魅力,从另一侧面也证实了中原盘古神话存在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
二、盘古神话的母题及中原盘古神话的元思维
由田野考察而构建出来的中原盘古神话原型看,中原盘古神话不是单一的神话,而是有众多地理基础的神话群,而且与古籍中的盘古神话母题比较,就会发现其独有的中原文化特色。
(一)盘古蛋中生——因果联系的神秘性
“盘古没有爹,没有娘。他从混沌的气团里孕育成人”和“天地混沌如鸡子,盘古生其中”这些神话母题都表明盘古从天地之间出生,显然这些母题试图通过人的孕育和生长过程解释宇宙起源。人产生之前的宇宙无人可知,但人产生后对宇宙起源的推测难免与人类个体的孕育相类比。尽管神话语言是一种隐喻性表达,无法用现在的逻辑进行解释,但是从原始初民对孕育的认识过程中,仍然可以看到他们对宇宙起源的推测。盘古没有爹娘反而从混沌中孕育而生,也许在现今的逻辑思维中很难被认可,但在原始思维中这是自然的,因为在原始思维看来,人的出生并非以受孕为唯一条件,因为逻辑思维中的矛盾关系在原始初民的思维里不是单一线性存在的,而是综合整体性存在。他们关心的是事物及其周围环境的神秘性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神秘性,即它们力场之间的相互复杂作用。这种作用无法看到却不断被感知,故而原始初民认为夫妻生活并不是造人的唯一决定性因素。正因为此,盘古从混沌中出生的母题,除了形象化地表达阴阳之动外,主要体现事物与其存于其中的环境之间的神秘性。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初民对最明显的直接的因果关系不感兴趣,比如对受孕一事,原始初民对夫妻生活导致受孕这样的因果关系并不重视,却十分擅长利用这些关系来得到必需的东西[2]486。其实,原始初民对因果关系并非不重视,只是他们感觉到明显的因果关系以外应该还有其他因素,他们注意的往往是神秘性的关联和作用。这种神秘性是事物及周围环境间神秘性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应该是复杂的、多元的、网状的因果联系。因为每一个行为、念头都会产生影响,加之它们的相互作用,就会产生结果。所以有因必有果,这种因果关系是基于事物或观念产生后的影响而言的,该影响包括宏观的、微观的以及心理的影响,所以从该角度而言因果关系是一种宇宙法则。
对于某些显性的影响,人类可以用自己的感官发现,而隐性的影响往往也能被综合性思维方式的原始初民所感觉到,但是他们却无法用显性的语言形式来表达,所以这种神秘性就是那种隐性因素的表现形式,明显的因果关系只是复杂的、多元的、网状的因果联系的一个方面。在他们看来夫妻生活不是主要因素,受孕是需要神秘力量参与的,特别是在非洲的某些原始部落,妇女不会到坟墓周围去,她们觉得坟墓周围的神秘因素会进入体内使之受孕;相反,不能受孕的女子也会被丈夫赶走,他们认为致使不孕的神秘力量会使家畜不受孕以及植物不结果,所以这种神秘的力量很重要。根据生理学的有关知识,人在受孕时,除了精子和卵子的结合外,精子和卵子的质量、子宫的条件、各种孕酮激素等因素也很重要,还有很多目前科学还不能确定的偶然因素等都对受孕产生影响,而这些因素之间的因果联系并非显性的,甚至是多重网状的联系造成了孕育过程的模糊而又必然。所以这些现代科学所无法确定的偶然的、未知的各种因素就是列维-布留尔所说的原始初民所想象的神秘力量,而这种神秘力量之间包含着必然的因果联系。
对于盘古来说,没有父母却能出生,这种情景就是原始初民对复杂因果超时空的直觉认识,所以张振犁教授认为“《三五历纪》和《五运历年纪》里关于盘古开辟神话的记录,都是具有代表性的,因此研究我国古代‘宇宙神话’中的原人哲学思想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而且原人哲学观点不过是寓于神话形象之中内涵的原始思维的意识形态而已”[3]32。从中可以看出神话形象,即神话思维的形象化是原始思维的艺术表达,它使得很多规律在形象化的基础上得以表述,而这种表达在现代思维看来好像天方夜谭,显得格格不入。实际上,原始思维感知到了因果联系的复杂性和全面性,感知到了以神秘性为基础并通过互渗律表现出来的呈网状的错综复杂的因果关系。所以在原始初民那里就变成了纯粹的直觉,以至于对所感知事物作出的行动如此迅速几乎是在瞬息之际。原始思维对神秘因果联系的感知是一种综合性的思维方式,有别于主客分离之后二元对立的逻辑思维,所以呈现出了元思维的特性。
(二)盘古开天辟地——关于空间的整体想象
盘古开天后,气之轻清者上升为天;气之重浊者下降为地。
盘古坐起来,天地之间的缝隙太小,挤得厉害,于是就用手撑天,脚蹬地,终于站起来。以后,身子每天长一丈,天地也离开一丈。过了一万八千年,盘古成了高九万里的巨人。天地被他撑开了九万里。后人演变为“九重天”。[4]41-42
盘古在混沌里生活一万八千年后,胳膊一伸、腿一蹬,一万八千年的混沌就打开了,往上飘的变成天,往下沉的变成地,手撑天、脚蹬地又过了一万八千年,身高九万里,天也随之升高九万里,所以就有了九重天之说。通过对人类生长的夸张想象来类比宇宙的生长。《淮南子·齐俗训》云:“往古来今谓之宙,四方上下谓之宇。”[5]209所以盘古开天辟地的母题正是原始初民对宇宙无始的时间维度和无穷的空间维度的形象表达。
在原始初民那里,每个方位都有神秘性。狩猎者要到哪个方向,就要向哪个方向祭拜祈求保佑,在每个方位都广布遍及使人和物有灵性的力场。盘古能高达九万里,这是逻辑思维根本无法想象的事情,如果片面地认为这只是神话的夸张手法和绚丽联想,那就无法走进原始初民的生活世界中。列维-布留尔认为,原始思维从来不拥有彼此孤立的观念,这些观念一开始就包括在复杂的表象中,这些表象具有集体和宗教的性质。神秘的因果联系遮盖了我们称之为实在的因素,当神秘的互渗不再被感觉到,则只能到处保留此物与他物之间的联想,好像是那些互渗留下来的残渣,实际上这仅仅是联想而已,因为它们结合在一起的内部联系或者说互渗消失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逻辑思维无法感受到的关于空间的想象,逻辑思维只看到情节而没有看到每个方位的神秘实在性,换一种说法,就是逻辑思维无法感受到原始思维的整体性、神秘性,这种整体的神秘性是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之前的统一融合状态,它融合了人、物、心以及它们之间相互作用的复杂关系。所以原始-神话思维所呈现出来的并非纯粹的纯客体的空间,而是主体意识中的空间感知和想象,就像《淮南子·天文训》中所载:“孔窍肢体皆通于天。天有九重,人亦有九窍。天有四时以制十二月,人亦有四肢以使十二节。”[5]165天是人意识中的空间,人亦是与天地相通的存在。《淮南子·本经训》又云:“天地宇宙,一人之身也;六合之内,一人之制也。”[5]344所以,主体与客体并非如逻辑思维认为的那样截然割裂,而是相互依存、如影随形。盘古开天辟地的母题就是原始思维下原始初民对宇宙空间的直觉性认识而形成的形象性表达,由此可以看出原始思维具有的前逻辑性,从而展现了原始思维的元思维的特征。
盘古打开的九重天,不是想象的词语,它其实包含了外在的全部空间,具有哲学意义上的客观实在性。张振犁教授在论述盘古神话时,分析了盘古神话中所蕴含的现实基础,指出盘古神话与桐柏山系、太行山系在地理上的关联。就像汉朝扬雄的《太玄经》中也有九重天,而每一重天都有名称,都指代一种生存的空间。在中原盘古神话研究中,“盘古开天辟地的地点落实在黄河流域的太行山一带”[3]32。所以,这不仅证实了原始思维的科学性,而且也证实了中原盘古神话作为宇宙起源神话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而开天辟地的过程也象征了盘古与原来混为一体的外在世界发生分离。因为原始思维包含着个体与社会集体之间,以及社会集体与周围集体之间的可感觉、可体验的互渗,二者彼此联系,一者发生变化,另一者也会发生变化,原来共生的情况不会完整。所以,盘古的长大与九天的生成是个体与环境分离的象征,这种分离并非绝对,因为这种万物之间神秘的互渗仍然像空气一样存在。
(三)盘古垂死化生——直观的转生观念
盘古死后,他的左眼变为太阳,为大地送温暖,右眼变为月亮,给大地照明。他睁眼时,月亮是圆的;他眨眼时,月亮成了月牙。头发、胡子变成了星星,伴着月亮走,跟着月亮行。呼气变成春风、云雾,使万物生长。声音变成雷电。肌肉变成土地,筋骨变成道路。手足四肢变高山峻岭,骨牙变金银铜铁、玉石宝藏。血液变江河,汗水变雨露,汗毛变花草、树木。精灵变人畜、鸟兽、虫鱼。从此,天地间有了世界。[4]42
在逻辑思维中,生命的终结就意味着一切的消失,而原始思维中的生命是循环的,死亡并非终结。列维-布留尔认为,在原始思维中,死并非外在客观因素导致的,致死的真正原因是那些神秘力量的作用,而在此之下任何手段都是可以的[2]412。原始人被野兽咬伤,在原始思维看来,野兽并非致人死亡的主因,而是在神秘力量的作用下,野兽不得已的选择,如果在没有野兽,其他手段同样会使原始人死亡,比如遭雷击、遭石头砸中。所以盘古并非被累死,他有开天辟地的能力,怎么能没有抵抗死亡的力量?只是通过这种神秘的力量,盘古实现自我转化,这种神秘的力场之间实现了彻底的互渗。
关于盘古垂死化生的母题,陈建宪教授从社会根源—日常经验出发,认为化生反映了原始人祭仪式,“既然自然物也是人,而人类也有生老病死,因此,在自然界出现反常现象(如大旱、洪水、久阴不雨等)时,原始人就认为自然可能像人一样,也会生病、衰老、死亡,因此必须不断地为它补充生命力,甚至必须以新的神去取代老的旧神,为了将人转化成神,初民必然要举行隆重的原始宗教仪式,这种仪式就是人祭”[6]92-98。如果从原始思维出发,原始人因为觉知到了表象底下深层次的神秘因素及复杂的因果关系,但是受这种整体性约束的思维并不能将其表现为线性的语言形式,却可以用直觉感知进而用形象的比拟表达出来,所以说这种本原上的原始神话思维具有科学性、实在性。
而人祭仪式只是原始思维觉知复杂实在性后,无力面对和处理而导致的行为选择。就像对于某些自然灾害,他们感觉到了是因为天气原因或者其他因素,至于到底是什么因素他们说不清楚,但他们选择了人祭的形式,这或许只是一种对自己直觉的印证,是原始思维在蒙昧情况下的一种运用形式。而人祭仪式也只是出现在某一特定历史阶段的社会意识形态中,所以用人祭仪式这样具体的社会经验来反映综合的原始思维,还是落入了用局部来证明整体的窠臼中,不免有片面之嫌。
“在这种前逻辑思维的作用下,各种客体存在物、现象能够以我们不可思议的方式同时是它们自身,又是其它什么东西,它们差不多同样以不可思议的方式发出和接受那些在它们之外被感觉的继续留在它们里面的神秘力量、能力、性质、作用,这也就是所谓的互渗律。”[2]79通过神秘的互渗,盘古垂死化生后还是自身,但却是另外的形式,而且神秘的力量以及作用仍然存在。从能量守恒的角度看,人、物、心以及它们之间的相互作用构成了统一的力场,当彼此之间出现此消时,必然面临彼长,因此当盘古作为统一的个体行将消亡时,必然会出现多个其他形式的存在。《淮南子·天文训》云:“是故‘一’之理,施四海;‘一’之解,际天地。其全也,纯兮若朴;其散也,混兮若浊。”[5]26因此,盘古垂死化生母题不仅解释了天体的起源,而且解释了万物的起源问题。这种观点超越了神创论,反映了基于一定条件下能量转化的客观现实,具有一定的客观实在性。同时也是原始思维对包括天地万物在内的转生观念的直观性表达。
(四)中原盘古神话的文化印记
通过以上对中原盘古神话的主要母题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原始神话思维关注复杂因果关系的神秘性、空间想象的整体性以及转生观念的直观性。相对于现代的逻辑思维,这些特征使原始神话思维呈现出了元思维性。因为“原始思维的形象性,人类初期,思维能力还不能了解从具体的事物矛盾中去抽取其中的理性规律,就是说还不善于利用理性知识,理性原理去认识事物,只能通过感性,通过形象去认识事物”[7]74。由此可见,原始思维中其实是包含理性规律以及感性认识的。原始思维的元思维性就体现在对主客观世界的综合性、复杂性、有序性的比拟和形象表达上。而且从中原盘古神话群中,我们可以看到中原文化的印记。
后人在这里建寺庙纪念盘古的功绩。
这里古代就建有盘古寺(后讹为“盘谷寺”)。有民歌说:“阴阳五行来聚化,盘古怀在地中央。”
盘古蹬破的宇宙蛋壳,被太行山压在下面,成了今天驰名全国的砚台石质层“盘砚”的最佳石质层。
至于桐柏山系的盘古神话,则是一巨神盘古用斧劈开气团(或大气包),落下一块成了大地。此外,还有不少材料说明:盘古开辟神话与洪水后兄妹婚神话融合后,还有一系列的文化创造神话。[3]35
除了盘古神话的核心母题,从以上的内容中我们还可以看到中原盘古神话中独有的地域文化特色。而且“随着历史的发展,显示出伴随历史进程而出现的丰富和变异现象,具有宗教化、历史化(尽管不明显)、现实(世俗)化的多层痕迹。它不是已经停止发展的化石,而是至今还在人民群众中产生着深远影响的活的民间神话”[3]37。中原盘古神话中盘谷寺的出现具有宗教化色彩,充分体现了先民的祖先崇拜;而其与民歌、风物传说(盘砚)的世俗化结合则表达了先民通过民俗和风物对自我文化身份的认同和不断肯定;与洪水神话的融合则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包容性。
三、中原盘古神话研究的当代价值
从中原盘古神话中体现出的原始思维,我们可以看到它对主客观世界的综合性、神秘性、复杂性、有序性的深刻把握,这种思维方式也是中华传统文化所根植的思维方式。尽管在思维发展演变的久远历程中,思维的分化和独立是一种生存的必然,但中国传统文化思维在理性思维和感性思维的分化中,比较缓和,或者更多地倾向于原始思维中的整体性,所以在艺术、绘画、音乐等诸多领域还具有浓重的“混沌整体观”,就如邓启耀所说:“中华民族传统思维方式在走过前综合思维必然要走的那段路(未分化)以后,似乎并没有真正实现一般期望的‘分化’。与分化比较明显的,以重分析推理和抽象逻辑的西方思维方式相比,我们民族似乎沿袭并发挥了前综合思维的更多特点。”[8]242而西方自从笛卡尔工具理性提出以来,特别是在当今社会,逻辑思维在科技主导下将主体与客体严重剥离,甚至主体也成了客体的工具,这种科技至上的思维方式将主体的尊严打倒在地,最终也将毁灭自己。所以从某种意义上说,逻辑思维是狭隘的、脆弱的,逻辑思维通过概念、逻辑、判断构建客体世界,但作为其基础的概念必须具有易变性、流动性,也就是德里达所说的延异。延异的存在打破了逻辑思维的僵化状态,并非揭示了思维的发展历程,原始思维的发现渐渐展现了思维的发展历程。它的发现并不要求思维方式的绝对逆转,但是作为前逻辑思维,它已经构成人类世代传承的基因,在我们的生命里涌动,我们要做的不是回避,也不是绝对的复辟。只是我们在以概念、逻辑、判断为支撑的逻辑思维的大道上不要忘记血液中涌动的各种神秘东西。而原始思维不仅流淌在我们的血液中,其实还保存在我们的神话中。而不断体味这些神话就是让我们重温原始思维的方法,特别是古老而鲜活的中原盘古神话群保存了我们民族的文化基因和历史根脉,因此对其进行深入的研究和广泛的讲述可以不断唤醒我们固有的原始思维,进而滋养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使其在包括人文艺术在内的各个领域展现独有的东方魅力。
中原盘古神话是原始-神话思维下对天地万物起源、存在、转生问题的形象化表达,同时反映了中原古老的文化风貌。约瑟夫·坎贝尔认为:“人类行为有意识模式背后的潜意识欲望、恐惧和焦虑似乎通过神奇的故事——它们假装描述的是传奇英雄的生活、大自然之神的威力、死者的鬼魂和群体的图腾原型,进而得以象征的手法表达。”[9]2从中原盘古神话群中可以看到盘古已经演变成祖先神被祭祀,充分体现了中原先民在面对困惑时的精神诉求。而盘古神话在中华大地上的广泛流传决定了盘古作为祖先神被华夏子孙所膜拜,“盘古创世祖先神话所描绘的想象中的地理空间,作为一种信仰,已经沉淀为中华民族儿女的集体意识,盘古及其开创的天地已成为人们精神寄托之所,或曰精神家园”[10]79-84。因此,中原盘古神话的研究和讲述有利于凝聚亿万中华儿女的民族情感。
中原盘古神话在流传过程中不断与民歌和风物传说(盘砚)结合成为活态的民间神话,至今仍有传唱和讲述的社会生活基础:一方面有利于中原盘古神话的进一步讲述和传播;另一方面通过实在物的方式将民族文化的记忆保存下来,有利于不断加强自我文化身份认同,使我们在与他者文化交流时能够产生强烈的文化自信。同时古典神话的民间化也启发我们在全球化日益加剧的今天,通过寻找神话传播、讲述、记忆的多种媒介方式,提高盘古神话在现代社会的影响从而保持神话的永久生命力。
中原盘古神话群与洪水神话的融合则体现了中原文化的包容性。洪水神话是具有普遍意义的世界性神话母题,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许多民族中都有广泛流布。中原文化因其历史地理的优势能够开放地、包容地吸收和借鉴其他各种文化,并在此基础上不断融合,从而在交流中增加了中原文化本身的丰富性。所以中原盘古神话群的发现启发我们在当今与外来文化交流的过程中,首先在保持本民族文化认同的前提下,尊重他者文化,以开放包容的姿态面对文化多样性,因为在“多元杂交的文化时代需要一种多元杂交的文化诗学。在我看来,这个文化诗学的核心应当是研究跨文化交流中对民族文化记忆的发掘、阐释和转译问题。它既是一种福柯式的‘知识考古学’,又是一种具有当代性、实践性和应用性的文化哲学,对于更好地适应全球化时代的多元和杂交文化,推进新世纪的民族文化建设,将起到积极的作用”[11]11-16。
中原盘古神话中的核心母题盘古蛋中生的过程揭示了万物之间复杂多元的神秘因果联系,而盘古开天辟地体现了主体和客体相互依存下的主体意识中的空间感知和空间想象,盘古垂死化生则表达了万物转生的内在规律,因此中原盘古神话是原始—神话思维的智慧结晶,从中原盘古神话中我们可以看到这种思维方式的元思维性。因此研究和讲述盘古神话对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承和创新具有积极意义,而积极发现和挖掘中原盘古神话群的独有文化价值对于凝聚民族情感、增强文化自信、加强文化身份认同以及推进全球化语境下文化的交流和融合都具有历史和现实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