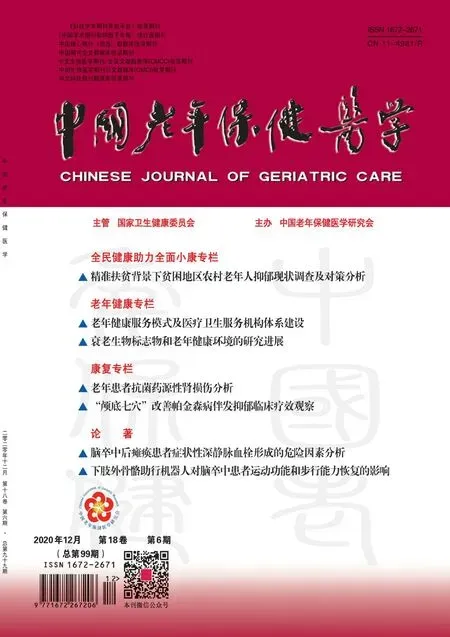老年人长期照护的国内外现状和对策研究
刘晓梅 杨 泽 庞国防 吕 渊 胡才友※
国际老龄化社会的标准为:60岁以上的人口占总人口比例达到或超过10%,或65岁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达到或超过7%。目前,中国是世界唯一老年人口过亿的国家。根据全国老龄办公布,2020年我国老年人口将达到2.48亿,老年人占比达17%,成为超老型国家。同时全国失能老人占比日趋增加:2012年3600万人,2013年3750万人,截至2015年约4063万人,占老年人口的18.3%[1]。建立适合中国国情的长期照护服务体系是当务之急。
1.长期照护
世界卫生组织将长期照护定义为由未接受相关培训的照护人员(家人、朋友等)与接受相关培训的护理员为保障失能或痴呆人群提供生活、心理等照顾活动体系,使失能或痴呆人群获得较高的生活质量,享受独立、自主、个人满足及人格尊严[2]。在人口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口的失能或半失能问题凸显,长期照护体系的作用更是日趋重要,长期照护体系提供必要的环境支持和照护,确保存在严重失能的老年人能够实现健康老化。
长期照护系统可以维护老年人的功能发挥,以符合他们的基本权利、基本自由和人权,确保老年人的内在能力拥有最优发挥,并且能够有尊严地完成实现其福祉所需的基本任务[3]。例如,早期保健可减少能力衰退,包括家属鼓励并帮助老人变得更加积极并且进餐合理;晚期保健可支持老人完成基本任务,如洗衣做饭,但这应该与卫生系统充分整合以保证能力得以优化。老年人居住于有利环境(例如家中轮椅可以通行、痴呆关爱社区)中,可以使这些任务变得更加简单。
全球范围内,如果要持续满足老年人不断增长的需求,必须加速发展长期照护服务。各国的转变需要多部门的协调应对,需要政府内外的广大领域内各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更重要的是,必须彻底颠覆头脑中对长期照护内容的固有观念,需建立有关长期照护的全新思维方式及服务系统。由于缺乏重要的政策再定位过程,很多国家在满足这一需求方面会落得更远。正规的长期照护服务将持续短缺,在提供服务的地方过时的居住照护模式很可能延续。依赖照护的老年人将继续成为容易遭受虐待的脆弱人群。长期照护和主流卫生保健服务将保持互不连接的状态[4]。
2.长期照护观念
长期照护系统的充分整合、建设是所有国家应对人口老龄化的深入发展的迫切需要,同时还应树立和推行长期照护的新思维方式,将长期照护融入优化其健康老化轨迹的努力当中,将核心目标转变为使失能者实现其功能的最大化发挥[5]。
照护依赖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对于无论处于何种经济发展水平的国家,人口老龄化都将大幅增加需要社会服务人员的数量和百分比,而能够提供这种照护的年轻人的比例却可能下降。尽管目前为止女性都扮演主要照护提供者的角色,但是这一情况也正在发生改变[6]。
2015年世界卫生组织《关于老龄化与健康的全球报告》中构建长期照护系统的路径和条件:①长期照护系统条件或基础的构建:明确意识形态,实施行动计划和建立筹资机制三个方面。②长期照护专业队伍的构建:专业人员队伍培育;工作待遇、条件和职业发展的保障;家庭照护者的支持,社区照护的建设。③长期照护的服务质量监管:服务标准和人员认证机制建立,建立质量管理系统,长期照护与卫生保健服务的协同工作机制的建立等。其中,长期照护服务专业人员培训及监管是构建长期照护系统的主要环节[7]。
3.长期照护系统管理国际现状
1987年日本颁布《社会福祉士及介护福祉士法》,日本厚生劳动省(负责医疗卫生和社会社会保障)1989年开始在全国范围内每年一次统一举办社会福祉士考试和介护福祉士考试。该法的颁布及执行为日本培养、储备了大批专业的家庭养老护理员[8]。
1987年美国颁布“综合预算调节法规”(Omnibus Budget Reconciliation Act,OBRA),明确规定长期护理机构的设置和管理要求、质量标准,以规范长期护理机构的管理和运作。该法规要求在长期护理机构中工作的人员的专业培训教育时间,并必须通过相应的笔试和技能考试,方可注册登记,执业上岗[9]。
英国护理与助产学会制定了针对家庭护理的一系列指南,规范家访护士的日常护理工作具有指导和规范作用,其中包括长期照护服务规范[10]。
针对长期照护德国制定多部与护理保障相关的法律,如《护理继续发展法》《护理假期法》《家庭护理假期法》《护理调整法》《家庭、护理与职业协调改善法》《护理加强法(一、二、三)》《预防法》《临终关怀法》等,确保提供高质量护理服务,使得有护理需求的老人能够继续自主生活,保证从事家庭护理的家人能够得到适当的支持[10]。
中国台湾长期照护服务提供机构由多个行政部门协同完成,如公共卫生部门的长期照护管理中心、内政主管部门的居家服务中心、少数民族委员会的家庭妇女服务中心、农业委员会的农村小区生活支持中心、荣民委员会的荣民服务处等[11]。
4.国内长期照护系统管理情况
我国的长期照护服务近年来发展迅速,发展过程有四个阶段:第一阶段是计划经济时期供养五保户的养老服务为主阶段;第二阶段是家庭和社会相结合的机构化发展阶段;第三阶段是居家为主、社区为依托的长期照护政策阶段;第四阶段是以构建体系为目标的长期照护服务政策的阶段。完善长期照护服务专业人员培训及监管政策是构建长期照护系统中的一个重要部分[12]。
4.1 长期照护服务国家职业技能标准 2019年10月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与民政部联合发布《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2020年9月16日国家医保局、财政部联合发布《关于扩大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试点的制度意见》,是我国政府应对社会人口老龄化、健全社会保障体系作出的主要部署。
4.2 长期照护服务相关地方标准 经查阅全国标准信息公共服务平台,可查询到以下地方标准:《家庭服务养老护理员服务质量要求与等级划分》(DB45/T 1272-2015,主管部门为广西壮族自治区质量技术监督局),《养老护理员等级规定及服务规范》(DB41/T 595-2009,主管部门为河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养老护理员培训规范》(DB22/T 2402-2015,主管部门为吉林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养老护理员培训规范》(DB33/T 2001-2016,主管部门为浙江省质量技术监督局),《养老护理员培训要求》(DB14/T 1901-2019,由山西省民政标准化技术委员会归口上报,主管部门为山西省市场监督管理局),《养老护理员服务质量要求》(DB1501/T 0007-2020,主管部门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养老护理员培训规范》(DB1501/T 0006-2020,主管部门为呼和浩特市市场监督管理局)[13]。
5.我国长期照护服务系统完善对策
5.1 长期照护职业标准的完善 我国长期照护服务目前现行的国内相关标准全部归口于民政部门,规定的相应内容也仅限于对老年人进行生活服务,如助餐、助洁、助浴、协助移动等,未包含老年人所必需的社区和家庭医疗护理需求,形成了标准空白区。而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民政部颁布实施《养老护理员国家职业技能标准(2019年版)》重要的不足在于,首先是缺少护理专业内容的内核,原本护理专业的内核实质上应是在上级医者指导下辅助完成对身心有疾患者有特定医疗内容的照料;其次是该文件没有指出高级职称的护理员依然是护理员,按《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分类大典(2015年版)》定义护理员作为医疗、护理辅助服务相关工作的人员的规定,其工作内容依然是辅助医护、公共卫生相关的社区医疗专业人员,而不是取代[14]。因为,国际上护理学是个统一的专业,不能够割裂,护理员直接的上级,逻辑上讲就是护士,护士的上级就是医生,不能越级替代。第三,护理员的职业属性不清,护理员职业是伴随医疗行业诞生和发展壮大的,其本质是医疗行业的一个分支,是与医疗行业最相关的职业,其职业中的医疗属性是不能忽略的,所以尊重和还原护理职业的医疗属性,准确定位其工作职责十分重要。
5.2 长期照护服务制度的建设 老年人长期照护是专业性极强的社会保障体系,建立体系完备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标准体系应由国家、政府主导。国家在对老年人长期照护提供财政支持的同时,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监管制度是长期照护服务良性发展的保障。
日本长期照护体系建设较为完善,于1987年、1992年分别颁布《社会福利士及看护福利士法》和《福利人才保障法》,明确规定老年人长期照护服务机构从业人员的上岗资质、业务技能标准要求[15]。中国台湾长期照护服务的提供模式主要分为机构式、居家式和社区式[16]。我国老年人长期照护主要实施于家庭和社区,机构为辅助。加强建立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监督制度,既要对机构、社区的老年人长期照护质量进行监督,也要对家庭老年人长期照护质量实时监管,促使照护人员接受培训并提高照护水平,必要时取消其照护权[17]。护理员职业是医疗行业的一个分支,是与医疗行业最相关的职业,因此长期照护人员培训、照护质量监管应隶属于医疗卫生部门,或与医疗卫生部门紧密结合。
总之,我国社会老龄化趋势日益严峻,只有建立覆盖所有老年人的完善的老年人长期照护法律法规、制度[18],实现失能与半失能老年人长期照护的社会化,减轻家庭的负担,才能从根本上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及老年幸福感。构建完善的老年人长期照护体系是创建和谐老龄化社会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