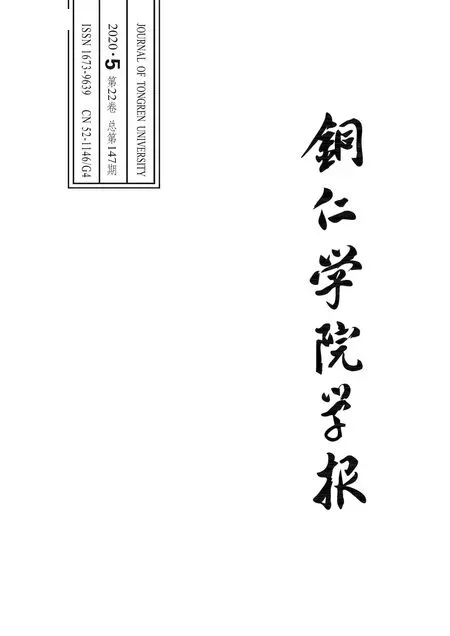颜延之《庭诰》与汉魏道教文学思想——以“心性论”为核心
徐东哲,蒋振华
【文学研究】
颜延之《庭诰》与汉魏道教文学思想——以“心性论”为核心
徐东哲1,蒋振华2
(1.山东理工职业学院 马克思主义学院,山东 济宁 272067;2.湖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
一直以来,儒家与佛教为颜延之思想之源头的观点已成为学者之共识,但有关道教对颜延之思想影响的研究却有所忽视。在传统的儒家思想影响论之外另辟蹊径,从道教思想对颜延之文学观念的影响方面入手进行分析,通过对《庭诰》条分缕析地解读,及同汉末道教经典文献《老子想尔注》的对比中,证明《庭诰》中的“心性”文艺理论,乃是颜延之在对汉魏道教文学思想的继承与发展中形成的。其将心性涵养与文学修养相统一的文学认识论、“本之自性”的文学创作论和“心照若镜”的文学批评论,及其倡导的恬淡寡欲、辞简意深的风格论,共同构成了基于汉魏道教思想、独具特色的文学理论体系。
心性; 玄学; 般若学; 道教
南朝宋时的颜延之《庭诰》,其书主旨乃在教授颜氏子孙立身修德、为人处世之道,可谓是颜氏家族现存最早的家训作品。正如颜延之本人所言:
《庭诰》者,施於闺庭之内,谓不远也。吾年居秋方,虑先草木,故遽以未闻,诰尔在庭。[1]55
颜延之将自己的道德观念与处事原则凝结在《庭诰》一书中,以此劝诫家族子弟修身治学,这是其著书的本来宗旨。但其书并非仅有家风家训方面的内容,而是杂糅了颜延之的宗教哲学、政治态度、文学主张等多方面的思想,尤其是在文学思想上《庭诰》之材料尤为丰赡。但究其本源,颜延之尤其重视的是人的心性涵养,其书立论之宗亦是以“心性”思想为理论根基。故其在《庭诰》开篇便点名此义:
今所载咸其素蓄,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1]55
颜延之之所以重视心性修养,主要是由其个人经历与社会思潮两个方面所决定的。个人方面而言,其子颜竣无疑对其造成了很大的影响。颜竣是刘宋位极人臣的重要人物,但其心性狷介,刚愎自用,不仅与同僚间关系恶劣,后来甚至与宋孝武帝之间也产生了隔阂矛盾。颜竣过分的自我膨胀使得颜延之对其命运忧虑不已。颜延之曾当面向颜竣提出批评,告诫他:“骄矜傲慢,其能久乎?”但无奈的是,颜竣对其训诫置若罔闻,依然我行我素,颜延之亦无可奈何。这点在《宋史》中有着清晰的记录:
(颜延之)常语竣曰:“平生不喜见要人,今不幸见汝。”竣起宅,谓曰:“善为之,无令后人笑汝拙也。”[1]57
颜竣的性格缺陷使得颜延之深刻地反思对家族子弟心性修养教育的必要性,这也是他在《庭诰》中不厌其烦地去训诫后人摒弃私欲、克己治心的重要原因。后来果不出颜延之所料,颜竣因“讪讦怨愤”触怒孝武帝,被下狱赐死,颜竣的人生悲剧可以说是颜延之重视心性教育的最好注脚。
从社会思潮方面而言,由于《庭诰》诞生于南朝,故其成书必然要受到南朝社会风气、宗教思想、政治环境等多方面的影响。而刘宋正值玄学与佛教般若学盛行之时,适时般若学中有关“心性”的理论对社会影响尤其深刻,在关于“性”之存灭的大辩论中,颜延之甚至亲自执笔反驳何承天的“性灭论”。由此而言之,颜延之对“心性”之学的造诣是极为深厚的,这点直接决定了他在《庭诰》的撰写中大量地采用了“心性”之学的理论来阐述其思想主张。
值得注意的一点是,《庭诰》中所体现的“心性”思想绝非仅限于般若学的范畴,而是颜延之博采众家之长后,所形成的独特理论体系。一直以来,儒家与佛教为颜延之思想之源头的观点已成为学者之共识,但有关道教对颜延之思想影响的研究却有所忽视。但无可否认的是,《庭诰》中大量的思想材料都证明了汉魏道教思想对颜氏的影响是十分之深的。本文首先对《庭诰》中的“心性”思想材料进行解读,并溯其源流、通其脉络。唯有明了《庭诰》中的道教思想因素后,对其“心性”文学思想的解读方可避免以偏概全。
一、《庭诰》“心性”思想原型解构
通过对《庭诰》的思想分析,可知其思想构成十分复杂,而其“心性”思想之主旨乃是以道教观念为原点而引申出的,饱含道教心性之学的哲理因子。颜延之撰《庭诰》的初衷,便是论治心之术,《庭诰》有云:“今所载或其素蓄,本乎性灵,而致之心用”。虽然儒家对修身养性之道亦多有阐释,但若深入剖析《庭诰》文本,可以发现其所阐发的治心之道与儒家心性之学之间是有所差异的。儒家讲修心之学,强调的是以礼制欲,使人之身心更合乎人情伦理之要求,其道乃人道,而颜延之在《庭诰》中则着重强调人的“灵性”,主张人应恢复到先天所具备的真性,而不以后天人伦束缚本性,渐至扭曲。这一承运顺化的思想主张与道家相一致,可知颜延之所云之“道”正是老子所云之“天道”。天道之运行的至高规律便为“道法自然”,唯有顺应自然,心方归清静,心性如若澄明,即使没有仁义道理约束,人也自然而然地归于朴素本性。颜延之在论“慈孝有悌”之义时,便是以“天道”观念进行阐释的。《庭诰》曰:
身行不足,遗之后人,欲求子孝“必先慈”。将责弟悌务为友。虽孝不待慈,而慈固植孝,悌非期友,而友亦立悌。[1]56
《老子》中即有曰:“六亲不和,有孝慈。”《老子想尔注》释云:“道用时,家家慈孝,皆同相类,慈孝不别。今道不用,人不慈孝,六亲不和,时有一人行慈孝,便共表别之,故言有也。”[2]43颜延之从“天性之道”的观点出发,指出“慈孝友悌”乃是由感情的相互作用所产生的和谐亲情关系,并非是由伦理纲常所引发出的概念,在这对伦理关系中,倘若一方失和,那和谐关系必将整体崩溃。故《庭诰》有云:“夫和之不备,或应以不和;犹信不足焉,必有不信。”[1]55颜延之对人伦关系的认知正是以老子的朴素辩证法为基础来阐释的,而没有从社会人伦关系来着眼。
《庭诰》反映出的道家天道思想,还可以通过其对“心性”的认识中加以理解。颜延之论“性”,包含着浓厚的宗教神秘色彩。虽然其对性出之于心的观点与儒家并无二致,但其却将性视作一种永存不灭的恒定存在,不因人的生死而改变,这一点可谓与儒家思想大相径庭。南朝时,曾有一场关于“性灭”与“性不灭”的重大争论,而颜延之所持之立场正是“性不灭”观。乍看之下,颜氏所云“性不灭”乃为佛教之观点,与魏晋道教大有差别。因为魏晋南朝道教尚重视炼形,未建立起自身的性命双修理论。但通过析研《庭诰》却能发现,颜氏已有意识地调和佛道两教观点,认为两者思想观上其实并无本质差别,他在《庭诰》中申明:
达见同善,通辩异科,一曰言道,二曰论心,三曰校理,言道者本之於天,论心者议之於人。校理者取之於物,从而别之,繇途参陈,要而会之,终致可一。若夫玄神之经,穷明之说,义兼三端,至无二极。但语出梵方,故见猜世学,事起殊伦,故获非恒情。天之赋道,非差胡华,人之禀灵,岂限外内。一以此思,可无臆裁。[1]57
其实在南朝之世虽然佛道之争已呈愈演愈烈之趋势,但主张二教合流的道教人士亦多有之。《中国道教思想史》对其问题有所论证:
在(魏晋)佛道二教相互对立的激烈争论中,仍有调和二教的声音存在。张融、刘法先、孟景翼、陶弘景都为调和论的支持者与倡导者。[3]545
从颜延之《庭诰》此段文字中可以窥见其将二教思想有意识地相统一的思想倾向,尤其对二教主张心性长存的认识更是深感赞同,认为其源出无二,差别无非是修炼方式的不同。但无论是重形修命的道教还是治心养性的佛教,最终都可以达到“性不灭”的至高精神境界。张融在《门论》中亦有与颜延之相同的观点:
道也与佛,逗极无二。寂然无动,致本则同。感而遂同,达亦成异。[4]38
所以在研究颜延之思想时应该认识到,其思想构成并非限于佛道中的一门,更不是简单地各取所长,而是在其本身的“心性不灭”的认识下,将二教视为一个整体。正是在南朝颜延之等通达之士的前识之下,三教一本的思想才逐渐发扬光大,为后来道教内丹学说及心性修养理论的诞生提供了理论基础。
研析《庭诰》有关“心性”理论对佛道思想摄取的源头,亦可以发现道教思想对其影响之深。颜延之在《庭诰》中阐释“心性”之说时,常借佛理研析心性文理。如其有曰:“夫以怨之非为心者,未有达无心救得丧,多见诮耳。”[1]55此处所云之“达无心救得丧”正源出魏晋间佛教思想。
魏晋之世正值般若学昌盛之际,其时佛学研究者围绕心性之有无问题各抒己见,形成了“六家七宗”的法系之别。其中僧肇之般若无知义受到了中土人士的大力推崇。关于僧肇的理论观点,冯友兰的《中国哲学史》中的一段文本阐释得相当透澈:“第三温法师用心无义。心无者,无心于万物,万物未尝无。”[5]55此段论无心之义乃是本之于“有无”这对哲学范畴来谈的。这与魏晋玄学思想命题相一致。般若学在中土发展之初便与玄学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甚至有众多士人将其与玄学视为同源一脉的思想产物。由于佛教思想中诸如“缘起性空”“万法皆空”等诸多思想在初入中国时并没有相应的哲学理念与其互为补充,故而佛教的晦涩义理难以被广大人民所接受,而要进行更为深入的佛理研究便更无从下手。为解决这一问题,魏晋间诸多僧人就将佛理嫁接于当时大为流行的玄学理论上,采用玄学的思想来阐释佛理,这便使得佛教思想更易为士人所理解与掌握。
彼时很多精通佛理的知名僧人也同时为技艺超群的玄学思辨大师,如支道林解释《庄子》,使众人为之叹服就是一个很经典的例子。佛教作为一个专注于精神修炼的教派,更为注重超脱彼岸,而以为此生此世如“梦幻泡影”,皆为虚幻,这一点同追求“与世长存,毕天不朽”的道教有着本质区别。故而后世道教人士会嘲笑佛门弟子,“只知修性不修命,此是修行第一病”。但不应被忽视的是,道教对于心性修炼方面的内容同样十分重视,早在内丹道兴盛之先,道教修行者已将“心性”视为重中之重。
早在先秦时代,道家文献中便已有丰富的“心性”修养理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便是《庄子》,魏晋间诸多佛教学者更是直接摄取了《庄子》“心性”思想来补充完善自己的理论。如《庄子》有云:“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应而不藏,故能胜物而不伤。”[6]285僧肇在其《般若无知论》中便直接吸收了庄子“用心若镜”的观点,其文曰:“是以圣人虚其心而实其照,终日知而未尝知也。故能默耀韬光,虚心玄鉴,闭智塞聪,而独觉冥冥者矣。”[7]153
继承先秦道家思想之正统,张道陵开创道教之初亦十分重视“心性”的重要作用,在《老子想尔注》中多次提到“心”对人一身性命的统摄作用。如其有曰:“不欲视之,比如不见,忽令心动,若动自诫,道去复还,心遂乱之,道去之矣。”[2]47汉代道教文献《太平经》中,亦对“心”之统摄作用有所论述:“天有五气,地有五位。其一气主行,为王者主执正。凡事居人腹中,自名为心。心则五脏之王,神之本根,一身之至也。”[8]187稍晚于《老子想尔注》《太平经》,诞生于魏晋时代的《西升经》,甚至已将修心养性置于养形之上,在其《身心章》即有言曰:“常以虚为身,亦以无为心,此两者同谓之无身之身,无心之心,可谓守神。”[9]50《西升经》所谓之心神守一,再后来则转变为道教修炼理论中举足轻重的一个概念。
魏晋间道教理论中的“心性”修炼之道,其所本仍在《老》《庄》,其功用而在于养生修命,颐养天年,这与般若学借玄学以阐佛理的初衷并不相同。但在玄理与佛学的融汇之中,二者关于“心性”研究课题间的界限已愈加模糊,理念也渐趋一致,这便是佛道二教渐趋合流所不能否定的一个结果,《庭诰》所反映的正是南朝宗教思想进化的一个缩影。
《庭诰》“心性”论与道教思想相关联的另一个重要方面则体现在其养生理念当中。颜延之对于魏晋道教中养生理论之理解是十分深刻的,他在《庭诰》中曾有论述:
为道者盖流出於仙法,故以炼形为上,崇佛者本在于神教,故以治心为先。炼形之家,必就深旷,反飞灵,糇丹石,粒芝精。所以还年却老,延华驻彩,欲使体合烟霞,轨遍天海,此其所长。及伪者为之,则忌灾祟,课粗愿,混士女,乱妖正,此其巨蠹也。[1]57
颜延之此段之描述与魏晋间服食养生的道教修身思路几乎是完全一致,亦反映出南朝道士群体在修炼思想上基本与魏晋时代一脉相承。而其所指出的道教修行中的种种误区也是一针见血,可以说是毫不留情地批判了南朝道教中的邪术陋习,这足以证明颜延之对道教思想研究的深入。其实在《庭诰》中有大量文本都是本之于魏晋以来的道教养生思想来阐释问题的,这一点被以往的研究者所忽略,而仅仅以儒家思想的角度去进行解读,这一点的确有失公允。如《庭诰》对“欲”之论述中谈道:
古人耻以身为溪壑者,屏欲之谓也。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1]55
先秦儒道二家对于“欲”都有论述。《孟子》有云:“养心莫善于寡欲。”《老子》有曰:“见素抱朴,少思寡欲。”但此处颜延之所论之“摒欲”,其出发点乃是从养生之道来谈的。他以为“欲”之为害乃在于其伤性害命而使生命不能长久,这一点与道教神思守一之法高度契合。《老子想尔注》有云:“道教人结精成神,……人之精气满藏中,苦无爱守之者。不肯自然闭心,而揣捝之,即大迷矣。”[2]196可见张道陵认为养生之本即在于要“自然闭心”,使心神稳定。如此方能不害真性,不伤人和。
提及颜延之的养生思想,一人对其影响极为深远,此人便是“竹林七贤”中的嵇康。颜延之对于“竹林七贤”仰慕久矣,但由于其对山涛、王戎后来的显贵有所微辞,所以尝作《五君咏》来咏怀其他五人,在述及嵇康时,颜延之咏曰:
中散不偶世,本自餐霞人。形解验默仙,吐论知凝神。立俗迕流议,寻山洽隐沦。鸾翮有时铩,龙性谁能驯。[10]57
言论间不仅高度赞誉了嵇康高洁傲岸的品行,更是对其养生修性的丰姿羡慕不已。嵇康撰《养生论》阐述其养生理念,可以说形成了自己的一套系统养生理论。颜延之对《养生论》必然是研究透澈的,故其在《庭诰》中专有一节阐释嵇康的养生思想。其论曰:
中散云,所足在内,不由于外。是以称体而食,贫岁愈嗛,量腹而炊,丰家馀食,非粒实息耗,意有盈虚尔。况心得复劣,身获仁富,明白入素,气志如神,虽十旬九饭,不能令饥,业席三属,不能为寒。岂不信然。[1]55
颜延之此处所引嵇康之言,其意就在于论证养生是自身为决定因素,而不应求之于外。之所以要重视自身之因素,其原因便在于“心性”。嵇康《养生论》有云:
故修性以保神,安心以全身,爱憎不栖於情,忧喜不留於意,泊然无感,而体气和平。又呼吸吐纳,服食养身,使形神相亲,表里俱济也。[10]125
嵇康以为形之长存须以神为根基,神灭则形散,而要使神清气正,则必先使心性安定。嵇康这一思想正是从道教思想中直接摄取而来。《老子想尔注》有云:
求长生者,不劳精思求财以养身,不以无功劫君取禄以荣身,不食五味以恣,衣弊履穿,不与俗争,即为后其身也。而目此得仙寿获福。[2]168
不以俗务扰心,而专一求神思守一之道,正是汉魏道教养生之法的精髓。在这一点上,颜延之继承了嵇康与道教养生思想的内核,以求“心性”安定为第一要义,从而奠定了《庭诰》全篇“心性”思想之基调。
二、“凡有知能,预有文论”——“心性”引发的文学认识论
颜延之阐释“心性”思想的材料中,很多内容都直接或间接地映射出其文学理念,他非常注重将个体“心性”涵养与其文学思想相参照,这一点与先秦道家文艺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与儒家“文以载道”的文艺思想不同,道家对文艺之美是尤为重视的。道家向来不将文学仅当作承载“道”的工具,而是将二者合而为一。无论是老子充满诗韵的五千言,还是庄子“无端崖之辞”的梦幻之笔,都是将无形大道与瑰丽文辞浑然天成地融合为一体,使读者在阅读中自然而然地体道悟道,正如庄子所谓“得鱼忘筌,得兔忘蹄,得意忘言”。颜延之亦是在道家文艺思想的感发下得出了“心性”与文理如一的重要观点,从而使道理与文辞水乳交融地共承一脉。对于“心性”与文学之关系,颜延之在承接先秦道家文艺思想的基础上进一步加以诠释,得出了许多新的结论。
谈及文学修为与“心性”之间的联系,颜延之在《庭诰》中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阐述。
首先,便是提出崇高的人格修养可以使人摒却尘俗凡事,拥有超脱世外的心境,而这种修为离不开文学的熏染,即文学对个体人格修养有巨大的促进作用。正如《庭诰》所言:
贫之为病也,不为形色粗黡,或亦神心沮废;岂但交友疏弃,必有家人诮让。非廉深远识者,何能不移其植。[1]56
贫困对人心智的戕害是十分严重的,古谚有曰:“人穷志短,马瘦毛长”。但此并不能一概而论,颜延之认为采用一定的方法便可在贫困中磨练心智。他所提及的“怀古之志”“琴歌之法”,便是借由文学的力量来提升自我的“心性”。怀古之歌,其实在《庭诰》中是有所指明的,其言曰:“诗者古之歌章,然则《雅》《颂》之乐篇全矣,以是后之□诗者,率以歌为名。”[1]57
古典诗歌,尤其是《诗经》,对人的影响作用十分巨大。孔子所云“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正合此意。颜延之沿用了儒家“诗礼修身”的教化传统,尤具有进步意义的是强化了“诗”的文学教育对人“心性”修养的重要作用,这一点十分值得重视。他将“诗”中的怀古之志作为“心性”培养的一种极具效用的手段,发现了文学对培养人超然心境的教育意义,这一点难能可贵。
其次,是文学可以培养“心识”,即逻辑思辨能力。“心识”对培养个体察识事理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庭诰》有曰:“含理之贵,惟神与交,幸有心灵,义无自恶,偶信天德,逝不上惭。”[1]55在颜延之看来,“心性”与“理”是相辅相成的存在,二者实为相互促进、同步发展的一对范畴。人要理解与领悟“理”需以“心性”为依托,而“心性”修养亦离不开“理”的塑造,这也正是其所言“得贵为人,将在含理”的原因。人之所以贵为灵长,就在于“含理”,在于“幸有心灵”。“心”是感知万物之理的重要器官,“心性”正是在人逐步了悟“理”的过程中日趋完善的。那么,如何去用“心”悟“理”,颜延之认为亦应通过文学来实现,这便需要人在哲学思辨上下一番功夫。
魏晋是一个玄谈昌盛的年代,人们在辩论玄学问题的过程中培养出严密的逻辑思维能力,使得“心识”提高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颜延之敏锐地抓住了这一点,发现了辩理活动对“心性”修养有着巨大的促进作用,唯有气质与睿智兼备,方可成就高尚的品性,当然,这也是魏晋士人们的共识。至于如何提升“心识”能力,则又回到了颜延之最初之观点:“凡有知能,预有文论”。[1]55
此言确实非虚。回顾魏晋以来的众多清谈名家,绝大多数都有作品存世,他们正是靠着自己的理论著作作为支撑,才能屹立于辩场而不倒,其如王弼之《老子注》《周易略例》,何晏之《论语注》,郭象之《庄子注》,都成为了后世玄谈名家的理论学习材料。时至颜延之的南齐之世,虽玄谈活动早已不复魏晋之时兴盛,但学者通过立论以相互辩难的学术风气已相当浓厚,不仅齐皇曾召集文士辩论过学术问题,而且参辩人员的身份多种多样,僧、道、士子、官员都有立论参与学术活动。颜延之本人亦立论数篇,较具代表性的便是其对“性”是否可灭的问题与众学者之间的文章辩论。其先后尝撰《释达性论》《驳何承天达性论》等文与何承天反复诘辩,力论“性长存不灭”之观点,这也便是后世闻名的“达性论”之争。兹举此例便可一目了然地发现颜延之对“文论”的热忱,这可证明颜延之认为文学可以促进“心识”发展,提高“心性”修养正是基于自己的个人经验所提出的观点。
再次,文学有提高人认知能力,拓展知识储量,提高人综合修养的功能。若无文学的熏陶与浸染,人的智慧难有突破与升格,由此而言之,文学并非仅仅是一种知识技能,它更是一种手段和方法。习练文论亦非仅限于提升人的文学素养,更在于其能够提升人的能力。在颜延之看来,文学能力的提升向来为青少年所忽视,故其言“此顾少壮之废,尔其戒之。”文学素养的形成是一个厚积薄发、潜移默化的过程,非一朝一夕所习得,即便是要取得“妙悟”,也需要具备相当深厚的文学功底及苦思冥想后方有所获,由此而言之,颜延之认为“心性”修养与文学修养乃是相辅相成的,两者相互促进,共同推动个人品格修为的提高。
文学能力的培养在颜延之看来也有着一定的方法,在《庭诰》中他就特别强调“交流”的重要作用。其言曰:“若不练之庶士,校之群言,通才所归,前辈所与,焉得以成名乎?”[1]55这种交流有着两方面含义。一方面是书籍的广博搜览,可谓之曰“跨时空知识的交流”,即“校之群言”。不仅限于当世之人,更要在群书中与诸子百家、前圣往哲对话,在典章史料中校理析辩,方此时才能打开胸襟,扩展见识,提升自我的文学思辨能力。另一方面,则是人与人之间的学术交流,当然,也未必局限在学术上。颜延之反对一个人的独思异想,“独学而无友,则孤陋而寡闻”。他对儒家这一学习思想的体悟十分透彻,《庭诰》言曰:“若呻吟於墙室之内,喧嚣於党辈之间,窃议以迷寡闻,妲语以敌要说,是短算所出,而非长见所上。”[1]55颜延之批判了封闭式的文学思考方式,并指出文学交流不应拘泥于朋辈小团体之间,而应尽可能拓展自己的文学圈子,与优秀的学者及文人产生思想碰撞。唯有如此才能对社会发展与文学思潮有一个全面的认识,充分提高自己的文艺思维能力与文学认识水平。颜延之同时强调了交流群体的重要性。颜氏极为重视人的周边环境,“芝兰之室,干鱼之厮”便是其至理名言。不良的交流活动只会损害人的思想,虽然魏晋以清谈驰名,但未必善言谈者一定有极高的思想造诣,倘若交流对象不当,其弊端丝毫不亚于独唔一室之内。
三、“心照若镜”——以“心性”为旨的文学批评论
自魏晋以来,中土文士便大量借鉴宗教术语来进行文学评论活动,其中尤以佛教术语居多,如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便引入大量佛教概念来进行文学批评。颜延之在《庭诰》中亦采用此种文学品评方式,借佛教与道教理念来阐释文学问题。而在其文学批评理论中,“心照”这一概念的提出尤为引人注目。《庭诰》有云:
以为灵性密微,可以积理知,洪变恍惚,可以大顺待。照若镜天,肃若窥渊,能以理顺为人者,可与言有神矣。若乃罔其真而眚其弊,是未加心照耳。[1]56
由此不难发现,颜延之认为仅仅凭借感官认知世界是远远不够的,必须要加以“心照”方可了解事物的真谛。“照”字经常为佛学典籍所用,指对世界的圆满无碍的透彻认识,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中便将其引入文学品评中,其言曰:“欲求博观,必先圆照。”[11]218颜延之在人的文学认识活动中,亦高度肯定了“照”的必要性,将“心照”作为人洞悉万物,深察文理的第一要义。
心照之法,概括而言之,便是“以心为镜”,藉个体“心性”为本来分析文学作品。“以心为镜”要求个体能够达到一种绝对无染,透澈澄明的境界,这与刘勰所提出的“虚静”的文学概念乍看之下十分类似,但差异却是十分明显的。这主要在于“虚静”是个体在鉴赏与创作活动的心境体验,而“心照”则要求个体在身心修养中要始终处于清净无染的状态。颜延之认为唯有将内心纯净保持一种恒长状态,方可达到“心照如镜”的艺术审美效果。上文所提及的“用心若镜”正是“心照”之法的直接理论来源。庄子以为,修心达到此境,已至圣人之位阶。这足以见“心镜”修为之难。如果说“虚静”是个体心灵澄澈的基本前提与要素,那么“心照”便是完成心性升格的必由之路。颜延之认为洞察物理之极才可达到的“体神不疑”,唯有通过“心照”方能完成,由此可见,在其眼中“心照”俨然已成为了格物致知的最终奥义。
“心照”尽管是一个充满佛学气息的概念,但正如前文所述,南朝般若学的产生乃是佛教借道家思想嫁接所成的产物,其“心镜”之论更是直接藉《庄子》诸论脱胎换骨而来,所以在《庭诰》中“心照”这一概念的道家思想色彩依然是十分浓厚的。先于《庭诰》的《黄庭内景经》中,对于自身心灵的观照之法便已十分成熟,而研析《庭诰》“心性”之说,亦可发现其对魏晋以来道教修行之中的内观之法有诸多借鉴之处。由此可言,颜延之“心照”的品评概念对道教文艺观念多有吸收。
颜延之首先确立了文学评论中的基本尺度为鉴赏者的“自性”,或谓之曰“本心”。《庭诰》有云:
且以己为度者,无以自通彼量,浑四游而斡五纬,天道弘也。振河海而载山川,地道厚也。一情纪而合流贯,人灵茂也。[1]56
“天”“地”“人”为道教中所谓的“三才”,当人具备绝对“自性”,得万物之道于心时便可遍悉万理。颜延之充分肯定了人在文学认识活动中的主观能动作用,认为当人具备了完善的心识之后,便可使本性澄明无碍,从而能够在分析作品时做到公正客观。颜延之秉持着道家一贯的主张,即认为人生来本性皆是圆满的,并无等级差别。《老子》以为,人从出生之时起便已具有“精气”“元气”,是后天的摧残才使得人不断丧失精元,迷失本性。而这一切的罪魁祸首,便是尘俗中的积习陋弊。颜延之在《庭诰》中反复论述这个问题,他以贫富差距为例,指出贫穷之所以令人“神心沮丧”,便在于“廉嗜之性不同,故畏慕之情或异”的人在世间的境遇本有万殊,故虽初始性情相同,而后天差异极大。倘若有洁身自好之人,心性会被打磨得愈加璀璨。“是以君子道命愈难,识道愈坚”。而更多普通人则会因困顿而生怨恨心、嫉妒心、分别心,渐渐丢失本心,丧失“性灵”。
颜延之谈及尘俗积邪陋弊对个体污染最为严重的方面便在其心识,其言曰:“习之所变亦大矣,岂唯蒸性染身,乃将移智易虑。”[1]55尘俗陋习在改变个体性情的同时,也在改变其思维方式及心理状态,使得人心性昏沉,神思迷乱,而至此人已然连正常的是非分辨能力都不具备,又谈何“用心若镜”地去品鉴文学作品?正因如此,涤除思想杂质,打磨“心镜”,便成为了颜延之“心镜”文学批判思想的主要内容,围绕这一问题,颜延之从以下几方面予以阐述。
品评时“用心若镜”,首要方面便是要将自我心性“反本”。《庭诰》有曰:“世务虽移,前休未远,人之适主,吾将反本。”[1]55“反本”在道家思想中是一个极为重要且内涵丰富的概念,《文子·自然》有曰:“立天下之道,执一以为保,反本无为,虚静无有,忽恍无际,远无所止,视之无形,听之无声,是谓大道之经。”[12]176在魏晋南北朝时代,佛教为阐释心学义理,遂借鉴了“反本”概念,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尝有论述:“盖佛性本有,反本而得。然则见性成佛者,即本性之自然显发也。”[13]87颜延之论述人之反本,首先需摒弃外在干扰,从自身着手。他在《庭诰》中便藉嵇康“所足在内,不由于外”之语言明此意。虽然此句是言养生之道,但这种不依靠外物而凭借自身先天真性的养生思想,同样与颜延之“反本”的文艺观相契合。“所足在内,不由于外”的思想不仅阐明了文艺必须由自身(鉴赏者)态度出发,发乎性灵方可得文章真髓,同时亦强调唯有“涤除玄览”,清空思想杂质,方可正本清源,从正确的观点评点作品,得出客观公允的结论。
颜延之所阐述的“反本”理念,重在研析心性复归本源的方法与途径,其对“本”的认知,从《庭诰》此段文本中亦可察验:
夫内居德本,外夷民誉,……不以所能干众,不以所长议物,渊泰入道,与天为人者,士之上也。[1]55
研读此处文本并不难发现,颜延之在“人之本”的理论认知上与老子的“道德”思想一脉相承,其倡导“泰渊入道,天人合一”的看法也是魏晋道教人士的思想共识。而如何使人返本归元,自性完备,《老子》中亦有论述:“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14]179颜延之对老子的这一论点高度赞同,其《庭诰》有曰:“寻尺之身,而以天地为心;数纪之寿,常以金石为量”。[1]56即以师法天地为治心之本务,而回归至原点,最终追溯为自然之道。
汉代张道陵撰《老子想尔注》,便将“自然”与“道”训为一体,其文曰:“自然,道也。乐清净,希言入清静,合自然,可久也”。[2]197可见若要得“反本”之法,必修清静无为之道,唯静以修身,方能使心复归本性之源。所以在颜延之看来,在文学鉴赏活动中,不仅需要“虚静”的平和心态,更需要一颗清静无为的心灵为先决条件;反而言之,倘若心性不正,充满邪思戾气,那么便会对作品的情思理趣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想要达到“虚静”的冥想心态更是无从谈起。综上所述,颜延之“反本”的观点乃是由道家的“清静无为”的修持法引入文学批评活动所得出的成果。
颜延之在研析“心照若镜”的文学批评方法时,不仅通过“反本”之法来打磨心性,使之澄明无垢,更是进一步提出“德贵有恒,心性勿移”的主张和理念来使“心镜”长亮不竭。《庭诰》有云:
人以有惜为质,非假严刑,有恒为德,不慕厚贵。有惜者以理葬,有恒者与物终,世有位去则情尽,斯无惜矣。又有务谢则心移,斯不恒矣。[1]55
颜延之此段论述阐述了其“有恒为德”的文学批评理念,即在批评活动中应建立一套自己独立的原则与方法,并将其贯彻始终,绝不因外界环境与风气的影响而轻易变化。颜延之在下文中举出文学批评活动中的两种极端思想来比较论证。其言曰:
或见人休事,则勤蕲结纳,及闻否论,则处彰离贰,附会以从风,隐窃以成衅,朝吐面誉,暮行背毁,昔同稽款,今犹叛戾,斯为甚矣。又非唯若此而已,或凭人惠训,藉人成立,与人馀论,依人扬声,曲存禀仰,甘赴尘轨。衰没畏远,忌闻影迹,又蒙蔽其善,毁之无度,心短彼能,私树己拙,自崇恒辈,罔顾高识……[1]55
在这两种极端思想中,一种是过分以自我为中心,刻意打压和诋毁他人作品,故步自封,无法吸收外界的建议和理念。而另一种则恰恰相反,是毫无个人主见地人云亦云,只知亦步亦趋地追随潮流,无条件地接受他人思想观点。这两种思想在文学批评活动中是万万不可取的,是批评主体没有用辩证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所形成的错误认识。
那么,树立一个正确的评价标准成为了解决这一问题的关键所在。颜延之认为,批评主体建立一套基于自我认识的正确文艺观是十分必要的。通过这一基准,批评者能够在坚持自我主观能动性的基础上,不断吸收外界先进的文艺批评理念来填充自己,进而形成一套自己的文艺批评思想体系。在批评者自己的文艺批评思想建立之后,就犹如形成了一面镜子,将客观世界的形象投射成为自我的认知概念。根据颜延之的观点,在以清静无为作为修持方法之后,个体“心性”可摆脱尘俗陋习的熏染,获得澄明圆满的心灵境界,而这种心境正是形成自我独立文艺思想的关键一步。其言曰:
唯夫金真玉粹者,乃能尽而不污尔。故曰:丹可灭而不能使无赤,石可毁而不能使无坚。苟无丹石之性,必慎浸染之由。能以怀道为念,必存从理之心。[1]57
颜延之此处所云之得道者常乐,便在于“心性”坚如磐石,可不受外物役使而“自我丧失”。这种自我觉悟乃是在“丹石之性”的基础上建立的。由此可言,倘若心性蒙蔽,那么建立正确的自我认识,形成自己独立的文学思想体系就无从谈起。
批评个体除了须以“心性”为基础建立自身的文学认知外,广泛吸引外部的优秀文学思想成果也是十分必要的。作为补充,颜延之提出了自己的理论学习方法。《庭诰》有曰:“观书贵要,观要贵博,博而知要,万流可一。”[1]57此言涵盖了两个方面的内容,即广泛阅读与提炼精粹。此二者并无先后之别,是阅读活动中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
同此相似的论述在刘勰《文心雕龙·知音》篇中亦有之:“是以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11]219刘勰在此以比喻的手法阐释了文学批评活动中广泛阅读、大量训练所形成的经验性认知。颜延之则是将此理念抽象为批评理论。结合之前关于“心性”的分析可以推断,颜氏所谓“博而知要”中的“要”,就是个体在鉴赏活动中,通过主观“心性”鉴照后所提炼出的理论观点。这些文艺观点,从某种意义上讲已从原著中抽离,经主体改造成为了自己文艺理念的一部分。故颜延之谓之“万流可一”,当书籍理论经自己吸收理解后,所有自己曾吸收的精要都已转化为自己文艺理论的有机组成部分,就有了连贯性与系统性。当自我澄明“心性”加之后来萃取的文艺精华融会贯通,合而为一后,主体的文学批评思想即得以形成。
“贵德有恒,心性勿移”的文学批评思想的另一重要内涵则是,应坚持贯彻自己的文学批评观念,不应受外界潮流的影响,扭曲乃至背离自我的文学批评初心。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有一个十分重要的思想原则:“修辞立其诚。”此“诚”的一个核心要素便是要敢于在文学作品中展示自我的真实文学思想,这一点在文学批评领域亦是关键的一点要素。评论主体在以“心性”为镜,建立自己的评论思想之后,倘若不敢坚持自己的正确原则,为外界影响所左右,那么一切便都是徒劳的。颜延之在《庭诰》中特别强调文学批评的理论自信,是由历史经验中所总结出的客观真理性认识。正确的理念尽管具备极高的思想价值,但要为人所理解与接收却是一个复杂和艰难的过程。老子对圣人“被褐而怀玉”的形象化比喻,极为精深地言明了思想传播与接受过程的艰辛。而愈是自我独立论断与社会主观思想相左,就愈是难以在众人庸俗的观念中立足。那么,是否敢于坚持自己的真理性认识,变成了文学批评思想传递过程的关键一环。刘勰在《文心雕龙·知音》篇卷首便发论曰:“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11]218
刘勰点明了文艺批评过程中主体认知与社会认知的矛盾,“知音难觅”亦成为了后世文论学者的普遍共识。而解决批评主体认知与社会思想潮流矛盾的关键,一方面是要努力完善文学批评的思想方法,将谬误控制在真理的范畴内;另一方面则要求文学批评者要敢于坚持自己的理念和推理判断,不违背自己文学思想的初心。只要不违背客观真理,掺杂个人功利性目的,那么批评主体的观点认识必将得到历史的公允评判。
四、“本之自性”的“心性”文学创作论
以“心性”思想为本,颜延之在《庭诰》中亦构筑了其独具一格的“心性”文学创作理论。在文学创作理论方面,颜延之从创作者的“自性”观念入手,着重分析了个体情性与作品风格的关系,提出了“本之自性”的文学创作理念。
诚如前文论述,“心”作为人感知外物的重要器官,是情感产生与性情所在的灵台,故与文学抒写有着不可割裂的联系。研析颜延之《庭诰》的文学创作理论,首先要剖析的便是“情”与创作的关系。从文学发展的大趋势上看,由两汉至魏晋,人们对作品评判的标准产生了由“志”向“情”的过渡发展,尤其是对诗学而言。在汉代《诗大序》中,汉儒便提出了“诗言志”的主张,旗帜鲜明地指出诗之精髓乃在作者合乎儒家伦理的志向表达,从而将诗歌乃至于文学都变成了教化的工具与儒学的附庸。而至魏晋之世,随着儒家正统思想的土崩瓦解,士人们纷纷投入道家思想的怀抱,尤其是在文学中更多地去抒心写性,直抒胸臆,重返向道家返璞归真的文学追求。在陆机的《文赋》中,其已提出“诗言情而绮迷,赋体物而浏亮”。至此“诗言情”的文学创作主张便正式确立。尽管在南朝文坛中,儒道文学思想一直处于交织状态,但通过对《庭诰》的分析,可以发现颜延之对诗以言情主张的赞同。如其言曰:
咏歌之书,取其连类合章,比物集句,采风谣以达民志,《诗》为之祖,裒贬之书,取其正言晦义,转制衰王,微辞岂旨。[1]57
颜延之首先肯定了诗歌之本为民谣歌曲,是普通百姓最为真挚的情感抒发。其实这一点在《诗大序》中也有阐述,但毛诗说肯定的“情”,乃是合乎儒家思想的礼教规范,而不是“情”本初所指的真性情。这种解释不仅使得“情”的内涵变得十分狭窄,而且从某种程度上曲解了“情”的本义,从而使“情”与真性相背离,进而与儒教伦理纲常混为一谈。
颜延之指出,情志之所以在汉儒的训诂下大变味道,乃是由其“取其正言晦义”以褒贬成辞造成的。颜延之在分析李陵诗后,虽认为其为假托之作,但因其悲怆的书写与真挚的情感抒发,所以可以无视其作者与时代的错误,当作优秀的文学作品来欣赏。故其在《庭诰》中提出:“逮李陵众作,总杂不类,元是假托,非尽陵制。至其善写,有足悲者。”[1]57从颜延之对《诗经》的分析与“李陵诗”的评判上可以推断,他所认可的情志乃与儒家理论教化思想有别,而更贴近于道家真性的观念。
可以发现,颜延之“心性”文学创作思想的核心便是创作者应“本之自性”,以自身真实情感出发而进行文学抒写。这一点也成为了后世道教文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唐代道教诗学思想作品《二十四诗品》中便有“性情”为本的创作思想。其言曰:
性情所至,妙不自寻。遇之自天,冷然希音。[15]65
惟性所宅,真取不羁。控物自富,与率为期。[15]176
无论诗歌还是文章,唯有寄托了真性情才能达到浑然天成的艺术境界,这其中所蕴含的是作者情感的自然状态,摆脱了一切外物羁绊,这是道教文学思想所秉承的至臻追求。在确定了“本之自性”的文学创作基调后,颜延之深入探索了性情与创作的关系,提出了如下观点:
(一)息欲明性——“欲”的克制与恬淡文风
情由心中所发,由外物所感而产生喜怒哀乐,但倘若不加以克制,便会由情中生欲而破坏人情感系统的平衡。《庭诰》有曰:“欲者,性之烦浊,气之蒿蒸,故其为害,则熏心智,耗真情,伤人和,犯天性。”[1]55当个体情感涌动超过一定限度,“欲”便会从中产生并左右人的心识,使人神思迷乱,心性有碍。因此“欲”的产生对人的心性修养及文学创作都是十分不利的。那么,适时的克制情欲就十分必要了。对欲望的克制早在老子时代便为重要的探讨课题,《老子》有曰:“不见可欲,使心不乱。”《老子想尔注》释曰:
不欲视之,比如不见,忽令心动。若动自诫,道去复还,心乱遂之,道去之矣。[2]47
张道陵认为心不动则万物皆不动,万物不动则欲当自清,心能自定。颜延之撰《庭诰》之主旨便在于以心性修养劝诫子孙守道惜福,故而对制欲息情之道十分重视。但与张道陵不同的是,他认为欲乃是由人之性情所发之产物,不可与人的性情简单地二元对立,而应看到其关联性。颜延之举出了“火含烟而烟妨火,桂怀蠹而蠹残桂”[1]55的例子以说明“欲”与“本性”的关系。“欲”发之于性,两者本为双生异体,所以简单地摒弃情欲反而会走向另一个极端,即抛弃个体感情因素而使精神麻木,丧失了主观能动性。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则是会使作品感情枯涩,失去感染读者的活力,这样无疑走上了与儒家伦理教条思想一样封闭僵化的老路,是十分不可取的。
正是基于此种认识,颜延之在《老子想尔注》的息欲明性思想上进行了发展。《老子想尔注》有云:
情欲思虑,怒喜恶事;道不所欲,心欲规之,便即制止解散,令如冰见曰散汋。[2]137
颜延之在《庭浩》中则作出不同的论述:
喜怒者有性所不能无,常起於褊量,而止於弘识。然喜过则不重,怒过则不威,能以恬漠为体,宽愉为器者,则为美矣。[1]56
虽然二者最终都回归到以道制妄欲,心定情性的主旨中去,但颜延之却将情欲看作是不可分割的整体,以中和之法来使情归于平静,从而使欲望自行消解,在欲望得以克制之后,个体心性便自然会趋于纯粹,而达到“恬淡宽愉”的心境。汤用彤在论述情与欲之关系时,也提出了调和二者的观点:
情制性则人为情之奴隶而放其心,日流于邪僻。性制情,则感物而动,动不违礼,故行为一归于正,《易•乾卦》之言“利贞者性情也”。[16]78
在颜延之看来,“恬淡宽愉”乃是个体摆脱欲望枷锁后获得的绝佳内心体验,此心境反映在文学创作中,则内化为作品寄旨遥深,情味难求的风格特征。作品的这种风味是超越言辞修饰与形象描写的更高层次的艺术风格特征,往往需要鉴赏者在形成对作品的整体性认识后方能逐渐领悟,作品语言往往是不能直接传达的,正所谓意在言外。魏晋诗作中常见此种意远情深、高旷超然的作品,这些作品通常便有着“言不尽意”的结尾。如嵇康“嘉彼钓翁,得鱼忘筌。郢人逝矣,谁与尽言?”[17]60;阮籍“求仁自得仁,岂复叹咨嗟”[17]65“谁言不可见,青鸟明我心”[16]79“烈烈褒败辞,老氏用长叹”[17]81;陶渊明“此中有真意,欲辩已忘言”[17]258;谢灵运“寄言摄生客,试用此道推”[17]149。其实单以作品文意去理解,很难去把握其主旨,辟如谢灵运此诗通篇绘景,并未言其道如何,阮籍咏怀诗句也并未明言其志,诗评家故有“嵇志清峻,阮旨遥深”[18]156之断语。
对魏晋这些带有道家思想色彩作品理解时,需着重把握的乃是其体道顺物、神通自然的心性体验,而不能仅聚焦于其内心之痛苦。如阮籍咏怀诸作,很多作品都有一个“内心痛苦——自我斗争——超脱升华”的情感发展过程,从心理学来讲,乃是一个自我向本我、超我升华的经历体验。作者在现实中苦闷、压抑,借道家自然清静之道修炼心性,终至达到“天心顺物”的恬淡宽愉境界,而使自我在心性上涅槃新生,重返自由。
钟嵘《诗品》尝言颜延之评阮籍诗作时“怯言其志”[18]190。颜氏不言阮诗之志并非由于其不理解诗作,乃在于颜氏认为阮籍作为体道者,其创作早已超脱于尘俗痛苦之外,其诗作中心与天通的恬漠诗意已非人言可描述。《庭诰》有曰:“日省吾躬,月料吾志,宽嘿以居,洁静以期,神道必在,何恤人言。”[1]55此段文字正述此意。当个体以清虚自然之道炼养心性,则其心对外界必定抱有宽容平和的态度,这种平静安顺的心态落笔则化为愉淡宽愉的文学情感。道教于情倡导“至诚”,于自然之认识倡导“至真”,恬淡的文学境界正是“至诚”“至真”的内外整合,颇如内心波澜皆无,镜照如水,则所映照之世界也必澄明无伪,方此时,心境与自然方可若合一契。
颜延之以辩证的眼光来分析情欲的问题,既正视了文学书写中“情”的重要意义,又在对欲望的处理上采取了疏导中和的方法,这是其文学创作理论的一大进步。“制情息欲”并非是要泯灭人的感情,而是要用心性制情欲,不使喜怒哀乐凌驾于人的理性之上。魏晋南北朝玄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便是圣人“有情”“无情”的论争,王弼秉持着“圣人有情论”的观点对人的情感问题作出了精妙论述:
圣人茂于人者神明也,同于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体冲和以通无;五情同,故不能无哀乐以应物。然则圣人之情,应物而无累于物者也。今以其无累,便谓不复应物,失之多矣。[19]450
从《庭诰》的文本中不难发现,颜延之对王弼的思想观点高度赞同,其对个体认知的最高评判也在于其是否能够“体神”,这亦是对王弼“圣人有情论”的一种阐述。故颜延之在肯定“情”的立场上,提出以性制欲,而不是扼杀个体情感,正是与王弼的观点一脉相承。
(二)“大道至简”的文学风格追求
道家朴拙至简的文学风格渊源久远,早在先秦时代,老子就对“大道至简”的命题多次申述,如《老子》有曰:“多言数穷,不如守中。”[13]100“信言不美,美言不信,辩者不善,善者不辩。”[13]149这一文学风格为道教所继承,并不断对其理论予以发展。如南宋郝大通便对道教朴拙文风作出论述:
夫至人达观,物无不可,故辞旨所发,务以明理为宗。非必骈四骊六,抽青配白,如世之业文者,以声律意度相夸耳。在禅学则曰:粗言及细语,皆成第一义。在孔门则曰:辞达而已矣。又曰:以意逆志,为得之矣。学者不志於道,而惟华采是求,岂为道日损,损之又损之道乎。[20]867
郝大通以三教圆融、万法一同的高度将简朴文风推上了至高的位置,在此文学立场上,道教文学观念几乎未曾发生过改变。在道教思想意蕴深厚的《庭诰》中,大道至简的文学观念体现得亦淋漓尽致。虽然《庭诰》的简朴文学风格思想只是道教文学思想史上微小的一环,但依然有必要对其思想的生成与发展及对前代文学思想的接受过程展开分析。
南朝文风以繁缛、绮丽华美著称,而其浮华空洞的缺点也常为人所诟病。延颜之自己的创作亦未能免俗,但其文学创作思想是否与其创作风格相一致,则值得探讨。《诗品》尝云:
汤惠休曰,谢诗如芙蓉出水,颜诗如错彩镂金。颜终身病之。[18]120
颜延之对汤惠休的评价终生耿耿于怀,可见对自身文学作品风格并不认同,及至反感。这种创作风格与文学思想的巨大差异,侧面反映出了时代大环境所造就的文学潮流与创作主体思想之间的矛盾。对于道教文学思想对南朝文坛的影响程度这一问题,还需要更多地研究探讨,但至少在颜延之个例上来看,其作品难以直观地传达其对文学创作思想的认知,故借助其思想文献来进行阐释便十分必要,《庭诰》的价值就在此处凸显。
通过对《庭诰》的文本分析,可以发现颜延之极为反对浮华思想,无论是在生活起居、文辞字令、思想修为上,他都极力主张“至简”。如其有曰:“浮华怪饰,灭质之具,奇服丽食,弃素之方。动人劝慕,倾人顾盼,可以远识夺,难用近欲从。”[1]56在颜延之看来,物欲对人心性的破坏作用是巨大的,它会致人品行堕落,道德沦丧。生活的奢华导致思想精神极度空虚,从而追求种种虚名,致使真性污秽不堪。从颜延之心性文学思想上来看,心是文学创作的源头,源不净则流必污,不健康文风的产生是必然结果。《庭诰》有云:“及诡者为之,则藉发落,狎菁华,傍荣声,谋利论,此其甚诬。”[1]56作家一旦为外界名利虚荣所束缚,则其文学创作必然失去真率之性,沦为谋取利益的工具,这种作品的危害性极大。
汉代道教曾对华美空洞的文风展开了严厉抨击,《老子想尔注》有云:“道绝不行,耶文滋起,货赂为生,民竟贪学之。身随危倾,当禁之。勿知耶文,勿贪宝货,国则易治。”[2]230可见就道教文艺思想来看,浮华糜丽的作品与声色犬马之欲望享受一样背德害道,不仅会使人心性迷乱,而且当这种不良之风形成之后,会加速社会的腐化堕落速度,导致国家的衰亡,这与亡国之音并无二致。
纵观颜延之所生活的南朝时代,绮丽之风与奢靡之风一直充斥文坛,文人竞相习仿,甚至形成了专门描述女性与艳情的宫体诗歌。这从一个侧面表现出社会的畸形病态,是人道德感与责任感日渐缺失的一个缩影。文学反映出社会意识演进流变的过程,而这一趋势的背后正是人们心灵的真实状况。道教文学思想中所倡导的以简为美,正是在愈演愈烈的繁缛绮丽文风下的一股反抗力量,但这一力量终究是过于孱弱,文士在吸收道教文艺中的超脱与逍遥后,始终对其率真的文艺诉求置若罔闻。颜延之虽然注意到了这一问题,但其创作中却未能有意识地加以实践,以至出现了作品风格与思想理念相左的情况。如果不能对其文学思想全方位加以剖析,则很容易出现认识误区,这是应为文学思想研究者所注意的情况。
颜延之在《庭诰》中反复提到“简”的概念,其概念并非仅指简其嗜欲,更关键的是要使心性归真,正谓之“简以养德”。《庭诰》有云:
岂若拒不其容而简其事,静其气而远其意,使言必诤厌,宾友清耳,笑不倾耳,左右悦目。[1]56
此段文字所谓之“简”,正是讲清静养心,究其旨意,最终回归于“心性”的范畴。颜延之对文风尚简的创作理论的创见在于,其对文风诞生源头开始展开探究,所谓正本清源,方可使文从字顺。即创作者心存正性,则作品风格亦会在潜移默化中产生变化。《庭诰》曰:
酒酌之设,可乐而不可嗜,嗜而非病者希,病而遂眚者几。既眚既病,将蔑其正。若存其正性,纾其妄发,其唯善戒乎。声乐之会,可简而不可违,违而不背者鲜矣,背而非弊者反矣,既弊既背,将受其毁。必能通其碍而节其流,意可为和中矣。[1]56
此段文字所论虽为酒酌之事,但其意理极深,可通文道。酒色之欲,历来为道教摄生者所禁,原因就在于其伤性者甚,但颜延之提出“正性”可使个体免于耽乐,正与佛教“红尘之中悟菩提”意同。反映在文艺思想中则是当创作者心性简朴归真之时,其文字亦将归于拙朴,而心性朴素则文风自归于简。《老子想尔注》曰:“朴,道本气也。人行道归朴,与道合。”[2]98道教所云之道与儒家之道有所不同,它不仅体现在伦理人情,更体现在万物运行之规律方面,道教之所以认为朴与道合,就在于“朴”是养性全身的根本方法。那么文风之中的“朴”,便是摒弃淫思奇巧,回归于真实的艺术境界。文学之“朴”,不是仅仅精简文辞所能达到的,它需要创作者的心性修为也要归于臻真之境。《庭诰》有云:
故性明者欲简,嗜繁者气昏,去明即昏,难以生矣。建言所黜,儒道众智,发论是除。[1]56
此处所言之“气”,乃是道教与儒家所谓的先天元气。但就文学而言,则是指的“文气”。“文气”是相当早的一个文学概念,儒道都对其有所阐释。《礼记·乐记》有云:“诗、乐、舞三者本于心,然后乐器从之,是故情深而文明,气盛而化神。”[21]432道教《太平经》亦有云:“天上诸神言,好行道者,天地道气出助之;……行文者,天与文气助之;行辩者,亦辩气助之;……”[8]238
可知颜延之所谓之“儒道众智”,正是文道与心志关系的阐释。而行文之气,毫无疑问也正是由心之所发,故简明心性,正是扭转文气的最根本途径。而“大道至简”的文学风格,也是与心性相统一的整体性概念,当创作者以“朴”为心性之统摄时,文气也自当向“情深而文明”的方向去发展。
[1] 沈约.宋书:颜延之传[M].北京:中华书局,1985.
[2] 饶宗颐,译注.老子想尔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3] 卿希泰.中国道教思想史: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4] 张融.门论:大正藏第52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5] 冯友兰.中国哲学史:卷下[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9.
[6] 孙通海,译注.庄子[M].北京:中华书局,2018.
[7] 僧肇.般若无知论:大正藏第45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5.
[8] 王明,译注.太平经合校[M].北京:中华书局,1960.
[9] 佚名.西升经:道藏第11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10] 戴明扬,校注.嵇康集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5.
[11] 王志彬,译注.文心雕龙[M].北京:中华书局,2018.
[12] 李定生,徐慧君,译注.文子校释[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
[13] 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55.
[14] 饶尚宽,译注.老子译注[M].北京:中华书局,2006.
[15] 司空图.二十四诗品[M].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2013.
[16] 汤用彤.魏晋玄学论稿[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
[17] 逯钦立,辑校.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北京:中华书局,1983.
[18] 曹旭,集注.诗品集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9] 裴松之,校注.三国志注:魏志钟会传[M].长沙:岳麓书社,2017.
[20] 郝大通.太古集:序道藏第25册[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8.
[21] 王文锦,译注.礼记译解[M].北京:中华书局,2016.
Yan Yanzhi'sand Taoist Literary Thought in Han and Wei Dynasty:With Literary Thought of Mind as the Core
XU Dongzhe1, JIANG Zhenhua2
( 1.School of Marxism, Shandong Polytechnic College, Ji’ning 272067, Shandong, China;2.College of Liberal Arts,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
The view that Confucianism and Buddhism are the source of Yan Yanzhi's thought is the consensus of scholars, but the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Taoism on Yan Yanzhi's thought has been ignored. Apart from the traditional influence theory of Confucianism, this essay analyzes Yan Yanzhi's literary concept from Taoism. Through the analysis of the, and the comparison with the classic Taoist literaturein the late Han Dynasty, this essay proves that the literary thought of mind inis formed by Yan Yanzhi when he inherits and develops of the Taoist literary thought of Han and Wei. His literary epistemology that unifies the cultivation of mind and literary accomplishment, the literary creation theory of "self-nature" and the literary criticism of "the heart shines like a mirror". He advocates that the stylistic is indifferent, concise and profound. They form a unique literary theory system based on Han and Wei Taoism.
literary thought of mind, metaphysics, prajna, Taoism
I206.2
A
1673-9639 (2020) 05-0023-14
2020-07-02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历代道经集部集成编纂与研究(17ZDA248)”。
徐东哲(1990-),男,山东济宁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魏晋南北朝文学。
蒋振华(1964-),男,湖南新邵人,文学博士,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中国古代文学思想。
(责任编辑 郭玲珍)(责任校对 肖 峰)(英文编辑 田兴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