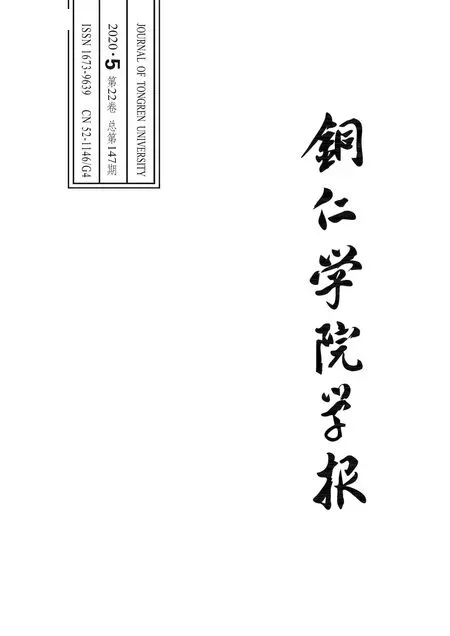疾病信仰与治疗仪式:黔江苗族疾病的医学人类学考察
向青松,孙 阳
疾病信仰与治疗仪式:黔江苗族疾病的医学人类学考察
向青松1,孙 阳2
(1.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2.湖南师范大学 历史文化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1 )
早期的苗族医药治疗有一种说法“巫医一家,神药两解”,苗医被赋予了“巫术师”和“医疗师”的双重身份,因而自古以来在苗族文化和苗族社会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位于武陵山区的黔江苗族中的苗医至今也具有“巫医一体”的特质。基于人类学的视角,探讨黔江苗族的疾病信仰与治疗仪式,深度剖析作为疾病治疗主体的“苗医”的身份象征与神秘性,最终形成对地方民族文化的认知,以此加深对民族文化异质性的认识。
苗族; 治疗仪式; 原始信仰; 医学人类学
一、问题的提出
在古代中国,医学技术并没有像现代医学这样发达,古人们更多地把疾病治疗与民间信仰、宗教观等结合起来,在特殊意识形态的指导下进行种种文化实践仪式。现代的乡村社会中,受自然条件与社会条件的影响,特别是地方民族文化的特殊性影响,依旧沿用祖辈遗存的疾病传统治疗方式。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来关注对于疾病的认知和治疗方式,一直是人文社科研究所关注的焦点,如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就特邀清华大学景军在2019年11月开展了“人文社科”第一期的工作坊,围绕公民健康、乡村疾病与医疗以及医学伦理等方面展开了一系列的探讨,随后又邀请国内外诸多学者开展了多期工作坊,并由此培养了一批专业人才,也加深了学者们对医学人类学的探讨。老一辈人类学家中,许烺光先生根据在云南发生的霍乱,以个案的方式进行分析,并结合香港的鼠疫进行对比探讨[1]。目前诸多学者关注少数民族地区乡村的少数民族疾病与治疗方式,在独特的灵魂观念支配下,哈尼族社会中保存着各种各样名目繁多的治疗仪式,徐义强从医学人类的视角对哈尼族的叫魂治疗仪式进行了探讨,指出哈尼人对疾病、死亡和健康的看法与其灵魂观、身体观密切相连。仪式治疗的疗效与选择又与其地方文化知识体系和外部社会因素息息相关。因此,只有将叫魂仪式置于哈尼族丰富的社会文化脉络中进行动态分析,我们才能发现哈尼族疾病与治疗实践的行动逻辑,得以了解传统的仪式治疗是如何起到维系当地社会运转的重要功能[2]。潘天舒在田野实地考察、深度访谈和挖掘历史记忆的基础上,通过对2005年浙江海宁地区从各级政府和防疫部门到普通民众应对禽流感威胁的策略和措施的分析,揭示了在危机过程中得以充分激发的“集体生存意识”,是如何促使传统“调适性智慧”与现代流行防疫知识的有机结合,并融入了抗击流行性瘟疫的现代实践中[3]。赵巧艳对侗族传统社会的主体医疗方式之一“收惊疗法”进行了考察,这一传统的宗教巫术性治疗术仍然在侗族乡村生活中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这一疗法与其侗族的灵魂信仰存在密切的联系,灵魂崇拜与安魂仪式在这一疗法中得以深深展演[4]。巴莫阿依指出,凉山彝族的疾病认知与其传统信仰密切相关,初步认为在彝族信仰中疾病具有七类超自然的病源,分析了彝族仪式疗者的类型及其特点;在历史进程中,凉山彝族形成了集灵魂信仰、祖先崇拜、鬼神信仰、灵物崇拜为一体的信仰模式,祭祀、巫术、占卜、禁忌为其活动内容的原生宗教信仰,这些信仰影响着彝族人对疾病的认识与实践,仪式医疗是彝族传统医疗实践的重要组成部分[5]。嘉日姆几指出彝族人临终关怀的实践来源于自身的文化土壤,从彝族人生死观以及从占卜、察言观色以及医院诊断的方式来界定临终状态等方面来分析彝族人的临终关怀行为,借助宗教仪式来实现对临终者及其家属心理支持[6]。看本加、林开强对丝路文化视野中的藏族护身符进行了研究,主要探讨了护身符所体现的对疾病的认知和治疗观念,并力图揭示藏族人的世界观、价值观和审美观,以及宗教信仰和身体之间的紧密关系[7]。医学人类学视野中的疾病治疗,根植于特定的社会文化背景,是一种综合性的应对疾病的过程。杨跃熊从医学人类学的角度对大理居民所患荨麻疹进行了分析,大理居民将荨麻疹的病因归因于游魂“姑悲惹”附身,并因此进行了一系列的仪式操作,然而在这些仪式治疗的背后展现了白族的生死观、空间观以及宗教观,而“姑悲惹”治疗仪式的背后更是展现了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之间的紧密关系[8]。罗钰坊以兴安村土家族的过关仪式为个案,从医学人类学与象征人类学的视野,分析了兴安村过关仪式请神上香、执符念降和断卦、过关解煞、送茅船四个过程与内在的实践逻辑,在共同文化形塑的疾病解释模式下病人及其家属在巫师构建的想象空间中的思想情感体悟以及仪式参与者对病痛治疗的共同参与来分担患者的病痛,最终使得患者和家属获得心理慰藉,同时构建新的社会关系[9]。不同的民族有其不同的文化背景,其疾病治疗仪式也各有差异,但都在这个特定的族群场域内发挥着特殊的作用。
不同的民族对于疾病的诊断和治疗都有自身的一套治疗方法,与地方本土滋养起来的本土知识结合,形成了关于疾病的地方性知识,并以此来认知和诠释疾病。目前学术界对于民间疾病传统治疗仪式逐渐予以更多的关注,而民间历史悠久的传统治疗方式也被当地人所认可。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主要有几点:第一,民间对于疾病的传统治疗方式由来已久,在地方文化中根深蒂固,深刻地影响着当地人的思维方式和行为实践;第二,现代医疗资源的分布不均,东部与中西部、城市与农村之间存在严重的资源不均;第三,现代医疗技术的发展,其医疗费用过高以及人们对于现代医学的观念存在一定的认知缺失。
黔江,《禹贡》为梁州之城;商周为巴国地;秦属巴郡;汉初,为涪陵县地。清光绪《黔江县志》:“黔江,邑邻五溪,界古黔州及施州,为川楚僻路,天下有事,易扰难靖。”[10]43这里,与彭水、酉阳、秀山等地联片,史称“蛮夷之地”。黔江现今位于重庆市东南边缘,巫山山脉与大娄山山脉结合部,武陵山腹地,东北、北与湖北省咸丰、利川市交界,西与彭水苗族土家族自治县相邻,东南、南与酉阳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毗连,地处渝鄂咽喉之所。境内属于亚热带湿润性季风气候,气候温和,四季分明;为山地地形,崎岖不平;农作物方面,以种植玉米、红薯、土豆等为主;在河谷地区,依据河流优势,多种植水稻,一年一季[11]。境内的居民来源甚广,主要有土著世居、巴人遗裔、以及移民迁徙、避难落籍、募民垦荒等方式迁移至此,多为苗族、土家族,小部分为汉族[10]583。黔江是重庆市主要的少数民族聚居地之一,是重庆市唯一的一个由土家族、苗族为主的少数民族自治县改设的少数民族区,黔江各民族的历史文化悠久,其苗族、土家族的婚礼、葬礼都有着浓郁的民族特色。[12]民居建筑为杆栏式建筑,有较为传统的吊脚楼、木制瓦房,也有较为现代的砖瓦房,当地的苗族、土家族大多生活在偏远的乡村。黔江处于武陵山区,偏远乡村交通不便,资源较为缺乏,因而在诸多乡村地区还采用传统的疾病治疗方式,而这些传统的治疗方式与当地的苗族文化密不可分。综上所述,一方面,目前学术界还没有对黔江苗族地区进行过疾病信仰与治疗仪式方面的研究,特别是缺乏从医学人类学的视角进行研究,这将是对该田野点研究上的一个创新。另一方面,对于民间苗族疾病传统治疗方式的关注,能够更好地了解苗族传统医疗体系,以及其中所蕴涵的地方民族文化特质,加深对民族文化异质性的认知。
二、民间疾病信仰
黔江苗族人对生与死有着独特的看法,其独特的看法的形成一方面是受当地民族传统文化的影响,另一方面是当地落后的条件所致。当有孩子出生的时候,被认为是一个新的生命的诞生,为此要举行隆重的仪式。按照当地传统的规矩,孩子出生十天后,就要举办一场宴席,名为“送饭”(为当地方言,主要是为了庆祝新生儿的到来和母子平安),主人家就会通知周围的邻居以及三亲六戚,庆祝新生儿的到来。在孩子生下来的三十天之内,产妇和孩子都不能出门,只能呆在家里,这被认为是对孩子和母亲的一种保护。而且对于饮食有着独特的选择,一般都是以肉类为主,蔬菜则少吃。一个月内不能出门的禁忌和饮食选择的背后,展现了当地苗族人的一种原始民间信仰,即在孩子生下来这段时间,母亲和孩子的身体是极其虚弱的,而新生命的到来也意味着灵魂投胎转世的新生,但世间也还有一些游魂的存在,此时很容易依附于体质偏弱的新生儿和产妇身体,为了避免游魂作怪,所以孩子和母亲在一个月内不能跨出家屋大门,因为家屋内有供奉的祖先在庇佑;而饮食的偏好选择也是为了增强体质,避免不好事物的沾身。其“送饭”仪式的社会结构,一方面是为了让当地的苗族人共沾新生的喜气,实现苗族族群的延续;另一方面,苗族亲邻在“送饭”这一天共同聚集到主人家,使得亲属关系网络再次紧密联结,通过给孩子“认亲”(是给新生儿认一个或多个干爹干妈,使得孩子在干爹干妈的庇护下得以健康成长)仪式使得新的拟亲属得以出现,实现了家庭与家庭间社会关系的再造。当人感觉到要离世之际,当然这里所说的“离世”主要是指自然死亡的人,多为老死之人。家人会聚集到一起,给将要离世之人准备一些好吃的食物,整个过程并没有太多悲伤情境。对于当地苗族人而言,生老病死是自然的选择,并不可强求。而在人去世之后,家中会举办隆重的葬礼来为逝者送行,并且也会为逝者寻找一块风水宝地,之后由“亡人”身份转换为“祖先”身份。事实上,葬礼作为“生者”向“逝者”的一种过渡,表达了对于逝者的认可和尊重,逝者最终会被纳入进祖先的牌位坊之中,能够被后人所祭祀和供奉,这在当地苗族人看来是一种功德和孝文化的展演。
早期的苗族医药治疗有一种说法“巫医一家,神药两解”,意思就是苗族人把巫术和医药治疗从二元对立转换成一元结合,最终发挥出其独特的功效。当然这是把原始的宗教信仰与疾病治疗结合起来。当疾病来临,黔江乡村的苗族人首先选择不是去医院寻求治疗,而是去找当地的苗医寻求帮助,传统的苗医在疾病治疗仪式过程中不会使用现代医学手段和技术,只是用一些在山上采集的草药进行辅助治疗,这就是民间一直流传的“千年苗医、万年苗药”。同时乡村社会中的苗医往往还具有一种民间“仪式”执行者的身份,通过一系列特殊的巫术仪式来找出隐性存在的“病源体”,在诸多仪式实践过程中,苗医的身份逐渐附带了“巫术师”的身份。疾病治疗不仅仅依赖于药物的治疗,同时也通过当地的民间巫术信仰来诊断和治疗,最终形成了“巫医一体”的身份和治疗方式。
凌纯声、芮逸夫在《湘西苗族调查报告》中指出,苗族人现在还保存的巫术有两种:一种是“化水”,是一种白巫术,其作用是治病救人;另外一种是黑巫术,其作用是害人生病,比如放蛊[13]。由此可见,他们二人将苗族医药归入为巫术的范畴,认为巫术是一种实用性的技术。在黔江当地,苗医的身份也与凌、芮二人的描述近乎一致。但在田野调查中发现,苗医承载着“巫术师”身份的背后,是与当地苗族的原始宗教信仰有着深刻的关联。当地的苗族人一直有着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等原始信仰,每次遇到重大灾难或者患病等都会先祈求祖先的庇佑,并在祖先的庇佑下得到治愈。逢年过节以及重大节日或者仪式时,当地的苗人都会带上猪头肉、白酒、香烛以及火纸(冥币)等敬献祖先神灵,在自家的家屋旁边也会点一些香烛和火纸,其目的在于敬献游离在家屋周围的游魂,以防家人受到伤害。当地的苗族人相信家中所遇到的灾祸,都是祖先需要后人尽孝的暗示以及世间各种游魂在作祟,故意在一些地方埋下祸根。所以,当地苗族人一直延续并信仰着这种原始的祖灵崇拜。这和许烺光在《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一书中描述的喜洲当地人有着类似的情景,喜洲人极度崇拜祖先和各种神灵,遇到好的或者不好的事情时,人们都会积极地祭拜祖先,当地人认为他们自己所经历的和所获得的东西都是在祖先的庇佑下才得以成功,并且祖先和各类神灵是不可侵犯的,必须要及时地进行各种献祭[14]。一旦对祖先不虔诚和不尽孝,那么这类人将处于祖先庇护的边缘,成为危险的边缘人。
三、疾病治疗仪式
在当地苗族人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的原始宗教信仰下,人们的各种行为实践也紧紧围绕着这个中心而进行。下面以一个疾病治疗的实例来看待当地苗族人的信仰与疾病治疗之间的关系。这一个例子是笔者在2019年田野调查时所获取的资料。笔者在村子中发现一家人在做“仪式”,据了解,这家人中有一位少年不幸得了一场大病,而从当地苗族人的思想观念和文化背景出发,一旦患病其首要选择就是寻求当地苗医的帮助,当时与这位少年交谈得知他一直处于头疼的患病状态,总感觉头隐隐作痛。于是,他的家人便去请了一位苗医过来看病,苗医观看了他的身体状况后,又围绕家屋环视了几圈,苗医最终下了一个结论,即家中的一祖坟旁边有两块石头压着。随后,笔者跟随他们家人去看了那座坟,旁边确实有两块石头因下雨从坡上掉落下来。然后在苗医的指导下,把两块石头搬离坟墓,又带来一些香烛、火纸和猪头肉在坟墓前献祭祖先,苗医嘴里也不断的念叨着一些经文话语。同时,这位苗医也给患病的少年备置了一些不同种类的草药,锤成粉末之后放入温水中喝掉。第二天患病少年就给我说他的头疼状态开始得到缓解。然而,几天之后又出现了头疼状态,这时家人觉得去医院检查一下为好,然而在诸多大小医院做了全面检查,甚至住院了几天,最后还是无功而返。而他们又不得不向周边地区的苗医寻求治疗。后来在少年亲戚的介绍下,认识了一位附近村子的苗医。于是,他们就把这位苗医请到家中,也是先检查了患病少年的身体和查看了家屋周边的情况。最终进行了三天的仪式,少年的病得到了痊愈。开始仪式的第一天早上笔者很早就赶到少年家中,发现苗医在家屋的大门前摆了一张小桌子,然后在一张黄纸上画了一道符,用刀轻轻割了一只公鸡的喉咙,滴了三滴血在那道符上,最后把这道符点燃烧为灰烬,放入装有水的碗让少年将其喝掉,举行这个仪式的时候,苗医嘴里也是一直在不断的念叨着,但至于具体念的什么不得而知,仪式完毕,让少年朝着家中祖坟的方向磕了三个头。第二天,苗医带着少年和他的家人去到祖先的坟墓前,苗医一直让患病少年跪在坟墓面前,他则是把提前准备好的各种祭祀物品放在坟墓前,接着他拿出装了一个稻谷和玉米的碗,将其稻谷和玉米撒在坟墓周围并围成一圈,而少年就在这个圈内,撒完从坟墓上采集了一种植物,让少年拿回去熬水喝;最后,让少年朝着家屋的方向又磕了三个头。第三天,苗医带着少年在家屋前面走了三圈,也是边走边撒稻谷和玉米,苗医手里拿着一个类似于经幡之类的东西,边走边念叨。经过三天的仪式治疗之后,少年的头痛症状确实有所减轻,苗医临走之前还留下了一幅类似于“观音抱子”的画卷,让少年的家人一直挂在家屋大堂,并且告诫要连续七天在饭前献祭祖先。经过几天的仪式后,少年的头疼状态有所缓解并最终痊愈。
当时看来,苗医的种种仪式行为在外人看来确实无法理解,甚至被很多人说成了“迷信”。殊不知这种疾病治疗仪式是与当地的苗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在种种仪式背后,均与当地苗族的生活以及精神信仰紧密相连。这些仪式实践所展现出来的是苗族人对于祖先的敬畏以及对于神灵的尊重,是当地苗族人延续着的历史文化和记忆。近年来,笔者仍然见过很多人依旧采取这种传统的治疗方式,有些人在苗医“巫医一体”的治疗下,疾病确实减轻以致最终痊愈。
一般认为,具身性思想萌芽于Lakoff和Johnsen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Lakoff和Johnsen在该著作中开宗明义地指出隐喻在日常生活中无所不在、无处不在,不仅在语言中,而且在思维和行动中处处都有隐喻的踪影,其隐喻的本质是用该事物理解彼事物,用某一认知领域的经验理解另一认知领域的经验,是原始域对目标域的投射[15]。随着人类学的出现,具身性(embodiment)也成为了人类学所关注的一个方面,其意指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差异,都可以通过人们的身体认知、身体观念、身体体验、身体感觉体现出来[16]。张文义从构词角度来探讨了具身性(embodiment)的概念,他认为英语中的body变动词embody时有两个意义:第一,把身体之外的社会放到身上,即身体再现了社会;第二,让身体具有力量。综合起来,embodiment就是社会的东西印到了个体身上,个体把它变成独具特色的东西[17]。
在民族志的研究和表述中,身体的“缺席”不应该再被视为理所当然的事情,所以,我们需要对身体的存在和作用进行反思;具身性就是这样的一个产物:我们对于世界的认识基于在世的存在的,只有以身体作为基本工具,我们才能与世界互动,进而理解;所以人类学必须立足于人们的内在感知,关注具身体验,理解外在的社会文化是以何种方式来完成自我的建构,进而作用于个体日常生活的[18]。黔江苗族人在寻求苗医的治疗过程中,对于患者而言,具身性(embodiment)的展演主要分为三个阶段。其一,家中有人患病,家属会第一时间去帮助患者去请苗医,很大程度上这也是患者的请求,首先就在心理上建构了苗医以及救治的这样一个形象和功用,这时患者就把“主体(自己)”之外的“他者(苗医)”放在了自己身上。其二,在仪式治疗中,苗医和患者的身份状态出现置换,苗医成为了仪式中的主体,而患者成为了“他者”,这时的“他者”在主体的药物和巫术仪式治疗下,身体体验和身体认知逐渐出现反应。具身性展演的最后一个阶段也是最重要的一个阶段,即患者在双重治疗后身体机能逐渐恢复,被认为是在苗医的帮助下得到了祖先的再次庇佑,修复了人与神灵之间的关系,身体的恢复再现了祖先力量的强大。其实,身体的变化被视为一种技术的展演,身体也被视为一个承载族群社会文化的象征体系。
四、人类学视角下的“苗医”
(一)“苗医”的身份象征
苗族医药在苗族社会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不同于现代医学上的西药治疗方式,苗药大多从深山老林或者悬崖峭壁上采集,黔江乡村社会中苗医所使用的苗药多为深林中获取。这些药物较为普通常见。苗医采集多种植物,将其磨成粉末或者切成小块,按照一定的比例调制。这样经过混合调制才能形成最终的药物,而单单一种植物却无法成为治疗疾病的药物。远古时期的苗族先民,对于大自然中自然现象和规律无法理解,如风雨雷电、生老病死等,于是他们对这些现象和运行规律产生了畏惧。当他们依靠自己仅有的常识无法来解释这些事物的时候,他们便把希望寄托在那些具有保护意义的事物上,并对其加以崇拜和信仰,祈求灵物不要将灾难降临在他们身上。这样就把人的属性和自然的属性通过崇拜和信仰的方式结合,于是就产生了苗族崇拜自然物的原始宗教。由于这些自然物所具有的“灵”,所以也把这些自然物当做“神”一样来崇拜和祭祀。后来,由于人群知识的拓展和技术的发展,逐渐转向对以“人”的崇拜和信仰,进而形成了祖先崇拜和灵魂崇拜。
黔江乡村社会中的苗医通过药物和巫术仪式的结合,来治疗人群所患的疾病。药物治疗也有其功效,能够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身体的疼痛,但当地苗族人认为这只是治标的方式,要治疗疾病之本,还是要通过相关仪式进行治疗,最终消除疼痛以及寻求精神上的安定。而巫术仪式的进行所受指导的是当地苗族社会一直以来延续的祖先崇拜、灵魂崇拜意识。其实,在当地苗族社会中,人群并不仅仅在疾病治疗的时候需要寻求苗医的帮助,而在家庭遭遇灾祸之际,也会寻求苗医的帮助,而苗医通过一系列的仪式进行驱灾辟邪,其背后的救治方式多是向祖先的敬献、与灵魂的交触。实际上,苗医是作为活着的人与逝去的祖先之间沟通的桥梁,作为生者与逝者的中间人,具有某种“灵力”的存在。而通过具有“灵力”的苗医举行相关的仪式,其人与祖先的距离在“拉近”,从而在祖先的庇佑下使得疾病得以祛除,患病之人得以回归本位。苗医的身份在现实和仪式中具有了二元性,在现实生活中被当地人视为是拥有某种“灵力”或者超自然能力的人,在举行仪式之际,则成为人与神、祖先之间沟通的桥梁,处于一种“阈限”状态。
(二)“苗医”的神秘性
苗医具有“巫医一体”的色彩,因而也展现出神秘性。苗医的神秘性展演主要分为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当找到苗医去治疗疾病之时,苗医并不是立马就答应施医,做出选择之前,苗医会简单地向家属了解病情。了解有关病情之后,苗医会单独来到自家家屋的香火神龛前,香火神龛主要供奉的是祖先和各路神灵。在香火神龛下,苗医跪下来使用工具进行占卜,通过特定的仪式来查看今天是否适宜出行治病。其实,在整个占卜过程中,苗医也是在寻求祖先的指示,占卜只是一种表面的仪式行为,但具体行医与否还需要得到祖先的明示和庇佑,因此附了神秘色彩。正如许烺光在《祖荫下》一书中,描述大理喜洲人所进行的日常生产和生活都要经过一定的仪式活动,以求得祖先的庇佑[14]。第二,药物配制的神秘性,当地苗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也会使用到一些中草药,根据不同的病症,调制出不同的配方,而这些调制的比例和配方只有苗医自己知晓,从不轻易语示外人。第三,仪式中操作的神秘性,苗医在举行疾病治疗仪式时,患病者及家人要准备好仪式中所用到的物品,如香烛、火纸、鸡、猪头肉等。仪式过程中苗医每到一处会念相关的咒语经文,患者要严格按照苗医的指示行事,整个仪式过程中,任何人也不得以询问苗医此种行事的缘由。苗医在治疗疾病过程中,各种仪式操作烙上了神秘色彩,似乎一旦具有苗医的身份,其治疗实践中便遵循一套身份规则和行医规则,决不可将仪式中任何巫术性的操作教给别人。作为地方文化浓厚的少数民族地区,苗医和详细的治疗方式都作为一种不容侵犯的习惯传统,烙上了神秘的色彩,在苗医看来,这似乎是不可泄露的“天机”,参与仪式的人们也在治疗与被治疗中维持着平衡,防止规则的打破,祈求“巫医一体”的医与灵。
其实,患者优先选择苗医进行医治,不仅是当地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更是一种对于祖先的敬意和信任,认为通过苗医的治疗仪式会重新得到祖先的庇佑。从当地苗族传统文化中的孝文化而言,苗医帮助患者治愈疾病是一种孝文化的表达,这种孝文化的表达有着双重含义。从显性表达来看,对于长辈而言,帮助长辈寻求治疗方式,被认为是在对长辈尽孝,长辈历经辛酸将其后人拉扯长大,实属不易,后人应该在长辈遇到困难时积极伸手帮助;从隐性展演来看,家中有人患病,家属优先寻求苗医的帮助,这被认为是对于已逝祖先的孝意,当地人认为苗医更多地承载了能与祖先交流的身份象征,寻求祖先的帮助说明内心一直把祖先放在一个重要的位置上。以此来展示当地祖先崇拜、灵魂崇拜的疾病信仰。
五、结语
从人类学的视角出发,对黔江当地苗族的疾病治疗体系进行探究,终而得出几点认识:其一,作为疾病治疗主体的“苗医”在黔江当地苗族社会中依旧占据一定地位,当地人患病首要寻求苗医的诊治,传统的苗医治疗方式至今未被湮没;其二,巫医并行,苗医集药物治疗与巫术治疗于一身,同时施行于患者,扮演多重身份;其三,苗族的祖先崇拜、神灵崇拜原始信仰在黔江苗族乡村中仍在延续。传统的苗族医学是与其民间原始信仰结合在一起,黔江苗族乡村社会中的苗医集“巫医一体”,在神圣与世俗的二元共生治疗仪式的这个场域内依旧发挥着作用。药物治疗与仪式控制仍然被当地人认为是一种合理和可被接受的治疗方式。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evi-Strauss)曾说过:“治疗术的本质在于使某一既定的局面首先从情感方面变得能够被想象,使肉体难以忍受的痛苦变得可以被思想所接受”[19]。其实这是一种从情感、思想接受的心理效应。黔江苗族疾病中所施行的“巫医一体”治疗仪式,其实不仅仅是一种对于身体生理上的治疗,更是一种地方族群的社会文化治疗,有利于维持地方族群社会的平衡与发展。不论仪式治疗是否具备生物学意义上的医学功效,在地方性知识系统内仍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1] 许烺光.驱逐捣蛋者[M].台北:南天书局,1997.
[2] 徐义强.哈尼族治疗仪式的医学人类学解读[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2):84-88.
[3] 潘天舒,张乐.流行病瘟疫与集体生存意识:关于海宁地区应对禽流感威胁的文化人类学考察[J].社会,2007(4):34-40.
[4] 赵巧艳.侗族灵魂信仰与收惊疗法——一项关于B村的医学人类学考察[J].思想战线,2014(4):70-75.
[5] 巴莫阿依.凉山彝族的疾病信仰与仪式医疗:上[J].宗教学研究,2003(1):37-40.
[6] 嘉日姆几.试析凉山彝族临终关怀行为实践[J].社会科学,2007(9):124-127.
[7] 看本加,林开强.信仰、符号与疾病治疗——丝路文化视野中的藏族护身符[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7(11):67-70.
[8] 杨跃熊.游魂、空间与荨麻疹——大理白族“姑悲惹”治疗仪式的医学人类学解读[J].湖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8(2):43-45.
[9] 罗钰坊.仪式疗法:土家族过关仪式的医学人类学阐释——以鄂西兴安村为个案[J].贵州民族研究,2018(1):89-92.
[10] 四川省黔江土家族苗族自治县编篆委员会,编.黔江县志[M].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1994.
[11] 何泽禄.黔江地区志[M].重庆:重庆出版社,2006:28.
[12] 向青松.黔江苗族婚俗仪式与亲属实践[J].凯里学院学报,2020(4):58.
[13] 凌纯声,芮逸夫.湘西苗族调查报告[M].北京:民族出版社,2003.
[14] 许烺光.祖荫下:中国乡村的亲属、人格与社会流动[M].台北:南天书局,2001.
[15] George Lakoff,Mark Johnsen.Metaphors We Live By[M].London: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0.
[16] 刘倩.身体的边界性与“去边界化”——基于医学人类学的研究和反思[J].医学与哲学,2017(21):35-38.
[17] 张文义.社会与生物的连接点:医学人类学国际研究动态[J].医学与哲学,2017(19):39-42.
[18] 和少英,姚伟.中医人类学视野下的具身性与多重世界[J].思想战线,2020(2).
[19] 列维•斯特劳斯.结构人类学[M].张祖建,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209.
Disease Belief and Treatment Ceremony: A Medical Anthropological Study on Diseases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jiang
XIANG Qingsong1, SUN Yang2
( 1. Research Center of Border Regions and Minority Nationalities in Southwest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Yunnan, China; 2.College of History and Culture,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1, Hunan, China )
In the early Miao medical treatment, there was a saying that "the witch doctor family, the two medicines", Miao doctor was given the dual identity of the wizard and the medical professional, and thus has played an important role in the Miao culture and the Miao society since ancient times. Miao medicine in Qianjiang of Miao nationality, located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also ha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tegration of witchcraft and medical professional".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anthropology,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isease belief and treatment ceremony of Miao nationality in Qianjiang, deeply analyzes the identity symbol and mystery of Miao medicine as the main body of disease treatment, and finally forms the cognition of local national culture, so as to deepen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cultural heterogeneity.
Miao, treatment ceremony, primitive belief, medical anthropology
C955
A
1673-9639 (2020) 05-0114-08
2020-04-26
向青松(1996-),男,苗族,重庆黔江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民族学,亚太民族研究。
孙 阳(1995-),男,河南安阳人,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代史。
(责任编辑 车越川)(责任校对 黎 帅)(英文编辑 田兴斌)